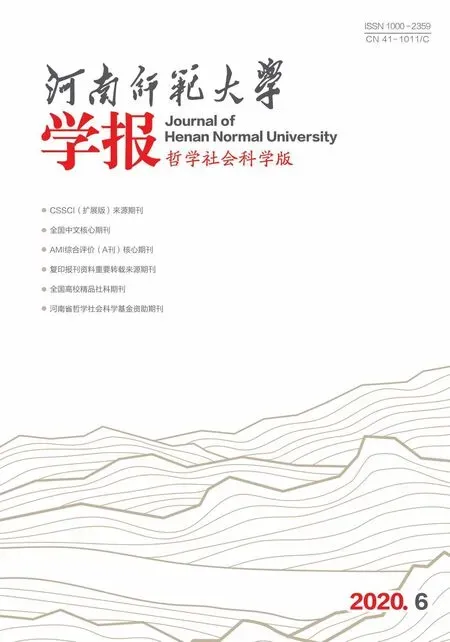中日现当代重彩画创作规律与审美旨趣比较研究
牛金梁
(河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重彩画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萌芽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岩绘艺术。两汉魏晋时期逐渐形成特定的形式和面貌,隋唐五代时期达到鼎盛。宋代以后,随着社公众审美取向的变迁,水墨画逐渐占据画坛主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重彩画一度成为艺术家表现生活的重要艺术形式。20世纪90年代,传统重彩画再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中国重彩画发展渐成蓬勃之势。日本是和我国毗邻的重要的东亚国家,其文化艺术和我国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和关联性。公元6世纪,日本的佛教重彩壁画得到初步发展,20世纪末日本画坛洋风绘画和本土绘画齐头并进,日本的西洋绘画和西方欧美国家的现代艺术紧密联系,诸如印象派、后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抽象主义、达达主义等西方现代流派在日本画坛轮番登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日本画的发展。在材料运用和表现方法上,中日两国的重彩画皆有自身的特点,形成了具有各自独特地域民族文化与审美取向的绘画艺术。
一、风景与山水:感观主义与自我心像的彰显
从历史的角度看,日本的古代绘画无论从题材上、表现形式上都和中国古代绘画十分相似,因为日本古代绘画的根源起始于中国,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母体已是世所公认的事实(1)李淼:《身体叙事中的流动美学——论汉画像中舞蹈图像的审美形态与文化表达》,《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日本的古代山水画和中国的古代山水画几乎雷同,室町时代的周文、雪舟及雪村便是当时的重要代表。
然而,日本画在经历了“脱亚入欧”运动后,已经和中国画渐行渐远。在山川草木风物的表现层面,日本画深受西方风景画的影响。借鉴西画的图式和色彩,用日本传统绘画工具和材料表现自然风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日本画运动时期已初具面貌,如横山大观的《山路》、菱田春草的《落叶》、竹内栖凤的《罗马之图》等作品。这些作品采用类似西方风景画的构图,色彩上用类似西方水彩画的薄画法,注重对光、空气和景物远近虚实的表现,这一时期基本上可以称之为日本画的“洋风化时期”。
这样的表现方式在以后的大正时期(1912—1925)和昭和前期(1926—1945)得到了巩固与发展,逐渐形成日本风景题材绘画的新面貌,如今村紫红的《热国之卷》、村上华岳的《冬晴的山峦》等。20世纪40年代前后,受战争的影响,日本画技法经历了短暂的停滞,但战争的创伤也为日本民众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该时期的画家将对政治和战争的厌倦都宣泄到山水与风景等自然题材之上。
和日本的重彩风景画相比,中国的重彩山水画在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举步维艰。19世纪末,中国和日本都经历了从闭关锁国到逐步开放的过程,随后,日本发起了著名的“明治维新”运动,用短短30年时间一跃成为经济、军事、文化强国。而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也企图通过改革变法兴国强军,但由于保守势力的强大,光绪皇帝倡导的“戊戌变法”不得不在几个月后夭折了,中国从此失去变革发展的重要时期。
20世纪初期,虽然中国也有大批画家出国学习西洋绘画,试图改造中国美术的落后面貌,但由于整体保守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中国美术对西方美术的学习和吸收则极为有限。贾方舟曾言:“中国画家在深厚的传统优势面前难以做到对西方艺术始终如一地专注和投入,更难彻底纳入西欧的体系之中,但日本民族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则要比中国彻底得多。”(2)贾方舟:《中国现代美术理论批评文丛·贾方舟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255页。中国山水画特别是水墨山水画经过了宋元明清千余年的发展,已经完全成熟和高度程式化,中国山水画和西方风景画属于两种文化体系下的不同艺术形式。
中国山水画属于典型的意象艺术,虽然说山水画家也需要面对自然界的山水进行观物摹写、对景写生,但画家在创作时更多时候靠的是“行万里路,观万重山,写万仞峰”后的胸有成竹和吞吐自由。中国山水画在视觉感受上运用散点透视的方法,将“平远、高远、深远”所观之景融于一体,与西画的焦点透视法相去甚远。在颜色的运用上,通常用五墨代替五色,虽也有青绿重彩风格,但这种着色方法也是对大自然色彩的归纳概括和主观心像表达。
在近现代接受西方绘画影响方面,中国山水画变化最小,远没有日本画转变的力度强大和彻底。早期的张大千、林风眠及后来的刘海粟、李可染、吴冠中等在山水画的用色、用光和图式上都有所发展,但中国山水画的大格局尚未改变。中国的现当代山水画在色彩和手法上还是以水墨写意为主,青绿工笔重彩山水画家还是少数。在为数不多的青绿工笔重彩山水画家中,能推陈出新,创造中国山水画新面貌者寥若晨星,较为优秀者如林凡、林容生、许俊、牛克诚等,他们的作品有《碎梦浮春》《四月清影》《西山记游》《倚春溪》等,这些作品多在色彩表现上下功夫,图式经营还是比较传统的。我们不得不说,中国山水画已经进入了历史发展的瓶颈时期,未来的中国山水画之路该何去何从,值得我们中国画界关注和思考!
二、线条与色彩的革命与坚守:中日文化的应变与传承
日本画在“脱亚入欧”运动中曾一度陷入绝境,在冈仓天心的引领下,一大批画家如狩野芳崖、桥本雅邦、横山大观、下村观山、菱田春草、川合玉堂等发起了拯救日本画的新日本画运动。其中,横山大观和菱田春草创造了独特的“朦胧体”画法,掀起了日本画革命的序幕,这场革命的第一枪便是“线”的革命。“为了表现光和空气,横山和菱田以掺有胡粉的颜料涂刷整个画面或作底子,苦心寻求调子的浓淡变化。由于使用了不透明的日本画颜料和墨几度涂刷,画面容易污染,调子微暗朦胧,被大村西崖骂为‘朦胧体’”(3)刘晓路:《20世纪日本美术》,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第33页。。这种弱化线条的表现,在开始时遭到了部分社会名流的诸多非议和责难,但不久很快就受到了其他画家们的重视,成为日本画突围求新的一条路子。
在随后几代画家的不断努力下,日本画越来越重视对色彩的运用,并且越来越往浓抹厚涂的方向迈进,日本画也进入了近现代的全盛时期。不管是“日展三山”的东山魁夷、高山辰雄、杉山宁,还是院展的速水御舟、奥村土牛、平山郁夫、松尾敏男、后藤纯男,以及创画会的山本丘人、吉冈坚二、加山又造、石本正、上野太郎、市川保道、泷泽具幸等众多日本画名家,都将色彩作为艺术表现的重要手段。
携手走过百年风雨的周有光和张允和,就是这么一对堪称凤毛麟角的夫妻。1998年12月21日,国际教育基金会举行百对恩爱夫妻会,年近百岁的周有光、张允和是其中最年长的一对。
当今的日本画是典型的重彩画,并且日本画的面貌呈现具象、抽象多种形式。日本画已从根本上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和改造,创造立足于世界的造型艺术,使日本画成为国际性艺术。今天的日本画已经越来越接近西洋品格,只是在表现材料上和审美上还保留着日本画的特色。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在谈到日本绘画的进步时,贾方舟指出:“只要他们认为是好的,就毫不犹豫地拿来,甚至不惜‘大换血’。这个民族从来不认为学习他人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才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走向现代。”(4)贾方舟:《中国现代美术理论批评文丛·贾方舟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255页。这就是日本民族的特点,正因为如此,才使日本能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
和日本画相比较,中国重彩画在近百年的发展明显是缓慢且保守的。如上所述,由于国情的不同,中国重彩画的复兴之路才刚刚迈出重要的一步。如果把“八五美术思潮”作为一个节点,中国美术经历了类似日本美术当年一样的学习西方现代主义美术运动。西方的各种现代主义美术流派在中国美术界轮番登场,从此,西方现代主义美术思潮席卷全国(5)李新生:《意境:在审美空间的想象和再造中发生:论中国山水画的审美理想及其艺术表达》,《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但时过境迁,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美术界已开始探索本土化美术的走向和出路,崇洋之风已经渐渐褪去。中国重彩画没有像日本画那样激进和彻底,保留了对绘画“线条”的积淀和改造。因此,线条是中国画的生命和灵魂,线条作为中国画最具特色的表现手段,它是区分中西绘画差别的重要特征。
无论工笔画还是写意画,中国画都特别重视对线的表现和运用,线的好坏基本决定了作品的好坏和品质。20世纪末,中国画坛展开了中国画前途与命运的大讨论,张仃明确提出了“守住中国画的底线”——即中国画的“笔墨”。“笔墨”的含义中一个重要的特征便是强调“线”在中国画表现当中的重要性和价值。
线条在中国画的发展历程当中已存在了千年,中国人用毛笔书写,用毛笔勾皴染点进行创作已成为一种习惯。20世纪末,众多中国画画家选择了去日本学习日本重彩画的材料和表现技法,这批画家在学习日本重彩画技法的基础上,不忘创新中国绘画的风格和表现形式,就目前中国重彩画的整体面貌而言,线条依然是重要的表现手段,但线条的表现手法和内涵变得更加多元,比如当代画家郭继英、李传真及孙震生等人的重彩画作品,他们的线条描绘已经超越了传统用线,给人以新的视觉体验和启发。
当然,也有一部分当代画家在重彩创作中消解了线条的作用,用类似没骨的、写意的方法创作作品。诸多作品也是对传统重彩的发展和再造,如画家张小琴、张导曦、潘缨、颜晓萍等画家的重彩画作品,他们发挥了矿物色彩表现的张力和可塑性特点,创造了写意风格的重彩画作品。蒋采苹曾经说过:“重彩画可以‘工’,也可以不‘工’;可以用线,也可以不用线。颜料的使用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其他画材也有不小的改变。”(6)蒋采苹:《名家重彩画技法》,河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2页。不可否认,当代中国重彩画在表现手法上已经呈现多样化趋势,无论“线”与“不线”,中国现代重彩画的创作目标是为了优秀传统艺术的复兴和发展。在艺术表现上,中国的重彩画家无意向西方靠近,将自身的作品画得像西画,也无意靠近日本重彩画风,创造符合我们民族审美和传统特色的重彩画,让中国重彩画走向世界,实现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复兴是我们的重要职责和历史使命。
三、制作性、装饰性与绘画性:民族性格决定艺术性格
日本重彩画具有较强的制作性和装饰性,这个传统从日本古代的绘画艺术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日本人好像天生就带有一种工匠精神,日语称“役人性”,即做事认真细致,精益求精。日语Japan,小写就是漆器,和中国的China小写指瓷器一样,是西方人对其直观的一种形象称呼,以一个国家的代表性物品称呼一个国家的名字,在世界上除了中国和日本,其他国家还是比较少见的,这说明这种物品对西方人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是让西方人佩服和惊叹的。
日本的绘画和日本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如刘晓路在《日本美术史话》序言中所讲:“在日本,生活中的文化和文化中的生活是统一的,以日本画为例,它的两大种类之一的障壁绘(另一种是绘卷物),包括袄绘(隔扇画)、壁画、屏风画,无一不与日常生活联成一体,既是艺术品,又是居室的有机组成部分。”(7)刘晓路:《日本美术史话》,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10页。日本古代绘画的制作性和装饰性在室町时代的狩野派身上逐渐形成面貌;桃山时代是日本装饰艺术的黄金时代,绘画被大量用于建筑和室内的装饰,出现了狩野永德、狩野山乐及长谷川等伯、海北友松等艺术大家;到江户时代的俵屋宗达、尾形光琳及伊藤若冲时,日本画的装饰性表现达到了技艺和审美的成熟时期。现当代的日本重彩画艺术在表现手法上继承了这种传统风格,将它融入自己的创作当中。
和日本重彩画的装饰性紧密相连的是它的制作性,从古代日本画开始,日本人就表现出了对“箔”的偏爱,特别重视对“箔”的运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狩野永德、狩野山乐、狩野光信、长谷川等伯、海北友松、俵屋宗达、尾形光琳、酒井抱一等人的作品中找到明显的例证。为了更好地配合宫殿建筑及豪宅别墅室内装饰的需要,画家们创造了在金银箔底子上来绘制作品的办法,大多数作品以工笔重彩的形式表现,浓丽的色彩在金色或银色底子的映衬下更加显得雍容华丽,增加了富丽堂皇的气氛。金银箔底子在作品绘制前就需要做好,需要极细的耐心和敬业精神,色彩的表现也需要多次晕染勾填方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所以,日本重彩画的装饰性是建立在辛苦制作的基础上的,从这一点来说,日本的重彩画和日本其他漆艺、雕刻、装裱一样,具有较强的工艺性。
现当代的日本画家在创作中一方面吸收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观念,在写实和抽象表现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另一方面,他们对古代传统绘画的装饰性和制作性也情有独钟,所以我们从他们的作品中经常能看到闪闪发光的金银箔就不足为怪了。如今,日本画家在箔的运用上又创造了各种烧箔技法,研制出了诸如“青贝”“赤贝”等新品种,扩大了箔在画面中的运用范围,丰富了人们的艺术视野。喜欢用箔并且用得很好的画家如东山魁夷、加山又造、平山郁夫、后藤纯男、市川保道、小嶋悠司、小笠原元等,他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巧妙地将金属箔运用在自己的创造当中,形成了新时代的日本重彩画。同时,日本重彩画在材料运用时,对颜料、纸张的使用也十分精细和考究。
目前,日本重彩画的颜料品种十分繁多,同一色相的颜色常常被细分成了十多个粗细不同的号目。为了补充天然矿物色种类的不足,日本人又发明了新岩,即高温结晶颜料,虽然在品相上稍微逊色于天然矿物色,但在当今优质矿物色缺乏的时代无疑是一种较好的弥补和替代,对我们当下的重彩画创作起到了积极的启示作用。
我国的重彩画创作也具有较强的装饰性,但这种装饰性和日本重彩画不同,它没有日本重彩画的富丽堂皇和雍容华贵,因为不像日本重彩画那么重视“箔”的运用,它身上少了些许“金属气”和“富贵气”,更多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典雅和庄重之美,这种气息也是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分不开的。我国隋唐五代时期是工笔重彩画发展的鼎盛时期,不仅出现了诸如展子虔、阎立本、李思训、李昭道、张萱、周昉、顾闳中等工笔重彩大家,也诞生了众多流传千古的不朽佳作。同时,这期间的佛教石窟、寺庙、殿堂、墓室壁画也盛极一时,除寺庙及殿堂壁画随建筑烟消云散外,石窟壁画和墓室壁画尚留有很多经典的作品。宋元以后,重彩画的主流地位虽然让位于水墨画,但重彩画的传统并没有完全中断,它在民间画工和少数宫廷画家那里依然延续。
中国古代的重彩画家不怎么喜欢用箔,除非是表现宗教题材,一般的绘画表现是极少用箔的,更不喜欢在整张底子上贴金银箔后再画,这样的传统一直影响到现在。中国的重彩画强调“三矾九染”和“薄中见厚”,画家通过层层渲染积色使画面形体及空间产生或微妙的层次变化,或丰富厚重的质感和体量感。它的装饰性主要来源于色彩的平面化。平涂是中国工笔重彩画的一种重要表现方法,但平涂不是完全没有变化的涂抹,它的前提是对形体凸凹起伏关系分染后的统一和概括,颜色看似平面,但平面下是有微妙变化的。这样的处理一方面显示出浓郁色彩的装饰性,另一方面显示出色彩多次渲染后产生的丰富的绘画性。
这样的表现方法如今依然是中国工笔重彩画的主要表现手法,在当今中国画坛具有较强的影响力,这方面的代表画家有蒋采苹、唐勇力、何家英、陈孟昕,林容生、唐秀玲、李传真等。当然,近几十年来,随着西方现代美术思潮和日本重彩画的影响,特别是一大批留日画家的归来,为中国重彩画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他们将日本重彩画的一些表现手法带到中国来,特别是厚涂法和贴箔、烧箔技法的引进,丰富了中国重彩画的表现语言,增加了中国重彩画的装饰性和表现性特征,中国重彩画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画家们尝试用各种新材料和新方法去进行自己的艺术实践和探索,去拓宽重彩画新的表现手法和视觉体验。主要画家有胡伟、陈文光、张导曦、郭继英、张小鹭等。正如著名美术理论家和画家牛克诚在《现代重彩画·序言》中所说:“新重彩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一方面向古代的工笔重彩画敞开,一方面也向当代一切优秀视觉艺术敞开。在这样一个开放体系之中,每一个重彩画家都可以找到一个最能表达自我的艺术形式。”(8)蒋采苹主编:《现代重彩画》,山东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2页。
从当代中日重彩画的众多作品中可以看到,日本的重彩画家也越来越重视绘画性的表达,而中国的重彩画家反过来也越来越讲究作品的绘制技巧和工具材料。“形而上”和“形而下”是相互依存的,特别是重彩画,要求画家既要有良好的艺术素养,又要有精湛的技艺技巧,如蒋采苹先生所说,既要“尊道”又要“重器”,这样我们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精神。日本重彩画的表现方法我们不一定都能接受和认可,但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特别是日本画家的敬业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和民族需要的。
四、小美与大美:中日民族交融而又互异的审美倾向
日本著名美术史论家高阶秀儿这样描述日本的艺术美学:“有一种一直延续到现代的日本人特有的审美意识,这是一种我们固有的意识。这种意识特点,第一,它像‘うつくし’一词本来是表达爱情的意思那样,是极为情绪性的、心情性的东西;第二,如同‘くはし’‘きよし’那样,它反映了日本人相对于‘大的东西’‘强的东西’‘丰富的东西’,更在‘小的东西’‘可爱的东西’‘干净的东西’上感受到强烈‘美感’。这与西欧审美意识之源的希腊‘美’相对比,可以说是极具对照性,因为希腊的‘美’是与‘强大的东西’‘丰富的东西’相对应的。”(9)高阶秀儿:《看日本美术的眼睛》,范钟鸣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7年,第10页。这是他将日本古代艺术和希腊艺术作横向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其实,这种比较同样适合于中日古代艺术。
由于中日两国自然地理环境具有诸多差异,处于岛国的日本形成了比较敏感、细腻的民族性格。该性格的形成与中国江浙闽粤地区的民众有相似之处,而中国北方人就略微有些粗犷、直率。在艺术表现方面,无论是建筑还是绘画,日本艺术整体上来说其重视“内在的高雅”更甚于“外表的辉煌”,如桃山时代的草庵式茶室、江户时代的桂离宫书院,长谷川等伯、海北友松以及菱田春草、竹内栖凤等人的绘画。日本画家平山郁夫也曾这样评价日本人心中的美:“日本人对于四季的更替及自然的变化极为敏感,尤其十分看重那些生命力较弱、短暂的东西。比起荣耀、灿烂,日本人更喜欢静寂、无常的东西。樱花一开即谢,但日本人却极喜爱,奉为‘国花’,樱花或许是日本人美学观的象征物,它具有瞬间的美、柔弱的美、淡泊的美。”(10)贾方舟:《中国现代美术理论批评文丛·贾方舟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256页。
日本现当代重彩画在整体的艺术美学追求上依然呈现出明显的传统倾向,如山本丘人、东山魁夷、高山辰雄等人的作品。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西方现代美术思潮的影响下,日本作品风格也出现了诸多改变,如石本正、上野太郎等人的作品。他们的作品或在西方的写实、光影上去借鉴吸收,或在抽象表现的观念、构图上有所摄取,如石本正在个人展览会上自述他的作品时所说:“我的画,既不是日本画,也不是西洋画,这次的(个人)展览会希望也能这样理解……今后想描绘的东西只要能令人感动,无论是什么我想都是好的。”(11)张小鹭:《现代日本重彩画表现》,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47页。这是日本画在二战后发生的重大的思想变革,它进一步拓宽了日本人的审美视野,对我国的重彩画发展也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相对于日本民族的艺术审美,我国的民族艺术审美呈现出与之不同的价值旨趣。整体上来说,我国的民族审美心理是“尚大的”“尚强的”。关于汉字“美”的解释,后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中道:“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美与善同意。”(12)杨辛、甘霖:《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4页。虽然后人对此抱有诸多疑义,并赋予“美”以不同的解释和理解,但事物或让人“赏心悦目”,或让人“精神受到陶冶”总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庄子《逍遥游》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又道:“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13)陆永品:《庄子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1页。
我国民族的审美心理从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已经露出端倪,生活在大山大水之间的华夏民族,更倾向于一种深沉雄大的审美感受,倾心于一种宏伟的、永恒的审美心理。从秦代绵延群山的万里长城,汉代朴拙大气的石雕石刻,隋唐巍峨的宫宇楼阁,到苏东坡豪迈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岳飞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皆是民族审美心理的直接体现。虽然中国的诗词文学中也有像柳永、晏殊、李清照等优美的“婉约派”,但民族的整体审美心理还是“尚大的”“尚强的”,与日本存在着较大差别。这种审美心理同样规制了中国绘画艺术风格的走向和趋势。现当代的中国重彩画在艺术美学层面受到传统审美心理的影响,我国唐、宋、元代的重彩壁画即是这种审美的体现,这一时期的重彩画气势恢宏,加之浓郁丰丽的色彩,皆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艺术追求,影响至今。
20世纪50至80年代,由于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此时期中国的重彩画题材以人物画居多,山水、花鸟画次之。人物画内容多具有历史和革命现实主义画风,追求的是宏大崇高的审美品格,如徐燕孙的《兵车行》、刘凌沧的《淝水之战》、叶浅予的《中国人民大团结》、任率英的《杨门女将》、潘絜兹的《石窟艺术的创造者》、刘继卣的《孙悟空大闹天宫》、刘文西的《同欢共乐》、许勇的《群众的歌手》、顾生岳的《春临东海》、林凡的《张骞回京》等。在绘画风格上,以写实风格占据主流,在审美风格上有突破者并不多,代表人物仅有林风眠、黄永玉、丁绍光等,代表作品分别为《伎乐》《山鬼》《幸福鸟》。
这一时期的重彩画创作虽然体现出奇异、瑰丽的新面貌,给人以崭新的视觉体验,但重彩山水和花鸟画的作品相对较少,且缺乏新意,只是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有所突破。毋庸讳言,中国的重彩山水和花鸟画水平亟待全方位提升,当代的中国画坛特别是山水花鸟画,还沉浸在水墨画的世界里,视色彩为俗艳之物,“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14)王维:《山水决》,见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上),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592页。的理念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中国重彩画的发展首先应该解决对色彩的重新认识和评价的问题。
近20余年时间里,中国重彩画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一代代画家的努力下,从事重彩画创作的画家越来越多,在中国画坛已经初步确立了一定的地位和影响,这是复兴我国传统重彩画的关键一步。近些年,一些著名的重彩画家已经成为中国画坛的主将,影响着中国画坛的风格和审美导向,如唐勇力、陈孟昕、刘新华、林容生、唐秀玲、郭继英等。其中唐勇力的代表作《开国大典》,以其雄伟的气势和浓郁的色彩赢得了世人的瞩目;陈孟昕的《碑颂》《一方水土》等作品,以其庞大群像构图和瑰丽的色彩创造了中国重彩画的新面貌和新视野;刘新华的《故土》《逝去的日子》等将中国重彩花鸟画的材质美和意境美表现得微妙得体,恰到好处;林容生的重彩意象山水《风清翠凝》《清辉》等,第一次将人们的视野带到了中国山水画的另一个世界里;唐秀玲的重彩花鸟作品《走过四季》《溢香》等,展示了中国花鸟画优美、精致的审美品格;郭继英的重彩画《夕》《远方》等,虽受日本重彩画的一些影响,但在艺术表现和意境的塑造方面还是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息。
结语
纵观中国重彩画半个多世纪的流变过程,近20多年来取得的成果是最为丰硕和喜人的。但不可否认,中国重彩画近几十年的发展是和日本重彩画的影响分不开的。随着西方绘画技艺达到巅峰,从文艺复兴到古典时期,浪漫主义、印象主义以及各种西方现代流派纷至沓来,中国画坛形成了相对多元和自由的绘画面貌,西方绘画和日本重彩画从不同方面激励着中国重彩画的重新崛起和自我价值的探寻。目前,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瑰宝,重彩画以其独特的面貌成为中国艺术作品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而今,中国重彩画正在以它崭新的面貌呈献给世人。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艺术的创作要以形神兼备、情景交融为美学价值追求。可见,“无论是工笔画还是重彩画,在将来是最先可以走出国门的艺术形式,因为它有相通性,它的色彩,它的造型,它的构图等,国外没有文化的阻断,可以直接感受到它的水平”(15)蒋采苹:《美丽中国·中国重彩画集》,天津杨柳青画社,2015年,第205页。。总体而言,中国现代重彩画的发展比日本重彩画滞后了多年,鉴于国情的差异,两种绘画艺术在语言表现和审美观照等方面各有千秋。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旨在通过两国重彩画的视觉感受探究其背后复杂的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以期为我国的重彩画发展找到突破口,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绘画表现形式,进而打造新时代中国画的全新面貌,推动中国画能够全面健康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