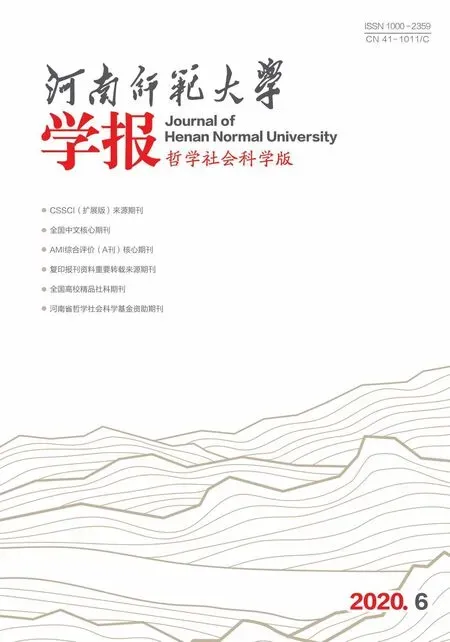论盛唐山水田园诗中的环境生态观
赵 潘
(河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
一、盛唐山水田园诗人概述
盛唐山水田园诗人主要以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健、祖咏和裴迪等为代表。孟浩然(689-740)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满腔抱负,但是仕途不顺,最终不得不游走于山水田园之间。他的诗歌多写山水田园,他不仅把它们当做艺术审美的对象,而且把它们当做心灵情思的寄托之所,譬如:“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诗句描写的是洞庭湖的壮丽雄伟,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气势磅礴的最佳表达。但与此同时,它也映射了波澜壮阔的时代,以及与这个时代所匹配的力量与豪情。遗憾的是,作为个体的诗人却无法参与其中,只能成为时代的看客,“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此时,自然的豪迈之景引来了诗人的失落之情,正是人与自然情景交流的至境之处。王维(701-761)的诗歌以山水为主,他也是盛唐时期主要的山水诗人。王维出身于贵族,后状元及第,可谓春风得意,但随后便经历宦海沉浮,遭遇人生坎坷,他的诗歌因此兼有洒脱和失意两种风格。与孟浩然所不同的是,他在自然当中不仅看到了情意,而且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自然的启悟,所以,他的山水诗虽写自然,但是又常常能跳出自然,于短短的诗句中现出超凡脱俗的灵动,从而增强了诗歌空灵的艺术境界。
储光羲(706-763)与王维齐名,唐人合称他们为“储王”。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位置于王维、孟浩然间,殆无愧色。”储光羲二十岁时便考中进士,但随后的仕途却不尽如人意,后隐退,复出又逢安史之乱,被迫失节后下狱,最后被贬谪岭南。这样的人生际遇实比孟浩然更凄惨、更坎坷,这就让他的田园诗歌多少带有一点严酷的现实成分,在平淡自然之中显示出质朴的风格来,他的诗歌在盛唐很有影响,“彻底奠定了田园诗在盛、中唐过渡期里的全面繁荣局面”(1)刘燕:《从储光羲诗歌看盛唐田园诗之新变》,《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9期。。常健(705-765?)也以田园山水为描写对象,他是进士出身,性情孤高,后来官场失意,终生不得志。他的诗歌语言简洁,意境清远,在盛唐诗人中有一定的位置。其他的还有祖咏、裴迪、綦毋潜等人。
纵观盛唐山水田园诗人,他们大致活跃在七世纪末到八世纪的中后期,除孟浩然进士不第,终身未仕外,其他诗人都有进士及第,为官从政的经历。他们共同见证了开元盛世那个“稻米流脂粟米白”的繁华时代,但也大都经历了“国破山河在”的安史之乱的时代,这一正相与反相的政治合力极大地冲击了这些诗人的命运,他们虽然寄情于山水田园之中,但是却于山水田园之中,展现出了对盛唐现实的某种关怀。
二、盛唐山水田园诗中的自然生态观:原始质朴
程郁缀认为自然首先指自然界,即大自然;而自然观则指古代诗歌中人类对客观自然的认识和审美情趣,作者把古代自然观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2)程郁缀:《古代诗歌中的自然观小议》,《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第一阶段,将自然作为崇拜和敬畏对象的自然观,主要体现在先秦早期的诗歌里;第二阶段,将自然作为审美和欣赏对象的自然观,体现在魏晋南北朝的诗歌里;第三阶段,将自然作为亲近和启迪对象的自然观,体现在唐宋时期的诗歌里。据此,盛唐山水田园诗应处于第三个阶段,山水田园本身就是人化自然的现实体现,而山水田园诗则是诗人们对自然的二次人化。
唐代在改造自然的能力上已经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提高。有研究者指出:“唐代在天文历法、数学、农业、地理、医药、水利、建筑、物理、化学、陶瓷、矿冶、印刷、造纸、纺织、造船等几乎所有古代科学技术领域都取得了众多的创新成果,科技史学界认为唐代已使中国古代科技步入成熟阶段。”(3)周尚兵:《对唐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再认识》,《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9年第12期。技术的进步必然会带来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进而提升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这样一来,人化自然的力量也会随之增强,自然就会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被裹进人类的艺术审美领域之中。透过盛唐山水田园诗可以发现,盛唐时期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农业生活,都表现出有利于艺术创作的特点,即自然生态的和谐性,盛唐山水田园诗往往把自然生态作为理想的寄托,这种寄托不仅反映了诗人出世精神的一面,而且反映了诗人入世精神的一面。
盛唐时期的地理环境和气候铸就了山水田园诗的画意与诗情。从地理环境以及气候角度考察盛唐历史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但以此分析文学的论文并不多见。实际上,如果说盛唐时期的环境、气候为唐朝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前提,那么同样,盛唐时期的环境、气候也为诗人们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生态。竺可桢指出,中国气候在七世纪的中期变得和暖,公元650、669和678年的冬季,国都民安无雪无冰(4)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3年第2期。。唐玄宗李隆基时,他的妃子江采萍曾在所居之处种满梅花,李隆基更是曾在蓬莱殿栽种桔子树。文学地理学认为,文学的地域性是由文学作品所赖以产生的地理环境造成的,而文学的地域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气候的差异性以及由气候的差异性所导致的物候所决定的(5)曾大兴:《气候的差异性与文学的地域性》,《浙江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用唐代时期的气候环境考察盛唐山水田园诗的自然生态,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即自然对这一时期的唐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善意,它构成了唐代开元盛世得以形成的客观自然条件。这种善意同样为盛唐诗人与自然之间营造了格外和谐的关系,自然的柔情似水和善意满满,自然成了山水田园诗人寄托立项的合适对象。
与适宜的自然气候相适应,盛唐时期的农业也呈繁盛之态。研究者认为:“气候的温暖湿润为唐代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6)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1期。据记载,“中国古代在元代以前粮食亩产量以唐代最高,达334斤。”(7)吴慧:《清代粮食亩产的计量问题》,《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农业的发展带来了农副业经济的繁荣。《四时纂要》中有对唐代农业活动的详细记载,除种植粮食作物外,唐人还扩大了茶叶、甘蔗、果树和蔬菜等作物的种植面积。适宜的气候也为北方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牧民生活有了稳定保障,北方许多少数民族与唐朝的交好不能不说与此有很大关系。农业的繁荣会给农民生活带来一定程度的改善,田园风光此时可能会在人们的眼中呈现出理想化状态,诗人的乡愁和落寞也由此有了落脚之处。有研究者在分析西北地区的农民群体生活情况时指出,“通过对唐代西北地区农民群体生活世界的考察, 可以看出唐代社会相对富足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世界, 反映了唐代稳定的社会秩序、日渐发达的生产力和民众自由的精神信仰状态”(8)张安福:《唐代西北地区农民群体的生活世界》,《齐鲁学刊》,2008年第6期。。这种富足在唐诗中也有充分体现:“元和时期宰相权德舆在过咸阳时曾受到村民的热情招待,看到村庄周围‘涂涂沟塍雾,漠漠桑柘烟’景象时, 曾‘自惭廪给厚’,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回归田园。”(9)张安福:《唐代西北地区农民群体的生活世界》,《齐鲁学刊》,2008年第6期。
综上所述,盛唐时期的气候温暖湿润,自然环境宜人,而农业的繁荣也给农村带来了相对富足的生活。与社会政治的复杂和喧嚣相比,自然生态呈现出鲜明的友好态度。盛唐山水田园诗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以及在诗歌中呈现出对自然的美化,无不与这一时期和谐的自然生态密切相关。
三、山水田园诗中的社会生态观:仕途沉浮
如果自然是诗人们的精神家园,是诗人们托物言志、寄托情思的审美对象的话,那么,社会在诗人眼里就不再是友好的对象了。盛唐原本应该建构的是一个良性的社会生态,但随着统治阶级的腐化堕落,社会生态遭到严重破坏,这无疑给盛唐山水田园诗人的写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科举考试是封建统治者延揽人才的一种手段,唐代的科举改变了魏晋以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固化结构,正如有研究者所说的那样:“唐代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的最重要变化,是世袭门阀的衰落与科举制的实行。在科举制度下士族与寒门由竞争而合流,旧士族的政治、经济特权和文化优势被科举出身者所取代,从而在上层统治者与下层社会之间造成一个新的士人阶层。与这一变化相适应,一方面出现了贵族文化、士族文化的下移,旧的儒学、文学传统在新兴士人阶层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为唐代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基本条件;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知识阶层的士人,被有效置于国家政治统系之下,其文化和文学制作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联系日趋紧密。”(10)谢思炜:《唐宋诗学论集》,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4-115页。尽管科举制度在唐代尚不够完善,但对唐代社会的稳定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李林甫执掌朝政以后,这种政治生态受到了破坏。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由李林甫任盛世权相,在其专政期间推行的一系列政治权谋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诗坛风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循资格’的铨选制度打击士人积极入仕的心态;其二,把持朝政控制自由言论;其三,关纳贤之门重创天下士子求仕之心。”(11)唐萌:《论李林甫专权对盛唐诗坛的影响》,《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9期。与此同时,唐代统治者对于潜藏危机的漠视所导致的安史之乱,则更加大了既有政治生态的破坏程度,国家也由此迅速走向衰弱。对此,有的学者认为:“‘开元盛世’及天宝年间的所谓‘盛’,主要反映了皇族、大官僚、大地主、大豪商等大土地所有者物质生活的奢侈腐化、文化生活的纷繁多彩,以及封建国家某些方面诸如城市经济、 商业贸易等等的隆盛;而其背后,则潜伏着深刻的经济、政治危机,特别是大地主垄断土地所有制疯狂兼并小农土地所有制,使封建国家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基础趋于崩溃,从而严重的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加剧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以及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危机,这是‘开元盛世’急转而为‘安史之乱’ 的根本原因所在,其间的‘用人得失’也是由这个根本原因引起的‘始速祸焉’ 的一个重要因素。”(12)张剑:《盛世何以有危局:安史之乱爆发原因新探》,《人文杂志》,1998年第5期。这段话包含两层含义:其一,盛唐之“盛”是上层之盛,城市之盛,商业之盛,上层的风尚吹向大唐这个基体,把贵族式的休闲方式带到了城市和民间,许多的山水田园诗人如王维、孟浩然等都曾与皇亲贵族交好的原因,或许能在这里得到解释。另外,达官贵人们的倡导,以及诗人的积极参与也使得盛唐文化的贵族气韵更加浓厚,所以,盛唐的田园诗中常常会有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这对他们来说似乎并不意外。其二,盛唐社会生态的转变基于社会结构潜在危机的扩大化,这种恶化了的农村田园生活在诗人们笔下也有反映。
可以说,从初唐到盛唐,再到中唐,社会生态经历了一个从良性到恶性的转化过程,这也是一个王朝由强盛走向衰落的过程。毫无疑问,这一由盛而衰的社会过程都直接作用到了生长于其中的诗人身上。尽管他们的个体经历不全然相同,与社会变化的振幅频率也不全然一致,有很多位山水田园诗人们在其青年时期就中了进士,并未受到科举变乱的冲击,但整体而言,这种影响还是很大的,如在安史之乱中受牵连的王维与储光羲,因乱归隐的綦毋潜、祖咏和裴迪。这些都在说明,即使社会生态处在良性发展的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人也已经表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不适应,更不用说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了。诗人们那种对官场既渴望又无奈,既想入仕又想出仕的心态,充分表明了传统诗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
四、山水田园诗中的精神生态观:回归自我
对山水田园诗人而言,盛唐的自然生态几乎是无可挑剔的,不管是“人化”自然还是自在自然,它们都对这个时代的人们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善意。中国文人历来都有寄情山水的传统,这种风气在盛唐时期就更加流行了。诗人们游历的脚步遍布城市、乡村,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到城市,这种生活方式、景观的差异以及后世城乡二元对立的恶劣生态在这里被诗意化地消解,自然成了诗人们的精神家园。
盛唐的开放性为诗人们提供了各种入仕的途径。可以说,对盛唐的这些山水田园诗人们而言,只要想入仕,他们就有进入官场以实现人生抱负的可能。但问题在于,未曾进入官场的人,置身于官场之外,他们往往对入仕生活充满了艳羡,以至于对无法参与到这个时代的洪流当中而感到遗憾;而曾经入仕的人,则往往又会因仕途沉浮而滋生不满,这就构成了他们性格的复杂性。面对这样的自然与社会,诗人们应该如何自处?这就关联到了山水田园诗人们的精神生态。这绝不是简单地用出世或者入世就能说明白的,对他们而言,不管以什么样的姿态入世都似乎觉得不舒服,而不管以什么样的姿态出世,却又都觉得自由自在。由此可以看到,尽管社会生态对诗人的生活会有影响,但是那只不过是外在因素,只有个体对社会的感受才是内在因素,所以,无论是面对社会的不适感也好,还是面对入世的挫折感也好,最终具备决定要素的并非全是社会生态之好坏,而是诗人们内在的精神生态的好与坏。
原本在农业社会和农业文明里,深处其中的人们对自然的亲近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行为。盛唐山水田园诗人以自然为题,以自然为歌,本身就对自然充满了敏感,因而也更容易亲近自然、热爱自然。从表象上看,盛唐山水田园诗人都不约而同地从自然那里找到了慰藉,却对社会始终怀着一种敌意,这种敌意其实正如对自然的亲善一样,也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它源于儒家文化生态观念,是传统精神人格的当代外化。可以说,诗人们的内在精神生态本身就是矛盾的,它具有双重性。由此反观所谓的雅与俗,媚俗与脱俗,出世与入世,它们也并非是二元对立,而是和谐地统一于诗人的精神世界里,构成了他们的内在精神生态。
有学者在谈及李白等诗人诗作时曾这样说:“在唐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构建中,特别是在盛唐诗人的文化人格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只注意了作家人格中的那些被认为是富有积极意义的层面,而忽视了对附势与媚俗这类人格层面的关注。应该说,这不是对作家文化人格的整体研究,这也势必影响到对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整体把握。……不可否认,盛唐时代,开放的人文环境使得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诗人极力追求个性的自我张扬。这种自我张扬的极致便是对独立人格的企慕与标榜,并诉之于文学创作。但是,封建社会建立于高度中央集权制的基础之上,‘权’与‘势’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社会存在,是封建专制的派生物。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象征着权力和地位,而权力与地位正是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13)杨恩成:《唐诗说稿》,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5-56页。这些结论是具有普适性的,它也适用于山水田园诗人们。事实上,王维之攀附玉真公主,孟浩然之四处奔走,均包含了直接的社会目的,其他如储光羲、祖咏、常健、裴迪、綦毋潜等人,也都曾是积极的入世者,他们不仅内“道”,而且内“儒”。换言之,对山水田园诗人们而言,儒家和道家思想在他们身上并行不悖地存在着,他们既追求功名,也追求自然恬淡,并不一定非得要在其中进行价值取舍,即使非要作出取舍不可,其原因恐怕也是情绪上而不是理性上的。他们或许追求功名而不可得,转而从自然中寻求安慰,但是安慰并不能抵消他们的功名之心。从这层意义上说,自然生态即使再完美也无法安慰盛唐山水田园诗人的心,这恰是那个时代所赋予他们的时代特征。盛唐既不是东晋,也不是南北朝,试想,在那个开疆扩土、气势恢宏的时代里,谁愿意安然地居于田园之中?
从生态学的角度考察盛唐山水田园诗人,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三点:其一,就自然生态而言,盛唐是中国人改造自然的力量正在增强的时代,诗人们的艺术实践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与其时代匹配吻合。农业生产力的大幅提高与农民生活的有力改善,可以让田园从人类的劳作之苦中脱颖而出,进而成为诗人们栖息的地方。其二,就社会生态而言,盛唐的社会生态不可谓不好,诗人们也从中受益很多,大都满足了自我的功名之心。安史之乱所带来的生态恶化,直接影响到了诗人们的社会地位,也直接导致了他们在自然中寻求安慰的艺术实践,但整体而言,诗人内在的人格机制才是他们不满足社会生态的根本原因。其三,就个人精神生态而言,追求自然的和谐与社会的满足,是山水田园诗人们不可分割的追求。雅与俗,追名逐利与蔑视功名和谐地统一在他们的精神深处。自然和社会都是他们的家,诗人们对它们的矛盾态度在更多情况下是情绪上的,而不是理性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