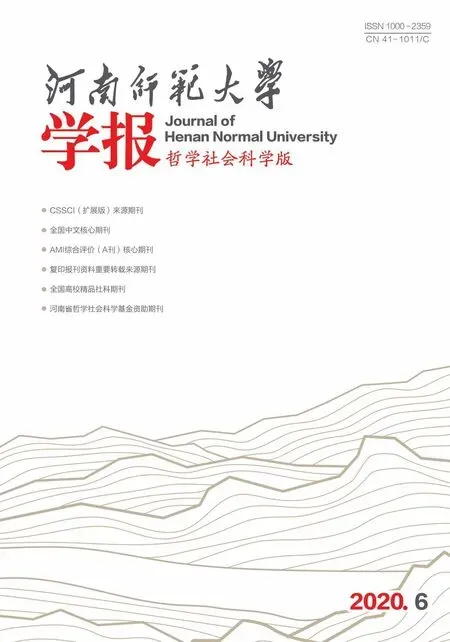俄罗斯联邦立法制度的演进及其规律
卢森通
(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1)
一、1917年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立法制度
与中国宪法的发展相类似,俄国宪法发展也是封建王权主动或被迫妥协的结果。在19世纪初,俄罗斯就存在一定的宪法观念和立宪主义思想。1905年俄国公布了《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诏书》《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律》和《杜马选举条例》。然而,根据这些法律的规定,妇女、青年、现役军人、贫农和工人等许多的居民阶层被排除在杜马选举之外。1905年10月17日沙皇颁布诏书宣布,“确立稳固的规则,以使任何法律未经国家杜马同意不得具有效力,并保障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杜马代表有真正参加监督我们当局的行为是否合理的可能性”(1)阿瓦基扬:《俄罗斯联邦宪法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226-227页。。这样,国家杜马由咨询机关转变为俄罗斯的立法机关。沙皇于1905年12月11日签署了新的选举法,扩大了选民的类别。在这部法中保留了不同的代表制、较复杂的工人和农民代表的多级选举制,还保留了妇女、青年、现役军人和维持游牧生活方式的部族不参加选举的规定。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国家杜马不是唯一的立法机关。早在1810年成立的国务会议,与国家杜马同时获得了讨论法律草案的职能,并被赋予参加立法的权利。在法律上,这两个机关是平等的,一个机关通过的法律草案,应当得到另一个机关的赞成,法律草案既可以先提交前者,也可以先提交后者。立法机关的设立,以及赋予杜马监督沙皇指定的执行机关的权利,可以认为是俄罗斯在君主立宪制道路上所采取的最初措施。
需要指出的是,经过一系列诏书和法律的颁布,虽然在外在表现上俄罗斯已经有了两院制的雏形(2)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Яковлева,1906,126с.,事实上的立法权还是由沙皇掌握。首先,立法机关是国务会议和国家杜马两院组成的。与国家杜马不同的是,国务会议一半成员是由沙皇任命的高官,而并不是经过选举产生;另一半成员由东正教神职人员、贵族、地方自治机关、学派、商人和手艺人选举产生。对于可能产生更多立法主张的国家杜马来说,国务会议是一种起遏制作用的因素。因为从人员构成上来看,国家杜马代表着平民的利益,而国务会议代表着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两者本身在利益上是相互冲突的。而且国务主席是由沙皇从国务会议中非选举产生的那部分成员中任命的,而将两个机关通过的法律草案送交给沙皇的只能是国务会议主席而不是国家杜马主席。
设立立法机关的文件颁布后,相应的《国家基本法》也要进行修改。沙皇尼古拉二世于1906年4月23日批准了新修改的基本法(3)Свод зако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Русская скоропечатня,1916,371с.。在《国家基本法》第一章规定,最高无限的权力属于皇帝,“服从皇帝的权力,不仅是由于畏惧皇帝的权威,而且是对得起良心”。《国家基本法》第五条规定,皇帝陛下与国务会议、国家杜马共同行使立法权。但是第五条同时规定了皇帝的优先权:(1)所有立法对象方面的动议,均由皇帝提出;(2)只有根据皇帝的动议,才能在国务会议和国家杜马中重新审议《国家基本法》;(3)法律由皇帝批准,未经皇帝批准的任何法律都不得实施。(4)阿瓦基扬:《俄罗斯联邦宪法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226-227页。当然,除了立法方面的权限,沙皇还有其他诸如行政权和财产权等方面的诸多权利。即使在《国家基本法》中较多地维护了皇帝的利益,但是改革并非停滞不前。为了保障代表平民的国家杜马在立法方面的权限,《国家基本法》又确认了以下权利:在不违法的前提下,和平地、不携带武器地召开大会的权利;每个人都有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口头地和书面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且有通过报刊或其他方式传播自己思想的权利”等。但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沙皇在妥协中所建立起来的这一套立法制度伴随着专制王朝的覆灭,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俄国走上了一条既不同于沙皇俄国又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即创立了一套全新的立法制度。
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阶段的立法制度
(一)工农红军代表苏维埃阶段的立法机关的确定
苏维埃国家政权原则的基础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所建立的,他们将国家政权机构视为“工作之行会,同时又是立法和执法机关”(5)В.В.拉扎列夫:《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296页。。苏维埃体制是苏联政治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苏维埃在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已经出现。1917年6月和11月苏维埃召开了两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开始从领导起义的群众性组织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机关。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88年12月,是苏维埃的产生和发展时期(6)《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2页。。
在苏维埃国家建立的初期,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是经常起作用的权力机关,它的机构和工作程序是在1917年11月2日(俄历)召开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确认的。从十月革命胜利之日,至1918年苏俄宪法制定之前,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共通过了109项决议、告居民书及其他文件(7)张寿民:《俄罗斯法律发达史》,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97页。。
1918年7月10日,第五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了第一部苏维埃宪法,苏维埃制度得到了宪法的确认,俄国宣布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地方政权全部归苏维埃掌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每年召开至少两次,由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召集(该条款在第九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修改为每年召开一次)。由此可见,苏维埃政权是全面否定沙皇时期的法律的。这一点与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对待苏联时期的法律制度的态度是不同的。
(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阶段的立法制度
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宣言和成立条约在第一次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获得批准(8)关于成立苏联的宣言和条约是由各加盟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批准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7月3日通过决议,批准和通过了关于苏联成立的宣言和条约。。为了巩固苏联的政权,划分联盟和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权限,1924年通过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该法规定,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是联盟最高权力机关。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权颁布在苏联全境均须直接执行的法典、法令、决议和命令。同时,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权停止或废除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各加盟共和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苏联境内其他权力机构的法令、决定及指令。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常委会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负责召集,每年举行一次。由此可见,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立法机关。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由联盟院和民族院组成。联盟院是不分民族的全联盟劳动人民的代表机关,它是按照人口比例,从各加盟共和国的代表中选出,而民族院代表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的劳动人民群众。每个共和国无论人口多少,都选派五名代表,每个自治州选派一名代表。两院组成人数不同但权力平等,都选举产生7人主席团主持本院工作。呈请苏联中央委员会审查的法案,须经联盟院与民族院通过,并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公布后,才具有法律效力。联盟院和民族院审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及人民委员会、联盟各人民委员部、各加盟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以及联盟苏维埃和民族苏维埃自行提出的一切法令、法典和决定。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两院制结构,使各民族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以及各共和国和各自治州的特殊民族利益都得到了保障(9)张寿民:《俄罗斯法律发达史》,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54页。。
苏联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最高权力机关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该主席团由中央委员会组成,共21人,其中包括联盟院主席团和民族院主席团的全体成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团及人民委员会的组成,须由联盟苏维埃与民族苏维埃的联席会议决定。
(三)人民代表苏维埃阶段的立法制度
实施长达40年的1936年宪法被1977年宪法所取代。伴随着新宪法的制定,立法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根据1977年苏联宪法的规定(10)Конституция СССР 1977 года.Известия,1991,70с.,劳动者代表苏维埃被人民代表苏维埃取代,成为“全民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我们知道,以前颁布的几部根本法都规定,全部权力属于“俄罗斯全体劳动人民”(1918年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第10条),属于“城乡劳动者”(1936年《苏联宪法》第3条)。1977年苏联宪法首次规定,“苏联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2条),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既作为人民主权的国家形式,也作为人民主权的社会形式。这种形式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国家的社会基础扩大了:一是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里曾经存在工人阶级和贫农的联盟,而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存在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的联盟(的确当时已不存在其他的农民);二是国家已经变成反映全体人民利益、反映社会所有社会集团和阶层利益的全民的组织;三是从规模上来看,国家的创造功能、建设功能已经变得非常大。所有上述原因新宪法都应当兼顾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苏联宪法从假定一个组成部执掌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全民国家和社会各个阶层均参与履行人民主权的职能。
1977年苏联宪法对国家机关给予高度关注,它包含了许多新的关于国家机关权限、活动程序的范围(11)Конституция СССР 1977 года.Известия,1991,70с.。例如,关于苏联最高苏维埃立法程序的规范,关于立法动议权主体范围的规范等。正是由于“苏联一切属于人民”这一宪法奠基性条款的规定,1977年苏联宪法相当详细地确认了国家代表权力机关的作用的提高。宪法在反映国家社会基础变化这一事实的同时,赋予了国家代表权力机关以新的名称——人民代表苏维埃。苏维埃的特殊作用,决定了要在1977年苏联宪法中列入以前几部宪法没有的专编“人民代表苏维埃及其选举程序”。两院制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仍然是苏联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为了与1977年苏联宪法条文相协调,1978年所有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都通过了本国的新宪法(12)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СФСР 1978 года.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1986,45с.。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与俄罗斯联邦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基本相同,但俄罗斯联邦实行一院制。在规定各种国家机关的活动方面,1978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在很大程度上仿效了联盟国家宪法,但也有自己的特点。例如,对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组成人员的数量作出了硬性规定,即975名代表,相当于全面地规定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的职权范围。
三、苏联解体后过渡时期的立法制度
(一)苏联解体后过渡时期的立法制度
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最高苏维埃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主权宣言》,宣布俄罗斯联邦拥有“绝对主权”。这一宣言是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于1990年5月通过,由在这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叶利钦签署(13)6月12日被确立为俄罗斯的独立日,被认为是“俄罗斯再生”“俄罗斯复兴”的始端。。1991年12月25日,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名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
1990年5月举行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叶利钦为俄罗斯苏维埃最高苏维埃主席,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民主派执掌俄罗斯国家权力之后,立即进行制定新宪法的工作,力图以国家根本大法形式,将民主派的胜利成果固定下来,改变俄罗斯联邦的社会主义性质,建立“主权的、民主的、社会的、法治的国家”;改变国家经济制度的基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代之以“自由的企业家活动”;改变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国家权力,建立西方式的三权分立的总统制国家权力体制。
在叶利钦同议会的斗争的过程中,双方纷纷提出有利于自己的宪法草案。议会试图通过制定一部议会制宪法来限制总统的权力。莫斯科“十月事件”中叶利钦的胜利为制定新宪法和建立总统制共和国扫清了障碍。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举行了国家杜马选举,同时对新的宪法草案进行全民投票,宪法最终获得通过。新宪法确定了俄罗斯全新的立法制度,同时改变了之前中央高度集权的模式。虽然俄罗斯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斗争已经结束,政权党的建立也缓和了总统和议会之间的矛盾,但是有必要提及的是,一部职权明晰的宪法是保障立法制度顺利运行的条件。俄罗斯独立初期出现两个立法决策中心并存的局面,以及后来两者之间的矛盾升级并且兵戎相见的直接原因是,新独立的俄罗斯缺乏一部完善的宪法,未能对俄罗斯各国家机关的权限作出明晰的规定。如果宪法不能反映各派的政治现实,那么作为宪法重要组成部分的立法制度的权威性也必然会受到挑战。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联邦对苏联时期法律的看法,与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对十月革命前所制定的法律的态度不同。苏联解体之后,苏联时期制定的法律并没有立刻失效,而是在俄罗斯联邦制定出新的法律之前,不与俄罗斯联邦宪法相抵触的部分继续发挥作用。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主要是因为沙皇俄国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斗争是以革命的方式来进行的,而苏联解体则是妥协的结果。因此,对于与俄罗斯联邦宪法不相矛盾的部分,苏联解体之后,独联体国家继续沿用。
四、俄罗斯联邦立法制度演进的规律
从苏联和俄罗斯立法制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在从苏联立法制度到俄罗斯的立法制度转变的过程中,立法制度处于一个过渡的状态。“国家与法,以及与之同在的社会政治体系和个别社会政治制度永远处于过渡状态之中,因为它们日常功能的发挥和发展是与它们从一种质向另一种质的不断转变同时进行的,因为它们一直在从一种质的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过渡”(14)马尔琴科:《国家与法的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9页。。当代俄罗斯立法制度的形成过程也是新旧制度的较量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联邦立法制度呈现出一定的特点。
(二)俄罗斯联邦立法制度具有转型期立法制度的规律
俄罗斯当前的立法制度的存在和立法实践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社会转型的迫切需求与特有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十月革命摧毁了沙皇俄国的统治,建立了苏维埃立法制度。然而,苏维埃立法制度并没有实现将“立法权力”赋予人民的初衷,最终导致立法权集中于国家领袖和党的手中。另外,苏联解体之后,选择了西方式的政权组织形式和立法制度,但俄罗斯的各种民主制约机制并未有效发生作用,立法制度在外在形式上与西方国家颇为相似,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尚存在诸多问题。
俄罗斯立法制度借鉴西方但是又不同于西方。俄罗斯立法制度的转型是建立在政治转型的基础之上的,即效仿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彻底摧毁苏共体制。俄罗斯的初衷是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但最终建立的是高度集权的总统制,不是“原版”的西方民主制。俄罗斯独立初期,作为政治精英的民主派当时选择欧洲-大西洋主义作为执政理念的基础。欧洲—大西洋主义认为,俄罗斯属于欧洲的一部分,俄罗斯理应走西方式的发展道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俄罗斯照搬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形成以三权分立为原则的政权组织形式。但他们没有考虑到制度在俄罗斯实践中会发生变形(15)穆亮雷:《当代俄罗斯国家决策机制及其启示》,山东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第52页。。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叶利钦时期,总统与议会之间矛盾重重,虽然在宪法法律制度上规定了立法、总统、政府、司法几个权力之间相互制衡,但是各权力主体之间的权力严重不对称。议会制是西方民主制的核心和主要标志,民主制度的核心是权力制衡。俄罗斯联邦新宪法生效后,俄罗斯社会民众与政权的疏远状况如故,新闻媒体依然受到政府机关和金融财团的控制。“俄罗斯的宪政模式仍然是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宪政模式”(16)徐坡岭:《俄罗斯政治制度转型的全球化约束与政治传统张力:俄罗斯政治制度重构的主导因素》,《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8期。。也正因如此,俄罗斯联邦的立法制度的实践依然带着诸多俄罗斯烙印。
与西方相比,俄罗斯是具有东方性质的社会,又是工业化起步较晚的“后发外生”的转型模式,不同于英美等“先发自致”发展模式。民主政体在俄罗斯尚未找到坚实的基础。十月革命前,俄罗斯还没有复杂的民主政治制度,君主专制没有提供广泛的民主和政治自由。苏联时期,利益通过统一形式表现,不同利益由党来划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立宪活动,但外部世界的压力也是显而易见的。西方国家处于强势地位,使俄罗斯面临被动局面。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里不可能提供充裕的时间和良好的条件,以供其从容不迫地建立起“原汁原味”的西方民主制。从沙皇俄国的立法制度到现行的俄罗斯立法制度之间两次大的过渡,明显地呈现出取代型的特征,并且都是在国家对社会丧失控制地位时发生的。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政权全面否定了沙皇俄国的立法制度,采用议行合一的模式;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联邦在刑法、民法、诉讼法等法律制度方面继续沿用苏联时期的规定,但这只是避免出现法律空白的权宜之计,而关涉重要权力分配的立法制度,苏联解体前后便进行了修改。
事实上,十月革命之前颁布的一系列法律中,有很多进步性的东西。另外,还有一些规定间接地促进了十月革命之后民主制度的建立。比如,十月革命前关于宗教和结社自由的规定,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起到一定的解放思想的作用。立法制度的变革,究其原因,皆是因为民众的思想启蒙。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权利是斗争得来的,而民众思想的转变是制度变革的最根本的因素。
(三)俄罗斯联邦立法制度呈现出较强的意识形态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过渡形态下的立法制度存在着诸多缺陷。因为国家、法以及社会本身存在着一种极其复杂的、充满着矛盾的状态,它伴随着对自己过去的重新评价,伴随着对自己最近的和长远的未来的痛苦选择。与任何一种政治体系一样,每一个国家的立法制度作为历史的范畴和一定类型的政治现象、制度和机构,都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框架内存在并发挥功能的。意识形态因素往往起着最为根本的作用。从苏联到俄罗斯立法制度的变迁是建立在从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否定和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接受的基础之上的。同时,私有化的政策打破了苏联长期以来计划经济的形态。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的转变构成了立法制度变革的导火索。
从十月革命推翻沙皇俄国到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向联邦会议产生和发展之前,俄罗斯联邦立法权的改变,建立在对“三权分立”彻底否定到对这一理论毫无保留的基本法观念的转型之上。在十月革命前,西方法律思想在俄国的传播是有派别的。针对沙皇政权的专制统治,当时存在两大派别的思想,一派是代表平民和无产者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俄国传播,另一派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律思想在俄罗斯传播。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法学和法律研究受政治制度导向的影响。否定、拒绝、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思想,甚至把在俄罗斯的外国学者和精英驱逐出境,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俄罗斯著名法学家马尔琴科教授在其《国家与法的理论》一书中写道:“如果说三权分立理论在前苏联文献中和现在的俄罗斯文献中得到过严肃认真的关注,那是非常牵强的。如果说在1985年春天(改革开始之前)曾经有学者研究过它,那也主要是从纯学术立场,或从批判的角度出发的。”(17)马尔琴科:《国家与法的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9页。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俄罗斯又重新启用一度被其否定的西方主流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甚至出现了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情况,西方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对俄罗斯的影响在现时期非常明显。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在法学理论的指导思想方面,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基本理论由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指导理论,转变为与其他理论学说并列或不被重视的理论。西方的社会契约论、社会功能说,以及社会民主主义在俄罗斯表现得很有市场,并把它作为西方社会能够战胜社会危机,使社会平稳前行的主要原因之一(18)张俊杰:《当代俄罗斯法学思潮》,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18页。。立法制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四)俄罗斯联邦立法制度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冲突
历史传统对俄罗斯政治制度演变有着重要的影响。俄罗斯自16世纪中期伊凡四世自称沙皇起,沙皇专制制度一直延续了300多年。由于漫长的专制时期和相对落后的国民经济,俄罗斯人自生的对于民主和法治的追求较之西欧、美国等地的人民明显乏力。俄罗斯是在苏联社会制度发生剧变的过程中诞生的,它经历过苏维埃时期,继承着沙皇俄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家的双重传统。在过渡时期,旧的立法制度被打破,新的立法制度尚未被充分建立起来。在立法机关无法有效行使自己职权的时候,更容易被专制政权所控制。
从历史上看,在俄罗斯悠久的专制政治传统中,议会从来没有真正发挥过像西方国家那样的作用。以国家杜马为例,国家杜马是沙皇俄国时期经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从1905年5月第一届国家杜马开幕到1917年二月革命为止,沙皇俄国共产生了四届国家杜马。十月革命胜利后,国家杜马这种议会形式被苏维埃制度所代替。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国家杜马,将其作为俄罗斯议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似之处在于,国家杜马的出现都是社会变革时期的产物,无论沙皇还是俄罗斯总统,都需要国家杜马维持他们的权威。国家杜马在立法实践中成为传统集权的一种附属。虽然俄罗斯具有西方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然而,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俄罗斯并没有西方的民主传统。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国家开展的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仍然是一种以高压和强制为基本特征的制度,中央集权化的官僚体制把整个社会牢牢地捆在了一起,这样的权力体制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层次都在产生崇拜和崇拜者。在权力的每一级,其最高领导者都会利用手里的集权制和等级制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势必会对立法制度造成影响,侵蚀民主立法制度成长的社会基础。
通过对俄罗斯联邦立法制度演进及其规律的认识,从侧面得到了一些启发,那就是我们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