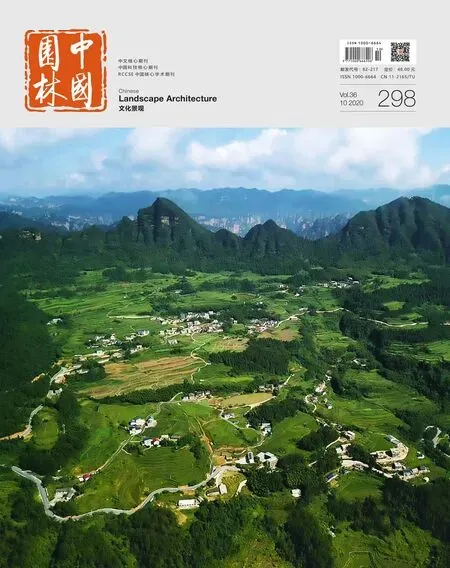文化景观保护的环境哲学溯源
韩 锋
1 生态文明视野下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保护国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全面促进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核心的“美丽中国”建设。“美丽中国”是对未来的理想和梦想,体现了中国改变当下境况的决心以及对未来目标和方向的决策。“美丽中国”以及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人类诗意栖息于大地的中国梦,是风景园林学科新时代的价值核心与目标引领。
2012年,中国提出“美丽中国”国策,时值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50%之后。有研究表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至50%左右时,是环境生态危机开始集中爆发的阶段[1]。中国也不例外,为30余年的高速工业化发展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水土污染、生态系统退化等各种环境问题集聚性爆发,人地关系面临空前危机和冲突。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中央要求转变环境价值观念,重建人地关系,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促进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全面形成,建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2018年3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统领山、海、林、田、湖各类国土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的自然资源部应运而生,全面开启了国土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及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中国要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光荣和危机中,走向生态文明,必须完成新型人地关系的重新建构。生态文明建设不是一场治理生态污染的“浅生态”运动,而是一场从根本上扭转自然价值观,重新确立人与自然关系的环境哲学运动,事关人类生存和生活方式、环境行为伦理以及可持续发展。
2 环境问题的根源和哲学思考
2.1 科学、技术与环境哲学
人类为工业化发展付出过惨重的环境代价。在1830—1860年间,英国成千上万人因泰晤士河的污染死于霍乱。其他重大公害事件,如1906年美国旧金山大地震及火灾事件,1943年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56年日本爆发“水俣病”(汞污染),1930年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2011年中国渤海湾石油泄漏事件,以及2013年上海黄浦江死猪事件等,均发生在经济发展至一定时期,突出反映了人类对自然资源掠夺性开发利用所带来的恶性后果以及所付出的环境代价。水火不容的人地关系,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健康和社会的持续发展,迫使人们对生活态度、生活生产方式以及环境公共政策进行反思。
环境问题,很容易让人寄希望于科学和技术的解决途径。土壤修复、水体治理、空气净化等,往往在环境危机爆发时成为最热门的科研、技术和产业领域。环境污染养活了一大批为治理污染而诞生的科研、技术及产业,但往往治标不治本,没有一个国家的环境污染是仅靠科学和技术能够解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出,脱离社会结构抽象地谈论技术与生态危机的关系容易落入技术决定论的陷阱[2]。是不是治理环境的科学和技术越先进,我们就可以制造更多的污染?答案显然不是这样。
较之表象的污染,环境问题提出了更基本的伦理和政治哲学问题,如人类的基本价值什么?我们的生活方式应该怎样?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如何?应该怎么与自然相处?等等。这些“如何生活、何种生活”的哲学和伦理问题,关乎生命价值和美丽中国的目标愿景,而科学和技术只是我们达到愿景目标的手段。环境伦理哲学要求我们从根源上剖析人类和自然环境间的道德关系、对自然的价值定位,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类对自然界的行为,评价价值观与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重建基于价值观的人地关系。环境政治哲学则要求我们洞悉公共环境政策背后的价值观,解释并论证所制定的环境政策,研究和评价环境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及后果[3]。
科学的途径基于事实现象,哲学的途径则基于本质根源。正如威尔·格兰特所说:“仅有科学而无哲学,仅有事实而无前景和价值,是不能使我们免于浩难和绝望的。科学给予我们知识,哲学才给予我们智慧。[4]”当然,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和评价也极大地受到科学的影响。应对环境问题的挑战,科学和伦理同样重要,没有伦理学的科学是盲目的,而没有科学的伦理学是空洞的。
2.2 环境哲学的5个核心问题
西方国家对于环境哲学的思考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科普作家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是环境保护运动的先河之作。书中首次揭露了美国农业、商界为追逐利润而滥用农药的事实,讲述了农药对于自然环境和人类的危害,描述了人类可能将面临一个没有鸟、蜜蜂和蝴蝶的寂静恐怖世界,引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环境哲学要求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既有哲学和科学进行深入的伦理反思,在哲学基点上实现革命性的转变, 确立自然的价值,建立对待自然的伦理态度和关于环境问题的世界观,进而指导和规范人类保护和修复自然的行动[5]。
关于环境问题的争论,极其纷杂。面对纷争,环境哲学关注的是纷争的根源,而不是急于着手去解决。只有从根源上洞察这些纷争的产生过程,才能厘清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环境哲学认为,纷争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各方所持的自然价值观不同,即自然观的差异。因此,自然究竟拥有什么样的价值成为环境伦理的核心问题。
围绕自然的价值判断,铂尔曼将当代环境伦理争论概括为以下5个问题核心[6]。
1)自然具有工具价值还是内在价值(非工具价值)?工具价值指某个物体因对人类有用而被赋予的价值,是人类达到自身目的的工具和手段。而内在价值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事物的价值,与它们对人类等其他目的和手段是否有用无关。
2)如果自然具有内在价值,那么价值的来源是什么? 谁创造了这些价值?价值主观主义者认为自然的内在价值是人创造的,与人的生活或特定的事物状态或品质相关联。价值客观主义者认为内在价值是客观存在的,等待着人们去认识和发现。
3)关于内在价值的对象定位。如果有内在价值,哪些对象具有内在价值? 单个的生命有机体?还是更抽象的关于质的多样性、丰富度、自然度或平衡性?内在价值是主观的还是客观存在的?
4)当感知的价值发生冲突时,谁来做伦理决策? 哪种价值更重要?
5)伦理一元论和伦理多元论。在地球庞大的伦理群体中,是否有可能达成统一的伦理原则?是否有适用于所有伦理问题的一致性原则?伦理是一元还是多元的?
以上5个核心问题的思考和争论,是环境伦理哲学各个流派确立自然价值的立足点。其中第一个核心问题,是环境伦理学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主义的分水岭。人类对自然的价值立场,往往与文化传统和科学认知密切相关。
2.3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在西方有着深厚哲学基础的,始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宗教传统,主导着西方传统伦理观点[5,7-8]。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具有理性的人类在自然界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具有比任何非人类事物更重大的内在价值。保护或促进人类利益至高无上,而非人类的自然世界被认为是人类的工具,只具有工具性价值。劳特利认为,根植于西方哲学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实质上是“人类沙文主义”,是导致自然毁灭和环境危机的根源,需要对西方传统哲学进行重大变革[9]。因此,对抗人类中心主义便成为西方环境哲学伦理的起点[10]。环境伦理在自然价值判断上对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提出了挑战。首先,它质疑人类相较于地球上其他物种的道德优越感。其次,从理论上探究和论证自然独立于人类的内在价值[7]。
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极其广泛,并已成为许多国际环境政策的基础。广为熟知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满足后代人的需求构成危害的发展”,未论及自然的任何价值及其需求。在环境伦理学视野下,这种表述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类物种的延续和福利,因而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政策产物[6]。2016年联合国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将自然价值保护与人类发展并置,将人类和自然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整体,关注人类和自然的共同福利,对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极大的扩展和深化。
非人类中心主义将环境危机的根源归咎于人类中心主义。基于生态中心论的整体主义,把人类道德关怀和权利主体范围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利奥波特的大地伦理学认为,人是大地共同体的普通成员和公民,需要尊重共同体以及其他伙伴[11]。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从价值上确立了自然所具有的客观内在价值,认为生态系统所具有的整体系统价值超越其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之和,人类对整体生态系统负有道德义务[12]。深生态学的创始人挪威哲学家奈斯认为,追究环境危机问题的深度体现了深、浅生态学的区别。浅生态关注技术、人口、消费所带来的污染和资源枯竭,关心的是发达国家公民的健康和富裕,治标不治本;深生态坚持对环境问题进行深层追问,将环境问题归结为人类的文化危机和生存危机,提出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转变人对自然的态度,人类必须在价值观、世界观、社会观、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上做出改变,是一场事关价值观的政治和社会革命[13]。深生态吸收了中国道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及佛教的生态智慧等东方哲学思想,把人与自然视作一个整体[9]。在这个意义上,与中国传统主体精神与客体世界的“主客合一”“天人合一”价值观,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激进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包括深生态的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原则,主张赋予自然主体性,要求人类通过自我精神和智慧的超越,主动降低人的地位,与其他非人类的利益平等,从本质上否认人作为自然人对环境的主动性和人类自身的内在价值。
马克思则辩证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反对将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割裂。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坚持以人为本,但与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自然是人类工具的观点(即强式人类中心主义)不同。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既是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生长的基础,也是衡量人类行为的尺度,在以人为本的价值基础上强调自然的重要作用,体现的是一种相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14]。马克思强调“自然界优先地位”,自然界先于人类历史存在;人类依赖于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提供人类生存、享受和发展的最基础资料[15],劳动和实践是人与自然的中介,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是连接双方的纽带[16]。其核心生态理念是“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同时,应注意尽量克服盲目性、自私性;以人为本与尊重自然相统一;人类应追求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17]。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属于弱式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反对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视为人类工具、凌驾于自然的价值观,但同时认为人类不可能避免以人类为中心,不依赖于人类的价值观(或出发点)是不存在的,自然的价值不可避免地要通过文化的透镜来审视[6]。弱式人类中心主义还指出,人类赋予自然的审美和精神价值,并不是自然所固有的,而是人类价值的转移和人文感知,是自然为人类提供的美学和精神的工具性价值,这种价值同样是人类中心主义的[6,18]。弱式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自然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社会和文化的建构过程[6,19]。
3 环境哲学的发展与文化景观保护的兴起
厘清以上关于自然的伦理哲学、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的价值观,对于理解和应用环境伦理,洞悉与自然相关的保护政策背后的价值观及社会驱动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环境哲学的发展及影响来梳理国际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历程,尤其是世界遗产的历程,其轨迹十分清晰,可以总结为以下4个阶段。
3.1 荒野保护——西方环境运动的兴起(20世纪60年代中—70年代末)
这一时期也是环境哲学的初始阶段。环境伦理立足于对传统西方文化的反省,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转向自然保护,环境运动随之兴起。此时的哲学思想,集中阐述自然独立于人类的内在固有价值。环境主义者和生态主义者认为人与自然是对立的,只有让人类远离自然,自然的价值才能得以保持。在此影响下,20世纪70年代中出现了动物权利、动物解放、解放水库等运动。以美国为主导的国家公园、荒野保护,倡导自然至上、“纯净的”自然保护,将人类排斥于自然之外,一时成为全球性的自然保护运动和保护模式,成为全球化过程中最大的文化输出。在此期间,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非洲诸多国家大量原住民因聚居地被划为荒野保护区而被驱赶[20-21]。然而,荒野保护模式,不但没有在本质上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反而使西方哲学从人类至上的极端走向了自然至上的极端,再次引发了人与自然的激烈对抗,造成了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对峙。这一阶段也是世界遗产诞生之时。正因为如此,《世界遗产公约》中自然和文化的分离具有非常鲜明的西方文化特征[22-23]。
3.2 文化与荒野的抗争——自然价值的社会与文化属性(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是文化与自然的抗争期,文化为在自然中的生存而战,为人类进化史而战。保护地荒野运动使大批以自然为家的原住民失去家园,流离失所,生活无依,全球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不但引起严峻的社会问题,而且引发文化危机。80年代有诸多的哲学批评和著作,大声疾呼文化和人权的平等。
这期间的环境哲学致力于深究第二和第三个核心价值问题,即自然价值及其产生、建构的认知,在开放的文化框架体系中,对于价值、意义确立过程中的主客观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并将伦理与政治学相关联,土著民族、东方思想包括中国道家思想都被纳入考察。在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阵营中,细分了各自流派,认识了自然价值及自然观的文化多样性,打下了保护自然的精神价值及与自然关联的文化多样性价值的基础。自然意义的赋予者,原住民社区及其价值逐步得到认知。自然开始回归社会,并承认自然价值具有社会建构性。
荒野概念则受到了来自文化史和进化论的批判。一些环境伦理学家认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荒野将人类文化排除在自然之外是错误的[13,24-27]。凯利考特认为西方关于荒野的观念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男性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工具[27]。人与自然分离的荒野,违背了进化论,荒野的保护意味着对自然演进及进化史的否定。荒野在文化生态学上的“定格”是以白人人种为中心的,它基于这样一种谬论:当欧洲人来到新大陆时,那里正处于“无人的荒野状态”,而事实上这些所谓的“荒野”是印第安人的故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荒野”概念不仅是文化的,而且是文化沙文主义的[24]。凯利考特认为“荒野”一词,对于非英语国家来说是“怪异的”,在中国等历史悠久的国家里没有“荒野”一词及其文化意象。他引用孔子的话,主张“名正才能言顺”,呼吁重新思考“荒野”这个名词的正确用法[27]。铂尔曼指出,自然保护的关键问题在于厘清人类是否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与自然是否是分离的,自然是否具有独立于人的内在价值,以及我们应该保护的是荒野(wilderness,无人的自然)还是自然的野性(wild nature)[6,10]?
此阶段,以IUCN为首的主张荒野和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国际组织,被迫与各国原住民团体进行协商谈判。自然保护运动走向与文化的妥协。在世界遗产领域,乡村景观、反“荒野”成为“去欧洲价值中心”的主战场。英国湖区申遗以及中国泰山等首次登录世界遗产,为世界遗产带来了多文化、社区、普通景观以及“天人合一”东方哲学等新的价值。
3.3 荒野的衰落和文化景观的兴起——自然价值走向文化多元(20世纪90年代初—2010年)
这一时期是环境伦理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环境保护运动也基本与此同步。此时的环境伦理吸引了全世界更多国家更多文化的关注,并加入了讨论。文化多样性的视角,在环境伦理的5个中心议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各族群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哲学和宗教信仰不同,自然的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认定及其载体,呈现出高度的主观性,因此不存在伦理一元论的可能性。环境伦理的多元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密切相关。在国际实践框架中,首先必须承认文化多样性,承认自然观的多样性,才有可能搭建自然和文化保护的平台。
20世纪80年代哲学价值观的转变,促成了90年代国际保护实践的重大变化。纯净的荒野式保护历程告诉了世界,荒野式的、把自然作为孤岛一样隔绝于人类的模式是行不通的,文化保护对象也不仅仅是精英的、历史性的,自然和文化保护迫切需要一套能够连接各族文化、全面系统的概念、架构和机制。并逐渐意识到文化族群对于自然资源的管理具有高度的生态和社会智慧,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和实践中产生的。
这些环境哲学的思考与转向与文化景观理论不谋而合。在文化景观领域中,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及其结果一直是其核心[22-23,28]。20世纪80年代的新文化地理学认为文化不是抽象的存在,文化是动态的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结果,具体存在于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之中,深刻地体现了文化景观的政治化特征。景观是“是文化的意象”[29],是“看的方式”而不是“所见的”外在客观情景,其意义和形态受到强烈的主观意识的影响,带有政治性和社会性,直指文化内涵的焦点——价值观。景观以“文本”的方式记录了这种意识和文化,具有强烈的社会象征意义以及文化多样性[30]。
在此背景下,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旗舰项目世界遗产文化景观诞生,成为连接自然和文化的桥梁,填补了自然保护与文化保护的裂痕[23]。20世纪90年代的IUCN主动实现了文化转向,强调自然遗产保护不是强制实行的与社会脱节的“孤岛”。1994年,IUCN设立第V类陆地/海洋景观保护区,保护具有环境和文化价值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地区,并成为IUCN最前沿的实践示范阵地[31-32]。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保护开始走向实质性的融合。
3.4 自然文化之旅——自然与文化携手同行(2010年至今)
从哲学上和实践上看第4个阶段是第三阶段的深化和延续。在哲学和实践上,自然和文化从两分法走向了更加多元、融合、整体的深化认识和实践。在环境哲学思考的终极意义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新一轮的共同体话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于2010年启动了生物与文化多样性10年联合项目,201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17个目标成为中心议题。在自然和文化保护领域,2013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两大组织携手推进融合自然和文化的“连接实践项目”(Connecting Practice Project)和“自然文化之旅”(Naturecultures Journey)。自然与文化的融合是一场填补西方自然与文化的裂痕、架构自然与文化价值的认知革命,是西方文化向东方文化的伟大转向,是西方二元文化向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转向,对于西方主导的国际遗产保护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旅程,至今仍在行进之中[22]。
在这一时期,国际遗产保护聚焦4个重点:
1)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同样重要,是人类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
2)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高度正相关,承认文化族群在创造和管理生态物种上具有重要的贡献,大力推进自然保护地基于社区传统智慧的自然资源保护和管理模式;
3)乡村景观包含的自然与文化价值正式进入遗产保护领域;
4)遗产保护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
4 中国的思考——建立基于“天人合一”环境哲学观的国家文化景观保护体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类发展的理想状态。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建立‘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及明白和合理的关系’”,才能最终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33]。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中国,为争取发展权利,消除贫困、保护自然环境,不断实践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运用中国智慧,探索中国之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于生态文明“六项原则”建构的2个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以及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正是在这个基点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创新。
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五位一体”,“美丽中国”“中国梦”是马克思理想社会制度下“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重要表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正在进行的是环境哲学深生态主义者虽然意识到但无力实现的、关于环境哲学价值的政治与社会革命,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和生态主义相结合的伟大理论与实践创新。
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完整而系统地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自然观、生态政治观、绿色发展观、生态权益观,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34],是建立2个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纲领,是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本道路,也是建立中国自然和文化保护体系的基本方针。
中国保护地体系建设,应从自然史与人类史辩证统一的角度保护自然和文化的价值,重视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价值领域,充分鉴别自然的科学价值以及与自然相关联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对照IUCN国际保护地体系分类,对以自然价值为代表的自然保护区、以人与自然和谐作用价值为代表的文化景观区以及以人类利用自然为代表的可持续发展区进行完整而系统的分类保护。中华民族参天地赞化育,农业文明古老灿烂,“天人合一”哲学思想渊源流长。中国的风景名胜区、乡村景观、园林营建等是东方和谐人地关系哲学思想的实践典范,高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宇宙观、自然观、生活观以及对自然资源、对土地的智慧管理。遗憾的是,在中国正在进行的保护地体系建设中,此类融合自然与文化、最具有中国环境哲学思想及国家文化身份代表性的文化景观价值,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并加以积极的保护和发展。本文呼吁在国家保护地体系中,设立文化景观保护类别,进行分类保护,对接国际保护地第V类“海洋/陆地景观保护区,使之成为中国和国际自然和文化保护体系的重要组织部分。
中国保护地体系建设,要吸取西方走过的自然与文化分离的弯路教训,尤其对于他国过往的自然保护概念及体系,在吸收其科学合理性的同时,需要进行谨慎的政治哲学和文化哲学甄别,不可照搬照抄。国家保护地体系建设事关国家历史与未来,要坚持文化自信,坚持中国道路,增强中国环境哲学的主体性自觉,关注中国哲学的独特价值及普遍意义,建构中国特色的自然保护哲学和社会科学。只有在完整识别自然和文化价值基础上,各项环境政策才有可能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促进社会发展,才不会陷入技术性的讨论而失去终极的价值目标,和谐人地关系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愿景才能达成。
5 结语
任何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都无法脱离文化意识形态,自然保护也不例外。“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35]。中国在处理新冠疫情上,充分展示了制度和文化的优越性。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景观传统智慧,应该在自然保护体系建设中发挥作用,保护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文化基因和优秀传统,保障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空间。在国际遗产保护的“自然文化之旅”中,中国应该起到核心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