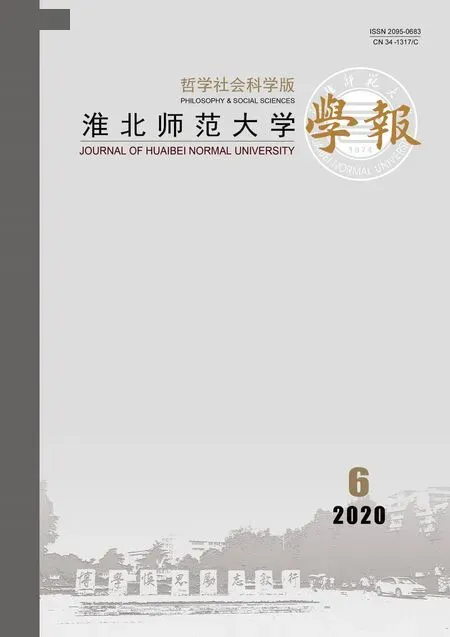《论语》中道德的三个超道德维度
陈 杰
(安徽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蚌埠233030)
关于《论语》中的道德,许多中国学人对德国思想家黑格尔的一段评论往往耳熟能详。他说,《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1]后来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重弹了这个论调,他说,“儒教纯粹是俗世内部的(innerweltlich)一种俗人道德(Laiensittlichkeit)……儒教所要求的是对俗世及其秩序与习俗的适应,归根结底,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2]针对这种观点,沈清松犀利地评论说:黑格尔对孔子的道德观“完全缺乏认识,只用自己的哲学系统和欧洲中心观点来生搬硬套”[3]。苏国勋则指出:“韦伯的《儒教与道教》基本上是因循黑格尔的看法……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论取向”[4]。在上述批评的基础上,本文力图立足于《论语》文本资料从正面证明《论语》中论述的道德不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只是一种“常识道德”,也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仅是俗世内部的一种“俗人道德”,它更蕴涵着人生的意义、支撑着政治的根基并寄托着人生的终极关怀。本文把这三个方面称为儒家道德的三个超道德维度。
一、超道德维度之一:成就人生意义
在西方,总体而言,道德哲学是以知识为中心展开的、强调理智思辨的学问。它虽然有着清晰的概念、严密的逻辑、精巧的结构和完整的体系,但往往与人的德性实践没有多大关系。与之相比,以《论语》为代表的中国儒家道德思想则是贴切于实际生活的,有一种提振和安顿人心的力量。它无意构建周密的知识体系,而着重于解决人格提升和人生意义问题,可谓是一种生命的学问。即以《论语》来说,它给人们提供了一套圆融自洽的价值系统。这套价值系统指明了人之为人所应具备的条件和资格,力图将人从“小人”注重功利的自然生命中超拔出来,使之成为道德高尚的君子,过上有尊严、有意义的真正“人”的生活。在《论语》的启迪下,不仅无数古代中国人活出了人生的意义,甚至有些现代西方人也获得了深刻的人生感悟。比如俄国学者鲁宾就说他从《论语》中为自己的生命找到了重要意义[5]。
在《论语》中,“仁”是最重要的道德概念,共出现了一百余次。围绕“仁”,还有礼、义、道、德等。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礼”贯穿起来:礼是外在规范,仁是礼的精神,义是礼的本质,道是礼的来源,德是礼的内化。它们共同代表了儒家崇尚的道德品格、标准和理想。践仁、循礼、行义、履道、修德,是儒家的人生主题、生活重心和自觉追求。儒家的志向不是“谋食”“干禄”“怀居”,而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论语·述而》)。让孔子忧虑的不是“无位”“贫与贱”“恶衣恶食”“人之不己知”,而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论语·述而》)。孔子的全幅生命不是浪费在“饱食终日”“言不及义”上,而是贯注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上。分而言之,关于践仁,孔子要求弟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曾子也提出要“仁以为己任”且为之“死而后已”(《论语·泰伯》)。关于循礼,孔子教导弟子“约之以礼”“克己复礼”,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关于行义,孔子要求人们“义之与比”(《论语·里仁》)、“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关于履道,孔子力主“信道”“忧道”“谋道”“弘道”。关于修德,孔子倡导“知德”“好德”“尚德”“崇德”“执德”。
践仁、循礼、行义、履道、修德的目的和后果不是斵丧人性,而是振拔生命、提升人格,使人成为堂堂正正的君子。“儒家认为人是一种依赖他人的关系性的存在”[6],而不是孤立、封闭、自利、自足的个体。孔子所谓“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论语·微子》)说的就是人需要生活在社会关系之中,并做到“和而不同”“群而不党”和“周而不比”。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君子。在西方,无论对于中古的基督徒而言还是对于近代以来的个人主义者而言,只有摆脱各种世俗关系的拖累或羁绊,才能更好地接近上帝或成就自己。而对于中国儒者而言,只有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适当关系中,才能真正完成自我,获得心灵安顿。而仁、礼、义、道、德正是构建、协调和完善这些人际关系的动力、指南和原则。它们的的本质指向和总体要求就是爱人。例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君子学道则爱人”(《论语·阳货》)等。这种爱是分差等的,由近及远不断向外扩展:从“入则孝出则悌”(《论语·学而》)开始,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再到“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学而》),最后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父子亲、长幼和、朋友信、君臣正、百姓安的社会格局。在这种格局中,不仅人人各得其所,而且相互之间建立了了声息相通、休戚与共的紧密关系,形成了“一啼一笑,彼此相和答;一痛一痒,彼此相体念”[7]的深厚情谊。曾皙曾描绘了他理想中的生活画面:“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引起了孔子的由衷赞叹。这一美好的生活画面可以说正是上述社会格局的一个缩影。
只有通过道德践履,实现了这种社会格局,建立起这种和谐的关系和深厚的情谊,个人才算真正完成了自己。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牟宗三说儒家“道德并不是来拘束人的,道德是来开放人、来成全人的。”[8]杜维明也指出,“依循道既不是抛弃人性也不是违背人性,而是意味着人性的臻于完善。”[9]不仅如此,也只有身处这种关系和情谊中,才能获得真正的人生之乐。即使在天下无道、社会离散、人我暌违、居穷处困之时,君子仍然深信他们对道义的坚守终将产生社会和谐的效果,因而有着永恒的价值,所以仍然能够安仁固穷、不忧不惧、坦坦荡荡、乐在其中并不改其乐: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
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正是在上述人格的完善过程与安乐坦荡的生活状态中,人生的意义得以充分展现出来。不仅如此,孔子还表示“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这表明,君子对道义的坚守实际上是在履行上天赋予的职责,由此他们可以上达天命,获得上天的肯定和加持。所以,由道德践履所达致的人生意义不是悬浮无根、变幻无常的,而是打上了超越或神圣的色彩,获得了终极的保证。也正因为如此,道德践履才真正成为儒家安身立命之所在。
二、超道德维度之二:奠立政治根基
在西方古希腊时期,虽然相对于城邦政治而言道德是从属性的东西,但两者毕竟是一气贯通、紧密相连的。到了近代,意大利学者马基雅维利首先将道德从政治领域中剥离出去,把政治与道德分割了开来。这被认为建立了独立的政治学科,开创了政治学近代化之路。直到现在,西方主流政治学仍然秉持价值中立原则,强调权利先于善,主张政府在实质性道德问题上保持沉默。虽然这种把政治和道德割裂开来的做法已经导致“公共商谈日益倾心注目于各种花边新闻和‘调侃秀’所提供的丑闻、刺激性绯闻和忏悔故事,最后连主流媒体也掺乎其中”[10],但是,这种将政治、道德二分的观念至今没有受到根本挑战。与西方这种观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传统儒家从来不把政治视为道德真空中的事务,从来不曾把政治与道德隔离开来。“内圣外王”是儒家的基本政治主张。“内圣”意味着修身,“外王”意味着从政或为政,“内圣外王”则意味着:道德是政治的前提、基础和根源,而政治则是道德的延伸、功效和归宿。可以看出,“‘内圣外王之道’所重在‘圣’,即把德性修养放在治国平天下之首位,这自是儒家哲学之特点。”[11]儒家的这种观念在《论语》中已得到明确阐述。
孔子指出,“政者,正也”(《论语·颜渊》);“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显然,己不正,则不能正人。没有“正”身的努力,也就没有政“治”的实践。离开了道德,政治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类社会就会沦落为邪恶的所在,为欺骗、偷盗、杀戮、战乱等种种不义所主宰。当然,离开了政治,道德也无从表现和落实。孔子之所以不遗余力地称颂尧、舜、禹等古代圣王,就是因为他们几乎完美地体现了儒家这种先正己后治人的内圣外王理想。
在《论语》中,为政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为政是一种职位活动,即获得或拥有特定政治职位的官员、贵族或君主实施的统治和管理行为。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及“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指称的就是这种狭义的为政。广义的为政是指任何人都可进行的具有政治影响或效果的活动。
对于狭义的为政而言,修身是为政的前提条件,亦即一个人必须先具备相应的道德素养才能有资格承担政治职责。有德才能有位,有位必先有德。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亦即“必学之已成,然后可仕以行其学”[12]。由于“孔子所说的学习之道,是一种修身之道”[13],所以,学而后仕意味着只有先具备一定程度的道德素养,才可以走上仕途。孔子表示:“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我从先进”。(《论语·先进》)这是说,先学习礼乐后做官的人是贫贱之人,先做官后学习礼乐的人是贵族子弟,而孔子赞成选用前者。所谓“立于礼、成于乐”,礼乐实为成德之途径。因此这段话表达的也是“以德取位”的主张。而在德性修养未达到从政要求时,就应暂缓取位为官。孔子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论语·泰伯》)这是孔子教导门徒:“学”没达到一定程度,就别要急着做官。因此,当子张来学干禄时,孔子教导他“多闻阙疑”“多见阙殆”并谨言慎行。如此,则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出于同样的道理,当孔子让漆雕开出仕时,漆雕开表示对此还没有充分信心,孔子流露出喜悦和赞许的神态。相反,孔子对子路使子羔担任费宰很不满,因为他认为子羔还小,不具备足够的道德素养和从政经验,让他为官只会害了他。(《论语·先进》)对于臧文仲不举用柳下惠,孔子也进行了谴责,认为他知贤不举,于德有亏,只能算是“窃位者”。(《论语·卫灵公》)如果德性不足而占据要津,就会导致不良后果。冉有德不胜才,而充任季氏宰,结果不但没能阻止“季氏旅于泰山”的僭越行为(《论语·八佾》),而且在季氏富于周公的情况下“为之聚敛而附益之”(《论语·先进》)。孔子之时,之所以“天下之无道也久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从政者在孔子看来都是“斗筲之人”,在德性修养上没有可取之处。(《论语·子路》)后来,《周易·系辞》告诫:“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周易·系辞下》,意即德薄者拥有高位,很少有不遭受灾祸的);孟子也强调“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都延续和发挥了《论语》的这种观念。
对于广义的为政而言,修身与为政、内圣与外王没有先后之分,而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不过,虽然从实践上看,修身与为政、内圣与外王不能截然分开,但从逻辑上说,修身和内圣仍然是为政和外王的基础。萧公权指出:“全部之社会及政治生活,自孔子视之,实为表现仁行之场地……故就修养言,仁为私人道德。就实践言,仁又为社会伦理与政治原则。孔子言仁,实已冶道德、人伦、政治于一炉,致人、己、家、国于一贯。”[14]这里,“仁”可视为道德之代称。可以说,践行道德的过程也就是治国理政的过程;反过来,治国理政的过程同样是践行道德的过程。这既适用于没有官职的“小人”,也适用于拥有官职的“君子”或“大人”。就前者而言,修身就是为政;就后者而言,为政就是修身。拿无职无位者来说,有人问孔子为何不从政,孔子回答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意思是,向父母尽孝、对兄弟友善等道德实践本身就是为政,何必非得做官才叫为政呢!拿有国有家者来说,所谓“为政以德”,可以理解为,为政就是从事道德实践,而这种实践又会带来“安人”“安天下”的政治效果。更具体地说,从政者的职责和活动主要不是掌握某种技能、实施某种政策、进行某种技术活动,而是“修文德”(《论语·季氏》)、“恭己正南面”(《论语·卫灵公》)、“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以及“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这样做的结果自然就是“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也就是“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当然,像耕稼、织造、冶炼、水利建设、道路维修、天文观测等等技术活动也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们自有“民”或“有司”等专门人员从事和办理,而且这些活动的开展要置于大人、君子的道德监督和统领之下。
只有在道德被用来支撑政治根基并指导政治实践时,人生意义才能从中显现出来。可以说,道德的政治效果是人生意义的载体。当道德产生的政治效果和人生意义不断向上攀升时,道德就实现了超越,成为终极关怀之所在。
三、超道德维度之三:充任终极关怀
关于儒学是否是宗教,学界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若按照西方一神教的狭义模式观察,儒学当然不是宗教。如果像美国学者蒂里希那样,将宗教定义为一种终极关怀[15],那么也可视儒学为宗教。因为,不可否认,儒学有自己的终极关怀。终极关怀是什么?是对能超出人生有限性、赋予生命以某种永恒和终极价值的东西的信仰和归依。可以说,几乎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终极关怀,区别在于有着什么样的终极关怀。如果说希腊文明的终极关怀是运用理性,基督教文明的终极关怀是皈依上帝,印度文明的终极关怀寻求解脱,那么儒家文明的终极关怀就是践履道德。[16]这一点已在《论语》中得到初步阐发。
孔子强调:“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所有这些凸显的都是人的德性力量及其带来的人的尊严。这是儒家被称为人文主义的原因。但如果仅仅高扬人性而否认天的存在,儒家道德就纯粹是世俗道德,也就担当不起终极关怀的重任,因为人毕竟是有限的存在。如果贬抑人而肯定和褒扬天,道德修行就无足轻重,其与终极关怀的关联也无从建立。道德之所以能够成为儒家的终极关怀,是因为儒家既肯定人具有天所赋予的神圣性潜质,又强调人自身的力量,认为通过道德修养,人就可以体现这种神圣性,上达天道、与天合德。
儒家不像西方传统的基督教那样,高扬神性而贬低人性;也不像西方近代以来的人文主义那样,凸显人性而摒弃神性,而是将人、天贯通,既承认天对人的化生作用与天道对人道的贯注功能,也认可人的力量和尊严,肯定人能够上达和遥契天道。在这里,天与人是一种相互会通、上下联动关系。如果说西方文化的特点是神、人隔绝的话,那么儒家文化的特点就是天、人合一。不过,在天人关系中,儒家是有侧重的,它不以天为中心而以人为中心,强调的不是天的惩恶扬善、无所不能,而是人的道德实践和修己功夫。儒学的重点始终落在人如何成德以体现天道上。[17]的确,孔子承认天及其作用。他有两段自白:“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在此,孔子自承其拥有的“德”“道”(“文不在兹乎”中的“文”即是“道”,“兹”指孔子自己)乃天之所赋,从而肯定了天对人、天道对人道的根源性意义。但在对天及天道做了一般性肯定以后,儒家强调的重点转向人及人道。德虽由天生,但人又不可不“执德”“崇德”,否则,“焉能为有,焉能为无?”(《论语·子张》)天道既已下贯,但由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那么弘道之责任就应由人来承担,否则,天道就得不到证立和彰显。所谓“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没有下学,何以上达?孔子从十五志于学至五十而始知天命,可见“下学”功夫之深。后来《中庸》提出“修身而道立”“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可谓与此一脉相承。这样,通过人的道德努力,“作为人格神之超越的‘天’或‘上帝’,开始内在于人的本性及其道德实践之中”[18],人崇德弘道的实践由此成为关键所在。只有努力从事道德践履,才能真正上达和摄取天道,使自己的生命与天融合为一,趋向无限,获得永恒。否则,就会远离天道,日趋于卑污和渺小。由此,道德成为了儒家、乃至古代中国人的终极关怀。
《论语》中的以下篇章都表明,孔子看重的是人如何成德以契合天道: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论语·述而》)。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论语·子罕》)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说明如果没有相应的道德实践,像基督徒那样祷告、忏悔都是没用的,这就是他拒绝子路为他祷告的原因(“丘之祷久矣”是他拒绝子路的婉辞)。关键在于以诚敬的态度“事人”“则天”“务民之义”“允执其中”,尽到自己该尽的道德责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上契天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超越世俗,获得永恒。否则,违德悖礼,罪至欺天,不但不能上契天道,反而会使自己远离天道,最终被天所抛弃。这正是孔子极度担忧和警惧的,这也是他病间发现子路行诈(“子路使门人为臣”)后严厉批评他(“久矣哉,由之行诈也!”)的原因。也正是因为“儒家强调通过德性生命的践行,最终达到与生生和谐的天地精神的遥契与贯通”[19],所以他们才如此重视道德践履:
子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论语·里仁》)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仁,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孔子及其弟子为什么那么看重仁,以至于达到“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和“死而后已”的程度?为什么闻了道可以死而无憾?为什么为了仁可以献出生命?实际上,从“杀身以成仁”“仁者必有勇”“仁者乐山”“仁者安仁”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孔子所讲的仁“实际已超过伦常道德,成为天地境界的审美—宗教感”,给了仁者“与天地万物平宁愉悦地合为一体”的快乐,并促成了与西方“罪感文化”、日本“耻感文化”不同的独特“乐感文化”。[20]这种快乐超越了浮泛无根、变幻无常的世俗之乐,而达到了“与天地参”的本体论层次,因而成为仁者安身立命、终极关怀之所在。
可见,《论语》中的终极关怀采用了一种内向超越的形态,与基督教所持的外向超越形态的终极关怀不同。外向超越,是把终极信仰完全寄托于高高在上、全知全能的上帝那里,而人只能匍匐在上帝的脚下,神、人之间永远不能相交。而内向超越则认为人道可以体现天道,只要人“觉解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分子,而且是宇宙的一分子”[21]682,“不但应在社会中,堂堂地做一个人;亦应于宇宙间,堂堂地做一个人”[21]604,他就可以从“道德境界”上升到“天地境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冯友兰指出“道德底事,又有一种超道德底意义”[21]683。
结语
按照现行通常的理解,道德只是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而在《论语》中,道德不仅仅是行为规范,它还蕴含着人生意义、支撑着政治根基并寄托着终极关怀。这三个方面可以称为儒家道德的三个超道德维度。它们是紧密相连、互相支撑的。道德所成就的人生意义只有在道德的政治效果中才能体现。放弃政治责任和社会联系,人不能独善其身。两者共同构成了儒家道德的世俗功用,充任终极关怀则透显了儒家道德的超越境界或神圣性质。这种超越境界需要从世俗功用中表现出来,并为这种世俗功用提供了终极根据和可靠保证。“所谓平凡里面有神圣,神圣里面也有平凡”[22],儒家不追求彼岸、天国,而是力求在这个世界中转化和提升这个世界,于有限中寓无限,即入世而求超脱。没有世俗功用的支撑,儒家道德的终极关怀就会悬空失灵;没有超越性或神圣性的提升和保证,儒家道德的世俗功用就会陷入卑污和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