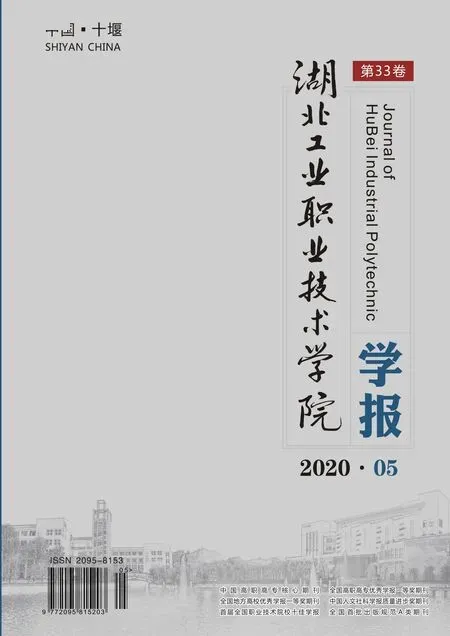静念园林好,俯仰终宇宙
——陶渊明士子精神之内涵
刘 芳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陶渊明辞官后回归田园,躬耕自资做了个普通的农民,但他又不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真正的农民对土地的情感和认知是深沉单一的,脚下的土地是赖以生存的食粮,不倾尽全力耕作就得忍受饥寒甚至危及生命,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的视线只有脚下的土地,而诗人陶渊明,虽然长久地伫立在土地上,但目光却投向了更广阔的天地,那里有社稷、有朝纲、有心灵、有理想。他就在这长久的守着土地而望着远方的生命里,逐渐成熟了思想、安顿了心灵、超越了自我,他把士子的精神扎根在这里完成了自己人生的吟唱。
一、归去来兮,守望家国
“富贵非我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1]晋安帝义熙元年,陶渊明辞彭泽令归隐田园,不久,写下了这归隐不仕的宣言。
关于诗人的辞归之因,说法不一,有自言之“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1],“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1],有他论之“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2]。”纵观陶渊明的从政生涯,他最后一次辞归发生在晋宋易代、政体转变之际,他作为寒庶士人,虽上有勋旧家世,却难以趋附新的政体。这其中既有陶渊明基于家族先祖为东晋开国勋臣的立场,在政治上于晋室仍有忠诚之义,也有儒学传承中入世精神的影响,人生是要有一番作为的,虽在乱世也当“择木而栖”,而新政权之刘裕显然是不合格的对象了,“在信仰和思想方面,刘裕出身行伍,不存在任何深刻的教养、传统和认同;刘裕也没有任何门阀社会的家族背景,其崛起完全出自武力及功业[3]。”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4]。”又说:“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4]。” 从汉魏到两晋南北朝,无疑是失道无道的黑暗时代,“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5],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虚无”[1],“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1], 无不充满了人生无常的悲叹,“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最能激动人心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阮籍这样,陶渊明也是这样,每个大家,无不如此[6]。” 不过,陶渊明的这种感叹“并没有那种后期封建社会士大夫对整个人生社会的空漠之感,相反,他对人生、生活、社会仍有很高的兴致[7]。”因为,陶渊明选择的是一条并不安稳的归隐之路——“田隐”,他与那些以隐待仕的名士是不同的,归隐田园不是他用来与社会抗衡的手段,而是他主动选择俗世生活,这样的隐居生活并不是远离世间,不问世事的,相反,他更关心国民的生计与天下的安宁,他的关心更加深刻,更加智慧——他在贫瘠的土地里埋首劳作,手里把着锄头,胸中装着社稷。宁静的田园使诗人得以冷静地反思与展望,他思考得更长远,那表明上平静淡泊的隐逸生活,实在是被我们误读了太久,无数个孤寂的日夜里,诗人的笔端倾泻下的不仅有静美无言的田园,还有睥睨王侯的骄傲,亦有猛志常存的刚健,也有桃源理想愿景的构建……
如面对刘裕篡权的黑暗现实,陶渊明把愤怒的指摘,化为“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1]” 的沉郁之言,汤汉《陶靖节先生诗注》曰:“谓恭帝禅宋也。裕既建国,晋帝以天下让,而又不免于弑,此所以流泪中叹,夜耿耿而达曙也[8]。” 易代之际,一介文士焉能作壁上观?诗人既不能忘怀现实,又不忍直视现实,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态度要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9]。” 诗人用冷眼旁观的热心肠对社会的黑暗不公发出了含蓄而深刻的呐喊。
当然,对人们良善的本性,平等的愿景也要小心守护,所以,诗人在桃花源里幻化出的那一群先民之后,是那么的可爱、淳朴,“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1], “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1],他们不排斥外人,尽心热情友好地对待,谦逊谨慎地保护住地,努力保持这自给自足的生活画卷。
陶渊明把传统文人的家国理想扩充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中,将 “有志不获骋”[1]的刚强精神转化为“俯仰终宇宙”[1]的淡远情志,在躬耕田园的守望中,诗人的内心不再是苦苦的挣扎或激烈的抗争,而是归于朴实和平静,“无论人生感叹或政治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对农居生活的质朴爱恋中得到了安息[7]。” 他用自己的生活实践提供了一种更加长久地持守家国情怀的可能,使后世文人频频回望。
二、安贫乐道,贫士恒心
我们常说陶渊明安贫乐道,安于贫穷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境况是难以想象的,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里,贫穷的潜台词往往是愚笨、懒惰、不思进取,身陷贫穷却不努力改变现状,是被耻笑的消极人生。但陶渊明似乎并不在意贫穷的生活现状,他仍然努力地躬耕田园,早出晚归,他自嘲辛勤劳作仍“草盛豆苗稀”[1],他因断炊而不得不乞食,他的农耕生活难以维系正常所需,温饱难继,若说头几年的家有奴仆、尚有良田还能让诗人于农事中抽身出来自味田园之趣,后来的房屋烧毁,幼子夭亡,收成锐减必然迫使诗人亲身锄田,而劳作意味着无尽的辛劳和不对等的收成,意味着每日从田间回到陋舍,必须面对的是破败的家庭境况,“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1]。” 在真实的贫穷面前,诗人该如何自守?
清代温汝能说:“渊明一生,得力全在‘固穷’二字,固则为君子,滥则为小人[10]。”固守贫穷,在贫贱穷困中不移其志,不坠其节,不动其心,不失其正,是陶渊明在躬耕田园中重要的精神支柱。
《论语·学而》云:“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4]从“贫而无谄”到“贫而乐”“富而无骄”到“富而好礼”,是人性的不同阶段,也是人生的不同境界,这种境界的提升需要回到自己身上找答案。虽贫穷,但不会因此低下头颅去逢迎他人,这是一种不随波逐流的清高,可取但是消极;虽贫穷,但能保持乐观的心态,不改变快乐的心志,平静祥和,可贵而且积极。而富而好礼,更突出了孔子对“礼”的内核追求,这是超然物外,荣辱不惊的坦然与平静,是内心更彻底的精神认同。
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4]陶渊明一开始的田产宅地僮仆或许可以称得上一定意义上的“恒产”,但这“恒产”很快就丧失了,其诗文里也有物质损毁的痛惜:“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令人悲叹,但诗人却少有痛悔之心,在越来越窘困的生活状态下陶渊明仍然坚持了他的操守,他的人格,他时刻都在提醒自己,虽然贫穷,但不能丢掉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底色,这个底色便是士子的恒心,是“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1],“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己”[1]的乐道精神,是古往圣贤高士们身上宝贵的精神力量。
《咏贫士》其一“万物各有托,孤云独无依……量力守故辄,岂不寒与饥[1]。”约作于晋宋易代之际。在政权更迭之下,众多节操不坚之人屈节投靠新政权,而诗人选择了辞官不就而“守故辄”,依然提醒着自己这条归隐守志之路,一旦选择了,就不免遭受生活的饥寒和精神的痛苦,就像其二中所说:“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1]。” 归隐田园后的贫苦虽不同于孔子困厄于陈的困境,但也承受了生活中的怨言,所幸的是还能从这些圣贤高士身上获得精神的勉励,如“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原生纳决屡,清歌畅商音”[1]; “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1]、 “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1];其五之“袁安困积血,邈然不可干。阮公见钱入,即日弃其官”[1]、 “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1];其六之“仲蔚爱穷居,绕宅生篙蓬”[1]、 “举世无知音,止有一刘龚”[1];其七之“昔在黄子廉,弹冠佐名州”[1]、 “惠孙一晤叹,腆赠竟莫酬”[1]。荣启期、原宪、黔娄、袁安、阮公、仲蔚、黄子廉,皆隐身不仕,固守穷节。在回望高士贤能品行的过程中,陶渊明努力汲取着安贫乐道的精神力量,“‘道胜无戚颜’一语,是陶公真实本领,千古圣贤身处穷困而泰然自若这,皆以道胜也[10]。”
肯定自己当下生活的意义,即使贫困潦倒依然坦然面对,这其实是对“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现实回答。陶渊明努力做好一个耕读者,用辛勤的操劳去对抗精神的彷徨,“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1]他在农耕生活里找到了君子的立身之道, 并迈向更自然超脱的生活境界。
三、吾道不孤,人生自然
陶渊明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记载:“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1]
孟嘉是陶渊明的外祖父,也是东晋名士,曾历任江州别驾、征西参军等职。由于陶渊明幼时丧父,常得外祖父照顾,所以孟嘉对陶渊明的实际成长颇有影响,陶渊明毫不讳言自己对外祖父的仰慕,他评价孟嘉一生说:“孔子称:‘进德修业,以及时也’。君清蹈衡门,则令闻孔昭,振缨公朝,则德音允集。道悠运促,不终远业,惜哉!仁者必寿,岂斯言之谬乎!”[1]给外祖父写传记,重点却不回顾功绩荣耀,而是着重表现其温雅平旷、任怀适意的气质风度,这是因为陶渊明在外祖父身上看到了一种可贵的性情,一种可以给他一生以滋养的人生哲学——“渐近自然”。
在这之后的岁月里,这四个字指引着陶渊明平衡于出与仕、进与退之间,使他能够把济世弘道的理想追求和安贫守贱、颐养情志的田园乐趣一同消融在隐逸生活中,而且,这隐逸的方式不是遁迹山林、遗世独立,而是躬耕自食。诗人认为,只有真正的躬耕田园才是合乎自然,不违心性的生活方式,“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1],闲居田园、读书养性可“忘怀得失,以此自终”[1],最大可能地保全自己完整的人格,渐近人生的自然。
于是,陶渊明离开了政治的旋涡,向南山进发了。他“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1],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1], “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1]…… 回归田园的生活里,有诗人初起的兴奋、日常的勤恳、收货的喜悦,仿佛自然真的具备魔力,可以完全抚慰诗人苦寂的心灵,直到灾难的不期而至,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1]。” 一场大火将诗人的居室焚烧殆尽,诗人只能暂住门前小船中遥看残墙断垣。普通人遇此变故,牢骚埋怨的情绪是难以避免的,而陶渊明却无意沮丧,他从灾难中回顾自身,“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1]。” 诗人回想自己自童年起便持有孤高不群之志,现已人到中年,形体虽已变化,但内心仍旧可以保持了无尘杂的信念、坚贞刚直的本性并不会因一场变故就消失殆尽,不如继续浇灌脚下的田园,正所谓“先生不着一笔,未仅仰想东户,意在言外,此真能灵府独闲者[11]。”
此后多年,陶渊明的隐居生活似乎再也无法回到初起时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1]了,他的生活越发艰难,“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1]。”一系列天灾人祸的降临使诗人全家衣食无着,温饱都难以为继,“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1]。” 因屡遭年灾,陶渊明在晚年饱受冻馁之苦,不得不出门“乞食”,诗人书写自己叩门“乞食”的窘境,语气如此平静,他的苍老、他的羞涩、他的真实反而更加震撼了我们,为了维持生存求助于乡邻,何耻之有?行乞乡邻并不可耻,这些善良的农民友人,能拿得出的也只是勤恳劳作后微薄的收获,他们虽未必能体会诗人的心灵境界,但接受他们的帮助不至于改变诗人的节操,诗人已莫大欣慰,感激不尽,“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1]。”
陶渊明从有薄产良田的归隐初期一路走来,物质上的生活每况愈下,相对应的,他精神上的状态也并非一帆风顺,他的喜悦、迷茫、无奈、刚强、平淡是兼而有之的。陶渊明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用“渐近自然”的人生智慧和诗人情怀,把他人生中那些波涛汹涌的刚强淡化了,把荣利道义的拷问搁置了,他越来越心平气和,也越来越成熟,他终于达到了一种更加从容淡定的境地。俯首于田园,这里的万物生长给了诗人丰厚的心灵滋养,他把豪情壮志春风化雨般融入田家语辞里,化村陋为圣洁,赋家常以理趣,在宽博淡远的襟抱中,诗人的作品越来越趋向自然祥和的人生之境。正如钱志熙先生所言:“他的宁静与澄明,也是终生持有的,最初只是一种性格,‘闲静少言’,‘弱不好弄’,最终上升为一种人生境界、一种哲学:‘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12]。’”
多年前,同样身在乱世的嵇康也发出过类似美好的企愿:“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徐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13]。” 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达到精神的自由和超脱,与自然合而为一,在自然中获得人生的解脱与人格的解放。
朱光潜曾说:“大诗人现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14]。” 若要一睹诗人人格的魅力,一定要走近诗人的生活与作品,因为他是身体力行地把生活的舞台搬到了人间田园,他独自走向了田园,离我们世俗人群好像越来越遥远,但他却长久地吸引着后世一代代的士子们。文人士子们如此固执地追寻桃花源境,按捺不住恰逢知己的兴奋去探寻他的作品,妄图在其中找寻出自己灵魂的印记,无数的人把他奉为精神上的楷模,灵魂上的伴侣,陶渊明终于在后人的希冀中活成了少数的大多数,他的道路终于热闹起来了——“时代对这些隐者的一再称扬,一定程度上正体现着人们对清高之士身行中可能包含的道德价值的肯定,以及希望借此补弊济世,矫俗纠时的期待[15]。”
以孔子“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的标准来探寻,余英时先生曾论:“中国史上没有任何一位有血有肉的人物完全符合‘士’的理想典型[16]。” 我认为,余先生还是太悲观、太局面了。若跳脱出君臣忠义的单一途径去体悟,陶渊明正是从那黑暗的时代里、彻底的绝望中走出来的一个鲜活的士子,他秉持自己的个性辟出了一方心灵的净土,让后世士子们四海晏清、高蹈超然的梦想在贫瘠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这正是人生价值的根基,也应继续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