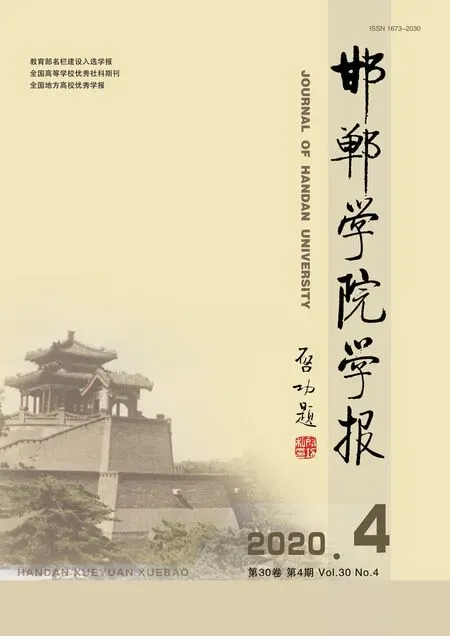门状考
张重艳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河北 石家庄 050051)
门状是唐中后期产生,盛行于宋代的私人拜谒文体。唐宋时期下级拜访上级要先呈递门状,类似于名帖,但是比名帖正式。目前,学术界对门状的研究主要是对敦煌文献中的门状结合传世典籍进行探索。周一良先生的《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1]307-330中有关门状的部分,结合敦煌文书,对门状的产生发展进行了梳理。张小艳老师《敦煌文献中所见“门状”的形制》[2]认为门状起源于公状,结合敦煌文书,分析了门状的形制。王使臻老师《敦煌遗书中的“门状”》[3]结合唐宋时期的笔记杂著,认为门状起源于起居状,对四件敦煌文书中的门状进行了详细解析。等等。迄今所见的门状实物中,传世典籍所存仅有《游宦纪闻》第1卷中的北宋医博士程昉门状;国家图书馆藏宋刻递修公文纸印本(缺叶配宋衢州州学刻宋元递修本)《三国志》第65卷(藏号7346,以下简称公文纸本《三国志》),现存30卷(1-30),蓝皮书衣,金镶玉装,长26.5cm,宽19.2cm,每页有衬纸,共16册,现存的30卷均为《魏书》。《三国志》纸背文献中有48 件南宋门状,是迄今发现数量最多的门状实物。从时间上来看,目前的门状主要是五代、两宋时期的门状。
一、五代、两宋时期门状
(一)五代后唐门状
敦煌文书中有3件后唐时期门状。
英藏敦煌文献S.529(2)是后唐同光二年(924年)定州开元寺僧归文上灵州节度使韩洙门状[4]302,文书迻录如下:
1. 定州开元寺僧归文
2. 右归文谨诣,
3. 衙祗候,
4. 起居,
5. 令公伏听 处分。
6.牒件状如前,谨牒。
7. 同光二年六月 日定州开元寺僧归文牒
英藏敦煌文献S.76V(1)是后唐长兴五年(934年)正月一日行首陈鲁佾门状[5]26,文书迻录如下:
1.行首陈鲁佾
2. 右鲁佾谨在
3. 衙门随例祗候
4. 贺,伏听
5. 处分。
6.牒件状如前,谨牒。
7. 长兴五年正月一日行首陈 鲁佾牒英藏敦煌文献S.76V(7)是乡贡进士刘某拜谒尊师门状[5]28,文书迻录如下:
1.乡贡进士刘□
2. 右谨祗候,顶
3. 谒
4. 尊师,谨状。
5. 闰正月 日乡贡进士刘□ □
三件门状的拜谒人分别为僧侣、军队的行首、乡贡进士。
敦煌文书P.3449,年代为后唐时期,赵和平先生的《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定名为“刺史书仪”[6]166,其中保留了两通参贺门状[4]363[6]206,笔者迻录如下:
具衔厶
右厶谨诣 台屏祗候 贺, 伏听 处分, 云云 。 具衔厶
右厶谨祗候 贺, 伏听 处分。
并着年月 日, 向下具全衔厶 牒
P.3449是刺史书仪,书仪里面的“云云”应是类似“牒件状如前,谨牒”之语。
(二)北宋门状
目前所见的北宋门状不多。《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BD1904V是北宋至道元年(995)僧道猷门状[7]256,文书迻录如下:
1.奉宣往西天取经僧道猷等:
2. 右道猷等谨诣,
3. 衙祗候起居,伏听 处分。①“伏听处分”四字被划掉。
4. 贺,伏听 处分。
5. 牒件状如前,谨牒。
6. 至道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灵图寺寄住
南宋张世南所撰《游宦纪闻》第1卷记载其家中藏有北宋治平四年(1067)士大夫往来所用的书状,其中一件内容如下:“医博士程昉。 右昉谨祗候参节推状元,伏听裁旨。牒件状如前,谨牒。治平四年九月 日,医博士程昉牒[8]8。”从内容上来看,此件是门状,“牒件状如前,谨牒”是元丰改制前门状的用语。
北宋时期的门状格式,在传世典籍中有记载。北宋司马光(1019-1086)《司马氏书仪·私书》有谒大官大状、谒诸官平状,实质是门状。“谒大官大状”[9]11,格式如下:
具位姓 某
右某谨诣 门屏衹候 起居(参、谢贺、辞违、随事。己欲他适,往辞人,曰辞。人欲他适,已往别之,曰攀违)某位,伏听处分,谨状(旧亦云牒件状如前,谨牒。状末姓名下又云牒。元丰改式,士大夫亦改之)。
年月日具位姓某状。
“谒诸官平状”[9]12,格式如下:
具位姓 某
右某祗候(世俗皆云谨祗候,按,谨即祗也,语涉複重,今不取)起居(谢贺、辞 违、随事。按,祗候某人起居,乃语自唐末以来,皆以云祗候起居某人,今从众),某位,谨状。
月日具位姓某状。“谒大官大状”中,“大官”应指比写状人职位大的官。“谒大官大状”与“谒诸官平状”的受状人皆为官员,两种门状的区别在于适用情境的不同,即根据写状人和受状人之间地位的高低来决定用何种格式。从文字上对比,“谒大官大状”比“谒诸官平状”多了“谨诣”“门屏”“伏听处分”字样。“谒诸官平状”中,司马光已经注意到了“世俗皆云谨祗候,按,谨即祗也,语涉複重”,因此“祗候”前去掉了“谨”字。《清波别志》卷上有“门状曰‘谨祗候’,谨即祗也,是皆时所尚,不容理晓。”[10]129明使用门状时,通常是“谨祗候”连用。
(三)南宋门状
公文纸本《三国志》纸背文献中共有门状48 件,笔者迻录两件如下:第15册第28卷第1叶背:
1. 雍熙寺僧 妙性
2. 右 妙性 謹祇候
3. 攀送
4. 判府直閣太傅,伏候
5 台旨。
6. 乾道九年四月 日雍熙寺僧 妙性 □
第4册第6卷第9叶背:
1.右朝議大夫、直徽猷閣、知平江軍府、主管學事向 汮
2. 右汮謹祗候
3. 叅
4. 司法奉議,伏候
5. 台旨。
6. 乾道八年六月 日 右朝議大夫、直徽猷閣、知平江軍府、主管學事向 汮 □
南宋时期的门状格式,在传世典籍中也有记载。元代刘应李辑《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甲级第4卷《状帖诸式·状(官俗诸式)》有“谒候大状”(司马温公古式):
具衔姓某
右某谨诣 门屏衹候起居
某官,郎中伏听
处分,谨状。
月 日具衔姓 某 状
还有“写门状式(俗用常式)”:
具衔姓 某
右某谨衹候
参
某官中大伏候
台旨
月 日具衔姓 某 状[11]19
《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中的“谒候大状”(司马温公古式)即是指司马光《书仪》中的“谒大官大状”。刘应李是宋末元初学者,据考证,其生卒年应在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稍前后到元泰定元年(1324)之前,刘应李中进士在 1274年,其时二十余岁,入元后归隐,后以授徒讲学为业[12]。《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首次刊行于大德十一年(1307),此书是刘应李在元初所撰,书中辑录了大量的南宋资料,结合刘应李的经历,书中“写门状式(俗用常式)”是南宋的门状格式。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三国志》纸背文书中的门状与“写门状式(俗用常式)”完全相同。《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甲集卷五《杂文诸式·丧礼》还保存了丧礼情境下慰大官门状式、慰平交门状式。慰大官门状式:“某位姓某 右某谨诣 门屏祗 慰 某位伏听 处分谨状 年 月 日具位某状”。慰平交门状:“某位姓某 右某祗 慰 某官谨状 月 日具位姓某状”。虽然行文没有分行,但“丧礼”下有五个字“温公书仪式”,从状式内容来看,慰大官门状是“谒大官大状”的套用,慰平交门状式是“谒诸官平状”的套用。
《三国志》纸背文书门状中也有古式门状,即刘应李“谒候大状”(司马温公古式),共有两件,第15册第27卷第16叶背:
1. 勑特授高州文學項 益謙
2. 右益謙謹詣
3. 台屏,祇候
4. 叅
5. 判府安撫徽猷,伏候
6. 台旨。
7. 乾道八年六月 日勑特授高州文學項 益謙 □
第12册第21卷第13叶背:
1. 右文林郎、前御前武鋒軍都統司幹辦公事鐘 邦佐
2. 右 邦佐 謹詣
3. 台屏,祇候
4. 辝
5. 判府安撫徽猷,伏候
6. 台旨。
7. 乾道八年六月 日右文林郎、前御前武鋒軍都統司幹辦公事鐘 邦佐 □
《三国志》纸背文书中的古式门状,与《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中的古式门状又有一些区别,“伏听处分,谨状”变成了“伏候台旨”,与俗式门状的后半部分相同。南宋时期门状古式和俗式并行,《三国志》纸背文书中的门状与《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中的门状格式基本契合。
综观五代、北宋、南宋时期的门状,门状是一种格式较为简洁,字数较少的文书体式,元丰改制前,门状大都有“牒件状如前,谨牒”之语,最后一行末尾有“牒”字。元丰改制后,“牒件状如前,谨牒”弃用,改成“谨状”,最后一行末尾“牒”改为“状”字。改制前带有此语的大都是官员之间私人拜谒的门状,英藏敦煌文献S.76V(7)乡贡进士刘某拜谒尊师门状,虽是后唐门状,但拜谒人身份是乡贡进士,尚无官职,受门状人此时身份是“尊师”,故不用“牒件状如前,谨牒”。
“谒大官大状”中,“起居”的用法,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作“参、谢、贺、辞违”,根据实际需要“随事”,“谒诸官平状”中,则少了“参”。《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中刘应李也注明“参、辞、贺、谢随用改易”,因此决定门状用意的即表示“起居”的词汇,仅一两个字。
二、门状的产生、形制、适用对象和情境
(一)门状的产生
在门状的起源问题上,张小艳老师《敦煌文献中所见“门状”的形制》认为门状起源于公状,是一种“以公状的程式来制作的拜帖”[2]79,“在行文程式上,公状与门状完全相同,在用途上则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前者用来申述事由,后者用作拜谒通名,内容上往往前者详而后者略”[2]84。张小艳老师仅注意到门状中的“牒件状如前,谨牒”与公状相同,忽视了门状产生的原因。王使臻老师《敦煌遗书中的“门状”》认为“门状本是私人性拜谒时所通进的起居状,唐代时其格式末尾用‘谨状’,但在五代宋时,却也出现拜谒大官时用‘牒件状如前’等公文中的用语,施于官之尊贵及吏之长者,表示特别的礼敬,一时成为风俗”[3]95。
门状起源于唐代起居状。唐代李济翁《资暇集》卷下“门状”条云:“门状,文宗朝以前无之,自朱崖李相贵盛于武宗朝,且近代稀有生一品,百官无以希取其意,以为旧刺轻(刺则今之名纸),相扇留具衔候起居状。而今又益竞以善价纸,如出印之字,巧谄曲媚,犹有未臻之遗恨。”[13]26点明门状产生的原因,是武宗朝百官认为旧刺礼数较轻,唐代问起居制度广泛流行,为了表示重视,官员拜访则留“具衔候起居状”。五代时人孙光宪(901-968)的笔记小说《北梦琐言》第9卷《李涪尚书改切韵》记载门状的起源:“古之制字卷纸题名姓,号曰名纸。大中年,薛保逊为举场头角,人皆体傚,方作门状。洎后仍以所怀,列于启事,随启诣公相门,号为门状、门启。虽繁于名纸,各便于时也。书云‘谨衹候起居郎某官’。即是‘起居’在前,‘某官’在后,至今颠倒,无人改更矣。有朝廷改之,亦美事也”。[14]198同样认为门状来源于起居状。《资暇集》没有明确点明门状的产生时间,认为门状萌芽于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北梦琐言》认为门状正式产生在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资暇集》《北梦琐言》记载的门状萌芽、正式产生的时间可以衔接起来。
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第1卷云:“今之门状称‘牒件状如前,谨牒’。此唐人都堂见宰相之礼。唐人都堂见宰相或参辞谢□事,皆先具事因,申取处分。有非一事,故称‘件状如前’。宰相状后判‘引’,方许见。后人渐施于执政私第,小说记施于私第自李徳裕始,近世谄敬者无髙下一例用之,谓之‘大状’。”[15]177说明门状中的“牒件状如前,谨牒”之语,来自于唐代都堂见宰相的礼仪,自李徳裕始,逐渐用于门状,以示谄媚敬者。“牒件状如前,谨牒”是公状用语,门状在发展过程中使用了此语,但不能说门状起源于公状。宋人叶梦得(1077-1148)《石林燕语》第3卷对门状和公状的使用进行了区分:“唐旧事,门状,清要官见宰相,及交友同列往来,皆不书前衔,止曰‘某谨衹候,某官,谨状。’其人亲在,即曰‘谨衹候’、‘某官兼起居,谨状。’祗候、起居不并称,各有所施也。至于府县官见长吏,诸司僚属见官长,藩镇入朝见宰相及台参,则用公状,前具衔,称‘右某谨衹候’,‘某官伏听处分’,‘牒件状如前,谨牒’。此乃申状,非门状也。元丰以前,门状尚带‘牒件状如前’等语,盖沿习之久,后虽去,而祗候、起居并称,犹不改。今从官而上,于某官下称‘谨状’,去‘伏候裁旨’四字,略如唐制,而具前衔,谓之‘小状’。他官则前衔与前四字兼具,而不言‘谨状’,不只有‘牒件状如前,谨牒’七字,则‘谨状’字自不应重出。若既去此七字,则当称‘谨状’。以为恭而反简,自元丰以来失之也。”[16]32《石林燕语》成书于宋室南渡之初,叶梦得已然注意到,清要官见宰相以及私人交往,用门状。在“府县官见长吏,诸司僚属见官长,藩镇入朝见宰相及台参”情境下,用的是公状,公状用语有‘右某谨衹候’,‘某官伏听处分’,‘牒件状如前,谨牒’,和元丰改制前门状的用语相似,容易混淆。门状、申状应用的领域不同,门状是私人交往使用的文体,公状是申状,是政府公文。
(二)门状的形制
门状从唐中期盛行,在宋代流行也是时起时落。《老学庵笔记》第3卷:“土大夫交谒,祖宗时用门状,后结牒‘右件如前谨牒’,若今公文,后以为烦而去之。元丰后,又盛行手刺,前不具衔,止云:‘某谨上。谒某官。某月日’。结衔姓名,刺或云状,亦或不结衔,止书郡名,然皆手书,苏、黄、晁、张诸公皆然。今犹有藏之者。后又止行门状,或不能一一作门状,则但留语阍人云:‘某官来见’。而苦于阍人匿而不告,绍兴初乃用牓子,直书衔及姓名,至今不废”。[17]37说明士大夫交往,宋初用门状,由于其中有“右件如前谨牒”,类似于公文较为繁琐,故门状格式简化,去掉此语。元丰改制后流行手刺。后又只流行门状,但是由于阍人不报告主人,南宋绍兴初年就开始流行牓子。
门状的形制和榜子、名纸、刺有明显区别。《禅林象器笺》第15卷有:“门状者,谒见人时,所呈单状也。纸阔六七寸,内不书文字,自左方卷之,用丝束分中少已上,题姓名于其上。又名参榜,或曰参状”。[18]1173榜子,又称作牓子,宋欧阳修《归田录》第2卷云:“唐人奏事,非表非状者,谓之牓子,亦曰录子,今谓之札子。凡群臣百司上殿上奏事,两制以上,非时有所奏陈,皆用札子。中枢、宣密院事不降宣敕者,亦用札子,与两府自相往来亦然”。[19]24欧阳修所说的是作为公文的榜子。榜子还可以用作名片,南宋《张协状元》戏文第35出有:“状元万福!且息怒,奴家不具榜子参贺”[20]150。榜子尺寸比门状小,《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甲级第4卷有:“凡榜子,用白纸阔四寸,许就中心写一行,横卷之,平常见人,添取覆两字,其余贺谢辞违,并临时于名下改之。”[11]20名刺比榜子稍小。《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甲级第4卷有:“凡名刺,用好门状纸,阔三四寸,左卷如箸大,用红线束腰,须真楷细书。或仓卒无丝线,则剪胚红纸一小条,就名上束定亦得。若辞人,则于名下书拜辞,谢人则于名下书拜谢,送人则于名下书拜违。”[11]21名刺的用纸,是好门状纸。
书写格式上,名纸、刺、榜子都有大体固定的格式,与门状不同。《司马氏书仪·私书》有上尊官问候贺谢大状、与平交平状、启事、上尊官时候启状、上稍尊时候启状、与稍卑时候启状、上尊官手启、别简、上稍尊手启、与平交手简、与稍尊手简、谒大官大状、谒诸官平状、平交手刺、名纸。《司马氏书仪·私书·名纸》有“取纸半幅,左卷令坚实,以线近上横系之,题其阳面(凡名纸,吉仪左卷题于左,掩之端为阳面。凶仪右卷题于右,掩之端为阴面)”[9]12。《司马氏书仪·私书·平交手刺》有:“与平交手刺(大约如此,时改临时):某爵(无爵者言官),某里姓某(无官者止称乡里,此平生未曾往还者也,若已相识则去爵、里往还,熟则去姓),专谒 见(谢、贺、辞别随事),某位 月日 谨刺”[9]12。榜子格式更为简单,《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甲级卷四有牓子写作图示,僧家榜子内容为:“某院住持僧 某 参”。道士榜子内容为:“某官道士姓 某 参”。术士榜子内容为:“术士姓 某 参”。[11]20
门状、榜子、名纸,出行时放在随身携带的书筒里,“后唐明宗朝,公卿大僚皆唐室旧儒,务以礼法相尚。其时进士明经,……重带书筒照袋(书筒乘启状,照袋贮笔砚纸墨,照袋制已具先说)。毎见公卿门,并数步外下驴整衣冠,敛仆驭,然后躬趍门下,求执事者通笺启刺字请见。[21]806书筒即盛放书信的筒,“启状”即书启、名纸、刺、门状类。照袋放笔墨纸砚,以供随时写门状、刺、启。门状要用纸折成经折状,开头一行为封面,其余根据内容折在里面,通常为几折。
门状有其使用规范。宾客拜访时,如果主人在家,客人告辞后,门状要归还客人。《齐东野语》第20卷“隐语”有“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实新来转一官。门状送还王介甫,潞公身上不曾寒。”“门状,辞别则主还之。”[22]256如果宾客拜访时主人不在,主人要修书一封把门状送回。敦煌文书伯3449保存有《封门状迴书尊》[4]358、《封门状迴书平交》[4]359,即是主人送还门状时写的书信,文书迻录如下:
“封门状迴书尊”
伏蒙 司空奖念过深,又垂
宠访,恰值出入,不果 迎门。将别
旌轩,无任 攀恋。所留
华刺,莫敢捧当,谨随状封
纳。续冀专诣 门屏,袛候
辞违,谨先修状谘 闻陈
谢,伏惟 照察。 谨状。 云云。
“封门状迴书平交”
昨日伏蒙厶眷私,特赐 荣访,
偶以出入,莫果袛 迎。既不遂于
攀延,实增慙悚。而更留于
盛刺,倍切悚惶。其余感铭,造次
奚喻。所留 宠示,岂敢捧当。谨
修状谘 纳,兼申陈 谢,伏惟
照察,谨状
不同身份的人,使用门状的形制不同。《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关于门状用纸有说明 “凡门状,用大白纸一幅,前空二寸,真楷小书,字疏密相对如前式。武官不用全幅纸,但阔四五寸,后不用具年,但云某月日姓某状。公吏同武官式,僧道同官员式,尤贵细书”[11]19。从门状的用纸说明来看,门状的适用者是官员、公吏、僧道。文官和僧道的门状用纸、格式相同,武官和公吏的门状用纸、格式相同。《癸辛杂识》前集有“今时风俗转薄之甚。昔日投门状,有大状,小状,大状则全纸,小状则半纸。今时之刺,大不盈掌,足见礼之薄矣[23]19”。大状小状之分,应该就是文官武官僧道公吏的用纸区分。南宋陆游(1125-1210)的《老学庵笔记》,成书于宋孝宗淳熙末年到宋光宗绍熙初年,第2卷记载了关于武臣用门状的纷争:“隆兴中,议者多谓文武一等,而辄为分别,力欲平之。有刘御带者,辄建言谓门状、牓子,初无定制,且僧道职医皆用门状,而武臣非横行乃用牓子,几与胥史卒伍辈同。虽不施行,然哓哓久之乃已”。[17]19宋代官员在放假三日后聚集上朝称为“横行”,武臣非横行用牓子虽然没有施行,但仍然争辩了很久。
(三)门状的适用对象和情境
虽然官方对门状的适用对象有一定约束,但是门状属私书范畴,宋代礼俗下移,使用越来越广泛。《野客丛书》附录一有:“胡如村言:嘉祐以前士风,宰相与庶官书启,具衔前名后押字,外封全写衔,封皮上头乘签子云:‘书上某官’。士人用名纸,有官即不用。吊慰人即用名纸,如见士人敬之者亦用门状,见常人即以手状。”[24]454北宋嘉祐以前,士人拜见时用名纸,“有官即不用”,即有官职时,则用门状。在丧礼时,对尊敬的士人也可以用门状,不用拘泥于丧仪主家是否有官职。见没有官职的人则用手状,即名帖、名刺之类。拜访自己敬重的人使用门状,在北宋成为美谈,如北宋欧阳修礼贤下士,访问布衣士人都使用门状。《曲洧旧闻》第3卷“欧公下士”有:“欧公下士,近世无比。作河北转运使,过滑州,访刘羲叟于陋巷中。羲叟时为布衣,未有知者。公任翰林学士,常有空头门状数十纸随身。或见贤士大夫称道人物,必问其所居,书填门状,先往见之。果如所言,则便延誉,未尝以位貌骄人也。”[25]119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北宋时期门状的适用对象大多是有官职的人。
丧礼是门状使用的重要情境之一。南宋朱熹《朱子全书·家礼》第4卷《丧礼·吊 奠 赙》有“凡吊皆素服。有状,惟亲友分厚者有之。具刺通名,宾主皆有官则具门状,否则名纸,题其阴面,先使人通之,与礼物俱入”。[26]913规定丧礼情境下,宾主皆有官职,则宾客作门状,否则名纸即可。《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甲集第5卷《杂文诸式·丧礼》保存南宋有慰大官门状式、慰平交门状式。
节日要送门状以示祝贺,朱熹的《增损吕氏乡约》中,对岁首、冬至、四孟月朔,辞见贺谢,有更为具体的规定,门状的使用范围更为广泛。“造请拜揖,凡三条:曰凡少者、幼者于尊者、长者,岁首、冬至、四孟月朔,辞见贺谢,皆为礼见(皆具门状,用幞头、公服、腰带、靴笏。无官具名纸,用幞头、襴衫、腰带、系鞋。唯四孟通用帽子、皂衫、腰带。凡当行礼而有恙故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则尊者先使人谕止来者)。此外,候问起居,质疑白事,及赴请召,皆为燕见(深衣凉衫皆可。尊长令免,即去之)。尊者受谒不报(岁首、冬至,具己名榜子,令子弟报之,如其服)。长者岁首、冬至具榜子报之,如其服,余令子弟以己名榜子代行。凡敌者,岁首、冬至,辞见贺谢相往还(门状、名纸同上,唯止服帽子)。”[27]237少者、幼者,对于尊者、长者,在拜见时均需作门状。
节日门状的使用已成滥觞,为时人所讥。《癸辛杂识》前集“送刺”:“节序交贺之礼,不能亲至者,每以束刺佥名于上,使一仆遍投之,俗以为常。余表舅吴四丈性滑稽,适节日无仆可出,徘徊门首,恰友人沈子公仆送刺至,漫取视之,类皆亲故,于是酌之以酒,阴以己刺尽易之。沈仆不悟,因往遍投之,悉吴刺也。异日合并,因出沈刺大束,相与一笑,乡曲相传以为笑谈。然《类说》载陶榖易刺之事,正与此相类,恐吴效之为戏耳。”[23]19这里的刺,是指门状。《清波杂志》第6卷“闞忘投刺”也有一则类似的笑话:“正、至交贺,多不亲往。有一士令人持马衔,每至一门撼数声,而留刺字以表到。有知其诬者,出视之,仆云:‘适已脱笼矣’。‘脱笼’亦为京都虚诈闪赚之谚语”。围绕节日门状产生的笑话竟然广为流传。
门状广泛流行的原因之一是时人送门状以示谄媚,为部分人所不齿。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第1卷在提到门状时称“近世谄敬者无髙下一例用之,谓之‘大状’。予曾见白乐天诗稿,乃是新除寿州刺史李(忘其名)门状,其前序住京因宜及改差遣数十言,其末乃言‘谨祗候辞,某官’。至如稽首之礼唯施于人君,大夫家臣不稽首,避人君也,今则虽交游皆稽首。此皆生于谄事上官者始为流传,至今不可复革。”[15]177门状的产生源于公状,应用于私人交往,这种行为本身是谄媚之事。《癸辛杂识》前集“送刺”有:“又《杂说》载司马公自在台阁时,不送门状,曰:“不诚之事,不可为之。荥阳吕公亦言送门状习以成风,既劳作伪,且疏拙露见可笑。则知此事由来久矣。[23]19”。司马光和荥阳吕公认为送门状是不诚之事。《司马氏书仪》以《仪礼》为据,结合唐代的《开元礼》,对不适应北宋时期的古礼进行了删减,同时也根据当时的需要,吸取有益于人情教化的的风俗,认为不合教化的则不取。全书并没有关于任何门状的字眼,连性质为门状的谒大官大状、谒诸官平状,都不称之为门状。《司马氏书仪》卷五“丧仪·吊酹赙禭”云:“凡吊人者,必易去华盛之服。作名纸,右卷之,系以线,题其阴面(凡名纸,吉者左卷之,题阳面;凶者反卷之,阳面在左,阴面在右)曰:某郡姓名慰。同州之人则但云同郡,皆不著官职。”[9]55如果仅从这条材料看,北宋时期丧礼的情境下,吊人者不用门状。前文所引《野客丛书》有北宋嘉祐以前士人吊慰用门状而非名纸的记载,说明北宋丧仪情境下,是使用门状的。笔者推断,司马光认为门状为不诚之事,反对使用门状,这也是《司马氏书仪》全书没有出现“门状”称谓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门状是唐中后期产生,盛行于宋的私人拜谒文体。门状起源于官场中的起居状。门状的形制和榜子、名纸、刺有明显区别。宋代礼俗下移,门状使用越来越广泛,并不拘泥于写受双方的身份。门状产生的原因之一是出于谄媚,为部分士人所不齿,司马光反对使用门状,因此《司马氏书仪》没有出现“门状”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