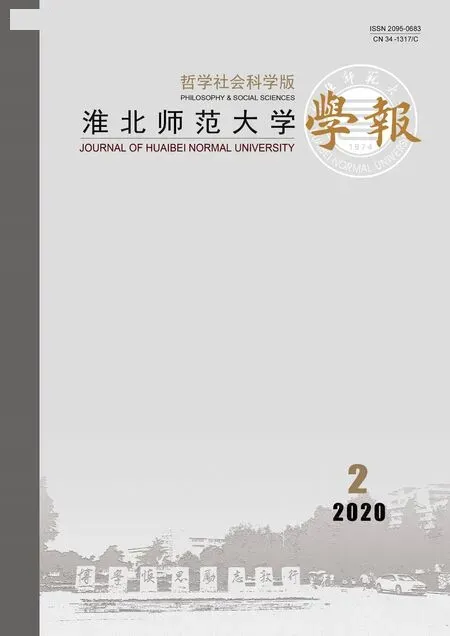90年代儿童电影的生产语境和艺术特点
谭旭东,胡维佳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200444)
新中国儿童电影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1949年至文革的“十七年时期”是新中国儿童电影的发展时期,80 年代是其第一次繁荣时期,而90年代为其第二次繁荣时期,进入21 世纪儿童电影则面临转型和调整。本文拟就90年代儿童电影的生产语境、艺术特点及问题做一些探讨,请方家指正。
一、90年代儿童电影的基本状况
90 年代儿童电影题材广泛,产量高,多元化。从1990 年到1999 年这10 年间,中国大陆共生产119部电影,是儿童电影产量最高的十年。
首先,90年代儿童电影的题材多元化、具有时代性。校园题材、家庭亲情题材、“小英雄”题材、名人成长传记、少数民族题材、科学幻想题材等,均有较好的表现。这些题材一部分是对以往儿童电影题材的继承,另一部分是在过去题材的基础上进行了发展创新,融合了90年代的时代印记。
其次,城市儿童电影和农村儿童电影更显突出。它们虽然是新时期初至9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的带着“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儿童电影类型,但在90年代,由于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农民工进城务工导致农村留守儿童增多等问题,反映在儿童电影上,即出现了更丰富的艺术表达。这一时期,城市儿童电影仍然保持有增无减的趋势,且题材相比于之前更加多样化。如,《我的九月》《花季·雨季》《男孩女孩》等。“随着农村与城市的鸿沟不断拉大,农村儿童在自然环境恶劣,物质极其匮乏、时刻面临辍学的艰难环境中,将走出农村定为自己成功的终极目标。此类话题成为农村题材儿童电影的基本叙述主题”[1]。反映农村儿童生活和生命状态的电影相当出色,代表性作品有《远山姐弟》《一样的天空》《杂嘴子》和《手拉手》等。
再次,在90年代儿童电影的剧本来源上,仍然有数量可观的儿童电影是对文学作品(尤其是儿童文学)的改编。虽然较之于80年代,文学和电影的互文性有所减弱,但是总的来说改编的儿童电影在整个90年代的儿童电影市场中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中,根据儿童文学改编的代表作品有四部:一是《草房子》(根据曹文轩《草房子》改编,1998 年,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编剧:曹文轩,导演:徐耿);二是《男生贾里》(根据秦文君小说《男生贾里》改编,1996 年,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编剧:秦文君,导演:张郁强);三是《花季·雨季》(根据郁秀同名小说改编。1997年,深圳电影制片厂、深圳市委宣传部,编剧:丛容,导演:戚健);四是《一个都不能少》(根据施祥生小说《天上有个太阳》改编,1998年,广西电影制片厂,编剧:施祥生,导演:张艺谋)。改编成电影的儿童文学作品主要有以下两类:一是紧密联系生活,贴近小学语文教育和现实需要的儿童文学畅销书,作品已经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和读者号召力,作品中的主角读者比较熟悉,如曹文轩的《草房子》和秦文君的《男生贾里》;二是儿童科幻小说和幻想故事,这方面我国比较欠缺,但国外就有很多例子。90 年代儿童文学的电影改编虽然不如80 年代,但也是儿童电影题材和内容的一个重要构成。
二、90年代儿童电影的生产语境
90 年代初,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发生显著的变化。90年代儿童电影也受到了来自当时中国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
首先,是市场经济下的电影商业化转型。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科学解答了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加快和深化了改革开放的步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由此也更加明显、充分。同年10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并要求积极推进文化改革。正是由于这样的社会背景,这一时期的影视文化共同面临着政治一体化和经济市场化这两个相互矛盾又可相互协调共存的现实情况。因此,以1992年为界,电影行业也面临着生产创作方式、市场机制、管理方式等方面的转型与改革。1990 年8 月28 日,中宣部、广电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故事片审查把关工作意见》,要求各电影故事片生产厂家在影片剧本经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或政府有关领导部门审查批准后,方可投产。1991 年1 月3 日,广电部发出广发影字1 号文《关于1991 年故事影片生产计划及有关事项的规定》,下达全年的生产计划为故事片102 至125 部,其中包括儿童片12 部,美术片48 本和外国译制片400 本。由此可见,一方面国家政府对于儿童电影的重视;另一方面,当时的儿童电影生产创作方式仍属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范畴。1993 年1 月5 日,广电部下发了《关于当前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及其《实施细则》,打破了由中影公司垄断式的发行体制,选择了面向市场化的改革道路。1997 年,广电部电影局发布《关于试行〈故事影片单片摄制许可证〉的通知》,宣布国有省级以上和具备相应条件的地市级电影单位、电视台、电视剧制作单位,均可向电影局申请故事电影单片摄制许可证。这一通知打破了制片厂的摄制垄断,为社会资本参与电影制作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电影行业在资金的引进,相关人才的吸纳上起到了推动作用,为商业电影的发展提供了环境。无疑,儿童电影为了生存发展自然也要走上商业化的道路。但是,90 年代中国儿童电影在商业化的道路上存在着包括机制惯性、艺术创新难度大等诸多障碍,也因其无法满足商业电影盈利的要求而受到电影市场的冷落。
其次,是媒介环境新变化。进入90年代,改革开放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大众传媒也开始了急剧转型和变革。其中,电视的普及以及因特网用户的快速增长对电影市场的冲击非常大。人们足不出户,只需要一台电视或者电脑就可以与世界连接,而电影则需要走入电影院或者租赁录像带,相较而言,电视和电脑网络的信息接收成本较低。电视和因特网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方式。1997年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的数据表明:至1996 年底,报纸、广播、电视已成为影响最大的三种传播媒介。有线电视的迅速普及对于电影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有线电视的实时性、便捷性、娱乐性、低成本等特点,在有线电视普及之后,很多家长把电视中播放的少儿节目、动画片等看作儿童电影的替代品。首先,家长不用带孩子去电影院或者通过其他渠道获取儿童电影,只要在家就能陪同孩子观看喜爱的电视节目,并且电视台播放的节目种类多,可选择余地大,给予了家长和孩子很大的自由选择权。其次,电视对于受众进行了准确的市场定位,分出了不同种类的电视台,比如中央电视台针对观众的不同需求设置了新闻频道、纪录频道、电影频道、少儿频道等,其中少儿频道放映的动画片、少儿节目等都具有一定的时长限制,相比儿童电影来说更加短小且寓教于乐。90年代电视对电影形成的冲击,进入21 世纪又很快被互联网和新媒体多替代,这是后话。
再次,是儿童文学观念对儿童电影的影响。90年代的儿童文学同儿童电影一样,面临着市场化商业化和多媒体电子语境,这也一定程度上促使儿童文学主动与儿童电影、电视之间发生紧密联系,以拓展表现空间和赢得更多的受众。这其实是儿童文学观念的变化,由过去的“儿童本位”立场向商业化写作转向,这一方面是因为90 年代儿童文学需要适应时代语境,获得更多市场份额;另一方面也因为90 年代儿童电影虽然受到电视冲击,但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媒介,可以吸引更多儿童关注儿童文学。在这样的观念转变之下,儿童文学界与电影界的密切合作顺理成章,一批儿童文学改编的儿童电影就产生了。这些电影既可以吸引原书的读者观看,又对儿童文学作品进行影像化处理,让读者接受起来更加生动有趣。比如,《我的九月》根据北京儿童文学作家罗辰生的小说《傻老师》改编;深圳16岁中学女孩郁秀根据自己的生活创作的小说《花季·雨季》也被改编为同名儿童电影;此外,曹文轩的儿童小说代表作品《草房子》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等等。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儿童文学无论是理论观念还是作家原创,与传统儿童文学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儿童文学可以为儿童电影提供理论观念的借鉴与作品资源的援助。”[2]儿童文学的自觉商业化、大众化等很多理论观念不但影响了后来的儿童文学创作,其“儿童本位”“儿童视角”等理念也被90年代的儿童电影逐渐借鉴吸收。
总之,90 年代是一个社会与观念及儿童成长环境变化最大最快的时段。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独生子女政策又使儿童在家庭中获得更加优越的地位,广泛接触现代大众传媒加速了他们的精神成长。“现代文化工业造就的电脑、电视、激光唱片、游戏机、录像机等,更使他们很容易走进一个没有国界的文化广场。从某种程度上说,成人是与儿童一起成长的……这种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不可能不在儿童生活和精神需求中表现出来。”[3]90 年代儿童电影就是在商业化、市场化的转型背景下,在电视、互联网等崛起的大众传媒的冲击下,与儿童文学相互推动之下生存发展的。这便是90 年代儿童电影不可忽视的艺术生产语境,其深刻地影响着90 年代儿童电影的类型与特点。
三、艺术特点
80 年代中后期,电影市场化带来了娱乐片的大热,其中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无疑与政府所提倡的“主旋律”价值观相冲突。到了90年代,这两种价值观所带来的冲突,直接体现在电影的转型上,即大众化转型——“在功能上,它成为了一种游戏性的娱乐文化;在生产方式上,它成为了一种由文化工业生产的商品;在文本上,它成为了一种无深度的平面文化;在传播方式上,它成为了一种全民性的泛大众文化。”[4]但这样的转型并不意味着主旋律电影的消失,相反,主旋律价值观和大众文化价值观进行了一定的融合,互相借鉴,使多元化的电影得以共存,促进了电影市场的繁荣。这一时期,儿童电影表现出一些鲜明特点,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题材与艺术风格的多元化趋势。90年代儿童电影在题材选取上偏向体现时代精神和社会热点的现实题材,同时,具有“主旋律电影”伦理泛情化的美学趋向。伦理泛情化是指“为意识形态注入伦理情感……使主人公的性格、动作、命运和他行动的环境、他所得到的社会评价以及影片叙事的情节、节奏和高潮都以伦理情感为中心而被感情化。”[5]如,《一个独生女的故事》《背起爸爸上学》和《一个都不能少》等,分别塑造了遭遇父亲去世,母亲重病,仍然扛起家庭重担,努力学习的瑶瑶,带着瘫痪的父亲到城里打工上学的16 岁少年李勇和信守承诺,让学生“一个都不能少”的十三岁山村代课老师魏敏芝。这些形象所承载的是一种主旋律价值观,且形象化的手法让观众更加容易产生共鸣从而潜移默化地受到精神教育。也就是说,“主旋律电影更新并增强了自己的表述能力, 摆脱了政治宣教的僵硬和保守,成功地调动了观影者的伦理情感,打开了主旋律电影一直希望的面向大众的传播渠道,并顺利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6]同时,90年代的儿童电影在大众化转型的过程中,选材和内容上更加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关注平凡儿童和弱势群体,还有部分关注少数民族儿童的电影。如《一个独生女的故事》反映的是独生子女问题。如《一个都不能少》反映的是偏远地区农村儿童的教育问题。
90 年代中国儿童电影在审美风格、艺术手法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很多导演对儿童电影进行着自己的尝试,并创作出风格多元的作品。如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导演的《一个都不能少》、冯小宁导演的《大气层消失》和张建亚导演的《三毛从军记》等三部电影,都是带有导演个人想法和创作风格的儿童电影。同时,第六代导演也走进儿童电影创作的行列中来。如管虎导演的《再见,我们的1948》讲述了1948年至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在一所国民党枪械修理厂下属的职工子弟小学里,一群孩子们由最初单纯的喜爱枪械、冲动地偷枪,到为年轻的进步女教师唐巩所启发带领,慢慢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所谓儿童片真的就只有孩子们看吗? 除了纯真的天性以外,孩子们的观赏经验真的非常幼稚吗?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东西,关键是如何实现它,或者说如何用我们现代人的方法再去论释那些‘嘎子’、‘胖墩’们的故事。”[7]影片中,导演以自己的视角,用新的方法去阐释了一个发生在祖辈年代里的故事。相较于侧重还原历史环境氛围的真实,导演在影片中更加注重人物情感命运、状态的塑造,由人物去实现这份历史的真实。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主动介入儿童电影,推动了儿童电影艺术的多元化,也使儿童电影有了比“儿童艺术”更丰富的艺术观念。
其次,“儿童本位”艺术观念的凸显。尽管每一位导演在电影中展现了带有自己特色的艺术手法和审美风格,但是总地来说,90年代的儿童电影在艺术创作上还是存在一定共性的。尤其是在“儿童本位”观念的凸显方面。“儿童题材影片可以有很多种划分标准,从影片的观众取向上看, 我以为可以分为儿童本位取向和非儿童本位取向两种。所谓儿童本位, 就是以儿童为中心, 以儿童的观念、儿童的想法、儿童的思维和儿童的审美习惯作为儿童影片创作和评价的一个指标, 这就要求创作者要真正关注儿童的生命状态, 真正走入儿童的精神世界。非儿童本位体现在电影文本中, 包括教育本位、艺术/文化本位等。”[8]简言之,非儿童本位的儿童电影大致有两类,一是带有浓厚的教育色彩,把儿童电影看作是教育儿童的工具;二是通过展现儿童世界来映射成人世界,表达一些成人的想法,或者使用的艺术手法过于复杂,让儿童难以理解影片内容和思想。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儿童电影都做到了儿童本位,但《我的九月》作为一部90年代初比较典型的“儿童本位”的电影,为这一时期儿童电影带来了新气象。《我的九月》之所以真正做到了以儿童为本位,关键在于导演尹力安排的全部情节展开都是围绕小主人公安建军的内心动作走向展开的,从安建军的视角讲述他由懦弱、自卑、退缩到自信、坚强、积极争取的成长过程,因此在情节的安排上都是按照安建军的心路历程呈现的。另外,导演选取了第一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相结合的表现方法,除了更好地表现出安建军的所思所想之外,还通过全知全能的客观视角去记录这个孩子的成长,以及他人对于这个孩子的评价。“《我的九月》以安建军的内心活动为依据作为影片的主要构架,但又不可能局限在他所能看到的主观视点之中。对待孩子,我们不是居高临下的,是蹲下去,贴近他们,但总的视角和态度则是俯瞰式的和达观的。我们是贯彻了纪实美学的思想,但这并不是用来束缚自己的手脚。”[9]这是尹力在谈《我的九月》的创作时所说的一段话。这部具有纪实风格的儿童电影,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安建军作为一个孩子真实的精神成长历程,同时又将成长与参加亚运会开幕式联系在一起,没有过分地拔高孩子的精神成长高度,也没有刻意地说教。
90年代一部分儿童电影关注对儿童精神世界的建构,这也是儿童本位观念的体现。这些影片为儿童建立起了一个充满诗意、美好、纯真的精神世界。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拥有自己的一片精神园地去抵抗种种困难和挫折是十分重要的。无论在哪个时代,儿童的天性和本真都是不可被忽视的,因此,儿童电影对于儿童来说,除了要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保护、尊重孩子的本性,富有童趣。而这一点,恰恰是很多儿童电影所忽视的。90年代的儿童电影为孩子构建美好精神世界的方式大致有两类:一类是诗意空间的构建,另一类是幻想空间的构建。其中,构建诗意空间的代表性作品有《草房子》。“草房子是那个时代记忆的象征符号……不仅鲜明地指出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等信息因素, 更是代表着逝去, 代表着追忆。”[10]影片以桑桑的视角去描写江南水乡的生活,描写油麻地小学的生活和那里的亲人老师和朋友们,风格清新自然、朴实无华,仿佛身处一个“世外桃源”。桑桑在这里获得的不只是知识,更多的是她作为一个小孩子,在童年时代应该汲取的营养——体会友情、感悟成长。纸月、陆鹤、杜小康、蒋老师和白雀以及桑桑爸爸等人物,是桑桑成长记忆的重要部分。作为贯穿整部影片的线索,桑桑以儿童视角去观察描写这些人物,体现了儿童眼中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和周围的人的。这部小说虽然是曹文轩的童年记忆,但却最大程度还原了一个孩子的成长记忆,向读者和观众展现出作者内心一直保留的纯真的诗意空间。“处于这一阶段的孩子,确实需打下一个具有亮色的底子。当将世界翻转给他们看时,应当更多地让他们看到纯洁、善良、美好的一面。”[11]另外,《天堂回信》也为孩子们塑造了一个诗意的精神空间。虽然影片中时代已经发展得很快,但是孩子和爷爷的生活却有着另一种平静幸福的节奏。影片还以童真的方式——用风筝给在天堂的爷爷写信,教会孩子去面对死亡。这样既守护了孩子心中的童真,又让孩子慢慢地接受这个世界的事实规则,从中获得精神成长。
以上,诗意空间的构建多建立在现实基础上,提供给孩子认识世界的新见解、新眼光。而幻想空间的构建多与科幻元素相结合,通过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趣味性来让孩子们在快乐中汲取营养。以《荧屏奇遇》为例,该片通过梦境将幻想世界与现实联系到一起,电视机则作为梦境实现的媒介。奇奇的梦使得影片中时间和空间不停切换,从而让奇奇去到另一个时空里展开一次次历险。“在时空并置带来的想象力飞翔中,时间概念与空间概念与影片情节的联系都非常紧密……《荧屏奇遇》用大量生动的细节表现了明朝人与现代人进入对方时空后产生的有趣场景。”[12]这部影片为儿童在历史时空上开启了想象的大门,且情节丰富,既有轻松愉悦的情节又有紧张刺激的情节,符合了儿童的好奇心和审美趣味。此外,还有《疯狂的兔子》,讲述了外星人入侵人类的故事,其中的关于人类命运的问题提出,引发了儿童对于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关注以及对科学的兴趣。
再次,徘徊在市场化的边缘。90 年代儿童电影多数仍处在市场化边缘或者未能实现市场化。在儿童电影的制作发行上,90 年代后期的儿童电影制作单位由电影制片厂为主体向着影视文化公司主体靠拢,这也间接说明了儿童电影正在向着市场化的方向靠近。但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仍有很多问题对儿童电影的市场化过程产生阻碍。比如,由于缺乏资金导致的宣传不到位。传统电影宣传方式在90 年代已经开始发生了改变,票房、盗版、明星、档期等话题,新闻发布会,开机仪式,首映仪式等都成为了新的宣传方式,然而这些宣传方式背后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电影本身的创作成本加上宣传成本,使得电影创作者在得不到票房回馈的情况下很难获得收益。因此,也出现了很多一味迎合市场,忽视电影艺术性的儿童电影。这也间接造成电影创作者创作儿童电影的意愿大大降低,让90 年代的儿童电影一度产生了低迷的状态,始终徘徊在市场化的边缘。根据《电影艺术》“国产电影票房排行榜”(1995-2002)可以看到有三部儿童影片的票房成绩都位列年度前十。《一个都不能少》位居1999年“国产电影票房排行榜”第二名,《背起爸爸上学》和《一个独生女的故事》分别位列1998年“国产电影票房排行榜”第七名和1995 年“国产电影票房排行榜”第八名。这无疑是儿童电影进入电影市场的成功典范。但是值得思考的是,《一个都不能少》并不是以儿童电影的身份进入市场的,它没有当作儿童电影申报,拍摄和宣传发行,也未参与儿童电影评奖。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当时中国的电影产业市场运作中,儿童电影是基本无法进入电影院线的。二是儿童电影还是以政府扶持为主,依靠制度优势,缺乏市场化意识和产业化思维。因此,90年代中真正能够进入电影主流市场的儿童电影数量不多,大多数儿童电影仍然处在市场的边缘,关注度较低。儿童电影究竟应不应该进入电影市场或者应该以何种方式市场化,是90 年代的儿童电影留给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
中国儿童究竟需要怎样的儿童电影,儿童电影如何真正满足儿童的需求都是需要探索的问题。90年代以来,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儿童的精神成长速度正超出成人的预估和想象。虽然90年代中不乏以“儿童本位”的佳作,但是创新发展的速度远远不够,尤其是喜剧和科幻类型儿童电影。“儿童电影群体中缺乏科幻小说家、文学家,又闭关自守,对当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欠缺,对未知世界想象力的淡薄,让中国儿童电影很难具有真正的科幻电影。”[13]反映社会问题的儿童电影固然具有教育意义,但是儿童天真、富有想象力和追求乐趣的本性也不容忽视。而且儿童生活的新颖性、丰富性和幻想世界的多层面和神秘性,也是儿童电影需要面对的。儿童电影在艺术表现上,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领地和拓展的空间。
结语
90 年代是儿童电影机遇和挑战共存的时期。儿童电影一面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和保护以及相关的资金资助,但另一方面“少年儿童的迅速成长超越了成人的想象,创作理念与受众需求的落差进一步加大,简单化、功利化和陈旧的生产方式使孩子们纷纷离开中国儿童电影,中国儿童电影‘需求与过剩产能’怪圈逐渐生成并激化。”[14]另外,由于国外优秀儿童电影的引进和影响,如伊朗儿童电影、美国儿童电影等,理论界对中国儿童电影创作的一味批评也十分不利于中国儿童电影的发展。可以说,儿童电影创作者面临着市场和理论界的双重压力,在创作过程中难以平衡,创作动力和激情也难免随之消弱。
总之,90年代的儿童电影承接着延续80年代儿童电影的繁荣与辉煌的重任,同时还要负担起在新世纪来临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适应电影市场化的任务。有人评价这十年是中国儿童电影发展史上的低迷期,但从更为理性的角度审视,90年代儿童电影经历了对过去进行反思调整,为未来进行准备和铺垫的十年努力。
——两岸儿童文学之春天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