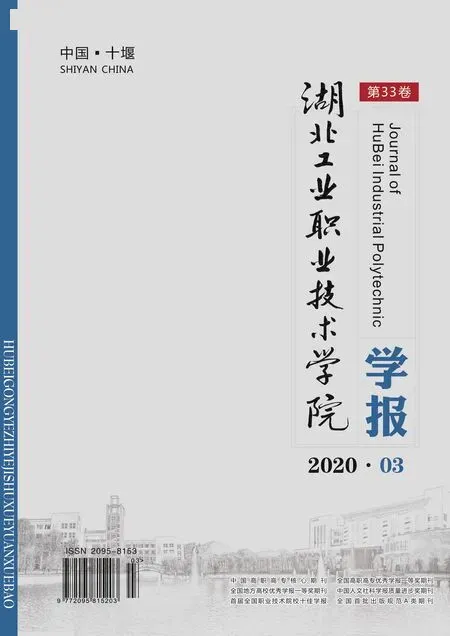东野圭吾小说《恶意》魅力探析
田紫钰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东野圭吾的代表作《恶意》是其挑战悬疑推理小说写作极限的佳作,被媒体和读者列为其巅峰之作,《恶意》创作的着眼点在于寻找犯罪动机,与重点放在杀人手法及真相推理,通过曲折的情节抓住读者之心的侦探主流小说背道而驰。东野圭吾通过《恶意》呼吁人们关注人性中“恶”的部分。本文立足于《恶意》的文本分析,探讨其魅力所在。
一、迷雾与黎明
小说《恶意》同其他推理小说类似,同样选用了由凶杀案这一典型素材来引出故事主要人物、推动情节展开。但《恶意》不同于其他推理小说的是,并非如以往解方程那样一点点求出最终X的值,而是仿佛置身于一个偌大的迷雾之林,必须冲破重重迷雾才能迎来破晓的黎明。
(一)遍布的迷雾
小说《恶意》的案情发展跌宕起伏,在尘埃落定之前,案件实情被层层迷雾所笼罩。
迷雾渐起,凶手野野以被害人日高好友的身份出场。刚开始就以日高“毒猫”事件以及日高所说的诸如“你说的那个女人是不是长得像木刻的乡土玩偶……有个读初中的儿子——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混蛋[1]8。”此类的犀利刻薄的言语将日高刻画成一个阴沉、冷酷甚至有丝丝心狠手辣之人。而从野野对好友日高“毒猫”事件的反感以及野野的谈吐等方面将野野刻画成一个礼貌、善良之人。此时此刻,迷雾已悄然来袭。
迷雾弥漫,凶手野野很快被捉拿归案,并对罪行供认不讳,但对其作案动机三缄其口。在警方的努力下,在野野的诱导中,在诸多似乎无懈可击的罪证以及野野与警方调查几乎吻合的自白书前,凶手野野成了被迫无奈,为心爱之人犯罪的令人同情的对象,而闻名的小说家日高瞬间成了受万人唾弃的剽窃者。案情至此,早已迷雾重重。
(二)破晓的黎明
黎明破晓之前,迷雾遍布。所有警方费尽心思查出的,凶手已经坦白的所谓的“真相”并不是案情真真正正的真相。在侦探加贺以自己对前同事野野的了解以及自己对此案尚存的疑虑之下,在彻查凶手与被害人的过去之后,几经波折,遍布的迷雾渐渐散去,隐藏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迷雾渐散。最初的杀猫桥段并非真的是日高所为,而是凶手野野为了营造出日高的残酷形象精心设计的,毒猫的真凶正是野野本人。从野野家中搜出的一切看似完整,毫无破绽的证据链其实皆是凶手野野耗费一年多的时间费尽心机筹备的。
黎明破晓。善良的日高从未伤害弱小的野野分毫,甚至多次无私给予其帮助。日高本于野野有恩,然而野野不仅毫无报恩之心,甚至恩将仇报,将之无情杀害。夺走日高的生命对于这场阴谋来说只是刚刚开始,并非野野的真正目的,野野真正想要做的是破坏日高辛苦建筑的一切,贬低日高的人格,让日高成为众矢之的。
拨开迷雾,隐藏在凶杀案背后的是自卑,是无能,是嫉妒引起的深深的恨意,是深不见底,让人脊背发凉的人性之恶。当这股恨意无限膨胀,所诱发的便是一场人性悲剧。
二、作品架构与艺术手法
读者在阅读《恶意》的过程中,总以为已将所有真相了然于心,然而却一再发现正不断掉入作者设下的一个又一个的陷阱里。这正是由于《恶意》不同于以往侦探推理小说的别具一格的创作手法以及独特的叙事手法造成的。
(一)悬念设置——翻板式
小说《恶意》中引人入胜的情节建构以及精妙绝伦的悬念设置是其俘获众多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在情节悬念设置上跌宕起伏、一波三折,主要呈现为“翻板式”的情节结构。
传统小说是以情节发展为脉络展开的,从而形成了一条或一条以上的线索。情节线索延顺、推移,要经历四个逻辑阶段:开端、发展、高潮、结尾。这种以情节发展为线索来组织、营造小说的结构,被称为情节结构[2]57。作为小说中一个重要分类的侦探小说,自埃德加·艾伦·坡以来,侦探小说这一特殊的文学样式创作出了一个虚幻的世界,它的创作受一定规则的制约,背景、情节与人物都依据一套模式,即:“罪犯—侦查—推理—破案”[3]28,人物设置为“侦探—案犯—第三人”[3]28。有类作品,由于某一原因的推动,情节顺势发展,但发展到一定阶段,主人公突然发现这一成为推动力的“原由”并不像最初判断的那样。至此,形势发生逆转,就好像一块木板突然翻过去。这样的结构被称为“翻板式”[2]27。东野圭吾小说《恶意》在情节设置上大体继承了以往侦探小说“案发—侦查—推理—破案”的情节模式。但在设计情节时,他采用了“翻板式”的艺术手法,使得小说更加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以往的侦探小说情节悬念设置在于“谁杀了他”,即凶手是谁,而《恶意》的情节悬念设置在于“为什么杀”,即探明作案动机。小说《恶意》在不到三分之一处,凶手就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对犯罪动机含糊闪烁。在之后三分之二的篇幅里,“犯罪动机”成了唯一的悬念,随着侦探加贺一步步追踪罪犯野野的作案动机,真相渐渐浮出水面。当加贺查明作案动机,野野也亲口承认并以手记的形式记录下自己的犯罪动机,当了解了野野作案动机后,所有人都会以为被害人日高是个残酷伪善之人,都同情凶手野野并以为事情已水落石出、尘埃落定时,情节就在此刻突然大翻转,原来这所谓的被查明的作案动机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阴谋,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野野一手策划的,目的就是毁掉被害人日高的声誉,让日高受世人唾弃,其实日高才是最和善的人,而野野则为最阴暗的人。凶手诱导了侦探,误导了大众。
“翻板式”的结构使得情节曲折并盘旋而上的向前推进。《恶意》中对案情真相的探索,经过一次次的侦查,仿佛渐渐靠近真相,但又一次次的将所探知到的结果给予否定。每当读者认定最终真相已然到来,案情终将结束时,却发现又一次被蒙蔽,作者不知不觉就将读者带入他所设计的迷局中。
(二)叙事结构——双线交织
东野圭吾在小说《恶意》的创作中采用了复线叙事的手法,以野野和加贺二人手记的形式将情节呈现给读者。分别以野野—罪犯,加贺—侦探,二人的视角带领读者解读全文。《恶意》的叙事手法和普通的叙事手法相比,无疑是更加独特的。其两条主线并行不悖,两条线索看似平行,实则相互交织。一方面是罪犯野野的手记,记录杀人案整个事件的经过以及自己的犯罪动机。另一方面则是此次案件侦探加贺的手记,记录探案经过以及最后的真相。推理小说中采用双线叙事结构,双线并行、双管齐下,使得整个案件更加扑朔迷离、扣人心弦。两条线索分别以野野和加贺二人的视角将案情涉及的所有人物、事件、场景、过程相互牵连,使得其得以同时向前发展,至结尾处、于真相时交织一处,经由反复回想对比,所有谜团才得以豁然开朗。
1.野野的诡计
双线之一——野野的手记。小说开篇便用野野的手记带领读者了解背景,走进案情。从野野这条线索中,展示给读者的日高的形象无疑是一个十分残忍且无耻的。一开始,野野和日高以及日高之妻日高理惠一起讨论那个开篇映入读者眼帘的奇怪的女人和她的爱猫究竟死于谁之手,日高理惠以及野野都认为无论以什么理由日高都不可能杀死那只猫时,日高最后竟然阴沉的说道:“是我做的”[1]10,不禁让人内心一颤,对日高的印象大打折扣。以至后来在告白之章,野野又以手记的形式自述作案动机之时,先是提及自己与童年故交日高通信以及和日高见面的闲聊中提到自己创作的第一本小说《圆火》时,日高热心提出要帮忙看看野野的小说内容如何并打算帮他介绍编辑,然而遇到瓶颈的日高发现《圆火》的故事情节极其有趣,完全沉迷其中,以至萌生想要抄袭野野作品的念头。对于想要知道自己作品究竟如何的野野打来的电话,日高一而再再而三的找借口搪塞,并想方设法打击野野,阻碍他成为专职作家甚至让他放弃作家梦。不禁让读者深感日高的自私和虚伪。后来写到因为野野和日高前妻日高初美二人之间萌生爱意,野野被告知初美想要分手,理由是日高可能已经察觉自己与日高初美的关系,怕自己所爱之人受苦,所以对日高萌生杀意。结果行动失败并被日高掌握了自己杀人未遂的所有证据。此后不久,日高将野野的作品《圆火》偷走,稍作修改为《死火》并以自己的名义发表。这无疑对野野来说是最好的报复,就像野野自己所说那样:“对作家而言,作品就好像是自己的分身,说得简单一点,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作家爱自己的创作,就像父母爱孩子一样。”[1]163然而日高对野野的报复才刚刚开始,日高紧紧的将野野攥在自己手中,以杀人未遂的证据将之控制,甚至逼迫野野为自己代笔,做自己的影子作家。日高不仅绝情的抢走了野野以往的作品,加以修改以自己的名义发表甚至还以野野和自己妻子初美偷情为原型创作小说,逼迫野野创作新的作品,用现成的小说来换取不将以他们偷情为原型创作的小说公之于众。直到日高和日高理惠新婚并准备移居温哥华,野野以为自己终于熬到头,终于重获自由之时,却发现邪恶的日高并没有打算放过他,一旦有需要,仍然会无情的利用他。
从野野的手记中,感受到被害人日高无疑是一个非常“恶”的形象。整部小说以野野的手记开头,先入为主,读者会不自觉的置身于野野的处境。再者由于手记本身带有很强的真实感,作者从野野这条线展示出的日高伪善残忍的形象便十分容易深入人心。以至于野野虽然将日高杀害,但仍然会让读者感到他本性并非罪无可恕,受到日高非人般的对待,一时冲动做出无法挽回的事,着实也是情理之中。
2.加贺的解密
双线之二——加贺的手记。从加贺的记录、独白中,可以发现其实野野才是那最“恶”之人,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全然“恶”的形象,内心极度扭曲,饱含了满满的恶意,没有一点点的善,哪怕是到最后真相大白之时,仍然没有一丝悔过之心。
日高没有杀害邻居的猫;没有盗用野野的作品;日高的第一任妻子日高初美和野野之间更是没有不伦之恋,他们二人之间哪怕连一丝丝的暧昧都没有,故而野野不可能因此萌生杀害日高的念头,日高也不会因此掌握野野的把柄,更不可能以此要挟野野成为自己的影子作家,长期折磨野野。反而,对于野野来说,日高甚至应该是他人生中的大恩人。
小时候野野不愿上学,日高不厌其烦的天天接其上学。在日高的帮助下,野野每天按时上学,顺利的读上初中、高中甚至大学。虽然日高平时对野野亲切有加,然而在初中的校园暴力中,日高被欺负,野野却是最直接的导火索,野野加入欺负人的行列,成为校园暴力头目藤尾正哉的喽啰,甚至时常在藤尾面前讲述日高的坏话,以至于藤尾对日高深恶痛绝,更是残忍至极、毫不留情的欺负日高。初中的野野还成为了藤尾强暴案的共犯,因为日高创作的《禁猎地》以这次校园暴力为原型,而藤尾的妹妹藤尾美弥子正在因为要求日高将《禁猎地》一书收回或改写而多次和日高谈判。野野害怕因为这件事,自己曾经不堪的回忆被曝光,为了换取这段被人唾弃的记录,他不惜牺牲生命。
虽然初中之后野野和日高再没碰面,日高仍大方地接纳了曾在初中时期仇恨他的野野,恢复了二人的友谊,不仅如此,日高还替野野介绍出版社,让之能在儿童文学立足。而在与藤尾的妹妹藤尾美弥子的多次谈判中,日高也一直都没有提及与《禁猎地》这本书有密切关系的野野。对于一直真心把野野当好朋友的日高,对于一直帮助野野的日高,野野没有一丝丝的感激之情,反而对日高充满深深的恶意,野野即便是赌上自己所剩无几的人生,也要奋力一搏以贬低日高的人格,让日高受世人唾弃。
3.双线交叉
在《恶意》这部推理小说中,东野圭吾以交叉的形式从加贺和野野这两条主线轮番介绍案情的探索过程。一方面带领读者寻求真相,另一方面又在不断的误导读者,阻碍读者获知真相。整部小说围绕野野的手记和加贺的记录,双线交叉并叙。两位主人公及相关人物相继出场,并在不同情境当中完成对人物角色的描写与塑造,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画面重复之感。两条主线看似平行,实则相互顺承,相互交织。
首先由野野这第一目击者的手记向读者阐明凶杀案的情况,接着穿插侦探加贺对案件中疑点的记录,随之又用野野的手记告知读者真凶为何人。双线交叉顺承至此,凶手是谁已真相大白,但小说的高潮才刚刚开始。小说最精彩的部分便是对野野作案动机的探查,于是接下来便穿插了加贺关于探究案情的记录,随着加贺通过种种蛛丝马迹查明了野野的作案动机,接着便顺理成章的插入野野的手记向读者更加详细的介绍其作案动机。由于野野对于作案动机丝毫不愿坦白,加贺无奈之下只有自己于困难重重中查找真相,最后终于查明,野野也终于坦白,然而殊不知这所谓的真相竟是凶手自己一手策划的。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以凶手利用侦探之口说出自己策划的动机,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更加信服这一结果。在读者都以为事已至此该是结案之时,加贺的探究记录又再一次映入眼帘,否定了之前公布的真相,案情来了一个惊天大逆转。
小说《恶意》就是通过上述两条线索的交替发展,将矛盾不断向前推进,使情节更加曲折,使人物性格不断丰富,主题不断深化。
(三)叙述视角——多重性
《恶意》的叙述视角并非是单一视角,而是以内聚焦视角为主,兼采用外聚焦视角等多重视角架构全书。
胡亚敏在《叙事学》一书中将视角定义为:“叙述者或人物与叙事文中的事件相对应的位置或状态,或者说,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4]小说艺术视角主要是从故事叙述角度而言的一种艺术技巧,视角对小说而言举足轻重,在对它进行划分时,国内学者多采用的是热奈特“聚焦”这一概念。
在小说《恶意》中,东野圭吾通过他视角,通过具体视觉交叉转化的方式带动故事发展。他首先运用内聚焦视角,将聚焦者设置为与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重合,每件事都按照凶手和侦探两个人的感受和意识来呈现,东野圭吾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以两位叙述者手记体的形式交叉呈现故事内容,这种叙事角度确定了作品在叙述视角问题上得以表现出自己的特性。在这样的小说叙述情景中,作者必须极力规避主观评价的部分,而是完全置身于小说中两位叙述者,站在叙述者的角度展现故事本身。读者不自觉的以这两位人物的眼睛去观察,原则上会倾向于接受由这两位人物所提供的视觉。也正因如此,读者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跳入作者设置的圈套之中,才会有一次次被告知真相又随之被否定的被欺骗之感。最后小说快结尾之处又采用了外聚焦视角,将观察者置身于小说人物之外,只能了解人物的外在特征,不能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因此作者在结局之处给读者设置留白,小说未带领读者走进凶手的内心世界,不知凶手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究竟是真的认识到有错并后悔,还是丝毫没有悔过之心,给读者留下了一定的遐想和沉思空间。
《恶意》之所以取得成功,很重要的原因是其视角的多变性,是其悬疑设置的巧妙性,东野圭吾将骗局写到了极致,一切出乎意料又仿佛有迹可寻,丝毫不显突兀,迷倒了无数读者。
三、《恶意》的双重意蕴
与其说这是一个关于谋杀与侦破的故事,是对谋杀的解析。不如说这是一个关于社会问题和人性悲剧的故事,是对社会问题的思索,对人性中恶的揭露。东野圭吾的侦探小说往往存在双重真相,一个关于案情本身,另一个则直指人心。在《恶意》这部小说中,东野圭吾不断地阐释“杀人动机”,而在阐释“杀人动机”的过程里,他像抽丝剥茧般把人深藏在内心的丑陋情感和现世社会的冷漠暴露出来。正如东野圭吾所说:“我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带给读者更多的东西,比如人性的独白,比如社会的炎凉。我想,这些东西是人类永远需要关注的命题,因此不存在‘过气’的危险。”[5]因此,在他描写的犯罪问题的作品中,充满了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和浓厚的人文关怀。
(一)扭曲的人性
人性是东野圭吾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话题,小说《恶意》毫不例外的将人性,尤其是人性之恶呈现于读者眼前。一个人内心深处隐隐潜藏的恶意,究竟能诱导他做出何等匪夷所思的事情,看看小说中的野野就能明了。尤其是在得知自己患有癌症,将不久于人世,心中的恶意便再也抑制不住,犹如熊熊烈火般喷涌而出,这种负面情绪初始时是极其细微的,结束时却极为澎湃。这个世界有两种恶意是最最荒谬而又无解的。一种是没有缘由的讨厌,就是单纯的看对方不爽,犹如小说中对校园暴力的描写,当问到暴力施行者为何要欺负被害者时,他只回答了一句话:“因为看他不爽。”[1]243多么简单的一句话,多么无意识的行为,却成了施暴最直接的导火索。而另一种则是由于对自己无能的无可奈何而加诸在自己所嫉妒的人身上的发泄似的恨。当杀人沦为其次,诋毁人格首当其冲,令人恐惧的其实并非暴力本身,而是那些讨厌自己的人散发的负面能量。
野野恨日高,恨他那么善良,恨他明明出身不如自己却一步步超过自己,恨他抢先一步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恨自己当初如此不屑的他如今竟有了光明的前途,恨他活在一个自己只能仰望、无法触及的高度。野野更恨自己,恨自己时运不济,恨自己龌龊不堪。所以,野野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连对自己的恨一并还给日高,用最残忍也最具毁灭性的方式彻底击败日高,让他带着世人的骂名下地狱。即便在他死后,仍然继续恨他。
东野圭吾笔下的野野并不是单单指某一个人,而是一个象征,象征心灵极度扭曲的一类人。细小的恶意潜藏在每一个的心中,恶意源于自私贪婪,源于一种唯我独尊、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考方式,这种所谓的恶意也是人性中不可避免的黑暗面。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是最美的爱情。恨不知所起,深入骨髓,是最冷的人性。当原罪被放大,总有一角能照出自己,东野圭吾将这种恶意放大到极端,让人们不得不省思深不见底的人心。
(二)冷漠的社会
东野圭吾的小说并不是脱离社会生活的传奇文学,在精彩纷呈的故事背后,是他对社会问题的强烈关注和对人生的各种体验。因此除了足以让人深思良久的人性问题之外,小说《恶意》呈现出的另一个直击人心的问题便是社会的冷漠问题,在这个社会中,群体性的冷漠不禁让人心底生出寒意。
这场刑事案件中,明明日高一家才是真正的受害者,然而世人却把案件当成演艺圈的八卦绯闻,不管是新闻媒体的报道还是电视的真人访谈,大家更感兴趣的是著名作家日高盗用友人作品的新闻,以及这其中牵扯的外遇事件,而非他被谋害的事实。日高死后,日高理惠作为亡者之妻本应得到大家的同情与安慰,然而扑面而来的却是一系列的世人的责骂与各种纠纷。如加贺所说:“据我推测,这些存心攻击的人应该都是日高的书迷,真正的文学爱好者恐怕很少。不,说不定这其中大部分人从头到尾就只知道日高这个名字。这种人净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还一天到晚注意哪里有这样的机会,至于对象是谁,他们根本不在乎。”[1]193加贺的这段话可谓是道出了人人都知道但却几乎没有人会真的将之拿出来进行批判以及想办法改善的社会真相。
在这个暴戾冷漠的社会大环境之下,人与人之间也越来越冷漠,缺少关爱与温暖。在这群体性冷漠的社会里,有太多的人都只愿做一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路人,都努力的将自己置身事外,又或者以他人的痛苦为热点取乐。然而殊不知在这同时自己也正被邪恶四面包裹,遇事时别人若也同样冷漠相待,那么便只有绝望的品尝自己亲手酿造的苦果,求助无门。东野圭吾通过《恶意》提醒世人,世界上最无用的,是你拥有着可让这个冷漠世界充满爱的方法而你却把它深埋心底。
四、结语
东野圭吾作为当今风靡全球的推理小说家之一,其作品不可避免的备受关注。《恶意》作为东野圭吾众多作品中最具盛名的小说之一,其畅销的内在原因自然而然的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之中。因此,本文通过对《恶意》的文本解析,探讨了《恶意》吸引众多读者的魅力所在。从作品的架构和艺术手法分析了其情节上悬念的设置主要为“翻板式”,由此不断地给读者带来惊喜或落差;其叙事结构主要为复线齐驱,以致伏线千里、隐显自如;其叙述视角主要是不定内聚焦多重叙述,使得叙述话语之间形成内在的张力和巨大的反差。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了人之恶的内在意蕴,从社会的角度分析了恶意的根源所在。
东野圭吾的小说之所以成为推理小说中的经典,《恶意》之所以成为其代表作,不仅仅是因为其独特的创作手法和作品风格,更多的是因为其反映的人性和社会问题直击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