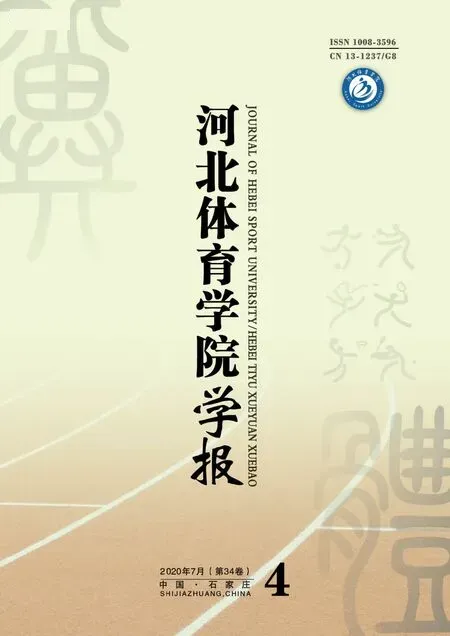新时代中国学校武术教育中主体塑造的文化逻辑
杨国珍,段丽梅
(运城学院 体育系,山西 运城 044000)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进入新时代,以文化自信作为精神支柱实现中国梦,隐喻了践行文化自信弘扬中国精神的时代要求。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近年来,国家对武术教育及发展日益重视。2004年,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发布的《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实施纲要》中建议体育课中适当增加中国武术;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又为武术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进入新时代,武术更是被赋予助力国脉传承的历史使命[1]。学校武术发展至今已百年有余,从设立武术课程之初“强国强种”的厚重期望到当前“学生喜欢武术不喜欢武术课”的悖论,甚至出现了学生“学跆拳道,体验中国武术精神”[2]的错位性主体塑造,反映出学校武术对主体培育的弱化或异化严重。“少年强则中国强”,学生是传承武术文化的主要群体,通过培育民族精神对学生进行主体塑造是新时代学校武术教育的使命,本文对学生主体塑造的文化逻辑展开研究,旨在促进学校武术更好地发展与改革创新。
1 记:武术教育的低效传承与主体异化的起点
1.1 学校武术教育的体育化传承与外向评价追求
学校武术教育开始于中国话语体系濒危的近代,学习西方给中国的教育带来巨大的推动与创新,但无形中也改变了中国教育的内在文化逻辑。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考察时指出:“中国教育‘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教育如此,体育亦然。学校武术教育文化逻辑改变首先开始于武术传承模式由师徒制转向班级制,1915年许禹生的议案《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得到教育部的政策性支持,武术得以在学校课程中迅速普及与推广[3],当时有评论指出:“教育界能注重于体育实自此始;吾国旧有武术得加入学校课程,亦自此始”,但学校武术传承的班级授课模式也自此始。学校武术班级授课的显著特征是强调外在动作的规范与标准,动作练习中“主观意识太强,一手接一手的做出来,是操控出来的”[4],某种意义上讲,造成了武术的“操化教育模式”并一直持续至今。
1.2 外向评价催生了记忆式学校武术教育与低效传承
16—19世纪,西方体育教育是一种注重外在技术训练效果的身体教育范式,其理论依据是实证自然科学,主要追求以仪器测量而得的肢体力量、速度等外在锻炼效果。虽然外向评价的实证效果明显,但学生多处于被动地位,动作学习中受外在程序指令而完成动作的成分多,自我意向性感知与体验完成动作的成分少,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学生主动参与感知及能动性实践的主体意识的形成。
20世纪初,中国学校武术教育一开始就走进了“体育化”的发展之路,效仿西方体育的方式与方法进行兵式体操和操化套路模式的教学,开启了追求规范与标准的“分解动作和控制练习速度和节奏”的外向效果评价教学模式[5]。学校武术教育中以教师为中心的操化教学导致学校武术低效传承,具体表现为操化练习中的武体分离,以马良为代表的中华新武术即是典型代表,当时分段分节地配以口令的教学体现为操化武术的教学范式[6]。学校武术班级制操化教学的初衷是易于推广与普及,但由于学生武术动作学习与身体动作意向的主动性、能动性分离使得实际学习效果大打折扣。强调标准与规范认识论的武术教学催生了学生以“记”为主导的学习方式,学生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一遍遍熟记动作等,造成当前“学生喜欢武术不喜欢武术课”“考完忘光”[7]等尴尬现象。学校武术低效传承的实质是操化教学催生了抽象主体的培育。“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尔反思之后,人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知识、价值、行动源头的一致性与普遍性主体,福柯将这样的主体归为一种限定性结构,并认为“只有在这种限定结构中,主体人才可以达到主体哲学渴望的可靠性。”[8]受西方体育话语裹挟的学校武术教育亦然,武术学习主要目的发生了转向,由生存教化培育具有内在自由人格的精神主体,转化为记忆动作方向、角度与幅度等外向规范与评价标准的机械化抽象的人。在以知识论为旨归的体育化学校武术教育中,学生的学习成效变成了表征规范与标准的数字,缺少了身体内在性的主体具身认知,武术真正的习练主体——学生(人)消失了。
2 感:武术传承的文化基因
2.1 武术的技击本质特征与敏感感知需求
武术是“击必中,中必摧”的攻防技击术,就其杀伤力而言可以造成伤害甚至危及人的生命,就武术技术本身传承而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敏感性是习武之人必备的能力与素质。关于武术学习方式,言传身教启迪下的体悟已成共识。清代武禹襄早在《打手论》中就明确做出了“心知才能身知,身知胜于心知”的经验总结。当前,一些传统武术传承人口述史如《逝去的武林》《高术莫用》等问世,传承人以切身体验与习武经历再次明证了武术就是练敏感,即“悟”而习武[9]。“悟”是习武人身体因“感”而有的直觉与反思,常在为何有此一动的“肢体间处处相互连通,相互呼应,构成一个整体”[10]的身体感应中唤醒身体的自我与主动意识。借形意拳名师李仲轩的话讲就是“打人跟预定似的”“看对手给什么好处”,要能根据情形随机应变,“反应是反应,反击是反击”[11],反应与反击“心动而手能为之”的知行一体才是真正的身体敏感。无论反应还是反击,都以身体之“感”为前提与基础。师傅教的东西只有自己练出来,身体明白了,才是真的明白了,必须经过实战模拟的感应训练才能体现为主体的能动化实践内容,否则一到较技时必然如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所云“手足仓皇,至有倒执矢戈,尽失故态。”
2.2 武术“性命双修”的功夫特征与交往、性情感知需求
武术不仅是攻防技击术,更讲究练武以成人,是内外一体化的“内圣外王”性命双修功夫与生活艺术[12]。关于功夫的修养,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武术的修养功夫是对孔子主张的继承与创新。在武术技术传承中,武术习练从外三合到内三合的自我与技术的合一,是追求劲力的结果。劲的典型特征为“一”,武术技术习练的术我合一功夫需要在“齐”“整”“通”等劲力的不断感知与体验中获得;武术人的社会交往由制人到“拳拳服膺乃为拳”制己的自我与他人(他物)的“人我合一”,是武术人善养浩然之气的结果,气以直养而无害,武术人际交往的“人我合一”功夫需要在“服人”“理解”“感动”等互动感知与反思中获得;武术身心修炼中由怒而暴的征服到由静制动的身心合一,是合目的性与规律性的内心审美的结果,武术以静为本,身心合一的修炼功夫需要在“感于物”“由敬而静”的蕴发感知与反思中获得。“武术教育是体知性在身、有身的身体教育”[13],有“可感之思”[14]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力。武术人的性情修养甚至对传统社会秩序的维持与建构发挥作用,“传统社会人有了纠纷不找官府,找行业外的第三方”,武术人常以“武人文相”在民事纠纷中“充当仲裁角色”[15],传统社会找武术人仲裁不是实证逻辑的作用,而是武术人给世人侠义、勇武、公正之“感”所起的作用。
2.3 武术整体性的万物一体世界思维与意象感知需求
“拳无拳,意无意,无意之中是真意”,指出了武术习练中练意不练力的特征。力是一种自然科学理性经验思维的产物,注重分解与规律,要获得力量,关键要进行肢体训练。理性经验思维认为力量锻炼主要是提高肌纤维的持久力和耐力。武术练意不练力,注重取象而达意,武术的意象认知是以一种整体性思维来认识世界。意象是想象的产物,是人类一种重要的感知觉,具有超逻辑性。有学者研究认为,武术的意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通过人与人、物、周围环境等构建起了“气—意—神的阶序叙事”[16]。关系性存在的认知前提是自我意识对世界意义认知的觉醒,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是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的主客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一种万物一体的生态关系,这种认知的觉醒需要依赖身体感知的主动唤醒。
3 武术新身体之“感”与主体塑造
3.1 武术的技术新身体生成与人化自然、自然人化的相互成就
马克思曾讲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武术除与西方体育锻炼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各项运动技能成绩等功能相同外,还可为人类贡献出体悟运动技能、形塑新身体的教育经验,如武术中枪法三尖相照、形意拳内外三合的新身体,成为延伸与拓展人感知能力的媒介。武术人不但借助器械等生成新身体,还通过思考与想象,与自然沟通生成人化自然的新身体。同时,人又需要自然人化进行文明化的生成,“人类只有否认自己的动物性,其自我身份才能得到确证”[17]。
《晏子春秋》“民物相攫,而有武矣”解释了武术的起源,武术是人与自然的生存斗争和人与人之间的身体较量。在长期实践发展中,人们逐渐积累了如何能打的效果更好、付出代价更少的经验。人们向大自然求助,诸如形意拳、太极拳、八卦掌等拳种就是人与自然沟通的产物。武术人不断吸取大自然的智慧融于武术,同时也构建了武术人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通过内视格拳形成武术的自然人化,如以“拳如流星眼似电,腰如蛇形步赛粘”等大自然为标准,“对真实身体理解的深化”[18]而自然人化。武术人采撷自然众物之长,不断突破自身限制,形成人与自然万物的互通有无。
3.2 武术的道德新身体生成与共同体建设的相辅相成
武术之感不仅表现在以技术突破自我,还表现在与他者的理解与感通而形成共同体。《说文解字》中“感”是指“动人心”,意思即感受意图,“‘感’让认识的主体和对象之间产生了一种了解,形成相互之间的反应。”[19]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中,血缘关系成为维系共同体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武术传承模拟血缘关系进行门户传承,通过情礼并施、角色扮演、亲亲时间中的身体交互等感应与理解家文化构建[20],不同于传统规训的伦理身体,而以亲亲之家整体化了的个体道德新身体进行门户共同体建设的实践。
武术道德新身体常通过替代式“物对手”、点到为止的“象征性对手”等以武会友的文明对技途径,以适度的用力及审美化形式转化武术“击必中、中必摧”的外向制人而为内向的制己[21],进行个体的道德自觉和修炼,同时维护着武术门户之间的稳定与秩序。武术人的道德新身体还将实存性的道德目标转变为改造社会的实践力量,如武术人常通过含蓄小动作、说招等和平比试的身体资本来塑造符号化的侠义、公正等社会形象,这种符号化的道德责任感目标某种程度上趋向于产生义务引导行动,既是主体自我的体现与生成,又是生活共同体之大家庭建设的前提与依据。武术门户道德新身体进行主体教化和服务生活共同体建设的经验是当前学校武术主体培育应该继续传承的文化逻辑。
3.3 武术的情感新身体生成与精神气质培育
“情”是人类与自然沟通、认知和利用自然的重要途径。中国将心理认知还原到“情”,武术融精神气质修炼与自然规律认知于一体,在情的体认中重新认知自我,也贡献出以“动作求道的情支撑”体现武术人气质[22]的本体化教育经验。“情”指的是“喜、怒、哀、乐、爱、敬之心”,传统文化认为此六心不是人的自然情感,是人的欲望对外物的“有感而应”,“六者之心,人之所不能无,唯感之得其道,则所发中其节,而皆不害其为和也”“人所具有的六种情绪要表达得恰如其当,要依赖于人类所具有的‘感’”[19]。这种观点与儒家修养功夫中的“已发”“未发”观点接近——感于情,在动作的发动处进行功夫修炼,主动积极地来应对世界。形意拳名师李仲轩讲“大自然里有的形意拳里都有”,武术正是“有感动就有功夫”[11]的修炼,武术习练中有虚势则喜、逼门则乐、过势则哀、着力则怒等习拳情绪与感知经验,知觉是依情而有的自觉和智照,正是在对怒以生暴而为人所乘等的感知与功夫修练中,武术技术才逐渐回归自我“静”的本心,可以说武术动作习练不只是练技术,更是人的修养功夫。孙禄堂说“武术可以变化人之精神气质”,刘奇兰拳论摘要有言“形意拳之道无他,不过变化人之气质,得其中和而已”。情因感而节制,“在这里‘感’不仅指‘感知世界的能力’,还具备‘辨识善恶的禀赋’”[19],武术因感能借助情绪“变化人之精神气质”[23],成就独特气质的精神主体。
4 武术以身体践行文化自信与重塑新时代中国人
4.1 身体教育:新时代学校武术需要重构内在超越的主体培育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24]。文化自信的核心和灵魂在于价值观自信,“只有坚持文化自信,才能真正坚定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自信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必须坚持文化自信”[25],这是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姿态,但“需要以纵深的历史视角和宽广的世界眼光”[26]。从公元前8世纪至2世纪的文明轴心时代开始,中国就靠着独具东方智慧的话语体系长期雄踞世界,鸦片战争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话语体系缺失,学校武术教育亦然,在西方体育教育话语裹挟下言传身教的武术传承出现了与身体分离的主体培育困局。历史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要做到文化自信,首先要做到文化自觉,复兴中国的话语体系。耶鲁大学原校长莱文曾指出“每一种教育模式都具有文化适应性”[27],“一个国家的教育模式要与文化相适应”[28]。中国传统文化是体悟式的文化,重构中国武术教育的话语体系不能脱离体悟即“感”这一逻辑起点。从上述武术主体塑造与培育可知,身体化的术我合一、人我合一、身心合一是中国本土与特色化武术“练以成人”[22]的教育经验,体现着武术主体培育内在超越性的教育话语体系。在以标准与规范等外在评价为主导的学校体育教育背景下,需回归身体、创新性继承与重构武术传承感知或体认内在修养功夫的教育逻辑,反求诸己以内在修养实现道德境界提升与自我完善,实现道德行为与道德完善的主体性培育。所以,以“感”为逻辑进行身体化的主体培育将是新时代学校武术教育的文化自觉实践。
4.2 武以成人:新时代学校武术教育培育知行合一精神主体的历史使命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与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宣示中国进入新时代,并进一步将“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确定为教育总方针,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培养“明大德、守公德、立私德”的新时代文化新人。如何培育“人”已然成为新时代教育的重中之重,也是助推中国梦进程中当代教育工作者必须面对的根本任务。在“武术何为”的元问题讨论中,中国武术是“性命双修”的“德”性文化[12],“武以成人”[29]已成共识,并提出了“由社会人而武术人”[22],由武术人又回归社会人(“学武术,做中国人”[30])的教育途径。在新时代“立德树人”背景下,民族精神是国家的灵魂与支柱,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特质与风貌,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提出学校武术教育助力国运昌盛与国脉传承的宏大理想目标,更加增强了学校武术教育培育宏观民族精神和微观个人德行一体化的中国人的历史使命。关于做人,明代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在继承孔子忠恕之道实践论基础上提出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是道德实践之必须,是人之为人的必须[31]。哲学家杨国荣先生认为人因事而在,事在人的存在过程中具有本源性的意义,“‘心’生成于‘事’,‘物’敞开于‘事’”“‘心’与‘物’基于‘事’而达到现实的统一”,并且指出,只有进入现实知行之域的人化对象才能具有现实的品格[32]。“武术是身体文化”[33],拳种是武术的标签或符号,“身知胜于心知”的拳种学习可使武术人达成技术学习、文化传承及精神培育一体化的学习效果[30],实现主体培育的内在超越。如此相异于认识论层面的操化武术学习,从本体论感知层面进行知行合一的学校武术教育将通过“武以成人”助力新时代中国梦实现。
5 结语
中国武术不是简单意义上身体操演性体育项目,只强调知识和技能的学校武术远远不能达到“武以成人”而助力国脉传承的教育理想。学校武术只有坚定“学武术,做中国人”的理想信念,重拾武术身体文化因感而悟、知行合一的内在超越逻辑,创新性地回归武术传承的功夫哲学话语体系,才能真正践行“武术是身体文化”的文化自觉,以“拳”练“人”通过内在修养功夫培育知行合一的主体性“中国人”,弘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价值观,服务复兴中华文明的中国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