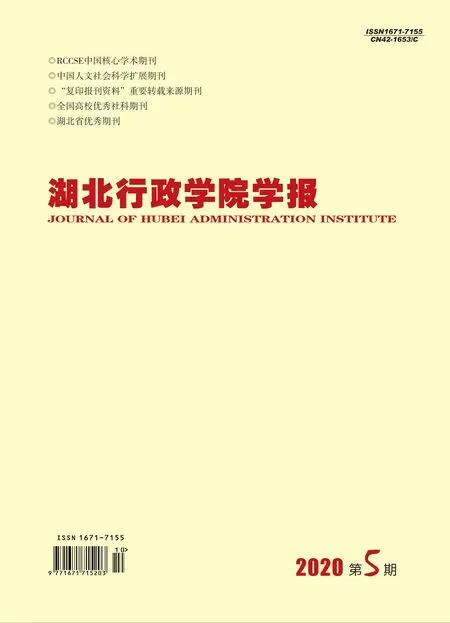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理论的三个贡献
贾 帅,俞良早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210046)
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是指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过程中,为了实现革命的目标,通过对革命形势发展变化的判断,在不同条件下采取的具体的行动方针和斗争方式。1883 年马克思逝世后,尤其是到了19 世纪90 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已发生新的变化,这就促使恩格斯不得不反思新的历史条件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提出了怎样的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应该如何解决,不仅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能否实现预期目标,而且还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败。因此,恩格斯晚年的革命策略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一、通过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方式的再认识,提出议会斗争和武装斗争两手准备的理论
斗争方式的选择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时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方式的选择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
19 世纪40 年代,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取得政权的唯一方式。恩格斯在1845 年完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写道,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不得不放弃和平解决英国社会问题的任何希望,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暴力革命。”[1](P48)《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是恩格斯在英国生活期间,深入工人住宅区,亲自调查了解工人阶级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而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恶劣的生存环境深深地触动了恩格斯,他认为,资产阶级为了获得利润,不择手段地压迫和剥削工人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可言,除了暴力革命,他们没有任何其他的斗争方式可以改变自身处境。基于这样的时代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2](P435)。也就是说,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尚不成熟,自我调整能力有限,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异常尖锐,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时唯一可能的选择。
到了19 世纪70 年代,尤其是巴黎公社失败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相对和平发展阶段,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意识到,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手段实现自己的目标。在1872 年9 月8 日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他说:“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在英、美等国家,“工人可能用和平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3](P179)马克思在这里用了“可能”这样一个字眼,说明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民主制国家,工人阶级或许可以利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可能并不是绝对,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式不能一概而论,必须根据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而定。比如,像德国这样的专制国家,宪兵的步枪还抵在无产阶级的“头上”,这时的无产阶级就没有办法用和平手段来实现自己的诉求。应该看到,利用和平方式实现斗争目标只是马克思提出的一个设想,这种斗争方式还未被真正付诸实践,不曾受到实践的检验,所以武装斗争在这一时期仍然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时的主要选择。
在马克思逝世之后,尤其是到了19 世纪90 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不小的胜利,无产阶级在议会斗争中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这促使晚年的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斗争方式有必要进行再认识,并提出了议会斗争和武装斗争两手准备的革命策略理论。
1.议会斗争是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
德国政府于1866 年开始实行普选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抓住这个机会,利用普选权扩大自己的政治实力。经过努力,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选票数量从1871 年的10.2 万张增加到1877 年的49.3 万张。1878 年俾斯麦政府颁布旨在镇压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反社会党人法》,在该法令实行期间,社会民主党被宣布为不合法,党的组织被取缔,党员的活动遭到镇压,选票也下降到1881 年的31.2 万张。1890 年《反社会党人法》被废除之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数量甚至增加到178.7 万张,超过全部选票数量的四分之一。恩格斯高度重视这种崭新的斗争方式,他认为普选权能够带来诸多好处,例如,“每三年一次计算自己的力量”;通过选票数量的大幅增长,“既增加工人的胜利信心,同样又增加对手的恐惧”;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为无产阶级的代表提供了一个讲坛,“在这个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权威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对手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4](P389-390)。在恩格斯看来,普选权是无产阶级手中的“新式武器”。在议会选举中,通过得票率,无产阶级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同敌对党派的力量对比,以便采取适当的斗争策略。在竞选宣传中,无产阶级的代表能够更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对其他敌对党派进行抨击,以争取更多的群众支持。随着无产阶级自身的成熟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无产阶级在议会选举中将推选出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候选人,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选出资产阶级的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讲,恩格斯认为能否正确使用普选权是衡量无产阶级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尺。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新的斗争环境下应当积极利用普选权开展合法的议会斗争,而不是拘泥于以往革命斗争中所采用的“街头巷战”。
2.绝对不能放弃武装斗争的手段
议会选举的成绩,使得部分社会民主党人沾沾自喜,甚至乐观地认为在德国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党的一切要求。但是1894 年12 月以来,德国政府扬言要实施《反颠覆法草案》,企图恢复在《反社会党人法》施行期间的法令,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担心恩格斯的文章《卡尔·马克思〈1848 年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一些比较尖锐的语句会引起德国政府的不满,于是请求恩格斯对《导言》进行修改。恩格斯做出了极大的让步,对部分语句进行了删改,并尽可能地不改变原意。可是文章发表之后,还是引起了部分人的曲解,甚至有人断章取义,认为恩格斯赞成绝对守法。恩格斯得知后非常气愤,撰写文章和书信对这些观点提出了批评。他在1895 年致理查·费舍的信中明确指出,“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任何一个政党会“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5](P401)。在这里可以看出,恩格斯并没有要放弃武装斗争的意思,相反,他批评了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人放弃武装斗争的主张,认为这样做对党本身是一种危害。他还强调面对不法行为只能拿起武器进行抵抗,社会民主党不应该放弃武装斗争的手段。实际上,不是在《导言》发表之后,恩格斯才提出不能绝对放弃武装斗争的观点,而是早在19 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初,他就阐述过。在1884 年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尔的信中,恩格斯就说过,没有任何一个政党会放弃进行武装斗争的权利[6][P240]。在1890 年致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他也指出,“在当前,我们应当尽可能以和平的和合法的方式进行活动。但是,毫无疑问,你那样愤慨地反对任何形式和任何情况下的暴力,我认为是不能接受的。”[7](P362-363)由此可见,虽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社会民主党人有条件也应当通过议会选举这种和平、合法的方式进行斗争,但是恩格斯从来都没有说过要绝对放弃武装斗争。采取议会斗争的策略还是武装斗争的策略,要考虑许多因素,诸如敌我力量对比,这不仅取决于无产阶级政党自身,还要看资产阶级政府的态度。因此,在恩格斯看来,那种声称绝对放弃使用武力的主张,奉行“别人打我们右脸,我们把左脸也伸过去”的政策,只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一厢情愿,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自取灭亡。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19 世纪40 年代的社会环境和革命形势导致无产阶级必须拿起武器武装反抗资产阶级以及封建残余势力的压迫和剥削;19世纪70 年代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使得无产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此时这只是一种可能、一个设想,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到了19世纪80、90 年代,晚年的恩格斯从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出发,总结出无产阶级应当做议会斗争和武装斗争两手准备的策略理论,成为指导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新理论。这是恩格斯晚年在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理论方面的第一个贡献。
二、通过对无产阶级革命根本问题的新探讨,提出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的论断
列宁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8](P19)不认清这个问题就无法自觉地参加革命,更谈不上领导革命。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是资产阶级一统天下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实践中考虑的国家政权问题,基本上是围绕着如何打破资产阶级一统天下的局面、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国家政权展开的。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要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不仅仅是改变国家形式
1848 年欧洲革命结束后,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巴黎工人阶级在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喊出了自己的口号,“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2](P469)。在这里,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六月起义中工人阶级的主张,即通过革命运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国家政权,即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马克思接着指出,在六月起义之后,“革命意味着推翻资产阶级社会”,而在二月革命以前,革命只是“意味着推翻一种国家形式”[2](P471)。如何理解这句话呢? 1848 年法国的二月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运动,它所推翻的七月王朝是君主立宪政体,它所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是共和政体。这两个国家形式虽然存在差别,但实质上都是以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它们代表的只是资产阶级不同派别的统治,并没有否定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而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不仅要改变国家的形式,而且还要改变国家的根本性质,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要推翻资产阶级社会。通过马克思的阐述,可以明显看出,马克思支持无产阶级通过革命运动去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而不仅仅是推翻一种具体的国家形式。马克思继续总结道,过去一切革命运动都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2](P761)。他的言外之意就是,以往革命运动的主要目标是夺取国家的统治权,完成这一目标之后,新取得政权的阶级就作威作福起来,利用这个国家机器继续压迫其他的社会阶级。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与以往的革命运动完全不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应当直接把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摧毁掉,然后再重新建立起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
2.马克思提出“不能简单掌握”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认识到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也存在合理职能
1871 年巴黎公社运动之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9](P95)“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承担责任的勤务员。”[9](P100)可以看到,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摧毁”的字眼在《法兰西内战》中已经变成了“不能简单掌握”这一比较温和的字眼。一方面,说明马克思仍然坚持不能直接在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观点。诸如常备军、警察局、官僚机构、教会等国家机关,体现的纯粹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压迫性质,这些机关在新的政权中不应该被保留下来。另一方面,马克思也肯定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中存在着合理的职能。常备军、警察局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是被用来镇压、对付无产阶级的工具,这样的压迫性质的机关在新政权下应该被铲除。可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初,周围还面临着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这时就需要用暴力来保卫整个国家的安全。所以,巴黎公社用武装的全体人民来代替资产阶级的常备军和警察,这样,既铲除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压迫性质,又继承了它的合理职能,即保卫无产阶级国家安全的职能。
3.恩格斯晚年提出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利用民主共和国的形式
恩格斯在1891 年提出这一论断,他说:“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4](P294)恩格斯为什么会提出这一论断呢?1890 年《反社会党人法》被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需要重新制定一个新的党纲,以适应形势发展要求。但是在制定新党纲过程中出现了不小的问题,部分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在德国“可以用舒舒服服和平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可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4](P294)。虽然这部分人提出了新构想,但他们在新党纲里连建立共和国的基本要求都提不出来,这恰好说明了这个想法只是一种幻想,同时也说明了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德国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同时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成,以警察来保护的军事专制国家”[9](P374)。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首先面临的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而德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已经懦弱到不能领导这场革命,更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怎么办呢?恩格斯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应当取而代之,代替资产阶级政党来完成这一任务。因此,有必要把有关民主主义的要求也写进党纲中去,扫清封建残余,为德国无产阶级和德国人民争取到自由民主的权利,然后再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无独有偶,意大利同样面临着这一问题。当时意大利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不够发达,典型的无产阶级人数还很少,“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够发展”[10](P524)。恩格斯设想,目前的革命形势有可能使意大利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共和国内,无产阶级将“获得普选权和显著扩大活动自由(新闻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取消警察监视等等),这是不应该忽视的新的武器”[4](P324)。也就是说,意大利同德国一样,都是在君主专制统治之下,意大利的无产阶级没有集会、结社、出版、言论自由等民主权利,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秘密警察的监视,无产阶级的活动范围受到极大的限制,因而也就很难有效地组织、联合起来。同德国一样,意大利首先面临的是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的任务,如果在意大利爆发革命,其结果将是出现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内,无产阶级将获得比在专制制度下更充分的民主权利,这些民主权利是无产阶级用来维护自身利益的新武器。所以,在恩格斯看来,民主共和国可以“为革命的社会主义争取广大的工人群众”[4](P561),可以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锻炼群众,如果能够合理利用民主共和国的形式,将有利于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恩格斯认可民主共和国的形式,但他并不醉心于建立民主共和国,他强调在资产阶级还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时候,不能“把社会主义的使命委托给它”[4](P652)。也就是说,建立共和国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无产阶级不应该仅停留在这一革命阶段,建立共和国之后还应该向社会主义的目标迈进。恩格斯在给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指出,“共和国像其他任何政体一样,是由它的内容决定的。只要它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它就同任何君主国一样敌视我们。”[4](P652)这里,恩格斯的意思是,民主共和国的性质是由它的内容决定的,它的本质是由掌握政权的阶级决定的。当资产阶级掌握着民主共和国的领导权的时候,那它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它对于无产阶级群众来说就是一种压迫形式,而不是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工具。民主共和国所赋予的民主权利,无产阶级可以利用,但也仅此而已,决不能幻想在民主共和国内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相反,当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共和国就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的形式加上无产阶级的内容就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只有在这个时候,社会主义的使命才能交由无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共和国”来完成。恩格斯还告诫拉法格说:“今后你们不能再把你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看作别国人民应当为之努力的东西来同君主制相对立。你们的共和国也好,我们的君主国也好,同样都是同无产阶级相对立的。”[5](P88)也就是说,虽然法国在当时是一个民主共和国,德国是专制君主国,法国在政治制度上比德国先进,但就这两个国家的本质属性来讲,资产阶级共和国与专制君主国并没有本质区别。
综上所述,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即国家政权问题上,马克思在1848 年前后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要“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不仅仅是改变国家形式。19 世纪70 年代,在总结巴黎公社运动经验时,马克思提出“不能简单掌握”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认识到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也存在合理职能,要把这部分合理职能“夺取过来”“归还给”无产阶级。19 世纪90 年代,恩格斯意识到,民主共和国的形式也是可以利用的,无产阶级应当通过积极争取民主权利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提出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的论断。从直接“摧毁”到“不能简单掌握”再到一定条件下合理利用,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政权问题的认识是一个逐步发展、逐步完善的过程。恩格斯晚年的这个论断是在指导无产阶级运动的实践中形成的,是对马克思之前提到的“将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夺取过来”的具体化,并使之更加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从而为无产阶级在新的条件下进行斗争指明了方向。这是恩格斯晚年在革命策略理论方面的第二个贡献。
三、通过对农民问题的再审视,制定“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慷慨地对待农民”的策略
农民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无产阶级运动中如何联合农民是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理论的重要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
19 世纪40 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对农民的认识是“农业人口直到现在仍然对社会上的一切漠不关心”[11](P565),“中世纪所有的大规模的起义都是从乡村中爆发的,但是由于农民的分散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极端落后性,这些起义毫无结果”[12](P59)。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看到农民的革命性,或者说,农民的革命性还没有表现出来,他们所认为的农民仍然是分散的、落后的。
1848 年欧洲革命使得马克思开始重新审视农民的社会性质。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解释了法国农民何以从支持路易·波拿巴的保守的农民转变为革命化的农民,从而阐述了建立工农联盟的必然性和重要意义。马克思指出,法国农民逐渐革命化从根本上讲是小块土地所有制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造成的。在拿破仑统治的第一帝国时期,小块土地所有制是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有力武器,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农民越想维护他们的小块土地就越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小块土地越来越成为机器大生产的桎梏。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浪潮中,农民日益赤贫化,进而使得农民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反抗也日渐明朗化。马克思总结道:“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农民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2](P526)“在革命进程把……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2](P470)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带领农民走出贫困,走出被压迫、被剥削的困境,无产阶级只有与农民联合起来,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自己的统治。可以说,无产阶级与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又是无产阶级自身发展的应然。
到了19 世纪90 年代,法德两国的农民运动高涨,无产阶级政党希望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农民的支持,农民问题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工人党在处理农民问题时犯了机会主义错误。恩格斯为此于1894 年写了《法德农民问题》一文,制定了“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慷慨地对待农民”的策略。
首先,恩格斯将法德两国的农民按成分划分为小农、中农和大农,这是制定这一策略的重要依据。他认为,在西欧最重要的农民成分是小农,他们既是现时的有产农民,又是未来的无产者。小农与无产阶级不同的地方在于,无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而小农还占有小块土地,即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但这种对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形式并不赋予小农以自由,恰恰相反,小块土地所有制在生产日益社会化的条件下对小农来说只是一种束缚。中农和大农也是私人土地占有者,他们的土地比小农要多,他们中的多数人需要雇佣劳动力,因此在中农和大农占优势的地方就势必会存在剥削。小农的保守性在于他们的经济地位、闭塞的生活方式使其牢牢抓住小块土地不放,反对主张把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而中农和大农的保守性甚至反动性在于他们维护雇佣劳动制,剥削雇佣劳动者,这是中农、大农与小农最本质的区别。虽然中农和大农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广和海外廉价粮食涌入造成的竞争也同小农一样正在走向破产,但仅就他们维护雇佣劳动制这一点来说,社会民主党人就需要去反对他们。
其次,恩格斯制定了“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慷慨地对待农民”的具体策略。恩格斯指出,虽然小农这个群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排挤下正在走向消亡,但无产阶级政党不应该加速其消亡,也不应该违背小农“意志而强行干预他们的财产关系”[4](P371),更不能采取暴力手段去剥夺他们的生产资料,这可以说是一个指导性方针。由此,恩格斯提出,要通过示范和提供社会帮助以组成合作社的方式来组织小农生产,从而变私人占有和生产为合作社占有和生产。这种合作社有三个优点:其一,使小农可以不是为了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而是为了小农的共同利益进行大规模经营,避免了资本家和大土地所有者对小农的剥削;其二,把小块土地集中起来进行规模经营的合作社,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节省了大量劳动力,省下的这部分劳动力可以从事其他诸如工业、副业的劳动,这就会使小农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其三,合作社的占有和生产更加接近于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的社会主义原则,使社会改造更加容易一些。如果小农接受这种合作社占有和生产的方式,那无产阶级政党“就要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合作社”,给小农提供资金、示范和社会帮助等等。如果小农暂时还不能接受,“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4](P372)。总之,在恩格斯看来,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要“坚决站在小农方面”,对他们要表现出极大的耐心,要慷慨地对待他们。
最后,恩格斯解释了为什么一定要采取这种策略。他指出,无产阶级通过提供资金、示范和社会帮助等方式来联合小农,可能会花掉一部分社会资金,但这些钱并没有白花,这是一项极其划算的投资。“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九”,但“我们使之(指小农——引者注)免于真正沦为无产者,在还是农民时就能被我们争取过来的农民人数越多,社会改造的实现也就会越迅速和越容易”[4](P372)。恩格斯的意思是说,不能等到小农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排挤下全部破产沦为无产者之后再来对其进行社会改造。小农是私有者,占有一小部分生产资料,但小农人数众多,他们占有的生产资料总得来说也是不少的,小农是可以争取的对象,获得小农的信任和支持,掌握他们占有的生产资料,实现社会改造就会容易一些。相反,当小农的生产资料完全被资产阶级剥夺过去之后,无产阶级政党也就失去了可以进行社会改造的凭藉,从资产阶级手中获得生产资料比从小农手中获得要困难得多。
综上所述,19 世纪40 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在革命中表现出来的分散性和落后性是令人失望的。1848 年欧洲革命之后,马克思认识到农民的保守性已经逐渐转变成了革命性,无产阶级应当同农民建立起巩固的联盟。可以看出,在19 世纪90 年代之前,马克思、恩格斯侧重于强调农民问题和建立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至于采取何种办法,他们很少论及,这是革命形势使然。到了19 世纪90 年代,农民运动的高涨使得恩格斯认识到,解决农民问题、吸引农民加入革命队伍的时机已经成熟,从而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具体办法,制定了“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慷慨地对待农民”的革命策略。这是恩格斯晚年在革命策略理论方面的第三个贡献。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13](P9)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永葆生机与活力,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就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继承者们能够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结合新的实践作出新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创新。晚年的恩格斯没有拘泥于他和马克思之前制定的革命策略,而是根据时代、实践、认识所提出的新问题、新要求,进行深入思考,从而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策略理论。这些新的革命策略理论,无不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学习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理论,尤其是恩格斯晚年在指导工人运动时解决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对于我们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和正确解决改革开放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首先,恩格斯晚年形成的这些革命策略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这些革命策略理论的形成过程蕴含着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法。它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不是亘古不变的绝对真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我们不能教条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必须随时随地以发展的眼光来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我们不能从文本到文本机械地研究马克思主义,而必须到实践中去体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马克思主义不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直接解答,而是为我们寻找答案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方法,我们不能从语录中去寻求现成的答案,而必须在实践中以科学的方法作出回答。总之,马克思主义不是死气沉沉的一潭死水,而是生机勃勃的源头活水,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方能真正领略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
其次,恩格斯晚年的这些革命策略理论为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解决一些历史性课题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4](P11)“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14]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以及在转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党和政府在坚持大政方针不变的基本前提下,对一些具体的办法和措施做出了调整,制定了一些新的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策。比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扶贫政策从体制变革性减贫到精准扶贫,就是党在扶贫政策上的与时俱进,它使贫困群众摆脱贫困,过上幸福的生活,不让任何一个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掉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