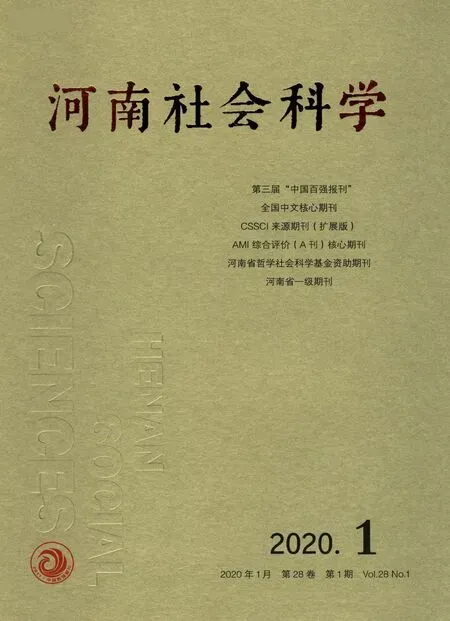从“唐宋变革”到“宋元近世”
——论宋代文艺思想的转型特征及其典范性与近世性①
李飞跃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4)
“汉唐”“唐宋”“宋元”“宋明”是古典文学与历史文化研究的基本范畴。在文学史上有“唐宋文学”与“宋元文学”的不同分期,艺术史上有“唐宋”与“宋元”之分,思想史上也有“唐宋”与“宋明”之别。基于不同视域,宋代文艺思想呈现不同的形态与景观。“唐宋变革”与“宋元近世”是认识唐宋元时期历史转型有影响力的理论范式,但前者的立足点在于以汉唐观宋,而后者则以元明衡宋,宋代的主体性与独特性未能凸显。将宋代文艺置于“唐宋变革”与“宋元近世”的双重视域之中,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宋代文艺“继往”的一面,也可以考察其“开来”的一面,凸显作为相对独立而非从属并置的宋代文艺思想的本体特征与历史地位。
一、宋代的社会新变与文化繁荣
宋代疆域虽然小于唐代,又不断受北方和西方少数民族侵扰,但长期以来却呈现出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大发展的局面。北宋太宗末年,全国仅400多万户,仁宗末年已增加到1200多万户,到徽宗初年更超过了2000 万户,人口总数突破1 亿,超出汉唐一倍,是清代以前中国人口数字的最高纪录②。南宋丧失了北宋近五分之二的疆土,宁宗末年的户数仍超过1260万。两宋涌现了一批户数众多、商户云集的大城市。唐代中期10 万人以上的城市只有13 座,到宋代中期已达46 座,尤其“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③。南宋城市的繁华程度较北宋有增无减,耐得翁《都城纪胜序》说:“自高宗驻跸于杭,而杭山明水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作,然中兴以来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倍也。”④
宋代将城中非农业人口“坊郭户”单独编列,市民可灵活调整商业布局的空间和时间。马克思说:“一切发展了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与乡村分裂为基础。”⑤北宋城市突破了汉唐“坊市制”限制,可面街设店。南宋城区的扩展又突破了城墙束缚,使市郊连成一体。坊市制度的破坏,区域性市场的形成,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都促进了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商业街区的形成、侵占官街河道事件的屡屡出现,以及城墙外附郭草市的增多,改变了宋以前中国传统城市的内部及外部形象,使城市具有近代城市的色彩。”⑥美国学者施坚雅(U.W.Skinner)将这种城市化称为“中世纪城市革命”⑦。城市人口的飙升和商业人口比重的增加造就了平民社会与市民阶级。宋代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性、结构性变化,影响和塑造了宋代文艺的基本形态。
鉴于五代藩镇之弊,宋朝中央高度集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⑧。皇权巩固后,开始重视文教事业,优待文士,借由科举出仕的文臣超过历代。君主多向文,宋太祖“性好艺文”⑨,太宗“锐意文史”⑩,真宗则“道遵先志,肇振斯文”[11],宋徽宗、宋高宗也都是文艺修养较高的君王。传统中国的物质文明至宋朝达到极高峰,“当日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先进的国家”[12]。科技成就尤其突出,“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13]。宋代更是古典文学和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当时朱熹已然断言:“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14]政治氛围相对宽松,文化管理较为开放,当时对诗文赋等文学创作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管控严格,而对新兴通俗文艺诸如说话、唱赚、杂剧等则放任发展。随着新兴文艺的影响越来越大,统治者开始对俗词俚曲、杂剧说话等进行批评引导甚至查禁,但已屡禁不止。
唐代的三教论衡,至宋则趋向三教圆融。宋朝君主承认“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号召“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15]。北宋大儒程颢之学“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16]。新儒家亲近和出入佛老,道教和佛教也主张相互融摄。道教内丹派南宗开山祖师张伯端宣称“教虽分三,道乃归一”[17],天台宗名僧智圆也主张“修身以儒,治心以释”[18]。南宋理学取代佛道成为社会各阶层的主要信仰,可以说就是一次宗教改革与思想革命。三教圆融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思维方式,赋予了讲唱、戏曲、小说等叙事文学以浓郁的近世思想色彩。
宋代书院数量众多[19],继承了编刻、聚藏、传播书籍的文化传统,又汲取和融合了诸家文化特点,发展成为教育与研究相结合的学术机构。经学上打破了“疏不破注”的师法,疑经思潮迭起。士人立德立言意识增强,重视独立见解和质疑批判,具有较强的理性精神。“士”之身份和角色的变迁,反映了整个社会和文化由贵族化向平民化的转变。“‘士’在唐代的多数时间里可以被译为‘世家大族’,在北宋可以译为‘文官家族’,在南宋时期可以译为‘地方精英’。”[20]他们的主要经历已非游宦从军,而是转向地方实业和文化建设,追求诗歌、书法、绘画、音乐等文艺的全面发展,是才艺兼修和综合素养较高的新式文人。“相对于唐人的漫游生涯和热爱自然风物,琴、棋、书、画、茶、酒、花、诗是宋代士大夫休闲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他们沉醉于人文意境,追求一种游心翰墨的人文旨趣和悠闲脱俗的精神享受。”[21]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的变化,导致宋代文艺的形态和功能出现了全新变化。
与以往宫廷、幕府、地域文人集团不同,宋代文人借由家族、师承、党派、书会、地域、流派等形成了具有共同爱好和审美追求的文人团体。随着科举、学校和书院的发展,形成了按师门学缘划分的“苏门六君子”,按照地域划分的“江西诗派”,按照政治观念划分的“元祐党人”等。他们有共同的文学主张与审美倾向,有意进行文集结撰,开始注意作品的保存、传播及阐发。随着《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大型类书编讫,《资治通鉴》《新唐书》《新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大批史籍相继出版,产生了“百科全书式”的《梦溪笔谈》和一代风俗写照的《东京梦华录》《清明上河图》。宋人好质疑、好议论,本身就是对累积资料的一种批判接受和基于当时人们经验的知识重构。
宋学的怀疑、批判、创新、兼容、尚简等精神氤氲到社会生活、文学艺术领域,使宋朝文化呈现出独特景观,甚至成为古典文化发展的一道分水岭。元人将汉、唐、宋称为“后三代”[22],是置其于中古文化区间而言。后人则更多关注宋代对近世文化的塑造,钱穆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23]金毓黻说:“国史上民族文化政治制度之大转捩,凡有三时期:其一为秦汉,其二为隋唐,其三为宋辽金。”“宋代膺古今最剧之变局,为划时代之一段。”“凡近代之民族文化,政治制度,几乎无一不与之相缘,而莫能外,是宜大可注意者也。治宋辽金史,实力治近代史之始基”[24]。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也指出:“11—13世纪期间,在政治、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这里不单单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而更是指一种质的变化。政治风俗、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和经济形态均与唐朝贵族的和仍是中世纪中期的帝国完全不同。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25]
概言之,中国社会在宋代已经走出了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为区间的中古,出现了一种类似于西方“文艺复兴”的划时代变革。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到价值观念的种种新变,使宋代文艺思想发生了深刻转向。宋代居于中国古典文艺承前启后的阶段,我们应从大历史格局中审视宋代文艺的时代特征,将之放在中古以至新文化运动以前的长时段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着眼其对近世文艺尤其通俗文艺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宋代文艺思想的价值意义与历史特征重新界定。
二、宋代文艺的历史转型与思想特征
宋代文艺处于中古向近世转型时期,从活动主体、种类构成到形态功能都发生了深刻改变。
一是作为活动主体的文人职业化与艺人社团化。宋前文学创作的主体多是贵族或中上层文士,作品主要用于润色鸿业、“为时事而作”,而宋代文学作者的身份地位、思想观念及创作倾向都发生了改变。随着科举扩员和冗官现象日益增多,读书人越来越难跻身统治阶层,被迫另谋生路,以至士大夫子弟“不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事笔札、代笺简之役,次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如不能为儒,则医卜、星相、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26]。一些文人以诗文为商品,走上了世俗化的市场之路。还有诗人化身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挟中朝尺书,奔走阃台郡县,糊口耳。庆元、嘉定以来,乃有诗人为谒客者。龙洲刘过改之之徒不一人,石屏亦其一也。相率成风,至不务举子业,干求一二要路之书为介,谓之‘阔匾’,副以诗篇,动获数千缗、以至万缗”[27]。有些文人与书商、伶工合作,直接参与文艺创演。据张政烺考察,周密《武林旧事》“诸色伎艺人”条所载乔万卷、武书生、王贡士、张解元、陈进士等23名演史者,“皆读书人,万卷极言其记诵之博也”,不过“此诸人未必皆出科举,盖有儒生试而不第者,所谓‘免解进士’‘白衣秀才’之类也”[28]。书会中亦有一些才高名重的公卿显宦,但以低级官吏、商人、医生、倡优居多。他们的文学创作主要是依据民间传说或经史演义,采用赚词、诸宫调、院本、杂剧、平话等多种文艺形式,呈现出与传统经典文学的不同形态与功能。他们组成的永嘉书会撰有《白兔记》、九山书会撰有《张协状元》、古杭州书会撰有《小孙屠》等,这些书会还兼营刻书与发行业务。新经典的生成,普遍具有集体化、通俗化与累积性特征。
社团化、集体化的文学活动,在民间文艺创演中最为通行。逢祭祀或节庆日,有歌伎遏云社、女童清音社、苏家巷傀儡社、富豪子弟绯绿清音社等[29]。如淳熙年间二月八日为桐川张王生辰,震山行宫朝拜极盛,有“绯绿社(杂剧)、齐云社(蹴球)、遏云社(唱赚)、同文社(耍词)、角抵社(相扑)、清音社(清乐)、锦标社(射弩)、锦体社(花绣)、英略社(使棒)、雄辩社(小说)、翠锦社(行院)、绘革社(影戏)、净发社(梳剃)、律华社(吟叫)、云机社(撮弄)”,可谓百戏竞集。会社成员人数普遍较多,仅清乐社有数社每不下百人,“福建鲍老一社,有三百人;川鲍老亦有一百余人”[30]。“姑以舞队言之,如清音、遏云、棹刀鲍老、胡女、刘衮、乔三教、乔迎酒、乔亲事、觉锤架儿、侍女、杵歌、诸国朝、竹马儿、村田乐、神鬼、十斋郎各社,不下数十。”[31]艺人们按照艺术门类交流心得,相互借鉴乃至共同创作和演出。他们分工细致,各有艺名,每种表演形式都有代表性名角。北宋闻名京师的讲史艺人有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小说艺人有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说诨话艺人有张山人,诸宫调艺人有孔三传、耍秀才等[32]。崇宁、大观以来,小唱最出名的是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当时说唱伎艺的专业化程度已非常高,如南宋时期的小张四郎,“一世只在北瓦,占一座勾栏说话,不曾去别瓦作场,人叫做小张四郎勾栏”[33]。他们在庆祝传统节日、婚丧嫁娶及宗教祭祀等活动中搭建乐棚、露台、彩棚等临时性表演空间,以及在酒楼、妓馆、府邸等私人演出场所定时演出,逐渐发展为日常化文艺活动。文人的职业化和艺人的组织化,尤其文艺社团的出现与运行、文艺作品的商业化,标志着近世文艺基本形态的形成。
二是不同文艺种类的涌现与文艺思想的二元分化。宋代民间流行的文学体裁、题材很快成为雅俗共赏的流行文学。文人士大夫自觉从事不同层次的文艺创作,如晏殊、欧阳修在朝为官以诗文名,兼事艳科小道的词的创作。宋太宗、宋徽宗、宋高宗等精通词曲、绘画、书法,亦好杂剧、说话等艺术。孝宗时,“后苑小厮儿三十人,打息气唱道情”,太上皇赵构很快辨识出:“此是张抡所撰鼓子词。”[34]此外,洪迈、刘斧、皇都风月主人等从事小说创作和收集,沈括、陈旸、周密、陈元靓等热衷于对民间歌舞的记载,都留下了传世之作。在柳永、赵令畤、秦观、曹组等人投入通俗文艺创作的同时,也涌现了一批天才的民间文艺家,他们基于实践形成或改进了鼓子词、诸宫调、赚词、杂剧等文艺形式。包括缠令、缠达在内的赚词,是诗词曲等抒情艺术向戏曲、小说等综合叙事艺术转变的一大关节。“熙、丰、元祐间,兖州张山人以诙谐独步京师,时出一两解。泽州有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35]“中兴后,张五牛大夫因听动鼓板中又有四片《太平令》或《赚鼓板》,遂撰为‘赚’。”张五牛因袭了赚鼓板的名称,运用缠令、缠达等曲体结构发展成为新的说唱艺术,“令人正堪美听,不觉已至尾声”[36]。据《梦粱录》与《武林旧事》载,临安勾栏的著名唱赚艺人达32人之多,其中李霜涯“作赚绝伦”。
传统经典文艺与民间新兴文艺共同造就了宋代文艺的大发展与繁荣。宋初时文与古文并争,诗歌日常化与说理化、议论性与叙事性交织,发展成为江西诗派与江湖诗派竞盛。俗词与雅词争竞,婉约派与豪放派并峙。音乐上雅乐与俗乐,绘画上院体画与民间画齐头争进。当时影响较大的佛教门派有禅宗与净土宗,前者流行于士大夫阶层,后者普及基层民众。禅宗从“不立文字”向“文字禅”蜕变,以俗兼雅。文艺的娱乐功能渐被政治和道德削弱,出现了“教化说”“言志说”“明道说”“比德说”等。一方面道学思想强化,排斥通俗文艺;另一方面民间文艺逐渐形成新的标准,具有了文学的独立性,它们共同构成了宋代文艺多层次的丰富景观。
三是传统文艺呈现出总结性、集成性成就。宋代文学作品通过印刷传播,不仅扩大了受众面,也避免了抄写中产生讹误,促进了文体的规范与统一。宋代各类文学体裁、各种艺术形式都获得集成性的空前发展。《宋史·艺文志》著录宋人撰述达“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三卷”。其中,“有别集流传者六百余家,如以无别集而文章零散传世者合而计之,作者将逾万人,作品超出十万”[37]。宋代作家作品数倍于唐代,涌现了一批经典文学大家,如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代占六家,诗歌方面形成了西昆体,出现了欧王苏黄等巨擘。歌词方面有欧苏、柳秦、周姜等争艳,书法有宋体与“宋四家”竞妍。各文艺门类都出现了具有宋代风格的代表性成就,宋词、宋诗、宋画、宋体、宋版、宋瓷、宋锦、唐宋大曲、宋金杂剧、宋元戏曲、宋元话本、宋代园林、宋代金石、唐宋传奇、唐宋八大家、宋明理学等一系列文艺成就诸峰并峙,几乎每个文艺类型都在宋代达到了极高水平。古典文艺在宋代取得了集成性和典范性成就,以至后来的主流文艺只能别开蹊径。
宋人在诗歌、散文、词赋、小说、戏曲等创作基础上,也提出了具有概括性和创造性的理论。“文道说”“妙悟说”“兴趣说”“点铁成金”“别是一家”等理论,从深层和根本上探讨诗词文艺术的本质与功能。西昆体、江西诗派、江湖诗派流行的同时,反思一直未有停止,屡见对“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学问为诗”的反思。刘克庄《叙林希逸诗》说:“入宋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主文,或负材力,或逞辩博,少者千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38]《沧浪诗话》的产生,“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复古时期的开始,此后直至清末,古典诗歌基本上是在复古中走完了自己的路程”[39]。李清照《词论》、王灼《碧鸡漫志》、沈义父《乐府指迷》、张炎《词源》等奠定了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宋词的史论基础。《宋文鉴》《瀛奎律髓》《草堂诗余》等总集的编纂,以及以《醉翁谈录》《事林广记》《唱论》《中原音韵》等为代表的基于观演体验和辨体尊体的宋元批评理论逐渐确立。
四是受众平民化使宋代文艺开始注重日常经验与通俗表达。接受对象的市民化或大众化,促进了音乐、舞蹈、文史等文艺形式的通俗化转型。仁宗年间,张方平奏论雅乐指出:“臣伏见太常乐工,率皆市井闾阎屠贩末类,狠恶污浊,杂居里巷,国有大事,辄集而教之,礼毕随散。”[40]专供国家典礼的太常乐工竟由杂居里巷的市井屠贩充任,而宋徽宗政和年间,“京师妓之姥曾嫁伶官,常入内教舞”[41]。民间商业性讲史活动日益活跃,汴京瓦市以讲史闻名的艺人就有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霍四究、尹常卖等。其中,霍四究擅长“说三分”,尹常卖长于讲述“五代史”(《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南宋时仅周密《武林旧事》中所载临安瓦市讲史者就有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周八官人、檀溪子、陈进士、陈一飞等二十三人。此外,尚有“讲诸史俱通”的王六大夫等。他们在向大众讲述历史知识的同时,也开始用民间视角对史事和人物加工再造,为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等经典小说生成奠定了基础。
“宋诗的日常生活化,可说是近世诗歌乃至近世文学的一个总体特征。”[42]宋诗较唐诗更注重写实,贴近生活,“过去的诗人所忽视的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或者事情本身不应被忽视,但因为是普遍的、日常的和人们太贴近的生活内容,因而没有作为诗的素材,这些宋人都大量地写成诗歌。所以宋诗比起过去的诗,与生活结合得远为紧密”[43]。宋诗议论时政,描写民生,品艺说理,达到了“无事不可入”“无理不可穷”的境地。“凡唐人以为不能入诗或不宜入诗之材料,宋人皆写入诗中,且往往喜于琐事微物逞其才技。如苏黄多咏墨、咏纸、咏砚、咏茶、咏画扇、咏饮食之诗,而一咏茶小诗,可以和韵四五次。”[44]“古未有诗”的题材物象、句式词语等入诗,促进了宋诗语言的通俗化和近体诗格律声韵的变异(如以古入律)。黄庭坚主张作诗“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其词“酷似曲”,被后人称为“蒜酪体”。杨万里诗的“俗语”不少来自当时的口语白话,通俗易懂。范成大诗“平浅”,陆游诗“明白如话,然浅中有深,平中有奇,故足令人咀味”(《艺概·诗概》)。严羽力主学诗必去俗体、俗意、俗句、俗字、俗韵等五俗,指摘的恰是宋诗中大量存在的创作现实。宋诗突破了唐诗的烂熟套数,趋近散文和口语的以文为诗,不避琐碎的日常事物,不求雕琢出新的语言表达。“诗家不妨间用俗语,尤见工夫”[45],几成诗坛共识。如果将一部诗歌史简化为诗歌语言形式的变化史,那么,“中国诗歌语言的演变过程中最具有‘革命’意义的变化,除了古诗到齐梁体诗及唐诗的那一次之外,就要算从宋诗一直延续到本世纪白话诗运动的诗歌语言演变了”[46]。
此外,柳永“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47],“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48]。后人称欧阳修与“三苏”文章的好处,“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却那寻常底字”[49]。范仲淹《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尹师鲁以为“《传奇》体尔”。黄庭坚自述“作诗正如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诨,方是出场”[50]。近世多数通俗文艺品种几乎都在此时产生,如小唱、般杂剧、傀儡、讲史、小说、影戏、散乐、诸宫调、商谜、杂班、弄虫蚁、合声、说诨话、叫果子等[51]。《西湖老人繁胜录》记临安瓦舍伎艺云:“唱涯词只引子弟,听陶真尽是村人。”因其题材与文词通俗,故为村民所喜。用口语或白话写出的小说,打破了文言对文坛的垄断。六朝志怪和志人小说主要记载神异鬼怪和历史名人,唐传奇主要写上层人物,宋元话本小说转而将城市下层人物和日常生活作为表现对象,鲁迅称之为“平民底小说”[52]。描写爱情婚姻的《调笑转踏》《碾玉观音》等作品热烈赞颂自由恋爱、自主婚姻,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反抗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婚姻制度,体现了市民阶层对爱情婚姻的看法和呼声。市民阶层成为作品主角,标志着中国文艺主体从贵族文士到平民大众的历史性转变。
五是集成性与综合化带来宋代文艺形式的融通转变。宋代文学从严辨体的同时,不断出现跨界和打通,如以诗为词、以文赋为词、以词为曲、以诗论艺等。苏轼“以诗为词”、周邦彦“以赋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提出了一批学理概念。不同文艺形式相互借鉴融合,书论、画论和曲论普遍借鉴传统诗论、文论术语,诸多文论或批评术语就是来自书画、乐舞,书画一体、诗画一体已成为重要学术命题。儒释道相互融合,宋诗好用佛典,化用佛道意象,抒发宗教体验。
在民间艺人和专业行会推动下,各种说唱艺术争奇斗艳,向着普及面更广、综合性更强的艺术形式发展。勾栏瓦舍集聚了众多百戏杂技艺人,宫廷艺人、官妓、营妓等混杂其间。流行的嘌唱、耍令与吟叫同出一源,嘌唱“驱驾虚声,纵弄宫调,与叫果子、唱耍曲为一体”,它们原本流行于街市:“若嘌唱耍令,今者如路岐人王双莲、吕大夫唱得音律端正耳。今街市与宅院,往往效京师叫声,以市井诸色歌叫卖物之声,采合宫商成其词也。”[53]相近艺术形式的结合,派生出新的说唱艺术“吟叫”,分为“下影带”“散叫”“打拍”等。形式不断翻新,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东京梦华录》载:“凡赚最难,以其兼慢曲、曲破、大曲、嘌唱、耍令、番曲、叫声诸家腔谱也。”[54]唱赚吸收了多种艺术形式要素,在南宋中叶后又发展为覆赚,为后世的戏曲、曲艺所吸收。说唱包含说、谈、讲、论、言等多种成分,话本兼具声音、图像和文字三要素,已开始从依靠声音为主的说唱、图像为辅的变相转向图文结合的全相话本。
随着文艺形式的综合化、集成化,文学与音乐、舞蹈、绘画、说唱、戏曲等结合日渐增多。文学扩大影响需同其他艺术形式结合起来,才能拥有更为广泛的受众。小说、戏曲等皆文备众体,甚至可以说是诗、词、曲、文、赋等文学形式的整合与升级。流行后世的诸多通俗文艺就形成于这一时期,或者可在宋代找到源头。为《夷坚志》提供素材的参与者超过五百人,多数虚构痕迹明显。洪迈《夷坚支甲序》云:“殆好事者饰说剽掠,借为谈助。”[55]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春的礼部试,洪迈以吏部员外郎充参评官,其间三十名考官中有十一位是《夷坚志》素材的提供者[56]。各种文艺形式的结合与综合,推动了从诗词文赋等纯文学向综合化程度更高、文备众体的戏曲和小说演变,因为“篇幅短小的文艺作品(如词、散曲等)已不能满足下层民众的审美要求,鸿篇巨制的戏剧、小说、评书等文艺作品应运而生。从此,诗文主宰文坛的历史宣告结束,戏剧、小说成为主导的文学艺术样式”[57]。
三、宋代文艺的典范性及其思想史意义
宋代是唐宋变革与宋元近世的交集,同一时代兼有中古与近世两种特征,体现了不同文化类型的转变与交融。与此同时,宋朝又与辽金夏蒙处于相同时空场域,宋朝的诗词文等经典文学促进了辽金元文学的提升,而辽金元乐舞、说唱等民族文艺又促进了宋代文学的发展,不同质态的文艺融合共同促进了文艺革新,尤其以戏曲、小说为代表的综合文艺兴起。新的文艺类型、概念范畴、审美风格与价值观念,让宋调与汉风、唐韵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艺思想中的经典范式。
首先,形成了古代经典文艺的宋型范式。史上从未有一个朝代像宋代那样在诸多文艺领域取得了集成性、标志性成就,形成了群峰耸峙的景观。宋词是一代之文学,宋诗与唐诗分庭抗礼,宋代散文是古文典范(唐宋八大家宋占有六),宋画、宋书、宋瓷、宋版、宋体、宋杂剧、宋话本等都是文艺史上有重要影响的经典范式。草书在创作精神、技法表现、风格特征等方面,改变了唐草的雄强狂放,由纵情宣意转为重理适意。仕女牛马成为中唐以来绘画的主题,山水画与风俗画则在宋代成熟并达到高峰。国画向以唐宋或宋元并称,而宋画则代表了中国古代绘画的最高水准,有学者甚至认为“吾国画法,至宋而始全”[58]。宋代也是瓷器发展的高峰,被西方学者誉为“中国绘画和陶瓷的伟大时期”。几乎所有手工业的传统工艺,都在宋代发展成熟。宋代工艺美术的造型、装饰与总体效果堪称工艺史上的典范,成为明清工艺争相仿效的对象。
不同艺术门类,都呈现出一致的审美风格与文化精神。宋人审美尚简淡,梅尧臣认为“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平淡的审美风格要有丰富的言外之意,欧阳修《六一诗话》主张“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说:“发纤稼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王安石《题张司业诗》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种寻常和容易,实际是经过一番曲折探索和艰辛努力才达到的。苏轼赞扬“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书黄子思诗集后》),宣情尚意的宋代行书及其崇尚平淡蕴藉的士人趣味获得普遍认同。宋人山水画“平远”居多,用墨较淡,在平和之中把人引向“远”“淡”境地。宋画创作已不仅着眼于高山大川的恢宏和博大,而且转向了物象本身的内在生命和意蕴,极大增强了绘画的概括性、含蓄性和象征性。简古、平淡中蕴含着丰腴隽永的深意,形成了“萧散简远”“古雅淡泊”的文人画美学思想。
学术思想史上历来是“汉宋”对举、“宋明”并称。宋代佛教的“思无邪”说及“中和”“清雅”“尚简”等观念,对后世文艺审美产生了深刻影响。宋代五大名窑出产的陶瓷应用了新的制作工艺,代表了追求纯净、造型和材料的新品位。南宋后期,词的雅化达到了极致,“清雅”“古雅”“淡雅”“骚雅”等词语成为人们褒扬词作的常用语言,受到广泛认同和极力推崇[59]。唐君毅称:“中国民族之精神,由魏晋而超越纯化,由隋唐而才情汗漫,精神充沛。至宋明则由汗漫之才情,归于收敛。”[60]收敛正是“平淡”的内向性宋型文化特征。“宋代独特的审美精神,是古典审美意识已进入后期的表征,是古典审美创造已高度发展、成熟,高度精致化的产物,是古典后期的审美理想。”[61]后世文艺范畴几乎都在宋人话语中开始形成,如与汉学相对的宋学、与唐诗派相对的宋诗派、与唐代书法重法度相对的重意趣、词派中的婉约与豪放、音乐中的雅乐与俗乐、绘画中的院体画与文人画、书籍中的宋版与宋体等,都是中国文艺思想的基本概念范畴。
其次,确立了近世文艺观念的价值标准。社会结构和大众风尚的变化往往决定了一种思想的兴衰及其转向,禅宗、内丹、理学的出现似乎都与唐宋时期门阀贵族的瓦解及士民阶级的兴起有着必然或密切关联。“唐、宋、元、明时期,禅宗、内丹、理学的交替出现,佛、道、儒这三大思想信仰系统都出现了内转化的趋势,内在化、心性化、德性化、主体化是唐、宋、元、明时期中国思想演变的大趋势,这种趋向也最终导致晚明‘三教合一’局面的出现,使中国文化出现了一个相对静态平衡的稳定结构。”[62]道教从佛教哲学中汲取养分,将其融入自身的养生思想向儒家士大夫渗透;同时吸纳佛教因果轮回思想与儒家纲常伦理学说向普通百姓渗透。陈抟、张伯端等吸收了儒家纲常伦理与禅宗心性之学,建立了完善的内丹学,取代外丹术成为道教修炼的主流,为金元之际新道教的出现奠定了基础[63]。宋代理学家几乎都有出入释老,以及援佛入儒或援道入儒的倾向。在日常生活中,儒佛道并行不悖、和谐相处,普通百姓也读儒书、拜佛祖、做斋醮。从接受外来文化为主的唐代文化,“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64]。因此,钱穆将宋学精神概括为“明体达用”:“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治,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而书院讲学,则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65]
宋代改经、疑经和删经之风盛行,走出了中古对经典的迷信和盲从。欧阳修、司马光、苏辙等人分别对《易经》《孟子》《周礼》等经典提出质疑,欧阳修在《易童子问》《诗本义》《春秋论》等文中对儒家经典频发诘难,声称“世无疑焉,吾独疑之”,要“一一究其所从来而核其真伪”[66]。在解经方法上开始关注义理大旨,不再拘泥于章句训诂。王安石宣称“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67]。朱熹指出:“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欧阳修)、原父(刘敞)、孙明复(孙复)诸公,始自出议论。”[68]程颐说“学者要自得”,“各自立得一个门庭”[69],以至当时“一人一义,十人十义”,“人执私见,家为异说”[70]。于是,宋学各派“学统四起”,王安石创立新学,苏氏父子创立蜀学,周敦颐及二程创立濂洛学,张载创立关学。南宋中期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与陈亮为代表的浙东事功学派,虽然主张不一,甚至针锋相对,但也能够实事求是,各展所长。宋代理学思想对元儒和明儒影响深远,宋代的怀疑精神和理性精神也是清代朴学的重要思想资源。
再次,宋代文艺对辽金夏元及东亚文化的影响。宋朝持续不断地对周遭政权领地进行文化输出,形成了新的汉文化秩序尤其是道统学统,塑造了东亚文明的基本形态。澶渊之盟后,图书成为宋辽榷场贸易的重要商品。景德三年(1006),宋朝廷明文规定:“民以书籍赴沿边榷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案罪,其书没官。”[71]尽管宋廷再三强调“卖书北界告捕之法”[72],但“人情嗜利,虽重为赏罚,亦不能禁”[73]。“拓拔自得灵夏以西……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所为皆与中国等。”[74]西夏景宗李元昊“仿中国,置文武班,立蕃学、汉学”[75],“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76]。毅宗李谅祚“遵大汉礼仪以更蕃俗,求中朝典册用仰华风”[77]。与此同时,北方文艺也南向流传。吴曾《能改斋漫录》载:“至政和初,有旨立赏钱五百千,若用鼓板改作北曲子,并着北服之类,并禁止支赏。”[78]“番曲”“北曲子”等辽金歌曲流行,促进了宋朝文艺样式的革新。唱赚有时还要综合“番曲”唱腔。北方歌曲流入南方,被吸收进新兴曲艺唱赚之中,后又融入诸宫调、北曲等通俗文艺。宋辽尤其宋金互遣使臣,带动和促进了南北文艺的交流。“宋方为五百多次,正、副使有名可查的为484 人。金方有295 次,正、副使有名可查的为291人。”[79]宣和间,“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皆歌之。……当时招致降人杂处都城,初与女真使命往来所致耳”[80]。“女真风流体等乐章,皆以女真人音声歌之。”[81]通使带来流行歌曲的同时,金人还多次索要杂戏、倡优诸色人等不计其数。
北宋与金的两次亡国,促使了文艺人才的大规模流动。靖康二年即金天会五年(1127),金人曾令开封府追寻到杂剧、说话、小说等伎艺人一百五十余家,押送军前。“内侍内人归酋长,百工诸色各自谋生,妇女多卖娼寮。”“《燕人麈》云:天会(1123—1137)时掠致宋国男、妇不下二十万……不及五年,十不存一。妇女……分给谋克以下,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邻居铁工,以八金买娼妇,实为亲王女孙、相国侄妇、进士夫人。”[82]南宋乾道六年(1170),范成大使金过真定,发现还保存着北宋大曲歌舞:“虏乐悉变中华,唯真定有京师旧乐工,尚舞高平曲破。”[83]北迁艺人促进了当地俗文学尤其戏剧文学的繁荣,包括真定、东平在内的元杂剧中心的形成就得益于这种流动。金亡,艺人又流落南方,带来了北方的通俗文艺。汴京沦陷,“仓皇禁陌夜飞戈,南去人稀北去多”[84]。“番腔”“番曲”等频见于南宋文人的记载。刘辰翁《卜算子》云:“十载废元宵,满耳番腔鼓。”《柳梢青》云:“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歌声。”北方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的一些乐曲不断传入中原,使北方游牧文化乐曲与中土文化相融合。一些民族乐曲流传下来,成为元曲的主要曲牌。
周边邻国高丽受宋朝文学、绘画、书法、音乐等影响较大,日本则在文学、佛教绘画、雕塑艺术等方面深受影响。宋朝书籍大量流入邻国尤其是高丽、日本和交趾。对高丽输出了《大藏经》《文苑英华》《逍遥咏》等典籍和地理、日历,高丽使者还阴访书籍带回国内。交趾时常向宋廷请求购书,并获准购买除“禁书”以外的各类书籍。北宋新兴瓷窑有河南钧窑、浙江龙泉窑、河北磁州窑等,以及后来成为我国陶瓷生产基地的景德镇。宋瓷品种繁多、器形多样、色调优雅,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销往西方。此外,宋代在医学、妈祖文化、茶文化等方面也对东南亚、南亚及西亚等地有大量文化输出。宫崎市定《东洋近代史》曾总结说:“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85]
最后,宋代文艺的近世特征及深远影响。宋代主要文艺类型都发生了转型,其精神、思想普遍呈现出鲜明的近世性。文学借由日常化书写尤其是商业化,独立发展成为一种审美、娱乐甚至商业艺术。主流字体和书法风格也发生了转变,绘画从彩色壁画转向更加自由的屏风画和水墨画。书法“尚意”与文人画“写意”都期望表达创作者的个性,标榜“自出新意,不践古人”[86]。艺术精神方面,唐人画气度博大、壮丽雄美,宋人画转为静远、平和、内向,黄休复《益州名画录》首次将“逸品”置于“神品”之上。园林方面,从司马光的独乐园、邵雍的安乐窝到辛弃疾的稼轩,宋代园林也展现了士大夫的独立人格与审美追求。建筑方面,“宋初秉承唐末五代作风,结构犹硕健质朴。太宗太平兴国以后,至徽宗即位之初,百余年间营建旺盛,木造规制已迅速变更;崇宁所定多去前之硕大,易以纤靡,其趋势乃刻意修饰而不重魁伟矣”[87]。可以说,几乎各个文艺门类都在宋代发生了显著、深刻的转型,并且迅速确立了宋代特有的文艺范式。
宋代是中古文艺向近代文艺转型的时期,开创了中国古典文艺的近世范式,具有广泛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唐宋说话技艺在故事叙述上的发展,不但影响着宋金杂剧大量选用小说题材,也吸引其在叙事思维、体制、方式上向小说靠拢。戏曲在包括小说在内的多种文艺的促进下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演述体制、审美趣味和文学品格之后,又为小说所借鉴。宋元时期不仅是从抒情文学到叙事文学、从文士文学到市民文学的文学形态的变化,甚至也是文学性质的变革。文学开始从润色鸿业向记录生活、刻画人性转变,“与诗词相比,戏曲、小说等俗文学篇幅较长,蕴含极深,所反映的社会背景更广泛,对人性的揭示也更深入。因此,作为真正的人学的文学是从元开始的”[88]。
宋学对其后的哲学、伦理学、教育学、史学、文学艺术与自然科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叙》说:“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持,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89]严复指出:“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90]迪特·库恩以其西方视角,在宋朝历史中发现了“中国意识”及其在后世的延续:“由宋朝那些有创造力的统治者、士大夫和艺术家创造的思想范式,以及儒家价值的复兴和重建,为后世历朝历代的教育、政府制度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建立了基础,并强化了汉人子孙头脑中的中国意识,这种意识在宋代之后持续了若干世纪。”[91]李泽厚也认为,“在中国民族性格与中国实践理性的形成发展中,在中国民族注重气节、重视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奋立志等建立主体意志结构等方面”[92],都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文化的普及,庶民阶级的兴起,根本改变了之前以贵族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可以说,近世中国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观点及情感模式均发端于宋代。宋明时代的社会文化和制度思想是相对汉唐的另一种经典范式,甚至可以说后来居上。王国维认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势所不逮也”,因为“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93]。陈寅恪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94]后来,邓广铭多次指出:“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95]“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96]这些评价足以说明宋代在我国文学艺术乃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当然,这种转型意义也是相对而言的。转型只是范式的更新,其基本知识与精神仍是连绵相承的。以往我们对“说话”的理解,主要是从民间文学角度考察,认为其低端、粗浅,但从经典文学的通俗化角度,“说话”正是经史的通俗化表达,是诗词的民间化形态,无论说经、演史还是诗话、词话,都是受众极广的主流文艺,孕育和引领了新的文艺发展方向。从单个文体出发,很容易突显文体之间的差异,忽略相互之间的关联。如果从知识传承、主体扩大与形态更新等方面来看,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形式大于内容,《史记》对《春秋》的重写、《资治通鉴》对《史记》的重写、《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的“按鉴重写”,其中有一以贯之的知识与精神。
从政治军事层面来看,宋朝尤其南宋是一个积弱王朝,相对于辽金元都是处于被动的守势。但从经济、文化等当代强势话语和研究热点出发,宋代反而赢得了政治军事所不曾达到的话事权与正统地位。宋代成为历史上最为文弱的王朝,没有了汉唐开边拓土、勒石燕然的气概,也丧失了御敌战胜的胆魄而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并最终倾覆。当时尤其是金元之际的北方文人并不是天然地认南宋为正朔。关汉卿[南吕一枝花]《杭州景》称杭州为“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王实甫《丽春堂》[仙吕·点绛唇]则发出了“破虏平戎,灭辽取宋,中原统”之声。金元文人这种以据有中原为正统的观念与呼声,最终还是湮没于宋文化不断发育和生长的滚滚长河。文艺的繁荣翼蔽了武功的贫弱,成就了宋代堪与其他盛世王朝相颉颃的历史地位。
文化宋朝不仅相对辽金元有强大优势,在中国历代王朝中也是一座空前绝后的高峰。政治与军事的落差已成为历史,文化艺术成了衡量历史地位和价值意义的主要标准,由此也形成了“盛唐隆宋”之说。这种认知是人们致力于从文化传统角度重新发现历史,重建价值认同与文化自信的结果。通过文化的相对优势来强化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包括陈寅恪、钱穆、邓广铭等人的论述,其出发点也是基于这种现实需求。如果要对宋代文艺进行整体性与多维度的考察,除了对宋代文艺本身的发展梳理之外,还应该对唐宋转型、宋元近世尤其近代以来历史的文化主导观念有所省思。
总之,我们要从不同视角看待宋朝,作出新的概括和界说,从而更为切实地把握宋代文艺思想的主流、本质、生成原因与历史地位及影响。从“唐宋变革”到“宋元近世”的不同理论框架中审视宋代文艺思想的基本特征,可以更为凸显宋代文艺的转型特征与历史地位,尤其呈现向来被忽略的宋代通俗文艺思想。宋代文艺的典范性与近世性既是别开生面的,也是相反相成的。宋代处于从中古到近世的历史转型时期,宋明通俗文学与汉唐经典文学共同构成了我国古典文艺的两种基本范式,共同塑造了我们民族的文艺精神和文化品格。
注释:
①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思想通史”子项“宋代文艺思想史”前期成果。
②彭雨新等:《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五编第一章,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页。
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56页。
④耐得翁:《都城纪胜》,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385页。
⑤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4页。
⑥吴晓亮:《宋代经济史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页。
⑦[美]施坚雅著、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3—24页。
⑧《朱子语类》卷一二八,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3070页。
⑨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四《崇政殿说书》,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1页。
⑩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宋太宗皇帝实录校注》卷三十一,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22页。
[11]宋真宗:《册府元龟序》,曾枣庄:《宋代序跋全编》卷三,齐鲁书社2015年版,第65页。
[12]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78—179页。
[13]李约瑟:《李约瑟文集》,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 年版,第115页。
[14]朱熹:《楚辞后语》卷六《服胡麻赋》注,《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00页。
[15]宋孝宗:《原道辨》,姚莹:《康輶纪行》卷十一,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01页。
[16]程颐:《明道先生行状》,《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二程集》,第638页。
[17]张伯端著、翁葆光等注:《悟真篇集释》,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
[18]释智圆:《中庸子传上》,《全宋文》第15 册卷三一五,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05页。
[19]据统计两宋书院已有397 所,一说有229 所。参见陈元晖:《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20][美]包弼德著、刘宁译:《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21]熊海英:《北宋文人集会与诗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9页。
[22]郝经:《陵川集》卷十《温公画像》及卷三十九《使宋文移》,《四库全书》本;赵汸:《东山存稿》卷一《观舆图有感》,《四库全书》本。
[23]钱穆:《理学与艺术》,《宋史研究集》第七辑,台湾书局1974年版,第2页。
[24]金毓黻:《宋辽金史》第一册第一章《总论》,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25][法]谢和耐著、耿升译:《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26]袁采:《袁氏世范》卷中《子弟当习儒业》,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页。
[27]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40页。
[28]《张政烺文集·文史丛考》,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27页。
[29]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1页。
[30]《西湖老人繁盛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年版,第2页。
[31]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年版,第3页。
[32]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
[33]《西湖老人繁盛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年版,第16页。
[34]《武林旧事·乾淳奉亲》。
[35]《碧鸡漫志》卷二。
[36]《都城纪胜·瓦舍众伎》。
[37]缪钺:《全宋文序》,《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38]刘克庄:《后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页。
[39]漆绪邦等:《中国诗论史》,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726页。
[40]张方平:《乐全先生文集》卷十一《雅乐论》,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709页。
[41]杨湜:《古今词话·无名氏》,《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页。
[42]张剑:《情境诗学:理解近世诗歌的另一种路径》,《上海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43][日]吉川幸次郎著,李庆、骆玉明等译:《宋元明诗概说》,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3页。
[44]缪钺:《论宋诗》,《宋诗鉴赏辞典·代序》,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
[45]胡仔:《苔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81页。
[46]葛兆光:《从宋诗到白话诗》,《文学评论》1990 年第4期。
[47]陈师道:《后山诗话》,《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1页。
[48]李清照:《词论》,《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94页。
[49]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论文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09页。
[50]孔平仲:《谈苑》卷四,《全宋笔记》二编第五册,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页。
[51]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61页。
[52]鲁迅:《鲁迅全集(八)中国小说史略 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87页。
[53]吴自牧:《梦粱录》卷二〇,第193页。
[54]孟元老著、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3页。
[55]洪迈编、何倬点校:《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1820页。王明清:《投辖录·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56][日]冈本不二明:《睽车志与夷坚志——“科学与志怪”之一》,《甘肃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57]龙建国、廖美英:《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文化艺术商品化》,《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58]潘天寿:《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
[59]南宋词集大量以雅词命名,并不断有词论家对雅化理论进行阐述,如张炎《词源》“词欲雅而正”“雅词协音,虽一字亦不放过”;沈义父《乐府指迷》“康伯可、柳看卿音律甚协,句法亦多有好处,然未免有鄙俗语”,皆肯定词体创作思想规范的雅正、词调音律的规范、语言修辞的文雅和品格气度的高雅。
[60]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中正书局1953年版,第70页。
[61]薛富兴:《中国美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6 年版,第148页。
[62]翟奎凤:《心性化与唐宋元明中国思想的内转及其危机——以禅宗、内丹、理学为线索的思考》,《文史哲》2016年第6期。
[63]虞云国:《略论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地位》,《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64]傅乐成:《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国立”编译馆馆刊》1972年第1卷第4期。
[65]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78、7页。
[66]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中国通史论文集》,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第340页。
[67]惠洪:《冷斋夜话》卷六,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7页。
[68]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2089页。
[69]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96页。
[70]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48页。
[7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四《真宗景德三年九月壬子》,中华书局1980 年版。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中华书局1957年版。
[72]脱脱:《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
[73]苏辙:《来城集》卷四二《论北朝所见于朝廷不便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7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640—3641页。
[75]张鉴:《西夏纪事本末》,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 年版,第65页。
[76]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3995页。
[77]吴广成、龚世俊:《西夏书事校证》,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
[78]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6页。
[79]董克昌:《宋金外交往来初探》,《学习与探索》1990年第2期。
[80]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28页。
[81]朱权著、姚品文笺评:《太和正音谱笺评》,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0页。
[82]确庵、耐庵编,崔文印笺证:《靖康稗史笺证》之六《呻吟语》,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9页。
[83]范成大:《真定舞》,《宋诗抄·石湖诗抄》,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41页。
[84]刘子翚:《汴京纪事二十首》,《宣和遗事·后集》,《四部备要》本,第28页。
[85][日]宫崎市定:《宫崎市定全集》第2 卷,岩波书店1992年版。
[86]苏轼:《苏轼文集》卷六九《评草书》,第2183页。[87]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年版,第148页。
[88]乔光辉:《元文人心态与文学实践》,《东岳论坛》1996年第3期。
[89]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页。
[90]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 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68页。
[91][德]迪特·库恩著、李文锋译:《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9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6页。
[93]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国学论丛》第1 卷3号,1928年4月。
[94]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7页。
[95]邓广铭:《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页。
[96]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