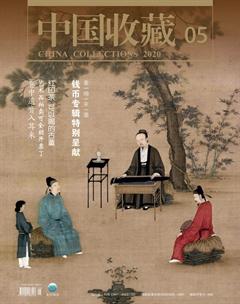文人琴 文人造
闵俊嵘
琴作为礼乐的一部分,在历代不断发展演变。目前能见到清代中和韶乐、丹陛大乐所用琴的实物,其形制有统一的规范,制作工艺和演奏方式与文人琴基本相同,但整体气韵略显呆板,使用频率也很低,只有在元旦、大婚等重要庆典时才用。所以古琴文化传播的主体是作为修身工具的文人琴,文人用琴文人造,或许虽不必亲自动手,实则每每参与其中。
在具体的斫琴实践中,除文人参与以外,皇室贵胄参与斫琴的成效似乎更为显著。比如宋徽宗,集天下名琴成“万琴堂”,并且御制宣和式琴“松石间意”。再如清乾隆帝,将收集的名琴登记造册,绘制御制琴谱。还有明代的弘治帝、崇祯帝,以及益王、衡王、宁王、潞王等皇亲国戚,都参与了制琴。他们与普通文人相比虽然位高权重,但从学识与艺术情操来讲,不能说一生写四万余首诗的弘历不是文人,也不能说编写了《古音正宗》的潞王朱常涝不是文人。

宋人摹顾恺之《斫琴图》故宫博物院藏
各有分工
斫琴包括木工和髹饰工艺两部分,其中“斫”字的释义是砍和削,主要指挖斫槽腹结构,安装岳尾等配件;髹饰指的是制作琴体表面的灰漆层,髹漆的本意是刷漆。这类工艺美术活动一般由工匠完成,但是斫琴有别于一般的造物活动。当琴的使用从祭祀和礼乐转移到音乐审美以后,就与文人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是出土发掘的器物,还是历代传世名琴;无论是宫廷官造琴,还是民间“野斫”,琴的制作与使用都与文人密切相关。他们或创制、或监制,或亲自参与制作。
斫琴技艺包括复杂的流程,一人很难将各个工序出色完成,最直观的就是宋摹本顾恺之的《斫琴图》。图中人物分为六组,共绘14人,左侧年轻力盛者在砍削琴面弧度,地上散落着木屑;左下方一年龄稍长者在挖斫槽腹,此二人属于基础木工组。右侧下方两人席地而坐,一人撸起袖子用笔在木块上标识切割的锯口位置,另一人执笔若有所思,似乎是在听右侧长者所言,等待长者指出槽腹内需要如何修正。琴胎旁边放有斧头、手锯、木锉和刨子等工具,这一组在作比较细致的槽腹木工微调和配件安装。两位执笔者所坐的垫子分别是狮和虎的整张皮,与旁边长者所坐的双层织绣垫子形成很大反差,反映出他们不同的身份特征。右侧的长者显然是属于比较儒雅的文人。画面右上方描繪—人在制作琴弦,在木制弦弓上绳丝为弦。
画面中部是另一位深谙音律的文人在调弦审音,此时的琴体已经髹涂完漆液,色泽较深。其右侧坐着一位督造者,两人所用垫子也有所不同,督造者使用的同样是比较朴素的织物垫子,之所以能成为督造者,推测是由于他在乐律造诣和审美经验方面高出一筹。
斫琴与督造过程中,一位手持凭杖的主人出现在画面左侧,他是这个斫琴团队的核心人物,负责把控进度与整体方向。此外还有五位童子,或随从、或伫立,还有一位背着包袱做奔跑状,或许是背着一包鹿角霜,正在赶往髹漆的作坊。画面中人物形象鲜明,所使用的工具,以及着装配饰体现出他们不同的身份特征。整个工艺流程说明斫琴在当时是一件复杂的事情,文人在其中发挥着统领作用。
感性记述
琴的常见样式有几十种,如伏羲氏、神农氏、仲尼式、连珠式、蕉叶式、中和式等。这些样式靠琴体的外部轮廓特征来区分,但不论哪一种样式,都遵循着一套槽腹规律,即琴体木胎结构比例关系。槽腹制度根本上决定了琴音色的风格与品质。
唐代李勉在《琴记》中载:“其身用桐,岳至上池厚八分,上池以下厚六分,至尾厚四分。”从琴体岳山至尾的厚薄尺寸记录很清楚,但前提是用桐木这种材料,如果换成其他木质,尺寸就会有相应变动。琴面与底的配比要达到和谐,否则会出现韵短、声焦等问题。北宋石汝历在《碧落子斫琴法》中对琴面底匹配关系作了详细描述:“凡面薄底厚,木虚泛清,利于小弦,不利大弦。面底皆薄,木泛俱虚,其声疾出,声韵飘荡。”
琴体槽腹、髹漆,以及琴弦和放置琴的琴桌,甚至弹琴所处环境的温度与相对湿度,都是除演奏者以外,会对音质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但是从斫琴角度来看,槽腹结构是最核心因素,它是材料学、力学、声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琴材的新与旧、阴与阳、疏与密等具体性能,琴体各个部位所用不同材料与尺寸之间都存在着辩证关系。
今天我们能把斫琴技艺分解开去做各种分析研究,而古人更多的是感性经验的总结,并通过文人用委婉的语言来描述。如《琴苑要录》中所述:“谁识倚山路,江深海亦深,洞中多曲岸,此处值千金。”其中“山路”“江海”“曲岸”等名称是对古琴纳音、龙池等部位的指代,“谁识”“亦深”“多曲岸”是指其中的奥妙无法用语言表达。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张“九霄环佩”琴,龙池结构正如秘诀中所讲,隆起的纳音有一道深浅不一的“山路”,崎岖不平,或许是天然形成的蛀洞,或许是斫琴过程中的人为。北宋苏轼在《琴书杂事》中记述雷琴独有余韵,为了探究其中奥秘,将琴破腹打开,发现龙池与凤沼处的纳音微隆如韭叶,音韵被拦截在池沼内使其徘徊往返,余音袅袅。这些经验需要在斫琴过程中不断实践,在操缦过程中细细体味每一种组合关系产生的音质变化,经过无数次的调整,最终总结出规律,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传播,这也是文人参与斫琴的意义所在。
重于漆艺
《斫琴图》里没有描绘琴体髹漆的场景,或许是因为画幅不够长,也可能因为髹漆动作不易表现,但琴体髹漆对于一张琴来说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
漆器髹饰工艺的历史要久于古琴,但关于髹饰工艺的记述文字却没有像古琴一样,有那么多的琴谱流传下来。其主要原因是单纯的髹漆工艺被视为形而下的体力劳动,文人士大夫很少参与其中,也不愿在其过程中留下自己的名字。而髹漆的工匠大多没有文字记录和著述能力,五代的《漆经》已经失传,剩下唯一的是明代漆工艺专著《髹饰录》。

从斫琴角度来看,槽腹结构是最核心因素,它是材料学、力学、声学等多学科的交叉。

《斫琴图》里没有描绘琴体髹漆的场景,可能因为髹漆动作不易表现,但琴体髹漆对于一张琴来说至关重要。
《髹饰录》分为乾集和坤集,详细记录了漆器髹饰工艺中所用到的材料、工具、各类装饰工艺,以及造物的法则和禁忌。其中坤集糙漆之第三次煎糙载:“右三糙者,古法,而髹琴必用之。今造器皿者,一次用生漆糙,二次用曜糙而止。”一般的器物第一遍糙生漆,第二遍糙调制的熟漆即可完成,而琴的糙漆按照古法必须糙三遍。由此可见,琴在古代造物中的地位要高于其他器物。琴谱中有大量关于琴体髹漆的记录,如《琴苑要录》中记载的合琴光法:“煎成,光一斤,鸡子清二个,铝粉一钱,研清生漆六两。”这些由琴人记录的髹琴技法反过来又丰富了漆工艺的内涵。
无论是对于帝王将相,还是文人士大夫,以及众多习琴、爱琴之人,琴声出于天籁、成于人心,借助器乐可以宣情、修身。如《琴诀》中所讲:“摄心魄,辨喜怒,悦情思,静思虑。”人们对生命情感价值的探索,常常源自于生活中喜怒哀乐的形成与表达。古琴可以帮助文人从现实生活中走出来,去关注诗意和远方,达到心平德和,琴就从器走向了艺,进而走向对德与道的探寻,无疑这是从古至今文人参与斫琴的原动力。
(注:本文作者系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