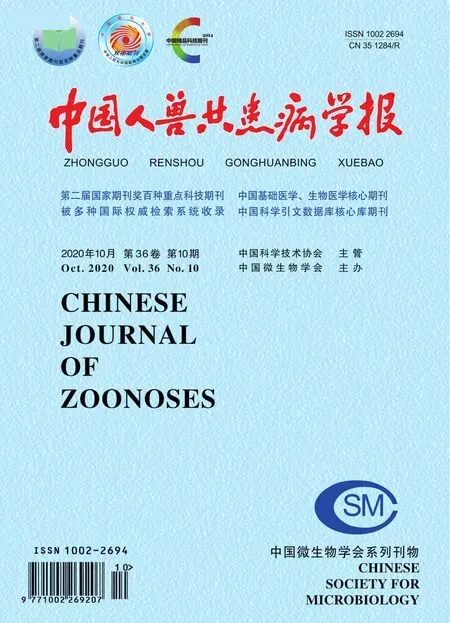SARS-CoV-2的研究进展
王常乐,王 磊,郝 冉,乔红秀,赵 艳,揣 侠
2019年12月底,我国武汉市暴发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后经全基因组测序分析证实该病毒属冠状病毒家族的新成员。2020年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将该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SARS-CoV-2,将其导致的肺炎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SARS-CoV-2感染人群数量迅速飙升,肺炎疫情持续扩散,一场没有硝烟的“抗疫战争”在世界各地悄然打响。本文旨在对SARS-CoV-2生物学特性、起源、感染与宿主免疫反应,传播及治疗等做出研究与探讨。
1 SARS-CoV-2生物学特性
1.1SARS-CoV-2 SARS-CoV-2属冠状病毒家族中β属的新成员,电镜下呈圆形或椭圆形,直径约为60~140 nm。该病毒由单股正链RNA(+ssRNA)、蛋白衣壳、包膜(包膜外有刺突)3部分结构组成[1]。在RNA聚合酶作用下,SARS-CoV-2可合成出与其基因组相匹配的单负链RNA(-ssRNA),进一步合成正义RNA(positive-sense genomic RNA,gRNA)和亚基因组RNA(subgenomic RNA,sgRNA),以发挥编码蛋白的作用[2]。
SARS-CoV-2基因组长约30 kb,其gRNA被合成出的病毒结构蛋白包裹后,共同组装成子代病毒颗粒。sgRNA负责编码刺突蛋白(spike,S),包膜蛋白(envelope,E),膜蛋白(membrane,M)和核衣壳蛋白(nucleocapsid,N)4种结构蛋白及其它辅助蛋白。Kim等在其研究中表明,SARS-CoV-2至少含有6种辅助蛋白,而在其基因组结构中,ORF1a、ORF1b、ORF3a、ORF6、ORF7a、ORF7b、ORF8、S、E、M和N被证实能够转录及编码蛋白,但ORF10的功能尚需进一步证实[2]。
1.2SARS-CoV-2理化特性 目前,对于SARS-CoV-2理化特性的认识多来自于SARS-CoV、MERS-CoV等冠状病毒的研究。以SARS-CoV为例,正常室温与湿度下,病毒在空气中存活约为24 h。相同湿度下,温度升高病毒活性降低[3]。一般来说,56 ℃ 30 min,70 ℃ 15 min基本可将病毒灭活。此外,病毒对紫外线敏感,且75%医用乙醇、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乙醚等脂溶性溶剂均可破坏病毒外的脂质包膜,从而有效灭活病毒。研究报道显示,将3.3×106TCID50/mL SARS-CoV-2感染Vero细胞,分别放置56 ℃ 30 min、60 ℃ 60 min及92 ℃ 15 min后,56 ℃和60 ℃环境并不能明显抑制病毒核酸在宿主细胞内的复制。只有当加热至92 ℃,才能够有效降低病毒RNA在宿主细胞的复制量[4]。研究人员发现,SARS-CoV-2在不同材质表面存活时间不同,即在铜、硬纸板、不锈钢和塑料表面分别可存活4 h、24 h、2 d和3 d[5]。一项发表在预印本medRxiv的研究,在室外空气颗粒物PM10中检测出SARS-CoV-2的RNA,预示病毒或可与PM10相结成簇,加强自身在大气中的存留能力[6]。
2 SARS-CoV-2的起源与进化
COVID-19疫情早期,Zhou 等[7]从5名患者体内获得了该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分析发现,SARS-CoV-2与SARS-CoV基因组序列的相似程度为79.5%,但与一种蝙蝠来源冠状病毒(Bat CoV RaTG13)的序列一致性高达96%,提示SARS-CoV-2或来源于蝙蝠。此外,1株来源于蝙蝠被命名为RmYN02的冠状病毒与SARS-CoV-2的全基因组序列相似度为93.3%,且在RmYN02的S1和S2蛋白交界处,同样发现了插入的氨基酸残基,尽管SARS-CoV-2与RmYN02的S1、S2蛋白交界处插入的残基不同,但残基插入是一个独立事件且能在自然界中通过重组获得[8],为探索SARS-CoV-2的起源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国科学院、华南农业大学及北京脑科中心的研究人员收集并分析了全世界各领域共享到Global Initiative on Sharing All Influenza Data (GISAID)数据库的93个SARS-CoV-2基因组数据,发现在这些样本中共包含58种单倍型,其中单倍型H13和H38属古老单倍型,通过来源于中间宿主或“零号病人”的中间载体,与蝙蝠冠状病毒RaTG13关联,并通过H3繁衍生出H1。这些都是导致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暴发COVID-19单倍型的“祖先”,从而证实病毒是外源流入该市场内,并引起大面积传播与蔓延[9]。另有研究分析160份SARS-CoV-2全基因组发现,由于氨基酸改变,病毒已生成A、B、C 3类突变体:其中A类为始祖病毒,广泛分布在美国、澳大利亚。B类为A类后代,集中分布在中国和其他东亚地区。C类为B类后代,在中国大陆尚未发现,主要分布在欧洲、中国香港和台湾[10]。该项研究样本量虽较少,但提示导致COVID-19暴发的源头不在武汉,SARS-CoV-2的起源仍需探索与验证。
3 病毒感染与宿主免疫反应
3.1SARS-CoV-2感染宿主细胞 冠状病毒主要是通过其表面的 S 蛋白与靶细胞上的相应受体结合进入细胞,完成感染的过程,已有研究表明,SARS-CoV-2与SARS-CoV一样通过血管紧张素转化酶II(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ACE2)进入细胞。 Bao等在感染野生型及hACE2(human ACE2)转基因型小鼠后,发现SARS-CoV-2能够在hACE2小鼠肺中增殖,并使得小鼠体重下降。免疫组化及组织病理结果显示其导致hACE2小鼠间质性肺炎,肺泡间质内明显淋巴和单核细胞浸润,肺泡腔内巨噬细胞积聚[11]。ACE2是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enin-angiotensin system,RAS)中的关键性酶之一,广泛分布在人体不同脏器细胞。多项临床数据显示,SARS-CoV-2可攻击人体心血管、肾脏、肝脏、中枢神经及肠道等系统,从而引起除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呼吸道症状外,还有心律失常、血凝异常、肾脏损伤、肝功异常、脑炎、腹泻等[12-15]。宿主细胞膜跨膜丝氨酸蛋白酶2(type II trans-membrane serine protease,TMPRSS2)被证实当SARS-CoV-2侵入人体时,其发挥着病毒S蛋白启动蛋白的作用,进而使得病毒侵入宿主细胞[16]。研究人员发现,ACE2、TMPRSS2基因高表达于人体鼻部杯状和纤毛细胞表面,表明鼻部组织细胞或为SARS-CoV-2最初感染部位[17]。一项揭示SARS-CoV-2入侵宿主细胞及免疫逃逸机制的研究中表明,SARS-CoV-2中S蛋白的RBD(receptor binding domain)比SARS-CoV的RBD具有与hACE2受体更强的结合能力,但SARS-CoV-2的RBD呈现出的“lying”状态比SARS-CoV的RBD呈现出的“standing”状态使得SARS-CoV-2不利于与宿主细胞受体相结合。但SARS-CoV-2可激活宿主的蛋白酶,同时利用Furin蛋白预激活其S蛋白。Furin蛋白、宿主蛋白酶以及TMPRSS2可发挥累积效应,从而增强SARS-CoV-2对宿主细胞的入侵;也正是因为SARS-CoV-2的RBD呈现出lying状态,帮助其逃避机体抗体的中和作用,出现免疫逃逸[18]。
3.2宿主免疫反应 人体固有免疫系统,时刻监视着外界入侵的病原体。肺部巨噬和上皮细胞,被认为是发现、识别侵入人体呼吸系统病原体,释放免疫信号,触发一系列免疫反应以清除入侵者的第一道屏障。细胞因子的分泌对人体肺部细胞和组织是把双刃剑。当其适度产生时,可作为免疫信号,积极有效参与宿主防御,并发挥有效作用。一旦分泌过量,可加剧宿主肺组织损伤,导致器官衰竭。一项来自单细胞RNA测序分析COVID-19患者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免疫细胞样本的研究显示,在其收集的9名COVID-19患者样本中,6名重症患者BALF中的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浓度高于3名中症患者及健康对照。同时,重症患者BALF中也具有更高水平IL-1、IL-6、IL-8等炎性细胞因子及趋化因子[19]。此外,其他临床案例研究报道同样指出,COVID-19患者血浆中的IL-1β、IL-8、TNF-α、IFN-γ等含量明显高于健康人群[20-21],显示SARS-CoV-2感染人体后,可引起宿主细胞释放过量细胞因子,即导致细胞因子风暴的发生。细胞因子风暴的形成或跟病毒感染宿主时结合Fc受体,介导抗体依赖性增强(antibody dependent enhancement,ADE)作用相关。即SARS-CoV-2刺激机体产生的中和抗体不能将其完全清除,形成的“病毒-抗体”复合物会与宿主细胞Fc受体相结合,增强病毒的感染。同时“病毒-抗体”复合物会激活促炎症反应信号,活化巨噬细胞,释放大量细胞因子,造成肺部组织损伤[22]。
国内、外学者均发现,人体呼吸道上皮细胞在受到干扰素(IFN-β、IFN-γ)的刺激后,会增加ACE2的表达,继而增加与S蛋白的结合。因此,SARS-CoV-2引起的宿主细胞因子风暴不单是造成对人体各组织器官的损伤,同时还可进一步增强病毒在宿主内的感染与播散[23-24]。研究显示,COVID-19恢复期病人体内含有针对病毒蛋白的IgM和IgG抗体[25]。此外,在这些恢复期病人血液内同样检测到针对SARS-CoV-2的CD4+、CD8+T细胞,可识别病毒的S、M、N 3种结构蛋白以及nsp3、nsp4等非结构蛋白[26]。这项研究证实,在特异性免疫应答反应中,T细胞能够对SARS-CoV-2做出有效反应,或对疫苗的研发提供帮助[26]。
4 COVID-19的传播特点
SARS-CoV-2对宿主感染能力极强,使得COVID-19在人群间迅速传播,世卫组织也已宣布COVID-19为全球大流行(pandemic)。目前,已造成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各国超80万人死亡。因此,及时更新与完善临床救治方案、总结治疗经验,共同分享科研数据与成果,有效开展疫苗的研究与临床试验,是人类共同战胜SARS-CoV-2及COVID-19的希望。
4.1传染源与传播途径 SARS-CoV-2传染源主要以COVID-19感染者为主。但无症状感染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27]。笔者认为:1)无症状感染者的病例数量不明确;2)无症状患者传播COVID-19的能力不明确;3)无症状患者体内SARS-CoV-2跟自身免疫系统间相互作用不明确。因存在这3点“不明确”,无症状感染病例更需要密切监测与防护防范,以阻止COVID-19流行的扩大化;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或地区开展血清学的调查与检测,有助于了解SARS-CoV-2在人群的感染水平,对疫情未来的发展趋势、疫苗接种、以及完善COVID-19的防控策略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是COVID-19的主要传播途径[27]。由于SARS-CoV-2可感染人体肾脏[15]和人或蝙蝠肠道细胞[28],因此,可在粪便、尿液中检测出该病毒核酸。一旦病患粪便、尿液造成一定环境、食物或水源污染,也可经粪-口途径传播。此外,人群长时间暴露在密闭环境中的高浓度气溶胶,即已在空气中形成的病毒气溶胶,也同样被认为是造成COVID-19传播的潜在途径。Liu等[29]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武昌方舱医院的病房(patient areas,PAA)和医务人员区域(medical staff areas,MSA),以及武汉市部分公共区域(public areas,PUA)共采集了31个位点的空气样本,利用数字PCR方法检测并定量气溶胶样本中SARS-CoV-2的RNA浓度。结果显示:武汉人民医院及方舱医院PAA和MSA的病毒RNA检测均呈阳性反应。但当患者数量减少及严格消毒后,RNA浓度可变为0。此外,在武汉PUA采集的12个样本中,4个区域的病毒RNA也呈阳性反应。研究人员推测被SARS-CoV-2感染的无症状携带者或许是人群密集区域引起病毒气溶胶传播的重要因素。因此,医院高危区域需经常通风和有效消毒,公共区域需佩戴口罩及减少人群密集区聚集,以分别防止SARS-CoV-2在院内及社区气溶胶传播[29]。
4.2影响传播的因素 目前,对于影响COVID-19疾病传播的因素,各国科研人员还处于探索阶段。Oliveiros等[30]采集了中国内地31个省份39 d内COVID-19的确诊病例,结合温度、湿度、降水和风速4个气象变量,进行拟合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发现,COVID-19病例数量与气温和湿度有关,其病例倍增时间与温度成正相关,与湿度成反比。浴场内SARS-CoV-2群体传播案例报道,湿度增加虽可使得病毒传播,但高温或许难以阻挡其侵入人体[31]。有研究收集分析了截至2020年3月9日中国内地COVID-19确诊病例大于10例的224个城市的病例和气象数据,指出气温升高或阳光紫外线强度增加或可不会影响SARS-CoV-2的传播能力[32]。上述多项已发布的数据结果,虽从气象变量、温度、湿度及阳光紫外线对COVID-19的传播作出初步研究探讨,但笔者认为对于影响COVID-19传播的因素,需进一步分析,尤其要扩增样本量,实际采集更多地域的气候与病例数据,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但目前防控COVID-19的传播更多是居家隔离,因此,进一步探索气温、湿度、光照紫外线等因素对疾病传播的影响或许将更为困难。
5 COVID-19的新型治疗策略
第7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中,对于COVID-19的治疗,可根据不同病情选择不同治疗场所,一般治疗、重型、危重型治疗及中医治疗4部分救治措施。即:监测生命体征,维持血氧饱和度,抗病毒抗继发细菌感染,循环支持,康复者血浆、血液净化、免疫治疗及中药方剂等。目前虽尚无针对SARS-CoV-2感染的特效抗病毒药物,疫苗研发也只是在临床I期、II期试验阶段,但笔者认为对于这次在临床救治COVID-19患者、特别是危重患者采用的一些新型治疗方法,值得总结完善,可在临床实践与推广。
5.1间充质干细胞治疗 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s)是一种可从人体组织分离得到并具有多向分化潜能的细胞,适宜条件下可分化为肺脏、肝脏、肾脏、神经等组织细胞。MSCs免疫原性较低,能够参与机体免疫调节。文献报道,MSCs能够平衡机体过度释放的炎性细胞因子,调控炎性微环境,产生免疫抑制分子、生长及趋化因子等影响免疫细胞的招募、迁移、活化及功能,具有广阔临床应用前景[33]。
截至今年2月底,我国临床实验注册中心已注册12项在研干细胞治疗COVID-19相关项目。SARS-CoV-2感染呼吸系统后,重症患者体内会出现细胞因子风暴,甚至发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可短时间内器官衰竭并导致死亡[34]。给予MSCs治疗后,或可通过抑制IL-1、IL-6、IL-12、TNF-α、IFN-γ等炎性细胞因子分泌,促进IL-10等抑炎因子产生,直接诱导CD4/CD25/FoxP3调节性T细胞,促进具有抑制炎症反应的M2型巨噬细胞极化等,平衡病毒感染宿主细胞引起的免疫反应[35-36]。此外,MSCs可分化为人体I型、II型肺泡上皮、肺血管内皮细胞,停留并修复损伤的肺组织,降低肺部纤维化,改善肺部受损功能。
目前,MSCs治疗COVID-19的相关基础与临床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笔者认为,在后续研究与应用中,应更为深入探索MSCs帮助机体防御病原体感染的具体过程与作用机制,以及MSCs进入人体后的去向与稳定性。同时,在治疗病毒引起的呼吸道感染疾病时,可学习与借鉴浙江大学第一医院李兰娟院士团队积累的干细胞治疗H7N9禽流感病毒引起肺部感染与纤维化的宝贵经验。并从这些经验、方法中摸索与总结出更为适合SARS-CoV-2及其它呼吸道病毒引起的感染性疾病的方案,为治疗病毒性感染提供新的手段。
5.2抗病毒血清 病毒感染人体后,可刺激人体免疫系统产生抗体,从而中和并清除侵入人体组织及细胞的病毒。2003年抗击SARS疫情时,钟南山院士团队证实,SARS-CoV感染人体后,刺激机体产生的IgM和IgG抗体对SARS-CoV具有中和作用,可保护人体免受SARS-CoV的二次感染[37]。笔者认为,借助于SARS-CoV治疗性抗体的临床应用与研究,或对治疗COVID-19患者具有广阔应用前景。
第7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中指出,可将COVID-19康复者血浆用于治疗病情进展快、重型和危重型患者。武汉部分医院也已给予患者输注血浆,并取得很好治疗效果。科研人员收集了14名SARS-CoV-2感染后轻症康复者的血浆,分别检测针对SARS-CoV-2的N蛋白(NP)、主要蛋白酶、及S蛋白受体结合区(S-RBD)的特异性IgM和IgG抗体。结果发现,COVID-19患者体内能够产生抗-NP和抗-S-RBD的IgM和IgG抗体,且IgG在出院2周后维持较高水平。此外,该研究指出,中和抗体滴度与NP特异性T细胞数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表面中和抗体或与抗病毒T细胞活化有关。进而提示,有效清除病毒的感染,需要协同体液与细胞免疫反应[25]。研究显示,SARS康复者体内分离出的中和抗体CR3022能够与SARS-CoV-2相互作用,而且SARS-CoV与SARS-CoV-2的抗体结合位点只差4个氨基酸,结合位点的高相似性或可为制备SARS-CoV-2抗体提供新方向[38]。
6 结 语
携手抗疫,共克时艰。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与灾难,全世界只有团结一致,共享最新科研数据与成果,共享临床一线总结的方法与经验,加强国与国、国与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才是人类共同战胜COVID-19的希望与法宝。笔者认为,虽然对于SARS-CoV-2的起源还尚未有明确定论,但爱护自然、保护动物,维持人与自然,人与动物间长久和谐与稳定才是人类立足于这个蓝色星球的根本。在治疗SARS-CoV-2或其他病毒引起的感染性疾病时,如通过严格伦理审查之后,可采用一些新型治疗方法,与传统治疗方法相结合,或可提高临床救治率,挽救更多生命。此外,有效的疫苗应用可终结疫情进一步传播与蔓延。
利益冲突: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