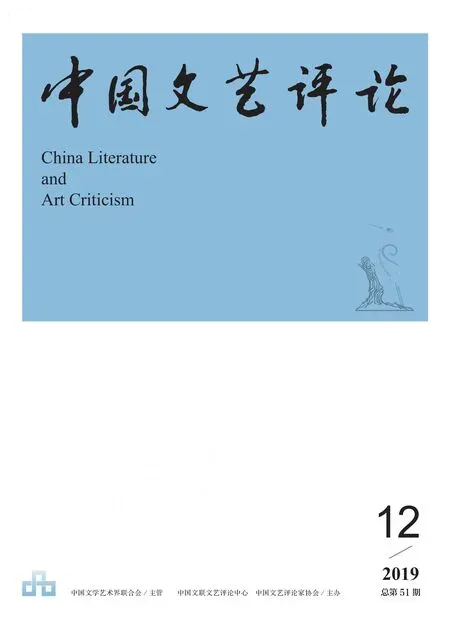做艺术上的“叛逆者”和“稳健者”
——访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
采访人:胡凌虹
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自称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早些年,他一直打“飞的”,全国各地跑。如今虽近80高龄了,依然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去传承、发展戏曲事业。近些年,尚长荣积极参与戏曲电影的拍摄,乐于从一位“戏曲界的超龄服役的老兵”变身为“中国电影艺术界的新兵”,且取得了杰出成绩。2019年,第十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18年度表彰大会授予他“传承国粹,精湛银幕”特别荣誉。而今他笑说自己已逐渐“重点转移”,“以前是在第一线舞台上打拼,现在确实要腾出手来在推动、传承上下功夫。所以近七八年来,我讲座也多了,对青年的教学、培养也增加了。这也是我们年长一点的戏曲人的一个担当”。可以说,京剧艺术如何传承、如何推动、如何出新,一直是尚长荣冥思苦想并积极实践的课题。
一、戏曲创作应“顺天应时”
胡凌虹(以下简称“胡”):您从艺几十年,可以说目睹了京剧艺术的一段发展变革史,有什么特别深的感触?
尚长荣(以下简称“尚”):京剧艺术的发展形成,不是由哪位凭空设想而成的,实际上是顺应了当时观众视觉听觉的需求。观众觉得单听一个剧种单调,京剧艺术的先贤们便融合了几个主要剧种之大成,形成了一种综合性很强的新的表演形式,晋京后形成了一个新的剧种,1876年上海的《申报》第一次出现“京剧”一词,所以应该说京剧是全国性的剧种,它的语言并非是一种地方语言,它是顺天应时的产物。经济发展到今天,回顾这段京剧历史,不是保守的,是不断发展的,但是它始终坚守着本体生命、遵循着本体风格而逐渐地与时俱进、去粗取精。特别是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的指引、厚爱、推动之下,京剧艺术走在一条康庄大道上,虽然其中也有坎坷曲折,但终究是一条准确的路子。从宏观上来讲,现在是咱们国家极为繁荣、极为昌盛的时代,无论是第一线上的舞台,培养后生的学校,还是普及弘扬、对外文宣,各方面工作都做得非常务实。
胡:您并不以传统戏、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来划分戏,认为只有“好戏”和“不好的戏”之别,在您看来什么是“好戏”?
尚:“好戏”就是演出时间久、有票房号召力、受观众欢迎的剧目。在20世纪上半叶,也就是我父亲办剧团的那个年代,京剧从业者们就已自觉不自觉地关注市场、关注观众、关注时代。叫座不叫座对于剧团十分重要,因为剧团是以票房维持生存的。剧团须根据观众欣赏需求的变化,适时调整、与之俱进。比如,周信芳先生的《明末遗恨》诞生于抗战时期的上海,由于戏中借明末故事痛斥当时上层统治者的腐败和不抵抗主义,对人民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因而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我认为,要延长戏的艺术生命力,就必须要研究当代的观众想看什么戏、爱看什么戏,必须做到让观众喜欢。所谓“好戏”,受观众欢迎的戏,戏中传达出来的思想情感能与当前的时代、眼下的观众有共同点、契合点。好戏不仅使观众获得艺术享受,同时还能引发人们联系自身的生活经历和实践进行思考,从而得出启迪、警示,只有这样,观众才会满意。
胡:您的新编历史京剧“三部曲”之所以被观众认可,也是因为注重观众、注重时代吧?
尚:新编历史京剧“三部曲”被认为是三台“好戏”,就是因为延续了老一辈京剧艺术家不断探索的路子,传承了京剧不断创新的理念,顺应了时代发展和观众审美的要求。我将这个历程称为“顺天应时”。具体说来,《曹操与杨修》提出了如何对待知识分子、如何容忍不同意见的下属以及强者与智者之间如何相处的问题。这在三十多年前曾一度引发轩然大波,具有划时代意义。《贞观盛事》提出了帝王和卿相之间应以什么样的心态、气度、精神来处理好纳谏、敢谏的问题,描绘了一幅盛世时代执政者的政治风貌。而《廉吏于成龙》则提出了执政者不仅应保持自身的清正廉洁,还应做到为官一方、保民安居乐业。“三部曲”分别被称作是“警世”“明世”和“劝世”之作,均为跟随时代应运而生、抓住时代脉搏的作品,因此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胡:很多人会觉得做演员很被动,但从您的创作经历中可以感受到很强的能动性。您曾说过“作为一个人,我与世无争;作为一个演员,我要奋力去争——争自己在舞台上、在艺术上的业绩。没有业绩,我无脸见爹娘、无颜对观众。”
尚:有人认为,三部新编历史京剧连续取得成功是因为我运气好。确实,遇到了那么多好时机、好剧本、好导演、好搭档,我的运气是很好——但我认为,生逢盛世,机遇面前人人平等,关键在于思想和艺术眼光,对题材、人物形象的选择;在于如何找到既取信历史又关照现实、既激活传统又融入时代的内容和形式。
《曹操与杨修》的文本是公开发表的,我并不比别人有优先权。20世纪80年代,好友史美强向我推荐在1987年元月号《剧本》杂志上刊登的《曹操与杨修》。一读之下,我立即被剧本深深吸引,但我当时所在的陕西京剧院无法排这部戏,于是我把院长的职务辞了,也放弃了优越的物质条件,于1987年10月怀揣剧本,听着贝多芬的《命运》坐绿皮火车来到申城,扣响了上海京剧院的门环,大家一拍即合。
记得排演时,马科导演曾对所有演职员说:“尚长荣的脸皮最厚。他老是伸长了脖子,等着让导演给他抠戏。”虽是一句玩笑话,却也说出了实情。要在戏曲舞台上体验人物、塑造人物,光凭演员自己还不够,必须有导演的帮助。导演的精到见解往往会激发演员创造出更精彩、更符合人物的表演手段。但同时我认为演员也不能完全依赖导演,光等导演来给自己“喂饭”。
京剧是一门以演员为中心的综合艺术,作为戏曲演员必须发挥主体作用,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参与到创作中去。在《廉吏于成龙》的“斗酒”中,京剧西皮的各种板式几乎被全部用尽;到后面于成龙与康亲王一决高下时,如何再能奇峰突起、再掀高潮呢?我建议尝试化用昆曲的“吹腔”,一试之下,效果令人惊喜。让花脸唱“四平调”,这是我一直想做的尝试。“四平调”是传统生行和旦行的腔,以前的净行是不唱的;但在《贞观盛事》中,我发现魏征当时修完奏本后陶醉于“翠涛”酒的舒畅心境,与“四平调”的抒情特征十分吻合,因此建议采用“四平调”,果然唱出了意境、唱出了意趣,得到了业内行家的好评。
戏曲创作过程中,编剧、导演等既有自己所擅长的领域,也有自己力所不及的地方——那就是在舞台上直面观众的经验。编剧、导演所设定的东西,并非全都是最佳的方案。因此,演员需要积极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把舞台经验化作自己的思路、自己的见解、自己的行动,最终使戏趋向完美。
二、激活传统、融入时代
胡:您自称为“保守阵营里的叛逆者,激进队伍中的稳健者”,您是如何看待戏曲传统的?
尚:纵观中华民族的戏曲艺术,剧目丰富、风格多样,展现模式是世界上独一份的。西方歌剧就是歌剧,舞剧就是舞剧,芭蕾就是芭蕾,我们的戏曲包含着唱念做打、诗词歌赋,表现形式极为丰富。如果非要问有没有一个固定模式的话,那么绚丽多彩且歌舞并重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戏曲艺术的模式,也是我们的优势。以前称京剧为北京Opera,这是不确切的,就应该是中国京剧、中国川剧、中国越剧……我们有独特的模式,不要妄自菲薄,把自己往西方的模式里去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戏曲的程式、语言、旋律遵循着美学原则和精神内核,代表着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这就是优秀戏曲的自信,我们的民族自信。

图1 尚长荣在京剧《廉吏于成龙》中饰演于成龙
民族戏曲艺术要发展,其精髓不但不能淡化,反而应该强化,必须守护戏曲的本体生命、本体风格,保持其浓烈的风格和特色。京剧是以声腔呈味、以程式呈美的。京剧观众不光要看戏的故事情节,还要欣赏演员的“玩意儿”。京剧表演艺术以程式为基础,离开了技法——“四功五法”、唱念做打、脸谱服饰等等,京剧就不能称之为京剧了。因此,对京剧艺术传统技法的传承是为根本,必须得到完全继承。
胡: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继承传统就得原汁原味,否则容易被认为是欺师灭祖,甚至会招骂,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尚:确实有一种观点认为,戏曲就是不能改的。但是现今我们佩服孔孟之道,却并不是完全遵循孔孟之道;我们敬佩非常杰出的古代思想家,但是不能教条主义或形而上学地遵循他们的思想。民族自信并不等于保守、墨守成规。传统并非不创新,古典也并非不时尚。我们很多前辈,对传统有继承、有推动,更有胆魄去改革。他们当年太勇敢了,也是很超前的,尝试有成功也有不成功,甚至有失败,但他们都能审时度势,能够沿着一个比较正确的路不断向前,所以迎来了京剧艺术和诸多兄弟剧种百花齐放、百花争艳的阶段。回顾戏曲艺术的道路,本身也是在包容创新、兼收并蓄中发展演变的。
从京剧发展历程看,技法、程式、“玩意儿”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王元化先生认为,程式化同样给演员提供了创造性的广阔天地,正如格律不会拘囿好的诗人、骈体文不会拘囿好的作家一样。程式可以进行不同的组合、链接及创造,它们并不是演员的“手脚镣”,它们也能为演员提供自由的艺术创造空间,演员可以通过程式去进行艺术创造、表现个性。我认为,技法归根到底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如果不从体验人物出发,一成不变地生搬硬套,用老方法来塑造新戏中的人物,那是注定会失败的。比如曹操这个角色,在任何剧目中只要曹操出现,就永远处理成一张“大白脸”,一上场先是一端肩膀,然后奸诈地嘿嘿一笑,总是带有一种让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的感觉,如此便走向了“死学活用”的反面,成为“死学死用”了。
所以,如果我们的步伐一直停留在吃前人留下的半碗冷饭,那一定是没前途的。我们要打开思路、打开眼界,不断学习古代、现代文化,中西方文化,让我们民族的文化、戏曲艺术永远青春鲜活,这样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民族的戏曲艺术才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胡:您觉得应如何把握好传统与创新之间的这个度呢?
尚:用八个字,以我经常做讲座的标题来概括:“激活传统、融入时代”。想搞创新,先把传统学好,先问一下自己,传统文化的积淀够不够深?优秀的传统技法学得怎样?有的戏乡土气息浓厚,却用西洋乐器来伴奏,不伦不类。有些人从国外学了点东西,就草率地拿来改造我们的传统戏曲,怎么不像京剧怎么来。这些急于改造传统戏曲的人,如果只是以洋为美,作品热衷于去思想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这样的所谓创新是绝对没有前途的。
戏剧创新必须“因剧制宜”。大玩“声光电”、搞“大制作”,这样的作品往往会丢掉戏曲的本体,放弃了戏曲以大写意技巧创造人物形象的特点和长处,也忽略了观众通过表演来认识并接受戏曲的需要。我们传统戏剧工作者切不要做花岗岩脑袋、顽固不化;也不要冲动、激进,一窝蜂地去猎奇,陷入走火入魔的境地,这两者都不可取。我们要在守护民族艺术的本质、风格的同时,用活传统戏曲的深厚技巧,推动其不断发展。戏曲要站得住、走得远,只有把历史的内涵和现实的针对性联系起来,在把握传统戏曲深邃底蕴的前提下,融入时代,适应新时期观众的审美需求和艺术品位。
胡:如何在创新中坚守京剧的艺术本体,同时又融入时代,塑造出符合当代人审美需求的人物形象?
尚:首先我会找到人物的历史定位,从而确定我的表演基调,才能进一步形成丰满的人物形象。比如决定演《曹操与杨修》后,我便在文字资料中开始了对曹操这个人物的寻找,从史书记载到历史评论,以及曹操的诗文,包括他颁发的政令、军令等等。最后,我确定了从人性出发追溯曹操心理历程的创作思路。这一思路的确定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对于人性和人类情感的探究是现代艺术的基本主题,同时也是还历史人物本来面目的必由之路。对人物形象的理解和切入,我称为“内功”。“内功”的获得,主要还是遵循了前辈艺术家的传统。侯喜瑞先生给我教戏的时候,对于每出戏、每一个极细微的动作都能说出个“为什么”,也就是寻找人物的心理依据。这种对人物的体认方式,在我们中国戏曲表演艺术中是固有的,是我们艺术传统的精华所在。
举一个例子,在一次央视春节晚会上,有一个节目是八位戏曲演员演绎八个包拯。我是最后一个出场,唱的是“打龙袍”,最后有一段唱是这样:“龙国太待我好恩情,宫中赐我金珰翅,又赐尚方剑一根,三宫六院我管定,压定了这满朝文武大小官员,哪一个不遵,仗剑施刑!”我觉得唱词不太合理,就请我的一个师兄改一改。他直言,你胆子太大了。我回答道,一场戏面对的是一场观众,这个节目面对的是亿万华人,原来的唱词太糙了,不贴合当下。在我的坚持下,后来部分唱词改为了:“执法雪冤肩重任,压定了贪官污吏恶霸豪绅,哪一个不遵,我仗剑施刑。”这就符合了当时老包的心理:他面对的不是满朝文武大小官员,而是贪官污吏恶霸豪绅,这也是当初老包的初衷。
所谓“外功”,是指形象展示于舞台的一切手段。在“内”“外”功的关系上,我的观点是“发于内、形于外”,做到“内重、外准”。在深切感受和把握观众脉搏的同时,以最灵活的方式,力求准确地拨动观众的心弦。在塑造“曹操”时,我突破了传统的净角行当界限,试图将架子的做、念、舞和铜锤的唱糅合在同一表演框架内,努力形成粗犷深厚又不失妩媚夸张的表演风格。这里我力图避免长久以来形成的为技术而技术、以行当演行当的倾向,使行当和技法为塑造人物服务。
很多前辈艺术家所创造的人物不仅能在舞台上光彩照人地立起来,而且能作为经典传下去,关键的一条是他们都具有全面而扎实的“内”“外”功底。今天,我们所缺乏的也正是“内”“外”功俱佳的全才演员。
三、电影让戏曲经典别样重生
胡:近几年,戏曲电影发展非常快,也取得了很显著的成绩。在您看来,戏曲电影对戏曲的传承和发展有着怎样的价值?
尚:事实上,中国电影史发展的每一个重要节点都有戏曲的参与,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戏曲电影《定军山》,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诞生,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鑫培主演,那时是无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几位名家的演出,如梅兰芳先生、马连良先生,还有我们上海京剧院老院长周信芳先生等,都有过演电影的记录,还有其他很多兄弟剧种,也都有戏曲电影。到了今天戏曲电影更是蓬勃发展,这也是一种必然,顺应了这个时代的需求,人们不仅仅到剧场去看戏,还经常带小孩去看电影。
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些年来戏曲电影有了新的发展,有了一个新的展现模式。早年,忠实于舞台的戏曲纪录片,虽然完整再现了剧目全貌,但在艺术普及、传播影响力方面相对较弱;到了今天,戏曲与电影双向结合,在电影的技术手法和戏曲程式的结合上做了更多的尝试和创新,二者结合逐渐从一加一等于二过渡到远大于二的艺术效果,包括对电影的现代全景声技术的充分运用,将戏曲的唱念做打以更为生动的方式呈现在镜头前,把京剧艺术最美妙的瞬间以强有力的展现形式传递给观众,更能感染观众。这不仅有利于戏曲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让更多不能或不方便进剧场的观众通过银幕欣赏戏曲,同时也有利于电影在类型与形式上的突破。中国古代、现代有那么多优秀的、富有正能量的故事,作为京剧人,我们有责任通过精彩的镜头、扎实的演技、先进的影像技术继续讲述这些故事,创作出更多好听好看、打动人心的优质作品。
胡:您从2008年到2018年拍了四部戏曲电影:滕俊杰导演的3D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事》,郑大圣导演的京剧电影《廉吏于成龙》。在戏曲界您已经功成名就,为何还愿意跨入电影艺术界做一个新兵呢?
尚:我第一次戴着眼镜看立体电影是20世纪60年代,在北京大观楼,看了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魔术师的奇遇》。当时我就说,戏曲拍立体电影肯定会好,可一旁坐着的戏曲同行非但没有鼓励我,还给我“撤火”。我觉得他们太保守,为什么不能试试立体电影呢?后来我有机会结识了滕俊杰、郑大圣等许许多多热爱戏曲的电影人,参与到戏曲电影的拍摄中。2013年,我与滕导、史依弘女士合作拍摄了中国首部3D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之前看3D电影《阿凡达》时,我很坚信,戏曲里真刀真枪拍出来肯定会更好。果然不出所料,在整个剧组精神饱满的投入以及新技术的充分运用下,最终呈现的效果果真不错!2014年《霸王别姬》应邀在美国好莱坞杜比剧院隆重首映。剧院门口的大街上到处都是影片海报。据说,为一部外国的影片组织这样隆重的首映式,在好莱坞也是第一次。坐到杜比剧院观众席里,我被当时现场的氛围所感动和震慑,观众反响也极其强烈。五所美国高校将此片作为学校的永久珍藏。2015年初,《霸王别姬》又幸运地斩获了由国际3D与先进影像协会颁发的“金卢米埃尔”奖。前不久京剧电影《贞观盛事》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作品上映,反响也很好。这些作品的拍摄让我更加坚信:将传统戏曲艺术搬上大银幕,不但可行,也非常重要。戏曲与电影的合作与探索之路是正确的、充满希望的。通过这些经历,我愈发真切地感到,越是民族的、越是戏曲艺术的精品,就越能得到国际的认可。优秀的传统文化应当紧跟时代的、科技的步伐;作为戏曲人,我们应当潜心打造,探索、挖掘、尝试更多未知的领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银幕佳作。在“京剧经典传统大戏电影工程”的指导下,相信未来会有更多更优秀的传统剧目将通过银幕与大家见面。
胡:戏曲贵在写意,电影重在写实,在拍摄戏曲电影过程中该如何找到契合点?
尚:这确实是一个难题。戏曲和电影的表现手法有太多的不同,如何将戏曲的手眼身法步、唱念做打舞通过准确的电影手段在银幕上呈现,是我们一直在探索的。几十年来,我陆续拍摄过不少京剧电影,似乎已渐渐找到一些方向和窍门。在剧场看戏时,观众距离舞台十米之外,主要是听音,看宏观的场面,比较直观、有震撼力。但电影也有它的优势,可以有全景、中景、近景,甚至是大特写,甚至于一个眼神都展示得非常到位。剧场舞台是完整封闭的空间,细节方面不能强化、突出,而电影镜头在体现表演和调度的同时恰恰可以弥补这些缺憾,同时还能从细节处进一步深化人物的内心情感。比如电影《贞观盛事》的拍摄无疑是“经典别样重生”,很多以前连我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表演细节,借助特写镜头变得更为清晰,而在电影语言的编织下,也能看到时空迅速转换带来的快节奏叙事,在保留戏曲精粹的基础上令剧情更为紧凑、引人入胜。《贞观盛事》的第四场是体现魏征直言敢谏的重头戏,与李世民正面冲突的爆发,这是全剧矛盾的最高点。舞台剧由于距离限制,只能从宏观上展现魏征与李世民的冲突,而电影镜头的优势在这时便凸显了出来:可以在剧场看不到的微观细节中凸显人物的情感和情绪。舞台囿于空间限制,太多的布景会显得拥挤甚至喧宾夺主。但电影可以让画面、场景比舞台更辉煌、更富诗意,全面展现那个时代的色彩与特质,同时为演员在镜头前的表演提供更多助力,对四功五法的展示也提供了更大的平台和更多的可能性。

图2 尚长荣在京剧《霸王别姬》中饰演霸王
胡:戏曲演员去拍戏曲电影,您认为要注意些什么?
尚:作为戏曲演员拍电影不要怕烦。我记得京剧电影《廉吏于成龙》里有一个镜头,好像是拍了13条。剧中,于成龙要走了,他的仆人问三千死囚怎么办时,他很无奈,咬着牙走了。这个镜头是又要摇,又要拉轨道,又有闪电,各个方面配合起来比较麻烦。在拍摄过程中,不是这儿不合适,就是那儿不合适,所以最终拍了十多条。他们问我,您烦不烦?我回答,一点都不烦,只要能选出一条合格的就满足了。此外作为戏曲演员在拍电影时,在镜头面前绝对不能犯自然主义的毛病。我们拍的电影不是生活片,是戏曲片,而且是有唱、有念、有表演,是戏曲形式的电影,所以表演是不能够淡化的。

图3 尚长荣在京剧《贞观盛事》中饰演魏征
四、戏曲表演艺术家的技艺水准并不属于个人
胡:您怎样看文艺评论对于艺术创作的价值?
尚:戏曲要发展,需要的不是一言堂,而是各抒己见。梅兰芳先生就非常善于征求意见,他是伟大的智者。作为戏曲演员,我们的观念应该理直气壮去阐述,同时也要善于倾听各种不同的声音,有很多评论都值得去研究。我参演的几个戏,都出了集子,把不同的意见声音都收在里面,包括批评的声音。对于不同意见,剧组认真分析对方说的有没有道理,如果是对的,哪怕不能做到闻过则喜,起码做到闻过即改。戏曲要发展,要允许创新,允许各种尝试,同时也要允许不同的声音、各方面的评论都存在,做什么事情都要做到客观,这样才能够走上一条康庄大道。
我73岁拍电影《霸王别姬》时,有专家朋友就跟我建议:你现在是73岁,你演的楚霸王可是30岁,不要过于稳重。这一句话马上提醒了我:演员年龄大了,在呈现艺术形象的时候不能出现老态,这点是挺关键的。《廉吏于成龙》上演之后获得了很多表扬,也得奖了。同时也出现了两三篇批评的、提意见的文章,有的分量还挺重的,我们创演团队就专心致志地学习,去征求意见。我们还专门去福州、泉州、厦门等地演出,因为于成龙“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故事就发生在福建,而且福建也是具有高水准创作的“戏窝子”。开研讨会时,我们特意说明:是真心来听意见的,是专门来求教的。在那里我们广泛听取了意见之后,剧组又进行了修改完善。专门开座谈会找人提意见,恐怕有的院团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现在有一些青年演员没成名的时候还能听得进去意见,有了一点名气就难以接受批评了,这样很不好。
胡:能不能接受批评,关键还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尚:是的。现在戏曲发展很红火,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要克服浮躁、深入基层、扎根人民,不能够因噎废食、闭关而自守,开放后会有各种正面的、负面的评价,就看你如何对待。要打造一个好的文艺作品,无论是领导、编剧还是导演、二度创作班子,都要像魏征那样敢于直言,敢于说真话;都要像李世民那样开明,善于听取各方意见、集思广益。
以前我们也走过弯路,也有过各种经验教训,回顾以往,远离浮躁、潜心创作、扎根人民,这样才能够创作出让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所以作为戏曲人要自重、自强、自爱、自律,要远离功利主义、远离政绩工程的需要。我们现在的作品要对我们后代负责,既要对得起祖宗,也要对得住子孙。把这些问题看清了,就会自然而然地远离过度的大投资、大制作、大宣传、大炒作。
我总觉得,一个有成绩、有积淀的知名艺术从业者,技艺不属于个人。因为我们都是投身于文艺大道之行中的一分子,没有什么可自我吹嘘、自我膨胀的资本。北京话叫“门儿清”,现在叫“明白人”。在艺术上我们要做明白人,在人生道路上我们要做明白人,在政治上我们要做明白人。这样,做一件工作、从事一个专业,心胸就更开阔了,追求就更有动力了。
这些年,我也经常参与文艺志愿活动,到高校、社区、企业等做讲座,走进百姓的舞台为他们演唱。老百姓都非常热情,这也激励着我们这些平凡的戏曲工作者。这些年来,我更看到许多的基层剧团,在艰难的条件下依然秉持着戏曲人应有的社会责任与文化担当。生活经验和艺术经历告诉我们:民族艺术和老百姓有着天然不可分割的联系,老百姓需要民族艺术,民族艺术更需要老百姓。
胡:您在培养学生方面也花了很多精力,有什么好的教学经验可以总结?对于后辈有怎样的期望?
尚:若看到不好的节目、不理想的演出,看到不成熟的演员,我们不应该歧视、蔑视。我现在似乎有更多的同情心,希望点拨和指导他们正确学习、练功,指出正确的方向,帮助他们尽快改正缺点。至于那些恶搞的、走火入魔的,我们不能原谅。有些在戏剧方向上有不同见解的人,会片面地阐述一些背离我们当代艺术方向的观点,年轻人如果不“门儿清”,误认为这是可行的,容易走上歧途。其实学习任何一门艺术都没有捷径,就跟我们学书法一样,得从头学,传统京剧是根,你得有深厚的技艺基础,没有这个积淀,就无法长久。干我们这行,当一个合格的戏曲演员,那是必须要付出汗水、泪水的,甚至是流血、负伤,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艺无坦途、贵在攀登。干戏曲这行肯定是清苦的,但真的沉浸其中,苦中也有乐。

图4 尚长荣给青年演员授课
上海京剧院近几年在经典剧目的传承与青年演员的培养上投入了大量精力,也为年轻人提供了许多展示平台。2014年起,历时三年打磨,上海京剧院推出青年演员挑梁的“传承版”三部曲。这三年中,我与这些年轻人朝夕相处,沿着精准传承的路子,把“上树”的招儿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们。课堂上我们谈戏、聊曲、讲前辈奋斗的故事。我期待着,他们不仅仅是学戏,更能举一反三,学会人物塑造的能力、提升文化修养、形成综合的演剧观,把所有的技巧、感悟、审美、判断力都融入到日常演出甚至是日常生活中。我希望青年演员敬畏传统,对诸多流派怀揣敬畏之心,同时博采众长,在学习传统、研究流派中,打开思路,在激活传统的思路下排演新创剧目时,不仅有深厚的技艺展现,还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呈现。每个演员都应该有自己的艺术个性和艺术风格。
我收学生不多,比较挑剔,相比天赋条件,我更看重的是品学兼优,尤其是德行。我很不喜欢那种师徒之间要跪拜磕头的模式。我特别喜欢的状态是,平时相处时都很宽松,但一旦工作起来,对艺术的追求都很严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觉得在传承、教学上要多做一点工作,培养我们的京剧接班人,这是我——一个京剧事业的“老兵”义不容辞的责任。
访后跋语:
首次采访尚长荣老师是在十多年前,他声如洪钟、思维敏捷、激情澎湃。近日有幸受《中国文艺评论》杂志委托,在上海京剧院再访尚老师,让人感慨的是,时光真的没有在他身上留下痕迹,他依然精力充沛,不曾停歇前进的脚步。跟尚老师敲定采访时间并不容易,虽年近80高龄,但他难得几日闲,拍京剧电影,盯电影后期,飞美国宣传,去外地做讲座、参加论坛,整日连轴转……前一阵又做了膝盖骨手术,这算是旧疾了。其实几年前在拍摄京剧电影《霸王别姬》时,尚老师的膝盖就有小小的受伤,而项羽是个盖世英雄,有很多的武戏,当时导演滕俊杰就建议道:尚老师,您的武戏全部请您的学生杨东虎来承担替身吧。但尚老师却摇头坚持说:只要我能行,滕导你别管,我一打到底。
一旦排戏,尚老师就全情投入,寻找人物、抠表演细节、琢磨台词……《贞观盛事》里,曾有人建议把两段词改了,生怕被认为是影射现实中的一些不良风气。尚老师回复道:我这人记忆力不好,改不了,一改在台上就只能胡念。尚老师直接拒绝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实情。他向来不死背台词,在舞台上道出的,必定是经过他反复斟酌后认为的人物此时此境最合适的情绪状态。“台词忌背书、唱腔忌念经。若囫囵吞枣似的背下台词,小和尚念经似的记住唱腔,然后毫无感情地在排练场上应付一下,是绝对不可能捕捉到人物最准确、最细腻、最微妙的情感状态的。”
不过,尚老师并不欣赏睁开眼睛就是戏,演戏演得傻了、木了。尚老师家里几乎没什么跟京剧相关的摆设,出了戏他就尽情享受生活,从生活中获得艺术灵感、汲取表演力量。访谈中,他颇有兴趣地聊起近期在追电视剧《特赦1959》;过了一会儿又开始反思、自责:现在太忙了,静下来看书少了。虽然早已功成名就,但尚老师很坦诚地说:某些时期,似乎有一点骄傲情绪,但是我不背以前的成绩包袱,直到现在,我仍然不成家不立派。若是一定要艺术归类的话,他说,应是属于父亲那一派。其父尚小云是著名京剧旦角、“四大名旦”之一。父亲治艺、治学、治家的理念和作为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
尚老师自称一直是“不安分”的演员。他敬畏传统,又敢于探索创新,很愿意尝试那些新技术。在他看来,优秀的剧种需要通过现代化的表现形式让当代观众接受。这大概也是他状态能如此年轻、艺术之树常青的缘由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