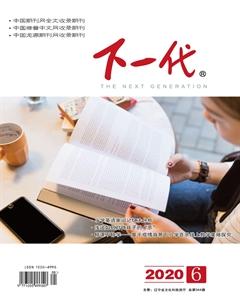试论“游戏精神的回归”
摘 要:游戏以其自主性和自由性的特征,确定其为儿童生命中的本真活动。基于辩证法的视阈,儿童的游戏一方面应是儿童的财产权利与活动属性,另一方面更是作为“人”的属性,任何均人应是游戏活动的缔造者与经营者。而令游戏拥有除其自身的精神之外的“人”的精神。而我们所处的当今时代,由于人的活动渐渐被劳动活动所替代,造成劳动世界与游戏世界的分离崩析,因而游戏精神也渐渐荡然無存。幼儿园活动组织的多样性也渐渐使游戏在幼儿园教学活动中走向对立。因此广大理论家与教育者呼吁“让游戏精神回归”,游戏的教育性价值与幼儿园教学失衡,“娱乐”却渐渐代替教育性价值使其异化,使教学逐步走向披着游戏精神外衣下的“边缘地带”。
关键词:游戏;游戏精神;教学
一、游戏的教育性意义
游戏应是儿童日常生活中不可取代的活动方式,其对助推儿童学习品质的稳步发展具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福禄贝尔曾指出:”游戏应该是儿童稳步发展的最高阶段,应该是属于这实践的人类稳步发展的最高阶段。“一个能够痛快地、有着自动的决心,坚持地游戏,直到身体疲劳为止的儿童,必然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有决心的人,能够为了增进自己和别人幸福而自我牺牲的人”这充分体现了游戏对于儿童学习品质及人格的塑造具有无法替代的意义与作用。游戏的教育性的稳步发展及认识,具有从形而上到全面、确切认识的稳步发展过程。50年代在精神分析学派理论学说的影响下,游戏在情感方面的稳步发展与影响凸显了其教育性的价值;70年代,学者开始关注游戏在儿童认知发展中的作用,其中以皮亚杰、维果斯基为代表的建构主义理论者为典型代表;80年代迄今,随着对儿童各个方面和领域研究的深入和逐渐成熟,游戏作为能够促进儿童身心的各方面综合发展的价值日益显著,如在我国安吉游戏的兴起与流行,关注点着眼在游戏与儿童心理负荷之间的联系和其是否具有促进意义。
总的来说,儿童游戏的教育性作用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游戏与儿童的身体发展
儿童在活动中自发形成运动形式即是游戏。而在游戏活动中,儿童以运动的形式进行活动,对于身体器官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如骨骼肌肉的强健、内脏器官的健康发展及神经系统的发育等等。此外,因儿童的游戏大部分是在户外生成和进行,儿童可以与自然界进行亲密接触,有利于其提高儿童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
(二)游戏与儿童的认知能力
在近几十年中有关于游戏与幼儿认知发展的互动关系的研究指出,游戏在幼儿认知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远不仅仅止于“练习”与“补偿”,而更具有“建构”与“生成”的作用。游戏一方面可以揭示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也为新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条件,尤其游戏在婴幼儿的认知发展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调节和促进作用。
(三)游戏与儿童社会性交往
婴幼儿的社会性交往活动以游戏为基本方式展开,基于游戏的社会性交往同样也是婴幼儿社会性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在婴幼儿的社会性游戏中,亲子与伙伴游戏是其主要方式,即婴幼儿时期的社会性游戏主要集中在亲子和身边的同伴中。在游戏过程中,儿童自然而然地来应对与人交谈、沟通、合作等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并且不得不去体会以及深刻理解其他人的欲望、感情以及观点和学会处理、接受和自已各不相同的观点,以此来协调自已以及其他人的互动关系。
(四)游戏与儿童的情感性发展
游戏的重要特征及是给予孩子愉快和轻松感情体验。在儿童的生活中,游戏占据着极大的部分和内容,也影响着儿童情绪情感的发展。一方面,游戏对于儿童形成成就感具有极大的促进意义,儿童在游戏中,或通过探索操作,或通过言语沟通等,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能够提高增强其自信心水平;另一方面,游戏对于培养儿童的审美能力和提升儿童的审美体验具有重要意义,儿童的游戏涉及不同的领域,如在美术游戏的活动过程中,儿童需要选择辨别物体的材料、形状、颜色等,将其组合成具有美感的新物体等;另外,游戏对于儿童的同情心和移情能力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如儿童在进行的对于现实人物、事件等模仿的游戏中,儿童需要对扮演“弱势群体”的人物给予同情和关怀。最后,情绪恢复也是游戏的重要功能,儿童将自己的消极情绪带入到游戏活动中传达,既保证了自己宣泄情绪途径的安全性,也修复了自己“受伤的心灵”。
二、游戏在教育界中的地位反思
从以上可以看出,游戏的产生虽历史久远,有关游戏的研究也渐渐深入,但游戏被视为教育界研究的重要研究对象也才始于19世纪。虽众多教育学家发表观点总结出游戏在教育中的独特作用与价值,但都只限于理论领域的研究。换而言之,将游戏纳入到教育的实践活动中,则起步较晚,且没有形成系统与完善的理论依据。而我国也同西方国家一样,近二三十年来,我国的绝大多数研究也局限在对幼儿活动的分析与论述上。正如刘焱强调:“游戏的教育学研究匮乏是‘游戏困境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期以来,人们要么把游戏与学前教育的关系看作是‘不证自明的,‘理所当然的,关于游戏的信念,更多地属于‘感性的直觉,对游戏进入教育领域以后所必然会产生的一系列特殊的‘教育学上的问题缺乏敏感性和深入的探讨”。
但近年以来,随着素质教育的兴起和对应试教育的不断批判,对儿童的权利和地位的深入研究,《儿童权利公约》也如是出文:缔约国确认儿童享有休息和闲暇,从事与儿童年龄相宜的游戏与娱乐活动,以及自由参加文化生活和艺术活动。游戏渐渐被教育理论学家大声呼吁“游戏精神应回归到儿童的生活与教育中去”,一线教育实践者纷纷立足提倡这一提议,大量以游戏为载体的园本课程在幼儿园中出台。教育工作者在没有系统与完整的游戏与教学实践结合的理论支撑下,以跨越式的方式实现了“教学的游戏化”,使教学无时无刻都在充满游戏的元素。这一状况,导致了教育理想的“丰满”与教育实践的“骨感”。
三、游戏式教学的实践形式
游戏究竟能否实现其精神的回归,将其精神与价值适时运用与体现在教学活动中,以下为笔者在**幼儿园进行观摩课时的记录:
游戏:我要和你抱一抱(音乐活动)
游戏规则:教师要求幼儿站起围成一个圈(15名幼儿),听音乐,当音乐声停止,老师喊出数字,要求幼儿按照老师所喊出的数字进行抱团,没有形成正确抱团的幼儿则不能继续参与游戏(老师不参与游戏)。
游戏过程:音乐开始,老师带领幼儿围着椅子转圈,第一轮游戏老师喊数字“2”,有七组小朋友顺利组团,剩余一名小朋友,淘汰,第一轮结束后,老师“采访”被淘汰幼儿:
老师(记者):“你没有找到人抱一抱,是因为什么?”
幼儿:“他是男生,我不想和她抱。”
老师(记者):“那你只能被淘汰了,心情怎么样?”
幼儿:“我不开心。”
老师(记者):“为什么不开心呢?”
幼儿:“我想和她抱”。(指向一个女生方向)
幼儿被老师放置在游戏活动之外,老师带领其余幼儿继续游戏并重复上述步骤。游戏进行了6轮,最终有2名幼儿获胜。而在游戏后期,渐渐有的幼儿表现出失去耐心与兴趣,在游戏中的注意力也不集中。游戏活动结束,老师长舒一口气,而幼儿脸上则表露出疲乏的神情。而对于听课者来说,教学目标与形式都是音乐活动,然而最终却没有任何有关音乐教育的形式呈现在课堂中。
虽然老师将游戏纳入到教学中来,其动机与行动都值得肯定,但仔细分析教学活动的结果,无论是从教育教学的视角还是游戏的视角,都是相对失败的。其原因可能在于没有将游戏与教学目标相结合,只注重其形式能让课堂氛围得到异于传统的改变,只关注幼儿的积极性表现却忽略其在活动中最终会获得或发展什么,而这样打着游戏式教学的旗号,实为教师的自我表演而并非真正的游戏或教学。长期以来,对“教”与“学”关系的狭隘理解,使得学校教育并不完全认同游戏的自发性。“通过游戏来学习”和“通过游戏来教”应该构成一个完整的等式。但是,长期以来,这个等式是不完整的,“通过游戏来教正是这种等式所缺失的一半”。
四、改善异化——游戏与教学的融合平衡
当前,幼儿园中无论是以游戏为特色的园本课程的开发还是教学形式的游戏化,都逃不过两种尴尬的处境:一是“为了附和游戏而游戏”,使游戏沦为教学的附庸品;二是盲目游戏,游戏难以实现其在教育中的价值和作用。而如何才能改善游戏在教学中的逐渐异化,改善“游戏不像游戏,教学不像教学”的幼儿园教学活动现象,尽可能促进游戏与教学的融合与平衡,从两个方面进行考量:
首先,定位于思想。幼儿教育理论者和从事教学活动的一线工作者需反思:幼儿园游戏是“自然活动”还是“教育活动”?只有明确自己的游戏观,才有可能对游戏与教学的融合做出解释。當前幼儿园中,游戏活动大多是以辅助的工具性手段帮助改变令人不满的教育现状,也就是说,游戏的发生是以教师为主导而非幼儿自发生成的活动。因此,这类幼儿园游戏反映不了幼儿的内在需求与满足,也就迎合不了幼儿的兴趣与热情,因此,在幼儿居于主导地位的幼儿园活动中,这类游戏以其“苟延残喘”的形式存在,缺乏持久的生命力或活力。但其“苟延残喘”的形式与状态却得不到反思或采取任何行动的改变,本质也许在于,现代学校教育将学习与游戏放置在绝对对立的二元里,使得教学与游戏无法达到真正的融合。
其次,定位在行动。游戏课程化或课程的游戏化,都是迎合当前教育界中的热点,从而要推崇出符合热点与前沿的学前教育发展脚步的观点和行动。而实质上,对于学生的游戏需要和新兴的游戏教学理念,学校只是披着学前教育文案的外衣“移花接木,偷换概念”。幼儿园从领导者到调研者到带班者,几乎不会批判地考虑当前关于游戏与教学所流行热点的合理性与适用性,其能否以合理的方式应用到幼儿园教学活动中和一日活动中去。为提高教学效率,将游戏与教学“强强联合”,理想的教学形式实现,却并没有将学生或幼儿视作教学行动中的主体加以尊重。这种“教”与“学”关系下的教学活动,学生身在游戏,精神却备受煎熬。“有两种方法可以让精神文化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文化成为一种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文化成为一种滑稽戏。”在教学活动中,也许可以等量代换,精神紧张形成的超负荷的学习活动会让教学活动所具有的精神枯萎;而只求形式追求玩乐的教学活动也会使教学活动的内在精神不复存在。
本尼特等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很少去澄清游戏中教与学的性质、不同的游戏情景的影响以及游戏与课程的关系。重要的问题在于说明教育情景中的游戏的性质与目的。那么如此便回归到对游戏的定位问题:游戏是教学活动还是自然活动?
五、结束语
虽然当前在幼儿园及教育领域中,游戏与教学的研究及表现形式不容乐观,但不可否认在倡导游戏精神回归的视角下,人们对于游戏和教学的重视以及在如何利用两者的关系帮助游戏和教学从单一的领域走向多元和试图解决“教学困境”与“游戏困境”的努力。游戏与教学的分离性也凸显着其本身所蕴含的教育价值和意义。对现状的批判也在于让自己和忙于跟风的忙碌的人们一些理性的思考:游戏与教学不应是翘板的两端,也不应是处在对立双方的位置中,而如何找到使翘板平衡的中心点,使游戏活动的方法于目的等与教学活动相匹配,仍然需要教育理论者和实践者在不断研究的过程中进行两者的相统一。最后,以刘焱老师的话作为结尾:”游戏与教学的困境,不再是简单的儿童发展特点加教育建议式的移植,而是以游戏进入教育领域后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为出发点,这正是解决“困境”的出路,但也是迄今为止缺少的“中间环”。
参考文献
[1]张焕廷主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M].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2][4][7][8][9][10]刘焱.儿童游戏通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武丹.游戏教学在幼儿教育中的应用研究[J].中国校外教育.2016
[5]李生兰.附录1:儿童权利公约[M].比较学前教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6]黄进.关于幼儿园游戏教育化的思考[J].学前教育研究.1999(4):28-31.
作者简介:
石洁(11.18);女;汉;安徽省滁州市;学生;研究生;儿童发展与教育;宁波大学;浙江省宁波市;31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