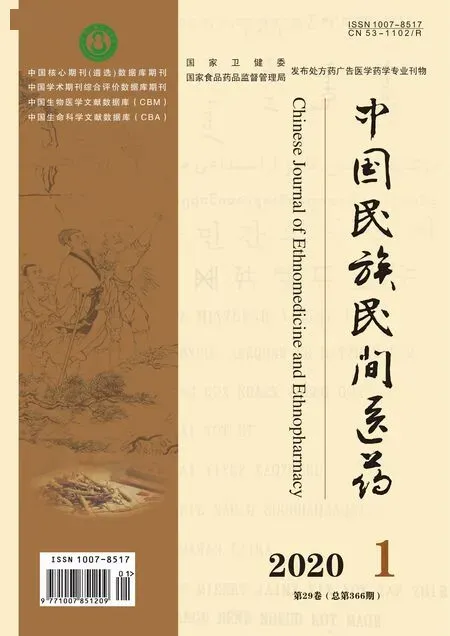原始宗教文化影响下的羌族医药研究
冯正平 范维强
四川省阿坝州食品药品检验所,四川 阿坝州 624000
羌族源于古羌,古羌人以牧羊著称于世,羌族不仅是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古代羌族主要活动在西北的广大地区,迁徙到中原地区的羌族大多华夏化。今甘肃、青海的黄河、湟水、洮河、大通河和四川岷江上游一带是古代羌族的活动中心。羌族人民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漫长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和疾病预防知识,产生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羌族医药。羌族医药以它的实用性强,疗效显著,就地取材,简便易行等特点深受广大羌民族包括当地汉、藏等民族的信赖和喜爱。
羌族医药形成历史久远,传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1],表明进入中原地区的羌支姜姓炎帝神农氏已经认识了一些药用植物用以治病。也正因为羌医药的形成较早,所以深受羌民族早期文化影响。人类最早的文化形态是原始宗教,原始宗教渗透于羌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影响着羌民族的进步和繁荣。至今,在羌族医药中仍有大量遗存,且对羌医学自然观和生命观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1 原始宗教文化对羌民族文化传承的影响
原始宗教是“宗教”的早期或原始形态,是人为宗教的“母体”、“基础”或源头[2]。原始宗教是在原始社会自然产生的,是以灵魂信仰为特征,以自然崇拜及其与之相关的巫术、禁忌仪式等为主要内容的宗教形式。原始宗教既是一个民族思想史的源头,也是一个民族文化史的源头。
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和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羌族思维方式尤其与宗教文化密切相关。宗教文化是羌族文化心理诸多特征的集中体现,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支撑性,羌族原始宗教的显著特点是以“白石”崇拜为特征的多种崇拜,认为“万物有灵”,存在多种信仰的崇拜,包括植物崇拜、动物崇拜、祖先崇拜、灵物崇拜和图腾崇拜等,尤其是与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天、地、水、太阳、树、牛、羊以至门、锅庄等自然物。在羌族自然崇拜的神灵系统中,各路神祇都有具体的具象,如太阳神、地神、山神、树神等众多神,这些神祇各司其职,却又神秘联系,这显示了羌族的朴素辩证观念,而且物质之间是有联系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正是基于这种朴素的唯物观念,羌民族有着二元对立的认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思维方式。
生活方式决定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当羌民族的思维方式经世代沿袭稳定,其行为方式也便形成传承了下来。宗教思想渗透在羌民族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生活方式所包含的所有生活内容基本与宗教有关,当然宗教活动就成为了他们最重要的生活内容。
医药是人类自觉活动的产物,传统医药学的起源,基本都与原始宗教息息相关。羌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认识到人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整体。朴素的唯物观念使羌民族有着“万物有灵”,“百药治病”的自然尊崇。羌族人的宗教信仰引领着他们生活方式的选择,成为影响生活方式的深层力量,对民族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社会活动具有超强的导向作用。基于万物有形、万物有灵、万物有情的原始意识之上,羌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使的羌人无限崇尚和珍惜与生活相关的山川大地、万物生灵,千百年来与自然和谐相处、绵延共生。岷江上游地区是现代羌民族主要聚居区,也是全国及四川药材的主产区。据历次中草药普查资料统计[1],羌族聚居区有中草药2300余种,其中常用羌药260余种。名贵中药有冬虫夏草、川贝母、羌活、大黄、当归、黄芪、党参、天麻、麝香、牛黄、熊胆等,且大多质地优良。仅茂县地区动植物、矿石类药材达790余种。这就为羌医药的产生、发展提供了优良的自然条件。
2 羌族医药文化的宗教文化背景
原始宗教占主导地位的性质和特点就是巫术。巫医同源并存,是世界各民族都有过的史实,羌族也不例外。裴盛基将传统医药划分为三类[1]:即传统民族医药知识体系、传统民族医药知识和萨满教医药知识。其中萨满教医药知识一般指巫医结合的传统医药知识,羌族传统医药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萨满教医药特征。羌族医药虽不具备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传承主要以言传口授和药方互换的方式流行,但在致病因素上却有自己的特色。羌医们普通认为“风、气、水、火、雨、石”为六大病因,其中比较独特的就是“雨”致病由于下雨天在外劳作而成,“石”致病是属于触犯了超自然力量(如鬼、神等)而受到惩罚。另外,羌医也有“情志”致病的说法,但并不像中医的七情致病,它所表示一个概念通常包括多种情绪变化,譬如怒、惊(恐)、喜、忧(悲)、思等[3]。可见,羌民族的疾病观和原始宗教文化密切相关。
羌族没有寺庙,宗教活动就是祭祀,由此产生了沟通人、神、鬼之间的联系的重要媒介——“释比”(亦称“许”、“诗卓”等,汉称“端工”),祭祀文化是“释比”文化的核心内容。“释比”文化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就是“释比”,“释比”这个特殊人物在羌族社会中扮演多种角色,他既是和大家共同劳动的普通人,又是氏族安全和兴旺的庇护者;他既是知晓宇宙的哲人,又是与神界交往的使者;他既是治疗患者的医师,又是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在医学方面,“释比”采用占卜问药、诵经驱邪、作法祛病等宗教形式对患者的心理产生一定的积极暗示、移情、安慰等效应,从而使患者调整情绪秩序,强化自我意识,消除异常心理,逐渐恢复健康。羌族“释比”既是祭师又是医师,既能沟通鬼神,又能用医施药,这个特性在羌族医药文化中尤其突出,并因“释比”在羌族社会的强大作用和重要影响而固化。古老羌民族民间早期有信仰巫师而不信医药的习性,一旦生病,先请“释比”跳神驱邪,打羊皮鼓“送鬼”,向神占卜问病,用羊毛、青稞、柏木、动物骨角等占卜工具,根据一定的手法,让其显示的信息,然后向神灵问询患者病因并采取相应治疗措施,或以鸦片和熊胆之类作为“万能药”治疗。随着历史变迁与族群的发展进步以及对疾病的认知经验不断丰富和医者能力的提高,“释比”对疾病的治疗手段不断丰富,增加了气功、心理等一些方法,如坐红锅、踩铧梨等法术的出现,让羌医药成为一个构成丰富的体系。
3 “释比”文化与羌医药的共生
羌族医药文化与“释比文化”有着共生一体的关系,“释比文化”、羌族文化和羌医药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4]。
“释比文化”与羌医药共生共长,第一,“释比”朴素的辩证施治观来源于万物有灵、事事有因的羌族宗教认知。第二,“释比”有着朴素的医治疾病的整体观,治病要找到病根,这个意识及行为使得“释比”的治疗理念为只要从各个方面探寻病因,病就可以被“驱走”。第三,“释比”有着慈善之心、诚实之心和献身精神,在治病过程中对病人一视同仁,尽心尽力,对羌族社会的伦理构建有着核心、表率作用。第四,“释比”敬神祭祀、诵经祛病等法事活动中,所念诵的经典等,其本身就包含着医学技术的内容,有着传播初级卫生知识的意义。
“释比”在千百年中承担着演绎、引领、控制、主导羌族社会精神走向和意识形态的重任。“释比”不仅承担传播传承羌族社会历史文化、规范社会礼仪等职责,还承担了消灾祛病、医治疾病的社会功能。“释比”是羌医药文化特殊的传承和实践者,在羌族社会,“释比”的存在对于民众的生存健康有着重要的意义。可以看出羌族宗教文化是羌族文化的内核,“释比文化”演绎诠释着羌族宗教文化;羌族宗教的灵魂是“释比”,“释比”是羌族文化的传承者。“释比文化”则是羌族宗教文化的核心,羌族宗教文化与“释比文化”有着紧密的共生性,当然“释比文化”也是羌族医药文化的核心内容,内涵丰富,影响深远,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认识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在羌族文化的传承中,“释比”起着重要的、独特的、不可取代的作用,羌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在完全的意义上为“释比”掌握,他们是羌民族文化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和传承者,是羌族令人尊敬的智者。
4 羌族医药的发展前景
羌族医药是羌族人民在悠久历史文化背景中,面对各种疾病的侵袭,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探索,在与疾病不断斗争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的临产实践经验。推动羌族医药事业发展是在新形势下保护和弘扬羌族文化的重要举措,将对开发和探索西部古羌历史、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产业开发、促进民族地区卫生事业发展、造福人们健康作出积极的贡献。民族医药发展过程都包含“传统”与“现代化”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如何在“民族特色”自我塑造中使羌医药传统文化摆脱原始宗教封建迷信的影响,使其走上规范化、科学化、产业化道路是羌医药传统文化优秀传承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通过正确引导羌族医药的的科研和生产,推动羌族医药的临床应用和产业开发,打造产学研一体,改变传承方式,加强交流与合作,走出去,引进来,依托本土优势资源,增强民族自信心等这些有效途径必将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促进新时代羌族医药事业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