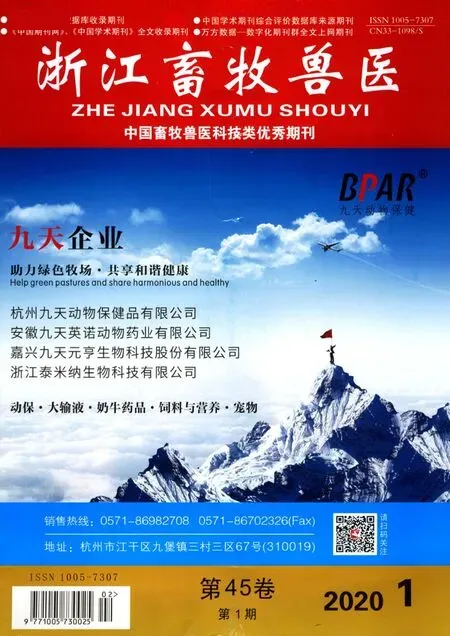畜禽养殖对环境的风险因子分析
屈 健
(浙江省兽药饲料监察所,浙江 杭州 311199)
我国养殖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过了多年的快速发展,已成为一个集约化的养殖大国。2004年我国猪、鸡饲养量分别占世界总量的49.7%和24.5%[1]。巨大的养殖量带来了巨量的排泄物,根据2010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告》,2007年集约化畜禽养殖产生粪便2.43亿t,尿液1.63亿t,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量铜2397.23 t,锌4756.94 t[2]。畜禽养殖中产生的氨气、硫化氢、粪臭素等恶臭气体以及畜禽排泄物中的氮磷元素、重金属、砷、病原微生物、抗生素抗性基因等,不仅对空气、土壤和水体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而且成为人畜共患病的重要传播途径,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的生存质量和身体健康[3]。因此,对这些风险因子进行分析,提出减少排放的方法,对提高环境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畜禽养殖对环境的影响
1.1化学污染 畜禽养殖产生的氮磷元素、重金属、砷和盐分等已成为影响土壤、水体的主要因素。其中,为了促进畜禽生长、改善畜产品的外观而在饲料中过量添加的微量元素以及有机砷制剂,经畜体排泄后,会污染表土层和地下水,不仅有碍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最终可能威胁到人类的健康。
1.1.1氮磷元素 有资料表明:万头猪场每年排放粪尿3.5-5.0万t,至少含有100 t的氮和20 t的磷;万羽蛋鸡场,年排放粪便73万t;千头奶牛场,年排放粪尿1.8-2.0万t;而每出栏1万羽肉鸡可产生30-40 t粪尿。未经处理的粪尿集中堆放,会导致氮磷的大量流失,据估计,畜禽粪尿中氮和磷的流失量分别为化肥流失量的122%和132%[4]。
由于畜禽对饲料中的蛋白质不能充分利用,致使50%-70%的氮以粪氮和尿氮的形式排出体外。粪尿中的氮,小部分以氮气的形式挥发到空气中,增加了大气中的氮含量,甚至会形成酸雨,对人、畜禽和农作物造成危害;大部分被氧化成硝酸盐,除滞留在土壤表层形成土壤污染外,其余渗入地下或随地表水流入江河,对水体造成污染,造成了生态的破坏,当饮用水源被硝酸盐污染时,会严重危害人体的健康。对陕西关中地区施用鸡粪的蔬菜地附近水井调查发现,部分水井的硝酸盐含量已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饮用水标准[5]。
畜禽对饲料中的磷也存在着利用率不高的问题,据专家分析:畜禽摄入的磷有50%以上被排出体外。施用畜禽粪肥易造成磷在土壤表面累积和流失,一部分磷与土壤中的钙、铜、铝等元素结合生成不溶性的复合物[6],造成土壤板结,影响农作物生长;另一部分经雨水冲刷后随地表径流排入江河湖海,提高水体中磷的水平,并与氮共同作用使水中的藻类和浮游生物大量繁殖,造成水体的富营养化[7],产生多种有害物质,导致水质的恶化和水中溶解氧的减少,从而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鱼虾等水生动物窒息死亡,且猪粪导致磷污染的风险高于鸡粪和鸽粪[1]。因此,畜禽排泄物中磷的污染在国际上更受关注[8]。
1.1.2重金属 铜和锌制剂可抗菌、促进采食、提高营养物质的吸收,促进生长发育[9]。近来猪饲料中铜、锌的添加量不断增大,摄入的铜、锌经猪体内代谢后有90%以上随粪便排出。张树清等[1]等对我国7个省市的规模化养殖场55个猪、鸡粪中铜、锌、铬、镉等8种重金属含量进行测定:猪、鸡粪铜含量范围分别为10.7-1591 mg/kg和18.6-775 mg/kg;锌为71.3-8710 mg/kg和83.9-699 mg/kg;铬为0-688 mg/kg和1.56-298.6 mg/kg,重金属含量猪粪明显高于鸡粪,经济发达地区明显高于落后地区。黄玉溢等[10]等对规模化养殖场的猪配合饲料和粪便中铜、锌、铬、镉等含量分析发现:饲料中铜、锌、铬和镉的平均含量分别为153.4 mg/kg、194.9 mg/kg、5.6 mg/kg和0 mg/kg,粪中铜、锌、铬和镉的平均含量分别为760.7 mg/kg、1042.6 mg/kg、18.9 mg/kg和1.3 mg/kg,饲料与粪中铜、锌和铬含量呈显著相关。若这些猪粪作为有机肥,按照德国腐熟肥重金属限量标准判定(国内没有标准),铜、锌、铬的超标率分别达100%、91.7%和33.3%。刘乐荣等[11]测定了以畜禽粪便为主的162个有机肥样品,发现铜、锌、铬的超标率分别为19.1%、16.78%和9.3%。如农田长期大量使用这些畜禽粪肥,会使铜、锌和铬在土壤表面聚集造成污染,破坏土壤的质地和微生物,影响作物产量和养分,最终通过食物链给人类的健康造成潜在的危害,故荷兰等一些国家已经禁止在日粮中添加铜和锌作为促生长剂。
1.1.3砷 有机砷制剂(阿散酸、洛克沙生等),除了促进畜禽生长和提高料肉比外,还可以提高抗球虫、抗菌能力及机体免疫力,改善畜禽产品的色素沉积及防止硒中毒等[12],在畜禽养殖中广泛使用。姚丽贤等[13]采集市售的76个猪饲料和70个鸡饲料进行测定:26.3%的猪饲料和24.3%的鸡饲料检出有机砷,阿散酸、洛克沙生的平均含量分别为21.2 mg/kg和7.0 mg/kg,且在室温下至少30 d保持形态稳定。据估计:若使用阿散酸,万头猪场每年至少要向环境排放120 kg的砷[14],使土壤和水源中砷的含量显著提高,从而影响农作物中的砷含量。土壤中的砷含量每升高1 mg/kg,甘薯块茎中的砷就会增加0.28 mg/kg[15]。王付民等[16]对广东省15个长期使用阿散酸的大型猪场周围环境和农田调查发现:猪场内施用猪粪以及距排污口50 m的土壤,其砷含量远远高于自然界最高砷含量的背景值(15 mg/kg),附近鱼塘水体的砷含量也超过0.05 mg/L的渔业水质标准;施用猪粪后的甘薯根内的砷含量超过国家规定最高限量3-6倍。甘薯和水稻具有富集砷的能力,其各种组织的总砷含量与土壤的砷含量成正比,且有机砷由畜禽排泄物进入土壤被作物吸收后,会以毒性更高的无机三价砷及甲基砷等形式累积在体内[17],当人食用了这些高残留砷的农产品时,会引起砷中毒,使体内巯基酶失活,导致细胞代谢紊乱,影响身体健康。
1.1.4盐分 畜禽排泄物中盐分对环境的影响一直被忽视,报道也较少。姚丽贤等[1]测定了集约化养殖场的61个畜禽粪样品,发现鸡粪、猪粪和鸽粪的总盐分平均含量分别为49.0 g/kg、20.6 g/kg和60.3 g/kg,其组成以钠钾离子为主。有研究指出:施用猪粪极显著提高土壤中钠的浓度[18];每公顷耕地施用46-92 t鸡粪,会使土壤轻盐化;施用92-184 t,达到中度盐化;施用184 t以上,土壤含盐量达到严重程度。张树清等[4]测定55个猪、鸡粪发现:猪粪的可溶性盐和氯化钠含量分别为1.9%和1.0%;鸡粪为2.7%和1.6%,如果这些畜禽粪大量施用到水分蒸发量大的土壤,会导致土壤次生盐渍化,存在影响作物生长的潜在风险。
1.2生物性污染 据统计:目前由动物传染给人类的人畜共患疾病约有250种,这些病主要通过畜禽排泄物和水源中的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卵如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布鲁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蛔虫卵等来传播。规模化养殖场若环境卫生不良,会导致畜禽粪尿中含有大量寄生虫和病原微生物,对土壤、作物有潜在的威胁[19]。据检测:畜牧场所排放的每mL污水中平均含33万个大肠杆菌和66万个肠球菌。张树清等[4]测定发现:猪、鸡粪中的总大肠杆菌在3.5×102/g~3.0×1010/g,其他细菌在3.0×102/g~2.8×109/g,蛔虫卵在0.2/g-14.8/g。这些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通过排泄物、水、空气等途径传播来污染饲料、畜禽,最终危害人类健康。
畜禽养殖中30%~90%的抗生素[20]和大部分铜[21]随粪便排出体外,这些抗生素和重金属进入土壤、水体后,对其内部微生物种群的抗生素抗性基因分布和传播起了主要作用,而抗生素抗性基因会导致多种抗生素治疗无效[22]。有研究表明:铜、砷等重金属和抗生素的复合污染可增加环境中抗生素抗性基因的丰度[23],并通过抗性基因的水平转移,对人类健康构成潜在危害[24]。
1.3恶臭污染 集约化饲养会造成畜禽的密度增大,栏舍内粪尿、饲料中的碳水化合物和含氮化合物在有氧和无氧的条件下,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二氧化碳、氨气、硫化氢、甲烷、吲哚、粪臭素(甲基吲哚)以及脂肪族的醛类、硫醇、胺类等有臭味的物质,其中恶臭气体浓度低时会引起畜禽应激,降低畜禽的生产性能;浓度高时不仅可引起幼畜中毒死亡,而且会加剧空气污染,导致温室效应,反刍动物排出的甲烷是引起地球变暖的最主要气体之一。氨气和硫化氢会对呼吸道产生较大刺激,影响人的呼吸中枢。
2 结语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畜禽养殖产生的重金属、砷、病原微生物、抗生素抗性基因等风险因子已成为影响环境的主要因素,极大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质量和身体健康,今后可进一步开展以下几方面的研究,减少养殖的污染排放:
一是从投入品饲料入手,研发新型的微量元素螯合物、酶制剂和微生态制剂等环保型饲料添加剂,提高畜禽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二要深入研究微生物处理、堆肥技术及植物吸收对排泄物中重金属、细菌、抗性基因的作用机制,提高对风险因子的降解、吸附效果。
三是逐步完善畜禽养殖的标准、法规。我国农业部1224号公告,已规定各种日粮中铜、锌、锰、碘、钴、硒、铬、钠和镁的最高限量标准,为减少畜禽排泄物中高盐对环境的影响,最好能补充钾离子、氯离子的最高限量标准;2017年中国兽药典委员会办公室对停止氨苯胂酸、洛克沙胂等3种兽药作为药物饲料添加剂在食品动物上使用进行公示,今后可进一步减少农业部公告第168号饲料药物添加剂清单中可用药物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