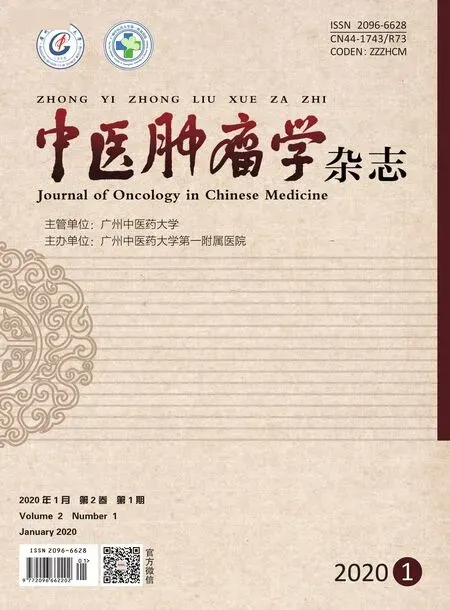杨金坤治疗肝癌经验
王强, 高峰, 曹妮达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杨金坤教授曾任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肿瘤学的学术带头人,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卫生局等多项科技进步奖。杨教授从事肿瘤临床工作近40年,尤其擅长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消化道恶性肿瘤,在治疗原发性肝癌方面独有心得,临床疗效明显。笔者有幸跟师学习,略有体会,兹将杨教授治疗肝癌的学术经验介绍如下:
1 对肝癌的认识
中医没有肝癌病名,将其归属于“肝积、肝著、积聚、癥瘕、黄疸、臌胀、肥气、癖积、痃癖”等病范畴。早在秦汉时期对肝癌就有了记载,《难经·五十五难》曰:“肝之积名曰肥气,在左胁下,如覆杯,有头足。”论述了本病的病名、病位、病性。《济生方·总论》描述“肥气之状,在左胁下,覆大如杯,肥大,而似有头足,是为肝积”等。这些说法均与原发性肝癌类似。杨教授认为:肝癌病属本虚标实,其发生与正气不足、外感邪毒、气滞血瘀、痰湿内停有关。在治疗上主张以健脾益肾,清热解毒,软坚散结为治则,辨证与辨病结合,多采用自拟健脾清肝饮加减运用,收效良好。
2 验方分析
杨教授结合我科既往治疗肝癌经验自拟健脾清肝饮,由太子参(党参)、炒白术、茯苓、柴胡、郁金、岩柏、马兰根、土茯苓、田基黄、生牡蛎、夏枯草、山萸肉、龙骨、谷芽、麦芽等药物组成,具有健脾益肾、清热解毒、软坚散结的功效。方中以四君子汤益气健脾,以山萸肉、煅龙骨填精固肾,兼顾先天后天之本,为方中君药;以柴胡、郁金疏肝解郁,岩柏、马兰根、土茯苓、田基黄清热利湿解毒,牡蛎、夏枯草散结消癌,共为方中臣药;谷芽、麦芽和胃安中调和诸药,为方中佐使。另外,方中生牡蛎、煅龙骨乃血肉有情之品,一生一煅,煅者微温而生者咸凉,一散一收,收者固本而散者祛邪,得中医药组方之要旨。合而观之,此方标本兼顾,药物组成和运用充分体现了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核心、辨病辨证相结合的精神实质。
健脾清肝饮作为原发性肝癌病人长期服用的基础方,诸药相合、性味平和,临证可结合不同证型化裁使用。如症见腹胀纳少,大便溏薄,肢体倦怠,神疲乏力,舌淡苔白,脉缓弱,证属气虚者,可将太子参改为党参,加黄芪以益气扶正;如症见咽干口燥,腰膝酸软,胁痛,五心烦热,颧红盗汗,或腹大胀满,青筋暴露,或牙宣鼻衄,舌红少苔,脉细数,属肝肾阴虚者,可加女贞子、墨旱莲、生地、蔻仁以滋水涵木;症见上腹部胀满,恶心呕吐,面目俱黄,皮肤瘙痒,大便秘结,小便赤黄,舌苔黄腻,脉弦滑,挟湿热者,可加金钱草、虎杖、茵陈;症见胁下肿块胀痛,痛有定处,疼痛呈针刺样或持久性钝痛,面色黧黑,或唇甲青紫,或皮下紫斑,或肌肤甲错,或腹部青筋暴露,或皮肤出现丝状红缕,舌质紫黯,或见瘀斑瘀点,脉多细涩,兼血瘀者,可在排除有明显出血倾向后,酌加莪术、三棱、土鳖虫、穿山甲、水蛭等;症见神疲乏力,畏寒肢冷,口淡不渴,呕吐痰涎,小便清长或尿少不利,大便稀薄,面色苍白,舌淡胖苔白滑,脉沉细无力,证属阳虚痰凝者,可加用半夏、南星、山慈菇、蛇六谷、白芥子等,伍以桂枝、细辛、附子等辛温辛热之品;如针对带瘤病例,则可酌情加用山慈菇、干蟾皮等辨病抑癌之剂。
3 经验用药
3.1 清热解毒、除痰散结药
慢性乙型肝炎病毒及慢性丙型肝炎病毒持续感染是肝癌发生、发展和复发的重要危险因素,更是肝癌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抑制病毒复制可减轻肝脏炎性活动和逆转肝纤维化,减少终末期肝病事件的发生,降低肝癌发生率、复发率和死亡率,有助于提高乙肝及丙肝相关性肝癌患者的总体生存率[1]。清热化湿解毒法可减轻肝癌实体瘤体积,显著降低AFP水平,改善临床症状[2]。以清热化湿解毒为主要作用的中药及中成药能够改善肝炎后肝硬化及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临床症状、体征、肝功能及抑制乙肝病毒的复制[3-4]。
杨教授结合我国肝癌病例大多具有病毒性肝炎基础的特点,选用岩柏、马兰根、土茯苓、田基黄为治疗肝癌常用的清热解毒药物,可减轻肝脏炎性活动,降低肝癌复发率。岩柏,味甘、辛,性平,功效清热,利湿,止血;马兰根,味辛,性凉,功效凉血、清热、利湿、解毒;土茯苓,味甘、淡,性平,归肝、胃经,功效解毒,除湿,通利关节;田基黄,味甘、苦,性凉,归肺、肝、胃经,功效清热利湿,解毒,散瘀消肿。四药常用量均为30 g。
山慈菇为杨教授常用的清热化痰药物,唐代《本草拾遗》(陈藏器,739)记载:“山慈菇,有小毒,生山中湿地,惟处州遂昌县所产者良,叶似车前,根如慈菇”。山慈菇性甘、微辛,凉。归肝、脾经,具有清热解毒、化痰散结的功效。《滇南本草》云:“消阴分之痰,止咳嗽,治喉痹,止咽喉痛。治毒疮,攻痈疽”。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山慈菇通过细胞毒作用、抑制肿瘤细胞增殖、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抑制肿瘤细胞的侵袭转移、抑制肿瘤新生血管生成、提高机体免疫力机体发挥抑癌作用[5]。山慈菇主要用于带瘤的晚期肝癌病例,辨证兼有痰湿证者尤为常用。常用量为15~30 g。经杨教授的临床观察,病人较长时间服用未见显著不良反应。由于历史、地域差异等多方面原因,山慈菇的品种混杂,诸多现代文献所记载的山慈菇涉及2科5属多种植物,可见作为常用中药的山慈菇存在着严重的名实问题[6],临床上代用、混用的现象较严重,对疗效造成影响,临床运用时需要注意辨明品种。
3.2 温阳散寒、化痰散结药
生南星、生半夏为杨教授常用化痰散结药物,多用于针对癌肿的化痰治疗,兼有阳虚者伍以附子以温阳化痰,常可收到稳定甚至缩减有形癌灶的效果。生南星味苦、辛,性温。有毒,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祛风止痉,散结消肿的功效。生半夏味辛,性温,有毒,归脾、胃、肺经,具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的功效。二者合用,化痰散结,以毒攻毒,是肿瘤治疗中的常用药物。近几十年来,不断有学者包括当代著名中医临床专家如邓铁涛、刘嘉湘、周岱翰等以大剂量生半夏治疗恶性肿瘤取得较好疗效的报道[7-9]。
然而,生南星、生半夏为有毒药物,中毒症状可表现为口舌麻木,恶心呕吐,严重者可致昏迷,窒息,呼吸停止。在临床运用中,通过长时间煎煮(大于2小时)并在餐后服药,即使大剂量运用生南星(30~ 60 g)[10-11]、生半夏(30~ 45 g)[12],亦可预防中毒。因此,杨教授在运用生南星、生半夏时从两药各9克开始逐步增加至15~30 g,并嘱患者长时间煎煮,以防不良反应。
兼有阳虚者,可合用附子9 g以温阳化痰。附子,味甘、辛,大热,归心、脾、肾经,既有温化痰结之效,更具温阳扶正之效,尤擅于振奋久病之阳。《本草汇言》曰其“回阳气,散阴寒,逐冷痰”。《医学衷中参西录》谓其“凡凝寒痛冷之结于脏腑,著于筋骨,痹于经络血脉者,皆能开之,通之”。现代药理研究证实,附子及其有效成分能通过不同途径不同程度地抑制和逆转肿瘤细胞的恶性表型,阻断肿瘤细胞增殖,对人体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亦有增强作用[13-14]。附子的常用量为9 g。另外,附子则善补火助阳、温化寒痰,山慈菇偏于化痰散结,二者一寒一热,化痰散结之功倍增,且无寒热偏颇之弊。
4 验案选析
病案1:陈某,女,60岁。于2010年1月初诊。患者既往有慢性乙肝病史多年,入院前10天出现右上腹胀满不适,当地B超:肝内多发巨大占位,AFP 205 ng/mL,上腹部及胸部CT:符合肝癌两肺转移。症见:诉右上腹胀满不适,疼痛不显,纳一般,二便如常,体重稳定,察舌质淡红,苔薄白,脉细濡。中医诊断:肝癌病,脾虚肝郁证;西医诊断:原发性肝癌两肺多发转移(肝功能分级Child A级,Ⅳ期)。患者于2010年1月17日行肝动脉栓塞术治疗一次。中医治疗法健脾益气,清热解毒,软坚散结。中药处方:太子参12 g,炒白术12 g,茯苓15 g,陈皮4.5 g,青皮4.5 g,岩柏15 g,马兰根15 g,生牡蛎(先煎)15 g,夏枯草9 g,制鳖甲15 g,天龙4.5 g。
服药至2010年3月第2次入院,患者腹胀较前缓解,无其他不适症状,胃纳可,二便调畅,舌红,苔薄白,脉弦细。肝功能分级Child A级;AFP 614 ng/mL。于2010年3月15日行第2次肝动脉栓塞术,并继续口服中药原方稍作加减。
至2010年6月第3次入院,患者出现干咳,仍有腹胀,舌红少苔,脉弦细。肝功能分级Child A级;AFP 1 000 ng/mL。上腹部及胸部提示肝内碘油沉积,周围仍有活性病灶,肺内结节明显增多。考虑目前治疗未能完全控制病情,肿瘤较大,如继续予肝动脉栓塞术可能对患者肝脏造成较大伤害,调整治疗方案,因患者拒绝索拉菲尼治疗,遂单用中药汤剂治疗,在原方基础上加用滋阴润肺、清热化痰药物:石上柏15g,石见穿15 g,石打穿15 g,山慈菇9 g,干蟾皮9 g,北沙参9 g,天门冬9 g等。患者服药至2010年10月复诊,患者无明显咳嗽,无腹胀,胃纳可,体重、生活质量较前增加,肝功能分级Child A级;AFP 4.12 ng/mL,上腹部及胸部CT:提示肝内未见明显活性病灶,肺内转移灶明显减少、缩小。患者继续服药并随访至2011年11月,病情仍稳定。
按语:该患者发病时为肝内巨大病灶,两肺多发转移,病程已至晚期,无手术机会;肝功能Child-pugh分级为A级,故而予行肝动脉栓塞术治疗以治其标;中医予健脾益气,清热解毒,软坚散结汤剂以治其本。方中以太子参、白术、茯苓、陈皮、青皮健脾理气为君,岩柏、马兰根清肝利湿解毒,生牡蛎、夏枯草、天龙、制鳖甲软坚散结为臣。治疗半年后复查提示患者肝功能保护尚可,AFP上升,肝内病灶部分控制,肺内病灶控制不佳,出现干咳,胸部CT提示肺内病灶进展。患者拒绝西医靶向药物治疗,后续治疗以中医汤剂治疗为主。遂在原方基础上加用北沙参、天门冬以滋阴润肺,石上柏、石见穿、石打穿、山慈菇、干蟾皮清热解毒、化痰散结。服药4月后复诊咳嗽症状消失,体重、生活质量较前增加,肝功能保护可,AFP恢复正常,CT提示肝内未见明显活性病灶、肺内转移灶明显减少、缩小。随访1年余病情仍稳定,疗效满意。
病案2:何某,男,50岁,既往有乙肝病史20余年,2001年11月常规体检时发现肝内占位,行全麻+硬膜外麻醉下右肝肿瘤切除+胆囊切除术,术后病理示:1.肝细胞癌,粗梁型,Ⅲ级;2.小结节型肝硬变;3.慢性胆囊炎。2002年1月10日于该院行肝动脉栓塞术1次。2009年7月起,患者AFP值开始缓慢升高,遂行上腹部CT示:肝癌术后,肝右叶前段动脉期见小片状增强影,肝左叶近第二肝门处门脉期见稍低密度影。2009年9月行上腹部MRI示:肝左内叶原发性肝癌可能大,肝硬化,脾肿大,考虑患者肝内病灶复发。2009年9月21日于中山医院行全麻+连续硬膜外麻醉下剖腹探查+术中射频。术中探查:重度肝硬化,硬化结节0.6 cm,无腹水,肿瘤位于肝左叶Ⅱ段,大小约2.5×2.5×2 cm,界清,无包膜,肝门淋巴结无肿大,门脉主干及左、右分支无癌栓。因肝硬化较重且肝脏较小,遂行局部射频及多点无水酒精注入术。术后患者AFP值波动于300~400 ng/mL,无明显下降。
2009年12月我院复查上腹部MRI提示肝癌术后,肝转移射频治疗后转移;肝硬化,脾脏肿大。初诊时症见:偶感肝区闷痛,腹胀,神疲乏力。纳可,便溏,舌淡苔白,脉弦细。中医诊断:肝癌病,脾虚肝郁证;西医诊断:原发性肝癌术后复发,射频治疗后(肝功能分级Child A级)。治疗采用静滴华蟾素、岩舒注射液抗瘤保肝。治以健脾疏肝益气、清热解毒、软坚散结法。处方:四君子汤基础上加用珠儿参12 g,岩柏30 g,马兰根30 g,生牡蛎30 g,夏枯草15 g,天龙4.5 g,八月札15 g,川朴9 g,白芍15 g,延胡索15 g,生米仁15 g,制鳖甲15 g,地肤子9 g,当归9 g,生侧柏叶15 g,佛手9 g,郁金9 g,生山楂9 g,鸡金9 g。每日1剂,水煎服,服药14剂。患者复诊症状改善,守上方继续服用。
后于2010年1月再次行肝动脉化疗栓塞术(肝左叶3×2 cm),介入术后AFP仍未下降。2010年3月查胸部CT提示两肺多发转移瘤。2010年6月17日胸部CT:两肺弥漫性转移瘤;两侧胸膜稍增厚;纵隔多发小淋巴结。2010年7月起再用中药汤剂,以前方加石上柏30 g,芙蓉叶30 g,山慈菇30 g,生南星15 g,生半夏15 g。嘱患者生南星、生半夏先煎1小时后再与诸药同煎。期间静滴华蟾素、岩舒注射液。
至2010年9月7日复查胸部CT:两肺多发转移瘤,与2010年6月17日片比较明显缩小。AFP亦明显降低,患者无显著毒性反应。此后生南星、生半夏按照每周3 g逐步加量,至生南星、生半夏用量各40 g时出现轻度舌麻、肝酶升高,予嘱患者加长煎煮时间,减量至各30 g,加熟附子9 g,白芥子12 g以温阳散结,垂盆草30 g,平地木30 g,鸡骨草30 g等利湿解毒,后不良反应消失。后随访至2013年10月,期间坚持中药汤剂口服,间中静滴中成药制剂,未行其它治疗,肝、肺内病灶基本稳定。
按语:患者初诊时为原发性肝癌术后8年,复发射频及酒精注入治疗后3月余,中医辨证为肝郁脾虚证,治疗予静滴华蟾素、岩舒抗瘤保肝,中药汤剂健脾疏肝益气,清热解毒,软坚散结为法。此后于2010年1月再行介入治疗一次,病情未得控制。2010年3月发现两肺多发转移。2010年7月起以中医治疗为主,首诊方中以四君子方合珠儿参健脾益气为君,岩柏、马兰根清肝利湿解毒,生牡蛎、夏枯草、天龙、制鳖甲软坚散结为臣。八月札、川朴、延胡索、佛手、郁金、白芍疏肝柔肝,缓急止痛为佐,余药随症加减。
该例久病阳气已衰,迁延难愈,辨为阴邪;且“肺为贮痰之器”,故辨为痰证,治以温化痰结之法。中药汤剂加用石上柏、芙蓉叶、山慈菇以清热化痰,生南星、生半夏以化痰散结、以毒攻毒。经治疗肺内病灶明显缩小。后经调整生南星、生半夏用量、合用熟附子、白芥子等温阳散结药物,病灶长期稳定达3年,效果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