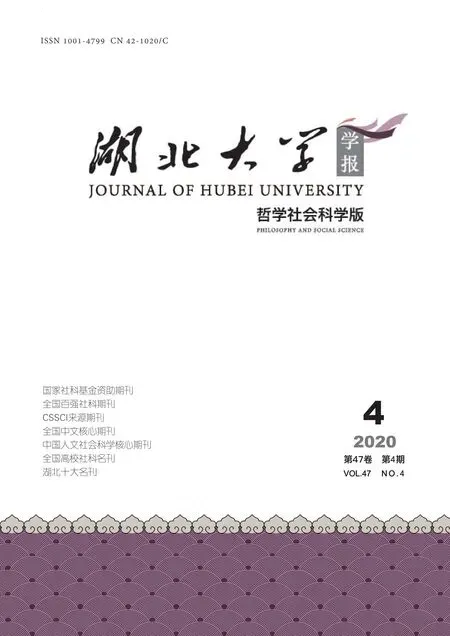大众知识论的当代发展:常识智慧与理性旨归
王姝彦,黄晓宁
(山西大学 哲学社会学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20世纪以降,西方学界逐渐萌发了知识论的大众(化)转向。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医学、法学、经济学等领域,人们开始重新审视那些自柏拉图时期就遭受批判的大众信念(popular belief)和常识观点(commonsense opinion),并且开始承认正视大众信念和常识观点本质上是对以往知识论研究传统的充实,而不是与西方知识论传统的尖锐对抗。这种转向开启了知识论研究的新入口。那些尚未在科学实践中被考量、被验证、被确立,但却依旧能够在大众文化中发挥效力的信念或观点是什么?又是什么使大众知识论在稳定我们的信仰和指导我们的实践方面发挥作用?是否有可能了解甚至掌握这些信念或观点的规律?这些构成了大众知识论(folk epistemology)研究的基本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大众知识论内涵定义争辩、理论源流的考察,以及对其理论框架内知识理论与知识直觉及二者相互作用方式的探究,来展现大众知识论当代建构的核心指向与致思理路,同时,通过对大众知识论所关涉论题机制性阐释等方面的分析,为大众知识论的进一步理性推展提供一种有益的尝试。
一、回望与探新——大众知识论的历史境遇与当代回归
知识论,简言之,就是对于知识(产品)和认知(生产产品的过程)二者本质的哲学探究(1)Benoit Hardy-Vallée,Benot Dubreuil,“Folk Epistemology as Normative Social Cognition”,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Vol.1,No.4,2010.。长久以来,知识论研究的目标有两个方面:其一,将知识的果实从纷繁复杂的信念外壳中剥离出来;其二,对知识的本质进行描述,如知识的特征(feature)、条件(condition)、来源(source)、确证(justification)和限制(limit)。而关于大众知识论,理查德·基奇纳(Richard F.Kitchener)曾指出,“或许指的就是人们对于知识本质‘未经开化’(untutored)的观点”(2)Richard F.Kitchener,“Folk Epistemology:An Introduction”,New Ideas in Psychology,Vol.20,No.2,2002.。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人类获取知识的渠道十分有限,对于知识的认识往往是感性而盲目的,大众信念和常识观点几乎占据了统治性的地位。但自柏拉图以来,知识论的长期传统将此二者批判为原始思维方式的残余,认为必须通过获得真理的方式对其加以纠正。在这一传统中,科学的发展总是被描述为一种反直觉的(counterintuitive)、去个性化的(depersonalized)理智经验(intellectual experience),被认为与普通常识并无关联(3)Noga Arikha,Gloria Origgi,“Introduction:Folk Epistemologies”,The Philosophical Forum,Vol.39,No.3,2008.。大众知识论在此传统中并没有得到认可与重视。
对于大众知识论的关注,最早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在《论题篇》中提出的endoxa这一概念,他将其定义为“被全体或多数或其中最负盛名的贤者们所公认的意见”(4)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53页。,但这一定义并没有将人们引向对大众知识论的重视。进入18世纪,以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为代表的苏格兰常识学派,强调了常识信念(commonsense belief),即普通人知识论观点的重要性。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观点受到误解和批判。20世纪以来,乔治·摩尔(George E.Moore)等人对常识信念的地位展开了辩护。不过,直到20世纪80年代,对于大众知识论的讨论才逐渐增多,而伴随着哲学和心理学的合流,西方学界对于大众知识论的专门研究才正式拉开了序幕。越来越多的科学史家发现,在广博精深的专门知识与众多旨在了解自然和社会的文化实践之间其实一直都存在着一座无形的桥梁——大众知识论,它贯通“知”与“行”,连接“深”与“浅”,沟通“雅”与“俗”。人们纵然有科学的利剑在手,但仍旧深受其影响。一方面,某些领域的知识,不论其科学证据如何,都可以依靠着我们自身对精神、身体以及周围自然和社会的日常理解所形成的解释力(explanatory power)而一直存在。例如,在生物学的讨论中,托马斯·厄恩(Thomas C.Erren)等人认为一些民族常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潜质,因为地球上任何地方的人类都一直在寻找因果联系来理解、塑造和控制他们周围的世界。民族常识是基于许多人的经验得来的,因此也可能存在一些真理。民族常识所预测的结果与整个群体的观察结果一致,并通过了大众的检验,如在高纬度地区更多人患有冬季抑郁症,睡眠是治疗许多疾病的有效方式,社交网络影响健康和导致疾病(5)Thomas C Erren,Melissa S Koch,V Benno Meyer-Rochow,“Common Sense:Folk Wisdom that Ethnobiological and Ethnomedical Research Cannot Afford to Ignore”,Journal of Ethnobiology and Ethnomedicine,Vol.9,No.1,2013.。而另一方面,在越来越多的领域,科学知识和大众信念之间有趣而复杂的关系亦渐渐呈现出来。例如,近年来,一些在民间获得了认可的食疗处方、人格类型理论、社会类型概念等在科学研究中得以证实,甚至有不少的科学研究围绕着这些大众信念展开了更加深入细致的探究。除此之外,即便一些抱定科学主义的研究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大众信念和常识观点的影响,他们在科学知识之“高”与大众信念之“低”中间,兼收二者的可取之处,不断完善其研究。因此,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大众知识论不仅没有被历史的车轮碾压分解,反而回归到学界的理论视野当中,众多学者对其争相讨论。
对于大众知识论究竟是什么或者可能是什么,西方学者先后给出了三种内涵界定。第一种界定指向字面解释,认为大众知识论指的是普通人对知识的可能性、性质和范围的描述。理查德·基奇纳就将大众知识论定义为“存在于普通人身上的,对于知识本质大众的、常识的理论”(6)Richard F.Kitchener,“Folk Epistemology:An Introduction”.;阿尔文·高盛(Alvin I.Goldman)认为大众知识论是“对于人们常识认知概念和规范的阐述”(7)Alvin I.Goldman,“Epistemic Folkways and Scientific Epistemology”,Philosophical Issues,Vol.3,No.3,1993.。这是一种相对宽泛的内涵界定,儿童知识理论(child’s theory of knowledge)和个人知识论(personal epistemology)的研究传统采纳的正是此种解释(8)Richard F.Kitchener,“The Epistemology of Folk Epistemology”,Analysis,Vol.79,No.3,2019.。第二种界定是一种限制性解释,认为大众知识论应强调知识论的一个方面,即知识归属。这来源于大众心理学(folk psychology)和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的研究传统。在马丁·戴维斯(Martin Davies)等心理学家看来,大众心理学有时可以被粗略地概括为对某一主体的行为或能动性的预测或解释,这种预测或解释是以该主体的信念和欲望的归属为基础的(9)Matin Davies,Tony Stone,“Folk Psychology and Mental Simulation”,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upplement,Vol.43,No.1,1998; Rebecca Saxe,“Against Simulation:The Argument from Error”,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Vol.9,No.4,2005.。据此推展,一些研究者认为大众知识论应该包括对某一主体的行为或能动性的知识评估(epistemic assessment),这种知识评估是以知识归属为基础的(10)Mikkel Gerken,On Folk Epistemology:How We Think and Talk about Knowledg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16.。大众知识论这两种界定上的纯理论的宽窄论辩,反映出两种不同风格的大众知识论。在广义范畴中,以普通人对于知识的可能性、性质和范围的观点为研究对象,将传统知识论所讨论的绝大多数问题,如分析与综合的区别(the analytic-synthetic distinction)、怀疑论问题(the problem of skepticism)、真理定义(definition of truth)、不同类型的知识(different types of knowledge)等等,纳入其中,可算作一种强大众知识论。在狭义范畴中,聚焦于研究个体在何种条件下能够拥有知识,专注于讨论知识的标准(criterion of knowledge)或个体处于某种知识状态(epistemic state)的证据,可算作一种弱大众知识论。除此之外,对大众知识论内涵的第三种界定,则着力于强调知识实践(epistemic practice)的观点。大众知识论包括一些默会(缄默)原则和预设(tacit principles and presuppositions),这些原则和预设是日常认知实践的基础和指导,支配着人们的前理论知识评估。但由于这些原则和预设是缄默的、非显性的,因此必须通过一种“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来对其进行表达,即通过反思日常知识实践来揭示这些原则和预设(11)Mikkel Gerken,On Folk Epistemology:How We Think and Talk about Knowledge,p.16.。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知识实践与知识论实践(epistemological practice)不可混为一谈。知识实践关注的是主体的知识行为,而知识论实践关注的是主体的知识论行为,二者并不相同。如果将理论视作表征(representation)的话,那知识论就是知识的表征。知识论居于元层次(meta-level),可视作元知识(meta-epistemic)(12)Richard F.Kitchener,“Folk Epistemology:An Introduction”.。大众知识实践是大众普遍的知识实践,我们既可以观察这种知识行为,根据标准的科学程序和规范对其进行描述、作出解释,也可以通过他人的描述和解释来了解其他文化的大众知识实践;而大众知识论实践则是大众的普遍知识论实践,例如,对于怀疑主义、外部权威的诉求、建构主义知识论、错误主义知识论、批判理性主义的表现所进行的研究,便是如此。
以上三种界定,进一步凸显出大众知识论当代回归的态势,这种回归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理论层面,这种回归标志着大众知识论可作为“解码”常识心理学、社会认知以及实验哲学的重要工具。在常识心理学中,针对大众知识论的解读,取消主义(eliminativism)与反取消主义(anti-eliminativism)围绕着信念概念(faith concept)的地位展开了激烈的哲学论争;在社会认知研究中,从知识的起源、形式以及确证等问题对大众知识论进行了多维度讨论;而在实验哲学方面,更是基于对社会科学、认知科学等领域实证方法的借鉴,对一些有关命题或理论的直觉展开探究,并用数据分析等方式,最终对这些命题或理论的合理性提出质疑或是给出验证。在实践层面,这种回归标志着大众知识论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医学、法学、经济学、文学、艺术学等多个领域所产生的解释效力得到进一步彰显和认可。例如,在心理学领域,珍妮特·奥斯汀顿(Janet W.Astington)等人围绕儿童心理理论(child’s theory of mind)和青少年知识论发展(adolescent epistemological development),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13)Richard F.Kitchener,“Folk Epistemology:An Introduction”.;在政治学领域,艾希姆·萨贾德·阿赫塔尔(Aasim Sajjad Akhtar)从巴基斯坦的国家、社会和文化入手,对常识政治进行了详述(14)Aasim Sajjad Akhtar,The Politics of Common Sense:State,Society and Culture in Pakista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pp.2-5.;在经济学领域,弗拉维奥·柯米姆(Flavio Comim)探讨了大众常识在经济思想中所具有的作用(15)Flavio Comim,“The Scottish Tradition in Economics and the Role of Common Sense in Adam Smith’s Thought”,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4,No.1,2002.。此外,大众知识论研究的多学科交叉融合倾向性也愈渐显现,比如大卫·默瑟(David Mercer)对大众知识论在医疗和法律实践中作用问题的研究(16)David Mercer,“Science,Legitimacy,and ‘Folk Epistemology’ in Medicine and Law:Parallels between Legal Reforms to the Admissibility of Expert Evidence and Evidence-Based Medicine”,Social Epistemology,Vol.22,No.4,2008.。
一言以蔽之,作为一种存在于普通人身上,对于知识本质大众的、常识的理论,大众知识论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出了传统知识论的划界。它在上述诸领域的延展与深化已使其在当代知识论的研究中日益受到关注。
二、析辨与廓清——大众知识论的理论源流梳考
从西方学界对大众知识论的解读与阐发中可以总结出,当代大众知识论研究的理论源流主要关涉三个方面的理论传统,即大众心理学、心智理论以及个人知识论。此三者各自立足于其理论阵营来解释大众对知识的看法,而当代大众知识论正是在三者有机融合与有效整合的基础上,秉承开放广博、弱化边界、兼容并蓄的性格,从而形成特定的研究内核与理路,进而得以有序推展。
其一,作为大众知识论的一种理论源流,大众心理学指的是普通民众和科学家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运用的心理学。在最基本层面,大众心理学包括运用心灵的概念来解释和预测行为(17)George Graham,“The Origins of Folk Psychology”,Inquiry,Vol.30,No.4,1987.。作为较早对大众心理学展开探究的哲学家,威尔弗里德·塞拉斯(Wilfrid Sellars)等人针对“作为理论的大众心理学”(folk psychology as a theory)这一观念进行了阐述(18)Wilfrid Sellars,Richard Rorty,Robert Brandom,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Cmbridge:Have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120-131.。但是,直到保罗·丘奇兰德(Paul M.Churchland),大众心理学与大众知识论的关系才被进一步点出。在他看来,大众心理学是“一种由一系列关于外部环境条件、内部精神状态和随后明显的行为之间关系的常识性概括或真理组成的理论”(19)Paul M.Churchland,“Eliminative Materialism and the Propositional Attitudes”,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78,No.2,1981.,“随着知识论的发展,问题和答案都是在人的常识理论框架内提出和表达的”(20)Paul M.Churchland,Scientific Realism and the Plasticity of Mi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6.。因此,按照他的观点,大众心理学就囊括了信念、 欲望、痛苦、意图(intention)等等,而由于大众的问题和答案都是在常识理论框架内讨论的,所以大众知识论也是大众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他学者也很快意识到了大众心理学可能包含大众知识论。例如,阿尔文·高盛就将我们常识的知识概念和规范(common-sense epistemic concepts and norms)称为知识习俗(epistemic folkways)(21)Alvin I.Goldman,“Epistemic Folkways and Scientific Epistemology”.。虽然有不少学者对大众心理学和大众知识论之间的联系持肯定态度,但遗憾的是,哲学家们对大众心理学和大众知识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多加重视,更没有进一步将大众知识论划入知识论的范畴,而是将其简单归入了心灵哲学的研究领域,致使不少知识论研究者与大众知识论失之交臂。但值得肯定的是,从心身关系的视角入手,可为大众知识论的研究提供一种成熟的运思方式,为探索大众知识论的必然性提供有力的支撑,并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较成熟的理论推演基础,进而在面对心灵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能够进行积极有效的回应。但与此同时,单从心灵哲学来解读大众知识论也可能存在某些局限性。究其原由,无论是选择支持身体与行为的物理主义和行为主义,还是选择支持心灵的理想主义(或观念论),抑或是兼顾两者的二元论,皆更多地关注于对理性主体内外关系和结构的讨论,而对于知识如何去定义等一系列传统知识论的焦点问题回应不够,对于理性主体知识实践的价值,特别是知识实践的社会价值进一步外扩探究的力度也不足。
其二,心智理论可以说是大众知识论又一重要理论源流。在保罗·丘奇兰德对大众知识论和大众心理学的关系进行思考的同一时期,大卫·普雷马克(David Premack)和盖伊·伍德拉夫(Guy Woodruff)也展开了有关心智理论的研究。他们认为,如果个体能够理解自身与他人的心理状态(mental state),包括目的或意向、知识、信念、思考、怀疑、猜测、假装、喜欢等等,并能够借助这一信息去预测和解释他人的行为(这与大众心理学相类似),那他就具备了心智理论(22)David Premack,Guy Woodruff,“Does the Chimpanzee Have a Theory of Mind?”,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Vol.1,No.4,1978.。其后,众多发展心理学研究者在此基础上陆续对心智理论,特别是儿童的心智理论展开了研究。基奇纳则进一步明晰了大众知识论与心智理论之间的关系。他假设儿童对前面提及的心理状态和心理概念的本质以及它们与行为的关系有所了解,而一部分心理状态实际上本就是传统知识论的研究核心,比如信念、记忆、直觉、观察、感知(perceiving)和知识。基奇纳将这些心理状态称为知识状态,如果儿童的这些心理状态可以被探究(比如儿童的梦的理论),那探究儿童的知识理论,包括儿童对知识状态是什么的理解,这些知识状态与环境条件、行为的联系,各种知识状态彼此间的联系等等,也是可行的。也就是说,儿童对一些心理状态和心理概念的本质以及它们与行为的关系所形成的认识,其实就是属于他们的知识的理论。简言之,如果孩子拥有心智理论,那他们也就拥有知识论。在儿童心智理论研究中,对于儿童的真理、证据、确定性、感知和因果关系概念的研究与儿童的大众知识论密切相关(23)Richard F.Kitchener,“Folk Epistemology:An Introduction”.。由此可见,在心智理论中存在一些既可视作心理状态,又可视作知识状态的“重叠因子”(overlap factor)。借助这些“重叠因子”,最初限于哲学领域的大众知识论走进了心理学的研究视野,并且首先在儿童阶段的研究领域产出了许多成果。事实上,“大众知识论”这一提法最早便是在一篇关于幼儿知识理论评论文章的题目中出现(24)Derek E.Montgomery,“Young Children’s Theory of Knowing:The Development of a Folk Epistemology”,Developmental Review,Vol.12,No.4,1992.。同时,这一研究向度也在某种程度上对大众知识论的可实现性予以佐证。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心智理论研究传统下的大众知识论,早期集中于对0至6岁儿童的研究,对青少年、成年早期以及成年时期的关注程度不够,对贯穿终身的认知发展讨论也极其有限。此外,关于大众心理学与心智理论的关系问题,基奇纳也提出,它们可能指的是同一理论,哲学家使用大众心理学这一术语,心理学家则使用心智理论这一术语(25)Richard F.Kitchener,“The Epistemology of Folk Epistemology”.,但也许还可以进行一种更为谨慎的解释:大众心理学和心智理论之间应该存在着一些重合的研究对象,其中就包括大众知识论。不论是从研究传统来看,还是从概念界定上看,大众心理学和心智理论二者都是对知识论的解释,或者至少是包含知识论的解释,二者都蕴含着对那些存在于普通人身上,对于知识本质大众的、常识的理论的思考。
其三,大众知识论的理论源流还涵括个人知识论的主要内容。20世纪以来,一些致力于心理学和教育学研究的西方学者对“个体如何形成知识和认知的概念,又如何利用这些概念来形成对世界的理解”这两大问题青睐有加,并对知识如何定义、如何建构、如何评价、栖身何处以及认知如何发生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追问(26)Barbara K.Hofer,Paul R.Pintrich,Personal Epistemology:The Psychology of Beliefs about Knowledge and Knowing,Mahwah:Erlbaum,2002,p.4.,提出了个人知识论,这在客观上开启了大众知识论研究的又一进路。迪安娜·库恩(Deanna Kuhn)曾指出,知识论理论发展的研究工作虽然增长迅速,但与其他关于认知发展的研究仍然脱节(27)Deanna Kuhn,“Theory of Mind,Metacognition,and Reasoning:A Life-span Perspective”,in P.Mitchell,K.J Riggs,eds.,Children’s Reasoning and the Mind,London:Psychology Press,2000,pp.301-326.。据前所述,大众知识论的研究显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个人知识论恰恰补齐了这一块短板。具体地讲,个人知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从发展的视角来探讨个人知识论的发展过程,揭示个人认识论发展的阶段和顺序,并提出相应的发展模型(28)王婷婷、吴庆麟:《个人认识论理论概述》,《心理科学进展》2008年第1期。。此外,不管是大众心理学,还是心智理论,对特定领域信念的研究都较为匮乏,这在客观上使得溯源于此二者的大众知识论研究缺乏对特定领域信念的关注。而依照个人知识论的观点,知识似乎并不是在单一结构(unitary structure)中组织起来的,更有可能是在特定领域内首先聚拢,随后再实现融合(29)Barbara K.Hofer,“Personal Epistemology Research:Implications for Learning and Teaching”,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Vol.13,No.4,2001.。这种对于特定领域的信念,即专门知识所进行的探究,事实上进一步对大众知识论的体系建构给出了有益而必要的补充。个人知识论对于发展这一结果变量以及特定领域这一个前因变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引导人们对知识论与教育、学习、指导之间的关系展开更为全面的探索,这为进一步探索大众知识论的理论架构提供了重要的思维向度。个人知识论涉及到发展心理学和发生认识论,而发展心理学和发生认识论又与心智理论有着一定的关联。究此关联的根源,在于心智理论与个人知识论都采用了发展性的研究方法,不同之处在于心智理论专注于0至6岁儿童的研究,少量涉及对青少年的研究,而个人知识论关注于描述和解释个人从青少年早期到成年的知识论建构的发展过程。职是之故,个人知识论无疑为大众知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生长点,点明了大众知识论的有效性和可实现性。另外,学界对大众知识论的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威廉·佩里(William G.Perry)对哈佛大学新生的知识论设想(epistemological assumption)进行了调查。自那以后,许多心理学家都致力于从发展心理学视角对普通人的知识论进行观察和解读,这构成了个人知识论典型的研究传统,同时也触发了学界对大众知识论的关注。个人知识论的探讨是大众知识论研究的重要路径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大众知识论只局限于或等同于个人知识论。长期以来形成的效力不减的民间常识以及争论已久的心灵哲学研究传统等等,很难通过个体的视角得以完全解释、融合或是消解。另一方面,即便是个人知识论的研究,事实上也在近些年出现了一些跨领域整合的趋向,如芭芭拉·霍弗(Barbara K.Hofer)的知识论“个人理论”(personal theories)观点就将大众心理学、心智理论、社会学的一些研究成果考虑在内,这无疑表明个人知识论、大众心理学、心智理论的研究也正呈现出进一步走向整合的趋向,并在大众知识论的理论与方法建构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以上,针对大众心理学、心智理论和个人知识论这三种理论源流展开了分析,但这并不意味着大众知识论的研究只能追溯于此,例如,在知识论的社会学化、历史主义和实用主义三条进路中,大众对知识归属和知识权力的诉求一直存在。在浅层次,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交织形成历史环境,大众对知识产生了表达、实现和争夺的欲望;在深层次,自然进化和文化创造交织形成生存环境,大众对知识形成了固定、可靠和有效的信念。因此,知识论的大众化转向,也是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传统的体现,其历史源流还存在进一步追探的空间。统而言之,认知过程作为一个由遍布大脑、身体和环境中的异质成分(heterogeneous components)组成的动态整合系统(30)王姝彦、申一涵:《认知整合与文化濡化》,《自然辩证法通讯》2020年第2期。,其研究日益呈现出多元化、融合化、共生化的特征。建基于此的大众知识论研究,对于跨学科、跨领域、多学科交叉融通整合的愿望也愈发强烈,这势必会延拓并形成一种更具活力与功用的研究进路。
三、知识理论与知识直觉——大众知识论当代建构的理论指向
具体到大众知识论在当代的理论建构而言,在明晰其理论源流的基础上,学界通过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入口,主要将其视域指向两方面的论题,即知识理论(epistemic theory)与知识直觉(epistemic intuition)。前者是指人们对知识的本质、来源以及确证的理性观点,其主旨在于阐明人们如何思考、推理和表达知识(31)Barbara K.Hofer,Paul R.Pintrich,Personal Epistemology:The Psychology of Beliefs about Knowledge and Knowing,pp.3-14.;后者则是指人们对知识感性的反应和判断,其重心在于聚焦具体的案例和事件,并从中探究大众直觉(folk intuition),诸如对“知道”(know)与“相信”(believe)加以区分等等(32)Jennifer Nagel,“Epistemic Intuitions”,Philosophy Compass,Vol.2,No.6,2007.。
就知识理论的研究来讲,主要是由认知、发展和教育心理学家所进行的,他们致力于对知识论的大众信念和理论(epistemological folk belief and theory),特别是其发展进程和个体差异加以论析。在发展进程方面,帕特丽夏·金(Patricia M.King)与凯伦·基奇纳(Karen S.Kitchener)提出知识论的发展要经历七个阶段,分为三个层次,即前反思思维层次(prereflective thinking level)(第一至第三阶段)、准反思思维层次(quasi-reflective thinking level)(第四至第五阶段)和反思思维层次(reflective thinking level)(第六至第七阶段)。知识首先被认为是确定的、明确的,并由权威人物传播;然后作为一种构建的和不确定的东西;最后解释为可测试的、可反驳的、不可靠的,但是要以证据为基础(33)Patricia M.King,Karen Strohm Kitchener,“Reflective Judgment:Theory and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Epistemic Assumptions through Adulthood”,Educational Psychologist,Vol.39,No.1,2004.。在个体差异方面,迪安娜·库恩通过访谈分析,展示了绝对主义者(absolutist)、多重主义者(multiplist)和评价主义者(evaluativist)不同的知识论风格(34)Deanna Kuhn,“Thinking as Argument”,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Vol.62,No.2,1992.。绝对主义者认为知识是绝对、确定的,迷信权威;多重主义者认为知识并不确定,但没有给出进一步的判断;而评价主义者则在多重主义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确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将证据视作知识的试金石。以上两种分类方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从发展心理学来看,知识理论经历了从稚嫩到成熟的蜕变,最终进入到知识确证的阶段;从知识论风格上看,以评价主义者为代表的知识确证派引领着知识理论的走向。这些都反映出知识理论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前理论观点,而长久以来被冠以“民间”和“非专业”帽子的大众知识论,其实与“知识即被确证”的传统知识论殊途同归。此外,大众知识论在教育或学术专业化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基本风貌,也佐证了这一点。贝齐·帕尔默(Betsy Palmer)、罗达·昂格尔(Rhoda Unger)、玛丽·贝兰基(Mary Belenky)、斯图亚特·卡拉贝尼克(Stuart A.Karabenick)等人通过对不同学科背景、不同性别、不同文化的受试者进行研究,最终得出:个体陈述的知识理论(individuals’ stated epistemic theories)与其处理矛盾证据(conflicting evidence)的方式相符合(35)Benoit Hardy-Vallée,Benot Dubreuil,“Folk Epistemology as Normative Social Cognition”.。受试者越相信知识是复杂的(complex)、试探性的(tentative)、有条理的(organized),他们就越容易在日常的争论以及学术环境中去修正他们的信念,保留判断,直到获得更多的信息(36)Marlene Schommer-Aikins,Rosetta Hutter,“Epistemological Beliefs and Thinking about Everyday Controversial Issues”,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Vol.136,No.1,2002; Ethelene Whitmir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dergraduates’ Epistemological Beliefs,Reflective Judgment,and Their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r”,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Vol.40,No.1,2004.。这也恰恰印证了,大众知识论不是静态僵化的,而是变化发展的。这与以往简单地将其划入单一直觉范畴的讨论相比,更具有说服力。
至于知识直觉,从以往的论辩来看,往往被认为与逻辑思维相对,充满跳跃性、个体性和或然性,因此难以捉摸。但事实上,知识直觉具有常规性,经由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地位等影响,会形成相对固定的形式。来自同一文化背景的人,易于形成内在的相对固定的知识直觉;而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人,其知识直觉也会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为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群体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对此,认知心理学家和实验哲学家已经给出了多项实验证据。例如,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E.Nisbett)等人对东西方人的感知、认知、决策的一系列差异进行了研究,提出了“默会知识论”(tacit epistemology,知识直觉的另一个名称)随文化而异(37)Richard E.Nisbett,Kaiping Peng,Incheol Choi,Ara Norenzayan,“Culture and Systems of Thought:Holistic versus Analytic Cognition”,Psychological Review,Vol.108,No.2,2001.。他们的研究结果指出:东方人要比西方人更容易适应矛盾、变化和观点的多元化;而西方人则更善于分类和进行本质性的判断。又如,乔纳森·温伯格(Jonathan M.Weinberg)、肖恩·尼科尔斯(Shaun Nichols)和斯蒂芬·斯蒂奇(Stephen P.Stich)还考察了文化是否会对“盖梯尔式案例”(Gettier cases)的哲学直觉产生影响(38)Jonathan M.Weinberg,Shaun Nichols,Stephen P.Stich,“Normativity and Epistemic Intuitions”,Philosophical Topics,Vol.29,No.1,2001.。可以说,就知识直觉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而言,知识直觉一方面受到文化影响,不断被驯化、被塑造;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对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在浅层次上打磨了一国的文化风貌和国家形象,在深层次上又进一步将文化沉淀、固定,最终以传统的形式延续下来。正是在此意义上,上述研究又可给我们重要提示,即在进行跨地域、跨文化交际时,除了对语言、习俗等常规要素进行考察之外,也可从知识直觉中探寻源流。此外,对于社会经济地位对知识直觉的影响,乔纳森·温伯格等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和论证。
由上不难看出,知识理论与知识直觉这两个研究范畴的发展,各自有其特定的目标来驱动。知识理论的实证研究主要着眼于教育关切(pedagogical concern):个体知识概念如何发展?个体知识概念如何受到教学和教育的影响?相比之下,由实验哲学家所进行的认知直觉实证研究,则旨在测试哲学直觉(philo-sophical intuition),进而辨明大众知识论的普遍特征。因为二者都论及大众知识论的本质和功能,所以它们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正如同道德直觉(moral intuition)与道德理论(moral theory)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一样。具体地讲,知识理论与知识直觉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知识理论的研究在一般意义上依赖于知识直觉。如果要确定人们如何看待知识,那么通常首先需要知道他们知道或相信什么,即对其知识直觉有所了解。缺少这一前提,知识理论的研究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二,知识理论与知识直觉之间存在有趣的析取(disjunction)关系(39)Benoit Hardy-Vallée,Benot Dubreuil,“Folk Epistemology as Normative Social Cognition”.。在道德认知领域,有一种现象被称为“道德失语”(moral dumbfounding),即人们倔强固执、令人不解地对某种道德判断加以维护,但又讲不出任何理由,也就是选择了道德直觉,而放弃了道德理论。同样地,在此类情形中,知识直觉并不导向知识理论,甚至可以说,跟随知识直觉,便意味着放弃知识理论。
在大众知识论的场域中,知识理论与知识直觉作为其核心论题,前者否斥了大众知识论为非理性或前理论观点的论断,后者则强调了大众知识论作为一种社会认知实践的重要意义。无论如何,对二者上述关系的确认则必然要面临进一步的问题,即二者之间的互相作用方式。
四、常识理解与机制确证——大众知识论当代阐释的理性旨归
关于如何处理知识理论与知识直觉二者的关系,马琳·肖默·艾金斯(Marlene Schommer-Aikins)提出了一种思路——将大众知识论视作一个多维度的研究对象,可能会有用处(40)Marlene Schommer-Aikins,“Synthesizing Epistemological Belief Research:Tentative Understandings and Provocative Confusions”,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Vol.6,No.4,1994.。知识的来源、稳定性以及结构则可构成这一最基本的多维架构。就知识的来源而言,可以包括科学、社会、语言、感知、理解、理性、直觉、内省、权威、专家等诸多方面(虽然有些并不可靠);就知识的稳定性而言,知识可以是永恒的、绝对的和普遍的,也可以是变化的、相对的和局部的;就知识的结构而言,知识可以被划分(原子的),也可以被整合(整体的)。基于此三个维度所建构的知识论多维空间,许多知识理论都可以在其中进行推演。
一方面,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会先通过知识直觉,将某些信息识别为知识。由于知识直觉的研究中已经多番论证了人们如何区分信念和知识,这也在同时指出了知识理论在何时或者如何介入(intervene)知识直觉。显然,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介入方式。另一方面,知识理论也可能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介入,即知识理论修正或影响知识直觉。正如迪安娜·库恩所强调的,一个人接受某件事是真实的合理标准会影响到他何时以及是否能接受新的断言(assertion),从而影响其信念修正和概念改变的可能性(41)Deanna Kuhn,“How Do People Know?”,Psychological Science,Vol.12,No.1,2001.。例如,某人相信科学是可靠的知识来源,那么仅仅听到“有一项科学研究说A”这一事实可能就足以触发他“A是知识”的直觉。相反,同样的断言可能在一个完全不信任科学的人身上引发不同的直觉。
进一步讲,理论自下而上介入直觉,揭示了知识理论产生的某种过程,即知识理论来源于知识直觉,从实践中总结、萃取、升华,最终固定于大众知识论中;理论自上而下介入直觉,不仅展现了知识理论的作用过程,同时也表明知识直觉在经过知识理论的修正及影响之后,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理性色彩,是与知识理论融合后的新直觉,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人们对于知识的瞬时理性反应,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认为这是人们经过知识理论训练之后所形成的一整套认知机制。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在科学知识不断更新的大背景下,大众知识论的当代研究不同于原始社会对于大众信念的盲目崇拜,而是秉持一种审慎、批判的态度,既不逃避更不抗拒科学知识的确证,并且伴随实证科学、文化实践不断加以自我过滤和更新。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知识,如一些植物学常识,在科学领域得到验证和认可,从而逐渐获得了“合法地位”;而另一些观点,如关于种族、性别的大众定义,在社会科学和生物科学中渐渐丧失了其原有的“合法地位”。此外,回溯某些大众知识论对象的地位,其在实质上也反映出了一套常识性的信念,而这些信念,无论其科学意义如何,反过来都可能很好地说明该对象的主流地位,甚或政治地位。例如,对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历来臧否不一、争论不休,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为数众多的民众心中,其依然占有一席之地,这种地位本身就值得对其加以反思。而在现实中,各种各样的历史、文化、社会、认知和生物偏见在稳定人们的信仰和指导人们的实践方面确实发挥着作用。为什么有些知识可信却不被相信,而有些“知识”不可信反倒被深信?对这些研究对象的地位和价值进行考察,自然也成为当代大众知识论研究的一个必要切入点,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对于大众知识论的研究,除却之前多番强调的心理学、哲学进路之外,还应当纳入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视角。由此可以说,作为一种常识理解,大众知识论之所以能够在人类社会持久存续并发挥作用,就在于其兼具了理性内核和感性外壳,融合了科学方法与常识思辨,并具有自我过滤与更新的传统,其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可谓不言而喻。
梳考西方学界对大众知识论的研究,可以说在大众信念概念系统化这一外部领域成果颇丰。这与大众心理学的研究传统相一致,正如斯蒂芬·斯蒂奇和伊恩·莱文斯克罗夫特(Ian Ravenscroft)在《何为大众心理学?》(WhatisFolkPsychology?)一文中所阐明的,大众心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部,而非内部。他们还将大众心理学的外部描述定义为:(1)“一套人们容易辨识并认同的大众心理学的‘老生常谈’(platitudes)”;(2)“一种将大众心理学的‘老生常谈’系统化、条理化的理论”(42)Stephen Stich,Ian Ravenscroft,“What is Folk Psychology?”,Cognition,Vol.50,No.1-3,1994.。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众知识论旨在分析的也是这种“老生常谈”。简而言之,一是人们如何认同知识直觉,二是知识理论如何以明晰的方式将直觉系统化。相较而言,当代认知科学则更加侧重于大众心理学的“老生常谈”输出过程的研究,如大众心理学是否由推理理论机制(inferential-theoretical mechanism)或是模拟机制(simulation mechanism)来实施,是模块的(modular)或整合的(integrated)、领域特异性的(domain-specific)或领域一般性的(domain-general),等等。近年来,学界逐渐将目光移向隐藏于大众知识论之下的一整套用来评估信念、推论、话语或其他精神产物的机制。在学习机制的研究领域,肖默在其知识论信念(epistemological belief)的“嵌入式系统模型”(embedded systemic model)中对理论观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描述,充实了信念系统与学习等之间的联系(43)Marlene Schommer-Aikins,“Explaining the Epistemological Belief System:Introducing the Embedded Systemic Model and Coordinated Research Approach”,Educational Psychologist,Vol.39,No.1,2004.。在可靠性机制研究领域,雨果·梅西埃(Hugo Mercier)从大众知识论的社会起源入手,认为推理(reasoning)对于大众知识论至关重要,进而从交流风险(dangers of communication)、一致性检查(coherence checking)、合理前提(good premises)、论证演化(evolution of argumentation)、个人与群体推理
和决策(individual and group reasoning and decision-making)几方面,对推理机制及其效果和效力进行了阐释(44)Hugo Mercier,“The Social Origins of Folk Epistemology”,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Vol.1,No.4,2010.。不言而喻,机制性的阐释与说明已经成为当代大众知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理性取向。
另一方面,伯努瓦·哈代·瓦雷(Benoit Hardy-Vallée)和伯努瓦·迪布勒伊(Benot Dubreuil)从大众知识论作为规范的社会认知的角度对其可靠性机制展开了讨论(45)Benoit Hardy-Vallée, Benot Dubreuil, “Folk Epistemology as Normative Social Cognition”.,这无疑进一步彰显了根植于社会实践的大众知识论,在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广泛而深刻的作用。正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所指出,只有当人们必须评估事物时,知识论的问题才会真正出现(46)John Dewey,The Influence of Darwin on Philosophy,and Other Essays in Contemporary Thought,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10,p.95.。由此可见,大众知识论展现出来的,其实是一种与柏拉图主义相倒的解释顺序。柏拉图主义是从概念开始,根据概念内容来解释其使用。传统知识论也是首先明确知识的概念,进而决定在何种情况下人们能够正确地使用它。大众知识论则提供了另一种方法论,即从人的直觉(判断)和理论(由推理连接的判断网络)出发,了解知识概念的使用,进而明晰知识概念的内容。显然,这是一种更加自然的观察视角,也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解释顺序。如果置于更大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考察,那么甚至可以说,人们评估行为过后所形成的知识论,其实就是社会背景下的必然选择。因此,当人们为一个论断的正当性而争辩时,其实就是在讨论其效用。如阿尔文·高盛所言,“必须认真对待那些既点亮知识前景又威胁知识前景的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47)Alvin I.Goldman,Knowledge in a Social Worl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vii.,由此可见社会维度之于大众知识论理性建构的重要性。
作为一种基于常识理解的大众知识论,是知识理论与知识直觉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所孕育出的实践智慧,是人们服从行为、推理规范的基础。因此,对于大众知识论及其阐释机制的讨论,既要从自然场域进行解码,更要从社会场域加以深探,这无疑是由大众知识论的自身性质所决定的。
总而言之,当代大众知识论在本质上就是对被科学知识推搡至研究边缘的大众信念和常识理解的一种重新正视。不可否认,历史上,大众信念和常识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科学思考,催生了科学概念,加速了科学知识的更新,而科学概念和理论又进一步甄别、解释、丰富了大众信念和常识观点,这种常识理解与科学分析的深度融合,成为民众理解周遭世界不可或缺的一种传统。概言之,大众知识论的当代发展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第一,为传统的知识论研究引入一种新的选择,将社会因素确立为知识论研究的重要因素之一,强化了知识论研究的社会基础;第二,兼顾了知识论研究中的主体性和客观性,正视了主体本身的认知视角在探讨知识本质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为科学知识的进一步更新、完善和传播强化了民间基础,同时也为科学知识应用于社会实践提供了推演模型和依据;第四,为各学科界定、运用大众知识论提供了一些可加以利用的理论砖石;第五,为讨论科技的发展与人类未来的关系、社会构成方式与人类行为方式的变化、人工智能与人类尊严、政治哲学与政治生活之关系等西方哲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48)江怡:《当代哲学研究面临的困境、挑战和主要问题》,《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理性向度与致思理路。职是之故,对于大众知识论的研究,应当是一条充满趣味与功用的道路,也是将知识论研究多元化、生动化的一种有益尝试。
附注:本文还受到山西省高等学校中青年拔尖创新人才项目“多维进化视域下的现代生命观研究”(2018052002)资助。
——访陈嘉明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