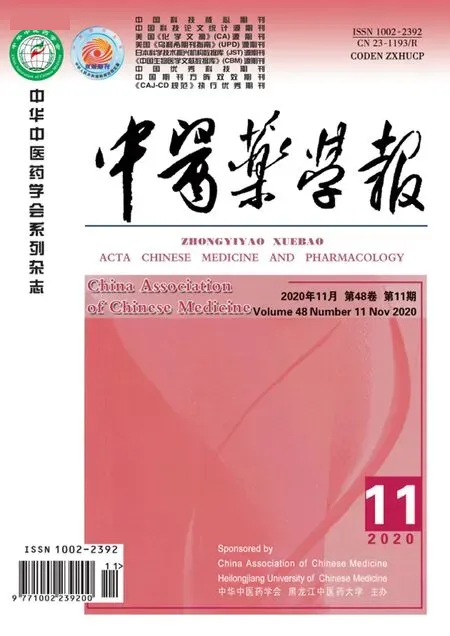析玉屏风散之君药,再释“方之精,变也”论
李冀,赵泽世,周轩,张文钊,付强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玉屏风散之方名可溯至南宋医家张松所著之《究原方》,其原著已亡佚,今人所见乃后世学者辑佚整理者[1]。南宋以降,与玉屏风散名异药同之方者有金元时期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之白术防风汤、黄芪汤,明代王肯堂《证治准绳》之白术黄芪汤等。名同药异之方者有明代龚信《古今医鉴》之玉屏风散,清代谢玉琼《麻科活人全书》之玉屏风散,清代江涵暾《笔花医镜》之玉屏风散等[2]。其名同药同但用量不同者甚多。本文通过举要删芜,意在探讨防风、黄芪、白术三药在方中之因君臣之变所致其方功效迥异,从而在彰显君药乃方中具统帅作用的同时,以示人“论方者,唯君不唯君;君效者,方之精也;方之精,变也”之理。所谓君效者,乃为方中之核心要素。君,《说文解字》谓:“尊也。”段玉裁注:“从尹口。尹,治也。口,发号。”效,《类篇》曰:“功也。”故君效实为一方功效之主旋律,是一方祛病疗疾所持之刃,更是析方之关键所在,譬喻树之主干,枝末可去,此不可移,若一方君效不立,则此方亦空洞不存。
1 防风为君论
金元时期刘完素以白术防风汤调治破伤风伴自汗出之病症。《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破伤风论第十二》载:“白术防风汤,白术一两,防风二两,黄芪一两。脏腑和而有自汗,可用此药”。此“脏腑和”乃为病情相对稳定,但仍需加以施治者。刘完素认为“破伤风者,从外至内,甚于内者则病也,因此卒暴伤损风袭之间,传播经络,致使寒热更作,身体反强,口噤不开。”即破伤风邪从伤损处侵入后,由表及里产生一系列“风”的症状。白术防风汤中防风用量倍于黄芪、白术,意在以防风为君,祛在表之风邪,以求断病之源,《古今名医方论》云:“防风遍行周身,称治风之仙药……为风药中之润剂,治风独取此味,任重功专矣。”《名医别录》载,防风可治“四肢挛急,金创内痉”之症,故防风又有解痉之用。黄芪、白术同用,既可托疮生肌,以阻风邪循肌腠伤损处入里之径,又可补益正气,以拒病内传之势,并兼固表止汗之用,二者共为臣药。本方驱邪扶正相兼为用,以防风驱邪为主,又以芪、术健固人身后天之本,使邪不干内,正如清代吴谦《名医方论》中所言:“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故治风者,不患无以祛之,而患无以御之……昧者不知托里固表之法,遍试风药以祛之,去者自去,来者自来,邪气流连,终无期矣。”
自金代张元素提出“力大者为君”以来,以药力大小为依据区分方剂之君臣佐使渐为医家所赞许,而药力大小又是由包括“药性”在内的多重因素共同决定的。“药性”是药物在方中药力大小的已知因素,是药物本身的固有属性。中药的药性,是医者据药后病患机体的反应而对中药的性质和特征做出的经验性概括。刘完素对防风解痉之用形成了一定的理性认知,并将其所悟得理念藉由玉屏风散组方之“变”,即白术防风汤得以体现。
2 黄芪为君论
历代不乏以黄芪为君统领防风、白术之组方,多为治疗气虚自汗之证,本文仅取三首释之。
《究原方》玉屏风散(录自《医方类聚》),其组成为黄芪二两,防风一两,白术二两,现行方剂学教材将其归至补益剂[3-6]。为治虚人腠理不固,易于感受触冒外邪而致自汗出之常用方。方以黄芪为君,既健补中焦脾胃之气,又兼补益肺气,肺合皮毛,故可实卫气以固表止汗。臣以白术,益气健脾。黄芪、白术二药相须为用,以求培根固本。气所虚处,邪必凑之,故方中佐用防风一料,走表以祛外邪,李时珍谓“黄芪畏防风”,其二者实为相激,激者,激发之意,正如李东垣所云:“防风……风中之润剂也,虽与黄芪相制,乃相畏而相使者也”。人命贵重如玉,三药合用,御外邪于人身之外,恰似屏障。
《世医得效方》玉屏风散组成为黄芪六两,防风二两,白术二两,用治气虚自汗较甚者。方用六两黄芪为君,补气固表,量大力雄,以示病者气虚之甚,津液耗散之严重。臣以白术健脾,助黄芪补气固表,且健运中州以生气血之源,使中气充旺,而卫外固,汗得止。防风既可入脾胃二经,以风能胜湿,则使芪、术补而不滞,又可走表散邪,以防邪寇内留,是为佐药。
《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解利伤寒论第十三》载:“黄芪汤,有汗则止也,黄芪、防风、白术各等分”。此方组成药味与玉屏风散相同,然以黄芪名之,意在示人表气当固。故黄芪为君,补气固表,以扶正御邪。尤以等量之白术为臣,所谓补君臣之胜,既能培土补益,又可固表止汗。佐用等量之防风,以祛在表之“微邪”。正如吴昆《医方考》所言:“是自汗也,与伤风自汗不同,伤风自汗,责之邪气实;杂证自汗,责之正气虚,虚实不同,攻补亦异,临证者宜详别之。”
岳美中曾言:“中医不传之妙,就是量”。药量是药物在方中药力大小的中药标识之一,对方中药物药力大小可起到直接的调控作用。在方剂药物组成相同的情况下,药物用量不同,其在方中的药力即会发生变化,进而方剂之君效亦会随之改变。《究原方》之玉屏风散,《世医得效方》之玉屏风散,《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解利伤寒论第十三》之黄芪汤,此三方因方中药物药量不同,最终全方所表现出的作用趋向亦不同。而此作用趋向实为医者据病情而设,其核心不离配伍,通过配伍将方中的药物配合应用,而使全方直入病所。
3 白术为君论
较防风、黄芪相比较而言,古今以白术为君遣药组方的医者不甚多见,但非言此药不可为君。清代名医陈士铎于《本草新编》云:“夫疟病,至难愈之病也……以用白术二两为君……此效之所以甚捷也。由此观之,则白术非君药而何……产前必多加白术以安胎,产后必多加白术以救脱,消食非多用白术何以速化,降气非多用白术何以遽定,中风非多用白术安能夺命于须臾,痞块非多用白术安能救困于败坏哉。人知白术为君药而留心于多用也,必能奏功如神矣”。可见,若以白术为君且善用之,亦可于相应病症奏桴鼓之效。
元代王好古《此事难知》载有白术汤,方由白术、防风各二两组成,既可上解三阳又能下安太阴,若病者有虚寒象,王好古又于《阴证略例》一书中加炙甘草一两至《此事难知》白术汤,亦名其为白术汤。《阴证略例》白术汤则由白术二两、防风二两、炙甘草一两组成,甘草炙则温中,用此一两甘温炙甘草意在微补脾气以助白术健运中气。若以黄芪代炙甘草,则黄芪之用量需轻之又轻,以使其药力居全方之末。
近现代亦有重用白术为君的医家,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魏龙骧、江苏孟景春两位中医师为代表,临证大量投用白术,少则一二两,重则可达四五两,专治气虚便秘,屡用不爽[7-8]。《灵枢·口问》谓:“中气不足,溲便之为变”,因脾居中州,故中气不足首责之于脾气不旺,以重剂白术强健脾气而通导肠内燥屎实为《素问·至真要大论》“塞因塞用”法之应用。
药物在方中药力大小所受诸多因素影响,上文中所提及之药性、药量、配伍,实为药力判定公式之核心因素。领悟前贤配伍组方之义所在,即可随变随用,随用随变,在灵活运用药性、调整药物用量、活用配伍等方面使方中药物之药力发生改变,在此过程中方之君效亦随之而变。临证用方忌固守旧方,在识证的基础上,医者当依病位、病性侧重不同,用药亦相应进退,可增损药物药量,亦可据药物药性峻缓择选恰当的药物,《阴证略例》之白术汤中所用炙甘草即是此例。临证贵在识证,辨明病者便秘之因由中州气虚不运所致,即可在可调控范围内调整白术用量。
4 “方之精,变也”论
同为防风、黄芪、白术三药组方,在不同辨证及立法为前提的确定下,其君药不同,其方之功用亦判若云泥。在防风、黄芪、白术配比为2∶1∶1(白术防风汤之原方用量配比)的情况下以防风为君,主治破伤风伴自汗出之病症;在黄芪、防风、白术配比为2∶1∶2,6∶2∶2,1∶1∶1(分别为《究原方》玉屏风散、《世医得效方》玉屏风散、《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黄芪汤之原方用量配比)的情况下以黄芪为君,主治因气虚而致自汗出之病症,然其所治之自汗轻重程度伯仲有别,以《世医得效方》玉屏风散所治自汗为重,其次为《究原方》玉屏风散,最后为《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黄芪汤。在以白术为君的情况下,既可与防风及少量黄芪配伍治疗三阳、太阴同病之轻症,又可根据病症需要而大剂重用以治气虚便秘。通过研习一首方剂据病症不同而立君药之不同,不仅可以丰富其组方含义,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该方临证的应用范围,此即方之“变”之价值所在。尝“玉屏风散”之一脔肉,而知“方之精,变也”之一镬之味,又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逍遥散,当视肝郁、血虚、脾弱病情缓急不同而灵活变化柴胡、芍药,当归,茯苓、白术三组药之君臣关系;再如《此事难知》九味羌活汤,张元素于原著中并未施以该方药量,其意即为后人需根据邪中经络之轻重殊异,灵活权变方中之君臣顺序。先师仲景曾于《伤寒杂病论》中载列医方314首,其方择药精当,配伍严谨,加减变化机动灵活,被后世誉为“经方”,其中大多数方剂虽可以君臣佐使规而矩之,却万不能囿此窠臼而故步自封。在领悟方剂组方原理、配伍规律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更需灵活加以“变”之,以冀所遣之药,所组之方为己所自如运用。
5 小结
玉屏风散药仅三味,却能被后世历代医家根据病症轻重之不一、左右之不同而灵活权变、增损运用,令人首肯“方无至方,方以效论”之“方之精,变也”之卓见。方中君药之变,方之功效亦异,此亦再现“药力判定公式”之“药力=药性+药量+配伍+……”中核心三因素之精奥[9]。药力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药性”“药量”“配伍”三点。此外,方剂之剂型、服法以及患者体质、心理等因素,亦可在某种程度上对方中的药物,尤其是君药之药力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公式是开放式的、非线性的。然而,在依此公式判定药力的过程中,又必须按照“药性”“药量”“配伍”这一逻辑规则和秩序进行线性的求证与思考,故运用该公式时又必须以线性思维方式为指导。简言之,该公式是通过以“线性”的思维方式对“非线性”的方剂配伍核心理论问题的理性思考而得出的[10]。自宋代成无己著《伤寒明理药方论》开方论之先河以来,不乏以君臣佐使解析组方原理者。以君臣佐使论方,强调主次,配合统制,固能使许多理论问题大而化之,却易使学者受此枷锢,此即“论方者,唯君不唯君”。在不同病症的需要下,玉屏风散之君药不同,方之君效亦不同,临证行之有效乃为医者企踵所求,此即“君效者,方之精也”。然“方无至方,方以效论”,医者切不可萧规曹随而弃方剂之活的灵魂,即配伍之所在,而泛泛纸上谈兵,不念其临证实效,需深谙方剂之最高境界乃“方之精,变也”[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