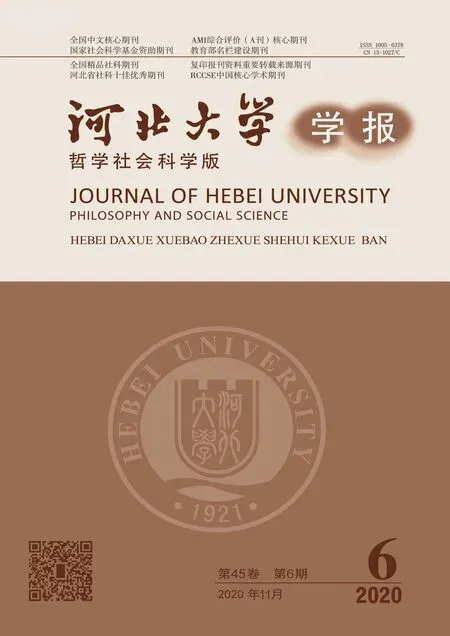“意识”怎么变成“意识形态”
——寻找消失的“观念”
廖伟凯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福建厦门 361021)
学界对人类“观念”(idea)或“意识形态”的起源研究,基本上有四种哲学思路,包括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洞穴寓言,英国经验主义者关于谬误的讨论(如培根的“四假象”、霍布斯的“语言哲学”、洛克的“经验论”),法国启蒙思想家反对偏见的观点(如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特拉西,特别是特拉西与拿破仑之间对意识形态的不同阐释),以及德国唯心主义(例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鲍威尔的“自我意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不过,直到马克思,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才在上述的哲学思潮的基础之上获得确定,它是在马克思原先抱持的德国“观念论”受到英法两国哲学观冲击后的产物。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主要论述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及《资本论》第一卷。或许是因为中文翻译的缘故,也或许是因为马克思在《形态》之前对“意识形态”一词的使用与表述相当少等因素,使得他在早期文本里对“意识”(Bewußtsein)一词的阐释,常被研究者等同为他对“意识形态”(Ideologie)的看法①这一个现象也出现在英语学界。麦克缪尔特里(J.Mc Murtry)在他的《马克思世界观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Marx's World-View)一书中即点出了consciousness与ideology常被简单等同起来的问题。参阅John Murray Mc Murtry,The Structure of Marx's World-View,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pp.123-128.。
然而,若细读马克思的文本却会发现,两个“意识”实际上是不同的。《形态》序言的第一句话“迄今为止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falsche Vorstellungen)”[1]509,[2]3已经开宗明义地指出两个“意识”之间的差别。从“虚假观念”一词的使用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所要批判的是意识形态家虚假、错误的“观念”而非“意识”(Bewußtsein)。当我们在“阶级意识”“虚假意识”的视野下来谈意识形态时,把两个“意识”联结在一起并没有多大问题;但是,正如我们熟知的,马克思也曾对意识形态做过“中性”的描述,那么若依据中文翻译而把两个“意识”等同起来,则会出现解读上的误差。因此,探究“意识”(Bewußtsein)在马克思早期文本中究竟指的是什么? 它最终如何与意识形态(Ideologie)关联起来? 二者间是否有其他中介概念? 这即是本文的主要工作。
一、马克思对“意识”的使用方法
在《形态》之前,马克思对“意识”(Bewußtsein)的阐释集中在《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及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44年手稿》)。不过,并不是每个马克思书写的“Bewußtsein”一词都具有哲学上的“意识”含义,因此仍需依据马克思前后文本叙述来理解。基本上他有三种用法。
“意识”一词最早出现在1837年11月10日马克思写给父亲的家书:“在这样的转变时刻,我们感到必须用思想的锐利目光去观察今昔,以便认清自己的实际状况。”[3]5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一版或二版都并未以“意识”来翻译,而译为“认清”(zum Bewußtsein unserer wirklichen Stellung zu gelangen)[4]9,不过这样的译法是正确的,因为“意识”一词在这里尚不具有哲学上的概念,而是一种表述生活的习惯用法。在这里可以看到马克思对“意识”的第一种使用方式:所谓的意识是“需经理解与认识”的意识。在中文版里,还可以发现其他“Bewußtsein”一词没有被译为“意识”的例子,例如:“Bewußtsein”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里被翻译为“它正在醒悟”(sie erwacht zum Bewußtsein)[5]140,[6]122以及“了解”(ein Bewußtseinüber…haben)[5]159,[6]136;在《评奥格斯堡<总汇报>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的文章》里,则被译为“弄清……论敌的反对意见”(ihre Einwendungen erst zum Bewußtsein bringt)[5]336,[6]278。相反地,中文版明确用“意识”一词来翻译“Bewußtsein”的例子有《区乡制度改革和<科隆日报>》的“意识到它的精神状态”(Geisteszustand zum Bewußtsein)[5]310,[6]255、《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获得……意识的”(zum Bewußtsein gekommenen)[7]125,[8]109。在这种情况下,意识“Bewußtsein”一词是伴随着“mit”“zu”等介词来使用的。依照句子的脉络,中文版有时翻译为带有“形容词语义”的“有意识的”“有意识地”,或如上述带有“动词语义”的“意识到”,但在原文中,马克思实际上都是以名词“Bewußtsein”来书写的。因此,本文将马克思以上这类对“意识”的书写方法归纳为:用来说明人类理解、认识事物的一个过程,透过理解、认识所获得的一个意识、感知,亦即“意识”是“需经理解与认识”的意识。
马克思还使用了不少与意识有关的“复合词(合成词)”,例如大量出现在他的博士论文及笔记中的“自我意识”(Selbstbewußtsein)、出现在《黑格尔法批判》内的“国家意识”(Staatsbewußtsein)、以及其他如“法的意识”(Rechtsbewußtsein)、“人民意识”(Volksbewußtsein)、“世界意识”(Weltbewußtsein)等,这些“意识复合词”在各自的文本中都有其哲学上的特定意涵。与“意识复合词”相近的另一种描述方法是把“意识”作为一种被定语修饰的名词,例如“理论意识”(theoretischen Bewußtseins)、“原子论意识”(atomistischen Bewußtseins)、“法意识”(rechtlichen Bewußtseins)、“市民意识”(bürgerlichen Bewußtseins)、“宗教意识”(religiösen Bewußtseins)、“公众意识”(öffentlichen Bewußtseins)、“政治意识”(politischen Bewußtseins)、“人民意识”(menschüchen Bewußtseins)等①考虑到德语变格与正字法的复杂性,因此这里的例子都以马克思的原文来做摘录。。从这两组有关“意识”的用法上可以发现,马克思强调的是位于意识(Bewußtsein)这一个名词之前的名词(复合词形式)或形容词(定语)。如果说,马克思的第一种用法是“需经理解与认识”的意识,那么这里的第二种“意识”用法,在本质上不涉及好坏、对错,而是指人们“已经理解与认识后”的一个具有特定指涉意义、被普遍接受与认同的认知。不过,马克思在这里谈的还不是意识形态。
马克思也把(名词)“意识”以不带定语的主、宾语来阐释,例如“auf das Bewußtsein anwendet”(运用于意识)[6]36,[5]34、“das Bewußtsein beruhigen”(使意识平静)[6]54,[5]58、“das Bewußtsein mußfassen”(意识必须明白)[6]54,[5]59、“Das Bewußtsein der Devotion verliert ja nicht”(可千万不要失去虔敬的意识啊)[6]102,[5]113、“wider das Bewußtsein sich vollziehend”(违反意识而实现的)等[8]60,[7]72。在这种用法里,“意识”在本质上同样不牵扯对错、好坏,且因为不带定语,所以“该意识”“仿佛”是被马克思以一个“独立的概念”来阐释。其实不然,只要透过前后文,一样是可以理解到“该意识”指的是什么。不过,这种不带定语的名词“意识”,其意义在《形态》中出现了重大转变①严格说来,自《44年手稿》起,马克思便开始对意识“本身”做阐释,但相比而言仍不如在《形态》中明确,《44年手稿》的“意识”还是时而带有黑格尔的影子。不少论文试图讨论马克思离开黑格尔的时间点,我们或许也可以说,考察马克思对“意识”一词的使用,也是一种判断马克思何时离开黑格尔的视角。本文第二部分“马克思的‘意识’观”,即是对这一判断方式的概括性初探。。在《形态》中,马克思开始严肃地把“意识”当一个“主角”来考察,开始认真地阐释这一个术语的内涵。如果说在《形态》前,“意识”只是被当成一个指涉特定意涵的哲学术语来使用,使得不解其意的马克思或以复合词、定语修饰名词的用法,或以形容词的用法,或以本文认为的一个指涉“经理解与认识”的意识等用法来出现的话,那么在《形态》中,作为(不带定语的)主语或宾语的“意识”(das Bewußtsein)就是直指意识“本身”,意识就意识,就是阐释的主角,而不再是修饰或指涉其他特定意涵。例如《形态》的经典名句:“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Nicht das Bewußtsein bestimmt das Leben,sondern das Leben bestimmt das Bewußtsein)[1]525,[2]136,在这里,“意识”完完全全被作为阐释的“主角”,这是以前的著述从来没有过的。
二、马克思的“意识”观
离开《莱茵报》后,马克思对“意识”的认知出现转变,对“意识—理论”与“生活经验—实践”的微妙区分,开始出现在他的写作中。首先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将“圣母马利亚的圣灵降孕”称为“意识事实”,并将“出生造就君主”称为“经验事实”[7]44。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将二者对立起来,而仅是说明这两种模式都是人类可以理解的事实。在《44年手稿》,无论是说明“自然界”还是“历史”运动,马克思也都做了类似的区分。例如,谈论自然界与人的关系时,他区分为“理论领域”的意识、精神无机界,以及在“实践领域”中运用自然界来达成生活的人类活动[7]272。在论述历史的运动时,他指出“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它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7]297。同样地,在《44年手稿》谈论异化时,他把宗教的异化归为是“发生在意识领域、人的内心领域中”,并认为经济的异化是一种“现实生活的异化”[7]298。简言之,在《形态》之前,“意识”被马克思归为人的内心思维领域,来区分于外部、经验世界中的现实生产活动。不可否认,在《44年手稿》内已可以看见唯物史观的萌芽,但就马克思对“意识”一词的使用而言,“意识”与“生活经验—实践”二者间还未有“谁决定谁”的表述,而是被阐释为两个独立、并行的领域。
到了《形态》,“意识”被更进一步地以“主角”的视野来阐释,马克思说明了意识如何产生、怎么发展,同时他也对“意识”与“生活经验”二者之间“谁决定谁”进行论证。马克思说道,在他考察历史的四个因素,即生活资料、需求、人口增殖、关系后,他“才发现:人还具有‘意识’”[1]533。意识的发展程度一开始是受交往与生产的发展程度所制约的,不过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原本只是动物式的、对环境感知式的、仅代表狭隘联系的意识,便因“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分工,使得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做出区分,意识这时候才能“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1]534。“纯粹的”意识即是指涉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从上而下所构建的、凭空想象的、不涉及人类真实生活的诸多观念。在《形态》里,马克思考究了“意识”的生成与发展,区分了反映自然的动物式意识、社会交往关系下的意识,以及因分工而导致的“纯粹”的意识。前二者的差别,仅在于代表物质实践的生产与需要在程度上的差别;而后二者的差异,却关乎马克思深究“社会生活”与“意识”二者间决定关系的重要视角,并开启其唯物史观的阐释。
《莱茵报》的挫败使得马克思对用“自我意识”来认识世界的思维产生疑惑,1844年的书斋生活让马克思在《44年手稿》里用自然、历史、异化来点出“意识”与“社会生活”的区别,但一直要到《形态》时,马克思才真正对二者间“谁决定谁”的关系做出判断。马克思指出,人类习惯用“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东西来区别自己与动物,但他认为,真正区别人与动物的,“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1]519,也就是生产他们的物质生活。在这一个比较中,“意识”不再如《44年手稿》一样,被认为是独立存在、可以自主作用的,而是被拿来与“社会生活”做比较,这开启了马克思考察世界方式的转变。马克思认为德国古典哲学是从“意识”出发的,在那里,“思辨的观念、抽象的观点变成了历史的动力”[9]131,并作为产生、规定和支配现实世界的动力,因而导致了“德国哲学家们在他们的黑格尔的思想世界中迷失了方向”[1]511。所以在《形态》中,马克思改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不仅透过理论来阐释,也同时透过实际批判来回答“意识”与“社会生活”“谁决定谁”的问题。
马克思在《形态》里指出,人类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以及现实生活所使用的语言才是生产人类观念与意识的原因,不过这些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因受到自己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形态的制约,所以随之而生的意识也就不同,这些不同的意识都只能是被人类意识到的存在,反映着人类不同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透过照相机倒影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生成的物理关系。即使“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1]525;相同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所持的观念、意识,也都仅是他们现实生活过程的一个反应。因此,马克思对“意识”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总结道:意识仅是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的意识,“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525。除《形态》之外,其实早在《44年手稿》里,马克思便透过“类意识”与“类存在”的概念来阐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马克思认为,“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1]188。在此观点下,个体的生活即是他的类生活、社会生活,其意识即是类意识、社会意识。根据马克思的说法,类意识是类生活的理论形式,人是透过类意识来“确证自己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且只是在思维中复现自己的现实存在”,而“类存在则在类意识中确证自己,并且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为思维着的存在物自为地存在着”[1]188。
既然意识的表现取决于人类的社会生活,那么“意识”是否就是“社会意识”? 在苏联教科书的解释里,“意识”是被用来阐释辩证唯物主义的,而“社会意识”是对应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部分,因此二者是不同的[10]126,[11]59。俞吾金教授透过论证“不存在非社会的‘自然意识’”[10]127来说明“意识”与“社会意识”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是同一个概念;学者李萍也认为马克思是在“与社会存在相对应的意义上”[12]135来使用“意识”一词,而“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生成的基础,故马克思所理解的意识就是社会意识,二者没有区别。学者们已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当然透过马克思自己的文本,无疑更能说清二者的关系。在《形态》中,他说“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1]533,简言之,意识就是社会意识①不同的看法请参阅邢贲思:《意识形态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第64-66页。。不过,这并不代表马克思在全部的思想时期都这么认为。如前面论证的,在《44年手稿》前,马克思仅是把“意识”一词作为一个具有特定指涉含义的哲学术语来使用,或以复合词、定语修饰名词的用法,或以形容词的用法,或以本文认为的是一个指涉“经理解与认识”的意识等用法来出现。因此,在《44年手稿》前,认定马克思的“意识”就等同于“社会意识”,这个说法是需商榷的,因为在那之前(严格说来是在《莱茵报》时期之前),作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社会”,遑论社会生活反映出来的“社会意识”,那时候的意识还是天国的意识,自《形态》起,这两个概念才是等同的。
三、被遗忘的“观念”
马克思曾在《形态》里将“思想、观念①观念(Idee)一词源于法文的idée或拉丁语的idea,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语的iδ ε'α(idéa,“形式”“外观”)及更早的iδεv(idéin,“看见”)。在柏拉图那里是“个别事务根底中的超越感觉的原型”;在康德那,观念变成“推动现实的形而上学原理”;黑格尔则赋予观念“与其现实对象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它成了存在于现实内部中“实现自我的绝对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继承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观点,差别在于改以“唯一者”“自我意识”“人类”等概念来表述“观念”。而马克思批判前者的出发点,则是建立在“观念”生成的现实生活(生产与交往)关系之上,观念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反映。参阅岩佐茂、小林一穗、渡边宪正编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世界》,梁海峰、王广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4-176页。、意识”放在同一个句子里来进行阐释(原文是:“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524]),其德语原文为“der Ideen,Vorstellungen,des Bewußtseins”[2]135,英文译作“…of ideas,of conceptions,of consciousness”[13]36。姑且不论中文版在不同地方对特定词汇的翻译常缺乏一致性(以Ideen为例,便有观念、概念、思想三种译法),仅就这里的德文与英文版来看,这三个词汇实际上存在一个从抽象(即Bewußtsein,consciousness)到具体(即Ideen,ideas)的程度区分。在马克思的表述上,很多时候Ideen与Vorstellungen或Begriffe或Gedanken常是并列在一起使用②Idee与Vorstellungen,Begriffe或Gedanken等词汇并用于同一个句子的例子,参阅文末参考文献[2]第62、64、135、148、170、179、184、236、372、491、504、804、808页等处。,很大程度上这组词汇的概念并没被马克思严格地区分。但是,他在使用由Ideen(观念)领衔的这组词汇时,却明显与使用Bewußtsein(意识)一词的方式有所区别。如果“Ideen与Bewußtsein有指涉程度上的差别”的这个观点能被认可的话,那么就必须对马克思的“观念”与“意识”的概念做出严格区分。只有在区分之下,才能说明由意识(Bewußtsein,consciousness)转变到意识形态(Ideologie,ideology)的逻辑。本文认为,这个转变得以成功的关键,即在于作为中介角色的“观念”。
那么,“意识”如何转变为“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眼中,首先,意识必须先具体化为观念③“观念”与“意识”是否有区别? 在1843年是似是而非的,例如在《区乡制度改革和<科隆日报>》里,马克思指出“法律只能是现实在观念上的有意识的反映”[5]314,在这段话的原文“so kann das Gesetz nur das ideelle,selbstbewußte Abbild der Wirklichkeit sein”[6]259里,“ideelle”(观念)与“selbstbewußte”(意识)都是以形容词出现,用来修饰“Abbild”(反映),二者接连写出来,表示马克思是想表达两个含义,但并列在一起来修饰同一个名词,这代表二词在性质上具有相似性。在1844年,马克思的表述暗示一个理论与实践的对比,在《44年手稿》,马克思认为异化的扬弃包含两个方面,“这要看一个民族的真正的、公认的生活主要是在意识领域还是在外部世界进行,这种生活更多地是观念的生活还是现实的生活”[1]186。在这段引文中可以看见,意识领域是与观念的生活相呼应来对比外部世界的现实生活,二者在性质上具有相似性。差别在于,意识是以理论的、个人内在的认知来表述,用来对比在实践的、展现在生活上的观念。而到了1845年的《形态》,马克思做出了区分,他透过对施蒂纳及整个德国哲学的批判指了出这一个差异。马克思写道“他们的出发点是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至于什么是宗教意识,什么是宗教观念,他们后来下的定义各有不同”。马克思也同时区分了“形而上学观念、政治观念、法律观念、道德观念以及其他观念”以及“政治意识、法律意识、道德意识”[1]514-515。。如果说意识是人类现实生活的表现,那么观念则是人类组织有意识的表现。马克思指出,在现实生活中,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所生成的观念,不管是产生于他与自然界、他与他人,或是他与自己,所有生成的观念(Vorstellungen)全“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有意识的表现”[1]524。精确地说,“意识”与“观念”无疑都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但差别在于,观念是对意识更近一步具体化(系统化、理论化)的结果,是人们可以言说出来的“意识”。例如,人类的社会生活决定人类必然有“法的意识”,而社会生活的差异,则使这一“法的意识”具体化为不同的“法的观念”。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批判,即产生在他与官方对“法的观念”的认知差异之上。此外,马克思在一段论述中批判了青年黑格尔学派以“观念出发”的谬误,也说明了观念是意识“具体化”后的成果。马克思先指出宗教、哲学、道德等都是“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紧接着表明不能从“观念(Idee)出发来解释实践”,这是因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1]544。观念是既成的意识,或如本文所认为的是“意识具体化后的成果”,它代表意识的形式和产物。因此,要消除意识的产物(也就是观念),若只是从“改变观念”下手,是徒劳无功的。再者,马克思在《莱比锡宗教会议》批判施蒂纳时,还有一段相关表述。马克思说“人们的观念(Ideen)和思想是关于自己和关于人们的各种关系的观念和思想,是人们关于自身的意识,关于一般人们的意识……关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整个社会的意识”[9]199。“人是什么”的这个问题“反映在意识中(ihren Ausdruck im Bewußtsein erhalten)就是关于人自身、关于人的生存方式或关于人的最切近的逻辑规定的观念”[9]200,[2]236。在这段中,马克思指出观念是关于人在社会中的意识,亦即是人类组织有意识的表现,是对意识更近一步具体化的结果。简言之,观念是意识转变为意识形态的一个相当重要,但常被忽视的中介因素。就意识形态生成的逻辑而言,意识必须先具体化为一个特定的观念,才有演变为意识形态的基础与理由。
在上述基础上,诸观念(意识的具体化成果)开始分道扬镳,以两种模式来演变为意识形态:一种成了代表上层建筑的中立意识形态,另一种则质变为带有负面意涵的意识形态。就前者而言,意识具体化为观念后,变成了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并以中立的姿态来出现,它的本质是由历史发展及其相对应的经济关系来决定。马克思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1]525换言之,意识形态是人类物质生活过程中的一种必然反映。实际从事活动的人所赖以生存的那一个时期的发展,及其对应的经济关系,将决定意识形态以哪一种姿态反映出来。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家所持的特定意识形态(不论对或错),也是在如施蒂纳个人的生活及当时德国的各种条件和状况下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本文认为,占据意识形态研究许多讨论篇章的“意识形式”,即是“意识具体化后”的“观念”。“观念”与“意识形式”的关系的相关阐释首先出现在《形态》中,马克思把意识的各种相适应的形式(entsprechenden Bewußtseinsformen),如道德、宗教,视为是观念的上层建筑,也就是意识形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将思想观念的上层建筑直接表述为“社会意识形式”(gesellschaftliche Bewusstseinsformen),它们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ideologischen Formen)。以意识形态具“中立性质”的观点来看,“意识形式”就是“观念”(具体化的意识),就是“意识形态”,因此将意识形态阐释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是合理的。对于意识形式在什么条件下可以等同为意识形态,西方学者也有过阐释。阿尔都塞区分了“一般意识形态”和“个别意识形态”,前者即是社会生活中不具价值、阶级、政治性的一种意识形式[14]31-43。伍德也以三个层面来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其中一层即认为马克思也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一般的社会意识形式,其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功能性[15]118-121。简单说,意识形式在具体化为观念的过程中,只要不涉及诸如阶级、政治等价值选择与判断,而更多是单纯地作为人类生活的反映时,这种视野下的意识形式(即观念)即等同于意识形态,也就是上述观念分道扬镳的两种模式之一。必须强调,上述模式是以意识形态的中立性质为前提,一旦考虑到意识形态亦有负面性质时,便不能轻易将前者等同于“意识形式”。
不过若将二概念仔细甄别,还是略有差异。邢贲思教授认为,意识形式相较于意识形态而言,多了对不具阶级性的自然界的指涉;学者杨生平从《精神现象学》的内涵来解读,意识形式是等同于“意识诸形态”[16]35;学者李萍给了一个概括性的阐述,二者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人类物质生活的反映,而差异则是因为意识形式相较于意识形态而言,拥有更大的范围与含义[12]135。从众学者的阐述可以看到一个主从关系:“意识形态”是由指涉范围更广的“意识形式”转变而来,或说“意识形态”只是“意识形式”的一种表现方式,可以是表述思想体系的中性意识形态,也可以是指涉带有阶级性、负面意涵的意识形态。那么,意识形态如何从意识形式生成出来? 杨生平教授精确指出,意识形态不是各种意识形式的叠加,而是后者“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总体性的思想体系”[16]35。至于负面义的意识形态如何产生? 张秀琴教授认为,“意识形态就是观念遗忘了自己的作为对物质形态的‘反思形式’这一从属身份,而赋予自己以某种必然性的社会现象和过程”[17]32。杨生平这里的“相互作用”即是本文前面指出的“意识先具体化为观念”的过程,而张秀琴阐述的“遗忘……‘反思形式’”则呼应本文接下来欲说明的“观念再质变为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点。
事实上,马克思在上述引文中阐释“Vorstellungen”(观念)的概念时,也在该词后面加了一个插入语:“wirkliche oder illusorische”(不管这种表现是现实的还是虚幻的)[2]989,[1]524。也就是说,意识在具体化后形成的“观念”,有可能是虚假的,它走向分道扬镳后的第二种演变模式,亦即“质变”为带有负面意涵的意识形态。这种带有负面义或虚假性的意识形态,其生成的主要原因在于:观念的“现实基础”(realen Grundlage)被抛弃了,这时候“观念就被了解为意识范围以内的观念,被了解为人的头脑中的思想了”[9]170,[2]210。导致观念仅在“意识范围”被理解是因为,观念原本是人的意识参与社会的对象性活动的成果,但是因为缺乏现实基础,观念便会“从对象性(Gegenständlichkeit)方面被撤回到主观(Subjekt)方面来了,就从实体被提升为自我意识了”,这些观念因而就成了“怪想或固定观念”(der Sparren oder die fixe Idee)[9]170,[2]210。此外,马克思也在另一段阐释意识形态的“颠倒功能”的论述中,说明了第二种类型的运作公式,他写道:“职业由于分工而独立化;每个人都认为他的手艺是真的”[1]586,真手艺与现实相互联系的这个关系的“错觉”在“意识中成为概念”(…werden…im Bewußtsein zu Begriffen)[1]586,[2]123,人们无法“超越这些关系,所以这些关系的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也成为固定概念。例如,法官运用法典,因此法官认为,立法是真正的积极的推动者”[1]586,因而导致“法的观念(Idee)。国家的观念(Idee)。在通常的意识中事情被本末倒置了”[1]587,[2]123。这里的“错觉”说明了人们脑中的观念发生“质变”。但不管“个人的现实关系的有意识的表现是虚幻的”,或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观念中把自己的现实颠倒过来”,马克思都认为,“质变”都是“他们狭隘的物质活动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社会关系造成的”[1]524。那么“观念”如何撤回到主观方面成为“固定观念”,哪些因素导致活动方式与社会关系“狭隘化”? 马克思提供了两条生成意识形态的线索:观念被“建构”与观念的“异化”。
四、意识形态的诞生
首先,意识形态①前一部分谈的是中性性质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观念”“意识形式”;这里开始的“意识形态”一词,皆是意指带有负面、虚假意涵的意识形态。可以单纯是特定阶级建构出来的产物,目的是用来维系自己的(统治的、宰制的)优势。马克思直言“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1]536-537。针对要如何“说成是普遍利益”,马克思在《形态》的另一处阐释道:“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ideell ausgedrückt)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552,[2]62能展现一个统治阶级的利益的东西,就是他们所属的、能反映他们阶级特质的观念;观念该如何表达,就须靠统治阶级有意识的思想表现,以一种具有普世性的姿态来把自己的思想表现出来。思想要能达到普遍的形式,马克思认为,就要越来越抽象化,因此他在谈到资产阶级的内部分工时,甚至直接指出存在着一群“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1]551。这群幻想的编造家,以及上述几段引文内马克思所使用的积极性词汇,如“说成是”(darzustellen)、“赋予”(durchzuführen)、“描绘成”(darzustellen)等,都说明了意识形态也可以是由特定阶级主动地建构出来的。马克思进一步阐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会把他们的思想与他们个人分开,目的是要创建“思想”才是独立地占统治地位的这一个假象。当这么做后,便可以“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思想’、观念……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概念的‘自我规定’”[1]553。建构者与其建构的思想产物相分离,正是意识形态获得独立性,得以发挥力量的关键要素。经过这一道步骤,所有有关人的关系都可以很自然地从“人的概念”“人的本质”中推导出来,“思辨哲学就是这样做的”[1]553。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与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法,正是马克思称当时的德国思想家为意识形态家的原因。在马克思看来,后者抱持“改变观念就可以改变世界”的这个长期笼罩在德国的错误虚幻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工人建立自我意识的可能,这一个错误观念反映着那群站在统治阶级立场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如何在他们“自认是正确的”认知之下,不断建构出“靠改变观念来改造政治”的这一种当时德国才有的意识形态。
其次,马克思认为“异化”也是意识形态生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异化现象的逻辑就是反客为主。虽然客体是由主体所创造的,但在特定条件下,客体反过来支配主体,造成关系上的颠倒,并由此产生异化的现象。异化的主体,对黑格尔而言是从唯心主义视野出发的“绝对观念”,在费尔巴哈那是建立在机械唯物主义上的“抽象的人”(即感性直观的“自然人”及其“类本质”异化),马克思则认为是从事实际实践活动的“具体的人”。对异化的讨论,马克思在《44年手稿》论述了四种异化形式,其中有关“人与其类本质”的讨论,即是探讨人的意识、观念领域的异化现象。意识形态的虚幻性是人类在异化劳动失去其类本质后的一种必然产物,这种虚假性不是对“物”,而是对“观念”的异化[18]81-83。观念是“具体的人”实际从事社会生活的有意识的反映,它原本是作为人的客体,但是当人与其对象化结果(也就是观念)之间的联结消失后,观念仿佛拥有了独立的性质,成了独立于人之外的他物,即规范人的意识形态。依据上述异化的生成逻辑,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直接表述中,归纳出“观念异化为(虚假)意识形态”的两个要点。
第一,观念的异化发生在人的意识具体化为观念的“过程之中”,进而质变为意识形态。马克思指出:“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1]165也就是说,观念的异化不是由人的意识来决定的,而是发生在人进行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或说是在人类类生活的对象化过程中产生的,而非黑格尔所想的是思维的、主观的、自我意识的异化。马克思从实践的视野来阐释异化的概念,这个出发点不但论证了意识形态的起源,也同时在批判唯心主义的颠倒世界观的过程中,逐步确认了唯物史观的正确性。第二,观念的异化是因为人在上述实践活动中,失去了与自己生成的观念之间的“联结关系”。马克思认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的类特性,“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1]162。人类“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让他们与动物做出区分,使人类成为“类存在物”,而人类的生活就是他们的“对象”,或说“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1]163。但是,异化劳动颠倒了二者的关系,让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1]162,异化劳动夺去了人类生产的对象,也就是他们的类生活。人类原本是具有“关于自己的类的意识”的,但是异化劳动的发生,使得人类生产的对象(也就是他们的类生活)被剥夺了;属于类生活的反映(也就是意识与观念),也同样失去了其与人之间的联结。如果说当个体与他的劳动产品、生产关系、类存在失去联系便会使他的劳动感受发生异化现象的话,那么当个体与他的类本质失去联结时,或说个体的生活本身成为其生活的手段时,这就产生了个体在意识、观念层面上的异化现象。意识与观念的异化,是被实践出来的,而劳动实践过程中的异化现象,正是虚假意识、虚假观念得以产生的原因,最后成了规范人的虚假意识形态。
虽然学界多数同意马克思在《44年手稿》透过对异化劳动与私有制的论述,并提出通过共产主义来扬弃异化等观点,说明了异化促成“虚假”意识形态的形成。但是实际上,马克思在《44年手稿》并没有使用过“意识形态”一词,也很少对“意识”进行直接表述(他此时对“意识”的表述,仍建立在黑格尔“自我意识”的特定概念上)。因此应该说,《44年手稿》仅说明“异化”是观念质变为虚假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但仍旧尚未直接表述“观念的异化”与“虚假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不过,马克思在《形态》里说明个人何以违反自己的意志、抛弃个人利益转而接受阶级利益的一段话,阐释了二者的关系。他说道:“个人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物化、异化,同时又表现为不依赖于个人的、通过交往而形成的力量,从而个人的行为转化为社会关系,转化为某些力量,决定着和管制着个人,因此这些力量在观念中就成为‘神圣的’力量”[9]273。对于这些神圣力量,马克思要施蒂纳懂得这样一个事实:“在一定的、当然不以意志为转移的生产方式内,总有某些异己的、不仅不以分散的个人而且也不以他们的总和为转移的实际力量统治着人们”[9]273-274。上述的“力量”是否就是“意识形态”,马克思在文字上没有明说,但从他紧接着的文字“把这一事实作为宗教去想象”[9]274以及“把统治着自己的力量都归结为观念的利己主义者的想象中被歪曲为无在他之上统治着他”[9]274等,都已说明了前述的“力量”即是指称“意识形态”。对马克思而言,异化后的个人行为,反映的是一个不依赖自身,而是通过交往所形成的意识形态,而“异化后的观念”,也就是意识形态,则可以表现为如宗教般虚假的,也可以是被歪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