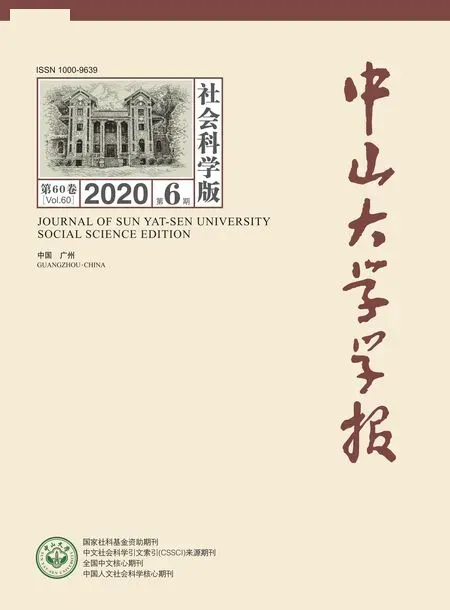个体和整体双重视角下康德的人性发展观*
刘凤娟
引 言
康德在其《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和《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①以下简称《普遍历史》《宗教》。中,使用了同一个比喻,并表达了相似的论点:从造就人的弯曲的木头中不可能制作出完全直的东西。这形象地揭示了康德对道德发展过程中人性改善的悲观态度。
在康德看来,人的本性中绝对自发的立法能力是永恒不变的,而其中的行动能力却可以在历史进程中运动变化。并且,他更突出人性在历史过程之中自我驱动和自我完善的主体能动性。这一定位是基于他对人性中向善的禀赋和趋恶的倾向,或者社会性与非社会性的内在矛盾的揭示。康德在其历史哲学、宗教哲学等多个思想领域都强调,人性中那些看似负面的元素对其正面元素具有促进和推动作用。从全部人类历史来看,人性的最终完善看起来恰恰是由其非社会性、根本恶所驱动的。这是康德对人性的最精彩描述。
然而,在这种辩证思想之外,康德还看似悖谬地表达了相反的论点。这就是他在上述两部著作中以弯曲的木头为喻所传达的立场:人性一方面似乎能够自我驱动着从恶向善,但另一方面又做不到这一点。本文的写作意图在于,揭示并解释康德对人性的这种看起来自相矛盾的评判,由此也试图呈现其历史哲学、宗教哲学等领域的思想演变和一贯性。文章第一部分将着重梳理、分析这个比喻的文本信息,澄清其中所包含的难题;第二部分尝试找出康德解决这一人性难题的思维方式、思想背景;第三部分细致阐明康德在不同文本和语境中对该难题的化解。
一、关于弯曲的木头的比喻
康德在1784年《普遍历史》第六个命题中提出了一个难题:“从造就出人的如此弯曲的木头中,不可能加工出任何完全直的东西。”①[德]康德著,李秋零译:《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0,30,29页。弯曲的木头是指具有感性偏好因而包含非社会性或趋恶倾向的人性整体,而完全直的东西喻指具有善良意志,同时对宪政有正确理解、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元首。这一难题是专门针对国家元首而言的。在康德看来,一种普遍管理法权的公民社会是大自然的最后目的,它代表着所有个体意志系统联结起来的普遍意志。为使这种联结成为可能,同时也为了使这普遍意志的普遍法律对每个成员具有同等效力,就需要有一个人来执行这普遍法律。康德指出,从外在自由角度,当人们“生活在自己的其他同类中间时,就必须有一个主人”②[德]康德著,李秋零译:《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0,30,29页。。因为其感性偏好会诱使他对自己的同伴滥用其自由,由此只能造成一种无法无天的乌合之众;即便在具有普遍法律的社会中,每个人在自己内心深处也总想着成为法律规定的例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能够代表普遍意志和普遍法律,并对每个人进行外在的强制规定的主人就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完善的公民社会是所有人在其外在行动或外在自由层面能够和谐共处的法制社会;只有作为现象的行动才是可以外在地加以强制的。而要使所有人的偏好和基于偏好的行动都被限制在这一和谐的法制社会中,那种代表普遍意志并实施普遍强制力的主人必须是一个自身公正的公共正义的元首。
但主人也是一个具有偏好的、生活在其同类中间的人,而一切具有感性偏好的人又都需要主人。因此,难题就产生了:完善的公民宪政需要一个自身公正的元首,而任何一个具有偏好的人都没有资格成为这种元首。康德认为,意志的良善乃至见多识广、经验丰富,这只能是在历史的终极目的那里才出现的事物,因而是人类最后才解决的问题。具有善良意志的人就是在道德上达到绝对完善性的理性存在者③这时期康德所说的善良意志主要是从内在道德完善来界定的,1784年的《普遍历史》提出了具备善良意志的正义元首,1785年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对善良意志作了正式的界定:这种意志不能在其他意图中作为手段,必须就其自身而言是善的;并且不是仅仅合乎义务而行动,而是必须出于义务而行动。。
然而,关于元首的这种困难却不会出现在其他人身上。康德在第五个命题中对偏好的解读甚至还具有辩证的意味:偏好能够造成最好的结果。“就像一片森林中的树木一样,正是因为每棵树都力图夺取别的树的空气和阳光,它们就互相迫使到自己的上方去寻求空气和阳光,并由此长得漂亮、挺拔;相反,那些自由地、相互隔离地、称心如意地伸展自己枝杈的树木,却长成了畸形,又歪斜,又弯曲。”④[德]康德著,李秋零译:《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0,30,29页。康德似乎认为,偏好对于成就一个自身正义的元首来说的确是一种阻碍,但对于成就一种并非绝对完善而是相对美好的社会秩序来说却是极其重要的驱动力。康德对人性中自私偏好的这种辩证解读,不仅在其历史哲学,更在其自然目的论、宗教哲学等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所以,当他在上述第六个命题提出偏好对于成就正义元首的那种困难时,这看起来是一种吊诡的、甚至自相矛盾的论断。康德很快意识到,这一难题在其单纯的历史哲学语境中是没办法解决的;在随后第七个命题中,他就转换策略,从一种合法的外部国际关系的角度来思考公民宪政的建立。
时隔十年,在1794年的《宗教》中,康德再次(几乎是原封不动地)使用了同一个比喻:“我们怎能指望用如此弯曲的木头制作出某种笔直的东西呢?”⑤[德]康德著,李秋零译:《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1页。在这里,这个比喻不再针对历史进程中政治共同体的元首,而是针对上帝治下的伦理共同体及其成员。但在这两处语境中,其观点是一致的。康德始终不相信个体能够凭借自身力量在经验中完全实现道德的绝对完善性。他指出,一个伦理共同体就是关于遵循道德法则的上帝子民概念,而能够称得上上帝子民的是那种在内在意念上达到道德完善性的人①笔者将正义元首与伦理共同体的子民相提并论,因为两者都具有感性偏好,是需要从其弯曲的人性达到同样的道德完善性的存在者。。作为上帝子民的理性存在者不同于作为政治共同体成员的理性存在者,因为上帝子民是就伦理共同体而言的,这种共同体是按照内在原则联结其成员的,因而与政治共同体具有本质不同的形式与制度。但无论是自身公正的公共正义的元首还是上帝子民,都应当是具有善良意志的道德上绝对完善的存在者;这种存在者毋宁是像耶稣一样的圣人,是具有感性偏好的人能够达到的极致。
在康德看来,人类社会不仅存在外在自由方面的自然状态,也存在内在自由方面的自然状态。前者是就人们在外在行动方面的无法律状态而言,后者指人们在意念中彼此散乱、甚至相互对抗的内在无道德状态。人不仅被其本性中的感性偏好驱动着走出律法的自然状态,也有义务自觉地走出伦理的自然状态,并建立一种伦理共同体。后者不是个体对个体的义务,而是人的族类对自己的义务。既然从具有偏好的人性中无法制作出来具有善良意志的完全公正的元首,那就同样不可能造就内在道德良善的上帝子民。但康德在这一比喻中要表达的意思是其表面含义吗?假如具有偏好的人无法达到其道德的绝对完善性,那么政治共同体和伦理共同体是否也就沦为一种空想了呢?
康德在《宗教》的另一处也使用了一个与此十分相似的比喻:“一颗坏树怎么可能结出好果子呢?”②[德]康德著,李秋零译:《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页。同时他也指出了理解这一难题的出路:一棵原初好的树曾经结出坏的果子,这并不比“一颗坏树结出好果子”更容易理解;也许这两个问题可以“相提并论”。康德在这里明显是以《圣经》故事为背景的。亚当一经上帝的创造就具有理性和感性双重立场;他既分有上帝的理智,又具有感性偏好。亚当的原初禀赋是善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是一个善良的人,而是说他具有向善的能力。只有当他自发地将善的原则和动机纳入其准则,并按照这种准则展开行动,他才能算是善的。与此同时,只有当他自发地将恶的原则和动机纳入其准则并展开行动之后,他才是一个现实的恶人。换一种说法,善恶都是他自己招致的。
康德在1786年《人类历史揣测的开端》中指出:“自然的历史从善开始,因为它是上帝的作品;自由的历史从恶开始,因为它是人的作品。”③[德]康德著,李秋零译:《人类历史揣测的开端》,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第118页。亚当在使用其理性和自由能力时,逾越了上帝的禁令,被逐出伊甸园;这被看作是人类历史的开端。亚当自由运用其理性的事件被看作是恶的。而在亚当违背上帝禁令之前,他是作为遵从上帝命令的原始的或潜在的善人存在的;因为亚当作为单纯的受造物体现的是上帝的全善的属性。康德在这里所表达的两种历史观对应于他在《宗教》中的两个问题:一棵原初好的树如何结出坏果子?一棵坏树如何结出好果子?康德以树木比喻人性;亚当在逾越上帝禁令之前就好像原初好的树木那样;而在其违背上帝禁令之后,亚当就被比作一棵坏树。康德在《普遍历史》和《宗教》中,历时十年都没有解决的难题(弯曲的木头怎能制造出完全直的东西),其实暗示了人类始祖亚当违背上帝诫命之后,也就是人类历史开始之后,个体如何重新向善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笔者只是澄清了这一弯曲木头的比喻中的难题。在这个难题中,有四个要点需要注意:首先,具有偏好的人(弯曲的木头)如何成为道德上绝对完善的人(完全直的东西),这个难题需要与“原初善的人如何堕落为恶人”的难题,结合在一起被思考。其次,一个人从原始的善的状态堕向恶的状态是由他自己招致的,这个人从恶的状态再回归善,也必须是他自己选择的。再次,这个弯曲木头的比喻,连同康德关于一棵好树和一棵坏树的比喻主要是从个体角度来思考的。最后,这个难题的症结在于,人为什么会自发选择变得弯曲(沦为恶人)?
二、个体与整体双重视角中人性的曲直
在康德的弯曲的木头的比喻中,难解的不光是人性的曲直问题,更是在不同视角、不同语境中,人性的曲直所表现出的不同形态。康德在其历史和宗教学说中对人性的理解,要比他在纯粹道德哲学中对人性的定位复杂得多。
在区分自然的历史和自由的历史时,康德对亚当被逐出伊甸园这一神话事件进行了精彩的诠释。“人走出理性给他呈现为他的类的最初居留地的乐园,无非是从一种纯然动物性的造物的粗野过渡到人性,从本能的学步车过渡到理性的指导,一言以蔽之,从大自然的监护过渡到自由状态。如果人们关注的是人的类的规定,这规定无非在于向着完善性的进步……对于在运用其自由时只关注自己的个人来说,在发生这样一种变化时有所损失;对于把自己有关人的目的集中在类上面的自然来说,这样一种变化却是收获。”①[德]康德著,李秋零译:《人类历史揣测的开端》,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第118页。很明显,对于同一个事件,康德从个体和人类整体两个不同视角来分析,得出的是完全相反的结论。
对于个体而言,人违背上帝的禁令、受到惩罚,并被逐出那个乐园;这可能是一系列他不愿意接受的结果。特别是,在上帝为其安排的原初居留地和尘世之间,前者使他享有天赋的幸福,甚至无需他自己付出过多努力;而在尘世的生存则充满苦难。所以,那个神话事件对于个体而言意味着一种损失。但从类的角度来看,这一事件可以被看作是上帝导演的一场宏大叙事的人类历史戏剧的关键环节。康德也许像奥古斯丁那样认为,“魔鬼向恶的转变以及恶人类似的转变,是上帝由神道而预知的。但是为了整个创世工程,上帝允许这件事发生”②[古罗马]奥古斯丁著,庄陶、陈维振译:《上帝之城》,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4页。。上帝创造亚当时赋予其原初的向善的禀赋和理性能力,但这不是为了让他在那天国的居留地毫无作为地浪费其天赋;康德在其著作中反复强调一个自然目的论的原理:大自然从不做无用功,自然中的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目的③参见[德]康德著,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判断力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8页。。那么,亚当违背上帝禁令,这一事件必定也有其深意。康德指出,违背上帝禁令的行动本身恰恰发动了潜藏在人性中的理性能力;理性自发地选择违背命令,这体现了人的自由。
康德将人违背诫命的行动看作是他从动物性向人性过渡的中介。即便上帝在创造亚当的时候已经赋予其生气和灵魂,但是一个仅仅按照外在命令生存而没有自发活动的存在者,毋宁仍然是动物性的存在。如果作为受造物的人始终没有发动其身上的理性禀赋,那么人类就会始终处于上帝的监护之下。人受神的监护就像自然中其他一切事物受神的监护一样,从中表现不出任何人之为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种永远处于上帝监护之下的人与其他自然物一样,只会遵循上帝所颁布的自然法则。由此,那种自由的人类历史就不会从任何地方得到其开端了;唯一能够设想的只能是上帝所发动的自然的历史。但很明显,康德认为,这违背《圣经》中所描述的上帝创世的意图。上帝创造一种具有理智和灵魂的理性存在者,是为了让他做符合其理性的活动,而不是任他荒废这能力。对于只关注其私人偏好的个体来说,违背上帝的诫命并受到惩罚,就是道德的堕落,就是善和幸福的损失;但对于上帝和全人类而言,这恰恰是一种进步。因为上帝赋予人的理性禀赋开始了其从潜能到现实的不断发展完善的历程;理性能力的运作是《圣经》和全部西方文化所共同承认的人性的根本。那一神话事件中所描述的道德堕落对于人类整体而言,恰恰意味着人性的觉醒。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思考:人虽然被赋有理性禀赋,但他是如何将这禀赋发动起来的呢?仅仅因为其感性偏好的影响吗?按照《圣经》中的记述,蛇诱使夏娃吃了那棵分辨善恶的树上的果子,夏娃又给亚当吃了这种果子。蛇在古代世界中象征着死亡和智慧,“创世纪记述中蛇和夏娃间智慧文学式的对话,和被逐出伊甸后死亡的出现,使人同时联想到这两个方面”①[美]华尔顿、[美]麦修斯、[美]夏瓦拉斯著,李永明、徐成德、黄枫皓译:《旧约圣经背景注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13页。。蛇、夏娃、亚当,这三个存在者构成了最原始的社会;如果不是蛇的诱惑,夏娃和亚当不会仅仅因为想要满足自身感性欲望而违背上帝的命令。人自身具有口腹之欲和对智慧的欲求,再加上外部因素的影响,才构成其违背法则的充分必要条件。
同样,在现实中,人身上的偏好就其个体而言也不足以促使他违背法则。一个离群索居的人是不可能在其偏好的影响下发动其理性能力,产生自由行动的。康德在《宗教》中指出,“当他处在人们中间时,妒忌、统治欲、占有欲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怀有敌意的偏好,马上冲击着他那本来易于知足的本性……他们包围着他,他们都是人,这就足以相互之间彼此败坏道德禀赋,并且彼此使对方交恶了”②[德]康德著,李秋零译:《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93页。。这就找出了人从其原初善堕向罪恶的根源。每一个人本来都具有其理性禀赋和各种偏好,但只有当他处在社会生活中、处在其同类中间时,其偏好才会诱导其理性自发地做出违背法则的行动。就此而言,一棵原初好的树如何结出坏果子的难题就得到了解答。那么,一棵坏树如何结出好果子的难题怎么解决呢?
孤立地看,个体身上的偏好不足以造成其道德堕落,同样也不足以成就其道德完善。换句话说,一个与其同伴相互隔离的人是无所谓善恶的,也无所谓人性的发展;善恶都是在社会环境中才产生的。在与同伴的共同生活中,他们出于其偏好的影响,相互对抗、竞争,由此促使每个人身上天赋能力的发展完善。社会生活中人们的非社会性即便不能充分地、直接地导致道德的实现,至少也能充当一种必要条件。
这种思路对理解人性中向善的禀赋也是具有启发的。Sharon Anderson-Gold从康德的这种思路中得出如下结论:“显然,作为每个个体的原始禀赋的向善的倾向,并不足以确保一种普遍的社会共同体。”③Sharon Anderson—Gold:Unnecessary Evil:History and Moral Progress in the Philosophy of Immanuel Kant,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1,p.33.康德将道德进步看作并非个体孤立的义务,而是个体对于其类的整体而言的义务。无论是人身上的向善的禀赋还是其趋恶的倾向,都只有在社会环境中才能发挥作用。可以设想,人性中善恶原则的内在矛盾不仅在个体之中,更在社会生活中共同推动着人性的发展完善,直至道德的最终实现。
康德指出,在人性的向善禀赋中有一种动物性禀赋,其中就包含着与其他人共同生活的社会本能。这就意味着,个体与其同伴共同生活在一起,这是无需理性、单纯基于其动物性本能就能设想的事情。康德通过善的禀赋与恶的倾向(或者社会性与非社会性)的内在矛盾来解释全部人类历史的发端、发展;他不像卢梭那样将自然人和自然状态描述为温顺的绵羊和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也不像霍布斯那样仅仅在自然状态中设想一种非社会性甚至相互敌对的人性。如果不是人性中社会性的动物本能使其生活在一起,人们不可能“在一种原始群居的环境中逐渐有意识地发展其自身”④刘凤娟:《康德论人性中的善恶共居》,《安徽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关于人性中向善的禀赋和趋恶的倾向及其与社会性和非社会性的关系,可详见此论。;如果不是人性中所存在的非社会性倾向,人们在社会中不会相互竞争和敌对,并由此推动其理性能力的进一步完善。实际上,人性中的曲与直是存在于社会环境和人性发展的任何阶段的。卡西尔就曾指出:康德的“历史哲学则强调人类只有通过社会这个媒介,才能实现其真正的道德任务”①[德]E.卡西尔撰,吴国源译:《康德历史哲学的基础》,《世界哲学》2006年第3期。。实现笔直的人性的关键是,“在无穷的历史进程中人类作为一个总体而达到道德化”②詹世友:《康德历史哲学:构建原则及其道德趋归》,《道德与文明》2017年第6期。。
因此,可以设想:康德之所以说从弯曲的木头中很难制作出来完全直的东西,这仅仅是从个体角度来思考的。离开社会和同伴,人身上的任何自然禀赋都只能永远处于沉睡状态,甚至其人性根本无所谓善恶或曲直。人从其原始的善趋向罪恶,以及从恶回归于善,这都是发生在社会中的。人性中的善恶因素也只有在整个社会中辩证地、历史性地相互对抗,才能促进终极目的的实现。如果将这弯曲的木头放在整个社会和全部人类历史中,未尝不能制作出笔直的东西。
三、如何从“弯曲的木头”中制作出笔直的人性?
人在同伴中沦落为恶,也必须在其同伴中完成道德化;解决这个人性难题的关键在于,将人放在社会视野中来思考。针对本文所述的该比喻的两处文本语境,当前要深入阐明的是:在政治共同体问题上那种自身正义的元首如何在公众和社会层面得到实现?在伦理共同体问题上那种道德的上帝子民如何在类的层面得到实现?
正义元首的实现应当从两个阶段来思考:首先,人类出自其偏好在追求私利、相互对抗中却达到了促进其人性完善的结果。这不是每个个体有意为之的结果,康德将其解释为大自然隐秘计划的实施。其次,道德的政治家允许公众公开使用理性并向臣民(哲学家)请教治国理政方略。这是社会中作为元首的存在者自觉自愿去实施的行动。
大自然的隐秘计划体现在人类历史的辩证发展进程中。人们在追求其感性欲望时推动了人性和文化的发展,特别是驱动人类社会产生出法制文化;而法律又成为规训人的自然本性的强制性力量。换句话说,人类对自身自然本性的追求造成了对这种本性的制约。康德在这方面最精辟的观点就在于:“建立国家的问题无论听起来多么艰难,纵然对于一个魔鬼民族(只要魔鬼有理智)来说也是可以解决的。”③[德]康德著,李秋零译:《论永久和平》,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第372页。具有非社会性和根本恶的有理性存在者为了自保而需要有普遍法律;虽然每一个人都暗中想要使自己成为这法律的例外,因而在其内在意念中所有人都是彼此对抗的,但普遍法律毕竟促使他们的恶的意念相互抑制甚至相互抵消;由此,在公开的和外在自由的层面上,他们反而可以和谐共处。看起来恰恰是凭借人们的自私偏好,国家才能够建立起来。因此,这样的历史辩证法不是从非社会性到社会性的平稳过渡,而是人性既自我驱动、自我发展又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曲折的动态过程。
道德只有在完善的法制状态与和谐的社会秩序中,亦即在内部完善与外部完善的国家宪政中,才有可能实现。所以,法制文化构成了自然与自由的联结点。Henry E.Allison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法制文化(culture of discipline)“使我们容易接受比自然能够给予的更高的目的;并且由于这些是道德的目的,这就使法制文化成为最卓越的道德的促进者(moral facilitator)”④Henry Allison:“Teleology and history in Kant:the critical foundations of Kant’s philosophy of history”,in Kant’s 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a Cosmopolitan Aim,(eds.)Amélie Oksenberg Rorty and James Schmid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40.。自由和道德的实现更像是非社会性的一个间接的和“出乎意料”的结果。人性也在这种辩证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得到完善,但自身正义的元首仅凭此是无法达成的。
然而,康德在《普遍历史》的弯曲的木头的比喻中已经明确指出,完全直的东西不可能从弯曲的木头中制造出来;并且,这种直的东西就喻指使公民宪政成为可能的自身正义的元首。这就产生了一个循环:具有善良意志的正义元首是公民宪政的前提条件,而公民宪政反过来又是这种完善人性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康德在其1795年的《论永久和平》中必定是意识到了这一理论谬误。在这里,他不再提及具有善良意志的正义元首,而是退而求其次,提出了道德的政治家概念。“一旦在国家宪政或者在国际关系中出现人们无法防止的缺陷,尤其是对于国家元首来说,就有义务去考虑怎样才能尽可能快地改善它们,使之合乎在理性的理念中作为典范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自然法权。”康德宣称:“掌权者最真挚地心怀这样一种修正的必要性的准则,以便保持在对目的(在法权法律上最好的宪政)的不断接近中,这却毕竟是可以要求于他的。”①[德]康德著,李秋零译:《论永久和平》,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第378,382,375页。国家元首对于内部完善和外部完善的公民宪政来说仍然是十分重要的。而这种存在者遵循这一原则:“要这样行动,使你能够想要你的准则应当成为一个普遍的法则(不管目的是什么样的目的)。”②[德]康德著,李秋零译:《论永久和平》,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第378,382,375页。这实际上就是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提出的法权原则。众所周知,这种原则不考虑人们的内在意图和目的的合道德性,只考虑外在行动的合法则性。但遵循这一原则的存在者仍然被叫做道德的③康德在其后期思想中所理解的道德概念似乎更宽泛一些:在其批判时期(例如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道德存在者就是那种具有善良意志和纯粹的内在目的的人;而在《道德形而上学》《论永久和平》等著作中,仅仅符合法权原则已经称得上是道德的存在者了。,因而就国家元首被按照这种法权原则来要求而言,他就可以被称为道德的政治家。
在社会中找到一种仅仅合乎法权原则的道德的政治家,要比找到《普遍历史》中所要求的具有善良意志的正义元首容易得多。因为,按照上述辩证历史观,人性在其自然的辩证运动过程中已经能够促使人们遵纪守法,这是在历史过程之中有望被实现的。需要强调的是:要促成道德的政治家不仅需要大自然隐秘计划的暗中实施④康德历史哲学中的大自然隐秘计划只是一种调节性原则,因此,人们不能按照构成性的视角理解这一概念,似乎人类历史背后真的存在某种隐秘力量在操控着人性的辩证发展进程。,更需要这种存在者自觉自愿地按照法权原则行事。而一个按照法权原则自觉维护和平的政治家,也不必自身具有最完善的知识和治国智慧,而是被允许在其同伴中寻求帮助。康德在《论永久和平》“第二条附论”中不无讽刺地提到,一个国家的立法权威、统治者求教于作为臣民的哲学家似乎是贬低身份,为此他只能悄无声息地要求哲学家自由并公开地谈论政治。德国著名康德哲学研究学者Volker Gerhardt教授认为,康德在这里宣布其永久和平的秘密条款时,“公然大量运用讽刺的手法。如果我们阅读这些秘密条款的真正内容,就会发现这种讽刺已变成最辛辣的挖苦”⑤[德]福尔克·格尔哈特著,孙迎智译:《哲学的弃权——论哲学和政治在现代的关系》,洪涛主编:《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第7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76页。。康德像三赴叙拉古都铩羽而归的柏拉图那样深切地意识到:“国王们思考哲学,或者哲学家成为国王,这是无法指望的,也是不能期望的,因为权力的占有不可避免地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⑥[德]康德著,李秋零译:《论永久和平》,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第378,382,375页。唯有退而求其次,让政治和哲学分属不同的存在者,让国王和哲学家至少能够和谐相处、互惠互利。
康德在第一批判中指出,“我们自古以来也一直都把哲学家这个名称同时理解为并且首先理解为道德学家”⑦[德]康德著,邓晓芒译,杨祖陶校:《纯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34页。。《普遍历史》中的正义元首就是一种既具有善良意志又具有治国智慧的完美政治家,类似于柏拉图的哲学王。而在《论永久和平》中,哲学家不一定直接治理国家,政治家不一定拥有完满的治国智慧和内在道德。他们之间只要有相互协作就可以。不难看出,康德最看重的是统治者允许哲学家乃至普通大众公开地、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这与其启蒙立场是一致的。康德在启蒙问题上具有如下观点:“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难以挣脱几乎已经成为其本性的受监护状态……公众给自己启蒙,这更为可能;甚至,只要让公众有自由,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公众只能逐渐地达到启蒙。”①[德]康德著,李秋零译:《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第40—41页。哲学家无疑是康德所说的那种最先摆脱受监护状态,因而正在启蒙甚至已经启蒙了的道德存在者,他们在自己周围传播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由此带领公众逐渐达到启蒙。一个允许臣民公开使用理性、自由发表言论,又能隐秘地求教于哲学家的政治家,就是完善的国家宪政所需要的道德的政治家。
道德的政治家保证了公民宪政的实施,也避免了统治者和公民宪政之间互为前提的循环。但他还不具有笔直的人性。只有内在道德上完善的理性存在者才能体现那种完全正直的人性,而这种存在者必须作为上帝子民,并在一种伦理共同体中被思考。上帝子民概念将人性的完善问题推进到宗教信仰领域。因此,从大自然的隐秘计划到道德的政治家,再到宗教信仰所保证的上帝子民和伦理共同体,康德通过这一系列策略来解决人性的曲直难题。
在对待道德和宗教的关系问题上,康德的态度也是令人费解的。一方面他说,道德为了自身之故绝不需要宗教,因为无论是为了认识义务还是为了驱动人们履行义务,道德的根据都只在纯粹理性之中,无需外求。但另一方面他也强调(正如上文所述),即便某些个体已经达到了道德完善性,这也很难维持下去;因为人只要生活在其同伴中间,就有再堕落的可能。此外,人们履行义务之后必定希望从中获得某种配享的幸福,而这种幸福不是道德自身就能直接保证的。出于这些理由,具有善良意念的人们必须联结成为一个系统整体;一方面确保其自身始终处于道德进步之中,永不退转,另一方面也保证配享幸福的实现。这个系统整体就是上帝治下的伦理共同体,为此,道德不可避免地导向宗教。
宗教的必要性在于它强化了每个个体道德进步和自我救赎的自信力,同时也超出了每个人在维持其道德完善时和在实现其配享幸福时的个体局限性。而信仰之于每个个体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耶稣作为每个人的纯粹道德榜样,促使他们坚定自身道德实践的力量,并转换实践的思维方式;上帝作为每个人的配享幸福的全知的和公正的分配者,促使他们联结成为系统的伦理共同体。
对于人性完善的问题来说,重要的不是人们外在行动的合法则性,而是其内在意念的合道德性。这需要“人的意念中的一场革命”②[德]康德著,李秋零译:《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48,98页。。经历这种革命的人就好像被重新创造了一样,成为一种新人;康德重新解释了《约翰福音》中耶稣向所有人颁布的“你们必须重生”(《约翰福音》3:7)的道德诫命。这种重生不是从习俗的改善开始,而是从思维方式的转变开始。每个人在其内心中将善的原则作为自足动机纳入准则时,所经历的就是思维方式的转变或心灵的革命。为了坚持人类理性的主体性立场,康德必须“把上面这一基督教的核心学说理性化,但是又不能丧失掉基督教思想的基本精神”③尚文华:《希望与绝对——康德宗教哲学研究的思想史意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54页。。
然而,个体通过对其内在的耶稣④关于耶稣在康德哲学中的意义可参见刘凤娟《康德哲学中的耶稣形象》,《清华西方哲学研究》2016年第2期。理念的信仰,只是坚定了道德进步的信心。在这个层面人性的最终完善还不可能被实现,因为这涉及到人的族类的使命,即“促进作为共同的善的一种至善”。而这样的目的“要求单个的人,为了这同一个目的联合成为一个整体,成为一个具有善良意念的人们的体系。只有在这个体系中,并且凭借这个体系的统一,道德上的至善才能实现”⑤[德]康德著,李秋零译:《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48,98页。。这个系统整体就是一种伦理的共同体。每个人通过对自身内部耶稣形象的效仿和学习,有可能达成思维方式的转变和道德的进步;但如果他没有与其他人一起按照一个至善的目的联结成为系统整体,不仅至善无法被实现,甚至就连其善良意志本身也有堕落的危险。
而为了成为这样一个伦理共同体的成员或者就是上帝子民,每个人都必须具有对上帝的纯粹信仰。上帝才是真正能够超越人的个体性限制,保证人类整体的至善目的之实现的那种存在者。而只有这种作为上帝子民的存在者才能算得上是完全直的东西。在康德的纯粹信仰中,上帝与耶稣一样是人类理性之中的概念,而不是被确证的神圣存在者。就耶稣和上帝都被转化为人类理性概念而言,康德的这种宗教信仰是一种纯粹信仰,并且隶属于其纯粹道德哲学。
此外,康德基于其纯粹理性的建筑术思维,将历史中各种启示性信仰方式也统摄于其纯粹信仰的理念之下;由此造成的是一种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史。启示性信仰虽然并不能直接地实现道德目的和人性完善,但却能够促进纯粹信仰的建立。或者说,人们将道德进步建立在启示性信仰之上,这是能够充当为纯粹信仰的手段的;从而也间接地促进了作为终极目的的至善的实现。所以,人类道德进步的过程伴随着其信仰观念的变迁。从弯曲的木头中制作出来完全直的东西,这是发生在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进程中的,也是发生在人类信仰观念的演变历程之中的。
结 论
康德使用这样一个关于弯曲的木头的比喻,形象地揭示了人性由恶向善的道德难题。但他从历史到政治再到宗教的一系列解决思路还是存在很大缺陷的。对待这一难题,康德似乎不能独断地说,从弯曲的木头中可以制作出来完全直的东西。因为这只是理论上可能、实践上可行的一种理性信念。但康德也不能说这个难题没办法解决,因为这会摧毁其道德形而上学的整个上层建筑。假如道德的终极目的没办法被人类所实现,康德还有什么必要建构其实践哲学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一方面区分了自然和自由、现象和物自身,另一方面却想要靠人自身的理性能力实现其统一。这就好像人要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荒谬。
笔者认为,人们必须在正视其理论缺陷的基础上吸取其思想精华。康德以人性的内在矛盾解释历史发展的思想,已经表现出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对这一难题的澄清,间接地揭示了康德、黑格尔等人在辩证法演变历程中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