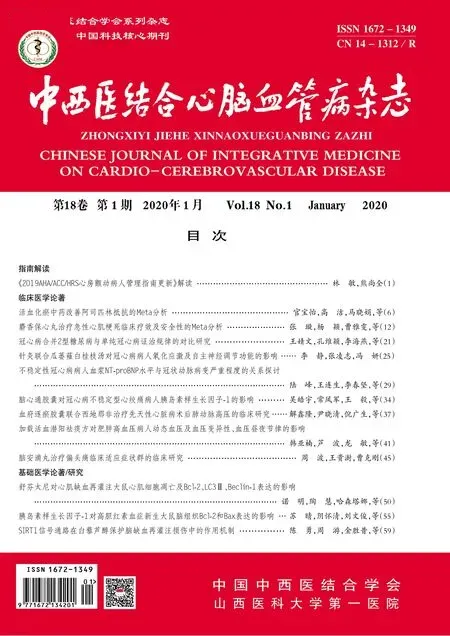抑郁症与血小板关联性的研究进展
抑郁症不仅给病人带来极大的精神痛苦,而且可引起病人炎症反应、神经内分泌功能紊乱等[1]。血小板在其颗粒中含有大量促炎症和免疫调节生物活性化合物,其在心血管疾病、凝血系统以及炎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精神障碍性疾病与血小板激活、平均血小板体积(MPV)、血小板计数(PLT)相关。本研究对抑郁症与血小板参数以及血小板激活相关性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1 血小板
血小板是3种血细胞(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中最小的,它没有细胞核,来自哺乳动物骨髓巨核细胞的细胞质裂解具有生物活性的小块胞质,随后进入血液循环,存活时间7~10 d。血小板具有黏附、释放、聚集、收缩、吸附五大功能,在炎症性疾病、血管性疾病中具有重要作用[2]。血小板含有3种重要的储存颗粒以及血小板膜(糖蛋白、磷脂),其中储存颗粒包括α颗粒、致密体颗粒、溶酶体颗粒,α颗粒包含了大部分的促炎和免疫调节因子以及黏附分子[3]。
2 抑郁症与炎症、血小板相关
炎症可能参与抑郁症假说,最早是由Smith[4]提出的,炎症假说认为:应激刺激引发炎症过程,进而使5-羟色胺(5-hydroxy tryptamine,5-HT)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the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HPA or HTPA axis)的正常生理功能发生改变,最终导致抑郁症的发生[5]。而前炎症因子可引起5-HT异常以及HPA功能亢进[6]。其中促炎症细胞因子,主要包括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细胞介素1(interleukin-1,IL-1)、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白细胞介素8(interleukin-8,IL-8)。
血小板及其产物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炎症反应的发生、发展过程。这可能与机体在炎症过程中,血小板能识别与炎症相关的病原微生物及其产生的各种信号有关,血小板被活化后可以产生大量的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从而产生多种免疫效应及调节功能[7]。在细胞因子方面,血小板中含有的CD40配体(CD40L)是一种膜转移蛋白,通过与相应受体CD40结合后诱导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巨噬细胞分泌大量细胞因子,如TNF-α、IL-6、IL-8[8]。研究认为,活化的血小板可表达 IL-1和 IL-6,其能诱导内皮细胞表达黏附分子,促进单核细胞、中性粒细胞等黏附到内皮细胞上,同时促进内皮细胞合成和分泌趋化因子,进一步提高血管通透性和白细胞募集趋化效应,参与炎症反应[9]。
3 抑郁症与心血管疾病、血小板激活相关
抑郁症病人存在血小板激活[10],抑郁症病人的5-HT系统、脑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系统在激活血小板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5-HT作为外周血小板激活剂之一,5-HT刺激会引起抑郁症病人更加广泛的血小板聚集和更强烈的信号反应[11], 5-HT受体-G蛋白偶联-环磷酸腺苷信号通路下诱发钙内流,激活血小板[10]。BDNF系统中转换生长因子β1、纤维蛋白原、P选择素、血小板第4因子(PF4)都在炎症反应中起到血小板活化作用[12]。Can等[13]研究表明,抑郁症患儿的血小板活性较健康对照组升高。
研究表明,抑郁症病人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如邸云翔等[14]采集47例确诊的抑郁症病人和47名健康人24 h动态心电图,分析心率变异性(HRV)指标及心律失常的发生率,结果显示抑郁症病人易发生室上性心律失常。临床上,较多已确诊的抑郁症病人会出现胸闷、心悸等与心血管事件相似的躯体症状,现在国内外研究大部分说明血小板激活在此二者的相关性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0,15]。
抑郁症主要通过增强血小板活性、炎症反应等生物学机制影响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10]。动脉粥样硬化是一个由血小板、白细胞介导的最终导致内皮功能受损的一个过程,在炎症反应过程中,血小板的激活起着重要作用[15]。有研究显示,心率变异的抑郁症病人可能通过血小板聚集、炎症刺激和脂质代谢的改变促发早期动脉粥样硬化和(或)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最终出现冠心病[16]。Bruce等[17]研究发现,合并缺血性心脏病的抑郁症病人,其循环血小板经历了一个由血小板应答级联至不可逆分泌的过程。Davidson[18]发现抑郁症合并心肌梗死病人较仅有心肌梗死病人的血小板活性更高,血小板炎症性反应增强。
4 血小板与抑郁症的相关性
血小板α颗粒包含的炎性细胞因子不仅增强了免疫炎症反应,如发热、肿胀、疼痛等,也进一步诱发了悲观厌世、睡眠障碍、疲乏、厌食等与抑郁症相关的临床症状[19]。不仅如此,外周血液中大部分5-HT、BDNF均来源于血小板,在5-HT摄取、储存和代谢方面,血小板5-HT与中枢5-HT有相似的5-HT2A受体,相同的5-HT基因编码,血小板5-HT已被看作是研究中枢神经系统5-HT摄取和释放的模型[20],进一步印证了血小板与抑郁症密切相关[21-22]。
4.1 MPV与抑郁症 MPV是血小板体积的平均值。抑郁症病人存在血小板过度激活及炎症反应[10],MPV与血小板激活及炎症反应呈正相关[23]。抑郁症病人MPV升高,其机制为精神障碍性疾病病人的交感神经、皮质醇及儿茶酚胺水平皆升高,肾上腺素激活肾上腺受体致MPV升高[11]。Lee等[24]研究发现MPV在精神分裂症病人中含量上升,其中MPV受血小板生成素和其他免疫细胞因子(如IL-6和TNF-α)调节,精神分裂症病人上述调节通道失调。有研究观察了2 286名参与者,其中289名参与者诊断为重症抑郁症,结果显示重度抑郁症病人MPV较无抑郁症者升高[25],Cai等[26]的研究支持了该观点,但进一步说明MPV并不随着抑郁症分值增大而增加。在抗抑郁症疾病方面,抑郁症病人服用西酞普兰后,MPV水平下降,减少了血小板激活[27]。研究发现,冠心病合并抑郁组病人MPV水平较冠心病无抑郁组高[28]。
4.2 PLT、血小板比容(PCT)及血小板分布宽度(PDW)与抑郁症 研究表明,PLT与炎症性疾病相关[29],如国外研究指出,具有自杀想法的抑郁症青少年病人较健康者PLT升高[30]。国内研究中,31例住院女性病人抗抑郁治疗后MPV、PLT较治疗前下降[31]。杨瑾啸等[32]研究认为非冠心病抑郁症病人较非冠心病非抑郁症病人的MPV、PDW、PLT升高,其可能的机制为MPV、PDW体现为大血小板,可增强血小板活性,最终发生抑郁症、冠心病。总之,抑郁症与PLT、MPV、PDW存在相关性,但目前尚无PCT与抑郁症的相关性文献研究。
5 抗炎性细胞因子、抗抑郁药物、抗炎药物之间的关系
众多文献表明,炎性细胞因子与抑郁症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而抗炎性细胞因子如白介素10 (interleukin-10, IL-10)、白介素1受体拮抗剂(interleukin-1 receptor antagonist, IL-1RA)、白介素 4 (interleukin-4,IL-4)、白介素 13(interleukin-13,IL-13)等对改善抑郁症状有良好作用,其中以IL-10最为重要[33]。众多抗抑郁药物具有抗炎作用[34],大部分都与抗炎性细胞因子相关。如去甲丙咪嗪和氟西汀都可以抑制接触性超敏反应,并升高 IL-10 的血清水平[35];而氟西汀与金刚烷胺的联合干预提高了强迫游泳应激大鼠的血清IL-10水平[36]。
如炎症假说为抑郁症的病因之一,那么临床上抗炎药物可能具有抗抑郁效果。有文献报道,在C反应蛋白、TNF-α高于正常水平时,TNF-α单克隆抗体英利昔单抗在治疗炎症病人时有明显的抗抑郁效果[37]。非甾体抗炎药乙酰乙酸单独使用时有抗抑郁作用,而与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合用时可增强SSRI的抗抑郁效果[38]。塞来昔布与氟西汀合用的抗抑郁效果优于单独使用氟西汀[39]。当然目前该方面的研究仍较为有限。
综上所述,抑郁症与炎症存在复杂的联系,而血小板在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抑郁症与血小板激活、MPV、PLT存在正相关可能,这为提高临床一线抗抑郁药物的疗效以及新型抗抑郁药物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