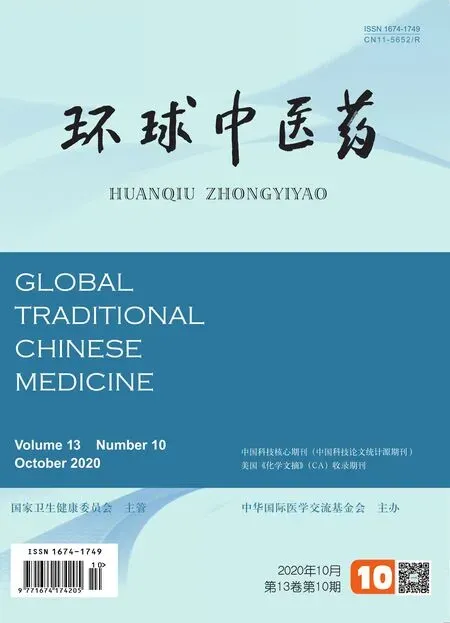从肝阳虚论述乌梅丸
任梓林 陶琳
乌梅丸出自《伤寒论》厥阴病篇,主治蛔厥,又主久利,历代伤寒注疏大家皆谓此方乃厥阴病之总方,明清时期,乌梅丸的证治规律趋于发展成熟的阶段,吴鞠通指出“乌梅丸寒热刚柔同用”,建国之后,众多医家从脏腑辨证角度对乌梅丸组方持“上热下寒、寒热错杂”论,各自对寒热部位的描述又有细微的差别,笔者通过查阅文献,对乌梅丸此病机提出疑问,并发现从肝阳虚的角度分析乌梅丸,则能解释其组方特点。本文通过阐述乌梅丸寒热错杂病机、肝阳虚未得到重视的原因、乌梅丸证肝阳虚病机发挥、乌梅丸证病案举隅等方面,提出乌梅丸“寒热错杂”病机是在肝阳虚的基础上,相火内郁化热而成,临床上需抓住脉、症两点,可扩大乌梅丸的应用范围。
1 乌梅丸证寒热错杂病机探究
《伤寒论》326条提出厥阴病提纲证:“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后世将乌梅丸作为厥阴病提纲证的处方,主治蛔厥和下利。六经辨证厥阴包括手厥阴心包络与足厥阴肝,《伤寒论》厥阴病主论足厥阴肝病。
在明清以前,医家研究乌梅丸尚处于认识和探索阶段,到了明清时期,乌梅丸的证治规律开始趋向于发展成熟的阶段,医家主要从六经辨证探究乌梅丸证病机,为后世发展乌梅丸证“寒热错杂”病机提供理论依据。柯琴首次提出了“乌梅丸为厥阴主方,非只为蛔厥之剂矣”的观点,并从全新的角度阐释了乌梅丸的组方配伍。俞根初在比较四逆汤和乌梅丸以后认为,乌梅丸内添加桂枝、附子、细辛和干姜的原因为“厥阴火郁,必犯阳明”,提出厥阴病证重在温胃阳,是藉生阳以破绝阴之法。温病学家叶天士以“泄肝安胃”作为乌梅丸证的纲领,将其灵活运用于治疗六淫之病和内伤杂病。吴鞠通指出“乌梅丸寒热刚柔同用,为治厥阴、防少阳、护阳明之全剂。”
建国之后,近代医家通过研究前人临床运用乌梅丸的思路,主要从脏腑辨证角度发展新的理论。大部分医家持“上热下寒,寒热错杂”论,各自又有细微差别,如南京中医学院伤寒教研组编《伤寒论译释》说:“本证总的说来,是膈上有热,肠中有寒。”黄煌教授认为乌梅丸为寒在脾胃,热在胸中,提出厥阴病提纲证重点突出了肝气郁结,风火上扰的症状,“气上撞心,心中疼热”揭示了肝郁的病机,“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揭示肝病及脾、 脾胃虚弱这一常见的病理现象[1]。刘渡舟教授[2]在《伤寒论十四讲》中认为乌梅丸的病机为肝热脾寒,或上热下寒,并强调寒是真寒,热是真热。肖相如教授[3]从厥阴的生理出发,认为厥阴病的基本病机为“阴阳不相顺接”,进一步提出乌梅丸证属上热下寒,“上热”之意即肝火循经上扰,“下寒”之意即脾气虚寒。姚荷生教授从寒温内外皆有厥阴病变的立场出发,认为阴阳错杂与风气内动是厥阴主证的统一病机,而肝风内动是其中的重要病机[4],在姚教授理论基础上,朱黎红等[5]提出乌梅丸方证的寒热错杂确切地说是上热中虚下寒证。邓志远等[6]量化分析乌梅丸的配伍特点,并得出结论:乌梅丸的病机寒热错杂,并非简单的上热下寒,而是肺肾心脾阳虚,肝郁化热风动。然而大部分学者通常将乌梅丸证病机笼统称为上热下寒,对于寒热的部位未细致描述,叙述组方特点一般为:方中黄连、黄柏性寒味苦,细辛、干姜、附子、桂枝、蜀椒性热味辛,寒热并用。然则为何清上热须用黄柏,有学者亦质疑乌梅丸之热既在上焦,何不用黄芩,并自圆其说:黄芩虽能清上焦之热,但因蛔虫扰动气血逆乱,饮食减少,中土化气乏源,恐用之徒伤正气[7]。此解释乃基于乌梅丸为安蛔之方剂,然临床中使用时并不必遵循此原则。故笔者对乌梅丸的方证提出疑惑,查阅文献后,发现从肝阳虚的角度分析乌梅丸,则能解释其组方特点。
2 肝阳虚未得到重视的原因
肝阳虚,在《素问·藏气法时论篇》就有记载:“肝病者,两胁下病引少腹,令人善怒。虚则目恍恍无所见,耳无所闻,善怒,如人将捕之。” 宋代陈无择所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五脏中寒证》提出肝寒之脉证:“肝虚中寒,乃母子相因,弦多则吉,但紧不弦,舌卷囊缩,为不利,故使本部脉,紧如切绳。 ”《太平圣惠方》的记载更加全面:“夫肝虚则生寒,寒则苦胁下坚胀,寒热,腹满,不欲饮食,悒悒情不乐,如人将捕之,视物不明,眼生黑花……诊其脉沉细滑者,此是肝虚之候也。”中医认为“阳虚则寒”,故此论应为肝阳虚。肝阳虚在宋代及宋以前文献中记载不在少数,明清以后关于肝阳虚论述锐减,至现代,中医诊断学教材不断改版从肝之气血阴阳虚衰俱存,到仅存肝血虚、肝阴虚,鲜有肝阳虚论述,探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8]:(1)受钱乙“肝为相火,有泄无补”和朱丹溪“肝常有余”的影响;(2)肝脏生理病理特点所决定的肝阳虚与肝阴虚相比,确属少见;(3)辨证上,或因对肝寒证虚实不分,或因为肝阳虚证常虚实相兼;(4)最主要的原因为常以脾阳、肾阳概言肝阳。三者虽均冠以阳虚,然其由于经行部位不同,故表现有所差异,亦有学者指出脾、肾、肝阳虚的辨别关键在于病位特征症[9]。
3 乌梅丸证肝阳虚病机发挥
3.1 肝阳虚所致寒热错杂形成机理
秦伯未[10]曾明确指出:“肝虚证有属于血亏而体不充的,也有属于气衰而用不强的,应该包括气血阴阳在内,即肝血虚、肝气虚、肝阴虚、肝阳虚四种。”从生理看,肝阳乃相对于肝阴而言,是肝主升发、疏泄、温煦、藏魂、藏血等的动力。肝应春,禀春生之气,为阳生之始,阳始盛而生万物,继而才有夏长、秋收、冬藏。肝主疏泄,肺主宣发肃降,肝升于左、肺降于右,是全身气机调畅、津血正常运行的一个重要环节;心主行血,肝主藏血,脾主统血,动则听命于心,卧则血复归于肝,共同完成人体生理的血液运行;从五行相克理论看,肝主疏泄,脾主运化,肝阳旺则疏泄及,气得升而降;肝气舒则土气疏,气血化生有源,肝血行则心得养,君主明则五脏安,身体康健。
从病理看,朱良春教授[11]指出:“肝为刚脏,内寄相火,肝阴肝血为本,肝阳肝气为用,肝阴肝血虽多不足之证,肝阳肝气亦有用怯之时。”临床大夫常从“肝为刚脏”“肝为将军之官”的角度认识肝脏,然从四时五行分析,肝中之阳,实乃春生少阳之气,始萌未盛,易受戕伐[12]。故肝阳受损时,肝失调达、舒畅之意,形成肝郁。其内寄相火,相火者,随君火以游行全身,因肝阳不足而肝郁,肝中相火亦不能随君游行于周身,故而相火郁则化热。这就是在阳气虚馁的脏寒基础上,又有相火内郁化热,因而形成了寒热错杂证。厥阴病之提纲证“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之症皆为相火内郁上攻所致,“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此为肝阳虚脏寒之征。若仅表现为阴寒内盛,阳气不足,是病在太、少阶段,据病之渐甚,而有太阴和少阴之分;若进一步发展出现肝气上冲、化火生热的上热症状,则表明疾病进入厥阴阶段。此厥阴病寒热错杂之寒与热均与肝有关,无上下之分,均由肝之生理特性决定其特殊的病理特点。
3.2 肝阳虚的临床表现
依据肝阳虚所致寒热错杂形成机理,肝阳虚的临床表现当分为两部分,一为阳气虚的脏寒表现,一为相火内郁化热表现。肝阳虚脏寒临床表现如[13]:胁肋满胀或隐痛,亦可循经上及胸膺巅顶,下及少腹胀痛,四末不温,面色苍白,肢体挛,形寒胆怯,悲观消极,惊恐不安等。相火郁而化热,此热可上攻、下迫,亦可外泛肌肤[14]。上攻可见头痛、头晕、口干、咽干、目赤、鼻痛、耳鸣、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下迫可见小便灼疼、肛热,外泛可见肢热。
3.3 肝阳虚之治法
肝阳不足,则应温补肝阳,不得用温剂辛散。秦伯未教授[10]在《谦斋医学讲稿》中指出:“肝脏本身阳不足,宜以温阳助长生气升发……补肝阳的方法,必须在养血中佐以温药升发,不能单用温热。” 陈士铎[15]在《石室秘录》中亦强调:“至于肝为木脏,木生于水,其源从癸,火以木炽,其权挟丁,用热不得远寒,用寒不得废热,古方治肝之药,寒热配用,反佐杂施,职此故也。” 秦伯未主要强调温热药中应当佐以养血药,陈士铎则强调寒热配用。故而肝阳虚之治法当温肝阳、益肝体、清郁火,乌梅丸融合二者观点,桂、辛、椒、姜、附等温煦肝阳,以助升发,连、柏化其阳郁之热,寒热并用,调理阴阳,人参补肝之气,当归补肝之体,乌梅敛肝之真气[16],组方特点集温、养、清为一体。从肝阳虚角度亦能解释黄连、黄柏之妙用,以黄连泻心火,泻子以达到泻母的效果,黄柏清肾之郁火,因肝肾同源,故而能清肝之郁火。病属厥阴,阳气衰微,阴亦不足,机体功能活动低下,此类病证,阳气渐复,转出少阳,方为向愈之机。然而临床中肝阳虚相对其他证候较为难以辨别,可以借鉴李士懋从脉、症两方面判断[16]:一是脉弦不任重按或弦而无力。肝脉弦,无力乃阳气不足;二是出现肝病的症状,为肝区胀痛、肝经所循部位的胀痛,表现为胸闷、少腹痛、腿痛、头痛、胸痛、胃脘痛、经行绞痛,以及寒热错杂、精神不振、懈怠无力、转筋、痉挛、头痛、吐利等,见一二症,又有脉弦无力,即符合肝阳虚证,可用乌梅丸加减治之。
4 乌梅丸证病案举隅
患者,男,60岁,便溏7年余,大便7~8次/日,完谷不化,凌晨2~3点解便,夜尿频,7~8次/夜,胃脘胀满,鼻尖满布暗红血丝,口干口腻,偶有口苦,电子肠镜检查:慢性结肠炎,脉弦细略浮,舌黯红体胖,苔白腻厚。辨证:肝阳虚,兼有郁火。给予乌梅丸加减,处方:乌梅15 g、党参15 g、干姜10 g、黄柏15 g、桂枝15 g、细辛3 g、肉豆蔻15 g、葛根15 g、山药30 g、鹿角霜15 g、当归10 g、炙甘草6 g,7剂后大便次数减少至3~4次/日,鼻尖红血丝范围缩小,口干口苦未作,原方再进7剂,症状基本消失。
按 患者凌晨2~3点解便,为足厥阴肝经所主之时,完谷不化,大便次数多,属于肝阳不足,不能温煦脾阳。患者口干口苦口腻,鼻尖满布红血丝,为肝阳虚气机闭郁化火,上攻所致。治疗上予以乌梅丸,在原方基础上,根据患者寒重于热,佐以肉豆蔻、鹿角霜温阳,山药健脾胃之气,葛根升清阳止泻,达到温肝阳、益肝体、清郁火目的。
5 结语
乌梅丸出自张仲景之方,后世将其作为厥阴病之主方。明清时期,乌梅丸的证治规律趋向于发展成熟的阶段,提出乌梅丸寒热刚柔同用。建国之后,大部分医家对乌梅丸组方持“上热下寒、寒热错杂”论,笔者对此病机提出质疑,查阅文献,从肝阳虚入手,提出“寒热错杂”是在肝阳虚的基础上,相火内郁化热而成。临床应用乌梅丸需抓住脉、症,依据病证寒热虚实的情况调整方中药物的比例,亦需根据主治疾病的不同进行化裁,助阳气来复以转出少阳。
综上所述,乌梅丸“寒热错杂”病机,是在肝阳虚的基础上,相火内郁化热而成。在临床运用乌梅丸不能局限于“下利、蛔厥”,需把握脉、症这两点应用指征,精准辨证,根据病证寒热虚实偏颇,调整药物,清上温下、补中敛肝,就可扩展乌梅丸的应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