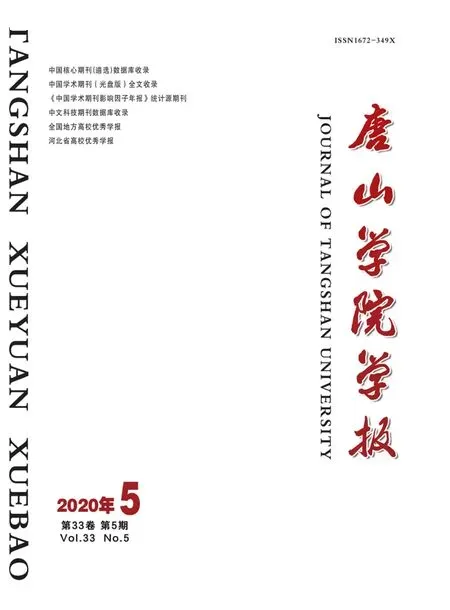扬弃与超越:论李大钊青春哲学对道家思想的借鉴
黄越泓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陷于列强环伺、瓜分盘剥的深重危机之中,险象环生;又经历了从封建帝制向现代国家的巨大转型,旧有保守势力与革命力量持续冲突,隐忧不断。将衰败、垂危的古老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欣荣的青春中国是当时中国人民所面临的最艰巨的历史任务,如何为中华民族的新生与复兴探寻理论基础是当时有志之士热切思考和讨论的最重大理论问题。1916年9月,《新青年》杂志刊登了集中体现李大钊早期思想的代表性文章——《青春》,该文从宇宙的运行机制和准则、人生的有限和寰宇的无尽、青年的历史责任和时代担当等角度对“青春”进行了体系化的阐释,为“青春”赋予了宇宙化、本体化、普遍化、哲学化的内涵,高扬起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主义旗帜。李大钊通过对“青春”内涵的全新阐释系统表达了他的宇宙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反映了他在20世纪初中西文化大碰撞背景下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理论探索和哲学思考,可以说青春哲学充分体现了李大钊的早期思想。
李大钊借鉴了中国传统思想、西方哲学以及近现代科学的先进成果,取精用弘,以构建青春哲学的理论体系。在李大钊所援引的多种思想资源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道家思想。李大钊对道家思想的借鉴与运用,不仅体现于《青春》一文中俯拾皆是的老庄典故与原文,直至“请诵漆园之语,以终斯篇”[1]318作为文章的结尾;而且也体现在他通过对道家宇宙观的吸收构建的青春哲学的形而上体系,他吸纳齐物论的观念丰富了青春哲学的思辨性,同时摒弃了道家消极颓唐的人生论。
对于李大钊的青春哲学思想,许多学者已经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著名学者朱成甲先生在其代表作《李大钊传》(上)中对青春哲学的产生背景、影响以及局限性进行了阐释和分析,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如何实现新生是青春哲学的产生背景,李大钊以哲学的思考方法,从中国是否能重获青春与永葆青春的积极角度探讨时代命题[2]468。李大钊“试图把不同的学说或者思想体系熔于一炉……表现了他思想的彻底的开放性……在思想上还存在着多元现象和杂糅现象,在思想表述上有某些朦胧和矛盾”[2]464。著名李大钊研究专家吴汉全教授在《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一书中亦有专门章节论及李大钊早期思想与道家的关系:“李大钊对道家学说中的辩证法思想和‘道法自然’思想尤为推崇。”[3]63吴汉全教授认为李大钊的早期哲学思想是西方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精神结晶,老子的“三生万物”的辩证法思想与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论被李大钊吸收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反映了李大钊对于道家文化的体认与承继。
本文的研究紧密结合李大钊思考青春哲学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语境,从宇宙观、齐物观、人生观三个角度重新审视青春哲学对于道家思想的借鉴,力求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好地分析李大钊如何在道家思想中找到中西文化的结合点并通过创造性转化实现与以进化论为代表的西方思想的融合再生。
一、青春哲学对于道家思想的借鉴
(一)宇宙观
“青春”,普通语境下指代年华岁月,是个人或者群体短暂性的、有限性的存在。李大钊对“青春”进行了拓展性的解释,“而此无初无终、无限无极、无方无体之机轴,亦即无尽之青春也”[1]309。李大钊指出,无论是运动抑或是静止的存在,有生命抑或是无生命的事物,都是宇宙的“无尽之青春”。李大钊赋予了“青春”以宇宙化的含义,将宇宙的一切皆视作无尽青春的体现。
李大钊青春哲学的宇宙观是建立在对宗教权威、超自然学说的深刻反思基础之上的,“历稽中国、印度,乃至欧洲之自古传来之种种教宗哲派,要皆以宇宙有一具绝对理性、绝对意思之不可思议的、神秘的大主宰,曰天,曰神,曰上帝,曰绝对,曰实在,曰宇宙本源,曰宇宙本体,曰太极,曰真如,名称虽殊,要皆指此大主宰而言也”[1]428。李大钊深信宇宙间有独一无二的真理,孔、佛、耶等皆是本于此真理而形成的宗教。“此真理者,必能基于科学,循其逻辑之境,以表现于人类各个之智察,非传说之迷信所得而蔽也。”[1]426李大钊认为宗教哲学的宇宙观尽管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是随着近代科学的进步以及人类视野的拓展,将宇宙之本源置于超自然力量之上的理论并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真理乃自然的因果的,宗教传说乃神秘的迷信的。”[1]427由此可见,李大钊所深信的是具有唯物色彩的科学宇宙观。
李大钊认为,宇宙的存在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并不受宗教意义上的神或神秘力量的有意识控制。“吾人以为宇宙乃无始无终自然的存在。由宇宙自然之真实本体所生之一切现象,乃循此自然法而自然的、因果的、机械的以渐次发生渐次进化。”[1]428细究李大钊此句,可知其所言之“真实本体”隐含着《道德经》中“道”的内涵,而其所言之“循此自然法”则与“道法自然”不谋而合。但是李大钊又跳出了传统宇宙观的窠臼,从近代西方进化论的角度审视宇宙运动,肯定了宇宙内含前进的力量,“若由相对观之,则宇宙为有进化者”[1]308。
在中国哲学史上,儒家与道家都曾提出过系统论的宇宙观。儒家基于现实的人文伦理活动而推演出作为终极价值的“天”,观人文以知天德,主张尽人事达致“性与天道”的统一;道家则是弥纶宇宙万物,从中抽象出某种理体——“道”,作为宇宙存在的根源,以归根复命、弥合人与“道”的矛盾。相较而言,儒家宇宙观的立足点重在伦理教化,而道家宇宙观的立足点重在自然演进。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认为“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任诸自然之淘汰”[1]429,儒家宇宙观的伦理色彩过于浓厚,难以被代表时代精神的青春哲学所借鉴与改造,而道家的宇宙观则能与李大钊的自然真理观相融通。
老子指出宇宙产生的根源是“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4]101,作为宇宙根源的“道”依据其自身的内在规律演化运行,生生不息。庄子把“道”视为时间上无始无终、空间上广阔无垠的存在:“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5]213
李大钊把宇宙视为时间上无始无终、空间上广阔无限的存在,与道家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宇宙果有初乎?曰:初乎无也。果有终乎?曰:终乎无也。初乎无者,等于无初;终乎无者,等于无终。无初无终,是于空间为无限,于时间为无极。”[1]308
不同于西方哲学从本体论的角度探究宇宙存在的本源,道家则从生成论的角度阐释万物之所以形成的本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万物得以产生和维持的根本所在。传统思想家对于“道生万物”的解释或以“气”释“一”归入道教,或从“无”释“一”流入玄学:“道始所生者一也,一生阴与阳也,阴阳生和、清、浊三气,分为天地人也。”[4]169道家学者认为从“道”中生出元气,元气又分化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互影响产生了天、地、人三者。儒家学者则奉玄学家王弼“以无为本”的“贵无”学说为圭臬,“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6],以形而上的“无”作为万物存在之根据。
作为一位博通中西的思想家,李大钊运用进化论的思想对“道生万物”进行了新的诠释:“老氏之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知宇宙进化之理,由浑而之画,由一而之杂,乃为一定不变之律。”[1]420李大钊肯定了宇宙朝着进化的方向运行乃是恒定不变的规律,将进化论引入其哲学观念以解释老子之说,突破了传统的以“无”“气”解释“道生万物”的体系,从而使宇宙万物呈现出“由固定而趋于流动、由简单而趋于频繁、由迟滞而趋于迅捷”的“向上之机,进化之象”[1]420。进化论原本是适用于生物竞争的法则,但经过李大钊的创造性诠释,则为道家的宇宙观赋予了新的含义。
朱成甲先生认为青春哲学的核心是宇宙论,李大钊的基本思路不是传统的“天人合一”,而是“人天合一”,即“李大钊将宇宙自然的客观实在、客观过程与客观规律,作为自己创造青春中华的客观前提与依据,并且明确主张这种创造活动以至整个人生,都力求和这种宇宙自然的客观过程达到和谐的统一”[2]468。“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学说,儒家、道家对此产生了不同的主张。李大钊因受到近代科学理性精神的影响,他的青春哲学的宇宙观排除了传统“天人合一”思想中不符合科学理性的部分,借鉴了道家“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统一,为传统的天人之学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
青春哲学的宇宙观包括绝对与相对的两重建构,从绝对的、整体的角度而言,宇宙作为一个整体是无尽无限的存在;从相对的、个体的角度而言,宇宙中的万象有进化、退化等种种殊别。李大钊崇尚唯物的自然真理观,也深受进化思想的影响,在宇宙论的构建上,借鉴了道家无所不在、自本自根的道体论,将之作为绝对层面的宇宙本体论,又融合了“道生万物”理论与西方进化理论,构建了相对层面的宇宙生成论,可以说基于新的理论完成了对道教宇宙论的借鉴与超越。
(二)齐物观
庄子在《齐物论》中以生动之寓言和天才之笔墨描写了人认识事物的种种局限性,指出人所执着的事物价值高低乃是基于特定立场而决定,虽然世间万物呈现出种种差异,然究其本质而言,人与自然万物共存共生、价值平等,即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或者说“道通为一”。客观而言,《齐物论》的结论尽管不一定符合现实情理,但是其论证过程和思维方式却闪耀着辩证思维的光辉。
“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5]171宇宙事物之间存在着种种对立差别,庄子认为此方与彼方是相对而言的存在,若从全体视角综合来看,则能于相对性中看到统一性。李大钊意识到道家齐物思想所蕴含的辩证法思想,因此将其创造性转化用于构建他的青春哲学体系。
李大钊借鉴了齐物论的辩证思维,指出青春是处于矛盾对立当中的存在:从相对的角度而言青春是有限性的流动,从绝对的角度而言青春又是无限性的永恒。“其变者青春之进程,其不变者无尽之青春也。其异者青春之进程,其同者无尽之青春也。其易者青春之进程,其周者无尽之青春也。其有者青春之进程,其无者无尽之青春也。其相对者青春之进程,其绝对者无尽之青春也。其色者差别者青春之进程,其空者平等者无尽之青春也。”[1]309
李大钊并没有因循于年华消逝、容颜易老等感叹青春有限性的旧说,而是以辩证的视角看待青春之有限性中所蕴含的无限性。从变化的角度而言,青春的进程时时更新、日日变化;从永恒的角度而言,青春的命运无穷无尽、循环不息,因此青春是永恒流动的存在。青春是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统一,蕴含着无穷的创造力与勃勃生机。
无论是追溯宇宙存在的开始时间,抑或是追问“存在”的有无,人们都难以给出或得到确切答案。庄子曾在《齐物论》中对宇宙之有限与无限展开追问:“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今我则已有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5]87庄子对于宇宙有限与无限的追问不可谓不深刻,但是却始终无法找到宇宙“有无之果孰有孰无”的答案,最终走向了相对主义。
道家认为死生皆是生命流转必然经历的过程,因而无须刻意求生恶死、乐生厌死,而应于死生差别中体悟生死价值的齐一,即所谓“万物一府,死生同状”“以死生为一条”。若脱离社会现实与伦理看待齐物论的“死生一体”,难免会得出不合情理的结论,但是不可否认齐物论的思维方式也蕴含着合理成分。现代哲学家刘笑敢先生认为:“任何概念都包含着自己的否定方面,生的概念就包含着死的因素,生的过程就包含着死的趋势。”[7]“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朝生暮死的菌类不知道什么是一个月的光阴,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蟪蛄也不知道什么是一年的时光。个体生命的长度不同,所感知的时空也随之不同,这是相对主义的时空观。
在《青春》中,李大钊对相对主义的时空观进行了评价:“夫晦朔与春秋而果为耶,何以菌、蛄以外之有生,几经晦朔几历春秋者皆知之,而菌、蛄独不知也?其果为无耶,又何以菌、蛄虽不知,而菌、蛄以外之有生,几经晦朔几历春秋者,皆知之也?是有无之说,亦至无定矣。以吾人之知,小于宇宙自然之知,其年小于宇宙自然之年,而欲断空间时间不能超越之宇宙为有为无,是亦朝菌之晦朔,蟪蛄之春秋耳。”[1]308在这段文字中,李大钊扬弃了相对主义的时空观,坚信时空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他认为,对于人类而言,个体生命的长度是有限的,而对于宇宙本身而言,时空又具有无限性,个人的有限生涯与宇宙的无尽长存是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故能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1]309。
庄子的相对主义暗含着人生短暂与无奈的消极意味,朱成甲先生认为:“道家把死生等量齐观,否认了生的价值,从而在人生态度上流入消极与虚无,这种‘超脱’是不足取的。”[8]李大钊虽然很欣赏庄子的思维方式,但并不认同庄子观念中的消极成分,故而将其中所含消极颓唐论调创造性地改造为奋发昂扬的青春哲学。
李大钊紧接着对“青春”的相对与绝对展开了论述:
仲尼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此同异之辨也。东坡曰:“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此变不变之殊也。其变者青春之进程,其不变者无尽之青春也。其异者青春之进程,其同者无尽之青春也。[1]309
李大钊认为绝对者是无尽之宇宙青春,相对者是宇宙青春之进程,青春的进程与无尽的青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其有者青春之进程,其无者无尽之青春也。其相对者青春之进程,其绝对者无尽之青春也。”[1]309相对主义的人生观容易消解人对于主流社会价值观的认可,淡化现实生活的意义,认为有限的人生在无穷的宇宙面前,无论何种努力都是微不足道的。面对这种消极思想,李大钊则将齐物论的思想加以提升转化,认为人只要把握当下的青春进程,锐进有为,则个人有限的青春就能与无尽的宇宙大化价值相通、命运相连。
不同于庄子的齐物论将事物的差别等量齐观而得出美丑无别、死生同状等不近情理的结论,李大钊则注意到绝对性与相对性、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差别中存在着统一性。由此可以看到,李大钊的青春哲学体系吸收了道家“齐物”的辩证观念,将个体的有限青春与宇宙的无限青春互动融通,为个人有限的人生赋予了绝对的价值。
(三)人生观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艰难处境,清王朝虽已覆灭,但是封建的意识形态仍旧具有广泛的影响;民国初创,封建势力借尸还魂,袁世凯复辟称帝,最终在全国的反对声中被迫下台;社会普遍存在对国家前途未来的种种忧虑,当时甚至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是东亚之病夫、待亡之国家、衰老之民族。李大钊没有因为近代中国的衰落而丧失对未来中国的信心,相反,他从中国“历数千年而巍然独存”[1]329的历史事实中看到中华民族强大的韧性和生生不息的动力,从而提出了“青春再造中华”的远大理想。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一文中指出:“吾人须知吾之国家若民族,所以扬其光华于二十稘之世界者,不在陈腐中华之不死,而在新荣中华之再生;青年所以贡其精诚于吾之国家若民族者,不在白发中华之保存,而在青春中华之创造。”[1]329他号召中国青年勇敢地担当起创造“青春中华”的大任,“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1]330,“鼓舞青春中华之运动,培植青春中华之根基”[1]332。
近代以来,不少接触西方启蒙思想的知识分子都十分重视并积极参与“青春”话题的讨论,通过对“青春”的赞颂以阐发变革维新、富国新民的思想,希望唤醒青年的蓬勃锐气,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陈独秀的《敬告青年》都热烈赞颂、讴歌青年,李大钊的《青春》亦是继承与发展这股时代思潮的代表作。
青年代表着勃兴的新生力量,能够冲决历史的桎梏、涤荡历史的积秽。李大钊赞美青年是“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1]330,希望青年能够冲破世间种种束缚,实现个人的精神解放,进而为青春中华的创造勇往奋进。至此,李大钊的青春哲学将建构“无尽之青春”作为终极关怀,消除了现实之人追求无限的精神渴望与有限人生的矛盾,又直面国家、民族、社会的现实问题,以再造青春中华的实践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青春大道。
李大钊从道家的思想中汲取了丰富的哲学养分,并将其创造性转化用于构建他的青春哲学体系,但是在对人生的终极价值的体认中,他并没有像庄子一样陷入颓唐、消极、避世的境地,而是对道家的思想进行了扬弃,一扫其低落消沉之弊,转而为昂扬奋进的精神。
如同许多思想家一样,李大钊对于人在现实世界的有限性与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有着深刻认识,这种认识最典型地体现在《青春》一文中:“秦政并吞八荒,统制四海,固一世之雄也,晚年畏死,遍遣羽客,搜觅神仙,求不老之药,卒未能获,一旦魂断,宫车晚出。汉武穷兵,蛮荒慑伏,汉代之英主也,暮年咏叹,空有‘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奈老何’之慨。最近美国富豪某,以毕生之奋斗,博得式之王冠,衰病相催,濒于老死,则抚枕而叹曰:‘苟能延一月之命,报以千万金弗惜也。’”[1]315
古往今来,人类对于长生不死的追求从未停歇,而人类希望拥有无尽生命的想法如此强烈,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有限的个体生命对于永恒存在的无限渴望。宗教信徒将对永恒的期待寄望于外在的神力救赎,李大钊则认为宗教所强调的修今生之苦难以换取来生之幸福的观点并不可取:“为贪来世之乐与青春,而迟吾现世之乐与青春,固所不许。”[1]316同时他认为贪图现实的享受、没有远大抱负、丧失理想信念的观点亦不可取:“而为贪现世之乐与青春,遽弃吾来世之乐与青春,亦所弗应也。”[1]316
李大钊破除了对宗教的恐惧与迷信,也不认为物质享受能带来真正的快乐。相反,他认为青年的使命在于冲破旧罗网,奋勇前行,促进青春中国的再生:“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一在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1]317
李大钊所谓“行健不息之大机轴”是对庄子“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的化用,青春所依立的就是行健不息的宇宙之道。宇宙万物的变化运行是无尽青春的进程,宇宙的生生不息、演化前行象征着青春的勃勃生机与盎然活力,唯有将有限的青春人生融进无尽的宇宙青春中,以宇宙之无限广阔统驭人生之有限,始可永享宇宙无尽之青春。
李大钊将现实有限之人生视为无限之宇宙的当下展现,并引用卡莱尔的名句“以吾人之生……特为时间所执之无限而已”[1]316以佐证之。李大钊提倡今日主义,“夫青年安心立命之所,乃在循今日主义以进”,认为只要立足于当下,奋进有为,就无须忧虑未来,当下的努力也具有永恒的价值:“无限现而为我,乃为现在,非为过去与将来也。苟了现在,即了无限矣。”[1]316
面对浩瀚无穷的宇宙,庄子认为渺小与脆弱的个人无疑是微不足道的。“块然一躯,渺乎微矣。于此广大悠久之宇宙,殆犹沧海之一粟耳。”[1]308不同于庄子,李大钊并没有停留在对时间和空间无限性之仰望、对个人渺小之感叹的层面上。他将个人的精神气魄与宇宙的无尽广阔进行贯通:“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世之气魄也。惟真知爱青春者,乃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惟真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者,乃能具此种精神与气魄。惟真有此种精神与气魄者,乃能永享宇宙无尽之青春。”[1]309李大钊用激昂雄壮的笔调扫尽颓唐黯然之气,鼓舞广大青年通过热爱人生、积极实践达致无限的精神境界。
庄子清楚地意识到人以肉体之躯进入世间之后所面临的困境:“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5]58人与物的“相刃相靡”、人与人的相互倾轧都是人不得不面临又无法逃脱的命运,道家唯有以“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理念安抚人心。不同于庄子寻求内心安宁的避世绝俗,李大钊希望青年人能够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世间、面对生活,用青春之力量创造青春的个体、青春的家庭、青春的国家乃至青春的宇宙:“盖现在者吾人青春中之青春也。青春作伴以还于大漠之乡,无如而不自得,更何烦忧之有焉。烦忧既解,恐怖奚为?”[1]316
庄子看到了世人汲汲于物质欲望的满足难免导致自身充满忧虑,役用他人或者被人统治也容易受到来自世间的伤害,真正有道之人则不以物质作为人生追求,亦不愿受制于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实之人是不能脱离物质而生存的,人与物最合理的关系就是“役物而不役于物”;同样,现实之人也是不可能脱离人际关系而生存的,人与人最恰当的关系就是“虚己以游世”。李大钊对于庄子“虚己游世”“不役于物,物莫之伤”的处世态度是颇为推崇的,道家坦荡的胸襟、开阔的视野、超然的情怀也是构成李大钊青春哲学的重要元素。
《庄子·山木》其中的一篇讲述了市南宜僚拜见鲁侯的故事:鲁侯满面愁容,市南子应鲁侯之请讲述去累除忧之道。李大钊十分推崇庄子不为物役、不以己忧、与道同行的境界追求,并引用此故事作为《青春》的收尾:
市南宜僚见鲁侯,鲁侯有忧色,市南子乃示以去累除忧之道,有曰:“吾愿君去国捐俗,与道相辅而行。”君曰:“彼其道远而险,又有江山,我无舟车,奈何?”市南子曰:“君无形倨,无留居,以为君车。”君曰:“彼其道幽远而无人,吾谁与为邻?吾无粮,我无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费,寡君之欲,虽无粮而乃足,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1]318
“故有人者累,见有于人者忧”[5]584,役用他人则有累患,被人役用则有忧患,庄子认为唯有与“道”同游方能无忧无累。庄子向往的是“虚己游世”“与道相辅而行”的境界,以消除现实人生所遇到的忧虑与伤害。李大钊将庄子带有避世色彩的“道”扬弃为积极入世的“青春大道”,“此其谓道,殆即达于青春之大道”[1]318,主张广大青年秉持一往无前的精神,努力实践革新奋进的活动,以达致“青春大道”:
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复何无计留春望尘莫及之忧哉?吾文至此,已嫌冗赘,请诵漆园之语,以终斯篇。[1]318
李大钊将青春与终极大道理会融通,构建了形而上的理论体系;又将青春理想的实现、青春价值的获取根植于创造“青春之中华”,始终对现实满怀热情与希望。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深刻的生存危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是摆在中国人面前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责任。道家的自然哲学、逍遥境界固然有其理论上的重大价值,但是儒家主张的奋发有为、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哲学无疑更切合时代的脉搏。“青年当努力为国家自重”,李大钊号召广大青年为再造青春中华而不懈奋斗的精神显然是吸收了儒家忧国忧民、坚韧刚毅的入世思想。李大钊多方汲取各家思想之精华,不定于一家,大胆借鉴道家思想的同时又正视其不足之处,并吸收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观,从而使青春哲学充溢着蓬勃生机与活力。
二、青春哲学扬弃与超越道家思想的原因及结果
李大钊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具有浓厚的儒家、道家文化情结,但是他并没有因循墨守,而是始终保持与时俱新的心态认识和接受新思想,在中西文化交融碰撞的背景下批判性地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笔者认为,李大钊之所以能够实现对道家思想的扬弃和超越,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李大钊早期多元化的思想体系是他能够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诠释的基础。李大钊自幼接受传统私塾教育,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儒家、道家的思想观念构成了他的人文底蕴;1905年,因清廷废除科举考试制度,正在应科举试的李大钊转入永平府中学堂,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学习英语以及西方的启蒙科学;1907年,李大钊考入北洋法政学堂,系统学习法律、政治以及西方文化;1913年,李大钊赴日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深入学习政治、经济等学科,留学经历丰富了李大钊的学术视野,也极大地提高了其研究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能力。李大钊广采博纳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于中外古今思想兼收并蓄,故而他能撷取道家思想之精华,用儒家积极入世、刚劲有为的态度弥补道家无为思想的不足,摒弃庄子相对主义思想不近人情、不合时宜的消极影响;同时他将以进化论为代表的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嫁接,以道家思想作为贯通中西的重要连接点,为道家思想的现代转化探寻了发展构架。
第二,李大钊对于传统文化批判性继承的态度以及调和中西促使文化融合再生的理路是他得以扬弃并超越道家思想的关键所在。李大钊虽然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却以其是否合乎真理的标准加以批判性继承,“孔子之道有几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则取之;否者,斥之”[1]427。李大钊对于道家文化也是批判性继承的态度,取道家思想的合理因素以体现时代风貌,而对于道家思想中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内容则予以排斥或补正。不同于知识视野大多局限于儒释道的传统士大夫,李大钊始终以世界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化:“而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则终非二种文明本身之觉醒,万不为功。所谓本身之觉醒者,即在东洋文明,宜竭力打破其静的世界观,以容纳西洋之动的世界观;在西洋文明,宜斟酌抑止其物质的生活,以容纳东洋之精神的生活而已。”[9]李大钊主张调和中西文化,他认为传统的东方文化以“静”为其精神底色,但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宜汲取西方文化中“动”的世界观,以推动中国文化在调和中西的基础上实现革故鼎新的现代转化。因此,就青春哲学的构建而言,既有对道家的宇宙论的阐释,又有对包括西方进化论在内的多种思想的吸收、借鉴,充分体现了青春哲学融合东西文化的调和性特征。
第三,李大钊对于进化论的认同和创造性解读是其扬弃和超越道家思想不可忽视的重要前提。“李大钊的早期哲学思想的中心在于论证进化论的普遍性……这一论证过程,离不开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运用。”[10]进化论传入中国后得到广泛的传播,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将生物科学领域的理论用于解释国家竞争以及社会发展的现状,在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国情与内忧外患的处境下让不少人感到悲观沮丧。若仅凭进化论看待中国的前途,古老的中国无疑已经历了成长期、兴盛期而正处于衰败没落的阶段。李大钊之所以提出创造青春中国的伟大理想,就是为了从哲学层面回答中国必然走向复兴和必将重获青春的重大理论问题,他不是仅从当时的现状与国情探讨中国的衰落与发展,而是着眼于宇宙之无尽与生生不息论证未来中国必将腾飞的命运。青春哲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汲取进化论而推进哲学发展的重要表征,“就李大钊早期哲学而言,进化论是其理论根基,这是毫无疑义的”[3]97。如果说进化论为青春哲学提供了解释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前进方向,道家则以其宇宙观的生生不息、推嬗无穷为青春哲学注入了运转动力。李大钊既将进化论哲学推进到崭新的阶段,又通过创造性转化将传统中国哲学的劲健雄浑、周行不殆精神汇入富有时代气息的青春哲学中,代表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哲学的发展水平。
总体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背景下进行的,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核心的理论资源,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青春哲学对于道家思想扬弃与超越的结果为李大钊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理论支撑。
其一,道家的辩证法思想为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作好了铺垫。李大钊认为历史演进是辩证的上升过程,这充分体现在他独特的“第三”文明观中,李大钊认为“第一文明偏于灵;第二文明偏于肉,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盖‘第三’之文明,乃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1]340。“第三”文明观为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而李大钊恰恰是运用了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辩证思想来论证“第三”文明观的。
其二,道家“无为之治”“道法自然”等思想为李大钊所承继。李大钊在体现其早期政治思想的代表作《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对道家政治哲学思想颇为欣赏:“则毋宁于牖育之余,守其无为之旨,听民之自器其材,自踏其常,自择其宜,自观其成,坦然以趋于至当之途之为愈也。”[1]268当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道家“无为而成化”“道法自然”等思想汇入到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表现为李大钊对于规律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于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统一的注重。
三、结语
李大钊通过对道家宇宙观、齐物观、人生观的批判性吸收和创造性转化,为“青春”的哲学化诠释和体系化构建奠定了扎实根基,同时摒弃了道家思想中去累除忧、避世逍遥的消极影响,而高扬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主义乐观精神。本文的基本结论是:青春哲学之所以能够借鉴道家思想并完成对它的扬弃与超越,一方面得益于李大钊思想体系的多元化特征,因李大钊多方汲取各家思想之精华,取精用弘,化为己用;另一方面是李大钊在认可西方自然科学、西方文明价值观的同时,力图从传统文化中探寻能够对接现代文明的积极因素,使传统文化通过融合西方文化转变价值取向而获得新生。可以说,青春哲学是李大钊早期思想体系成熟完善的标志,其创建与李大钊对道家等传统文化的借鉴是分不开的。青春哲学对道家思想的扬弃与超越在李大钊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亦产生了积极作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