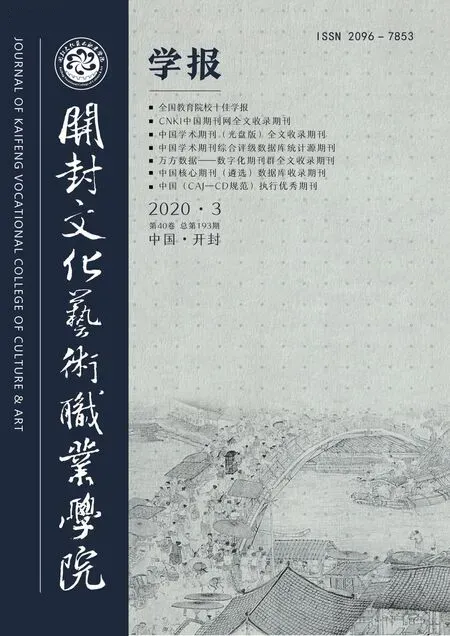电影《边走边唱》的文化想象
孙 青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初等教育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
在《命若琴弦》这部小说中,史铁生以他近乎理想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关于复明的寓言,将自己的生命体验融入生生不息的命运轮回,这其中饱含着他对顽强坚韧生命动力的渴望与坚守,是一曲神圣庄严的生命乐章。陈凯歌与这部作品的碰撞、交集,也正源于此番共鸣与感动。
一、颠覆原有的人物形象
陈凯歌曾在一次采访中说道:“我现在拍成的电影中没有一个是根据现成的小说拍摄的。一个都没有。而且我不认为存在这样的小说。我必须按照我的想法去结构一个故事。我自己先有一个想法,先有一种感动,而且这种想法与文学的创作正好契合。但要拿文学作品拍电影,这方面没有现成饭可以吃。”[1]147感动于史铁生所呈现的生命哲思是陈凯歌进行电影改编的起点,但绝不是全部。陈凯歌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文化想象融入电影,颠覆着原著的故事内核。
(一)在重塑中不断丰满的人物形象
《命若琴弦》中老瞎子的人生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弹断一千根琴弦,配药复明。《边走边唱》中老瞎子则在多重身份间转换——师傅、父亲、瞎子、神神、“幸福的人”、渴望情欲的男人。在复杂人性的刻画中,老瞎子成为了一个情感丰富、渴望像正常人一般生活的老者形象。在与师傅临终告别之时如梦魇一般重复着“千弦断、琴匣开……”的老瞎子,从童年开始就背上了沉重的复明重担,在压抑中幻想着与面店老板娘的情爱,在现实中反对小瞎子和兰秀的爱情,在得知药方骗局后砸毁了师傅的墓碑,在回归理性后如父亲般指引着徒弟石头。在众人追捧的神神和处于社会边缘的瞎子等多重角色间徘徊的老瞎子,绝不像史铁生笔下那个从寓言中走出来的顿悟老者一般质朴无尘,归于平凡。陈凯歌所塑造的老瞎子身上充满了人性的挣扎、思辨色彩,有着世俗与叛逆的一面。
《命若琴弦》中的小瞎子,单纯稚嫩、不谙世事,在爱情的伤痛中走向了和老瞎子一样的复明之路。而在《边走边唱》中,陈凯歌将执着执拗、不服输、具有青春式反叛的特质倾注在小瞎子石头身上。石头体格强健、自尊心强,不相信琴弦药引之说,只求活在当下。他与常人下棋、与体格强健的同龄人比试、琴弦弹断几根就是几根……在恋爱受到师傅阻挠之时,说出了师傅嫉妒他的论断,是一个做事果敢、行事叛逆的少年形象,颠覆了原著的人物设定。
(二)打破人物的宿命轮回
史铁生曾在《宿命与反抗》中说过:“所谓命运是人难以改变的,人只能在一个规定的条件下去发挥人自身的力量,这种规定的情境就是宿命。”[2]他也正是用“宿命论”去构建盲人琴师的寓言,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循环往复的命运闭环——人永远走不出历史所限定的命运,只能像老瞎子一样在有限的条件下发挥自身的力量,寻求生命的意义,以超然的态度去反抗绝望,甚至在小瞎子的生命中延续同样的宿命轮回。
陈凯歌在《边走边唱》中为老瞎子和小瞎子都安排了不同于原著的结局,以此打破宿命轮回的闭环。老瞎子在临终前不再去编造复明的谎言,而是选择走出自己的人生困境,在琴弦断裂的情况下用自己的歌喉完成了生命的绝唱,找回了他作为一个盲人琴师的价值。小瞎子放弃继承“神神”的位置,开启了自己边走边唱的人生,宿命的闭环就此被打破。《命若琴弦》中史铁生以寓言的形式将师徒二人的命运连接在一起,在代代相传中走向轮回,师徒之间的关系更多是一种传承和坚守。《边走边唱》则着重刻画师徒之间在对待身体残疾、人生信仰、情爱观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以小瞎子的形象展示带有少年青春期特点的叛逆不羁,为电影增添鲜明的反叛和启蒙色彩。
二、隐藏在荒诞中的文化批判
“人就其本性来说,是追求明晰和统一的,他在内心深处渴望着幸福和理性,而世界给予他的却是沉默和神秘,如一堵模糊而不可穿透的墙,这样,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呈现出不可解的荒诞。”[3]401该理论阐述了荒诞的本质,也契合了《边走边唱》从整体上所呈现出的荒诞氛围。
《边走边唱》的荒诞感伴随着电影的始终,从荒诞化的场景设置到荒诞化的符号设定,呈现出一种诡异、神秘、晦涩甚至略带空洞感的氛围。其中,荒诞的符号包括:面店伙计、面店老板、药铺掌柜、奔走大哭的老者、嬉笑不断的小孩,等等。荒诞的场景包括:药店围观、老瞎子化解孙李两大家族矛盾、兰秀的死亡,等等。
(一)看客们的精神病态
面店的伙计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好像在可怜老瞎子,又好像在嘲笑老瞎子,更像在可怜、嘲笑他自己的疯症。药铺的老板在看到无字的药方后发出诡异而迟缓的笑声,加之那群黑压压地挤在药店门口的看客们,连同那个笑声不止的小女孩,诡异又冰冷的气氛使得老瞎子沦为众人的笑柄,没有显示一丝的同情。穿行于街市的老头哭嚎个不停,仿佛与此刻老瞎子的内心形成了共鸣,显得荒诞而落寞。陈凯歌用这一连串的荒诞符号和场景投射出一个巨大而畸形的笑声,在诡异而复杂的气氛中暴露看客们扭曲病态的灵魂,从小孩到老人无一幸免。
(二)庸众的盲目崇拜
老瞎子仅靠琴声就化解了孙李两大家族的争斗。虽然一方面老瞎子通过传唱神话故事起到了开化思想的启蒙作用,但是人们拥戴他的原因却是他有一个看似神秘、代代相传的药方。对于未知事物的敬畏、盲从构成了庸众最主要的文化心理,表现出他们的无知,也构成了陈凯歌所要传达的文化批判,显示出这一范畴内荒诞符号和场景的空洞性。通过这一文化批判展现陈凯歌对于当时中国民众的文化想象,以及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众文化兴起的失落之感。
(三)对残疾的偏见
兰秀的死亡、小瞎子被老孙家的族人殴打的场面成为了一个经典的荒诞式场景。兰秀跳崖的时候小瞎子大喊道:“我看不见!”这里看不到一丝民众对于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小瞎子和兰秀付出真心的爱情以极度荒诞的方式被扼杀,在最大程度上呼应着人们对于残疾的偏见。兰秀的父亲因为“老孙家的女儿总不能嫁给一个瞎子”这一理由带领族人恐吓小瞎子并当众羞辱他,直接导致了兰秀跳崖自杀的结局,由此显示出人性的偏见与自私,这是陈凯歌有意曝光在大众视野内的文化批判。
三、精神困境中的文化想象
(一)残疾的隐喻
如果说肉体的残疾尚有药可医,或如那张无字的药方一般可以被期待多年,那么精神的残疾则需要爱和信仰来疗愈。残疾的隐喻正是指向精神的残疾,指向信仰和爱的缺失。
眼睛的残疾将老瞎子引入一个信仰的圈套——“千弦断,琴匣开。琴匣开,买药来。买得药,看世界,天下白。”(电影《边走边唱》台词)当真相大白的那一刻,老瞎子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他砸碎了师傅的墓碑,拿起石头砸向再次混战的两家族人,他再也弹不响自己的命运之弦,因为生命的琴弦早已随着信仰的缺失而断裂,他无法面对自己求而无果的人生。陈凯歌所描绘的老瞎子并没有完成如史铁生一般的信仰救赎,而是作为一个广义的象征性隐喻,电影将文化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大多数遗失信仰的沉沦者。
(二)身份认同的错位与焦虑
“身份认同是个人或者集体界定自身处于某一特定语境中自我身份的标志。”[4]33在老瞎子身上,身份认同的错位表现在别人眼中的“神神”和自己眼中的“渴望获得视力的瞎子”之间的巨大差异。特别是当老瞎子得知无字药方的真相之后,在他心中“渴望获得视力的瞎子”的身份认同也崩塌了。再次来到壶口瀑布时,老瞎子向散发着神秘气质的智者——面店老板发出了“我是谁”的诘问。得到的回答却是:“你是这世上幸福的人。”老瞎子却仍只觉自己是一个被社会置于边缘,无法拥有正常人生活的瞎子而已。身份认同的错位,是造成老瞎子精神困境的主要原因。
对于小瞎子而言,“我是谁”的精神困境主要体现在自我心理认知的错位。“人的自我心理认识,特点为主体的自我等同感和整体感,是人对于自己与某种类别、范畴(社会地位、性别、年龄、角色、范例、规定、团体、文化等)之同一性的认识(部分是有意识的,部分是潜意识的)。”[5]小瞎子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健全”的人,甚至在要强和自尊心的驱使下,他认为自己比常人更胜一筹,眼盲并不能影响他的人生。然而,在别人眼中,他是“神神”的徒弟,是“神神”的接班人,更是一个不配拥有爱情的瞎子。直到兰秀死后,小瞎子才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发出了像复仇一般的怒吼:“想看!”身份认同的错位给小瞎子带来了抹不去的伤痛和终身的遗憾。
身份认同的错位使师徒二人倍感焦虑和无奈,电影最终以一则寓言神话的隐喻消解了他们的精神困境,那便是走进人群。《边走边唱》中老瞎子先后两次给小瞎子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俩是瞎子。第一次老瞎子说:“玉皇大帝有两个儿子在天河里洗澡,一不留神从云缝里漏了下去。玉皇大帝派天兵天将下凡封了两个儿子的眼睛,还说下界那么脏的地方,可不敢让他们看见。”这段话听起来像是给小瞎子和自己的心灵安慰。可是第二次老瞎子却说:“天兵天将也看不出哪个是玉皇大帝的儿子,于是封上了所有人的眼睛。”这个看似晦涩难解的寓言用史铁生的论断去解释再贴切不过——“健全人也有局限,这些局限也送给他们困苦和磨难。很难说,健全人就一定比我们活得容易,因为痛苦和痛苦是不能比出大小来的,就像幸福和幸福也比不出大小来一样。痛苦和幸福都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那完全是自我的感受”,“所以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我们毫不特殊”[6]50。电影中面店老板一家的生活简单而机械,生活的重心整日围绕着劈柴、生火、和面、下面展开,除了劳作的声响只有家中傻儿子的痴笑能打破这可怕的沉默。很难说这一家人的生活比老瞎子师徒二人苦练琴技、怀揣希望、相依为命的生活更为幸福圆满。
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上的残疾,或是肉体,或是精神,当这一老一少走进人群,他们并没有比别人更加“残疾”。当他们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平等”,自然也就感受不到因身份认同错位带来的焦虑和痛苦。那么,他们的精神困境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前提,这或许是影片《边走边唱》给出的最诗意的答案。
(三)“爱”的救赎
《边走边唱》中老瞎子和小瞎子都以“爱”的方式找回了自我。在老瞎子身上,“爱”的救赎体现为以下三点:一是情欲,二是母爱,三是自爱与爱人。首先是情欲。“现代性标明这样一个事实:感性肉体取代了理性逻各斯,肉体的解放成为‘现代性运动’中的重大母题。”[7]335肉体解放也暗合了《边走边唱》对于情欲的处理。在老瞎子病中,兰秀贴在老瞎子的胸口,他将兰秀幻想成了面店的老板娘,以梦境的形式释放了自己的情欲,缓解了病痛。自然情欲的释放让老瞎子缓解了长期以来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病态压抑,揭示了肉体解放的救赎主题。其次是母爱。当老瞎子得知无字白纸的真相之后,在面店抓起了老板娘的手,老板娘不仅没有挣脱,还将其揽入自己的怀中,像怀抱婴儿一般抱住了老瞎子。母性的光辉在这一瞬间冲淡了情欲的色彩,老瞎子像个孩子一样在母亲的怀中得到安慰。在这场真实的情感释放中,老瞎子仿佛寻回了他生命中长期缺失的一个重要角色——母亲。母性治愈也成为电影阐释人类精神困境救赎途径的重要主题。最后是自爱与爱人。老瞎子在琴弦断裂的情况下用自己的歌喉完成了生命的绝唱,以自爱的方式找回了他作为一个盲人琴师的价值。他将小瞎子视为自己的儿子,将兰秀当作自己的儿媳,化解了师徒不和,以爱他人的方式圆满了自己的一生。
小瞎子“爱”的救赎之路则更为激进和叛逆,他的“爱”里带着强烈的自尊,是一种对世俗和蒙昧的反叛,带有启蒙和“青春式叛逆”的色彩。在与世俗的对抗中,他相继失去爱人(兰秀)和亲人(师傅),在失去爱的绝望中仍不向命运低头。小瞎子决定一根根地弹断琴弦,用自己的方式来“睁眼看世界”。他不盲从,带着充满爱意的风筝和师傅的期望继续前行、边走边唱,踏上了反抗命运的救赎之路。
结语
《边走边唱》在角色的设定上负载了新的文化想象和批判。围绕视力残疾的师徒二人展开矛盾冲突,在不同价值体系的对抗和反思中肯定了挑战世俗的“青春式反叛”,在荒诞的氛围中抨击蒙昧的文化弊病,以“爱”的救赎的方式完成了对于人类精神困境(“残疾”)的文化想象。
电影《边走边唱》呈现出压抑、晦涩、叛逆和感伤的调性。以师徒二人不同的人生走向和命运结局共同构建了电影的美学追求——求而不得的缺憾之美,生而无畏的叛逆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