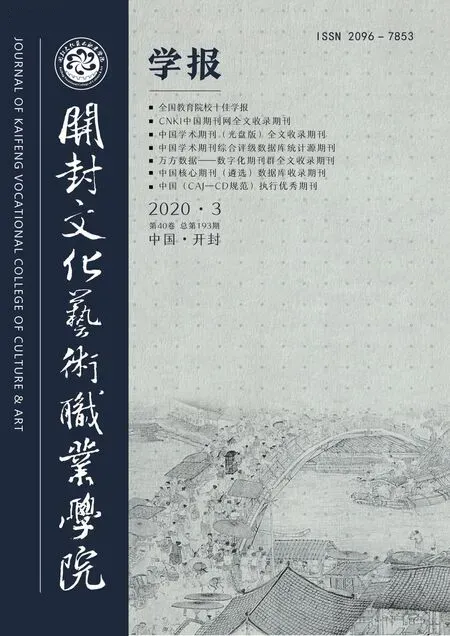归去来兮
——陶渊明之“见”的感知现象学分析
郭广新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 文学院,云南 丽江 674100)
一、陶渊明之“见”
陶渊明《饮酒五》有一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然而,在梁萧统《昭明文选》中收录的最早的陶诗却是,“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到了宋代,苏东坡认为,“望”字应作“见”,他在题跋中写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改意,此最可疾。”[1]132苏东坡之后,人们大多追随苏东坡的看法。不过,到了清代,又有人持相反看法。清朝何焯就质疑说:“就一句而言,‘望’字诚不若‘见’字为近自然,然山气飞鸟,皆望中所有,非复偶然见此也。‘悠然’二字从‘心远’来。东坡之论不必附会。”[1]132但笔者认为,何焯忽略了后面的“飞鸟相与还”中还有一个“还”字,正是这个还字使得“山气飞鸟”虽然好像是望中所见,但也应该是偶然见出的,如此,后面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也才得以成立。斯人已逝,又缺少文献佐证,望或见很难确定。笔者在这里依据法国学者梅洛·庞蒂的视觉理论,认同苏东坡的说法,原因是“见”字才能显出“真意”,“相与还”才能显出“真意”。
二、“见”的传统视觉文化阐释
“见”首先是指一种视觉,但是,关于视觉有多种情况,也有多种解释。从文化哲学方面来看,视觉基本有两种,一种是经验主义的,或者现代科学的,认为视觉是客观事物对眼睛的刺激在大脑中留下表象;另一种是现代哲学或者心理学的,认为视觉是主体对客观事物的构造。虽然这两种对视觉的解释不一样,但都是建立在主客二元对立的基础上,都属于一种认识性的看。这两种视觉的目的都是想要抵达事物,透视事物的本质。
认识性的视觉是单向性的,它由主体发出,并始终朝向客体。在这里主体是主动的,客体是被动的,客体等待着被看、被认识,主体自信地以为通过看获得的表象就是客体的真实反映。虽然到了近现代哲学,开始质疑这种客观反映论,认为表象只是主体的构造,如康德的先验主体对客观世界形式的赋予,胡塞尔的先验主体让客体在意象行为中的呈现,但是,它们仍然隶属于认识论,目的仍然是要去认识世界,主体仍然对客体具有主动性,视觉仍然是主体朝向客体的。
这种认识性的视觉文化,孕育出了许多相应技术。比如,天文学领域的望远镜,生物学领域的显微镜,医学领域的CT和核磁共振,生活领域的监控录像。望远镜的发明是为了将人类的视线伸向宇宙的深处,直接看到宇宙的生成演化;显微镜的发明是为了将视线渗入最细微处,察微知著,通过对微观世界的直接观察把握世界的真相;医学领域的CT和核磁共振的发明是为了让视线穿透人的肌肤,透骨露髓,直接看到体内的病情所在;监控录像的发明是为了看清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细微举动,了解社会真相。这些视觉技术无一不是带着一种认识世界的冲动。它们都是使视线进入事物,照亮事物,使事物的本质能够显露出来。
从认识性的视觉文化看来,认识性的视觉不仅能够通过将主体的视线朝向客体获得事物的本质,而且能够将获得的本质用数据、图例和语言加以准确描述,将本质准确传达出来。
认识性的视觉文化不仅体现在一些视觉技术方面,还体现在西方的一些古典艺术和现实主义艺术等写实艺术方面。写实性艺术往往把艺术称为一面镜子,认为艺术可以反映现实,现实生活能够在这面镜子中得以逼真呈现,透过艺术这面镜子可以让人们看到生活的本质。这面镜子在反映现实时虽然往往是从某个角度来叙述或者描绘的,但写实主义的艺术家们总是把在某种固定的角度呈现出来的内容误以为真。
如果用这种认识性的视觉理论来解释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见”字的话,那么主体的主动性、主体对客体的单向性以及所见的可言说性都将会被突出出来,诗歌意义好像就是,陶渊明有意地抬头去看南山,把自己作为看的主体,把南山作为窥视的对象,努力地去贴近南山,当然按理也能够把南山加以抽象的言说,但这明显与后面的“欲辩已无言”相矛盾。所以,见字理解为认识性的看是不合适的。“望”字带有很强的主动性,“悠然见南山”也不应该是“悠然望南山”。
三、“见”字的感知现象学分析
认识性的视觉一直以来是视觉文化的主流,但在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看来,这种带有功利性的视觉不仅无法帮助我们探究事物的本质,反而会遮蔽存在。
梅洛·庞蒂认为,真正的存在不是抽象的本质,而是一个比本质世界还更原始的原初世界。原初世界是一个身体处身于其中的世界,身体根据自身的处境探测周围的空间,构造上下、左右、前后。梅洛·庞蒂写到:“承担某一视点的主体,作为知觉与实践场的我的身体,是有某种所及范围的我的动作,它将所有我熟悉的物体划入我的领域。”[2]101这就决定了,身体往往只能从一个有限的视角感知事物,只能感知到事物的部分侧面。身体只有不断变换视角才能丰富完善对一个事物的整体感知。梅洛·庞蒂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中把知觉的身体界定为拍摄世界的蒙太奇,他说:“拥有感官,例如拥有视觉,也就是拥有我们因此而能够接受被给与的一切视觉组成的、可能的各种视觉关系的一般的蒙太奇。”[3]50但空间是广大的,视角是无穷的,我们永远也无法穷尽所有的视角,身体也永远无法达到对事物的整体感知,身体总是从一个视角过渡到另一个视角,向着未知视角不断地开放,未来的不可知性让每一个视角的感知实现的同时也不断地否定它。梅洛·庞蒂把这种感知的特点称为可逆性。
所谓可逆性,就是身体在感知的同时也在被感知。梅洛·庞蒂称,在现实生活中会有一种现象,即当用右手去触摸正在接触某物的左手时,左手会在一瞬间回过来接触那只正在接触某物的右手。梅洛·庞蒂称这就是可逆性。可逆性不仅体现在触觉中,而且体现在一切感知中,包括视觉,在看中也存在看者与被看者的可逆性。在梅洛·庞蒂的知觉世界中,看无能为力把客体对象化,因为当目光送出的同时,总是会受到一种抑制,这种抑制来自不可见,看在不可见面前总是会受到一种阻力,这种阻力让被看者从对面迎来。不可见驱使人去看,但不可见又无法对象化,它会让看者感到失落,给看一个逆向作用。正是因为事物永远无法被看尽,也正是因为不可见的存在,才使得被看者向看者显现,不可见的不可见性又使得看者向被看者显现,就像互看一样。梅洛·庞蒂在著作中经常喜欢引用一个画家安德烈·马尔香的一段话:“在森林中,我多次感到并不是我在观看森林。有些日子,我觉得是树木在盯着我,与我搭讪……”[4]120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中的视觉与梅洛庞蒂的可逆性的看非常接近。关于“悠然见南山”,日本汉学家井上一之曾经专门著文考证过,他认为,要想解决历来的有关“见”“望”的争论,就要弄懂“悠然”的意义,因为悠然是后面视觉词的修饰词。井上一之认为“悠然”解作“自得”是从清代吴淇《六朝诗选定论》开始的,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凡是表现“自得”之感用的都是“从容”“晏然”“恬然”和“淡然”。另外,井上一之认为,“悠然”是东晋出现的一个新词,在陶渊明之前和之后的诗中,“悠然”多解释为“远”,所以陶诗中“悠然”解作“自得”可能性不大。井上一之还通过研究认为,陶渊明重视传统,所以“悠然”也应该继承了“悠”和“悠悠”的传统意义,即“忧思”。在此,笔者认同井上一之的说法,“悠然”首先解作“远”。陶渊明受道家文化影响非常大,道家创始人老子曾说:“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5]62“反”历来被解作“返”,即返回的意思。所以,“悠然见”不是远远地看见,而是在远看南山的同时南山又不断地回来迫近诗人,在南山迫近诗人的同时南山又远离了诗人。就像梅洛·庞蒂的可逆性视觉一样,事物的不可见性诱惑看者努力地去看,让看者的目光伸向远方,但不可见使得看者永远无法抵达事物,就会对伸向远方的看产生阻力,这种阻力就体现为目光的返回,似乎目光又从对面射了过来。在这种情况下,看者与被看者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目光在两者之间交叉。于是,看者对被看者就会产生似远实近,似近又实远的体验。
这种体验其实是陶渊明对一个本真存在的世界的感受,在这个世界中,陶渊明遭遇的不是客观的南山,而是携带有不可见性的南山,南山的不可见性自然带来一种旷古的忧思,南山的难以抵达无法穷尽也自然会让陶渊明“欲辩已忘言”。至于清朝何焯认为山气飞鸟是望中所得,但诗中一个“还”字已经说明,这仍然是一种可逆性的看,而不是单纯的“望”。
结语
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并非认识论意义上单向地看见南山,而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见”到南山,他在这种可逆性的“见”中,在一种“悠然”的或者忧思的情绪中,抵达了一个更加原初的存在世界,一个互动的世界,一个自然自在的、澄明的、诗意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