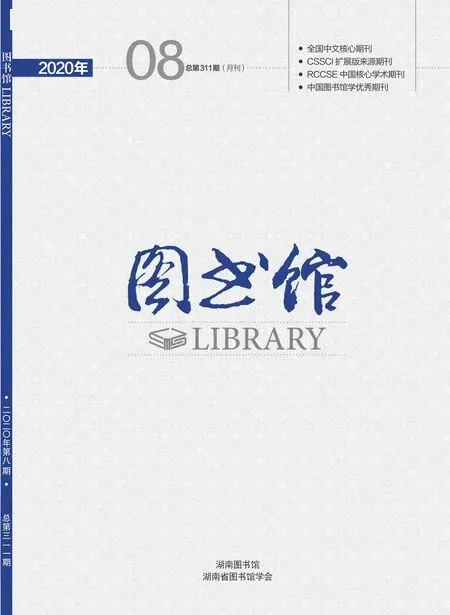我国传统书院读书法的传承与衍变
——以历代书院学规为中心的考察*
邹桂香 高俊宽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江苏苏州 215123)
1 引言
书院作为一种相对自由独立的教育机构,在我国教育史上存续近千年,形成了不少影响深远的教育体系和方法。纵观整个书院教育史,不少书院都制定有学规,亦称学约、学则、教约、揭示等,规定学生立志为学、修身处世、待人接物、读书治学的基本要求,成为书院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曾把学规的内容归纳为三大类,其一就是指示读书、治学的门径和方法,“多是山长半生攀登书山,畅游学海经验的总结,皆为肺腑之言”[1]1,实质上形成了一种独具中国本土特色的书院导读方法体系。尤其是阅读经史、背诵经典作为我国传统教育模式最基础的环节,对生童学子阅读方法的指导尤显重要,影响至深。其中“朱子读书法”影响最为深远,亦称“朱子读书六条目”,不仅是我国教育史上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也是阅读文化以及传统读书法研究的应有之义。
所幸学界对书院学规学约等此类特殊文献,已经进行了相对完整的辑录和整理,如《中国书院学规》《中国书院学规集成》及《学规菁华》等,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性资料。学界对“朱子读书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朱子读书法”在当代的现实意义,对当前中小学生阅读教育的意义,以及读书对立身强国的重要性,如叶梦婷的《读书是立身强国之要》等[2]。鉴于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与“朱子读书法”之间密切的继承关系,学者李晓宇《朱子读书法六条的传衍与变异》,关注到“朱子读书六条目”在后世的衍变情况[3];对历代书院学规中的阅读法和导读活动进行宏观考察的研究尚付诸阙如,有待深入。文章在梳理我国历代书院学规学约的基础上,结合学界既有研究成果,分析“朱子读书法”的内涵,探讨其在不同时期书院教育中的衍变与传承规律,发掘朱子读书诸条目在现代各级学校教育中的现实价值,以及对当前青少年的经典阅读、大学生群体的研究型阅读,乃至当代复兴的书院教育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
2 “朱子读书法”在书院教育中核心地位的确立
南宋时期,书院大兴,并逐步形成系统完整的书院教育理论,以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为代表,亦称《白鹿洞书院学规》《白鹿洞书院教条》,提出修身、处事、接物的基本要求,确定了“博学、审问、谨思、明辨、笃行”的为学顺序,该揭示与“朱子读书六条目”成为后世各类书院和学校教育的总纲领,影响深远。
2.1 “朱子读书六条目”的形成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世称朱文公,祖籍徽州府婺源县,是宋代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在我国教育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朱熹一生与书院关系密切,曾在多地书院讲学,与其有关的书院遍及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等地。尤其重要的是,他对读书理论和读书方法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如《观书有感》《读书之要》《沧洲精舍谕学者》等,尤以后人据其言论整理出来的“读书六条目”影响最深。据李晓宇考证,传世的“朱子读书法”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汇编朱子文集或语录中论读书法的内容,如宋黎靖德《朱子语类》中的“读书法”,清李光地等纂修的《御纂朱子全书》中的“读书法”“读诸经法”“论解经”“读史”“史学”等,以及钱穆《朱子新学案》中的“朱子论读书法”。另一类是将朱子论读书的内容和方法,总结成六条纲目体的四字成语,如宋代辅广辑录、于和之校刻的《朱子读书法》,以及张洪、齐熙对辅氏原本“搜集附益,更易次第”而成的“朱子读书六条目”,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纲简目详,便于记忆,在书院学规中最为常见,文章所述的“朱子读书法”即指“朱子读书六条目”。
2.2 朱子读书法的内涵
朱子读书法诸条目,不同版本的次序略有不同,各书院学规的引用也互有差异。读书法的主要内容为:①循序渐进:读书要有先后顺序,先读经,后读史,又要先易后难,每本书也要有诵读考索之序;读群书也要有先后缓急之序。②熟读精思:读书要熟读,达到成诵才算是精熟。只有熟读玩味,方能道理自现,才能达到从无疑到有疑,再由有疑到无疑的境界。③虚心涵泳:读书必须虚心平气,沉潜静心,反复玩味,时间久了自会晓得文中道理。此条与熟读精思条有异曲同工之妙。④切己体察:读书应该“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各自尽于燕闲静一之中”[4]122,所谓的学以致用,首先应用在“成己”上。⑤着紧用力:也是重要的治学方法,即“为学会刚毅果决,悠悠不济事”[4]132。治学必须要抖擞精神,专一用工,痛下工夫,达到饥忘食渴忘饮的境界,切不可虚度时日。⑥居敬持志:读书要定心静坐,摒弃闲思乱想,心如止水明镜,即“须将心贴在书册上,逐字看得各有着落,才能悟得道理分明”[4]138。读书六条目不仅是读书的方法,也是治学所应持的态度,被纪昀称为“条分缕析,提纲挈领”。元明乃至清前期,理学和心学成为学术主流,学者多推崇朱子的“主敬”“静澄”“体察”之法,对“朱子读书法”确信无疑,认为沿此正确路径,必有大进境,绝大多数书院读书规程的核心即是“朱子读书法”。
2.3 《读书分年日程》对朱子六条目的细化
程端礼(1271—1345),字敬叔、敬礼,号畏斋,元代庆元(浙江鄞县)人,“端礼独从史蒙卿游,以传朱氏明体适用之指,学者及门甚众”[5],作为朱子后学,程端礼自然会关注朱子读书法。他曾于集庆江东书院讲学,在《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中对朱子读书六条目有详细的体认和阐释。元顺帝初年,程端礼刊刻《读书分年日程》,把读书分为八岁入学之前、八岁入学之后以及十五岁以后三个阶段,以循序渐进为主线,详细规定了读书的顺序、具体方法和时间分配,被称为从童蒙到成人的课程规划,其中的“日程节目,主朱子教人读书法六条修。其分年,主朱子宽著期限、紧著课程之说修”[6],明确与朱子读书法的关系,其主旨精华皆得自朱子,即所谓“欲穷理先须读书,而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又在于居敬而持志”[7]。该日程对每本书的读、温、背均有规定,并有“读经日程”“读看史日程”“读看文日程”“读作举业日程”等日程空眼簿式,以记录读书的起止日期,类似于每日课程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虽然是为家塾童蒙读书而作,但对当时及后世整个教育系统的阅读指导影响甚巨,不少书院学规中时能见其踪迹,亦出现不少效仿之作,但始终传承着朱子读书法的精髓。
3 “朱子读书法”在书院教育的传承与影响
朱子读书六条目提纲挈领,指明了士子读书治学的基本门径和方法,《读书分年日程》对读书六条目加以系统细化,构建了读书治学的详细框架,后世整个公私教育系统的读书治学之法均未能脱其窠臼,亦被书院奉为圭臬。
3.1 书院对“朱子读书法”和《读书分年日程》的融合
朱子读书六条目简明扼要,不少书院选取其中若干条或稍加变动而成为学规的一部分,明成化元年,李龄在江西鳌洲书院拟定的《规示诸生八事》中,即提出“读书必循序,不可躐等,先读《小学》,次读《四书》《五经》及御制书、史、鉴,各随资质高下”[1]632。与朱熹素有渊源的白鹿洞书院更是一脉相承,明万历年间,葛寅亮在《白鹿洞书院课语》中,指出“学以渐博而相通,心以积疑而起悟,默坐静心为第一要义,读书惟取炼心,屏居静室”[1]663,对朱子读书法的融合清晰可见。光绪中期,邵松年在开封主持制定的《明道书院日程》中“登记法”“结总法”“师评法”,均是对朱子读书法的衍变。
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问世之后,不少书院学规更是直接引用,形成了一个读书治学的指导体系,把朱子读书法中的若干条目,与程氏读书分年日程中的严日课,订立读书计划结合在一起,出现“朱子读书法”“白鹿洞规条”与“分年读书之法”相伴而行的情况。《读书分年日程》不仅作为书院生童的读书指南,亦成为书院的课程表,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清代前中期,当代学者徐雁平曾著《〈读书分年日程〉与清代的书院》一文专门探讨[8]。康熙年间最为突出:汤来贺订《白鹿洞学规》于“潜心读书”条,注明“学者或仿先儒分年之法,每年读一书,又推其意而为分月之法,每月读一书”[1]675。罗京作《白鹭洲书院馆规》,于“诵读”条下明示“各宜自立日课簿,每日或看经书若干,或读时文若干、古文若干,以及论表策判若干,《通鉴》《性理》各书若干”[1]736。张伯行订立苏州《紫阳书院读书日程》认为:“人生一日不读书与读书而无法程,虽勤惰不同,其为失则均也。”[1]253其通经、读史、作文的思路与程氏日程大致相似,要求生徒对每天所读所得以笔记之,亦同程氏之法。邵廷采订立的《姚江书院训约》中“读书宜进”条,所倡读书之法与《读书分年日程》接近。沈起元在娄东书院掌教时,曾订立教规,顺序同程氏《读书分年日程》,在读史、作文方面更有类似之处。乾隆初年,陈宏谋作《豫章书院学约十则》,提出要“熟读精思,从容详味,然后及于传注,然后及于诸说,平心静气,以求其解”[1]615。时至道光年间,王涤心在《菊谭书院学约》中仍提出“我辈今日为学,必学孔子,欲学孔子,必学朱子”[1]975,足见“朱子读书法”影响之深远。
3.2 对书院藏书的引领和导向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朱子读书法”及《读书分年日程》中所提到的阅读书目,不仅得到了当时读书人的一致推崇和认可,并且成为众多书院的藏书目录,引领书院藏书的主流,因此有学者将程氏《读书分年日程》视为推荐书目,自有其合理性。斛泉在《崇正书院条约》的“书籍宜购求”条中,认为书之购藏“宜切遵程氏《分年日程》所载,并国朝所定经史性理治道制度等书”[1]975,成为书院藏书的导向。除了被列为必读书目的儒家经典及史学文献之外,对道家、佛家、小说、文集,以及淫词、艳曲、戏文类图书则予以排斥,不少学规戒条中明令禁读一些书籍。明嘉靖年间,高贲亨订立的《洞学十戒》中的第八戒即“观无益之书,谓如老庄、仙佛之书及《战国策》,诸家小说、各文集,但无关于圣人之道者皆是”[1]649。明万历年间,冯从吾订立的陕西关中书院《士戒》:“毋看《水浒传》及笑资戏文诸凡无益之书。”乾隆初年,陈宏谋在《豫章书院学约十则》中,亦认为应该抵制“淫词艳曲,尤宜焚弃,不宜寓目,倘留案头,便是不祥之物”[1]615。清嘉庆年间,梁廷柟在广东《粤秀书院学规》中指出:“非圣之书勿读,无益之文勿观”。道光朝中期,王寿天在《柏香书院详定章程规约》中规定:书籍除“十三经”及诸史之外,其余淫词、艳曲、小说杂流与一切消闲谴兴等,概不准携带入院。盖潜修一室,当勉附圣贤之林,是禁邪书,即所以遏人欲于将萌也[1]1580。这些学规中读书范围的禁约,基本上与当时政府的禁书政策相一致,明确规定生童学子只能阅读书院所规定的“圣贤书”,以巩固儒家传统经典的地位。长此以往,学子的视野日渐狭隘和固化,书院教育的自由、独立和研究精神受到禁锢,创新意识受到摧残,官学化、科举化的倾向日益严重。
3.3 晚清书院对朱子读书法的调适
清中期以来,随着实学和新学的兴起,以及教会书院在中国本土的成立,传统书院的教育模式受到冲击。同光年间,在部分学政及抚疆大吏的推动下,一些新型书院成立,部分书院逐步突破僵化的教育模式,提倡读致用之书,如龙门书院、格致书院、中西书院等。1870年,刘熙在《龙门书院课程六则》的“勤读书”条指出:“至百家之书,有足发明经史及有关学问,经济者,各随其能而博览焉。然后以余力学为文辞及科举之业。”[1]118虽然仍以传统经史为主,但已经开始鼓励学子们开阔阅读视野,关注经济致用之学,同时把文辞科举放在末位,出现了重要的学术转向。光绪年间,随着教育改革的思潮兴起,书院教育改革的步伐加快,朱子读书法及读书分年日程在有限的范围内得以调适。1874年,张之洞在成都建尊经书院,并编撰《輶轩语》,提倡应读有用之书,以考古、经世、治身心[9]。其“语学篇”指出读经、读史、读诸子、读古人文集的为学之道,仍试图把读书为学调控在中国传统学术范围内;“劝学篇”则指出先中学、后西学的学习顺序,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彰显其对中国传统文化阵地的坚守。此后,张之洞又编纂《书目答问》以指导青年学子阅读传统经典。著名学者王先谦于1894至1903年间主持岳麓书院,注意时务,倡导新学,设立算学和译学,他在1897年《岳麓书院月课改章手谕》中指出:“若如今尚复自封故步,专侈游谈,岂不轻朝廷而羞当世之士耶?”[1]1061开启了我国书院的近代化变革历程。此期还出现了涵括新内容的《读书分年日程》的仿效之作,如1897年梁启超编撰的《读书分月课程》和《读西学书法》,以求读书要随世变的大环境相适应,满足学子们快速学习和吸收中西方知识的需求。在清末新型的书院中,各类分科的课程表,逐渐取代僵化的《读书分年日程》,读书方法的指导也大幅减少。随着清末学制改革和书院改制,被推崇近千年的朱子读书法最终淡出各级学校教育的视野。
4 朱子读书法在书院的传承特色
朱子读书法以程朱理学为核心,与主流学术思潮相呼应,为后世历朝统治者所提倡,同时强调读书为学先要立志静心,才能涵化气质,提升修养,并在各书院山长和著名学者群体的助力下,在书院得到广泛的传衍推广,弦歌不绝,彰显其鲜明的传承特色和规律。
4.1 以理学为核心与主流学术相辅相成
南宋以来至清前中期,政府统治以新儒家思想为基础,学术领域亦以理学和心学为主流,统治者的提倡加上学者群体的推崇,故此以经史为主要阅读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中心的“朱子读书法”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坚若磐石。明嘉靖年间,乌从善在《博陵书院条约》中规定:“《四书》以外,当读《五经》。实相源流,俱不可不读。若濂、洛、关、闽诸书,甚是透辟,有功圣门,吾人并当读究,最有裨益。”[1]825康熙年间,李来章在《南阳书院学规》中制定了为学次序、读书次序,即以《小学大全》《近思录》《伊洛渊源录》《续近思录》《四书语类》《理学正宗》《性理大全》等理学典籍为主,以四书五经为首选阅读文献。“朱子读书法”经过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的细化后,在“存天理,遏人欲”的教条下,极少有经世之学的提倡,四书五经之外,几乎无书可读,缺乏新鲜血液的输入,局限了思维和创造性,书院逐步沦为科举与时文的附庸。如前文所述,清朝中后期,虽有个别书院与时俱进,适时改革,但多数书院仍固守教条。如光绪年间,刘光贲在陕西《味经书院教法》中仍坚持:“四书,群经之心法也。而《大》《中》章句,《论》《孟》集注,朱子生平精力悉萃于此,剖析疑似,辨别毫厘,学者尤当于大义微言,求其根本。今定日日熟读精思,沉潜涵咏。又宜兼读《近思录》《北溪字义》《性理精义》及各家语录,参互研究,则必于身心性命之理豁然有得矣。”[1]1660在清末激进速成的教育思潮的推动下,书院的教育改革显得迟缓和落后,最终只能在教育改制的呼声中无奈谢幕。
4.2 读书首要立志以达到变化气质的效果
朱子读书法注重个人体验,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格物穷理以致知,即立志后方可读书。故此,“立志”“务本”“专一”成为众多书院学规的首要规条,是读书为学的基本条件。元朝至正年间,拱辰公所的《孔宅书院学规》中即有言:“学有体要,一曰立志,吾人为学必须立志,后此功力,视此以为准。如矢之赴的,水之趋壑。若志不先立,悠悠忽忽,醉生梦死,过却一生,大可哀矣。……一曰穷理,讲求经义,论断史册,或验之于应事接物,或证之于沉思默会。……程子格物十九条,穷理之方尽矣。”[1]157即所谓“为学莫先于穷理,理穷必在乎读书”。清道光年间,张梧冈的《钟吾书院学规》仍坚持认为“志定,而后用功次第,可循序而进,澄怀静验,当自得之;非亲切体认,则言之皆成糟粕”[1]301。多数学规把读书立志与切身体认融为一体。读书为学的效果,即修身养德与涵化气质。康熙年间赵士麟在《正学书院会约》中指出:“学以变化气质,求至于圣贤之道也。……立志,学莫先于立志。志不立则学鲜有成者,有必为圣人之志,而后有求于圣人之学。”[1]44乾隆时期,王文清在《岳麓书院学箴九首》中提到:“力学何为,变化气质。气质有偏,好恶斯辟,惩忿窒欲,式砭其疾。”[1]1048道光年间,程家颋的《墨池书院学规》指出:书院所以培植人材,读书所以涵养德性、变化气质[1]996。具备“修齐治平”的心胸和“内圣外王”的气质学养,也是传统社会培养人才的重要标准。
4.3 山长及学者群体助力朱子读书法的传衍
朱子读书法注重循序渐进,涵泳虚心和个人体味,在性理之学盛行时期,影响并造就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和山长群体,他们在切身体验的同时,甚或出现一些颇具神秘色彩的个人体验和顿悟。
清代前中期,书院得到繁荣发展,也是朱子读书法和读书分年日程发展的高峰,陆陇其不仅重刊了程氏《读书分年日程》,认为“《读书分年日程》非程氏之法,乃朱子之法;非朱子之法,乃孔孟以来教人读书之法”。而且在书院讲学时多次发挥朱子读书法的内涵,在其《风池书院课艺序》和《闽中校士录序》中有集中体现。嘉庆年间,沈维鐈任湖北学政时,也刊印了程氏《读书分年日程》,他晚年主讲杭州敷文书院、松江敬业书院,朱子读书法借此途径得以推广。著名学者陈鹤晚年掌教江宁尊经书院和钟山书院,在《答李平川书》中亦阐释读书用功之法:“元儒作《读书日程》。先四书,次诸经,次《通鉴》,次古文之不诡于道者,与夫考证论辨之切于治道制度身心日用者,而要之学以道为志。人以圣为志,此其书可取以为用功之法也。”[10]山长及学者群体结合自身的读书实践,着意发挥朱子读书法的内涵,进行诠释和解读,形成名目繁多但旨趣相仿的各类学规,朱子读书法则藉由书院这个平台,得以绵延传承。
5 结语
“朱子读书法”、《白鹿洞书院揭示》与《读书分年日程》,在书院教育及书院精神的传承过程中,实质上形成了一个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整体,也成为后世书院学规的核心。以南宋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不再拘泥于经学名物的考据和文字训诂的传统,对儒学的核心要义进行符合时代精神要求的再解释,强调基于独立思考基础上的“微言大义”,即从“六经注我”转向“我注六经”。这种疑古改古的新精神,并鼓励在阅读过程中对经典文献的质疑问难,对当前提倡的大学生群体的研究(阐释)型阅读,颇有值得借鉴之处,在当前的研究型阅读中仍然适用。朱子读书法中的“循序渐进”“熟读精思”“着紧用力”等条目,提倡对文献的熟读、诵读和精读,对于当前青少年群体的经典文献阅读,仍不失为重要且有效的方法,至今仍有着广泛的影响力。20世纪20年代胡适先生在其《书院制史略》中把我国的书院精神概括为自由、独立、研究三大精神[11];80年代,季羡林先生的《论书院》把书院教育总结为六条经验[12],指出书院教育对于现代教育的意义。值得欣慰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书院教育出现复兴的浪潮,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书院,活动频繁,仍在赓续着书院教育传统,书院精神仍然吸引着教育、文化、学术界的注意力。不少高校成立独立的书院,开展博雅和人文教育,汲取传统书院教育的精髓。一些具有深厚人文积淀的中学,也重拾书院教育的精蕴,开始实行书院教育的构想和尝试,其中仍能看到朱子读书法精髓的延续和传承,令人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