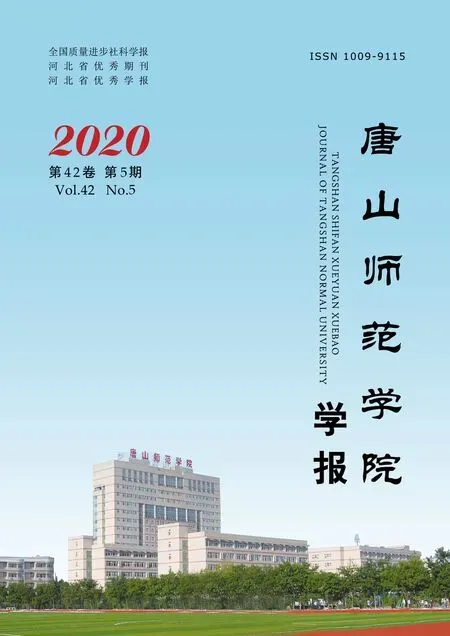莫言八九十年代的乡土小说的叙事策略——农村真相的还原与淡化
曹金合
莫言八九十年代的乡土小说的叙事策略——农村真相的还原与淡化
曹金合
(洛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934)
莫言从历史的风尘步入现实的纷纭复杂、气象万千的日常生活的空间的时候,首先建立了与故乡的紧密联系。莫言21年乡村生活的摸爬滚打使得他对乡村生活的文学反映,采纳的是对乡村的诗意浪漫色彩尽情剥离之后,展示出的困苦、贫乏、肮脏、污秽的真实生活景观的原生态还原策略。但他对某些距离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比较远的不尽如人意的生活现状也采取了淡化的叙事方式,这就形成了莫言不同于其他乡土作家的独特风貌。
莫言;八九十年代;乡村小说;还原;淡化
莫言从历史的风尘步入现实的纷纭复杂、气象万千的日常生活的空间的时候,首先建立了与故乡的紧密联系:“虽然我身在异乡,但我的精神已回到故乡;我的肉体生活在北京,我的灵魂生活在故乡的记忆里。”[1]高密东北乡作为祖先的血地和自己生于斯、长于斯、最终也将葬于斯的血缘纽带一直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对改革开放以来方针政策的变化带来的农村现实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风貌的变化,莫言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小说中一直予以跟踪描述,有时为了表达自己对现实生活中的官僚主义、部门主义、教条主义、不正之风等伤害无依无靠的底层民众的切身利益的愤恨之情,甚至不顾小说不能与政治和社会现实生活太靠近的艺术创作规律的禁忌,而采取了急就章的方式。当然,莫言也知道采纳文学的“无用之用”的功能来介入和干预现实社会的梦想是太天真了,具体的方针政策的细微变化对民众的社会生活发生的立竿见影的影响与文学对民众的精神生活进行的潜移默化的渗透所起的作用不可同日而语。况且用文学的方式直接干预政治的后果导致的艺术的直白还在其次,文学的“反干预”风险倒是主流意识形态借助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2]轻而易举就能达到的警戒效果。所以,莫言对农村中的现实真相采取了相应的叙事策略来遮蔽某些原生态的风貌。
尽管莫言采用主观化的调侃口吻,对建构高密东北乡的文学共和国野心勃勃:“我应该举起‘高密东北乡’这面旗帜,把那里的土地、气候、河流、树木、庄稼、花鸟虫鱼、痴男浪女、地痞流氓、刁民泼妇、英雄好汉……统统写进我的小说,创建一个文学的共和国。当然我就是开国的皇帝,这里的一切都由我主宰。”[3]从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反映关系来看,文学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的升华作用对莫言八九十年代的创作同样适用。但莫言21年乡村生活的摸爬滚打使得他对乡村生活的文学反映,采纳的不是知青那种肤浅的体验方式,也不是借鉴文人那种春风得意之后的急流勇退,或者是仕途失意之后的韬光养晦而采取的归耕陇亩式的田园生活方式,而是对乡村展示出的困苦、贫乏、肮脏、污秽的真实生活景观的原生态还原。在《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的创作谈中,莫言将他对现实生活中的农村刻骨铭心的心理感受表达得淋漓尽致:“十五年前,当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高密东北乡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时,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仇恨。它耗干了祖先们的血汗,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我们面朝黑土背朝天,付出的是那么多,得到的是那么少。……”[1]所以当他把贫困的乡村生活的创伤性记忆转化为对乡村土地的描摹的时候,就出现了《欢乐》的中学生齐文栋偏执的价值判断和情感色调:“我不赞美土地,谁赞美土地谁就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我厌恶绿色,谁歌颂绿色谁就是杀人不留血痕的屠棍……”[4]这样的情感与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5]显然不是在一个层次上的。莫言面对着贫瘠荒寒的土地对个体的生命吞噬的彻骨的悲凉和恐惧感受,所描绘的令人颤栗的乡村现实显然与主流文化的宣传有比较大的差距,所以他对某些距意识形态的要求比较远的不尽如人意的生活现状也采取了淡化的叙事策略,这就形成了莫言不同于其他乡土作家的独特风貌。
一、乡土社会的宿命意识和迷信观念的真实表露
偏僻落后的乡村形成的未受现代文明浸染的宿命意识和迷信观念是现实中的乡土社会比较明显的表征,讲究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宗法社会在安土重迁的恋乡情结的作用下,会在狭小的圈子里形成封闭保守的观念。许多的自然事物和现象在无法得到科学解释的情况之下,就为迷信观念的登场提供了舞台空间,荒寒的生活环境和代代遭受的苦难生活所形成的宿命意识也就成为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法。这样的生活现状和思想观念在莫言反映乡村现实的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球状闪电》中的茧儿只是一味地按照传统的贤妻良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恪守的勤俭持家以实用为标准的朴素的审美观念与丈夫所要求的开放大方、注重形象的衡量标准显然有太大的差距,自己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之后,只好用“哭也不顶事,命中没有莫强求,胡思乱想不中用”[6]来自我安慰。《天堂蒜薹之歌》中的高羊(羔羊的谐音)之所以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成为被侮辱被践踏的弱者,却还能怡然自得、知足常乐,靠的也是宿命意识:“都想好,孬给谁?都想进城享福,乡下的地谁来种?天老爷造人的时候使用了几种材料,高级的为官为相,中级的当工人,低级的当农民。像咱这道号的,都是下脚料做的,能活在世上为人,就是大福气。”[7]宗法制文明中的等级观念和官本位对民众的无情盘剥所造就的宿命意识,并没有在现代文明的民主、平等观念的冲击下退出历史舞台,相沿成习的自我糟践和自我安慰成为培养和传播宿命意识的温床。所以他看到四叔家的两个儿子都还没有娶上媳妇、日子过得比较恓惶的时候,安慰四叔的话:“人比人要死,货比货要扔,咱只能跟叫花子比,虽然穷,还没吃了上顿没下顿,穿得破,还强似光腚。日子不顺心,身体还健康,有点瘸腿拐胳膊,还强似得了麻风病,您说是不是四叔?”[7]这就是乡村社会真实的生活状态。从四叔默许的神情来看,缺少宗教信仰的乡村社会,在失去神性的一味对苦难的超脱之后,宿命就成了大行其道的救命稻草。所以,在四叔被车压死之后,大儿子也用“命该如此”来解释他爹的车祸,并言之凿凿地认为“阎王要人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想那阴曹地府里也有它的规矩”[7]。为什么千千万万的路人毫发无伤、只有自己的父亲被车压死的钻牛角尖是典型的弱者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情况之下,认命也就是自己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思路。这种对乡村宿命问题的表现贯穿于莫言90年代的小说创作始终,从小知识分子和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共性,展示了处于同一个文化圈中的乡民对宿命认同的广度和深度。乡村中的良医作为读书解字的文化人其实更相信命,无论是古道热肠还是见死不救都以“命”作为行为的出发点,“越是医术高的人,越信命,越能超脱尘俗”的共性概括,就是对《良医》中描摹的乡村中像“大咬人”“陈抱缺”等有真本事的医生的恰当评价;由生理上的异秉引出命运上的截然不同的差距,也是乡民解释“人生有命,富贵在天”的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8]。在小说《三十年前的一场长跑比赛》中,秦主任的小手按照“大手捞草,小手抓宝”的民间认知标准,生来就是老天爷早就安排的抓印把子的[9,p60];《牛》中的富农杜大爷对自己没有当八路成为“吃香的,喝辣的,屁股下坐着冒烟的”公社书记一类的官员当然是非常后悔的,但他认为“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是没有用处的[9,p355]。难能可贵的是,莫言对这种乡村的愚昧、保守、落后的宿命意识并没有采取启蒙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高高在上的介入姿态进行揭露和批判,而是采取模仿“说书人”的不介入的行为姿态,从而让小说回归到艺术的本源状态和原初理想,最大限度地呈现客观对象的原始风貌:“小说家没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声音,讲故事如同在讲已经发生、尽人皆知的事,而声音是世界的声音,它封闭在故事中,等待着一张嘴张开让它流动、激荡。”[10]
莫言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对他的创作评价是“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其实,莫言对乡村生活的还原过程中所出现的鬼怪和神灵等神幻景观,更多地属于本土性的迷信传说,与魔幻现实主义“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的艺术原则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因为以《百年孤独》的卓越成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再声明:“他那种种魔幻式的描写‘都是以事实为根据的’,他说拉美的现实就是‘魔幻的’。”[11]但莫言的小说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本土的《聊斋志异》《封神演义》《西游记》等小说的双重影响下呈现出的“原乡”色彩,更多地带有迷信的质素。这种迷信观念对乡民的生活方式、思想情感、伦理道德、个人品格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它成为还原乡村的生活样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最大的特点是在“敬鬼神而远之”的“信则有,不信则无”之间游走,封闭的乡村便把这种带有迷信色彩的个人经历,或者是道听途说的传奇添油加醋演绎一番,作为一种游戏和娱乐方式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乡村人的价值观念和评判标准。莫言的“讲故事的人”的身份定位与乡村讲古的信息传播模式如出一辙,这样就以普通乡民的一员钩沉打捞沉睡的乡村民间记忆,真正还原出乡村的本真面貌。《爆炸》通过卫生员姑姑之口讲述了荒凉的乡村经常出现邪魔鬼祟的原因:“前十几年,咱这地方人烟稀少,孩子少得像星一样,人只要少,邪魔鬼祟就多。那时候,我常常半夜三更去给人看病,遍野都是闪闪烁烁的鬼火。”[12,p28]倒穿鞋子就能追上破布或烂骨头幻化的鬼火、狐狸发光、狐狸炼丹的迷信故事成为乡村信奉“万物有灵”的重要依据。在《奇死》中的老耿被日本鬼子捅了十八刀而大难不死的原因是“以德报怨的狐狸救了他的命”,狐仙的故事通过他诉苦大会上的讲述而广为流传[13]。这种带有迷信色彩的传说在莫言的小说中比比皆是:《罪过》中描写的鳖湾里鱼鳖虾蟹的神奇王国;《弃婴》中绘声绘色讲述的断腿狐狸把鲜美的牛肉饺子变成驴屎蛋子来惩戒打死他的愣头小伙子的故事;《奇遇》中描摹的在外当兵的“我”探亲回家的路上,遇到前天已死去的赵三大爷用烟袋嘴抵债的事情;《夜渔》中讲述的帮“我”捉螃蟹的亦神亦仙的女人,25年后再和“我”在一个“东南方向的大海岛”相见的预言,无论是时间还是地点都与在新加坡相逢的条件吻合的神奇经历;《模式与原型》中介绍的遵循民间复仇的伦理习俗仪式,乡村妇女打架羞辱他人的祖先的方式是赤身裸体跳到供养祖先牌位的桌子上,“双腿开叉坐着,呱唧呱唧拍着肚皮哭、骂”[14],导致的后果是失去祖先的庇护之后霉运连连的悲惨结局确实让人匪夷所思;在《战友重逢》中,死去的战友钱英豪讲述运河里的鱼精、鳖精、蟹子精被包黑的十二盘铜铡铡得血流成河,把龙王变成的穿青布衫的蓝胡子老头逼得心服口服;《丰乳肥臀》中的三姐成为鸟仙后,未卜先知、明察秋毫的治病行为完全符合迷信的装神弄鬼的理性判断,但三姐把对她开的药方抱有蔑视态度的人的惩罚,又显示出她是一个得道的高人,并且不仅三姐如此,“在高密东北乡短暂的历史上,曾有六个因为恋爱受阻、婚姻不睦的女性,顶着狐狸、刺猬、黄鼠狼、麦梢蛇、花面獾、蝙蝠的神位,度过了她们神秘的、让人敬畏的一生”[15];《我们的七叔》中的七叔遭遇车祸死去之后还能修车、喝酒、聊天,还能像活人一样在村头迎接“我”并告诉“我”有关存折的秘密。
由此可见,莫言受民间的花妖狐魅的本土资源的影响至深,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创作情结潜在地规约他八九十年代小说创作的题材选择和情节设置。可以说,民间与鬼神相关的迷信大多成为乡村民众茶余饭后的谈资,并且在谈论的过程中一定要加上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见证人来言之凿凿地说明自己讲述的故事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其实,众人也只是抱着“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态度,把讲故事的人的经不起逻辑推敲的闲扯当作一种消遣和娱乐。这样的最为常见的乡村生活的真相,也只有莫言之类的谙熟地域文化的“土著”居民才能还原到位。特别是他的《草鞋窨子》成为对乡村生活还原的典型样板,在编草鞋的窨子里,男人们在漫长的夜晚谈论的话题除了与性有关的外,便是云山雾罩、天南海北的精灵故事。小轱辘子讲述的破布、烂棉花、死人骨头之类的东西变成的鬼火,以及“脱下鞋来,鞋跟朝前用脚尖顶着跑”才能逮着鬼火的方法,显然是在各地流传的大同小异的迷信故事,但人们却对这样的无稽之谈的故事百听不厌,因为里面充满了神秘性和传奇性。所以整部小说围绕着有关鬼怪和精灵的一个个彼此并无关联的故事,还原出乡村漫无边际的聊天风貌。形状比黄鼠狼略小一点的会说人话的“话皮子”,每逢傍晚就在断墙边喊:“哎哟地,哎哟天,从西来了张老三;哎哟爹,哎哟娘,一砖打倒一堵墙……”[8,p222];蜘蛛精作为采花贼要奸污在伏天夜里乘凉的两个少女,被老婆子识破之后,用扫帚替换熟睡的女儿躲过一劫;五叔讲的老光棍门圣武家住着“阴宅”和穿一身红缎子的女鬼调情的事情,并为自己的鬼故事的真实性寻找依据:“前几年我们这里邪魔鬼祟多啦,后河堤上有一个大奶子鬼,常常在半夜三更嘿嘿地冷笑”[8,p232];于大身说的抹过人中指血的笤帚疙瘩受日月精华四十九天之后就成了精,点起火来烧它就会吱吱啦啦地冒血沫子。无论是见多识广的小轱辘子和于大身的亲身经历,还是不善言谈的五叔讲述的本村刚死去的熟人,目的都是为了让听众达到信以为真的效果。当然,“莫言小说中的种种传奇的生活现象,实际上是他对笔下中国社会、历史乃至人性反思和表达的一种特殊方式。在莫言的每一个传奇故事的背后,都包孕着他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看法”[16]。乡村生活的传奇性和迷信色彩,正是莫言抛弃先入为主的高高在上的启蒙意识后,展示乡村生活本相的叙事策略所要达到的效果,也是在科学和文明的发展走向理性的偏执之后,莫言对越界主宰的现代文明的功利主义的惊醒与反思,并切身实践起“伪士当去,迷信可存”[17]的反启蒙现代性的乡村主题。
二、乡村恶劣的生存条件的原生态还原
乡村的宿命意识和迷信观念的大行其道与贫穷的物质生活、恶劣的生存环境、艰辛的劳作条件有密切的关系,看不到任何希望的艰辛劳作是莫言刻骨铭心的记忆。莫言在《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源泉》中曾深情地回忆道:“生活留给我最初的记忆是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绿色的汁液流到地上,溅到母亲的胸前,空气中弥漫着野菜汁液苦涩的气味。”[18]所以,莫言在拥有写作的权力来表述自己被乡村苦难和饥饿缠绕的记忆的时候,乡村的超强度劳动和物质的匮乏,就成为他描述乡村灰暗的生活面貌的素材支点。《秋千架》中的暖姑并没有因为她是女人就可以减轻乡村劳动的强度,作为一个曾在故乡摸爬滚打又在城市中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的知识分子,怀着悲悯的情怀“远远地看着一大捆高粱叶子蹒跚地移过来,心里为之沉重。我很清楚暑天里钻进密不透风的高粱地里打叶子的滋味,汗水遍身胸口发闷是不必说了,最苦的还是叶子上的细毛与你汗淋淋的皮肤接触”[19,p136]。通过逃离与回归的知识分子的视角,更能感受到拉开时空的距离之后的劳动艰辛,这场没有任何诗意可言的劳动场景打破了体验生活的外来者做田园诗人的美梦:“她的头与地面平行着,脖子探出很长。是为了减轻肩头的痛苦吧?她用一只手按着搭在肩头的背棍的下头,另一只手从颈后绕过去,把着背棍的上头。阳光照着她的颈子上和头皮上亮晶晶的汗水。高粱叶子葱绿、新鲜。她一步步挪着,终于上了桥。”[19,p136]面对着她背上的跟桥的宽度差不多的草捆、被沉重的叶子捆压得凹进去的肩膀、短促的喘息声和扑鼻的汗酸,“我”对故乡的蓝天、白云、小河、村庄的思念之情,与“高粱地里像他妈x的蒸笼一样,快把人蒸熟了”[19,p136]的残酷现实相比是多么得苍白无力!这也充分地显示出“莫言小说与鲁迅和沈从文小说的不同,就在他完全是‘本地人’身份,他对农活的细切手感和身体感觉,以及农活知识是非常内行的,一看小说就知道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本地人”[20]。这种对农活的精致刻画、劳动场面和劳动艰辛的原生态还原也体现在他的《爆炸》中:“妻子高抬着铡刀等待着,父亲弯着腰,把一个麦捆塞到铡刀下,妻子一弯腰,铡刀‘嚓’一声,麦捆一分为二。母亲努力蹒跚着,用那杆桑木老杈把麦穗挑起来,挑到场上散开。我的女儿在麦场上打滚,她吃麦粒吃到嘴里一根麦芒子,麦芒子噌噌地往嗓子里爬,她脸憋紫了,一边哭一边咳,妻子吓出一脸冷汗……”[12,p22]这种农村见惯不怪的麦收场面绝没有《过故人庄》中所描绘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浪漫诗意,简单机械、单调乏味的劳作生活中时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和危险。女儿没有卫生意识和经验常识,吃麦粒被麦芒子卡住的细节描绘确实触目惊心,为了生存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孩子的现状也是农村中最突出的现象和问题。莫言就是这样无情地撕碎了笼罩在乡村田园风光的温柔面纱,显示出不避丑陋和肮脏的本真面目。
当然,农村的贫穷和落后除了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导致的生产效率不高有关之外,还与城乡物资交换方面存在的不平等的价格剪刀差以及国家政策中的农民经济负担过重有密切的关系。正如《欢乐》中备受拮据生活煎熬的齐文栋的大哥对鲁连山的三儿子所发的牢骚:“庄户孙,庄户孙,不知是哪个皇帝爷封的……你们想想,哪还有庄户人的好?种一亩地要交五十元提留……修路要庄户人出钱,省里盖体育馆要庄户人出钱,县里盖火车站要庄户人出钱,乡里办学校要庄户人出钱,村里干部喝酒也要庄户人出钱……羊毛出在羊身上,庄户孙!”[4]这是80年代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之后,庄户人不堪承受的皇粮国税的真实反映。税负让农民的微薄收入用在改善生活的消费方面少之又少,“农村真穷,农民真苦”的生活真相,在莫言的小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在穿戴方面,“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消费规则,就是七八十年代的偏僻乡村最生动的写照。《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在深秋还“赤着脚,光着脊梁,穿一条又肥又长的白底带绿条条的大裤头子”[21,p179];《秋千架》中的农村少妇暖姑,把那件泛着白碱花的男式蓝制服褂子脱下来之后,上身就“只穿了一件肥大的圆领汗衫,衫上已烂出密麻麻的小洞”[19,p138];《天堂蒜薹之歌》中的四婶平时就穿着一件“用蚊帐布缝成的半袖小褂,长久不换洗,白色蚊帐布早失去了本色”[7,p41],无论男女老少,穿戴的破旧与肮脏就是当时乡村生活真相的逼真反映。在饮食方面同样是没有任何讲究,《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队长“一手里拤着一块高粱面饼子,一手里捏着一棵剥皮的大葱”[21,p179]就是一顿饭;《牛》中围绕阉割牛的风波引出的有关吃的悲喜剧,将“文革”时期的乡村生活状况暴露无遗。总之,七八十年代的乡村贫穷落后的生活现状在莫言笔下得到了逼真的刻画和描摹。
三、乡村生活真相的淡化和遮蔽
从哲学意义上讲,由于理解的历史性所导致的主体对观察对象的盲视和洞见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可避免,所以熟悉乡村生活、尽量还原真相的莫言也不可能穷尽对象的各个方面而不带有主观的色彩。其实,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作为自己的观照和描述对象就已经带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这是莫言在创作中不以自己的主观好恶和独立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对莫言的乡土小说组成的大文本做整体上的考量和评价的话,他的小说采用的某些叙事策略和艺术技巧又有意识地造成了对乡村生活真相的遮蔽。这首先体现在哲理化意蕴的追求对乡村生活的模糊化处理上,莫言认为“没有象征和寓意的小说是清汤寡水。空灵美、朦胧美都难离象征而存在”[22]。反映在他的前期乡村小说中,刻意地追求“球状闪电”“金发婴儿”“红萝卜”等意象所具有的象征、暗示、隐喻等艺术色彩,就不可避免地在对乡村生活进行模糊化处理的过程中遮蔽掉某些具有明示意义的真相。特别是由一个美丽的梦境引发的《透明的红萝卜》的创作,在题材的选择和处理上,由于涉及“文革”时期政治意识形态比较敏感的话题所采取的淡化处理方式,是以对乡村生活真相的变形和扭曲为代价的。借助黑孩的行为特征来表现“颠倒的世界混沌迷茫,不灭的人性畸曲生长”[23]的主题的时候,“透明的红萝卜”作为他的生活希望和精神追求的象征,淡化了他在严酷的生活环境中所遭遇的苦难。刻意追求的生活的明亮色调,并没有在特定地域文化的多色调中达到辩证统一。“文革”时期的苦难遭遇对乡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给人的感觉是点点星光之下的黯哑与苍凉,欢乐和幸福的感受只是点缀在无边的痛苦深渊中的若有若无的陪衬。《球状闪电》中出现的发展现代养殖方式所带来的独立、自由的价值观念与传统的依赖、保守的价值观念的冲突,也不是“球状闪电”所能解决的。农民企业家蝈蝈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对结发妻子的冷淡、对父母教导的忤逆等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作者并没有如实地、逼真地予以刻画。特别是对于两代人接受的文明和文化、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代沟问题,仅仅通过蝈蝈的娘说的“你娶了老婆忘了娘,老天爷不会饶过你。……天老爷圣明着呢,你要是敢和爹娘分家,就让滚地雷劈了你个狗杂种”[6,p47],结果就真的一语成谶,落下球状闪电劈了儿子,这于情于理都难以服众。
其次,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极端发展,打破了反映生活真相的主客观之间的平衡,视界融合的缺失导致生活真相的夸张变形和匪夷所思。莫言太相信不受任何文学陈规和创作规律压制束缚的想象力的自由飞翔,“……我主张创作者要多一点天马行空的狂气与雄风,少一点顾虑和犹疑。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艺术风格上,不妨有点随意性,有点邪劲。”[24]《爆炸》中感觉化的爆炸导致的生理感觉和心理感觉、外感觉和内感觉的变化太随意,本来在理性的规约下味觉、嗅觉、听觉、视觉、触觉的辩证统一,在彼此走向太随意的对立分裂之路后,大大超出了还原乡村生活真相的企图和人们可以理解接受的感觉阈限。特别是父子之间围绕流产问题激发的父亲揍儿子一巴掌的刻骨铭心的感觉:“父亲的手缓慢地举起来,在肩膀上方停留了三秒钟,然后用力一挥,响亮地打在我的左腮上。父亲的手上满是棱角,沾满着成熟小麦的焦香和麦秸的苦涩。六十年劳动赋予父亲的手以沉重的力量和崇高的尊严,它落到我脸上,发出重浊的声音,犹如气球爆炸。几颗亮晶晶的光点在高大的灰蓝色天空上流星般飞驰盘旋,把一条条明亮洁白的线画在天上,纵横交错,好似图画,久久不散。飞行训练,飞机进入拉烟层。父亲的手让我看到飞机拉烟后就从我脸上反弹开,我的脸没回位就听到空中发出一声爆响。这声响初如圆球,紧接着便拉长变宽变淡,像一颗大彗星。我认为我确凿地看到了那声音,它飞越房屋和街道,跨过平川与河流,碰撞矮树高草,最后消融进初夏的乳汁般的透明大气里。我站在我们家浑圆的打麦场与大气之间,我站在我们家打麦场的边缘也站在大气的边缘上,看着爆炸声消逝又看着金色的太阳与乌黑的树木车轮般旋转;极目处钢青色的地平线被阳光切割成两条平行曲折明暗相谐的汹涌的河流,对着我流来,又离我流去。乌亮如炭的雨燕在河边电一般出现又电一般消逝。我感到一股猝发的狂欢般的痛苦感情在胸中郁积,好像是我用力叫了一声。”[12,p19]父亲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影响下,情急之中对儿子的暴力发泄本来是乡村生活中最常见的风景。但在这里,简单的生活真相被“圆球”“大彗星”“平川”“河流”“大气”“太阳”“地平线”“电”等科学术语所稀释和遮蔽,即使是辩证的“狂欢般的痛苦感情”的逼真描绘,也难以在文意的承续中得到读者阅读期待视野的接纳和认可。这样的例子在他早期的极端化书写中比比皆是,如备受诟病的《红蝗》对乡村喜欢在田野间拉屎的行为方式和粪便的铺张夸饰的描绘就大大超出了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四老爷再喜欢拉屎、再喜欢拉屎的时候思考问题,也无法从三段论的逻辑推理中得出“他拉出的是一些高尚的思想”的结论,高密东北乡的大便如何成形、网络丰富,也不可能“像贴着商标的香蕉一样美丽”。这些匪夷所思的天才结论和“美丽”的比喻不仅仅是对艺术审美的极端反叛,也是对现实生活中美好的事物的极端亵渎。这是对想象力太过信任的莫言在早期的乡土小说的创作中留下的缺憾,直到21世纪之后他才有所反思:“我过去认为我是可以钻到农民心里去的,但现在,年轻一代的农民的心理我已经不了解了。我过去总是以想象力为荣,认为只要有了想象力,什么都可以写。现在明白,想象力必须有所依附,如果没有素材,想象力是无法实施的。”[25]
[1] 莫言.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J].当代作家评论,1993,10(2): 37-39.
[2] 潘西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0.
[3] 莫言.说说福克纳这个老头儿[J].当代作家评论,1992, 9(5):63-65.
[4] 莫言.欢乐[J].人民文学,1987,30(Z1):6-42.
[5] 艾青.大堰河[M].广州:新世纪出版社,1998:112.
[6] 莫言.球状闪电[J].收获,1985,20(5):36-62.
[7] 莫言.天堂蒜薹之歌[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10- 262.
[8] 莫言.白狗秋千架[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347.
[9] 莫言.透明的红萝卜[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44- 372.
[10] 李敬泽.莫言与中国精神[J].小说评论,2003,19(1):72-76.
[11] 远浩一.关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J].当代文坛,1985, 4(12):61-64.
[12] 莫言.爆炸[J].人民文学,1985,28(12):19-38.
[13] 莫言.红高粱家族[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4:354.
[14] 莫言.白棉花[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334.
[15] 莫言.丰乳肥臀[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226.
[16] 胡秀丽.莫言近年中短篇小说透视[J].当代文坛,2002, 21(5):48-52.
[17] 鲁迅.文化偏至论[M]//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8.
[18] 莫言.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源泉[J].法制资讯,2012, 6(11):73-77.
[19] 莫言.秋千架[J].中国作家,1985,1(4):135-144.
[20] 程光炜.小说的读法——莫言的《白狗秋千架》[J].文艺争鸣,2012,27(8):10-19.
[21] 莫言.透明的红萝卜[J].中国作家,1985,1(2):179-203.
[22] 朱向前.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艺术评点[J].小说评论, 1986,2(2):50-54.
[23] 徐文斗.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史[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3:357.
[24] 莫言.几位青年军人的文学思考[J].文学评论,1986,17(2): 42-50.
[25] 莫言.文学与世界[J].东吴学术,2012,3(1):147-149.
Narrative Strategies of Mo Yan's Rural Novels in 1980s and 1990s:The Reduction and Dilution of Rural Truth
CAO Jin-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 Luoyang 471934, China)
When Mo Yan stepped into the complicated and varied space of daily life, he first establishe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his hometown. His twenty-one years’ rural life makes his literary reflection of rural life adopt the original ecological restoration strategy of poor, dirty and filthy life which is stripped away from the romantic color of the countryside. However, he also adopts a diluted narrative style on some unsatisfactory living conditions which is far away from the requirements of mainstream ideology. That forms Mo Yan's unique style and features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other local writers.
Mo Yan; 1980s and 1990s; rural novels; reduction; dilution
I206.7
A
1009-9115(2020)05-0030-06
10.3969/j.issn.1009-9115.2020.05.007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16CZWJ02)
2020-03-13
2020-05-27
曹金合(1973-),男,山东枣庄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校对:任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