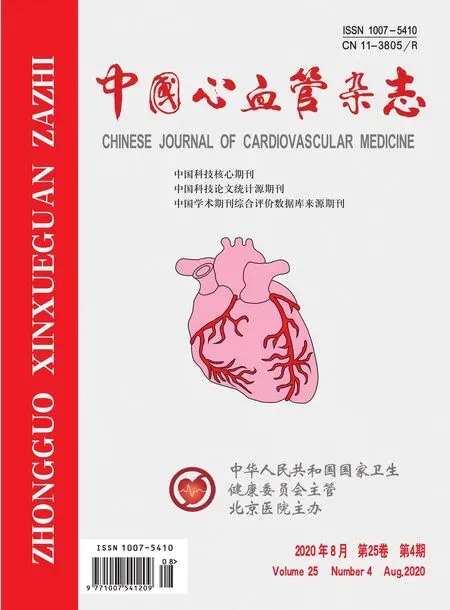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心肌损伤的诊疗进展
罗斌 任景怡 郑金刚
100029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心脏科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其病原体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 novel coronavirus,2019-nCoV)[1-2]。COVID-19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流行,截至2020年7月11日,全球累及报告确诊病例达1 228万,死亡病例达55万,病死率达4.5%[3]。COVID-19临床主要损害肺脏,表现为肺炎,此外还可累及全身多个器官,其中7.2%~12%的患者可出现急性心肌损伤[4-5]。在COVID-19重型和危重型患者中心肌损伤更为常见,可高达22.2%~31%,常起病隐匿且恶化迅速,短期内可进展为急性左心衰竭、顽固性休克或致命性心律失常,最终导致死亡[4-8]。因此早期识别,并根据患者所处疾病的不同阶段实施有针对性的治疗措施,对于降低COVID-19患者死亡率,特别是改善重型及危重型患者的预后至关重要。目前对COVID-19的认识正在逐步深入,我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已发布了相关诊疗方案及暂行指南[2, 9-10]。本文将结合最新文献报道和作者团队的诊治经验对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定义、发病机制、临床评估和治疗方案做一综述。
1 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临床定义
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通常由2019-nCoV感染引起,在组织学和病理学上与普通病毒性心肌炎比较并无特征性差异,其主要为临床诊断。定义为在COVID-19患者中出现心肌损伤标志物[肌钙蛋白(cTnI/cTnT)]升高和(或)降低超过参考范围上限的第99百分位数,且无心肌缺血的临床证据,同时可伴有B型利钠肽(BNP)或N末端B型利钠肽原(NT-proBNP)水平升高,心电图或超声心动图新发异常表现[11]。
2 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病理生理学机制
在COVID-19患者中,心脏是除肺脏以外需要特别关注的重要脏器。病理解剖结果发现,患者心脏可见病毒颗粒及其浸润性病变。心肌细胞可见变性、坏死,间质内可见少量单核细胞、淋巴细胞和(或)中性粒细胞浸润。部分血管内皮脱落、内膜炎症及血栓形成。心脏尸检结果提示,心肌少量炎症浸润,但无实质性的心肌损伤,提示病毒可能并非直接损伤心肌[12]。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病理生理学机制尚未十分明确,导致心肌损伤的病理机制可能包括病毒直接损伤和免疫介导损伤,成人以免疫损伤较为严重[13]。
2.1 免疫及炎症机制
2019-nCoV可侵袭心肌细胞或其他组织细胞并在细胞内复制,诱发机体产生细胞免疫反应和体液免疫反应,引起包括血浆白细胞介素6在内的多种炎症因子水平显著增加。炎症风暴可导致心肌及全身多器官组织损伤,严重者可引起血流动力学障碍甚至死亡。异常的免疫系统激活、过度的巨噬细胞极化和在组织器官中聚集所致的间接损伤是导致病情急剧恶化的重要病理生理学机制[12]。Liu[14]等对COVID-19患者尸解结果显示,COVID-19主要引起的深部气道和肺泡损伤为其特征性炎症反应,心肌未见炎症细胞浸润。但姚小红等[15]报道,COVID-19患者微创尸检显示心肌细胞肥大、部分心肌细胞变性、坏死,间质轻度充血、水肿,少量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浸润,电镜下见部分心肌纤维肿胀、溶解。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心肌间质浸润的炎症细胞主要为巨噬细胞和少量CD4+T细胞,心肌急性损伤和小血管损伤可能是由于2019-nCoV诱发炎症的全身反应所致。老年患者临床预后较差,其部分原因可能与免疫系统功能减低和炎症反应增加相关,从而加速病毒复制,延迟炎症应答时间,造成心脏、大脑和其他器官损伤。
2.2 微循环障碍
姚小红等[15]报道的微创尸检结果显示COVID-19患者多脏器小血管内透明血栓,提示患者生前发生了弥漫性血管内凝血。COVID-19重症患者在合并低氧血症、呼吸衰竭、低血压、休克等情况时,血管内皮功能受损继发血栓形成,可导致心肌微循环障碍,心肌因缺氧致高能磷酸化合物的产生和储备功能降低,细胞功能随之发生改变,导致心肌细胞损伤甚至坏死[13]。
3 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临床评估
COVID-19所致心肌损伤的临床表现差异很大,各年龄段均可发病,老年人群以及合并多种基础疾病的患者易并发重症心肌损伤,严重者可导致死亡。重症心肌损伤以起病急骤,进展迅速为特点,可表现为心力衰竭、循环衰竭(低血压或心原性休克)以及各种恶性心律失常,并可伴有呼吸衰竭和肝肾功能衰竭等多器官受累,通常需要使用血管活性药物、正性肌力药物、机械辅助循环[如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和呼吸辅助治疗。
3.1 心血管表现
2019-nCoV感染的前驱症状多发生于1~3周,非特异性,可伴有气短、呼吸困难、头昏、极度乏力、食欲明显下降、晕厥等症状。心血管表现从轻微的胸痛、胸闷症状,伴有心电图改变的心悸,到危及生命的心原性休克和室性心律失常均可出现。Huang等[4]报道的41例COVID-19患者的临床特征显示,约1/3的患者伴有基础疾病,包括20%糖尿病、15%高血压和15%心血管疾病。其中12%(5例)诊断为急性心肌损伤,主要表现为高敏肌钙蛋白I(hs-cTnI)水平升高(>28 pg/ml)。随后的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分析了138例连续入选的COVID-19住院患者,其中7.2%伴有急性心肌损伤,16.7%的患者可发生房性期前收缩、房性心动过速、心房颤动、室性期前收缩、室性心动过速等心律失常[6]。
在COVID-19重症患者中心肌损伤发生率明显升高,且与患者预后密切相关。在需要收入重症监护室的患者中,心肌损伤发生率可高达22.2%~31%[4, 6]。《柳叶刀》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COVID-19死亡患者中有59%存在心肌损伤,从发病至出现急性心肌损伤的中位时间为14.5 d,此外还有52%发生心力衰竭[16]。重症患者可迅速进展为急性左心衰竭或心原性休克,出现肺循环瘀血或休克表现。COVID-19所致心肌损伤的患者临床多无器质性心脏病基础,心脏泵功能异常多仅表现为弥漫性心肌收缩减弱、左心室射血分数下降。由于其病情进展极为迅速,心肌代偿机制尚未建立,心脏泵功能急剧恶化,严重者可发生猝死。
3.2 肌钙蛋白和利钠肽变化
在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实验室检测中以肌钙蛋白(cTn)最为敏感和特异[11]。研究显示,与存活患者相比,hs-cTnI水平升高在死亡患者中更为常见(46% 比1%)[16]。心肌损伤标志物的持续性升高表明心肌持续进行性损伤和加重,提示预后不良。利钠肽(BNP或NT-proBNP)水平通常显著升高,提示心功能受损严重,是诊断心功能不全及评估其严重性、判断病情发展及转归的重要指标,因此发病极早期检查正常或仅有轻度升高的患者,短期内需要复查[11, 13, 17]。
3.3 血清学抗体检查
对COVID-19患者可进行血清学抗体检测,有条件的实验室可开展病毒中和试验确定抗体效价。2019-nCoV特异性IgM抗体多在发病后3~5 d后开始出现阳性,IgG抗体滴度恢复期较急性期有4倍及以上升高。阳性的病毒血清学检测并不意味着心肌感染,而只是提示外周免疫系统与病原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外,人体感染病毒后产生的IgM抗体,在急性感染期达到峰值后逐步下降,通常会持续存在8~12周或更长时间。康复者血浆中具有治疗价值的是IgG抗体,而IgM抗体存在并不影响治疗效果,因此在特殊检测中不再要求进行IgM抗体的检测[18]。
3.4 超声心动图检查
超声心动图检查简便易行,可提供心脏结构、功能、心包等多方面信息,建议对疑似或确诊心肌损伤的COVID-19患者进行床边动态监测。超声心动图检查可见以下变化:(1)弥漫性室壁运动减低:表现为蠕动样搏动,为心肌严重弥漫性炎症导致心肌收缩力显著下降所致,早期变化进展会很快;(2)心脏收缩功能异常:均可见左心室射血分数显著降低,甚至低至10%,E/e’升高,但随病情好转数日后很快恢复正常;(3)心腔大小变化:多数患者心腔大小正常,仅少数患者心腔稍扩大,极少数明显扩大;(4)室间隔或心室壁可稍增厚,系心肌炎症水肿;(5)可出现心室壁节段性运动异常,系短期内炎症受累不均所致[19]。
3.5 心电图及动态心电图监测
COVID-19患者心电图异常以窦性心动过速最为常见,伴或不伴有ST-T动态变化[20];2019-nCoV不仅会对心肌造成损伤,对心脏的传导系统也会造成损伤,导致患者出现心律失常。可出现频发房性期前收缩或室性期前收缩、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心房扑动/心房颤动、阵发性室性心动过速;新发束支传导阻滞或房室传导阻滞提示预后不良;肢体导联低电压提示心肌受损广泛且严重;心室颤动较为少见,为猝死和晕厥的原因。出现恶性心律失常时应持续心电监测[20]。
3.6 有创血流动力学监测
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患者的血流动力学经初步治疗未能改善的,推荐行漂浮导管监测右心房、右心室、肺动脉以及肺毛细血管楔压,或行脉搏指示连续心排血量技术(pulse index continuous cardiac output,PiCCO)监测心排血量(CO)、心脏指数(CI)、胸腔内血容量指数(ITBI)、全心舒张末期容积指数(GEDI)、血管外肺水指数(ELWI)、肺血管通透性指数(PVPI)、每搏输出量(SV)、平均动脉压(MAP)、容量反应[每搏量变异性(SVV),脉压变异性(PPV)]、外周血管阻力指数(SVRI)、左心室收缩力指数(dPmax)。推荐常规进行有创动脉压监测,作为判断病情及治疗反应的标志。
4 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治疗
因COVID-19所致心肌损伤发病急骤,病情进展迅速,早期病死率高,治疗上应采用各种可能手段,尽力挽救患者生命。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临床表现差异较大,需根据疾病严重程度进行个体化治疗。治疗原则:临床上应尽早采取积极的综合治疗方法,除一般治疗(密切监测、营养支持、维持水、电解质与酸碱平衡等)和普通药物治疗(改善心肌能量代谢、减轻心脏负荷等)外,还包括抗感染、抗病毒、丙种球蛋白、中药治疗以及生命支持措施等,必要时可行心脏移植[12, 21-22]。
4.1 抗病毒治疗
瑞德西韦(Remdesivir)是一种新型核苷酸类似物,体外和动物研究均显示其具有抗病毒活性,对包括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SARS-CoV)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MERS-CoV)在内的相关冠状病毒有效[23-24]。但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结果显示,与常规治疗相比,瑞德西韦治疗重度COVID-19成人住院患者未观察到明显疗效[25]。
此外,治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的复方蛋白酶抑制剂洛匹那韦/利托那韦也受到关注。该药在体外研究中具有抗SARS-CoV活性,动物研究显示一定的抗MERS-CoV活性。然而,近期发表的一项真实世界研究显示,洛匹那韦/利托那韦(LPV/r)和阿比多尔未能促进COVID-19患者咽拭子病毒核酸转阴或改善症状,联用LPV/r和阿比多尔对病情改善无益[26]。
4.2 免疫调节治疗
COVID-19所致心肌损伤的危重症患者,胸部影像学快速进展、淋巴细胞进行性下降。尽管糖皮质激素曾广泛用于治疗SARS,但并无患者获益的充分证据,且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治疗后存在短期和长期不良反应。当前在COVID-19患者中,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并不推荐应用糖皮质激素,但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等其他适应证者除外[10, 27]。研究发现,糖皮质激素与流感患者死亡风险增加有关,也与MERS-CoV感染者的病毒清除延迟有关。
4.3 合并心原性休克和急性左心衰竭的药物治疗
常规心电监护监测一般生命体征,积极治疗诱因和病因,除了常规的对抗急性心力衰竭治疗外,必要时尽早实施ECMO辅助循环和呼吸。待休克、心力衰竭纠正平稳后可考虑抗病毒、免疫调节等其他措施[13]。
4.3.1 心原性休克的药物治疗 根据休克的原因进行治疗,COVID-19合并大量出汗、呕吐、腹泻等导致容量不足时,可适当补液,但注意补液速度。根据动力学监测(如PiCCO监测)指标决定补液速度和剂量,建议使用去甲肾上腺素药物作为一线血管活性药物,必要时可加用血管加压素升血压治疗。
4.3.2 急性左心衰竭的药物治疗 包括正压通气、血液超滤和利尿剂,在心率明显加快时小剂量使用洋地黄类药物,尽量少用单胺类强心剂,以免增加心脏耗氧和心律失常。由于血压低,所以应谨慎使用血管扩张剂。为了减少急性左心衰竭发生,应根据液体平衡和血流动力学状况决定液体进出量。对于心力衰竭严重甚至心原性休克的患者,需积极使用生命支持。
4.4 心律失常的治疗
针对心律失常类型并结合患者血流动力学状况进行相应处理。严密监护,COVID-19合并心肌损伤患者常存在低血压或休克,其处理原则应遵循现有的心律失常指南[20],同时亦应在充分考虑患者心脏泵功能和血压的状况下选择合适的药物或处理策略。
4.5 生命支持治疗
充分液体复苏基础上改善微循环,必要时使用血管活性药物,同时注意血流动力学监测。所有重症心肌炎患者均应尽早给予生命支持。
4.5.1 循环支持 (1)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ntra-aortic balloon pump,IABP):对于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器官功能衰竭治疗中出现严重肝功能不良的患者,推荐尽早使用IABP进行治疗;(2)ECMO:COVID-19患者合并急性心肌梗死、恶性心律失常、急性心力衰竭或其他原因导致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经血管活性药物、IABP等治疗效果不佳或病情迅速进展,应立即启动静脉-动脉体外膜肺氧合(V-A ECMO)。
4.5.2 呼吸支持 重症、危重症COVID-19的患者外周血氧饱和度小于92%时,建议给氧,合并低氧性呼吸衰竭的成人患者,建议使用高流量吸氧(HFNC),密切监测和短期反复评估呼吸衰竭的恶化情况,必要时行机械通气治疗。在优化了通气、使用了抢救性治疗以及俯卧位通气后依然存在顽固性低氧血症的患者,如有条件,推荐使用静脉-静脉体外膜肺氧合(V-V ECMO)[28]。
5 小结
总之,COVID-19患者合并心肌损伤时临床医师应予以高度重视,应尽早识别并密切监测肌钙蛋白升高和(或)新发心律失常的患者。重症COVID-19患者合并心肌损伤后病情可迅速恶化,急剧进展为心力衰竭和心原性休克,预后极差,应尽早实施全方位救治手段,血管活性药物、循环机械支持系统(IABP和ECMO)以及呼吸辅助支持系统的应用可能会对改善这些患者的临床结局产生有益的影响。未来仍需更多的临床随机对照研究提供进一步的循证医学证据支持。
利益冲突: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