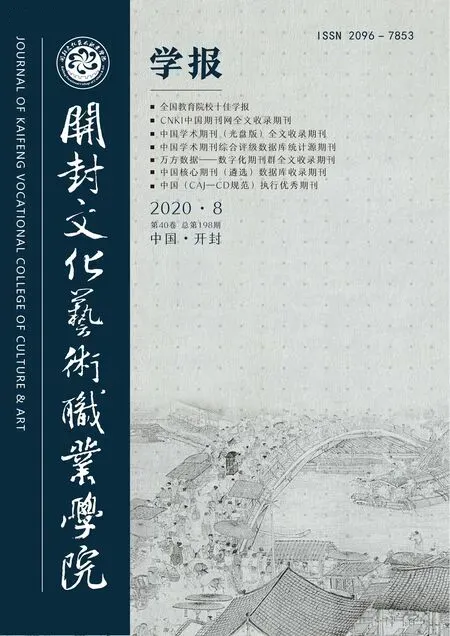从暴力走向和解:身体写作在《天佑孩童》中的体现
苏婷婷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通识教育学院,福建 泉州 362700)
《天佑孩童》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非裔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最后一部作品。该书延续了她一贯的写作风格,继续关注黑人的命运,但不同的是这个故事的时间背景为美国当代社会,讲述了一群受过童年创伤的人如何走出自己的精神和心理困境的故事。《天佑孩童》篇幅不长,作者除关注“90 后” 女主角布莱德的童年创伤外,还通过独特的叙事方法将其他几个人物的成长经历和心理创伤娓娓道来,比如:她的男友布克、老师索菲亚、后来结识的朋友雷恩等。布莱德的人生跟这些受过不同创伤的人因为种种原因产生了交集,并通过身体的暴力互动实现了关系的和解,每人都开始踏上自我救赎之路。本文将以她人生中三段重要的关系作为切入点,探索作者如何通过身体写作来描写布莱德与他人关系的变化,以及如何从这些关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一、身体写作
身体可以是一种文化符号,即物质(或肉体)、心理、精神的结合体。一个人往往通过身体与他人发生社会关系而得到认可。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创始人伊莱恩·肖沃尔特认为,身体写作即“女子的身体,女子的差异刻入语言和文本的行为”[1]262。该理论最初于20 世纪70 年代中期由法国女权主义者埃莱娜·西苏提出,在她看来,女性的身体并非仅仅是肉体,也蕴含了丰富的女性生理、心理、文化信息,展现了人的生理和社会双重属性。同时,因为身体是社会的,女性的自我认知必然是一个与外部世界、与他者互动的过程[2]。当前,对女主角布莱德的研究主要是从人格结构、创伤理论、妇女主义、角色理论、伦理性等方面展开,也有个别学者从她的身体出发,关注的是她黑色身体的变化或者她的黑色身体在商品社会的困境及意义,继而对自我身份进行思考[3]。本文则是把身体作为这部作品中一个强大的叙事动力,探索作者如何通过身体写作来展现布莱德与他人的关系。同时,从这个角度入手也能更好地了解布莱德心理问题产生的根源,也对有人格创伤的人如何实现生命成长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二、布莱德与母亲、老师索菲亚、恋人的关系
(一)与母亲的关系
因为当时社会的种族歧视,布莱德拥有一个不幸福的童年,她生下来的皮肤非常黑,“午夜黑,苏丹黑”。尽管她的父母本身都是肤色较浅的黑人,但对布莱德与生俱来的那种黑度仍十分震惊和害怕。她的父亲因为她的肤色怀疑她母亲偷情,因而抛妻弃女,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而她的主要抚养者母亲则采取的是另一种形式——避免跟她有任何接触,从来没有牵过她的手,小时候给她洗澡时脸上总是一种厌恶的表情,草草了事。年幼的布莱德甚至希望母亲能扇她耳光或者打她屁股,以感受到她的触摸。尽管年幼的布莱德没有被家暴,却遭受了另一种形式的身体暴力,即冷暴力。童年时期的受虐和创伤经历与成年后的人格发展密切相关[4]。这也为布莱德成年后的种种心理问题埋下了伏笔,成为她的心理和精神困境的根源。然而,从她母亲的视角讲述,读者却看到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母亲之所以这么做是担心布莱德会因为肤色问题在这个种族歧视的社会里难以生存下来,因而尽力避免跟她产生身体接触和存有亲子温情,希望以此来“训练” 她、培养她的社会适应能力。最终如她所愿,布莱德在事业上相当成功,成为一家化妆品公司的高管,物质条件丰富,可是,童年时期的种种阴霾却在布莱德一生中难以消散,不仅没有办法找到自我,实现自我身份认同,而且无法跟他人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由于母女俩一生都没有对话和沟通的机会,布莱德成年后跟母亲的关系很疏远,只给她寄钱,极少探望,两人的关系一直没有和解。
(二)与老师索菲亚的关系
布莱德在8 岁时,为了取悦母亲,毅然选择在法庭上说谎话诬陷当时的老师索菲亚骚扰儿童,导致她入狱15 年。虽然这件事之后,母亲牵了布莱德的手,她获得了少许来自母亲的温情,但她也为此愧疚万分,并时常打听索菲亚在监狱的情况。终于,在获知她出狱的日子,带着礼物尾随她回家以表示歉意,作者在描述二者的互动时,除最初为询问身份时有简短的对话外,并没有其他表达,而是着力描写了布莱德受到的一顿毒打。“她打了我一巴掌,用拳头打碎了我的下巴,再猛击我的肋骨,然后用她的头撞我的头。”[5]32“我的舌头找到了血,牙齿都还在,可是我却起不来了。我感到左眼睑抬不起来了,右胳膊也动不了。”[5]21“我想喊救命,可嘴巴好像是别人的,爬了几英尺才站起来。”[5]21“我的嘴巴肿得像生的肝脏,整张脸伤痕累累,右眼像蘑菇一样肿。”[5]21这些描写看起来很暴力、很惨烈,也很不近人情,但布莱德在被打时,始终无言地承受,“我没有发出一丝声音,当她扇我巴掌时甚至没有抬一只手保护自己”[5]32。她觉得无法理解索菲亚这种行为,但似乎又合情合理,因为她认为“用拳头说话是索菲亚在监狱里使用的语言,骨折和流血是跟其他犯人的交流方式”[5]38。也就是说,出于歉疚,布莱德主动用身体承受了这顿毒打,从而与自己和解,抚平内心的羞愧。而索菲亚也在这样的身体暴力中得到了解脱和释放,也算是对她15年牢狱之灾的一个交代。“那个黑人女孩帮了我,不是因为她头脑里想的愚蠢东西,不是她的钱,而是我们都没想到的礼物——十五年都没流的眼泪,不再压抑,不再有肮脏,现在我洁净并有力量了。”[5]70通过施行这样的身体暴力,索菲亚的愤怒和冤屈通过痛哭得到了尽情宣泄,也暗示和布莱德的关系有了一定的缓和。
(三)与恋人的关系
因为童年时期的阴影,布莱德没有办法与异性建立正常的恋爱关系,她常年与不同的男人通过肉体进行短暂交往,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从内心接受一个人,直至遇见了布克。布克也带有自己的童年伤痛——因为目睹哥哥在年幼时惨遭性侵并被杀害而陷入痛苦的回忆里。一天,他因无意得知布莱德与虐童犯索菲亚有联系而心生芥蒂,不辞而别,留下布莱德暗自神伤。在经历了一次车祸后,布莱德决定主动探寻与布克分手的真相。两人见面后,他们关系破冰的切入点也是一场激烈的身体暴力,“布克的眼睛因为仇恨忽明忽暗,他的手指着门口让她出去。布莱德迅速往前走了九步,并用最大的力气扇了他一个耳光。他用力打了下她的背,把她打倒。她吃力地爬起来,在柜台上抓了个米什劳啤酒瓶,直接在他头上摔破。布克躺到在他的床上,一动不动。”[5]152经过这次暴力冲突后,他们两个才进行语言交谈,将内心的想法真实地表达出来,最终消除误会,重归于好。两个在童年时期受过创伤的人,各种伤痛深深埋在心里,并不擅长其他形式的沟通,最终还是通过身体暴力来实现和解。
因为暴力往往意味着关系的破坏,所以对于在正常环境中成长的孩子来说,身体暴力是无法理解和接受的。而在莫里森笔下,身体暴力反而成为这些有创伤经历的孩童情感宣泄和自我救赎的出口。身体里面隐藏着内疚、不解、痛苦、挣扎、无奈、绝望、愤怒等心理活动,在家庭、人际关系、社会环境等多重打击下,当内心的痛苦累积到一定阶段无法用语言或其他方式表达时,可以通过身体与他人进行互动来缓解,比如:索菲亚对布莱德进行的暴力殴打、布克和布莱德的互殴等。而由于布莱德与母亲没有身体接触的可能,母女关系也就始终没有改善的可能。暴力从表面看是身体的活动,实则是人物心理活动的明证,是他们通过身体对现实进行的一种抗议、表达、宣泄、沟通与和解。这种身体写作方式当然不是实现和解的唯一的途径,但如果当事人没有办法与人正常沟通和交流时,唯有身体是诚实的,身体可以成为他们的代表,表达他们内心真正的需求。莫里森就是通过身体写作的方式,用大量的暴力描写,让读者感受到女主角背后的痛苦和绝望,也为她找到了一条实现与他人和自己和解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