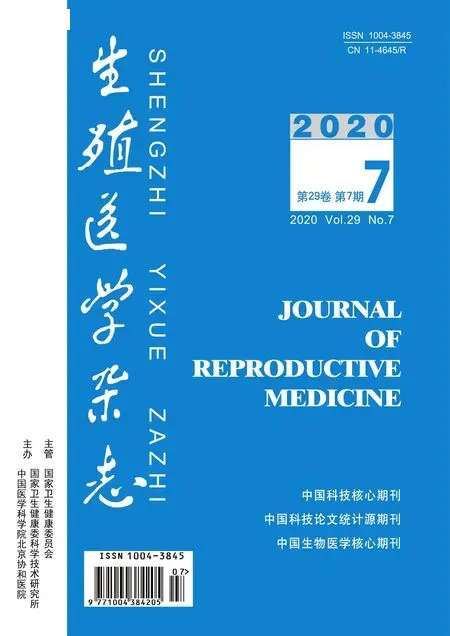阴道微生态与不孕症及其IVF-ET术后妊娠结局的相关性探讨
邓岚兰,宋学茹,杨慧鹏,黄建华*
(1.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空港医院妇产科,天津 300308;2.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天津 300052)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10年报道[1],全球不孕症患病率约为15%。中国女性不孕症发病率约为7.4%[2]。一项最新的多国家、多中心数据显示在1990~2010年间,不孕症患者人数从4 200万增长到4 800万,虽然大部分地区的患病率未发生显著变化,但不孕症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3]。近30年来辅助生殖技术获得突破性发展,已成为不孕不育治疗的核心手段。然而国际范围内试管婴儿的累积活产率仅为28%左右[4],影响其成功的因素涉及到多方面,阴道微生态(vaginal microbiota)的改变目前逐渐引起学者关注。已有研究证实,特定的阴道微生态群落类型不仅影响生殖健康,还可能是不孕症的病因之一[5]。进一步的研究将关注阴道微生态菌群对生育力的影响,以及阴道微生态是否会对不孕症IVF-ET治疗结果产生影响。本文对阴道微生态与女性不孕症的关系,以及不孕症患者阴道微生态的改变对助孕结局的影响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不孕症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参考。
一、阴道微生态对女性生殖能力的影响
(一)健康女性阴道微生态
阴道微生态体系由阴道内微生物菌群、机体内分泌、局部免疫和解剖结构共同组成。女性阴道壁粘膜有多种共生微生物定植,它们在保护阴道抵抗病原感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女性生殖健康产生深远影响[6]。目前认为正常阴道菌群以乳杆菌为主,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在微生态领域的应用,人们对生殖道菌群分布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育龄期妇女阴道菌群被归为5类(Community State Types,CSTs),CST-Ⅰ、Ⅱ、Ⅲ、Ⅴ这4种类型都以乳杆菌为主(分别为卷曲乳杆菌、加氏乳杆菌、惰性乳杆菌和姜氏乳杆菌),而CST-Ⅳ主要包含以厌氧菌为主的其他多种类型细菌[7]。其中,CST Ⅳ-A亚组包含中等量的乳杆菌(以惰性乳杆菌为主),CST Ⅳ-B则主要包含与细菌性阴道病(Bacterial Vaginosis,BV)高度相关的菌种[8]。阴道微生态的分布因地域、种族不同而有显著性差异,亚洲和白人健康妇女中阴道微生态菌群以乳杆菌为主的分别占到80.2%和89.7%,而在西班牙和黑人妇女中该比例却仅为59.6%和69.1%[7]。另一项针对年轻健康黑人妇女阴道菌群的高通量测序显示,仅37%的健康妇女阴道菌群以乳杆菌为主,约有25%的无症状妇女阴道菌群以非乳杆菌为主,但不是疾病状态,往往此种类型妇女阴道分泌物中存在促炎症细胞因子和激活的免疫细胞,提示此种类型的阴道微生态可能与感染有一定关系[9],而且出现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显著增高[10]。这就衍生了学者们对于健康的和最优的阴道微生态的探讨,即这种无症状的以非乳杆菌为主的阴道微生态环境可能是健康的但不是最优的。研究发现惰性乳杆菌对维持正常阴道微生态并无促进作用,还可能增加宿主感染沙眼衣原体的风险,是正常菌群向异常菌群转变的过度状态[11]。而绝经前的健康妇女阴道微生态以卷曲乳杆菌为主,因此新的观点认为以卷曲乳杆菌为主的阴道微生态才是真正健康的标志[12]。在阴道微生态领域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挖掘。健康女性阴道菌群分布受到激素、月经、性生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处在一种动态平衡之中,这种平衡对维持女性生殖健康有重要意义。
(二)阴道微生态与不孕症的相关性
引起不孕症的病因较为复杂,常包括输卵管因素、子宫因素、子宫内膜异位症(EMs)等因素,而近年来生殖道感染已被证实与不孕症的发生密切相关。将不孕妇女与健康妇女的阴道菌群对比分析后发现,不孕症组阴道菌群以念珠菌(26.5%)和肠球菌(23.0%)为主,健康组则以乳杆菌(27.8%)和微球菌(15.3%)为主,二者的构成有显著差异[13]。一篇纳入了12项以Nugent评分为评价标准的meta分析(n=3 229)显示,在不孕女性中BV患病率比对照组高2倍[14]。对先天性不孕症患者阴道分泌物进行二代测序发现,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先天性不孕症患者阴道菌群谱与BV患者一致[15]。Wee等[16]的研究也证实有不孕症史的妇女与有生育史的妇女相比阴道菌群分布有差异。可见阴道菌群失调与不孕症有一定相关性,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原本被认为是无菌的子宫内膜、输卵管等上生殖道也发现存在菌群,而阴道微生态失调也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与输卵管性不孕、子宫内膜因素性不孕存在关联。
1.阴道微生态与输卵管性不孕症的关系:输卵管因素是引起不孕症的常见病因之一,正常女性的宫颈发挥屏障作用可有效减少或防止微生物侵入上生殖道,但在某些病理情况下条件致病菌或某些外部侵入的病原菌可上行引起上生殖道感染,严重的会导致输卵管炎症使得输卵管完全堵塞或破坏输卵管内膜导致瘢痕形成,影响输卵管蠕动,进而引起输卵管性不孕症的发生。有研究对300例输卵管性不孕症患者盆腔积液和阴道分泌物中的病原菌进行检测,结果发现输卵管性不孕症患者阴道分泌物中优势菌群发生变化,盆腔积液中病原菌检出率升高,处于菌群失调状态[17]。另一项研究显示在输卵管性不孕症患者阴道分泌物中沙眼衣原体检出率高,解脲支原体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加德纳菌和普雷沃菌的比例较正常受孕女性高,提示解脲支原体和沙眼衣原体感染与女性输卵管性不孕症有关,可能是引起女性不孕症的主要因素之一[18]。而在患有BV的IVF妇女中,因输卵管因素导致的不孕显著高于未患BV的妇女(P=0.001),提示与BV相关的细菌可能上行到上生殖道引起亚临床感染和盆腔炎症,引起输卵管损害并降低生育力[19],这可能与生殖道上皮组成的免疫屏障对许多细胞因子都较敏感,在BV中容易遭到破坏有关[20]。沙眼衣原体等常见的盆腔炎症致病菌在患有BV的人群中更普遍[21]。由此可见,虽然在不同取材部位和不同人群中的研究结果有所差异,但输卵管性不孕症患者总体呈现阴道微生态失调状态,且BV以及其他相关致病菌很可能上行感染引起输卵管性不孕症的发生,但目前尚缺乏对阴道微生态失调引起输卵管性不孕症的直接证据,未来还需更大样本量和更规范的研究方法来进一步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
2.阴道微生态与子宫内膜因素性不孕症的关系:女性生育力主要取决于子宫内膜容受性,其受激素、解剖学结构和免疫系统的影响,而微生物群落影响着局部和全身免疫。自1989年Hemsell等[22]首次从健康妇女子宫中分离培养出多种定植细菌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宫腔并非无菌,而是呈现以乳杆菌为主的多样化定植[23]。正常妊娠子宫内膜容受期间,子宫内膜的定植菌群处于高度稳定状态,而炎症状态下子宫内膜容受性明显降低,腹腔积液中存在活性氧和各种炎症因子,致使早期胚胎的生存环境相对恶劣[24]。有研究对102例不孕症患者的宫腔积液进行测序分析发现,不孕症患者子宫内膜菌群大多以非乳杆菌为主,将这部分患者子宫内膜乳杆菌浓度提升到>90%的水平,可改善IVF后的胚胎着床率[25]。对子宫内膜优势菌为非乳杆菌的患者使用抗生素联合益生菌制剂治疗,可明显改善患者妊娠结局[26],提示恢复以乳杆菌为优势菌的子宫内膜微环境既可以改善女性生育力和助孕结局。长期以来,上生殖道的感染被认为是由阴道病原菌上行感染所致。将放射性标记的蛋白微球滴注到阴道,最快2 min就能上行进入子宫内[27],表明液体和微颗粒可以在阴道-子宫间相对自由地移动。Mitchell等[28]对要进行子宫切除的妇女的阴道分泌物和子宫内膜菌群进行qPCR检测,发现子宫内膜虽存在一些特有的细菌,但其主要菌群与阴道分泌物中主要菌群相同,只是菌量更低。Swidsinski等[29]的研究发现BV患者中有一半人群的子宫内膜中存在阴道加德纳菌生物膜。这些研究均表明阴道菌群可上行到上生殖道影响子宫内膜菌群。另外,在对EMs引起的不孕症患者研究中发现,EMs在阴道炎、宫颈炎患者中发病率更高[30],EMs不孕女性与未合并EMs的女性比较,阴道、子宫内菌群组成均有统计学差异[23]。可见阴道菌群失调可能增加EMs发生率,甚至造成广泛的盆腹腔粘连,影响胚胎着床。子宫内膜是胚胎种植和发育的直接场所,因此随之分子技术的发展未来应该更多关注子宫内膜菌群对女性生育力的影响。
二、阴道微生态与IVF-ET术后妊娠结局的相关性
随着微生物测序等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阴道微生态失调对助孕结局存在影响[31-32]。有学者对31例接受IVF助孕的患者阴道分泌物进行测序分析,发现阴道分泌物群落类型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包含:乳杆菌属、加德纳菌属、梭菌属、葡萄球菌属和小杆菌属,第二类则包含除第一类外的其他菌属,而成功妊娠的女性阴道分泌物乳杆菌含量更高,且主要为第一种群落类型中的菌属[31]。宫颈是连接阴道及宫腔的重要桥梁,一项针对265例IVF-ET助孕女性开展的宫颈菌群培养的研究显示,大肠杆菌培养阳性率为64%,葡萄球菌属培养阳性率为8%,培养阳性组IVF移植成功率、临床妊娠率及持续妊娠率均低于培养阴性组(分别为24% vs. 37%,P=0.02;17% vs. 28%,P=0.04;9% vs. 16%,P=0.01)[32]。对接受IVF治疗和未接受IVF治疗的不孕症患者进行研究,发现接受IVF治疗的患者子宫内膜菌群乳杆菌含量低于未接受IVF治疗的患者,其原因可能与IVF操作过程和接受IVF患者的背景有关,如:频繁的经阴道检查、既往人工授精史、频繁使用抗生素、控制性促排卵(COH)中激素水平波动、取卵和胚胎移植操作以及卵巢刺激的副作用(如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等[25]。阴道微生态失调可能影响助孕结局,而在IVF-ET治疗实施过程中各种因素也会引起阴道微生态的改变从而对助孕结局产生影响。
(一)子宫内膜菌群与胚胎反复着床失败(RIF)的相关性
随着促排卵方案的改进和实验室培养条件的改善,单个周期移植妊娠率增加,但RIF的发生率仍较高。胚胎着床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母体、胚胎及母胎界面免疫反应均可影响该过程导致着床失败,其中非整倍体胚胎是移植失败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在大龄女性中。但整倍体胚胎移植失败率仍达40%左右[33],提示可能存在其他导致移植失败的因素。正常子宫内膜菌群处于免疫平衡状态,参与形成子宫内膜免疫共同体,维持宿主抑制细菌增殖和侵袭的能力[24]。Moreno等[34]的研究发现,子宫内膜菌群以非乳杆菌为优势菌的妇女其胚胎着床率显著低于子宫内膜菌群以乳杆菌为优势菌的妇女(60.7% vs. 23.1%,P=0.02)。而在RIF合并慢性子宫内膜炎患者的子宫内膜中发现NK细胞含量下降,内膜基质中B淋巴细胞募集,子宫内膜局部Th1/Th2免疫失调,可阻碍胚胎着床[35]。有研究对16例子宫内膜炎患者的子宫内膜组织进行分析,发现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IGFBP1)表达上调,同时白细胞介素(IL-11)、趋化因子配体(CCL4)、胰岛素生长因子(IGF-1)下调,可以推断由子宫内膜炎引起的RIF是炎症表达异常、局部免疫失调、趋化因子介导的综合过程[36]。子宫内膜局部炎性微环境通过改变黏附因子正常表达,进而引起子宫内膜B淋巴细胞浸润,渗透至子宫内膜上皮细胞及腺体区,分泌各种免疫蛋白抗体影响子宫内膜容受性,从而影响胚胎着床[37]。
(二)COH对阴道菌群的影响
COH是IVF-ET治疗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在COH过程中体内雌激素水平短时间内快速升高使得阴道菌群分布产生变化。在妊娠期,随着雌激素水平升高,阴道菌群分布可能发生改变,其中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的发病率会偏高[38]。Hyman等[39]研究了30例接受IVF-ET治疗的女性在不同阶段体内雌激素水平和阴道菌群组成情况,发现所有患者的雌激素水平从初始卵泡至成熟卵泡阶段均显著上升,其中54%伴有阴道菌群改变;从注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至胚胎移植阶段,有5例患者的雌激素水平急剧下降且均伴有阴道菌群改变,提示阴道菌群改变与雌激素水平具有相关性。另一项研究显示,IVF-ET周期中接受长方案COH的患者,在进行COH后阴道微生态失调者较COH前显著增加(15.3% vs. 32.0%,P=0.05);COH前已有阴道微生态异常者更容易发生微生态失调(26.8% vs. 60.9%,P=0.01),提示接受COH的患者更容易发生阴道微生态失调,且COH前已有阴道微生态失调的患者在接受COH后更易发生失调,影响IVF-ET治疗的成功率[40]。因此可在HCG日对COH者行二次阴道微生态检查,并注意加强宣教及外阴清洁。不同的促排方案对阴道微生态会有不同影响,实施COH后阴道微生态的变化对IVF-ET术后妊娠结局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
(三)IVF-ET操作对阴道菌群的影响
目前认为宫腔内菌群是由阴道菌群上行定植,而阴道病原菌上行感染可导致炎症反应。胚胎移植过程中移植管也会将阴道及宫颈处微生物带入宫腔,进而对助孕结局产生影响。一项对80例接受IVF-ET助孕妇女的研究显示,若胚胎移植管上培养出细菌会降低临床妊娠率[41]。宫颈黏液或宫腔内出血导致的移植管污染可降低临床妊娠率,黏液量越多临床妊娠率越低[42-43]。越来越多的研究也开始支持在进行胚胎移植时若移植管上定植了卷曲乳杆菌将会提高胚胎种植率和活产率,同时还可降低感染几率的假设[44]。上述研究均提示,维持以乳杆菌为主的阴道、子宫内膜微生态对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结局有益,因此在进行胚胎移植前应尽量全面评估。
三、结语
女性阴道微生态处在一种动态平衡之中,能影响宿主的生理功能,反之宿主的生理变化也可以影响阴道微生态的组成和功能。阴道微生态失调不仅能引起阴道的慢性炎症,更与多种因素导致的不孕症存在关联。除常见的沙眼衣原体等致病菌外,BV引起的阴道微生态失调也可能导致一些亚临床改变,成为女性不孕症的危险因素。以非乳杆菌为主的阴道微生态可能激发宿主免疫反应从而降解宿主粘膜屏障,使机体更易发生感染从而导致不孕或早产等不良妊娠结局[10],恢复以乳杆菌为主的阴道、宫腔内环境有助于改善助孕结局;同时要注意在IVF-ET治疗过程中COH、取卵及移植等操作的影响。阴道微生态与宿主间的相互作用与IVF-ET治疗后结局的关系仍存在诸多疑问,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宫腔、输卵管等上生殖道微生态对助孕结局影响的研究也已开展。未来还需关注对阴道微生态的作用机制和功能方面的探讨,明确其与不良助孕结局之间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