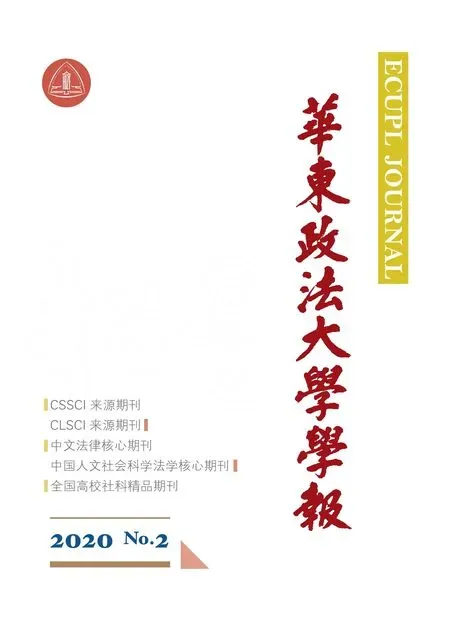我国反垄断法修订中比例原则的引入
焦海涛
一、比例原则的引入背景
起源于警察权规制的比例原则,被德国行政法学鼻祖奥托·梅耶誉为行政法中的“皇冠原则”,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陈新民也类比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中的地位,将比例原则视为行政法中的“帝王条例”。比例原则最初意指公权力的行使应以对相对人造成最低伤害为前提,所以又称“最小侵害原则”“禁止过度原则”。〔1〕参见黄学贤:《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研究》,载《法律科学》2001 年第1 期,第72、76 页。比例原则反映的是目标(ends)与手段(the means)之间的关系,〔2〕See Eric Engle, “The history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an overview” 10 Dartmouth L. J. 8 (2012).强调目标与手段的平衡。这种平衡在很多法领域都要顾及,而不限于行政法,所以,比例原则可用来解释、处理较多法律问题。实践中,比例原则在德国行政法中诞生以来,已呈现出普遍化倾向,〔3〕参见陈景辉:《比例原则的普遍化与基本权利的性质》,载《中国法学》2017 年第5 期,第279 页。不仅被其他国家广泛接受,也渗透于其他法之中。〔4〕甚至有学者试图将比例原则引入私法之中,可参见黄忠:《比例原则下的无效合同判定之展开》,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 年第4 期;郑晓剑:《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及展开》,载《中国法学》2016 年第2 期;纪海龙:《比例原则在私法中的普适性及其例证》,载《政法论坛》2016 年第3 期。
比例原则在反垄断法中不仅可以适用,也应当适用,甚至构成反垄断法实施的基本要求。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反垄断法的实施主要体现为公权机构的执法活动,外在形式就是行政行为,基于比例原则在现代行政法中的基础地位,反垄断法的实施也需遵循比例原则的要求。反垄断执法的基本方式,体现为公权机构对市场主体施加限制,这种限制必须贯彻“最小侵害原则”,即不得超过实现反垄断法目标所需的必要限度,如果有多种措施都能实现该目标,执法机构应当选择对市场主体限制最小的方式。就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来说,比例原则的引入还有更为重要的现实背景——我国反垄断法实施时间较短,执法活动更需比例原则的约束与指导;在垄断行为的分析模式模糊不清,而反垄断法的实施必须注重多元价值权衡的现实背景之下,比例原则的作用更为明显。
(一)反垄断执法裁量权的约束在我国当前更为迫切
我国反垄断法实施时间较短,以比例原则来约束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自由裁量权在我国当前具有迫切需要。对公权行为来说,比例原则与自由裁量相伴,越是存在自由裁量的领域,越需对公权行使施加比例原则的限制。反垄断法实施中存在大量的自由裁量行为,比例原则的限制自然必不可少。而且,我国《反垄断法》实施刚刚十年,除制度本身的不成熟外,执法机构的法律地位、执法经验与执法能力与反垄断法历史较长的国家相比亦有不小差距,执法的粗放性、摸索性在较长一段时期内都难以避免。在这种情况下,以比例原则来促进执法活动走向规范,并确保执法理性,就显得更为重要。
早期反垄断法较多使用绝对化的语言,垄断行为本身较为简单,违法性标准也没有太大争议,因而法律适用并不复杂。这种情况现已彻底改变。为了应对变动不居的经济现实,以及越发具有多重效果的垄断行为,现代反垄断法规范的特点之一是高度开放且极为灵活。不仅实体规则无法穷尽对各种垄断行为的规定,“本身违法原则”的适用空间也越来越小,大多数垄断案件都需结合具体情境综合分析。执法机构越来越难以单纯依靠有限的实体规则处置案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相机抉择”的自由裁量过程。〔5〕参见焦海涛:《论现代反垄断法的程序依赖性》,载《现代法学》2008 年第1 期,第52 页。甚至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一种垄断行为之前被认定为违法,之后可能需要进行合理性分析,甚至被豁免。不论是法律规则使然,还是现实生活需求,自由裁量权的赋予是确保反垄断法的实施具有妥当性的必要举措。在这种情况下,为防止反垄断执法的“内部化”,以及避免给市场主体造成不必要的负担,对执法者自身的控制也成为现代反垄断法的应有内容之一,而控制方法除设置严格的执法程序以确保公权的行使符合公共利益外,比例原则也是重要的约束手段。
比例原则强调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平衡,意味着执法机构在维护竞争秩序时,应采用适当且必要的方式,不是所有的垄断行为都应被禁止,也不是所有应被禁止的垄断行为都需施加高额罚款。如果缺少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平衡,执法活动既可能无法实现目标,也可能处罚过度。例如,在传统经济中具有危害性的垄断行为,在互联网等新经济领域可能是一种普遍的商业模式,过于严厉的执法未必有利于激励创新与提高效率;又如,对垄断行为的罚款数额,大多立法只规定一个宽泛幅度,这时如果缺少比例原则的约束,市场主体可能会承受不必要的负担,甚至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造成差别对待。
对一个具有丰富执法经验和较高执法能力的机构来说,自由裁量权的适当行使一般不会成为问题,但在执法经验与执法能力均有不足的情况下,自由裁量权就是一个较大的风险因素。在规范层面,我国反垄断法赋予了执法机构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在确保自由裁量权的适当行使上,由于经验与能力限制,我国执法机构还缺少足够的、令人信服的自我约束能力。内部控制机制无效时,只能依靠外部制度约束,但遗憾的是,我国这方面的制度供给也不足。一方面,《反垄断法》第六章关于执法调查与作出决定的程序规定十分简单,执法机构并未受到严格的程序约束,更不用说比例原则的限制。例如,《反垄断法》并未要求执法机构对拟作出的处理决定详细说明理由,甚至根据第44 条,执法机构即便认定垄断行为违法而作出处理决定的,也可以不向社会公布——如果不向社会公布,执法机构就没有压力去解释为何会选择这类处理决定以及为何会设定这样的处罚措施。另一方面,我国《行政处罚法》中也未明确规定比例原则的主要内容和适用方式,只简单提及“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反垄断执法机构依照该法对市场主体作出行政处罚时,很难在目标与手段之间进行实质性衡量,更多还是依据《反垄断法》的规定,而《反垄断法》提供的处罚空间十分广阔,如罚款数额通常为行为人上一年度销售额的1%至10%。在这种情况下,到底选择哪种处罚措施,适用哪个罚款比例,全凭执法机构自己判断。
从实践看,由于缺乏比例原则的约束,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处罚决定书中,很少会对处罚措施的选择、罚款比例的确定进行详细解释,一般只是简单描述一个事实之后,即交代处罚结果。例如,在2016 年的“艾司唑仑药品垄断协议案”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出,“根据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以及当事人在垄断协议中的不同作用、对调查的配合程度等因素”,依法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实施垄断协议,并“对在垄断协议的达成、实施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华中药业,处2015 年度艾司唑仑片销售额7%的罚款”;“对垄断协议的参与者、在调查过程中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且有立功表现的山东信谊,处2015 年度艾司唑仑片销售额2.5%的罚款”;“对垄断协议的跟随者、违法程度较轻且能积极主动整改的常州四药,处2015 年度艾司唑仑片销售额3%的罚款”。在这里,尽管执法机构提及罚款数额的确定考虑了众多因素,但我们并不知道涉案当事人在这些因素上存在哪些差异,也不清楚这些因素是如何被考虑的。
我国当前反垄断案件的处罚决定书基本采用上述的“事实描述+罚款结果”模式,在“事实描述”与“罚款结果”之间,缺少必要的关联性分析;而且这些“事实描述”也极为简单,通常只是交代了若干因素,而很少涉及这些因素的具体表现及发挥作用的方式。在这些处罚决定书中,我们只看到了7%、2.5%和3%的罚款比例,无法得知这一比例具体是如何确定的,垄断行为的性质、持续时间,当事人的作用,以及对调查的配合程度究竟各自起着多大的作用。甚至在有些案件中,由同一执法机构作出决定,涉案行为完全相同,当事人配合调查的情节相似,最终的罚款比例仍有较大差异。例如,同是发改系统处理的转售价格维持行为,2013 年茅台、五粮液案的罚款比例是1%,而2014 年的一系列汽车业垄断案中,克莱斯勒被罚比例是3%,一汽大众被罚比例是6%,奔驰被罚比例是7%,东风日产被罚比例是3%。这种差异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在执法机构的处罚决定书中并不能找到充分的依据。
总之,在自由裁量权不可避免时,执法机构的经验与能力越是不足,就越需要比例原则的约束。
(二)比例原则能为反垄断执法活动提供指引
反垄断执法是一项复杂的专业活动,我国《反垄断法》实施不久,经验问题无法短期弥补,而立法给予的执法空间又较大,这种情况下,如何选择合适的执法措施,对执法机构亦是严峻的考验。在这方面,比例原则可以提供一定的指引。
其一,比例原则可用于指导案件处理结果。如果从比例原则的要求出发,根据不同案件所要实现的目标差异来选择相适应的处理措施,对执法机构来说也是一种参考。例如,有的案件中垄断行为的违法性严重或者情节恶劣,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后果,基于确保反垄断法有效威慑的目标,对这些垄断行为就必须施以严重的法律责任;有的案件中垄断行为的违法性不明显、不确定,或者情节轻微、损害后果不大,则迅速纠正涉嫌违法的行为是更重要的目标,威慑效果的形成主要不依赖于对这些案件的执法,所以,执法机构就可考虑选择与行为人和解,即适用《反垄断法》第45 条规定的承诺制度。
其二,比例原则有助于增强案件处理的说理性。我国法律实施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是,执法活动一贯说理不足。当人们对某些行为的违法性与损害后果容易形成共识时,执法活动中的说理不那么重要,但反垄断法不同,反垄断法适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变动性强,不仅垄断行为的边界很不确定,大多垄断行为的竞争效果也难以依靠经验与常识来判断。例如,当前实践中较为普遍的平台企业“二选一”行为,是否构成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在平台企业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时,这类行为是否还会产生竞争损害?“二选一”是否也可能构成纵向垄断协议?诸如此类争议或疑问在每个垄断案件中都可能出现,经济现实的变动性、法律规范的不确定性与开放性亦使反垄断法实践不断面临新问题的挑战。因此,执法活动只有进行了充分的说理,法律适用的妥当性、合理性才能有所保障;针对新问题或争议问题的说理,也有助于人们明确法律态度,进而对法律适用形成合理预期;此外,说理本身也是反垄断法的宣传与竞争理念的普及过程,这在反垄断法实施初期十分重要。一旦强调比例原则的约束,执法机构就必须解释为何认定行为违法,怎样开展执法程序,以及基于哪些因素的考量而设定这样的法律责任。这些道理一旦说清,执法活动自然更经得起推敲,也能逐步走向精细化。
(三)比例原则构成垄断行为合法性分析的重要内容
比例原则可作为垄断行为豁免分析的重要工具,进而构成垄断行为合法性分析模式中的重要内容。这在我国当前反垄断法中的豁免标准不够清晰的背景下具有重要价值。
垄断行为的合法性判断是反垄断法适用的核心任务,也是反垄断法上最为棘手的问题。肇始于美国的反垄断法,早期阶段对垄断行为规制严厉,大多垄断行为被视为“本身违法”,而随着反垄断经济学认识的深化,“合理原则”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大。欧盟反垄断法中虽然没有这两种原则的区分,但在垄断行为的禁止性规范之外,亦构建了无比庞大的豁免体系,不仅有各种以单行法形式存在的集体豁免条例,〔6〕如研发协议集体豁免条例、专业分工协议集体豁免条例、技术转让协议集体豁免条例、保险市场协议集体豁免条例、汽车业纵向协议集体豁免条例和纵向协议集体豁免条例等。《欧盟运行条约》(TFEU)第101(3)条、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执法指南及企业并购控制条例中的个案豁免条款更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任何被指控从事垄断行为的当事人,即便不符合集体豁免标准,仍可援引个案豁免制度来进行抗辩。可见,美欧两种分析模式尽管存在差异,但一个共同点是强调垄断行为可能存在正当理由或积极效果,因而不是只要存在消极效果就认定其违法,而是需要进一步分析是否应当被豁免。
垄断行为一旦被豁免,本质上就免于违法认定。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豁免分析不是垄断行为合法性认定中的“例外”,而是必经阶段,即所有的垄断行为,执法机构在分析其合法性时都要判断是否应当被豁免。〔7〕参见许光耀:《〈反垄断法〉中垄断协议诸条款之评析》,载《法学杂志》2008 年第1 期,第18 页。既然豁免分析与垄断行为合法性密切相关,豁免制度也就构成了垄断行为合法性认定中的重要一环。
反垄断法豁免分析的本质是利益权衡,即在涉案行为产生了限制竞争效果时,基于限制竞争的必要性和同时带来的积极收益而容忍这种限制。这正是比例原则的主要内容。比例原则也强调目标与手段的平衡,一方面要求手段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防止手段造成的损害超过目标收益。从这个角度看,比例原则可作为豁免分析的重要方法。具体来说,任何垄断行为都是为了追求一定的目标,在目标合法的前提之下(如果目标不合法,手段就无须再分析了),〔8〕比例原则所包含的三个要求似乎不包括目的的合法性,但有学者指出,欧盟法院和我国学者的基本看法是,比例原则中的适当性要求本身就包含了合目的性,即目的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参见杨登峰:《从合理原则走向统一的比例原则》,载《中国法学》2016 年第3 期,第98 页。如果采用限制竞争的手段来实现该目标,按照比例原则的要求,则必须确保限制竞争具有必要性,属于最小限制,且限制竞争的效果不能超过目标收益。符合比例原则的垄断行为,可以被豁免,否则就应被禁止。
我国《反垄断法》中也有豁免制度的规定,但不论是第15 条规定的垄断协议豁免、第17 条涉及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豁免,还是第28 条规定的经营者集中控制豁免,在豁免标准上都语焉不详,要么缺少手段上的必要性限制,要么缺少结果上的利大于弊要求,且相互之间还有不一致之处。这一方面不利于执法机构准确适用豁免规则,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企业对自己行为形成合理预期。基于此,有必要引入比例原则,对我国《反垄断法》中的豁免条款进行改造。
(四)比例原则是实现多元价值平衡的重要工具
在如今价值多元的时代,比例原则之所以重要,还有一个特殊背景,即现代反垄断法的实施进行了更多的价值考量。反垄断法致力于经济效率提升,但经济效率不是孤立的目标,经济发展必须与整个社会进步相协调。我国当前强调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就是一种典型的综合发展观,各种经济的与非经济的价值追求融贯其中,如协调发展强调平衡,绿色发展强调环保,共享发展强调分配。但毫无疑问,这些价值之间容易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在现代反垄断法的实施中十分普遍。解决价值冲突离不开利益衡量,比例原则是利益衡量的重要工具。
传统的反垄断经济学理论认为,垄断者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必然会将产量设定在边际利润等于边际成本的时候,这时的产量远低于竞争性水平下的产量,价格却比竞争性价格要高。换言之,市场主体之所以限制竞争,目的是通过限制产量、提高价格来获得更多利润。但实践表明,企业从事垄断行为有时也可能不为私利,或者同时有利于公益的实现。例如,竞争者之间订立限产协议可能是为了履行环境法上的义务,如淘汰污染环境的产能;〔9〕参见焦海涛:《环境保护与反垄断法绿色豁免制度》,载《法律科学》2019 年第3 期,第107 页。出版社限制图书零售价格可能是为了用畅销书的利润补贴不畅销书的亏损,从而保证不畅销书的顺利出版,进而保护文化多样性。〔10〕参见焦海涛:《文化多样性保护与反垄断法文化豁免制度》,载《法学》2017 年第12 期,第81 页。这类限制竞争行为,从目的或效果上看,具有明显的公共利益属性,尽管这些公共利益可能是非经济性的,与反垄断法的经济效率目标存在较大差异,但在强调经济与社会同步发展的今天又特别重要。尤其在我国,过去一度重视单纯的经济发展已带来了严重的环境与社会问题,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法律制度,应在促进发展目标上实现由单一的经济发展向综合发展的制度转型。对这类限制竞争行为,反垄断法如果一概予以禁止,效果上可能促进了竞争,但却牺牲了环境或文化方面的公益,结果可能得不偿失。
比例原则可用于解决这类利益冲突。比例原则要求合比例、适度,其精神在于反对极端、实现均衡,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11〕参见王利明:《民法上的利益位阶及其考量》,载《法学家》2014 年第1 期,第84 页。如果竞争秩序的维护,不必通过禁止这类限制竞争行为也能实现,则执法机构禁止这类行为就超过了必要的限度;或者,禁止这类行为带来的竞争收益,不足以弥补环境与文化破坏带来的利益损失,则执法活动也不合乎比例。同样,如果实现环境保护或文化多样性保护的目标不必通过限制竞争的方式,则限制竞争行为就不合乎比例,进而可被禁止;或者,环境与文化方面的收益难以匹配限制竞争带来的效率损失,则损益不平衡,限制竞争行为也有可能被禁止。
二、比例原则的适用边界
比例原则在反垄断立法中较少直接规定,因为它是公权行使行为的普遍要求,通常规定在具有宪法属性的法律规范之中,或者具有基础地位的行政程序法中。欧盟法中的比例原则主要体现为《欧盟条约》(TEU)第5(4)条,即“按照比例原则,联盟行动的内容和形式不应超过实现条约目标所必需的范围”。〔12〕《欧盟基本权利宪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第49(3)条也规定了刑事领域的比例原则,即“惩罚的严重程度不得与犯罪行为不成比例”(The severity of penalties must not be disproportionate to the criminal offence)。虽然该条并不专门针对反垄断法,但基于《欧盟条约》的宪法性地位,比例原则在欧盟法中也就具有宪法地位。〔13〕See Firat Cengiz, Alrosa v. Commission and Commission v. Alrosa: Rule of Law in Post-Modernisation EU Competition Law Regime, http://ssrn.com/abstract=1674345, p.17, accessed October 22, 2019.欧盟法院明确将比例原则视为欧盟法中的基本原则。〔14〕See Tor-IngeHarbo, “The Function of the Proportionality Principle in EU Law” 16(2) European Law Journal 159 (2010).
在反垄断法实践中,比例原则的适用早已得到肯定。例如,欧盟委员会在1998 年颁布、2006 年修订的“罚款指南”〔15〕See Guidelines on the method of setting fines imposed pursuant to Article 23(2)(a) of Regulation No 1/2003, OJ [2006], C 210/2.详细描述了如何根据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与持续时间来设定罚款数额;在2003 年判决的通用汽车案中,法院认为,尽管在决定罚款数额上欧盟委员会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但法院仍有权核实罚款数额是否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16〕See Case T-368/00, General Motors Nederland BV and Opel Nederland BV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3] E.C.R. II-04491, para.189.
在适用对象上,不同于传统公法领域中比例原则主要规范公权活动,反垄断法中的比例原则不仅与公权行为(public acts)相关,也与私人限制竞争行为有关(private restrictions of competition)。比例原则不仅适用于执法活动,还适用于私人主体(包括行政性垄断的实施者)实施的限制竞争行为。这主要体现在限制竞争行为的违法性认定或豁免分析之中。通常,当行为人主张限制竞争行为基于追求一个合法目标或带来促进竞争效果时,应证明该行为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被免于违法认定或被豁免。美国反托拉斯法中规制垄断协议的“合理原则”就暗含了比例原则的要求。合理原则允许被告提出限制行为促进竞争效果的抗辩,抗辩提出之后,原告一旦证明存在“明显限制性较小的替代方式”,被告的抗辩就不被接受。〔17〕参见兰磊:《比例原则视角下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解释——以视频网站上广告拦截和快进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为例》,载《东方法学》2015 年第3 期,第75 页。美国《横向合并指南》和《非横向合并指南》也允许效率抗辩,但将效率界定为“合并特有的效率”(merger-specific efficiencies),意即该效率由合并产生,且在没有该合并或不采取其他具有相同反竞争效果的措施时就不可能获得该效率。〔18〕See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ugust 19, 2010), p.30.欧盟竞争法中的豁免分析同样包含了比例原则:垄断协议当事人援引《欧盟运行条约》(TFEU)第101(3)条进行效率抗辩时,必须证明协议对效率的取得不可或缺(indispensability);合并控制中的效率抗辩,如同美国一样,也要求当事人证明必须产生了“合并特有的效率”(merger-specific);〔19〕See 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horizontal mergers under the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OJ [2004] C31/5, para 78.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为规制中,除效率抗辩外,当事人还可基于“客观必然性”(objective necessity)进行抗辩,而所谓的“客观必然性”主要就是指滥用行为的实施对一个合法目标的实现具有必要性和相称性。〔20〕See Guidance on the Commission’s enforcement priorities in applying Article 82 of the EC Treaty to abusive exclusionary conduct by dominant undertakings (2009/C 45/02), OJ [2009] C 45/7, para. 28.
在适用方式上,反垄断法中比例原则的适用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比例原则的适用包含三个必须同时满足的要求,也即所谓的“三阶理论”:一是适当性,也称妥当性,〔21〕参见余凌云:《论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载《法学家》2002 年第2 期,第33 页。指手段适合用来实现目标,即所采取的手段与目标相关并有助于目标实现;二是必要性,也称不可替代性,指在实现目标的各种手段中,应选择最为温和、侵害最小的手段,或者说当前手段之外并不存在侵害效果更小的替代性手段;三是均衡性,指目标与手段之间合乎比例,即手段造成的伤害不应超过目标实现带来的好处。这三个要求可分别简称为适当、必要和均衡,“适当”可形象理解为“是否可以这样做(这样做是否服务于目标的有效实现)”,“必要”可形象理解为“是否必须这样做(要实现目标是否只能这样做)”,“均衡”则是从结果上进行“利益衡量”,防止出现“大炮打麻雀”之类的情况出现。〔22〕参见黄学贤:《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研究》,载《法律科学》2001 年第1 期,第77 页。基于此,比例原则可解释为,当有多个措施都能达成目标时,应当选择损害效果最小的措施,且因此造成的不利影响,不应与所追求的目标不成比例。〔23〕这是在1994 年涉及农业政策的“Crispoltoni 案”中,欧盟法院对比例原则的解释。See Joined Cases C-133/93, C-300/93 and C-362/93, Antonio Crispoltoni v FattoriaAutonomaTabacchi and Giuseppe Natale and Antonio Pontillo v DonatabSrl., [1994] ECR I-4863, para. 41.严格来说,比例原则的适用必须逐一检查上述三个要求是否全部满足,但实践中,比例原则的适用标准相当灵活。有学者就指出,欧盟法院在适用比例原则时,有时只检查适当性与必要性标准,而欧盟成员国法院甚至仅适用最后一项即均衡性标准。〔24〕参见高秦伟:《论欧盟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载《政法论丛》2012 年第2 期,第89 页。在反垄断法中,比例原则的适用同样十分灵活。〔25〕See Ivan Draganic,“ State Aid or Compensation for Extra Costs: Tuning the Test of Proportionality in EC Competition Law” Eur. St. Aid L.Q. 693( 2006).很多时候,这三个条件也并非累积适用,尤其是第三个要求即均衡性,在有些案件中会被忽略。〔26〕See Wolf Sauter, “Proportionality in EU competition law” 35(7) E.C.L.R.327 (2014).原因之一是,反垄断法上的有些行为,不能单纯地进行结果衡量,尤其是效率评价,为了实现更重要的目标,即便带来效率损失,有时也应容忍。〔27〕相关分析可参见焦海涛:《社会政策目标的反垄断法豁免标准》,载《法学评论》2017 年第4 期,第136 页。此外,第二个要求即“必要性”的判断,有时也不那么严格,并非真的要求穷尽分析可能实现目标的所有手段,然后选择损害最小的手段——垄断案件的经济性与复杂性决定了很多时候这也不大可能。
在适用范围上,比例原则适用于反垄断执法的全过程,但在不同的执法程序中存在差异。从整体看,垄断案件从启动调查到作出决定的整个过程,比例原则都应被遵守。只不过,执法调查中的比例原则适用,与一般行政执法程序并无太大差异,本文不再关注。就执法机构作出的决定来说,现代反垄断法实施的一个典型特点是案件处理结果的多元化,在不同的案件处理程序中,是否以及如何贯彻比例原则难免存在差异。
垄断案件经调查而作出的执法决定主要分为三类:一是违法决定,在确认违法后通常还施加一定的法律责任,最常见的是罚款;二是执法机构与行为人之间经和解程序而作出的承诺决定,在我国反垄断法中主要体现为“中止/终止调查决定”;三是执法机构基于行为人的有效抗辩而作出的豁免决定。三类执法决定对相对人权益的影响不同,比例原则的贯彻要求也就有所区别。一般来说,违法决定会对相对人施加直接限制,具有必然的“侵害性”,比例原则应被严格适用;承诺决定通常不直接“侵害”相对人权益,但有间接影响,所以比例原则可以适用,但承诺决定的产生基础是和解,如果相对人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接受了对其更为严重的限制,对执法机构是否还应施加比例原则的要求,可能需要进一步分析;豁免决定对相对人权益基本没有不利影响,比例原则在执法机构身上也就没有适用余地,所以,豁免决定中的比例原则分析,应该主要针对企业行为,本质上是分析垄断行为合法性。
基于上述认识,下文将详细分析在不同的执法决定中,比例原则贯彻的基本要求及主要差异。之所以按照执法决定的种类而非反垄断法调整的三种或四种垄断行为类型来分析比例原则的适用,主要基于四个方面的考虑。(1)不同的执法决定,对相对人权益的影响差别较大,比例原则的适用要求也就有所不同,这种差异是将比例原则引入反垄断法之中必须予以区分的。(2)尽管在不同的垄断行为类型中,比例原则的适用也有差异,但这种差异与不同执法决定中比例原则的适用差异相比要小得多,所以后者更值得关注。例如,不论是对垄断协议还是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进行执法,比例原则对执法机构的要求应当不会有实质性区别。(3)在违法决定中适用比例原则,人们很少有异议,但承诺决定和豁免决定中是否以及如何适用比例原则,学界还较少关注,所以,比例原则在这两类特殊的执法决定中的适用,有必要集中予以论述。(4)比例原则尽管也可用于分析垄断行为的合法性,但主要还是约束执法机构的一种法律实施原则,所以,依据执法机构的行为来论述比例原则可能更合理,也更能体现比例原则的适用价值。
三、违法决定中的比例原则
(一)处罚措施的选择
执法机构经调查确认企业违法,进而作出违法决定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处罚措施的选择。比例原则强调手段与目标之间的相称关系,在违法决定中,处罚是手段,选择的处罚措施应与处罚所要实现的目标相关并有助于该目标的实现(适当性),且在可以实现目标的各种处罚措施中,应选择相对人负担最轻的措施(必要性)。
处罚措施是否适当与必要,需要结合其对目标的实现程度来判断。那么,处罚的目标是什么?有学者指出,垄断行为被确认后,有效的救济措施应当实现三个目标:一是制止当前的违法行为;二是阻止相关行为再次发生;三是恢复被破坏的竞争条件。〔28〕See E. Thomas Sullivan, “Antitrust Remedies in the U.S. and EU: Advancing a Standard of Proportionality” 48 Antitrust Bull. 420 (2003).这三个目标的共同本质是确保反垄断法规则的有效遵从。《欧盟运行条约》(TFEU)第103(2)条明确指出,罚款的目的是确保TFEU 第101 条和第102 条禁止性规则的遵从(compliance)。为了保证规则遵从的有效性,必须施加有威慑力的处罚措施,所以也可以说,处罚的目标是形成威慑(deterrence)。威慑主要指对行为人及其他人以后从事类似违法行为形成阻碍效果。波斯纳认为,“一个救济体系的基本目标是威慑人们不敢违反法律。另一个目标是对违法行为的受害者进行补偿,但这是一个次要的目标,因为,一个规划合理的威慑体系将把违法的几率降低到一个很低的水平,而且,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作为副产品,这样一个体系将会保证充分的补偿,除非补偿的执行成本高到无法承受”。〔29〕[美]理查德·A.波斯纳:《反托拉斯法》,孙秋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313 页。在2014 年的“Saint Gobain 案”中,欧盟常设法院也指出,威慑是罚款的目标,也是欧盟委员会计算罚款数额的参照点(a reference point)。〔30〕See Cases T-56/09 and T-73/09, Saint-Gobain Glass France and Others v ommission, ECLI:EU:T:2014:160, para. 380.只不过,反垄断法所追求的威慑,应当是一种有效威慑或者说最优威慑(optimal deterrence),〔31〕参见王健、张靖:《威慑理论与我国反垄断法罚款制度的完善》,载《法律科学》2016 年第4 期,第125 页。既要防止威慑不足,也要防止威慑过度。威慑不足(如罚款数额过低)不足以预防后续违法行为,威慑过度(如罚款数额过高)则会对企业正常行为产生不良影响——波斯纳指出,“严厉的惩罚也许会阻止处于禁止边缘的合法行为”,“也许会导致潜在的被告过于回避他意图进入的区域”。〔32〕[美]理查德·A.波斯纳:《反托拉斯法》,孙秋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314、315 页。
在有效威慑目标之下,判断处罚措施的选择是否适当,主要看处罚措施是否服务并有助于有效威慑目标的实现。处罚显然是为了形成威慑,但要确保威慑的有效性,就要避免威慑不足。具有适当性的处罚措施应当足以匹配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如果违法行为严重,处罚措施较轻,则处罚难以起到威慑效果。对违法性越是严重的垄断行为,执法机构应选择越为严厉的法律责任。有些国家对构成“本身违法”的横向垄断协议引入了刑事制裁,正是为了确保处罚措施的适当性。
在有效威慑目标之下,判断处罚措施的选择是否必要,主要看处罚措施是否超过了实现有效威慑的必要限度。如果说适当性要求主要是为了避免威慑不足,必要性要求则主要是为了避免威慑过度。一般而言,选择的处罚措施越严厉,越能形成威慑效果,但如果处罚的效果超出了有效威慑的范围,则超出部分应被认为不具有必要性,例如,对轻微的垄断行为施加刑事责任就没有必要。在各国立法中,垄断行为的处罚措施,通常体现为一个威慑效果递增的责任体系,包括终止违法行为(如我国反垄断法中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罚款、取消主体资格(如我国反垄断法中针对行业协会的“依法撤销登记”)、刑事责任等具体责任形态。具体选择哪种处罚措施,执法机构应根据垄断行为的客观因素和行为人的主观因素,在个案中进行权衡。很显然,不是所有的垄断行为都必须施加罚款或刑事责任。
影响处罚措施选择的客观因素主要指垄断行为自身状况,包括垄断行为类型、造成的损害后果、违法行为的持续时间等。例如,当行为人仅达成但未实施纵向垄断协议时,罚款可能就是没有必要的。影响处罚措施选择的主观因素主要指行为人的过错程度及事后消除垄断行为的努力,包括行为人是否知晓垄断行为的违法性、是否被胁迫参与垄断行为、是否主动终止垄断行为及是否积极配合执法调查活动等。例如,对一些横向垄断协议来说,罚款是确保反垄断法威慑力的必要手段,但当违法者对行为的违法性并无合理认知时,罚款就未必必要,终止违法行为可能就足以让行为人以后主动回避这类违法行为。
(二)罚款数额的确定
在确认罚款的处罚措施具有适当性(罚款有助于形成有效威慑)和必要性(不罚款不足以形成有效威慑)后,接下来还要确定具体的罚款数额。确定罚款数额也需要进行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分析,目的是在确保有效威慑的前提下,找出最低罚款数额。罚款数额过低,无法实现有效威慑目标(不适当);罚款数额过高,又可能产生过度威慑(不必要或不均衡)。
1.适当性分析
适当性分析主要是防止罚款数额过低不足以形成有效威慑。威慑是通过提高违法行为的成本让人们不敢从事违法行为,那么,违法成本应提高到什么程度?经济学的方法是考虑垄断行为的社会成本(social costs)。社会成本即垄断行为施加于整个社会的成本,包括行为人自身承担的私人成本和由行为人之外的其他主体承担的额外成本。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差异决定着罚款数额的高低。两种成本之间的差异越大,就说明他人分担的社会成本越多,垄断行为造成的社会损失就越严重,因而需要更高的罚款数额。罚款的目的就是将垄断行为的社会成本转化为行为人的私人成本。波斯纳较为推崇社会成本的分析方法,认为“它是一种效率的标准,因此是为反托拉斯违法行为设计救济时特别适宜采用的标准”。〔33〕[美]理查德·A.波斯纳:《反托拉斯法》(第2 版),孙秋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313-314 页。
不过,社会成本的概念过于抽象,计算也较困难,实际上没有提供罚款数额的具体确定方法。罚款数额是否合适,需要通过一些客观因素来衡量。大多数国家反垄断法以列举方式,概括了确定“罚款的基础数额”(basic amount of the fine)的典型考虑因素,再辅以一些从重/从轻情节(aggravating/mitigating circumstances)来调整基础数额。例如,欧盟第1/2003 号条例第23(3)条规定,在确定罚款数额时,必须同时考虑到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gravity)和持续时间(duration);我国《反垄断法》第49条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确定具体罚款数额时,应当考虑违法行为的性质、程度和持续的时间等因素。从重或从轻情节的内容,在欧盟2006 年“罚款指南”中有详细列举,〔34〕See Guidelines on the method of setting fines imposed pursuant to Article 23(2)(a) of Regulation No 1/2003, OJ [2006], C 210/2, paras 28, 29.我国正在制定的《关于认定经营者垄断行为违法所得和确定罚款的指南》(征求意见稿)也效仿欧盟并做了更详细规定。
欧盟第1/2003 号条例和我国《反垄断法》第49 条规定考虑因素过于简单,而且所列举因素之间也不是并列关系,例如,违法行为的持续时间,实际上反映的就是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持续时间越长,违法程度也就越严重。我们可以从静态与动态两个方面,大致将影响罚款基础数额的因素分为两类,这两类因素都可统称为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
第一,违法行为的固有属性(静态),即违法行为属于哪种类型的垄断行为,也就是欧盟“罚款指南”所称的违法行为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infringement)。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首先可通过行为性质反映出来,诸如横向的价格固定、市场划分、限制产量等垄断协议,由其固有属性决定,危害性通常比纵向协议大得多,对这类行为要想形成有效威慑,必须处以更高数额的罚款。〔35〕See Guidelines on the method of setting fines imposed pursuant to Article 23(2)(a) of Regulation No 1/2003, OJ [2006], C 210/2, para. 23. 我国正在制定的《关于认定经营者垄断行为违法所得和确定罚款的指南》(征求意见稿)也对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销售数量、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这三类垄断协议设定了上一年度销售额3%的初始罚款比例,而其他横向垄断协议和纵向垄断协议的初始罚款比例只有2%和1%。可以说,这类违法行为具有“固有的严重性”(inherent gravity)。〔36〕See Hans Gilliams, Proportionality of EU competition fines: proposal for a principled discussion, https://ssrn.com/abstract=2524375, p.7, accessed October 22, 2019.这种严重性主要体现在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之上,因为实施这类行为通常没有其他目的,就是为了限制竞争。这也是欧盟将这类行为称为“目的型限制”(restrictions by objects)的主要原因。〔37〕欧盟区分了垄断协议限制竞争的目的和效果,由此将垄断协议分为目的型限制(restrictions by objects)和效果型限制(restrictions by effects)。目的型限制又称核心限制(hardcore restrictions),指那些直接以限制竞争为目的协议。对这些限制,通常不需要进行效果分析就可推定其具有违法性。大多横向垄断协议和转售价格维持行为,在欧盟都被归入核心限制的范围。See Yi Heng Alvin Sng,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object’ and ‘effect’ in EU competitionlaw and concerns after Groupement des cartesbancaires (C-67/13P)” 37(5) E.C.L.R. 179-185 (2016).违法行为的固有属性是评估违法行为严重性的第一步,在此之后才会评估违法行为的实际影响。在多个案件中,欧盟法院甚至认为,反竞争行为的效果(effects)不是评估罚款数额的决定性标准,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因素(factors relating to the intentional aspect)可能比效果因素更为重要。〔38〕See Case C-194/99P,Thyssen Stahl v Commission, [2003] ECR I-10821, para.118; Case C-534/07P,Prym and Prym Consumer v Commission, [2009] ECR I-07415, para.96; Case C-501/11 P, Schindler Holding and Others v Commission, ECLI:EU:C:2013:522,para.134.
第二,违法行为的实际损害(动态),即违法行为给市场竞争带来的限制效果。实际损害是反映违法行为严重程度的直观标准,一个符合比例原则的处罚措施,必须反映违法行为的实际损害。〔39〕See William E. Kovacic, “Designing Antitrust Remedies for Dominant Firm Misconduct” 31 Conn. L. Rev. 1312 (1999).一般来说,实际损害需要在个案中依据下列因素评估:(1)与违法行为相关的销售额大小;(2)违法行为所涉及的商品与地域范围;(3)违法行为人合计的市场份额;(4)违法行为是否被实施以及被实施后的持续时间;等等。
根据上述两个因素确定的只是罚款的基础数额,基础数额在个案中还要根据从重/从轻情节进行调整。从重/从轻情节这里不予讨论,但欧盟“罚款指南”还规定了两种增加罚款数额的情况,这两种情况是否符合比例原则需要进一步分析:一是经营者的全部销售额远远大于与违法行为相关的销售额;二是在违法收益可计算的情况下,违法收益超过了依据指南确定的罚款数额。欧盟“罚款指南”解释增加罚款数额是为了确保罚款的威慑力(specific increase for deterrence),换言之,如果不提高罚款数额,难以实现有效威慑的目标。果真如此的话,增加罚款数额就符合比例原则中的适当性要求,但这两种情况不可相提并论。第一种情况下,企业的全部销售额中可能很大一部分与违法行为没有关联,而罚款要反映违法行为严重程度的话,只能以“与违法行为相关的销售额”作为计算基础,不能因为企业全部销售额大就施以更高的罚款。第二种情况有所不同,违法收益与违法行为的实际影响密切相关,违法收益高意味着违法行为产生更多的损害结果,如果综合各种因素而确定的罚款数额低于违法收益,只能说明违法行为的严重性未能被充分评估,这时提高罚款数额是适当的。可以说,违法收益也是评估违法行为严重性的一个因素。〔40〕See CaseT-404/08, Fluorsid and Minmet v Commission, ECLI:EU:T:2013:321, para. 145.从确保有效威慑的角度看,在任何一个案件中,罚款数额都应当高于违法收益,否则就无法阻止以后类似行为的发生。这可能也是我国反垄断法将罚款作为“没收违法所得”之外的处罚措施的原因。
2.必要性分析
比例原则下的必要性分析,主要是进行LRA/LRM(Less Restrictive Alternative/Measure)测试,即找出能够实现目标的各种措施,然后选择限制效果最小的措施。就罚款数额来说,主要是确定能否通过更低的罚款来实现有效威慑目标。必要性分析的一个直观方法,是进行比较,即看是否存在具有可比性的违法行为(comparable infringements)却被处以更低数额的罚款。所谓具有可比性的违法行为,主要指严重程度相当的违法行为。
最常见的比较法是历史比较(纵向比较),即看之前是否存在相同或类似行为却被处以更低罚款。在找到之前存在一个严重程度相似但罚款数额却更低的违法行为时,也不当然意味着LRA 测试的失败。因为必须考虑随着时间推移,罚款数额需要随之调整的可能性(如销量没有明显变化,但物价上涨导致销售额增加),尤其在之前的类似行为发生较久时,不能单纯进行罚款数额的比较。此外,还有两种可能导致罚款数额增加但却不违背比例原则的情况:一是之前的违法行为处罚不合适,罚款数额没能充分反映出违法行为的严重性;二是人们对同一行为的违法性认识发生了变化,之前被认为不太严重的违法行为,现在严重性被充分认识到了(当然,也可能出现相反情况,如人们对转售价格维持的认知)。此外,还可进行地域比较(横向比较),即看在相同的法律适用标准下,是否存在其他地域的相同或类似违法行为被执法机构处以更低罚款。在我国,反垄断执法可向地方授权,这个问题更具有可比性。对违法程度相同的垄断行为,尽管可能由不同的执法机构处理,但法律标准应当一致。如果不同地域间存在明显差异,则说明罚款数额的设定存在问题。
3.均衡性分析
比例原则的第三个要求是均衡,即进行结果上的衡量,防止弊大于利。罚款数额是否符合均衡性要求,主要看罚款带来了多大的不良影响。这里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可能产生的效果,其中一个较为特别的因素是企业的支付能力(inability to pay)。经过适当性与必要性测试之后的罚款数额,如果超过了企业的支付能力,可能不符合均衡性要求,进而需要调整。
超过支付能力的罚款可能会让企业濒于破产,而破产会带来一系列经济与社会问题,如产业链断裂、市场竞争被削弱,就业与社会稳定也可能受到影响。超过支付能力的罚款也会影响公司股东、职工和债权人利益。此外,在高集中度市场,罚款容易通过产品提价来转嫁给消费者,所以过高的罚款也会影响消费者福利。〔41〕参见王健:《威慑理念下的反垄断法刑事制裁制度——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修改稿)〉的相关规定》,载《法商研究》2006 年第1 期,第5 页。
为防止罚款过度,反垄断法通常会对罚款数额设置上限。我国《反垄断法》规定的罚款上限是上一年度销售额的10%,这主要借鉴了欧盟第1/2003 条例第23(2)条的规定,即“对每个参与违法的企业或企业协会的罚款,不应超过其前一营业年度总营业额的10%”。营业额10%的法定上限,基本与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无关。欧盟法院的观点非常明确,之所以设定10%营业额的上限,就是防止企业无力支付。在2014 年的“Saint-Gobain 案”中,欧盟常设法院认为,不同于根据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来确定罚款数额,营业额10%的法定限制具有独立目的,主要是避免对企业施加超过其支付能力的罚款,因此,评估最高罚款数额必须参考企业的规模与经济能力(size and economic power)。〔42〕See Cases T56/09 and T73/09, Saint-Gobain Glass France and Others v Commission, ECLI:EU:T:2014:160, para. 451.欧盟委员会的“罚款指南”除在第32 条重申了营业额10%的法定上限,还在第35 条规定,特殊情况下委员会可基于企业申请考虑企业的支付能力,但不会仅仅基于企业不利或亏损状况而减少罚款,只有客观证据表明,依据指南施加罚款将不可避免地危及企业生存或使其资产失去价值时才会减少罚款数额。不过,由于第35 条的适用限制条件较多,实践中并不常用。2014 年作出处罚决定的“钢铁研磨剂案”(steel abrasives)是一个例子。对本案所有当事人来说,钢铁研磨剂销售额占营业额很大比例,因此,所有当事人的罚款数额都达到了总营业额的10%,委员会在考虑到各公司特点及参与违法行为的不同后,减少了罚款。〔43〕See Antitrust: Commission fines producers of steel abrasives €30.7 million in cartel settlement,IP/14/359,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4-359_en.htm, accessed October 22, 2019.
与支付能力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企业规模。规模较小的企业,支付能力也弱,所以确定罚款数额应当考虑企业规模。欧盟法院在判例中也提到了企业规模,但是在解释营业额10%的法定上限时提到这一问题,而营业额10%的上限不足以兼顾规模较小企业的支付能力。对“单一产品公司”(single product companies)来说,这尤其是一个问题。所谓单一产品公司,指除违法行为所涉及的市场外,该公司无其他业务。根据各国罚款通例,罚款的计算基数是涉案销售额。例如,欧盟“罚款指南”规定的罚款基础数额是“与违法行为相关的营业额”乘以一定比例(根据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确定,最高可达到30%),再乘以违法行为的持续时间(按年计算);我国正在制定的《关于认定经营者垄断行为违法所得和确定罚款的指南》(征求意见稿)也以“涉案商品的销售收入”作为计算罚款所依据的销售额,再乘以基础罚款比例(1%、2%或3%),并根据持续时间上调罚款比例(以一年为基数,每增加一年上调1%)。对单一产品公司来说,涉案销售额也就是其全部营业额。这样一来,以此为基础计算出来的罚款数额很容易就超出其支付能力。我们假设下列情形:某单一产品公司甲的涉案销售额是100万元,另一公司乙的涉案销售额也是100 万元,但全部销售额是500 万元。如果它们从事了违法程度相同的垄断行为且持续两年,假设罚款比例是5%,则按照欧盟“罚款指南”,两家公司都需支付罚款100×5%×2=10 万元。10 万元的罚款数额均未超过两家公司全部营业额10%的上限,但很显然,对甲公司来说,10 万元的负担明显要重得多,甚至已超过其支付能力。所以,在营业额10%的上限之外,完全可以将企业规模作为一项独立因素,用作判断罚款数额是否超出企业支付能力的考量因素。英国公平贸易办公室(OFT)在其2012 年制定的“罚款指南”中就明确指出,罚款数额不应与企业规模和财务状况不成比例。〔44〕See OFT’s guidance as to the appropriate amount of penalty, September 2012, 2.19-2.20, http://oft.gov.uk/shared_oft/business_leaflets/ca98_guidelines/oft423.pdf, accessed October 22, 2019.
基于企业支付能力而调整罚款数额表面上看可能有违“过罚相当原则”,但这正是比例原则所蕴含的基本精神。这倒不是说要对弱者给予更多保护,而是因为罚款必须考虑实际影响,防止弊大于利。如果罚款动辄让企业破产,则随之而来的竞争削弱、资源浪费、工人失业乃至经济稳定等问题就是罚款带来的“社会成本”,这些成本很大一部分将由行为人之外的主体承受。罚款是为了惩罚违法行为人,只有罚款的效果由行为人承受,罚款才有意义。因此,一个基本原则是,罚款不应达到让企业濒临破产的程度,就像对自然人的罚款/罚金不应危及其基本生活一样。如果行为人从事的垄断行为违法性特别严重,也可优先考虑通过其他方式如停业整顿、吊销证照来让其付出代价。将罚款数额与支付能力挂钩,正是一种结果上的利益衡量,体现的就是比例原则中的均衡性要求。
四、承诺决定中的比例原则
反垄断法中的承诺决定,是一种特殊的垄断行为处理方式。在执法机构调查垄断案件时,如果被调查的企业向执法机构作出终止、修正或从事特定行为的承诺,执法机构认为承诺足以消除垄断行为消极影响的,可以接受该承诺并据此作出承诺决定,从而结束案件调查程序。承诺决定对企业行为是否违法保持沉默,也不会对企业施加任何惩罚,〔45〕See John Temple Lang,“ Commitment decisions under Regulation 1/2003: legal aspects of a new kind of competition decision” 24( 8) E.C.L.R. 347( 2003).但企业需承诺从事特定行为,以消除涉案行为的消极影响。企业承诺的义务会载于承诺决定之中,而承诺决定与执法机构的其他决定在效力上没有区别,所以,承诺决定也会对企业行为产生限制效果,为此,承诺决定的适用也应坚持比例原则。〔46〕See Alberto Pera, Michele Carpagnano,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Commitment Decis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29 (12) E.C.L.R. 672 (2008).
(一)承诺内容的确定
承诺内容首先应符合适当性的要求,即有助于实现承诺决定的目标。承诺决定主要适用于危害性不大、处罚依据不明确或者调查陷入僵局的案件,对这些案件的处理不在于形成有效威慑,而是尽快消除涉案行为的消极影响。〔47〕参见焦海涛:《反垄断法承诺制度的适用范围研究》,载《法商研究》2013 年第2 期,第85 页。要实现这一目标,承诺决定的内容必须明确并有合理期限。承诺内容首先应当具体,不能含糊其词、模棱两可,而要尽量采用确定性的表述,诸如“争取”“尽量”“进一步”“大幅”“明显地”这类较为弹性的标准应尽量避免。此外,承诺内容应具有及时性。如果可能,应明确义务履行的具体期限;对不能明确设定期限的义务,也要保证履行的及时性。
承诺内容的确定还应满足必要性要求,主要体现为在确保目标实现的情况下,执法机构不得要求企业作出超过必要限度的承诺。必要性判断依赖于LRA 测试,意味着当解决竞争问题的措施有多个时,企业可选择对其影响最小的措施作出承诺,执法机构不得要求企业作出过重的承诺,更不得事先拟定好承诺内容让企业被动接受。〔48〕参见焦海涛:《反垄断法承诺制度适用的程序控制》,载《法学家》2013 年第1 期,第89 页。在必要性判断上,应坚持的一个基本共识是,行为措施优于结构措施。企业承诺采取的措施可以是行为性的(behavioural)也可以是结构性的(structural),〔49〕See Antitrust: commitment decisions -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MEMO/13/18,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13-189_en.htm, accessed October 22, 2019.前者指从事特定行为如承诺给予许可,后者指剥离特定资产或业务。两种措施具有不同影响:行为措施对企业来说负担更轻,但执法机构需要持续监督,执法成本较大;结构措施通常能一次性解决竞争问题,执法成本较小,但资产或业务剥离对企业影响较大。由于结构措施会对企业造成严重甚至不可逆转的影响,故只要能解决竞争问题,企业通常只需对行为措施作出承诺。只有在行为措施无法解决竞争问题,如难以产生与结构措施同等效果,或实施任何同样有效的行为措施会给企业造成更重负担时,才应采取结构措施;且对企业在垄断行为发生前就已存在的结构,只有当存在导致持久或反复的违法行为的重大危险时,才能要求企业承诺予以调整。
(二)市场主体主动承诺的特殊性
在比例原则约束下,执法机构不得要求企业作出过重承诺,这是防止出现“监管施压”(regulatory arm-twisting)〔50〕See Sonja Eibl, “Commitment Decisions: An Australian perspective” 26 (6) E.C.L.R. 335 (2005).的重要制度安排。比例原则对企业的最大好处是减轻负担,但问题是,如果企业自愿作出较重的承诺,而非执法机构的要求或强制,则承诺决定是否还需接受比例原则的限制?
在欧盟实践中,“Alrosa 案”首次探讨了承诺决定中的比例原则适用。该案基本情况是:全球两大原钻生产商De Beers 和Alrosa 在2001 年订立了一份五年期的供货合同,由Alrosa 保证向De Beers每年供应价值8 亿美元的原钻。欧盟委员会对该合同启动了两项调查程序:对两家企业启动了垄断协议调查,对De Beers 另有一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调查,因为供货合同具有排他性,会导致其他潜在原钻供应商无法向De Beers 供货。2004 年,两家企业向委员会作了共同承诺(joint commitments),提出将交易量逐年降低。该承诺因遭到其他利害关系人反对而未被欧盟委员会接受。2006 年,De Beers 重新作出单独承诺,欧盟委员会据此作出了承诺决定。〔51〕See Case COMP/B-2/38.381 -De Beers, OJ [2006] L 205/24.依据承诺决定,De Beers 承诺从2006年开始逐年缩减向Alrosa 购买的原钻量,至2009 年不再购买。
这份承诺决定会导致Alrosa 失去最大客户,于是它以利害关系人的身份起诉到初审法院(现已改为欧盟常设法院,即GC),要求撤销承诺决定。GC 审理时认为,有着比禁止De Beers 与Alrosa 之间交易更轻的措施来达到解决竞争问题的目的,欧盟委员会却没有对这些措施进行评估,而是直接依据De Beers 的承诺禁止了两家企业间的交易,这违背了比例原则的要求。GC 还指出,两家企业在2004年作出了共同承诺,欧盟委员会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个义务相对较轻因而更符合比例原则的措施不能解决竞争问题。〔52〕See Case T-170/06 Alrosa v Commission, [2007] ECR.II-02601, paras 126, 129.基于此,GC 在2007 年撤销了欧盟委员会的承诺决定。
本案特殊性在于,逐渐缩减乃至最终取消与Alrosa 交易的承诺是De Beers 自愿作出的,欧盟委员会并没有对De Beers 提出强制要求。在欧盟委员会看来,比例原则仅适用于执法机构对企业提出要求时,企业的自愿行为不受该原则约束,所以欧盟委员会上诉至欧洲法院(ECJ)。GC 认为,承诺决定来自第1/2003 号条例第9 条,而该条是对条例第7 条(终止违法行为决定)的替代,〔53〕第1/2003 号条例第9 条规定,如果欧盟委员会打算对企业作出终止违法行为的决定,则企业可向委员会作出修正或终止垄断行为的承诺,委员会可据此作出承诺决定。根据这一规定,承诺决定实际上是“终止违法行为决定”(条例第7 条)的替代程序。所以两条目的一致,都是为了确保竞争规则的有效适用。〔54〕See Case T-170/06 Alrosa v Commission, [2007] ECR.II-02601, para.95.言下之意是,既然目的相同,手段的要求也应相同,不能在适用第7 条时要求欧盟委员会遵守比例原则的要求,在适用第9 条时就不必遵守这一要求了。所以,即便企业自愿作出过重的承诺,也不能减轻欧盟委员会遵从比例原则的要求。〔55〕See Michele Messina, Jean-Claude Alexandre Ho, “Re-establishing the orthodoxy of Commitment Decisions under Article 9 of Regulation 1/2003: Comment on Commission v Alrosa” 36(5) E.L. Rev. 740 (2011).
ECJ 却认为,第1/2003 号第9 条和第7 条有着较大区分,虽然二者总体目标都致力于竞争规则的遵从,但直接目的并不相同。依据第9 条,委员会无须认定违法行为存在,适用该条的目的是解决委员会对竞争问题的担忧,而第7 条的适用需要认定违法行为存在并据此作出决定。这种区别会影响比例原则的适用。在依据第7 条作出终止违法行为决定时,根据比例原则,委员会只能给企业设定最低限度的义务要求。但在接受企业承诺时,遵从比例原则仅意味着,委员会只需考虑企业提出的承诺是否能够解决竞争问题;委员会没有义务去比较承诺内容与违法决定中义务之间的大小,即便承诺内容超过了违法决定中的义务,也不应认为不符合比例原则。而且,企业主动作出承诺,也意味着它们认可了这种让步。〔56〕See Case C-441/07 P, Commission v Alrosa, [2010] ECR I-05949, paras 46-49.基于这些判断,ECJ 得出结论:GC 混淆了比例原则在第7 条和第9 条上的不同要求,侵犯了欧盟委员会在承诺决定上的自由裁量权。〔57〕See European Commission, ECJ reverses CFI judgment on De Beers commitments Decision, EC Competition Law Reporter (No. 103 - February 2011), VOLUME 2.
该案具有重要意义,它区分了承诺决定与违法决定中比例原则的不同要求。这种区分的主要理由在于,违法决定是一种单方行为,而承诺决定是一种合意行为,在合意行为中,企业所受到的限制并非来自执法机构的单方决定,而是源于企业的自愿行为。〔58〕See Manuel Kellerbauer, “Playground Instead of Playpen: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s Alrosa Judgment on art.9 ofRegulation 1/2003” 32(1) E.C.L.R. 8 (2011).所以,在承诺决定中,执法机构没有义务去比较是否存在比企业作出的承诺更轻的措施。这种区分意味着,当企业主动提出承诺内容时,即便义务过重,执法机构也可直接据此作出承诺决定,而不会被认为违背了比例原则。只有在承诺内容是执法机构提出时,才不能要求企业接受过重的承诺。
当然,免除执法机构的比较义务,前提是企业作出承诺时完全自愿。现实中可能出现执法机构强迫企业作出承诺的情况,或者企业作出承诺时,执法机构不接受,而是提出了不允许市场主体修改的承诺建议。这时,承诺决定形式上是合意,实际上是执法机构滥用公权的结果,企业应当可以向法院起诉承诺内容的确定不符合比例原则要求。〔59〕See Manuel Aleixo, “An Inaugural Fine: Microsoft’s Failure to Comply with Commitments” 34(9) E.C.L.R. 476 (2013).在“Alrosa 案”中,虽然承诺是De Beers 单方作出的,但根据ECJ 对案件事实的描述,在两家企业最初的共同承诺被利害关系人反对后,欧盟委员会实际上曾建议过双方作出终止交易的承诺。〔60〕See Case C-441/07 P, Commission v Alrosa, [2010] ECR I-05949, para. 21.虽然最终Alrosa 没有接受这一建议,只有De Beers 作出了承诺,但De Beers 承诺的内容正好与欧盟委员会的建议一致。这能否说欧盟委员会滥用了权力,间接导致承诺内容的确定?
五、豁免分析中的比例原则
在反垄断法实施中,比例原则不仅可用于分析执法活动是否超出限度,也可用于分析限制竞争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前者的适用对象是执法机构,后者的适用对象是垄断行为人。在限制竞争行为合法性分析中,比例原则的意义主要体现为,行为人的限制竞争行为如果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可能被免于适用反垄断法的禁止性规定,或者即便符合禁止性规定也有可能被豁免。第一种情形可称为合法的限制,即不构成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垄断行为,第二种情形则是可豁免的限制,即虽属于禁止范围,但因具有较大的积极效果而可豁免。为方便论述,文章将两种情形统称为豁免分析。
(一)合法的限制:附属限制
反垄断法实施经常遭遇的一个难题是经济效率与非经济目标的冲突。垄断行为带来效率损失,反垄断法以经济效率为目标,但有些限制竞争行为追求一个合法的非经济目标如环境保护。这时,单从效率角度看,反垄断法应禁止这类行为,但这可能有碍非经济目标的实现。比例原则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个难题,这体现为反垄断法实践引入的“附属限制理论”(ancillary restraint doctrine)。
附属限制的概念首先由美国Taft 法官在1898 年的“Addyston Pipe & Steel Co 案”中引入谢尔曼法;〔61〕See U. S. v. Addyston Pipe & Steel Co., 85 F. 271 (1898), p. 282.在1986 年的“Rothery 案”中,Bork 对附属限制作了经典论述:作为一种附属限制,进而免于适用本身违法原则,该限制必须从属或附属于一项独立、合法的交易;所谓附属性,是指该限制服务于主合同目标的更有效实现。〔62〕See Gregory J. Werden, “The ancillary restraints doctrine after Dagher” 8 Sedona Conf. J. 17 (2007).欧盟法院在1994 年的“DLG 案”中,认为农业合作社DLG 通过章程中禁止会员从事与其相竞争的业务不构成对《欧盟运行条约》第101(1)条的违反。〔63〕See Case C-250/92, Gøttrup-KlimGrovvareforening and Others v. Dansk LandbrugsGrovvareselskabAmbA (DLG), [1994] ECR I-5641, para. 40.这里虽未使用附属限制的概念,但实质上运用了附属限制理论。在1999 年的“Albany 案”中,欧盟法院提出了与附属限制相近的“固有限制”(inherent restrictions)概念。法院认为,在经劳资双方集体谈判而达成的协议中,某些限制竞争条款是固有的,如果对这些条款适用《欧盟运行条约》第101(1)条,则集体协议所追求的社会政策目标便会落空。〔64〕See Case C-67/96, Albany International BV v Stichting Bedrijfspensioenfonds Textielindustrie, [1999] ECR I-5751, para.59.到了2001 年的“M6 案”,欧盟法院正式解释了什么是附属限制,即与一项主要目标的实现具有直接关联并且必要的(directly related and necessary)限制。〔65〕See Case T-112/99, Métropoletélévision (M6) and others v Commission, [2001] ECR. II-2459, para.104.
欧盟委员会在执法实践中也认可附属限制的概念。在“垄断协议豁免指南”中,欧盟委员会认为,如果一项协议(也即主合同)的主要内容不具有限制竞争的目的或效果,与实施该协议直接相关且具有必要性的限制也不会受《欧盟运行条约》第101(1)条的调整。这与“M6 案”确认的附属限制概念完全一致。所谓直接相关,是指该限制从属于主合同且与主合同不可分割;所谓必要性,是指该限制对主合同的履行来说客观必要且与主合同相称。〔66〕See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2004/C 101/08), OJ [2004] C 101/97, para. 29.
从上述实践与规范可知,附属限制有两个核心要件:一是限制竞争行为服务于一个合法目标(主合同);二是限制竞争行为对目标的实现具有必要性。如果一项限制竞争行为构成附属限制,则免于适用反垄断法中的禁止性规定,即被认为属于合法的限制。这两个要件实际上就是比例原则中的适当性与必要性要求。适当性指限制竞争行为服务于(从属于)目标的实现,必要性指没有限制效果更小的措施能实现该目标。严格来说,必要性分析需要不断进行LRA 测试,但有学者指出,在附属限制认定中,LRA 测试不是决定性的(determinative),严格的LRA 测试需穷尽分析所有可能的替代措施,这对企业来说负担过重,所以实践中常用“合理必要性”测试(Reasonably Necessary Test)替代。〔67〕See Claire E. Trunzo, “Ancillary Restraints in a Competitive Global Economy: Does the Possibility Exist for an Ancillary Restriction to be Reasonable in Light of Section 1 of the Sherman Act?” 29 Duq. L. Rev. 301(1991).所谓合理必要性,指在能合理预见的各种措施中,当前措施属于最小限制,并不需要证明一定不存在其他替代措施。
附属限制理论由比例原则衍生而来,但区别在于,比例原则中的均衡性要求,在附属限制理论中很少被提及。附属限制理论主要是一种定性分析,一般不需要进行结果上的衡量。即便有时也强调手段与目标相称,但这种相称性不是严格的正负效果衡量,而是指尽量以不利影响最小的方式来实现目标。欧盟“垄断协议豁免指南”明确指出,附属限制分析不涉及对促进竞争与反竞争效果的任何衡量,这种衡量专属于《欧盟运行条约》第101(3)条。〔68〕See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2004/C 101/08), OJ [2004] C 101/97, para.30.
正因不涉及结果衡量,附属限制理论的适用范围应当有所限制。如果以限制效果较为严重的手段来实现一个较小目标,即便手段具有附属性,也不宜直接认定合法。基于这种担忧,有必要将“目标的合理性”纳入考虑范围,即分析附属限制所要实现的目标是否具有合理性。虽然这里不需要进行严格的利大于弊的测试,但应坚持的底线是:与目标相比,限制竞争的手段是次要的、从属性的;换言之,必要时手段是可牺牲的。基于这种认识,对企业行为与政府行为进行附属性分析时应当有所区别。
企业实施限制竞争行为大多出于自利追求,本文建议对这些行为应该严格甚至禁止附属限制理论的适用,除非当事人能证明具有附属性的限制竞争行为并没有带来弊大于利的后果(即至少是利弊相当),否则要想免于违法认定,只能依据豁免规则进行效率抗辩。但是,企业实施限制竞争行为有时也不为自身利益,而是具有公益性目标如保护环境或者文化多样性。例如,企业间达成环境标准协议,约定淘汰高污染、高能耗的原料、设备;或者为了履行环境法设定的义务如包装废物回收义务,而与他人签订排他性的委托回收协议。这些协议很可能具有限制竞争效果,但目的具有公益性,法律应当鼓励这类协议的达成与实施。为此,如果协议中的限制条款满足附属性要件,应当排除反垄断法的适用。对具有公益性目标的企业行为适用附属限制理论,好处是免于效果衡量,因为环境收益属于非经济性收益,具有整体性、长期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很难与限制竞争带来的效率损失进行量上的比较。但是在环境问题异常严峻的今天,为了保护环境而适度牺牲经济效率应被允许。
政府实施的限制竞争行为,实际上有两类:一是我国《反垄断法》规定的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二是不涉及权力滥用的限制竞争行为。第一种行为由于“滥用行政权力”的限定,已没有合法性分析的余地,而且这些行为通常目的不合法(如地方保护),不可能符合比例原则。对政府实施的第二类限制竞争行为,即追求一个合法目标却因为疏忽、不知情、不得已等非故意因素而产生了限制竞争效果的行为,完全可以进行附属性分析。附属性分析的基本要求是,政府在追求合法的管理目标(如社会安全、环境保护)时应尽力避免对市场竞争的限制,如果限制竞争不可避免,应采取限制效果最小的措施。构成附属限制,进而不被视为违反反垄断法的政府限制竞争行为,应当满足以下基本条件:一是基于追求一个合法的管理目标,对政府行为来说目标合法主要指有合法的权力来源;二是限制竞争具有必要性,即不采取限制竞争的方式无法实现管理目标;三是没有限制竞争效果更小的措施能够实现同样的目标;四是不能造成持久消除竞争的效果,通常指限制竞争的期限不应过长,例如,政府与企业签订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合同,可能是确保公用事业有效经营的必要措施,但该合同具有明显的排他效果(被授权企业数量较少),所以不能是无期限的。
我国目前正在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其适用范围较广,所有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都要进行审查,而不限于滥用行政权力的限制竞争行为,所以在公平竞争审查中附属限制理论具有较大的适用空间。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34 号)中专设了“例外规定”的内容,意指某些政策措施虽具有限制竞争效果,但符合特定条件的可以实施。这里设置的条件,基本就是附属限制的标准。其中,“对实现政策目的不可或缺”是必要性的基本内容,而“不会严重排除和限制市场竞争”和“明确实施期限”则是确保只产生最小的限制竞争效果,也可以解释为必要性的内容。
(二)可豁免的限制:效率抗辩
一项限制竞争行为不构成附属限制,则进入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原则上推定禁止,但不意味着当然会被禁止,因为当事人仍可进行效率抗辩。效率抗辩的具体标准,不同国家立法不尽一致,但大同小异,基本都是比例原则的要求。〔69〕《欧盟运行条约》第101(3)条规定了垄断协议豁免的四个要件:一是有助于改善商品的生产或销售,或者有助于促进技术或经济进步;二是能使消费者公平地分享到由此产生的收益;三是限制行为对实现上述目标不可或缺;四是限制行为不会消除市场竞争。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执法指南”和“合并控制指南”分别规定了滥用行为规制和合并控制中的效率抗辩标准,与垄断协议效率抗辩的标准基本一致。See Guidance on the Commission’s enforcement priorities in applying Article 82 of the EC Treaty to abusive exclusionary conduct by dominant undertakings (2009/C 45/02), OJ [2009] C 45/7, para. 30; 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horizontal mergers under the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OJ [2004] C31/5, paras76-88.且与附属限制理论淡化结果衡量不同,在效率抗辩中,比例原则必须被严格适用。〔70〕See Wolf Sauter, “Proportionality in EU competition law” 35(7) E.C.L.R. 329 (2014).
效率抗辩的比例原则分析,首先是判断适当性,即判断限制竞争行为是否有助于效率目标的实现。行为人必须提出充分证据,证明限制竞争行为带来了效率。限制竞争行为实现的效率越明显,其适当性也就越充分。这里的效率,必须是直接的客观效率:一方面,限制竞争行为与效率之间必须有直接因果联系,〔71〕See Cases IV/36.957/F3 - GlaxoWellcome (notification), IV/36.997/F3 - Aseprofar and Fedifar (complaint), IV/37.121/F3 - Spain Pharma (complaint), IV/37.138/F3- BAI (complaint), IV/37.380/F3 - EAEPC (complaint), OJ [2001] L 302/1.而不能是不太确定的间接联系;〔72〕例如,行为人主张实施垄断协议可以避免过度竞争从而增加收益,而收益的增加可以用来研发更多的产品。这里,通过实施垄断协议增加收益与研发产品之间的联系就属于间接联系,具有太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效率应具有客观性,〔73〕See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2004/C 101/08), OJ [2004] C 101/97, para. 49.即当事人必须能够证实其效率主张,〔74〕See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ugust 19, 2010), p.30.或者说效率具有明确的可验证性(verifiability)。〔75〕See 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horizontal mergers under the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OJ [2004] C31/5, para 86.欧盟法院在1966 年判决的“Consten and Grundig 案”中认为,一项能够豁免的协议必须具有“显著的客观收益”。〔76〕See Joined cases 56 and 58 - 64, Consten and Grundig v Commission, [1966] ECR 229, p.348.至于效率的具体内容,可以有多种形式,如成本效率(价格更低)、质量效率(质量更好)、产品多样性效率(选择机会更多)等。《欧盟运行条约》第101(3)条是关于垄断协议豁免的规定,其列举的效率内容包括:有助于改善商品的生产或销售,或者有助于促进技术或经济进步。
适当性确定之后,需要判断效率抗辩是否符合必要性要求,即是否可以通过非限制性手段或限制效果更小的手段来获得该效率。如果不采取限制竞争的方式也能实现效率,限制竞争就没有必要;如果采取限制效果更小的措施也能实现效率,当前的限制同样没有必要。《欧盟运行条约》第101(3)条明确要求当事人主张效率抗辩必须证明限制行为对实现效率目标具有必不可少性(indispensability);欧盟“滥用行为执法指南”对必要性的解释是“一定不存在具有更低反竞争效果且能够产生同样效率的可替代行为”;〔77〕Guidance on the Commission’s enforcement priorities in applying Article 82 of the EC Treaty to abusive exclusionary conduct by dominant undertakings (2009/C 45/02), OJ [2009] C 45/7, para. 30.美国与欧盟合并控制指南中的效率抗辩均要求当事人证明产生了“合并特有的效率”,即效率是合并的直接结果且通过不太具有反竞争效果的替代方式不能达到同样的程度。〔78〕See 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horizontal mergers under the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OJ [2004] C31/5, para 85.必要性分析对手段的要求较高,实践中容易被误解为要求手段的唯一性。其实,这里并不需要证明在没有限制竞争行为的情况下效率一定不会实现,而是要证明,限制竞争行为比在没有这种限制的情况下可能产生更高的效率。也就是说,如果限制行为的缺乏会消除或显著减少由限制行为所产生的效率,或显著降低效率产生的可能性,那么这种限制就是必要的。
效率抗辩中比例原则分析的最后一步是利益衡量,即要求积极效果超过消极效果。反垄断法之所以禁止限制竞争行为,是因为限制竞争会损害效率,当事人基于效率进行抗辩,当然应证明限制竞争行为带来了超过效率损失的效率收益。效率抗辩中的利益衡量有两个重要基准。(1)不能消除竞争。“效率来自竞争”是反垄断法的基本法理,“有效竞争的维持”是反垄断法的基本目的。“不能消除竞争”是比例原则适用的底线,因为对竞争过程的保护优于从限制竞争行为中获得的促进竞争收益。〔79〕See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2004/C 101/08), OJ [2004] C 101/97, para.105.如果手段具有消除竞争的效果,则目标收益再大也不足以与手段匹配。欧盟“DSD 案”在这方面具有典型意义:DSD 公司在德国经营包装废物回收和再利用系统,具有包装废物回收义务的企业大多将回收义务委托DSD 公司履行,DSD 公司再通过服务协议(Service Agreement)委托各地的收集公司实际回收,协议保证在一个地区只委托一家收集公司且持续15 年。欧盟委员会认为,排他安排是确保收集公司回收基础设施投资成本的需要,但排他权长达15 年之久,可能使得未能与DSD 订立服务协议的收集公司在很长时期内也难以进入该市场,这样一来它们可能很快从市场中消失,这相当于在包装的收集市场上消除了竞争。基于此,欧盟委员会认为这一期限过长,在当事人缩减了合同期限后才作出了豁免决定。〔80〕See Cases COMP/34493 - DSD, OJ [2001] L 319/1, paras 53-55.(2)消费者导向。反垄断法追求的经济效率最终指向消费者福利,〔81〕See Rex Ahdar, “Consumers, Re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the Purpose of Competition Law” 23(7) E.C.L.R. 353 (2002).所以效率评估必须坚持消费者导向,即考虑消费者能否分享由此产生的收益。欧盟“合并控制条例”指出:效率分析时应考虑效率是否会与反竞争效果互相抵消,尤其是其是否会与消费者损害相抵消;〔82〕See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of 20 January 2004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OJ [2004] L 24/1, Recital 29.欧盟“横向合并指南”表述更为直接:评估效率主张的相关基准(relevant benchmark)就是消费者的处境不会因合并而变得更糟。〔83〕See 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horizontal mergers under the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OJ [2004] C31/5, para79.效率抗辩中的利益衡量,主要就是将限制竞争行为的效率收益与对消费者的负面影响进行比较,确保效率收益能够补偿限制竞争行为对消费者产生的负面影响。当然,这里的“消费者”不同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的消费者,而是包括限制竞争行为所涉产品的所有直接或间接用户,〔84〕See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2004/C 101/08), OJ [2004] C 101/97, para.84.且不能只考虑特定消费者,还应考虑消费者整体。〔85〕See Case T-131/99, Shaw and Falla v Commission, [2002] ECR II-02023, para. 163.
六、结语:我国《反垄断法》相关条款的改造
基于上文分析,建议在我国反垄断法制度体系中引入比例原则的要求。这些内容既可通过《反垄断法》的修订规定下来,也可仅在《反垄断法》中作出原则性规定,之后再以配套法规、规章或指南规定更详细的内容。
第一,明确处罚措施的适用关系。我国《反垄断法》中法律责任条款(第46 条和第47 条)的主要内容是“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这里规定了三种处罚措施:“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但它们之间是“并处”关系,即同时适用。以比例原则来看,合理的处罚措施应与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相匹配并不超过必要限度。对所有垄断行为并处三种处罚措施不满足比例原则中的必要性要求。首先,“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完全可以作为一项独立的处罚措施,在那些垄断行为尚未实施、情节轻微且行为人积极采取补救措施,或者基于被胁迫、不知情而实施垄断行为的案件中单独适用,不必非与罚款并用。欧盟第1/2003 号条例第7 条就将“终止违法行为”作为欧盟委员会的独立决定之一。其次,将“没收违法所得”与“罚款”并处,也可能面临问题:一是违法所得很多时候无法计算,欧盟“罚款指南”尽管规定当违法收益大于罚款数额时可以增加罚款数额,但该规则仅适用于违法收益可计算的情况之下;二是两者功能没有本质区别,都是确保反垄断法的威慑力,罚款完全可以替代没收违法所得,在这种情况下,不如直接适用相对更易计算的罚款;三是在没收违法所得之外,再处以上一年度销售额1%至10%的罚款,容易使得最终责任超过必要限度。
第二,修正罚款数额的考虑因素。《反垄断法》第49 条将“违法行为的性质、程度和持续的时间”作为确定罚款数额的考虑因素,这三个因素之间并非并列关系:违法行为的性质可理解为违法行为的类型,但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完全可以包含持续时间。如果列举持续时间,那么与持续时间具有类似作用的涉案销售额(与违法行为相关的销售额)、涉案范围(商品市场和地域市场的大小)为何不作列举?此外,基于比例原则的均衡性要求,罚款数额不应超过企业的支付能力,所以建议将支付能力作为独立考虑因素予以规定。
第三,引入承诺决定的比例要求。《反垄断法》第45 条规定了承诺决定制度,但未涉及承诺内容的确定标准和确定程序。建议从两个方面在承诺决定中引入比例原则:一是要求承诺内容应足以消除涉嫌垄断行为的消极影响,但应仅限于解决执法机构所关注的竞争问题;二是规定由经营者提出承诺内容,除非经营者请求,否则执法机构不应代拟承诺内容。
第四,降低公益行为的豁免标准。反垄断法应鼓励各类主体从事有利于公益的行为,但在考虑是否给予公益行为豁免时,不能仅依据效率抗辩标准。效率抗辩包含正负效果衡量的要求,而公益行为未必会带来反垄断法意义上的效率,所以,单一的效率抗辩标准可能会阻碍公益行为的有效豁免。为此,可引入附属限制理论,对不论政府还是私人主体实施的公益行为,主要进行附属性分析,在构成附属限制的情况下,不必进行结果上的利益衡量,就可赋予其合法性。我国《反垄断法》第15 条规定的垄断协议豁免情形中,第(4)项属于公益行为,即“为实现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救灾救助等社会公共利益的”,但该条并未对公益行为与其他行为作出区分,统一适用效率抗辩标准。这样处理难以顾及“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救灾救助等社会公共利益”的特殊性,很难真正给予这类行为豁免。
第五,严格效率抗辩的适用条件。我国《反垄断法》第15 条基本以《欧盟运行条约》第101(3)条为蓝本,确立了垄断协议豁免的效率抗辩标准。第15 条第1 款列举了垄断协议豁免的几种情形,第2 款规定了垄断协议豁免的两个条件:不会严重限制相关市场的竞争并能够使消费者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但与欧盟立法相比,我国《反垄断法》第15 条的问题在于,既没有要求垄断协议必须带来足够的经济效率,也没有对垄断协议施加“必不可少性”限制。《欧盟运行条约》第101(3)条规定的豁免条件中,第一个就是效率要求,即“有助于改善商品的生产或销售,或者有助于促进技术或经济进步”。效率要求是豁免的前提,不要求垄断协议产生足够的经济效率,如何评估垄断协议的适当性、必要性,以及如何对正负效果进行比较?〔86〕可能有人主张,《反垄断法》第15 条第1 款列举的豁免情形就是效率要求。这种理解很难成立,因为效率要求应当是一种客观标准,而不能是当事人的主观目的。我国《反垄断法》规定豁免情形时均使用了“为……的”这样的表述方式,这只是反映了协议目的,目的是不可以作为经济效率来认定的。此外,效率抗辩还应强调限制竞争的手段对效率的取得不可或缺,不满足这个要求,限制竞争的手段就不具有必要性。这个问题在《反垄断法》第28 条中也存在。该条规定了经营者集中审查中的效率抗辩标准,即“集中对竞争产生的有利影响明显大于不利影响”。这里只要求产生了较大的积极效果,并未对集中的必要性作出限定,意味着即便存在不太具有反竞争效果的替代方案也能达到同样目的,集中也是可以被豁免的——这显然不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