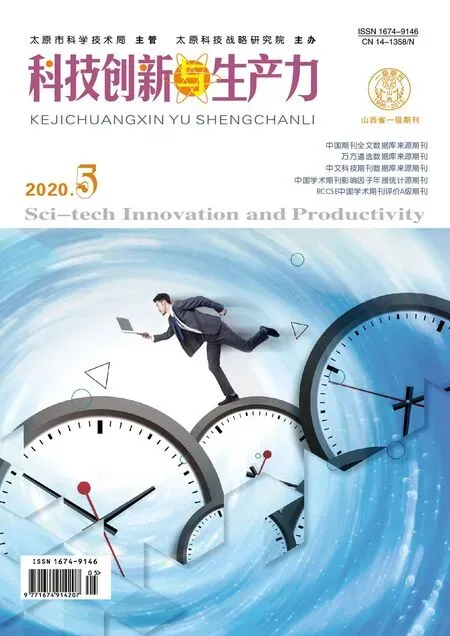外部性视角下的农村水资源分配
刘俊娜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200030)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升,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逐步提升。近几十年,人口呈现指数式增长,对于自然资源的索取也日渐增多,然而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却逐步减弱。尤其是水资源的短缺和污染、水利基础设施的滞后,都存在外部性的现象,由此带来的水资源分配问题更加凸显,而水资源分配问题又会极大地制约地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要想解决这一难题,必须从公共经济学的外部性视角,分析水资源分配问题产生的根源,针对具体问题提出解决措施。
1 水资源分配问题的文献综述与回顾
笔者查阅相关文献发现,国外学者更多地从水资源的属性和特征出发,将水资源分配方式总体概括为3种:行政化分配、市场化分配、准市场的混合分配。水资源作为 “公共池塘资源”,将政府作为第三方引入水资源分配中,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手段。科斯的产权理论认为,只要产权明晰,无论初始产权设置如何以及把产权界定给谁,都将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按照该理论,只要水资源的产权明晰,水资源配置就能达到最优状态。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大量实证案例中,突破了以往学者们所认为的 “要想解决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只能在集权式政府规制和完全私人所有两者间做出唯一选择”的观点。1993年以来,LYNNE G D等[1]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任何一种 “唯一”的水资源配置方式都无法彻底解决水资源分配的难题;1999年,DINAR A[2]提出,应该把政府和市场两种方式结合在一起,同时注重发挥公众参与和民间传统在水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国内学者主要针对水资源分配主体之间的竞争或者合作进行研究。在竞争方面,2005年,肖志娟等[3]应用博弈论原理与方法,求解应急调水的合理补偿量问题,解决调水各方的利益冲突;2018年,Fu Y C等[4]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使用多目标优化模型,分析社会公平等条件影响下的水资源分配方案。在合作方面,国内学者主要研究各用水资源主体之间统筹水资源,并进行统一合理分配,2016年,付湘等[5]采用合作博弈方法,建立水资源用户合作博弈模型;DEGEFU D M等[6]使用纳什协商方法,研究稀缺性的水资源分配问题;2020年,王先甲等[7]从现实分配情况出发,指出在水资源分配过程中,各用水主体既存在竞争又离不开合作,因而构建了具有外部性的合作博弈模型,分析水资源分配问题,确定均衡的水资源分配量。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水资源分配问题都有独特而深刻的见解,然而对农村这类特定区域水资源分配问题的研究较为少见,而且从公共经济学的外部性视角分析该问题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本文从公共经济学的外部性视角,选取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某村作为调研对象,通过查阅资料、访谈村干部等方法,研究该村水资源分配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法。
2 农村水资源分配问题案例简介
2019年秋冬两季,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出现了严重的干旱现象,无降雨的情况持续近5个月。河流日渐干涸,农村农业经济损失严重,甚至出现100多个村人畜饮水困难的情况。县城虽然停止了一些景观用水,例如喷泉不再开放,但并未采取其他相关限水措施,县城供水正常。笔者调研的村子自2019年入秋以来干旱日趋严重,原有饮用水河流供水不足,村长启动集体资金为村民修井修坝也未能缓解群众饮水困难的情况。在正常年景中,村民们靠天吃水,无需接通自来水管道,问题还不是很突出,但是,2019年遇到的旱灾非同寻常,许多山林树木干旱而死,山泉干涸,村民最先受到严重的冲击。
3 基于外部性的农村水资源分配状况分析
3.1 污染产生的外部性影响农村水资源分配
首先,根据萨缪尔森对公共物品的分类可知,由于水资源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因此被定义为准公共物品,农村地区的水资源是农村的准公共物品,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它是农村社区特定范围内村民可以共享的产品,能够满足当地村民的消耗所需。由于农村水资源大多来源于河流、小溪、山泉等,无法确定其产权,因此导致无法向村民 (或污染水资源者)直接收费。其次,农村地区的村民居住较为分散,个别村民污染水资源导致全村用水存在安全隐患,尤其是在笔者调研的村子竟然发现有个别村民在水资源保护源头种植果树,过度使用化肥农药,甚至将残留的农药瓶和化肥塑料袋丢弃于河中,造成水资源源头的污染,全村饮用水无法保证质检过关,导致分配到各家各户的水资源质量堪忧。然而,农村水资源具有固有的非排他性和竞争性,产权不明使得污染水资源的村民无需为此行为承担责任,也无需为此行为付费。最后,村民一直有畜禽养殖传统,许多畜禽养殖农户通过个体小规模畜禽养殖来补贴家用。令人担忧的是畜禽产生的粪便已经远远超出农作物施肥所需之量,加之现阶段村民贪图方便,更倾向于选择使用化肥,而非畜禽粪便农家肥,这就导致畜禽粪便的大量堆积,堆积成灾之后自然而然地向河流排放,导致产生大量未经处理的污水,造成严重的水资源污染,村民用水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个体畜禽养殖带来的经济收益只属于个别农户,而水资源污染使得水资源分配过程中影响了农村每户的用水质量,危及全村人的身体健康,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水资源污染也使得农村生态环境承担了较大的损失,毫无疑问,这些都属于负的外部性和外部不经济。
3.2 私人贩卖产生的外部性影响农村水资源分配
从笔者调研的村子河流情况来看,尽管水资源具有流动性,然而村里有个别村民将管道接入河流上游,截流清澈泉水,用于个体零售山泉水,每日运送6次,将近6 t。大量的水资源用于交易,水量急剧消耗,就会造成地下径流减缓,地下水位随之下降,河流下游的生态环境就会造成破坏。该村河流沿途没有其他较大的水源支流补给,且恰逢2019年入秋以来的干旱,降雨量小,蒸发量大,因此水位下降更加严重,村民吃水问题更加严峻,生态环境受到恶劣的影响。按照往年正常年景,该村水资源这一纯公共物品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然而,2019年出现的干旱和某村民贩卖水资源的现象,水资源的消耗增加,补给不足,随之而来的水资源分配就成为了大问题。该村民对于产权界定不明晰的水资源进行贩卖,并未对水资源进行付费,造成以下问题:首先,该村其他村民平均享有的水资源量减少;其次,水资源量的减少会破坏河流沿岸的湿地和一些水生物栖息地,鱼虾等水生物减少,加重土地荒漠化程度,造成沼泽干枯等现象;最后,水量减少会加大村民采水的成本,造成一些农田被弃耕,村民的经济效益严重受损。可见,个别村民对水资源贩卖带来的负外部性使得水资源分配存在较大的问题。
3.3 水利设施建设的外部性影响农村水资源分配
水利基础设施是水资源利用的重要载体,它能够限制水源的流量,调节水资源的存量,由于水资源分配基于水利基础设施,因此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决定了农村享有水资源的机会和经济效益。从笔者调研的该村来看,主体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依赖于政府部门的项目配备,2019年发生干旱时,主要靠村长带头组织村民修建水井、水坝。然而,生活用水供给不足的尴尬局面依旧存在,水资源存量的紧缺使得分配成为头等大事,许多村民分配到的水量不足以维持生活用水量,导致村民纷纷去河里挑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便是水利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农村水利事业发展比县城更为滞后。水利基础设施属于外溢性较强的公共产品,如果地方政府在该村修建水利基础设施,那么经济效益会容易外溢到其他区域,而其他区域不承担空间成本,存在显著的外部性。现阶段,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水利基础设施由政府财政承担,尤其是城市的水利基础设施几乎可以得到政府财政的全面覆盖,而农村则面临政府财政投入不足的困境。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的滞后使得水资源在农村的供给存在隐患,水资源供给不足造成分配不足,村民即使背靠水源地却水也不够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部分地方政府考虑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外溢性而建设投入不足所致。
4 外部性视角下农村水资源合理分配的建议
4.1 建立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形成 “绿水青山”保护者与 “金山银山”受益者之间的利益调配机制,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行。河流作为地域关联度高和空间整体性较强生态系统,在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中有较为显著的成果。生态补偿机制作为一种环境经济政策,其目的就是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进而更好地调整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生态补偿机制与 “污染者付费” “破坏者付费”原理一致,都是通过经济激励来保护水资源。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时,要明确政府责任,水资源作为纯公共产品,政府作为提供主体显然承担重要的责任,则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于政府财政。政府可以对生态补偿机制进行前期规划,在预算中设计一部分专门用于生态补偿的资金,在过程中提供一些技术指导来缓解水资源污染的外部性带来的水资源分配问题。号召村民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对减少了使用量的村民给予生态补贴,同时制定科学的化肥、农药使用标准量;对于畜禽养殖农户同样提倡转变排污方式,制定排放标准,对减少了排放量的村民同样给予生态补贴;对于部分在水源地进行种植的农户给予劝导,使其放弃种植污染水源的作物,政府以生态补贴等手段激励种植户,减少因水源地种植引起的水资源污染。
4.2 界定水权所属以确保水权有偿交易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人们认识到了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通过市场对水资源进行配置才能更好地发挥水资源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界定水资源产权,提倡用者付费,杜绝“搭便车”的行为。要实现水权交易就应该先关注水资源归属问题。我国各地区河流、山川、湖泊等水资源的所有权其实都归国家,按照现行法律,水权交易标的不能是水资源的所有权,而是水资源的使用权。由于我国宪法有明确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修建管理的水库、大坝等各项水利设施由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因此农村地区对于这一类型的水资源具有排他性使用权。那么按照规定,水资源的使用权由每一位村民平等享有。再按照水资源属地管理原则,可以较为清晰地界定水资源使用权的归属主体。农村水资源使用权的归属主体则要按照公平的市场交易原则在市场中交易水资源的使用权,讨价还价,确定合理合法的交易方式、交易数量和交易价格,而不是任由村民私自贩卖集体享有的水资源。同时,在交易过程中,政府丝毫不能放松监管工作,确保农村水资源使用权的公平分配和公平交易。水资源使用权的有偿交易能够更加深刻地体现水资源的稀缺性,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4.3 政府引导建立农村水资源管理机制
现阶段,地方政府对于农村的水资源分配存在缺位和错位的情况,部分地方政府没有提供充足的资金供给农村水资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导致农村水资源分配存在较大的难题。因此,地方政府必须牵头建立农村水资源管理体制,明确县、乡镇等各级地方政府的水务职能,科学制定农村水资源分配和投入建设的制度,逐步改进农村水利基础设施,扭转农村背靠水资源却缺水用的尴尬局面。农村也可建立特定的农村水资源管理协会,熟知本村水资源流量和走势,向地方政府提供水资源供需预测、水资源配置数量以及水资源污染治理等意见和建议,提高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科学合理性,降低开发和使用成本,更为稳定地保障农村用水。而且,农村水资源管理协会还可代表村民对上级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实时监督,提高农村水资源的管理效率,保障农村水资源的合理分配[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