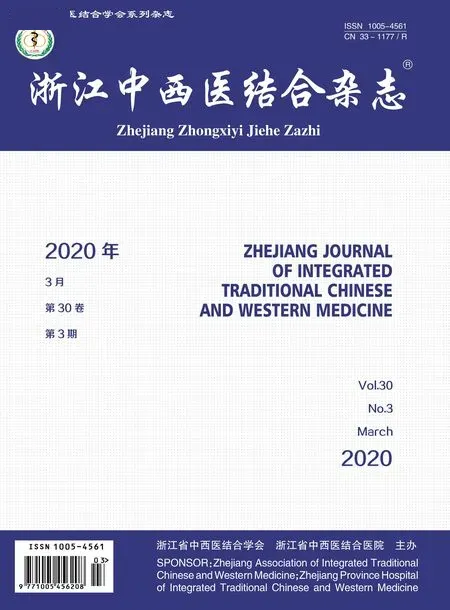冯斌运用疏肝解郁降逆法治疗癔症性呃逆经验
郑自力 冯 斌
癔症,即分离转换障碍,现代精神医学多认为其属于心因性疾病,其症状的发生与精神刺激因素密切相关,躯体运动障碍是其临床表现之一[1],以癔症性呃逆为首发症状的病例在门诊上并不多见。冯斌教授系浙江省立同德医院主任医师,从医30 余年,擅长采用中西医结合诊治各种难治性精神疾病,现将冯老师运用疏肝解郁降逆法治疗癔症性呃逆的经验总结如下。
1 病因病机
呃逆是指胃气上逆动膈,上冲喉间,以呃声连连,短促而频,不能自制为主要表现的病证[1]。癔症性呃逆,是癔症性躯体障碍的表现形式之一,以精神心理因素为诱因,引起膈肌痉挛,发出呃声,声响有力,症状可持续数分钟甚至数十分钟,而无器质性病变[2]。
1.1 追本溯源 始于情志失常 临床常见呃逆之病多由饮食不当或脾胃虚弱所致,但癔症性呃逆由情志刺激起病,故情志失常是该病的重要病因。冯老师认为该病患者具有以下特点:(1)发病前有与人争吵、过度思劳或积郁不满等经历;(2)受到的精神刺激突然且强烈;(3)态度消极,情绪压抑;(4)无人倾诉,缺乏心理疏导。以上因素均可导致情志不利,从而影响气机运行,形成气结、气滞或气逆的病理状态。情志活动是机体正常生理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度的情志调节,有助于维持体内气的正常运行,当精神刺激过于强烈,超过了人体正常的耐受能力时,气的生理活动就会受到影响,正如《素问·举痛论》所述“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思则气结”,提示七情不舒可伤及气机运行,引发气机紊乱。
1.2 气机紊乱 肝疏泄失职 冯老师指出,气机的协调平衡是五脏六腑维持正常生理功能的重要基础,《临证医案指南》记载:“气郁不舒,木不条达。”周学海言:“凡脏腑十二经之气化,皆必籍肝胆之气以鼓舞之,始能调畅而不病。”[3]故气机运行与肝的关系最为密切,若气机舒畅则肝气条达,气滞不行则抑制肝气疏发。癔症性呃逆由情志不遂所致,气不能疏而郁结于肝,气不能行而滞留于肝,气不能出而内闭于肝,其病理表现为气机紊乱、肝失疏泄,故临床多见于肝气郁结者。肝失疏泄、情志不畅,故见郁郁寡欢,心情低落;肝脉不畅、气机阻滞,故见胸胁满闷,甚或疼痛;邪气滞肝、脉气紧张,故见脉弦。此证候提示肝气疏泄失职,为该病采用疏肝解郁之法治疗提供依据。
1.3 肝胃不和 症见呃逆不止 胃主通降,以下行为顺,为胃之生理特性,肝气郁结,横逆犯胃,胃气不能通降下行,以致胃气失司,不降反升,上冲喉间,故见呃逆不止。《古今医统大全·咳逆》曰:“凡有忍气郁结积怒之人,并不得行其志者,多有咳逆之证。”[4]明确指出情志不遂、气机郁结可导致呃逆发病。冯老师认为,临证见呃逆时,应追问病史,了解患者情志变化,不难发现呃逆之症并不局限于脾胃,常可从“肝”论治,肝失疏泄,犯脾克胃,胃失通降,故而上逆,症见呃逆连连、嗳气纳减等肝胃不和症状。综上所述,癔症性呃逆当责之于肝,以肝气郁结,胃气上逆为主要病机,病性属实。
2 治法方药
2.1 立法选方 冯老师强调临诊拟方,必先准确辨证,辨证有失,则用药失策,易失治误治,延误病情。纵观该病之病因病机,冯老师认为该病当以疏肝解郁,降逆止呃为法,以柴胡疏肝散为基础方,肝胃同治,药用柴胡、枳壳、白芍、甘草、香附、陈皮、川芎,重用香附、枳壳,辅以少量当归、白术、茯苓。方中柴胡疏肝解郁,白芍养肝敛阴,一散一收,使肝之升发得当;枳壳理气消胀,伍以柴胡,一升一降,使肝气得疏,胃气乃降;香附疏肝理气,配柴胡以增效,畅通气机以达郁;川芎行气以开郁,活血以畅血脉,气血兼顾;陈皮理气行滞,燥湿化痰,苦以通降,助胃气降逆;甘草入胃经以缓急,亦可调和诸药。辅以少量当归使血行而不滞;白术、茯苓以健脾助胃,使纳运相得,胃和则降。
2.2 随症加减 该病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受到情志波动和气机变化影响,常伴有不同兼症,辨证论治时当结合证候特点,灵活用药,切勿拘泥。冯老师常选用以下药物进行配伍:(1)胁肋胀满者,由于肝郁阻碍气机运行,积聚于胁肋而致胀满,可配伍郁金、佛手、香附疏肝理气;(2)嗳气恶呕者,多由胃失和降,气冲上逆,可加用旋复花、代赭石降气止呕;(3)不思饮食者,见于消化不利,饮食积滞,可加炒鸡内金、炒稻芽、炒山楂消食开胃;(4)心烦口苦者,见于肝郁化火,火热上炎,可加用黄芩、栀子清热泻火;(5)便秘不畅者,多由腑气郁滞,传导失职,可加用火麻仁、厚朴下行通便;(6)头晕乏力者,多由气虚不升,清窍失养,可加用黄芪、红景天益气补虚。配伍时需斟酌用量,过犹不及,例如理气药大多辛温香燥,易耗伤气阴,故对气弱阴虚者应避免过服久服,或配伍中加少量滋阴益气药,以兼顾调和。
2.3 情志疗法 情志刺激是癔症性呃逆发病的重要病因。因此,在临床工作中,除了运用药物治疗以疏肝降逆,还应注重心理治疗[5],加强心理疏导。冯老师针对该病常用方法:(1)认知行为疗法:即指导患者正视问题的存在,修正其对事实的错误认知,在情志因素与躯体障碍之间增加心理过程干预,重新建立其对外来刺激引起机体反应的评价过程;(2)家庭治疗:癔症的发生可与家庭矛盾有关,若家庭成员能够配合,可建议其一同参与到患者的治疗当中,给予患者环境支持和心理支持;(3)暗示治疗:通过劝慰和安抚,建立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用言语暗示转移患者对自身症状的过度关注,强化患者对治疗的信心。以上方法既可单独应用,也可联合使用。无论采用何种方法,均应结合患者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性格特征、家庭环境及文化水平等因素,才能实现最佳疗效。情志疗法可从根本上解除精神刺激因素,使患者精神情志相协调,心情愉快,气机调畅,升降有常,更助药到病除。
3 医案举隅
3.1 病案1 李某,女,59 岁,2018 年3 月17 日初诊。该患者于10 余年前,因丈夫外遇离家,而抑郁不畅,不知喜怒,脘腹满闷不适,并出现打嗝,呃声洪亮有力,百米开外亦可闻之,每日数十次,难以自制,每于思虑丈夫外遇之事时加重,症状反复发作。多方诊治,疗效不佳,来我院求治,刻诊见:呃逆声响,洪亮有力,顿而反复,伴忧郁不畅,胁肋胀满,脘闷纳呆,夜间难眠,舌淡红,苔薄白,脉弦。西医诊断:癔症,焦虑症。中医诊断:呃逆,证属肝气郁结,胃气上逆。治宜疏肝解郁,降逆止呃。方用柴胡疏肝散加味:柴胡12g,枳壳20g,白芍12g,甘草3g,香附9g,陈皮12g,川芎9g,白术、茯苓各10g,当归12g,14 剂,水煎服,1 天1 剂。同时予舍曲林片50mg、利培酮片1mg,早饭后服,氯硝西泮片0.5mg 睡前1h 服,均为1 天1次。并结合认知行为疗法,耐心倾听患者讲述病史,引导其对丈夫的行为进行评价,详细诉说内心感受。冯老师表示同情和理解患者的遭遇,告知其打嗝不适始于对丈夫的不满,是情志刺激转化为躯体障碍的表现,鼓励患者重新审视自己对此事的认知过程,了解压抑情绪并不是应对外来伤害的正确方法,应通过对外倾诉调整心情,通过自我反思将内心积怨从日常生活中剥离出来,采用积极态度面对未来生活。二诊:呃逆明显减少,1 天2~3 次,自觉腹中气不得畅,食积难消,苔腻,脉弦滑。提示气阻中焦,食积未消,证属肝气犯胃,饮食积滞,加炒鸡内金10g,炒稻芽、炒麦芽各20g,吴茱萸3g 以助消食,14 剂,利培酮片减至0.75mg,1 天1 次。三诊:呃逆基本消失,偶有1~2 次呃逆声,诸症均减轻,考虑全方理气药量偏重,易耗伤气阴,去麦芽、减枳壳,再进14 剂巩固疗效,利培酮片减至0.5mg,1 天1 次。四诊:病情治愈,呃逆完全消失。
按:冯老师认为本例患者因受精神刺激而出现呃逆症状,属于癔症性呃逆,常伴见情绪抑郁,胁肋、脘腹满闷,不思饮食,脉弦等,其病机为肝气郁结,胃气上逆,故予柴胡疏肝散疏肝解郁,重用枳壳、香附以理气降逆,伴饮食积滞,予少许炒鸡内金、炒麦芽、炒稻芽消食和胃,症状好转后应及时斟酌减量行气之品,以避免耗伤气阴,药证相合,疗效满意。针对情志病因,患者起病虽与家庭矛盾有关,但考虑到现实因素,无法完成家庭治疗,故予认知行为治疗,通过引导患者疏泄内心愤懑和积怨,耐心解释病情,纠正错误认知,减轻情志刺激对患者心理造成的持续影响,同时鼓励患者乐观面对生活,积极调整情绪,使气机调畅,气血平和,则诸症改善,呃逆得治。
3.2 病案2 张某,女,60 岁,2018 年5 月11 日初诊。主诉:频繁打嗝30 余年。患者农务繁重,每于日晒下劳作时,常感胸闷不舒,低热乏力,自诉似“中暑”之感,甚感疲惫,加之家务劳碌,日常饮食不规律,饥时易多食,食后易腹胀,时而出现打嗝,呃声低缓,持续时间长,发作时自觉腹中胀气,尤以右侧胁肋部明显,伴便秘,时有夜寐不安。患者自觉内心之苦无人倾诉,每于心情不畅时出现呃逆不止,近30年来症状反复,至当地医院检查未发现器质性疾病,遂来我院就诊,刻诊见:呃声低缓频发,不能自控,右侧胁肋胀满,胸闷不舒,神疲乏力,情绪低落,胃纳减少,舌淡红,苔薄白,脉弦细。西医诊断:癔症,焦虑症。中医诊断:呃逆,证属气虚肝郁,胃气上逆。治宜疏肝解郁,益气和胃。方用柴胡疏肝散加减:柴胡、陈皮、川芎、香附各12g,枳壳15g,白芍12g,甘草3g,当归12g,白术、茯苓各10g,黄芪15g,吴茱萸5g,炒稻芽、炒麦芽各30g,14 剂,水煎服。同时予舍曲林片50mg 早饭后服,1 天1 次。倾听患者诉说心中苦闷,予心理支持治疗,增强治疗信心,嘱适当休息,规律饮食。二诊:呃逆声轻,次数减少,胃纳好转,体力增加,食后仍有腹中积气感,大便秘结仍未缓解,舌苔薄黄,脉弦。患者气虚得补,故乏力改善,胃气得降,故食纳增加,然患者慢性起病,日久气郁化火,故见肠燥便秘,气积郁滞于腹,故见腹中积气,予枳壳改炒枳实15g,川芎加至20g 以增行气之功,当归加至20g 以润肠通便,加黄芩10g 以清热泻火,共14 剂,嘱勿劳累,多与人交流倾诉。三诊:呃逆偶见,腹胀明显减轻,时有排气,大便通畅,精神舒畅,提示食积已消,肝火已清,去黄芩、炒稻芽、炒麦芽,续服14 剂,以资巩固,并予心理疏导,教导患者进行自我情绪调节。四诊:呃逆消失,诸症得愈,予舍曲林改半片,渐至停药。
按:本案患者因心中苦闷无人倾诉而表现为呃逆不止,症状发作与情绪波动之间关系密切,故属癔症性呃逆,情志失常是重要病因。患者因长期劳累体虚,饮食不当,以致情志不舒,影响气机升降,气不能疏则郁结于肝,肝气失司,横逆犯胃,不能协助胃气通畅下行,以致胃气上逆,故见呃逆不能自制。肝位胁肋,气结难行,故见胁肋胀满;气机阻滞,机体失养,故见神疲乏力;肠道气滞,传导失司,故见大便秘结;邪气滞肝,脉气紧张,故见脉象弦细。纵观病因病机,证属气虚肝郁,胃气上逆,治以疏肝解郁为主,同时兼顾益气和胃,予柴胡疏肝散加减,辅以黄芪、炒稻芽、炒麦芽益气消食。随证加减,标本同治,初期虽气逆已降,但气积未除,予理气药炒枳实破气消积,中期气郁化火,配合黄芩清热泻火,当归润肠通便。后期随病情好转,诸药减量,收效显著。该病由情志不畅而诱发,冯老师认为,情志既可致病,亦可治病,因此在使用药物治疗同时,心理治疗亦不可或缺,本案患者体质虚弱,信心不足,故予心理支持治疗,疏导情志即是梳理气机,以使肝气得疏,胃气通降,则呃逆自止,诸症乃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