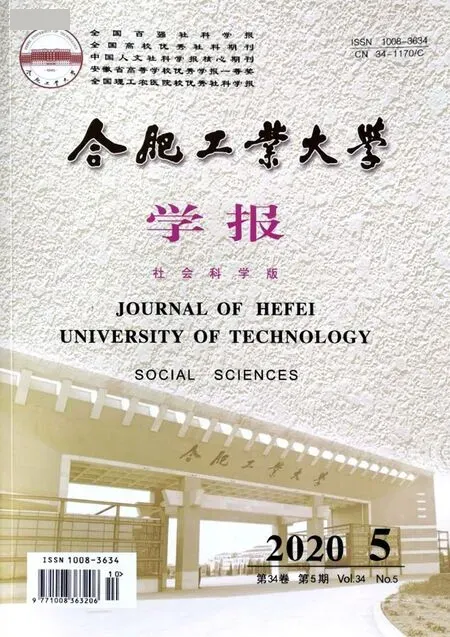现代性重压下的怀旧悲歌
——菲茨杰拉德的怀旧建构
赵梦鸽,戚 涛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合肥 230601)
一、引 言
作为社会世态小说家的代表之一,菲茨杰拉德的作品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其所处时代的精神风貌与社会形态。萨克文·伯科维奇明确肯定了菲茨杰拉德在美国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菲茨杰拉德成为爵士时代的声音,成了那个巨大的、铺张奢侈的社交聚会的诗人”[1]。
学界对菲茨杰拉德长篇小说的既往研究仍主要集中于《伟大的盖茨比》与《夜色温柔》,其研究成果不可谓不丰硕。有文献分析作家所受到的浪漫主义流派(沃兹华斯与济慈)的影响以及作品中的国际主题。受西方文化研究思潮的影响,还有研究从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跨学科角度多维分析菲茨杰拉德的人生及其作品。如柯克·柯纳特在《菲茨杰拉德的消费世界》中运用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的观点分析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消费浪潮对作者本人及其作品的影响[2]。从研究趋势与方法来看,除延续文学重文本的传统,通过结合社会文化语境,学者们对菲茨杰拉德的作品进行了多方位的细致分析。但鲜有学者从怀旧的视角对菲茨杰拉德及其作品进行解读。究其原因,过往分析策略稍显单一。
本文从菲茨杰拉德在社会转型期间所产生的怀旧情结入手,关注其在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心理状态,并结合社会历史分析,主张现代性焦虑导致其归属感的缺失,继而借助文学批评中怀旧概念的补偿机制,在文本中进行怀旧性建构。马西森认为,“文学反映了一个时代,同时也照亮了这个时代”[3]。菲茨杰拉德的怀旧情结与现代性的侵袭息息相关。20世纪20年代,“现代意识”的撩拨与文化传统的对峙使得社会处于一种失范的状态。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导致传统社会纽带的瓦解及身份认同的断裂。物质主义及精英主义的话语暴力催生了高度疏离的人际关系。身处迷惘的现代性情境,菲茨杰拉德通过怀旧,在作品中建构田园牧歌式的“金色中西部”及充满温情的社会纽带,以消解现代性的消极属性。
本文将具体分析现代性如何触发菲茨杰拉德的怀旧情结,从历史和文化的双重维度发掘个体在社会过渡期所经历的“机器过程”,这一发现对认识美国文学、美国文化及国民性极具参考价值。
二、怀旧与现代性
1.怀旧内涵的现代性变迁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怀旧的认识经历着现代性的变迁。早在17世纪,怀旧便被视为一种精神疾病,由瑞士医生霍弗尔首次提出,用以形容外籍雇佣兵的思乡之苦。进入19世纪,怀旧作为一种精神疾患被医学界剔除,人们随之将其纳入单一的情感范畴,在时空上表现为对“逝去的美好”、“遥远的故乡”等怀念之情。20世纪以来,怀旧作为现代性视域下一种愈发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开始引起社会学家的广泛关注。美国学者查尔斯·茨威格曼就曾将怀旧的病理学背景与社会学理论相结合,得出一个关于“生活的不连续性”的结论,他认为怀旧源于人类突然中断、剧烈分裂或发生显著变化的生活体验。它是现代人为弥补生活的不连续性而自行采取的一种自我防御策略[4]2。斯维特拉娜·波伊姆教授也将怀旧与现代性相联系,“怀旧这种一直存在的疾病逐渐演变为不可治愈的现代状况……全球都在流行这种怀旧病,越来越多的人渴望在一个碎片化的世界中获得一种连续性”[5]288;她认为这种流行病是“身处历史加速剧变时代的人们的一种防御机制”[5]279。
如吉登斯所言:“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6]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后传统秩序。传统或惯习,都是在相对确定的层面赋予生活以秩序。而在流动的现代性社会,个体行为模式已变得变化莫测、不稳固和开放。个体曾信奉的传统价值观念遭遇解构,牢固的社会人际纽带遭到瓦解。在不确定性和充斥多样选择的现代视域下,社会成员的生活往往处于一种“失范”的状态,继而引发个体生存的缺失感、焦虑感。在这一语境下,怀旧作为一种现代性问题油然而生,成为现代文化和社会转型带给人类社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后果。
2.怀旧性建构与自我认同
戴维斯认为:“怀旧是我们用来不断地建构、维系和重建我们认同的手段之一。”[4]285现代人的认同危机普遍来源于传统与现实的脱节,而怀旧作为一种防御机制,实质上是对生活节奏、历史变迁节奏加速的现代性社会的心理适应。现代性使个体遭遇种种复杂的选择,并且由于它是无原则的,由此构成了现代生活的不确定性。当归属感在现代生活成为一种奢侈,怀旧则成为一种当下流行的趋势。怀旧的内涵也超越其原有的时空范畴。怀旧的本义即思乡,然而在流动的现代性社会,空间及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对个人已失去传统意义上的归属感。当代怀旧已不再受制于某一客观存在的地理位置,而上升到精神维度,更多地指向承载个人归属感的精神家园。它不再局限于对“过去”及“故乡”的向往与怀恋,怀旧的客体已扩展到“任何可以带来归属感的存在,任何‘神圣的他地’、‘另外的时间’或‘更好的生存状态’”[7]63。正如博伊姆所说:“怀旧本身具有某种乌托邦的维度,只不过不再是指向未来。”[5]287
若要理解怀旧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认同的连续性,或者说,怀旧如何满足个体对归属感的渴求,那就有必要对怀旧发生作用的机制作更仔细的分析。学者认为,“怀旧主要通过疏离、理想化及认同三种策略实现理想化建构,三者分别起着防御、建构和补偿的功能。这些建构主要体现在‘社会纽带’、‘自我认知’和‘另类生命意义’三个方面”[7]63。疏离的基本逻辑即个体通过刻意疏离缺乏安全感和温情的现实世界以减轻焦虑。理想化的重点则是对时空环境和温馨社会纽带的建构。通过赋予对怀旧主体来说意义非凡,却在现实中难以寻觅的另类价值,为后者提供一个乌托邦式的栖息之所。正如亚丁所说:“怀旧为个体提供了一种手段,从而象征性地逃避使其沮丧和迷惑的文化条件。它允许个体将自我安放于意义避难所,一个逃离压迫的文化条件、感到安全的地方。”[8]
三、菲茨杰拉德怀旧情结的成因
1.迷惘的现代性情境
许多人将20世纪20年代视为美国步入现代社会的第一个十年。菲茨杰拉德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同时也见证了这一时期的兴衰荣辱。他曾高声礼赞这浮华的时代,也在其大幕徐徐落下之时,为其鸣一曲哀歌。短暂的狂欢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对往昔温馨质朴的旧日时光的怀旧情结。
爵士乐时代,喧嚣的现代生活中流淌的每个音符都在不停地流动与跳跃,转瞬即逝,让人难以把握。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更新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从亘古不变的传统田园社会转向流动的现代性城市空间。“随着公路网的不断扩展和延伸,城市和乡村之间,至少表层意义上的界限正在模糊、消解。”[9]文明在城市混乱的重负下断裂,马尔科姆将这一时期美国的特征描述为 “一个奇怪的文化混合体”:
“这是一个美国人生活风格完全改变的年代,国家正从一个以生产为主体的社会向以消费为主体的社会转型;这是个乡镇向大城市大规模移民的时代。而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一种‘现代意识’的突然增强,生活节奏突然加快,以及道德观念方面的巨大改变。简而言之,这是一个过去与现在急剧摩擦的时代,一个失去方向的时代。”[10]11
正如马尔科姆所指出的,20世纪20年代是个充满矛盾的年代。传统势力与现代精神两股力量相互博弈,人们眼望着未来,心向着过去。处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之间的文化青年们自我标榜为“迷惘的一代”。他们自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在与现代性的遭遇中倒戈。他们热切期待变革,感触着现代性引致的焕然一新的社会风尚。然而现代意识在某一层面又动摇了他们的文化根基,进而引发焦虑。
现代性的冲击不仅仅在最敏锐的青年作家群体中有所体现。劳伦斯·里范恩指出:“相当比例的人在面对20年代这一新时代的冲力时,感到失落、受挫。他们就像‘迷惘的一代’中最敌对的成员一样,感到与时代的精神气质和发展格格不入。他们试图扭转主宰现代美国的潮流,回到过去的道德规范之下。他们思念伴随自己长大的村社生活,相信这种生活与美国价值密不可分。”[11]45寻找美国经验、建立民族身份认同,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集体文化焦虑。在不确定性和多样选择的现代视域下,潜伏着个体的焦虑与缺失感;在狂欢享乐、声色犬马的爵士乐时代,暗藏着个体的断根与危机感。在如此矛盾的语境下,一种混杂了渴望与迷茫、激进与怀旧的复杂情绪应运而生。当现代性遭遇个人主义极强的美国性,令失范的情形变得更为糟糕。
2.城市文明的“圈外人”
斯宾格勒将都市中心的兴起看作是文化转折点的标志:“代替一个真实的、土生土长民族的,是一种新型的、动荡不定地黏附于流动人群中的游牧民族,即寄生的城市居民。他们没有传统,绝对务实,没有宗教。”[12]278伴随美国拓疆运动而来的,是另一场运动方向截然相反的文化剧变,财富从乡村(西部)转移到了城市(东部)。纽约成为当时美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缩影,既是“希望与梦想之城”,也是“金钱与堕落之地”。
相较于精英云集的东部和新兴的西部海岸,美国中西部既是传统田园理想的象征,又是落后保守的代表。因渴望在文化转型中寻求身份认同,菲茨杰拉德迫不及待地出逃平庸单调的家乡小镇,前往喧嚣华丽的纽约接受大都市精神的滋养。然而经历挫折与失败后,他意识到身处这个“魅力与孤寂并存的世界”是多么不胜惶恐。菲茨杰拉德曾在《我遗失的城市》中自述了自己作为“闯入者”的复杂情绪:“记得有个孤独的圣诞节,我们在城里没有一个朋友,也没有一栋房子可以去。我们找不到可以依附的核心……说得更确切些,纽约把我们给忘了,所以任凭我们住下来。”[13]78菲茨杰拉德成为大都市的“无家可归者”,他心向往之的“大都市精神”成为疏离、冷漠的代名词,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对理想主义的绞杀更是给菲茨杰拉德当头棒喝,“我那些关于纽约的宏伟梦想被一一玷污”[13]79。
菲茨杰拉德怀揣出人头地的梦想来到纽约这一“抱负与成功之地”,渴望在东部的上流社会占据一席之地。然而“世袭有钱阶层”的封闭性与排外性、精英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话语暴力却使他游离在东部精英社交圈外,成为城市文明冒失的闯入者。这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社会纽带的建构,并引发身份焦虑。
菲茨杰拉德因《人间天堂》一举成名,收获了金钱与爱情。然而作为城市的“典型产品”,他感到似乎突然被推入都市生活的旋涡,“几乎已经对自己到底是谁一无所知,也弄不明白我们在从事什么工作”[13]89。他本人曾在《纽约晚邮报》头版的访谈中,坦诚了自己的酗酒、精神上的崩溃和创作力的枯竭。
跌宕起伏的城市体验使菲茨杰拉德意识到纽约所承载的现代性的消极属性,它的潘多拉之匣。正如理查德所言:“现代城市徒具一副许诺的外表,似乎它具有巨大生命力(许诺了人世间所有的神秘与美丽),而在其内在现实中,却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把我们推向死亡的东西(一个死人躺在一辆堆满鲜花的灵车上,从我们身边经过)。”[12]95菲茨杰拉德沮丧地发觉以纽约为代表的东部大都市的局限性。都市生活归属感的缺乏迫使他将对温情、平等的理想投射到远离现实的他时、他地,并渴望在远离东部城市的中西部小镇寻觅往昔的淳朴与天真。“他第一回目睹城市边界消逝在四面的乡野,融入在一片蓝绿之间,唯有后者才是真的无远弗届。”[13]78然而在菲茨杰拉德对城市的精神逃逸中,似乎又夹杂着一丝向往。他无视都市文明中愈发商品化的爱情,执着地在现代社会寻觅爱情的永恒与纯粹。在精英主义与物质主义的双重话语暴力下,菲茨杰拉德的这一需求无疑再次遭遇拒斥。
3.爱情的“弃儿”
如程锡麟所说,菲茨杰拉德一生中对社会地位和“飞黄腾达”倾注了大量的精力[14]182。菲茨杰拉德对有闲阶级的特权生活既充满向往,又愤愤不平。凭借贵族遗风的沉淀和良好的家庭教育,他无须刻意培养其文雅谦和的魅力,便能毫不逊色地混迹于上流社会的社交圈。然而在20世纪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肆虐的美国,金钱是阶级堡垒的通行证,它为东部的富人们铸就一道围墙,并将异己分子拒之门外。
上流社会的爱情法则进一步区分了阶层。菲茨杰拉德对东岸精英生活的向往,致使他似乎总倾心于上流社会的名媛,而“圈外人”的身份则使其爱情追求屡屡受挫。吉内芙拉·金是芝加哥家世显赫的名媛,菲茨杰拉德凭借与生俱来的翩翩风度俘获了她的芳心。然而,她的父亲查尔斯·金直截了当地宣布:“穷小子不应该想着娶个富家千金。”这段失败的恋情令菲茨杰拉德刻骨铭心,以致成名后,他在很多作品中都以吉内芙拉为原型,塑造了一个个“金子般的女郎”。在菲茨杰拉德辍学参军期间,他又与亚拉巴马州的社交名媛泽尔达·塞尔坠入爱河。泽尔达后因菲茨杰拉德“钱”途黯淡,取消与他的婚约。“圈外人”的身份及物质主义的话语暴力让菲茨杰拉德屡次成为爱情的“弃儿”。直至菲茨杰拉德因《人间天堂》一举成名,才得以恢复婚约。面对失而复得的爱情,菲茨杰拉德在日记中写道:这个一年之后口袋里金钱叮当响才娶到那个姑娘的男人,将永远珍视他对有钱阶级终身的不信任和敌意[14]179。
四、菲茨杰拉德作品中的怀旧性建构
1.理想时空的怀旧性建构
马尔科姆曾如是评价菲茨杰拉德:他以敏锐的嗅觉洞察到了变化时代中飘忽不定的、矛盾的、未定型的、但又是真实的思绪与心态,表达了新旧更替时期的认识混乱和朦胧的恐惧。这是他最优秀作品的价值所在[10]35。迷惘的现代性情境、断裂的社会纽带,以及都市文明中精英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话语暴力使菲茨杰拉德在转型期的现代社会无所适从,渴望疏离现实,转而在作品中借助理想化策略,从“金色西部”的理想时空、“过去时”的爱情纽带两个方面进行怀旧建构,试图从虚幻的想象中汲取些许精神力量,用以消解现代性的消极属性。然而其建构并不完美,在一定程度上并未完全起到补偿作用。
菲茨杰拉德笔下的主人公大多来自美国中西部,且都经历由最初的叛逃到回归中西部的历程。作为美国“花园神话”的载体,中西部寄寓着美国建国初期天真质朴的田园理想,成为原始道德的发源地。田园理想深深根植于美国的国民性中。从杰弗逊的时代开始,美国理想的基本意象便是乡村风景,一个扩展到整个大陆秩序井然的绿色花园,史密斯认为这一主象征包含了一组表示幸福、成长、增加以及在土地上幸福劳动的隐喻[15]。共和国成立之初,美国人十有八九是农民。丰裕悠闲、淳朴安定的乡村共和国成为建国以来理想社会的典型模式。霍桑、梭罗等作家或在作品中表达对机器侵蚀田园理想的焦虑,或身体力行,在恬静的瓦尔登湖畔开启远离尘嚣、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
理查德认为:“正如T.S艾略特一样,菲茨杰拉德向过去寻找已经消失于历史中的某个理想时刻。对艾略特来说,那是17世纪的伦敦;对菲茨杰拉德来说,那是美国共和国初期。”[12]209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的甚嚣尘上导致道德权威的丧失,身处现代城市喧嚣的精神“荒原”,菲茨杰拉德不由回望建国初期悠然恬静的西部田园牧歌。出于对归属感的需求及维护身份连续性的需要,他借助理想化策略,把对往昔质朴田园理想的渴望投射到远离此时、此地的理想化时空,在作品中以对立的方式对东西部进行怀旧性建构。西部以城镇为表征,代表承载美国田园理想的精神家园、富有道德内涵的文化符号;东部以城市为表征,代表物欲横流、人情淡漠的精神荒原。怀特认为菲茨杰拉德对东部和西部的截然划分就如詹姆斯对美国乡土气的美德与欧洲讲究优雅的感受力的两相比较一样透露着诗意和真相[16]。
然而20世纪初,随着经济科技的高速发展,机器文明逐渐吞噬田园牧歌的发声,西部往昔的花园神话随之遭遇破产——“自由土地已消失,现在最后一亩农田已经归属于私人公司了”[17]。传统农业逐渐被工业及其催生的金融机构所湮没,从这些机构中诞生了一批如汤姆·布坎南、沃伦家族(1)上述分别为菲茨杰位德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夜色温柔》中的人物。之流的有闲阶级及其享有特权的新世界。盖茨比作为从中西部走出的“天选之子”与汤姆等东卵人的交锋实则展现了传统道德秩序与金钱至上法则的矛盾以及浮华的城市文明与传统田园牧歌的冲突。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尼克起初感到“中西部不再是世界温暖的中心,而倒像是宇宙的荒凉的边缘”[18]3。西部平淡乏味的城镇,街头巷尾三五成群絮聒家长里短的小镇居民,曾让尼克一度十分向往“东部无可比拟的优越性”[18]4。于是怀揣对都市文明的憧憬,他动身前往东部,并“自以为是一去不返的”[18]4。然而当尼克亲历“梦想之地”的堕落与腐朽后,东部由其最初心向往之地变为避而不及之所。
来自东卵上流社会的汤姆和黛西,他们看似高贵精致的生活背后,潜藏道德精神危机,与盖茨比天真浪漫的品质形成鲜明对比。汤姆世袭贵族的出身却未赋予其相应的品质与做派,在尼克眼中反倒成为“酒徒色鬼”般存在。他与黛西貌合神离,并明目张胆地与有夫之妇勾结,而后者则对丈夫的不忠熟视无睹,甘当“一个美丽的小傻瓜”,灵魂空洞地虚度光阴。汤姆和黛西深谙上流社会的法则,世故冷漠,心安理得地享受所谓特权阶级的“特权”。小说中,菲茨杰拉德借尼克之口,讽刺东部城市的堕落风气及特权阶级的道德滑坡:汤姆和黛西,他们是粗心大意的人——他们砸碎了东西,毁灭了人,然后就退缩到自己的金钱或者麻木不仁或者不管什么使他们留在一起的东西之中,让别人去收拾他们的烂摊子”[18]70。
盖茨比实则成为黛西和丈夫博弈的牺牲品,他所特有的西部人的天真淳朴正是菲茨杰拉德在现实中认同却难以寻觅的另类价值。盖茨比道德上的优越感使他对城市中的尔虞我诈不甚了解也并不在意,他忽视都市文明中身份、阶级的复杂性,对东卵与西卵间无法逾越的鸿沟视而不见。正如理查德所指出的,“盖茨比缺乏都市所需要的世故。对目标的浪漫化理解,若是在边疆,可能会获得成功,城市的诱惑对他来说是一个复杂的陷阱”[12]215。在属于汤姆和黛西之流的城市空间,根植于盖茨比内心的淳朴美德反而使其在与“城市”的交锋中屡遭算计,最终葬送性命。
小说结尾,菲茨杰拉德安排尼克重回中西部,在空间上疏离道德堕落、冷漠疏离的东部都市,此举寄寓了作者本人对田园牧歌的怀旧情结,成为背离现代性的精神逃逸。中西部小镇相对封闭的风气与家长里短的琐碎在现代性的映衬下,已成为一种不可多得的温馨与安宁,当尼克重新踏上归家的土地,倏然间感受到与这片土地一脉相承的文化精神:“迎着车窗闪耀,威斯康星州的小车站暗灰的灯火从眼前掠过,这时空中突然出现一股使人神清气爽的寒气……在奇异的一个小时中难以言喻地意识到自己与这片土地之间的血肉相连的关系,然后我们就要重新不留痕迹地融化在其中了。”[18]197中西部的田园理想自身承载的天真质朴、温馨稳定的特质正是菲茨杰拉德在现实中认可却无处寻觅的另类价值,通过理想化策略建构出的中西部小镇成为其在现代性重压下寄托“归家”向往的精神乌托邦。
2.社会纽带的怀旧性建构
怀旧通常起因于归属感缺失,怀旧者往往对温馨、稳定的社会纽带充满期待。爱情作为最底层、最基础、最基本的社会纽带形式,寄托了人们对归属感、安全感的美好期许。然而在充斥瞬间性、短暂性和流变性的现代社会,受金钱、阶层所捆绑的爱情愈发商品化。菲茨杰拉德现实生活中屡屡受挫的感情追求和失而复得的爱情经历令其患得患失,从而愈发渴望在现代粗俗的物质社会提炼爱情的永恒。
斯科特·唐纳森认为:“爱给菲茨杰拉德的生活带来了情感危机,也为他的小说创作直接提供了素材。”[19]在现代性和美国性的挤压之下,菲茨杰拉德在文本中建构的多是“过去时”的爱情纽带。受主流话语环境的压迫,其笔下的主人公因物质、阶层方面的劣势,从未真正拥有过爱情。然而这种夹缝中的“过去时”的爱情给予菲茨杰拉德怀旧的社会纽带得以存在的特殊时空:男主人公单方面的相思与执着使爱情在精神上得以延续,成为永恒。学者认为,与现实博弈能力越强者,其想象中的纽带和价值,更贴近现实;反之,则越远离现实[7]66。菲茨杰拉德通过对爱情纽带的怀旧处理使爱情在远离当下与现实的安乐乡中仍然鲜活。如此远离现实的建构,也反映出菲茨杰拉德在主流话语暴力之下的谨小慎微。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菲茨杰拉德将盖茨比与黛西的爱情纽带放置于特定的时空之下:五年前的军营,动荡的战争前夕,盖茨比在刻意隐瞒其贫寒出身的前提下与贵族小姐黛西发生了一段露水情谊。黛西是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者,盖茨比视为至高无上的过往情感对她来说只是另一簇用以点缀空虚世界的烟火。在权衡阶层和物质的利弊后,黛西“转年初春过后”便心满意足地嫁给了门当户对的纨绔子弟汤姆,继续她浮华空洞的生活。
故事到这里本应结束,无非是另一个司空见惯的穷小子爱上富家女,最终意料之中惨遭抛弃的结局。然而菲茨杰拉德却将盖茨比建构成天真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他难以理解上层社会身份、地位的复杂性,并对尼克的忠告置若罔闻,并幻想黛西从头到尾爱的仅他一人。五年前与黛西片刻的激情却成为盖茨比一生永恒的追求。尼克评价道:“他那种强烈的感情是世人难以置信的。”[18]56
再次重逢,黛西却将盖茨比视为与花花公子汤姆博弈的筹码。当汤姆当众戳穿盖茨比所从事的为上流社会所不齿的勾当时,黛西则忙不迭地再次退回到上流社会的安全线内,哀求丈夫将她带离。即使如此,盖茨比仍未放弃对黛西的爱情,“黛西之于他犹如绿岛当年之于荷兰水手一样,而他也像他们一样,错把一时的情感当作永恒的可能”[12]67。对黛西来说,她与盖茨比的爱情即使曾经存在过,也只是片刻的悸动。而盖茨比却为了爱情的幻梦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单方面在精神上实现了爱情的永恒与纯粹。
吉林指出:“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的人物多坚守自己的爱情与理想,试图在瞬息万变的当下寻找恒久的价值,因而陷入了詹姆斯所说的多愁善感者的理性主义误区。”[20]45《夜色温柔》中,菲茨杰拉德对迪克和妮珂爱情的建构也折射出他对爱情之永恒的向往。
迪克则是盖茨比形象的延续。在《夜色温柔中》,迪克曾是一位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心理医生,他具有多重性格,既天真又复杂,既浪漫又自律。迪克依靠他那充满活力、鼓舞人心的自我,成为美国救赎者的象征,是其牧师父亲强调的“良知、荣誉、礼貌和勇气”[21]346的产物。迪克心甘情愿地接过特权阶级丢下的棘手包袱,为妮珂打造了一个爱的伊甸园,使爱人不为混乱的外部世界所累。米娜认为“迪克牺牲了足智多谋的自我,甘愿成为爱和救赎的源泉以及‘腐败家族的最后希望’。他乐意去救赎、去服务、去治愈、去创造爱并变得有用。这就是他的魅力所在”[21]348。然而随着妮珂日益独立,迪克却愈发沉沦。妮珂通过榨取他生命的精华,不仅成功幸存,而且巩固了自己的人格。而迪克却因为完全献身于爱情而最终一无所剩,孑然一身回归到家乡的中西部小镇。
罗伯特·奥恩斯坦认为菲茨杰拉德关于“美德和骑士精神的小镇观念”[14]65是一种业已消失的价值观,“那种罗曼蒂克不属于现在,而属于被想象的记忆美化了的过去,属于由错觉允诺了的不可实现的未来”[14]61。菲茨杰拉德在怀旧想象过程中,通过对爱情纽带进行怀旧式处理,从而给予爱情以合理存在的时空。主人公的单相思使爱情单方面地在精神上得以延续,从而在单一的时空维度,实现对永恒、纯粹爱情纽带的建构,以期弥补愈发商品化的现代爱情所带来的失落感。
五、结 语
菲茨杰拉德作品中强烈的自传色彩和深刻的历史意识真实地反映了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时代精神。作为爵士乐时代的代言人,菲茨杰拉德在社会转型期中在作品中流露出的怀旧情结折射出现代化进程中个体所经历的迷惘与困惑。本研究通过发掘美国知识分子对待机器文明吞噬田园牧歌的发声,对认识美国文学、美国文化及国民性极具参考价值,得以一窥社会转型时期“美国中西部清教徒式的浪漫想象与执着的理想主义”与工业社会机器文明的冲突缩影,从历史和文化的双重维度发掘个体在社会过渡期所经历的“机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