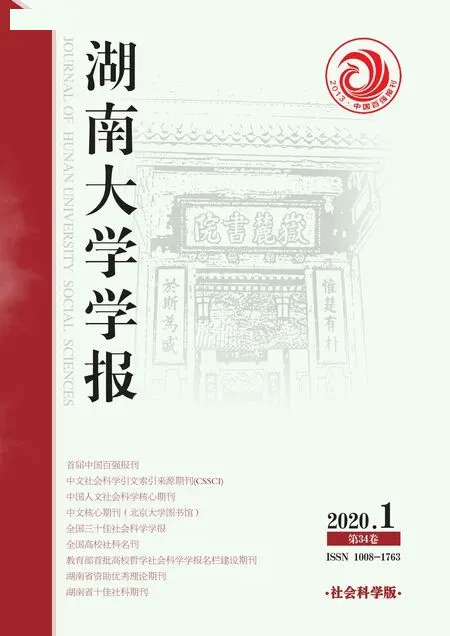“一体”训仁与以“公”释仁:二程仁说的比较 *
朱汉民,李立广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以“万物一体”训仁与以“公”释仁是本体论仁学阶段两种代表性仁说,前者即指程颢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莫非己也”[1]15;后者即是程颐的“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个公字”[1]153。二程虽然共同体贴出一个“天理”本体,都是理学的开创者,但在“仁”的训释上差别较大,一个以“一体”训仁,一个以“公”释仁,这两种训释有什么不同?由此引出了程颢、程颐兄弟哲学思想的差别问题,他们的仁说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如何评价这些思想差别?
本文认为,程颢、程颐兄弟仁说的差别,可以看做是“仁之体”与“仁之用”、生命境界论与道德实践、直觉工夫与穷理去欲之间的差别,由此,二者仁说也各有利弊。他们的仁说之所以存在这些差别,与他们的气质个性与思想境界不同有关。
一 “仁之体”与“仁之用”
就本体论仁学而论,“万物一体”思想来自张载《西铭》,其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深受程颢赞许:“订顽一篇,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学者其体此意,令有诸己,其地位已高。”[1]15所谓的学者其体此意,即“通万物而谓之道,体万物而谓之性”[2]64。程颢深会此意(西铭某得此意)[1]39,据此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论断。
程颢的以“万物一体”言仁,既是本体论,又是境界论。在本体论上,“万物一体”言仁,确定了“存理”之必要性,在境界论上,其确立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的体认天理方法。
程颢的“万物一体”论,其“一体”是具有本体意义的性、理。万物一理、万物一性就是“一体”之仁。他说:
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生生之谓易”,生则一时生,皆完此理。[1]33
天降是于下,万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谓性也。[1]30
从理上看,万物自然生生,理便在其中,因此,天地万物都有是理,此理即生生之理,故可称为“万物一体”。从性上看,天地万物发育流行,就是生生之理的显现过程,也是各正性命的过程,即“性者万物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2]21。从本体论上来看,万物之理就是万物之性。因此,万物一体是建立万物皆有其性(理)的基础之上,所谓一体之仁,就是生之性、生之理。
“万物一体”是通过仁者内心的体证。这种本体之仁是一种形上存在,因此,“一体”之仁难以言说,需要主体的内在体证。他说:
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之功用。仁至难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1]15
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譬最近。[1]33
在他看来,孔子通过“推己及人”来诠释“爱之仁”,是在人与人之间将心比心,即这种“能近取譬”是在人情上释仁,只是“仁之方”。与之不同的是,程颢认为,“万物一体”是在性理上言仁,故而难以名状,只能通过主体的整体性思维去把握,真切地体悟我与万物之间的一体关系。这种关系就如人的手足一样,如果缺乏这种“感通”知觉,就不属于己了,即“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程颢也是以譬喻的方式诠释了一体之仁,这种“感通”,就如“切脉最可体仁”[1]120,本质上是一种内在直觉。
所以,他强调“感通”的目的即是要人通过直觉来体认到仁体是一个形上的存在,但是这个仁本体其实也是人文化的道德伦理:
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1]121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1]77
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于人身而言之,乃所谓道者也。[3]344
作为万物中的一类,人与万物一样都有其性理。就人自身而言,这种性理就是父子君臣等一类的道德伦理,也即“仁之理”,而且这类“伦理”,非人为安排的,其与天理一样都是自然的“定理”,这样,人文之理与自然之理统一起来。天理本体与仁本体合一,使儒家伦理获得了宇宙本体意义,而具有普遍性、绝对性、权威性。本体论仁学所谓的“存理”,即主体能够觉识、体证这一形上仁体的存在,以摒弃一切不合理的情感、欲望等形下的经验,来明理、体仁、复性。
程颢以“一体”言仁,其哲学价值在形而上的层面上肯定了“仁”的本体性。但是,若要存理、体仁,就得是“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则无我也”[1]125。这就需要超越作为个体存在的情感、经验,也就涉及到主体如何处理内外、主客关系,以及作为个体存在的内外、主客之间的关系如何,仁体以什么方式呈现,这类问题则由程颐的“仁之用”来解决。
程颐提出以“公”释仁,把内外、主客关系、己与他、个体与群体、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一体”关系,确定为“公”,即“仁之道”。从某种意义上说,程颐以“公”释仁,是“一体”释仁自然的展开。程颐说:
又问:“如何是仁?”曰:“只是一个公字。学者问仁,则常教他将公字思量。”[1]285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将公便唤做仁。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只为公,则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也。[1]153
仁道难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为仁。[1]63
程颐教人思量“公”,即思量内外、物我之间的“一体”关系,这样就能体悟到仁。就此而论,其与程颢一样,也需要对天理的内在体认;不同的是,程颢强调“仁之体”就存在于我们的本心之中,如果每一个体从自己的内在本心出发,就可以发现“仁之体”,进而达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的“大我”“无我”的精神境界。但是,程颐关注到个体自我是具有情感欲望的存在,这些个体之“私”可能与“仁之体”是有冲突的,所以他强调个人应该要“无私”,以持守崇高的天理。虽然“无我”与“无私”本质上都是“公”,但是他将程颢基于人的内在体验与生命境界上的“廓然大公”转向外在“公”与“私”的对立,所以他的仁学主要体现为“仁之施”“仁之用”。因此,仁之“一体”与仁之“公”的关系就是体用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的存在,所以他强调“非以公便为仁”。
因此,程颐的兴趣不在于“万物一体”的精神境界,他把对仁的内在体验引入外在道德实践中,他说: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仁者用心以公,故能好恶人。公最近仁。人循私欲则不忠,公理则忠矣。以公理施于人,所以恕也。[1]372
在程颐看来,好人恶人是“仁之用”,即仁者用公心处理现实中己与人之间关系,就此而论,人不循私逞欲,是心之公,也就是“忠”,以之施于人叫做“恕”,即一贯之道。这样,程颐把人心之公,转化为孔孟的忠恕之道,而忠恕正是原始仁学的践履功夫,所以他说:“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则自忠恕,其致则公平。”[1]153在他看来,忠恕之道是公平处事原则,人的德行修养必自忠恕始,做到了忠恕,那么就能做到公平。可见,以“公”释仁的理论价值就在于“公”所具有的实践性、现实性。
此一思想也被朱子所吸收,他对程颐以“公”释仁的实践面向又作了一番论证。他说:“公却是仁发处”[4]116,认为公是仁的发用,即“公”是“仁”的方法,只有做到了“公”,才是行仁。对于“仁”与“公”之间的关系,他又做了进一步阐释:“仁在内,公在外。”“惟仁,然后能公。”“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极至处。”[4]116实质上,这种关系就是体用关系。正是“公”的实践面向,是仁体的发用,是克己的功夫,所以朱子也强调:“公不可谓之仁。”[4]117
如果说“一体”释仁的旨趣在于主体内在的体验,通过对内在心性的自我超越,以获得对形上仁体的体证,那么,以“公”释仁的宗旨则在于其对外部世界的关切,通过维护内外、主客关系统一,使己与人、个体与整体、人与社会保持一体关系,是合内外之道在道德实践层面的展开。
二 生命境界与道德实践
理学家建构的仁学,“有一个最终目的,便是引人成圣”[5]370。如何才能成为圣人,这不仅要有崇高的生命境界,还需要坚实的道德践履。
程颢提出的“一体之仁”,既是一种本体论,更是一种“生命境界”论。程颢心目中的一体之生命境界,与仁作为形而上的本体一样,难以用语言名状,故而需要人内心去体识。程颢反复说:
人能放这一个身公共放在天地万物中一般看,则有甚妨碍?虽万身,曾何伤?[1]30
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者哉?[1]74
子曰:至公无私,大同无我。虽眇然一身,在天地之间,而与天地无以异也。夫何疑焉?佛者厌苦根尘,是则自利而已。[1]1172
“浑然与物同体”“天地为一身”和“人与天地一物”都表明人与天地万物构成了一个宏大生命体,在这个生命体中,人与天地万物同性、同理,同生共在同一时空中,是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在这个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中,如果“人特自小之”,则是不仁,只有把自己放到天地万物中当作一物来看,则有与天地同流,万化归一的生命体验。这种生命境界则要求每一个生命要超越个体“小我”,才能达到对“大我”境界的体证,即“至公无私,大同无我”的内在体验。
“万物一体”之仁说,提升了人的生命高度,以天人一体之视阈来审视人自身,即人与天地万物一样源自生生之仁,并与万物息息相关。即是:
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1]120
人只为自私,将自家躯壳上头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佗底。放这身来,都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1]33-34
在他看来,仁者即以万物一体的“大我”,超越了自身的形质,消弭主客界限,内外两忘。进而言之,这种“大我”就是“不能有诸己”,也即是“无我”。这样立身于天地之间,才能与万物大同;如果人只为“自我”“私己”,必然会漠视“天理”“仁体”,唯有视己如物,使“小我”的境界得以提升、扩展,才有崇高的生命体验,即其所谓的“大小大快活”。这种境界体验即要求每一个生命要超越个体的情感、欲望,才能达到对仁本体(性理)的体证,否则就是自私、自小,而不仁。要而言之,想成圣人,必绝私己,即“无我”。
“廓然而大公”是一种内在体验。程颢所说的“大公”,是摒弃“小我”,而“无我”,主要体现在心与情上。他说: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1]460
圣人致公,心尽天地万物之理,各当其分。[1]142
这种“大公”就如天地无“私心”、圣人无“私情”一样来对待万物,以超然旷达的胸襟来顺应一切外物。这种“廓然而大公”仍然着力于圣人的人格修养和生命境界上,他所说“圣人致公”实质上就是明理,也即体仁。他并没有以“公”来统一内外、主客之间关系,他的兴趣在于使“仁的理解内在化、境界化”。[6]265
程颐的以“公”释仁引出“无私”论。如果说“一体”之仁是在生命境界上,引出了主体内在心性的超越性,那么以“公”释仁,则是在实践层面上,触发了公与私的紧张。因此,在其仁说上,程颐就强调了“克私奉公”的必要性:
虽公天下事,若用私意为之,便是私。[1]77
子曰:公天下之事,苟以私意为之,斯不公矣。[1]1222
子曰:理与心一,而人不能会为一者,有己则喜自私,私则万殊,宜其难一也。[1]1254
程颐则把“廓然而大公”这种境界体验外在化,以之来裁量内外、己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公天下之事”则不能存有“私意”,“有己”即是自私。
实际上,公与私在孔孟仁学中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儒家所推崇的井田制就涉及公与私问题,孟子说:“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7]87若依孟子所论,也只是先公后私,而非因公废私。有论者指出:“只有在‘公’‘私’的价值义上,孔孟儒家才讲‘大公无私’和‘公正无私’;并且,此所谓‘无私’,不是‘无我’‘无己’,不是对私利的否定,而是不奸邪、不偏私。”[8]57-64
但在程颐以“公”释仁的学说中,公与私的对立十分尖锐。其突出表现如下:其一,一体之公与个体之私不容并立。只要有“私意”“有己”的存在,则会打破一体的和谐,即“私则万殊,宜其难一也”,难以达到一体之仁的境界,这仍是内在体验,与存理灭欲的工夫有关联;其二,公与私的关系,就是“无我”与“有己”的关系。在实践层面上,实践主体只要怀私处事,就无法做克私奉公。其三,大公无私是圣人人格修养功夫。“圣人无私无我,故功高天下,而无一介累其心。”[1]1271在他看来,道德主体做到无私、无我,就是圣人。
这种公私观进入心性领域,即与道德主体内在的“无私”“有己”密切相关,这样,对人的道德评价只简约为一个公私之分,反映到价值上就是一个义利之辨。
三 识心工夫与去私工夫
二程兄弟的“识心”与“去私”都是成圣的功夫,但是程颢所主张的仁之“一体”提升了人的生命境界,突出了儒家内向的识心工夫;而程颐“以公释仁”则强调了外在的道德准则,并由此提出存理灭欲、克己去私的工夫。
程颢认为,仁是“万物一体”的本体和境界,这须借助于自我内心之仁的体认才能实现。所以,大程提出体认“仁体”的工夫,以破除“我”与“物”、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回归到“理一”的本体之仁与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程颢的“识仁”是一种直接体悟仁道本体、进入天人境界的工夫。先秦儒家以“仁”为重要的道德原则,宋儒进一步将“仁”本体化,“仁”成为“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最高境界,而所谓“识仁”,也就是对人物同体的仁之存在、境界的直觉、体悟。程颢说: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待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1]16-17
程颢的“识仁”,不是在自我之心外的“防检”,更非自我之心外的“穷索”,而是对自我内在之心的察识,意识到“万物皆备于我”,体悟到吾心之仁乃天地之仁,天地之仁亦吾心之仁。所以,程颢强调从自我主体之“心”去体悟、察识形而上之仁体。他说:
学者识得仁体。实有诸己,只要义理载培。[1]15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言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1]15
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1]15
由此可见,程颢的“识仁”方法,也就是一种对自我内心的体悟、察识的内求方法。
当然,程颢以“一体”训仁,侧重于本体、境界之仁,能够强化道德主体性,充分调动人的主体能动性。但是,以“一体”训仁,易于使人脱离生活实际,而遗身忘世,其弊如朱子所言:“泛言‘同体’者,使人含糊昏缓,而无警切之功,其弊或至于认物为己者有之矣。”[9]3281朱子担心“一体”训仁,导致物我不分,会消弥了人的主体意识,进而失去了警惕、省察的修养功夫,至于“格物”,则更无从谈起。朱子亦云:“学者若得胸中义理明,从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应曲当。人若有尧舜许多聪明,自做得尧舜许多事业。”[4]237明理、体仁不是终极目的,圣人还要以此去度量事物、做尧舜事业。如果圣人只论生命境界,则势必远离人的生存现状和生命本身,这其实是宋儒所不愿看到的。需要指出的是,程颢提出的圣人人格境界太高,非是常人所能企及。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诚贯于金石,孝悌通于神明。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1]637,足以见其胸怀澄澈、气象浑然。其“心普万物而无心,情顺万物而无情”的超然、洒落的生命态度,以及与万物为一体的生命体验,尤为难得,岂是一般人所能学到、做到的?
相对而言,程颐的“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1]316,则显得平实多了。程颐以“公”释仁,故而在修养工夫上,主张通过在实践层面的“克己去私”的工夫,进而达到对仁的遵循。所以,程颐特别强调理与欲、公与私的对立:
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虽有意于为善,亦是非礼。[1]144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1]312
敬则是不私之说也。才不敬,便私欲万端害于仁。[1]153
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须是克尽己私后,只有礼,始是仁处。[1]286
与“私欲”相同意义的,还有“自私”“私意”“私心”“私己”“有己”等等,在程颐看来,这些个体之“私”都会妨碍人的明理、复性、得仁。
原始儒家一直强调义利之辨,从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的“舍利取义”,到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再到程朱理学,依然固守儒家这一价值传统。但在理学阶段,儒家的人格目标由“为君子”转为“成圣人”,由此产生了求仁与成圣的功夫不同。其一,孔孟的求仁是诉诸人的感性经验,是仁之方,程颐的成圣是诉诸人的道德理性,是复性、明理;其二,理欲之辨、公私之辨是义利之辨合乎逻辑地发展。原始仁学中的义利之辨只是一种价值导向,孔孟在如何进行价值选择方面却没有申而论之,而程颐通过理欲之辨、公私之辨对其作出了理论上的补充和完善,是对这一命题的深化,换言之,存理灭欲和克私奉公的价值取向依然是舍利取义。若要明理,诚如程颐强调:“损人欲以复天理,圣人之教也”[1]1170,“无人欲即皆天理”[1]144。若要成圣人,不得不存理灭欲。但他又认为克私奉公也是成圣的法门:“圣人无私无我,故功高天下,而无一介累其心。盖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己也。”[1]1271“圣人自是至公,何更避嫌?”[1]234因此,在程颐看来,存理灭欲、克私奉公都是十分重要的成圣功夫。
四 二程不同仁说形成的原因
从程颢以“一体”训仁,到程颐以“公”释仁,体现出理学时期本体论仁学发展多样化形态。为什么二程兄弟的仁说会有这种差异呢?这就涉及儒家哲学乃至中国哲学的形成特点。理学的义理构架往往与理学家的生活世界及个人气质个性有关。二程兄弟两种仁说上的差异,确实与二人的生活世界、气质个性、思想境界的不同有密切关系。
二程的学术差异与二人的气质个性有关,朱子曾经作过比较:“明道说话超迈,不如伊川说得的确。”“今之想象大程夫子者,当识其明快中和处;小程夫子者,当识其初年之严毅,晚年又济以宽平处。”“明道语宏大,伊川语亲切。”“明道十四五便学圣人”,“伊川谨严,虽大故以天下自任”。[4]2358-2361程颢的“超迈”“宏大”“明快中和”的个性和“学圣人”的志向,使其对仁的阐释趋于内在化、境界化;而程颐的“的确”“严毅”“亲切”的性格,以及其“以天下自任”的抱负,对仁的理解自然趋向于外在性、严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