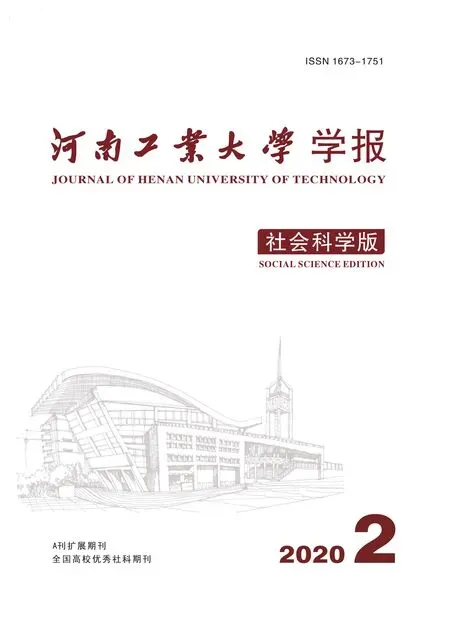明清时期上党梆子的历史源流和社会功效
陈少晶,崔顺利
(忻州师范学院 历史系,山西 忻州 034000)
上党梆子是晋东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传统戏剧之一,它与运城地区的蒲剧(又称蒲州梆子)、晋中地区的晋剧(又称中路梆子)、忻州地区的雁剧(又称北路梆子)并称为“山西四大梆子”。关于明清时期上党梆子的源流和形成,很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清乾隆年间的严长明、焦循,清末民初的徐珂,乃至现代的范紫东、齐如山、王绍猷、圆遗徐慕云、周始白、马彦祥等学者、专家,都对此做过简单探索[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余从著述的《戏曲声腔剧种研究》,周传家所著的《新花部农谭》等戏曲史专著,都对上党梆子在明清时期的源头流变做过简单的介绍。
但是由于戏曲史家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地位、所掌握的史料、所研究的角度和方法的不同,人们并未深入探究过明清时期上党梆子的产生和发展。以张庚、郭汉成先生的《中国戏曲通史》为例,大多数戏曲史著作都只是在讲解梆子腔形成的过程中,简单叙述了其分支上党梆子的源流。而且,目前学界对上党梆子的研究主要侧重在上党梆子的生存现状、传承保护以及未来发展上。相对而言,对于明清时期上党梆子这一地方戏曲的历史源流以及其在明清时期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功效几乎无人涉猎。本文即从此入手挖掘其历史价值。
1 明清时期上党梆子的源流
1.1 明末清初上党梆子的起源与发展
上党,位于今山西省东南部,古潞泽辽沁四州一带,主要包括今长治和晋城等地,其东依太行与华北平原为界,西屏太岳与晋南接壤。自古以来,上党便是山水雄奇之所,兵家必争之地,史称“得上党而望中原”。上党梆子便是流行在上党地区的一个古老剧种,其发源地为古上党的泽、潞二州。上党梆子的主要艺术特色是以上下句唱词相结合的板腔体为主,“昆、梆、罗、卷、黄”五种声腔同台演出的剧种,兼有地方小戏俗曲作为曲牌连缀[2]。上党梆子在初始时被官府称为“土戏”,民间把它与秧歌等地方小戏对比而称作“大戏”。1934年至1957年间曾赴省城太原演出,被称为“上党宫调”。1957年山西省举办第二届戏曲会演时,由省政府正式定名为“上党梆子”。上党梆子音调高亢明朗,粗犷朴实,表演强烈明快,慷慨激昂,铿锵有力,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在2006年被收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1.1 明末清初上党梆子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原因
首先,上党地区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活动,是明清之际上党梆子得以形成的重要土壤。在上党地区,上党梆子形成前的歌舞形态最早可以考证到西汉时期。在西汉皇族刘安及其门客撰写的《淮南子》一书中,就有“阳阿薤露”和“阳阿奇舞”的记载。这里所指的“阳阿”就是今天晋城市的大阳古镇,“薤露”则是一种古代挽歌。“阳阿奇舞”引述的典故是指西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能在盘子上翩翩起舞的故事,而培养赵飞燕的正是当时阳阿侯国的阳阿公主。从《淮南子》中记载的“薤露”和“奇舞”中可以看出,当时这里的歌舞形态已经比较完备了。
除歌舞以外,上党地区也诞生了较早的戏曲元素。在唐代,以“诙谐滑稽”著称的“参军戏”(参军原为官职名称,参军戏就是戏弄参军的意思)开始盛行。但实际上,参军戏早在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就已经出现,据《太平御览》引《赵书》的记载:有戏名曰《周延参军》,讲的是后赵时期有一个叫周延的参军因为贪污黄绢被罚而被调侃戏谑的故事。这个记载就发生在后赵石勒建国的上党地区。唐开元年间,在民间参军戏流行的同时,上层统治者也对戏曲推崇备至。唐明皇李隆基性喜戏曲,曾三次训幸上党,大搞乐舞,至今仍然被上党地区的戏曲从业者称为“梨园之祖”。上层统治者的支持和民间百姓的喜爱都对上党戏剧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宋元时期,话本、杂剧的兴起也为明清之际上党梆子的产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据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泽州孔三传者,艺汴京,创诸宫调,士大夫皆可颂之。”[3]此后,诸宫调这一说唱的艺术形式很快被孔三传及其家人带到自己的家乡,为以后上党梆子的独特说唱艺术奠定了基础。泽州也因此成为上党梆子萌芽的沃壤。
到了明末清初,上党梆子才得以形成。在经历了汉、唐、宋、元这一漫长的历史文化沉淀之后,生活在上党这一片古老土地上的人们才最终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戏曲文化。在明代,分封在上党地区的历代沈王,既无兵权,也无政权,只能“以声色诗酒自娱”。因此,明代两百余年来,上党地区的藩王就对上党的地方戏曲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王宫内部也有很多戏班和戏曲从业者的存在。据乾隆三十五年《潞安府志》记载:“沈宣王朱恬烄,好歌舞,工文辞,审音律。”其后来子孙亦大抵如此。清初,社会动乱,大批王宫艺人流落民间,为上党梆子在民间的绽放提供了充分的人才条件。
其次,明清时期上党梆子的形成与当时这里独特的民间音乐艺术也颇有渊源。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上党八音会。上党八音会是一种民间音乐组织,在上党一带十分普遍。虽然它的历史已经无从查考,但它在明清时期十分盛行是毋庸置疑的。至今长子县西南呈村仍然保留有一座清初创建的制造铜制打击乐器的作坊。作坊的创建是为了满足上党八音会对乐器的需求,同时也证明了上党八音会在明清时期的繁盛。
上党八音会因其使用的“笙、箫、锣、鼓、管、笛、旋、钹”8种乐器而得名,而上党梆子使用的乐器竟然和它完全相同。不仅如此,明清时期上党梆子的许多曲牌和剧目也和上党八音会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如“一马三箭”“小桃红”“石榴花”“当当鼓”和“大十番”等曲牌,二者都完全一致[2]。这就不能不说上党梆子与上党八音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关系了。
实际上,不少上党梆子业余自乐班就是从八音会起家的,也有一些上党梆子职业班社就是由自乐班发展而成的。从这个“八音会—自乐班—职业班社”的发展,也可以窥见上党梆子形成的一些线索来。
除了上党八音会以外,明清时期流行于上党地区的民间武术“古传太极”,也对上党梆子的舞台动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上党梆子的基本功“三把”,讲究“上练一口气,下练三步走”,其行进、打斗、站立等动作都有“古传太极”的影子[2]。还有上党地区繁盛的民间祭祀和迎神纳福活动,也为明清时期上党梆子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自古以来,上党地区人民的信仰就十分复杂,既有道教、佛教等主流宗教信仰,也有遍布各村、各镇的神鬼信仰(如壶关县百尺镇的狐仙奶奶、集店乡的唐王庙等)。因此,祭祀活动也十分频繁。而且,只要举行大的祭祀活动,就一定会有歌舞演出。自明清之际上党梆子逐渐形成以来,它更是成为祭祀歌舞的主流。
总之,上党梆子在明清之际能够形成,无不得益于上党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当地独特的艺术生存环境。当然,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的倡导,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性地影响了上党梆子的产生和发展进程。而明清时期的这些民间音乐和曲艺以及繁盛的祭祀活动,给上党梆子提供了生长的土壤,使它从无到有,不断壮大。
1.1.2 明清时期上党梆子形成与发展的表现
上党梆子在明末清初开始形成。大约在明代前期,山陕豫三角地带形成了原始状态的梆子腔,然后向外传播。上党梆子是它东行后,在此地吸收营养逐渐壮大的。这个过程中,乐户演出的队戏、院本,起到过巨大作用。而“昆、罗、卷、黄”四种唱腔也被它学习、吸收并包罗起来,同时也受到了弋阳腔的滋润,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上党梆子中,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上党昆曲。阳城县上伏村大王庙戏台上有顺治十五年万顺班演出《春灯谜》《恩荣第》《双包记》等的题壁[4],其剧目均为昆曲。而且,昆曲在上党梆子“昆、梆、罗、卷、黄”这五种唱腔中排在首位,说明昆曲对上党梆子的影响也可能是最早的。
清初,弋阳腔(又叫弋阳梆子,最早产生于陕西,是秦腔的一种)对上党梆子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雍正版的《泽州府志》和嘉庆版的《沁水县志》中都有“台上弋阳唱晚晴”的记载。这就表明当时上党地区有了弋阳腔的演唱,而上党梆子中的生、旦、花脸等行当的划分也与弋阳腔一般无二。也就是说,上党梆子一定受到过弋阳腔的影响。
上党罗戏和卷戏原本是独立的戏种,但是由于时代变迁已经失传了。现在人们只能从当时的一些记载中看到它曾经活动的痕迹。据清人李绿园所作的小说《歧路灯》记载,在乾隆年间,就已经有山西泽州的罗戏在河南开封城内演出。在今天的长治市武乡县就有乾隆四十二年的卷戏题壁记载,所记剧目为《顶灯》。罗戏和卷戏在上党地区的发展也被上党梆子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
明末清初是上党梆子产生和发展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其主要内容以梆子戏为主,兼有昆曲、罗戏、卷戏等剧目。如梆子戏中经常上演的杨家将戏《天波楼》《雁门关》和岳家将戏《渡康王》《巧缘案》,卷戏中的《卖荷包》《打刀记》,昆曲中的《长生殿》《赤壁游》,罗戏中的《打铁》等[5]。其作品丰富多彩,兼容并包,受到了当地居民的热爱。许多明清时期上党梆子的古老剧目现在仍然在民间不断上演。
由于上党梆子从明末到清嘉庆年间的不断发展,演出也随之而增多。许多上党梆子剧团也在演出期间留下了不少的舞台题壁,这些题壁有的是记载演出盛况,有的记载演出内容,更有甚者,则记载了剧团对东道主的不满等,不一而足。
明代的舞台题壁只有一条,该题壁记载了一个班名叫明史班的戏班,但年代不详,剧目不清,所以无从分析[2]。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上党梆子起码在明末清初时就已经初具规模并且已经可以参加演出了。
现存乾隆年间(1736—1795)的题壁共30条,其中11条看不清剧目,另19条有89个剧目。在这些剧目中,《长坂坡》《请诸葛》《金狮坠》《千里驹》《教子》《虎西门》是上党梆子剧目,其中《金狮坠》在“文革”以后还有剧团演出。《封相》《林童会》(应作临潼会)《春灯谜》《蝴蝶梦》为昆曲,《庆顶珠》《回龙阁》《去西川》《空城计》《战长沙》为皮黄,《顶灯》是卷戏[2],说明此时上党梆子已是“昆、梆、罗、卷、黄”同台演出了。
对诸多戏曲流派的吸收和继承以及众多的舞台题壁都表明,上党梆子在明末至嘉庆以前就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了,许多剧目也在这一时期形成。
1.2 清中叶以来上党梆子的发育与壮大
嘉庆到道光年间(1795—1895),是上党梆子发育和壮大的时期,嘉庆王朝是清代从康乾盛世到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道光年间清王朝的统治继续走向衰落,内忧外患日益显露。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上党梆子却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且不断孕育壮大。
1.2.1 清中叶上党梆子发育壮大的条件
上党梆子的孕育与壮大在19世纪前后,相当于清代的嘉庆、道光年间。这一时期,陕西、四川、湖北一带发生了白莲教起义,这三省的农民斗争十分激烈,使得曾经一度是梆子戏发源地的陕西遭遇动乱,当地的戏曲活动,自然也受到了很大影响。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秦腔(弋阳腔)戏曲演员纷纷往外迁移,寻找新的生存环境,其中有一部分演员就云集上党,使得上党剧坛出现了一个新的繁荣局面。
据清嘉庆十九年长子县岚水乡宣家坪村舞台上的题壁记载,当时有上党梆子《双锁山》,上党皮黄《白玉带》上演,这与传统秦腔名剧《双锁山》《血诏带》十分相似,而嘉庆二十四年泽州县青莲寺中佛殿题壁有四美班《荐葛》、嘉庆年间泽州县川底乡半坡村舞台题壁有福祥班《骂曹》等剧目记载,与秦腔剧目《荐诸葛》《徐母骂曹》也十分相似[2]。因此,这一时期上党梆子能够发育壮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秦腔的滋养。
实际上,上党梆子在嘉庆、道光年间的发育壮大,除了受到了弋阳腔(秦腔)的影响以外,也对先前所吸收的昆、罗、卷、黄做了进一步的融合,这一时期上党梆子“昆、梆、罗、卷、黄”五种唱腔要素均已具备,并且在不断继承完善。如上党昆曲的细腻、上党皮黄的音乐、罗戏与卷戏的动作等,在上党梆子中都已经表现得十分融洽[2]。
1.2.2 清中叶上党梆子发育壮大的表现
在嘉庆、道光年间,上党梆子发育和壮大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大量优秀戏班和演员的出现,另一个就是大量舞台题壁对这一时期上党梆子演出活动的记载。
在嘉庆、道光年间,上党梆子著名的艺人有连小河、冯春木等人。连小河,道光年间年著名上党梆子演员,上党沁水人,自幼学戏,祖父、父亲也都从事梨园事业。因其父悉心教导,自己又十分下功夫,所以艺术造诣颇深,曾在当地留下“三天演了三班戏,班班都要连小河”的故事。冯春木也是道光年间上党梆子的著名演员,据说他当时扮演的《夺秋魁》的梁王柴桂,《送印杀差》的马强,《四明山》的李元霸,《血诏带》的曹操,《金亭关》的史大奈,《齐鲁界》的齐襄公等,驰誉路府各地,一时之间无人能与之抗衡。在一大批优秀艺人涌现的同时,上党梆子最著名的戏班之一,壶关乐意班(又称十万班)也在此时成立。
除了许多著名演员和班社以外,至今上党地区还保留了不少嘉庆、道光年间上党梆子演出的舞台题壁。其中嘉庆年间舞台题壁现存45条,大多记载了一些戏班名称和演出剧目。道光年间的舞台题壁有133条,演出剧目的内容也更加丰富[3]。
众多优秀的艺人,繁盛当时的戏班,以及大量的史实记载,无不印证着上党梆子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和壮大。
1.3 清中后期上党梆子的鼎盛和衰落
与所有的戏剧一样,上党梆子也扎根在了其特定的土壤上,自诞生之日起它就不断地受到当地人民群众和艺术家的滋养,在良好的政治环境、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发达的经济条件下,得以快速发展,并且很快走到了其顶峰。然而,在短暂的辉煌过后,上党梆子也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危机。清末以来政治环境逐渐动荡,经济形势急速下滑,人民流离,上党梆子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1.3.1 上党梆子走向鼎盛的条件
上党梆子的鼎盛时期是从咸丰年间开始的[6]。咸丰帝是清朝的第七位皇帝(从顺治帝开始算起),他在即位后勤于政事,锐意改革,重用汉朝大臣,使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环境总体趋于稳定。而靠近京畿之地的山西也得益于京城庇护,政治安定。这就为上党梆子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政治环境。
除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以外,上党梆子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也有着良好的经济条件。清中叶以来,晋商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商人团体,并且首创了现代银行汇兑业务的雏形——票号,史称“汇通天下”,这一度使晋商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其时不仅一大批山西商人号称“海内最富”,也使得山西成为富庶之地。清咸丰三年(1853年)山西巡抚哈芬在奏折中说:“近复细加访询,实缘晋省富饶,全资商贾。”同年,和硕惠亲王在奏折中奏道:“富庶之省,莫过广东、山西为最。”[1]由此可见当时山西具有所有艺术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环境,上党梆子也不外于此。
到了同光年间,中国北方的戏剧整体得到了大的发展,各类戏曲名伶辈出,而因北京银号皆山西帮,喜听秦腔(山西梆子戏的雅称),故梆子班亦极一时之盛,其中,义顺和、保胜和两班最为著名。至此,包括上党梆子在内的梆子戏,也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了。
1.3.2 清中叶上党梆子走向鼎盛的表现
上党梆子在鼎盛时期的舞台碑刻等多达689条,是整个上党梆子现存碑刻、题壁最多的一个时期。虽然这一数据有许多已经模糊不清,但是从这一时期庞大的遗迹数量中,也能窥见其繁荣的景象。
据光绪辛巳年续编的《壶关县继志》(上卷)《艺文志》记载:“上党梆子所聚梨园为一州之首”,表明上党梆子在当时已经十分兴盛。当时壶关的乐意班(十万班)、长子的南陈村乐意班、晋城的复盛班、陵川的庆云班、沁县的万盛班、长治的公义班、晋城的公顺班(尹寨二班)、大阳三义班等,都曾经显赫一时。其中,壶关县河口村的乐意班(十万班)更是声名远播,曾到山东、河南等地演出,据说还到过北京。屯留小乐意班、黎城发义班、潞城三乐班等争芳斗艳,引人瞩目。上党梆子的一代宗师,人称“戏王”的赵清海,就在此时活跃于上党剧坛。在他的前后还有申灰驴、李大友、赵朝阳(朝阳旦)、郎小喜、段二森、郎不香、郎发香、马高升、郭圭圭、张长锦、王富喜、廉明昌、郑根成等名角,犹如繁星满天,光辉交映。
在这一时期上党剧坛基本是上党梆子一统天下(几个秧歌和刚诞生的上党落子无力与它抗衡)。晋南的安泽和河南的涉县(今属河北)都有上党梆子职业班社(已知安泽有和成班,涉县有天益班)。区内也有些班社到晋南、吕梁和豫北、鲁西南、鲁西北演出(现在晋南的蒲县,吕梁的临县,山东的聊城,都发现有上党梆子班社演出的题壁),这表明上党梆子的发展已经极其辉煌。
1.3.3 清末上党梆子的衰落
上党梆子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又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及其周围省份发生丁戊奇荒,受灾人口达1亿人,1000万人口被饿死。上党梆子的许多剧团被迫解散和迁出。尽管还有少数职业班社做些断断续续的演出,也因戏价太低(甚至只给吃喝),难以糊口,处境艰难,而业余的自乐班几乎全部停止了活动。
除了灾荒对上党梆子的影响以外,当时山西的经济尤其是晋商也受到了一定的打击。清末,临近上党地区的河南一带爆发了捻军起义,造成了北方地区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晋商的商业贸易受到了很大威胁,有许多晋商纷纷破产,导致支持上党梆子发展的一大经济支柱倒塌,最终使得上党梆子日益没落。
天灾,人祸,经济破产,政局动荡,社会环境的不稳定,等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使上党梆子乃至整个山西的戏曲艺术的生存环境都变得十分恶劣,在辉煌之后,逐步走向衰落。
2 上党梆子的社会功效
2.1 上党梆子与明清时期的地方经济
在前文中讲到,上党梆子的诞生在很大的一方面是因为得到了山西商人的支持和追捧。但是上党梆子作为一种文化艺术,它与它所依赖的社会经济条件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山西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群体的崛起,为明清时期上党梆子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条件;反之,上党梆子的兴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山西商品市场的繁荣。
善于经营的山西商人不仅把上党梆子作为一种简单的娱乐和消遣方式,而且还开发了它的商业用途,把它作为一种开辟市场、繁荣贸易的手段。因此在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地的广大城乡,节日祭祀,酬神唱戏常和商品交易同时举行。
在明清时期,位于太原府南郊的晋祠,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节日和祭祀活动50余个。其中,较为盛大的节日和祭祀活动都要唱戏,非三五日而不绝。每当有这种盛大的节日祭祀和戏曲演出时,四方商贾也纷纷闻讯云集于此,以借机出售货物,发展贸易。
据刘大鹏的《晋祠志》记载:“(五月)十八日士人致祭关圣帝君于晋祠北门之关帝庙,演剧赛会凡三日,售货物农具为最。”又有《浮山县志》论载:“唯每岁三月二十八日,东门外东岳庙会……演剧凡三日,开市贸易,招集远近商贾,诸般货物,邑人称便焉。”[7]这些酬神活动所聘请的戏班大多数都是山西四大梆子戏戏班,而上党梆子戏班也赫然在列。
至今,上党地区仍然保留着许多酬神唱戏与商业贸易并存的传统。在今天的长治市区,每年农历四月十五都有大型的城隍庙庙会,为期三天,以供人们祭祀和交易。据说这一活动从万历年间就已经开始,现在仍可以看到上党梆子戏与当时的地方经济尤其是城乡贸易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它给许多小商人和农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易平台,并且保持至今。
正如《汤阴县志》所称:“有会必有戏,非戏则会不闹,不闹则趋之者寡,而贸易亦因之而少甚矣。戏固不可少也。”那么,既然有戏曲演出,那么演出的费用从哪里来呢?其来源大致也有3种,第一种就是官府把所收取的车马牛税,拿出一部分来作为演出活动的经费。第二种就是把当地出租给商户时所收取的场地费,捐出一些来支持演出活动。第三种就是商户经营收入的一些银钱。因此,戏曲演出活动一直有充足的经济支持,因为官府、商人、百姓都在这种盛会中得到了好处,所以人们也往往乐此不疲。特别是对商贾来说,在这种场合的销售额和成交额要高于平时的许多倍,所以每遇这样的盛会,他们总要预先准备充足的货源,从百里之外赶来贸易。这也说明梆子戏与当地经济发展的一种密切联系。
2.2 上党梆子与明清时期的社会政治
上党梆子在明清时期与社会政治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民群众对现实社会政治中公正、正义的诉求和对腐朽统治的批判,另一个是清中叶以来统治阶级对于戏曲内容的改造和利用。
首先,在明末清初,上党梆子中出现了一大批反映封建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剧目。其内容大多用农民和下层知识分子的眼光审视历史,批判奸臣昏君,表现农民起义,歌颂叛逆者的形象[5],反映了下层人民对公平正义的诉求。上党梆子形成于明末清初。然而,自明崇祯以来,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农民起义,外有后金军在辽东的步步紧逼。内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外部民族矛盾也岌岌可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清初,汉族人民反抗异族统治的斗争被清王朝血腥镇压,在清王朝的残酷统治下,他们虽然不敢直接演出明末的农民起义和汉族人民反抗清王朝统治的斗争剧目,但他们从三弦书、鼓书、评书等民间说唱文学中选取素材,创作了《庆顶珠》《打龙袍》和诸多杨家将、岳家军等优秀的上党梆子剧目,这些剧目在不同程度上都反映了人民对封建黑暗统治的反抗和对抵御外来侵略势力的颂扬。
其次,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上党梆子的利用。在嘉庆、道光、咸丰时期,上党梆子得以飞速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统治者的推崇有关。自嘉庆以来,上党梆子出现了许多宣扬忠君、爱国的剧目。如《忠孝节》中佘太君尽忠斩子,《双龙会》中杨家将七郎八虎闯幽州、代君赴宴、尽忠而死等。这些剧目的演出,事实上是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的。
总之,不管是反映人民大众的政治愿望,还是对于封建统治的有利维护,上党梆子在明清时期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3 上党梆子与明清时期的思想文化
上党梆子作为一种戏曲文化,有着自身独特而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在明清时期,它不仅是上党地区人民主要的生活娱乐方式,而且对于上党地区人民性格的塑造、思想的教导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明清时期上党梆子中,有许多杨家将的戏和岳家军的戏。如《天门阵》中,穆桂英奋力拼杀,往来冲锋,彰显了巾帼英雄的豪迈气概;《风波亭》里,岳家军将士虽死无惧的忠义,等等,他们无不指引着上党人民的忠义、仁勇。而《打渔杀家》中渔民们反抗乡宦强权、《打龙袍》中正直的大臣为正义反抗皇权等内容,也充分塑造了上党人民勇于反抗的精神,并将这种精神发扬光大,传承至今。《佳妻》《双凤缘》中情感的细腻与真挚,也对上党人民的情感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实,纵观整个中国戏曲发展史,戏曲的主要作用是审美、娱乐。但不可否认的是,戏曲对于人民情操的陶冶、精神文化的丰富以及普遍道德的培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孙玫先生在《中国戏曲跨文化研究》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就中国传统戏曲而言,在传统社会里很早就有文人把儒家以文载道的传统引进戏曲,借高台以施教化。”[8]戏曲文化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有着极大的影响。上党梆子也不外乎于此,它塑造了上党地区人民勇毅、豁达、细腻的性情。
明清时期的上党梆子除了有着重要的道德教化作用外,还有着丰富多彩的艺术特色,是中国乃至世界舞台艺术的瑰宝之一,丰富了中国和世界文化与艺术的多样性。而且,许多戏剧如“枣梆”等,也是由光绪年间的上党梆子外传发展而来的。
总之,明清时期形成和发展的上党梆子,极大地丰富了上党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塑造了上党人民独特的人格魅力,是上党人民需要守护的艺术珍宝。
3 结束语
上党梆子在今天的晋东南和豫西北地区仍然十分活跃,是这些地区的主要戏剧之一。一般民间的商业集会和农历的重要节日,上党梆子戏班仍会被邀请演出,以增加集会的人气和表现节日的热闹。这些都得益于其历史的深远和当地民间文化的滋养,得益于其兼容并蓄的精神内涵。实际上,上党梆子的发展还对其他戏曲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山东的“枣梆”及河北的“西调”,就是其中的分支。
总之,上党梆子属于地方性传统戏剧,它不仅是山西四大梆子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古典戏曲系列的一个分支,从明末清初起到现在已经有400余年的历史。它经历了初创时期兼容并蓄般的发展,清代嘉庆、道光、咸丰时期的鼎盛以及清末以后的衰落,其历史进程绵长悠远,历史内涵浓郁厚重,对于上党地区民俗文化的丰富,以及人们精神生活的满足,都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