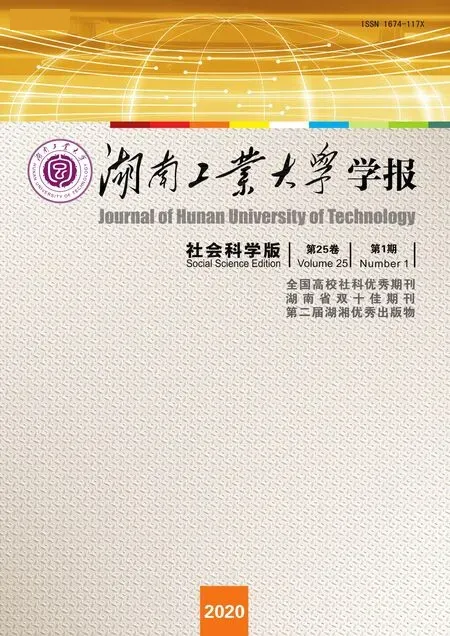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野下霍桑小说探析
吴伟萍
(闽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纳 撒 尼 尔 ·霍 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是美国19 世纪影响最大的浪漫主义小说家,其作品标志着美国文学的成熟,被公认为是19世纪美国最灿烂的文化遗产。霍桑毕其一生创作了许多传世佳作。他出版了4部长篇小说,包括《红字》 (Scarlet Letter,1850)、《福谷传奇》(The Blithedale Romance,1852)、《玉石雕像》(The Marble Faun,1860)、《带有七个尖角的房子》(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1851) 等,其中《红字》已成为世界文学经典;其100多篇短篇小说,主要收入到《故事重述》(Twice-Told Tales,1837,1842)、《古宅青苔》(Mosses From an Old Manse,1846)、《雪影》(The Snow-Image,and Other Twice-Told Tales, 1851)等小说集中; 2部童话集,包括《奇妙故事》(A Wonder-Book for Girls and Boys,1852)和《乱树丛故事》(Tanglewood Tales,1853),这两部童话已成为美国儿童文学的经典。此外,他还出版了大量散文、随笔、游记、传记等作品。霍桑作品大多以新英格兰为背景,反映了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社会风貌,在当时就已经享有很高的声誉。霍桑作品受到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 爱 伦· 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麦尔维尔等文学大师的好评,他们也都深受其作品的影响。兰德尔·斯图尔特(Randall Stuart)是霍桑的传记作家,他这样评价:“总的看来,霍桑作品探究了人类心灵深处的真实状况。他所表达的思想是最高意义上对生活的思考和对未来岁月的预测,具有一定的永恒性。”[1]250
“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在发展的进程中会形成一种被共同接受和认可的伦理秩序,在伦理秩序的基础上又形成了维护这种秩序的各种道德准则和规范。”[2]文学的本质为伦理,即文学创作的推动力源于人类表达伦理的需要以及对于共享道德经验的渴望。“文学的任务就是描写这种伦理秩序的变化及其变化所引起的道德问题和导致的结果,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提供经验和教诲。”[3]17在具体的文学文本中,伦理主要是指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中所形成的被社会普遍认可和接受的伦理道德准则和规范。人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社会环境中,就必然要受到伦理道德的约束,否则就会侵犯或损害他人的利益及群体的共同利益。从本质上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目的是阐释文学文本的伦理道德特性,从伦理道德的视角对文学文本中所描写的社会现象进行解读并作出价值判断。
霍桑小说反映了人类心灵的真实状况,带有强烈的伦理道德的批判性,极具个人风格。国外学界对霍桑小说的研究多集中在主题内容、结构布局、创作艺术、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方面,国内学界对霍桑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艺术特色、女权主义、原型、超验哲学、文化、生态批评、符号学等方面。由此可见,国内外研究很少涉及霍桑小说中的伦理维度。伦理维度是文学研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维度,从伦理维度研究霍桑小说无疑能提供一种新的观照视野,借以重新审视霍桑的社会责任感和伦理意识。尽管霍桑小说没有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但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等伦理关系在其小说中都得到了深刻的反映和阐发。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来看,霍桑小说实则是对那个时代伦理道德的记述。他不仅客观地反映出整个时代人们的道德风貌,而且对其进行分析,找出导致伦理混乱的原因,并以严肃、慎重的态度试图为面临伦理困境的人们找到救赎之道,以供世人借鉴。在他笔下,恶的就是要鞭挞的,善的必定是遵守伦理的,善恶与伦理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小说旨归是探索人性之奥秘,并在探索人性之时呈现出悲悯的伦理基调,这也就是霍桑小说的伦理内涵。因此,运用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探讨霍桑小说是可行的,其能为研究霍桑小说提供一种新视角。
一 对恶的深层探索
作为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霍桑作品对人类心灵真实境况的关注程度是衡量和评价他的一个尺度。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1930)认为:“霍桑的作品把人类灵魂深处的罪过揭示得一清二楚。”[4]加尔文教气氛浓重的清教徒家庭、社会环境和时代思潮使得霍桑成为了一位思想极为复杂而矛盾的作家。批判人性的阴暗面和社会现实是霍桑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霍桑的作品仿佛要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其作品思想深刻、独树一帜,既有历史的深度,又富有现实的意义,呈现出独具的思想魅力。
小说《红字》是一部以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也是霍桑的传世杰作。小说以当时严酷的清教视为罪不可赦的一桩“通奸罪”(adultry)为核心展开情节,展现了与这桩“罪行”有关人物的精神世界,层层深入地探究了有关罪恶和人性的道德问题。小说第一章《狱门》开篇写道:“新殖民地的开拓者们,不管起初对人类品德和幸福有着怎样的理解,总忘不了要在草丛中划出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修建墓地,再划出另一片修建牢房,这是当时人们最基本的需要之一。”[5]1在此,霍桑表达了对人性最为基本的态度,即罪恶是绝对存在的,人性的阴暗面是人类固有的缺陷,只不过其表现形式各异。小说中,牧师丁梅斯代尔(Arthur Dimsdale)是一位狂热的宗教活动家,他毕业于英国著名大学,力图把自己的学识带到北美的蛮荒地区,以启蒙殖民地的教民。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牧师的丁梅斯代尔竟失去了理性,直接违背清教教规,与同教区的海丝特(Hester Prynne)发生恋情,成了一个犯了隐藏“通奸罪”的典型。表面上,丁梅斯代尔平静阳光,定期向教民宣扬清教教义,忠心耿耿地履行着作为牧师的神圣职责,教民因而把他走过的路都视为圣洁的。然而,丁梅斯代尔内心深处却难以平静,因为被自己的隐秘罪,即象征“红字”(鲜红的A 字,adultry一词的首字母)的罪行压抑着。小说中这样描述他:“尽管他看来极其纯洁、高尚和神圣,但他从父亲或母亲身上继承了一种强烈的兽性。”[5]98显然,丁梅斯代尔经历着情感与理智矛盾的痛苦。那就是,一种力量要求他恪守清教教义与伦理道德,保持自己正被教民尊崇的牧师的荣耀,满足尊重需要;另一种力量又强烈地促使他去满足自己对爱情的需要。“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要先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寻找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用伦理的观点对事件、人物、文学问题等给以解释,并从历史的角度作出道德评价。”[3]17丁梅斯代尔隐藏的“通奸罪”已牢牢地镶嵌在当时清教教义的戒条之中。因为违背了社会伦理道德准则,最终丁梅斯代尔不堪心理重负,内心分裂,耗尽了生命,成为悲剧典型。小说中的齐灵沃斯(Roger Chillingworth)是一个集多种矛盾于一体的可悲而又可憎的人物。他选择与海丝特的结合并非为了爱情,只是为了“用来温暖自己最朴素的福分”[5]23。因而,“他与海丝特的婚姻就是错误的,不自然的嫁接,一开始就燃着红色的熊熊烈火。”[6]尽管如此,可他在婚姻上的做法却是无可非议的,符合伦理道德规范。当齐灵沃斯远离海丝特两年之后,当他回来时不经意地看到妻子作为通奸罪的典型站在受刑台上,被教民围观、辱骂和攻击,这一幕严重伤害了他的自尊与情感。“他不愿意蒙受一个不忠实的女人给丈夫带来的耻辱。”[5]32他无疑也是一位受害者,因而获得了人们的同情。如果齐灵沃斯公开地将事情上诉法律去做裁决会损害他的自尊与名誉,那么他是否有权力采取自己的方式进行复仇呢?在《爱之艺术》(The Art of Loving,1956)一书中,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认为:“人身上存在着一种天生的欲望,就是希望了解他人的秘密。如果探求秘密的方式走入极端便成了施虐狂,即折磨对方,强迫他在痛苦中泄露自己的隐私。这种对他人秘密的探求,隐含着暴虐与破坏的深层动机。”[7]齐灵沃斯的生活原本似乎受着理性、严格的道德信仰所支配。他这样说过:“我努力地增长自己的学识,忠实地用于增进人类的福祉,我原本的生活是由诚挚和宁静的岁月构成的。”[5]122然而,此时的他从本我的原则出发,其结果是,仇恨使一个皓首穷经、温文尔雅的学者在复仇心理的驱动下完全丧失了人性。他威胁妻子海丝特的同时,还以医生的名义去探索丁梅斯代尔内心的秘密。他充分地利用现有的一切规则和手段,巧妙地躲避他人的指责,让一切的“错”看起来都理所当然。最终,“齐灵沃斯凭借自己的智慧将自己变成了魔鬼”[5]201。“满不在乎地亵渎了人类心灵的尊严”[5]202。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Soren Kierkegaard,1813—1855)说:“理性的人则是现实的,对世界充满承担和责任,清楚明白人世间的伦理道德规范。”[8]75因此,有别于感性的人,理性的人知道这世界处处设限,充满着不可能。面对不可能,理性的人只有放弃。齐灵沃斯则忘掉了自身的理性,以恶还恶,实施对他人灵魂的窥探和考察,把人性之恶(主要是仇怨)融入自己的生命。当他对牧师丁梅斯代尔满是罪孽与虚伪的心灵进行揭露时,牧师丁梅斯代尔对他的睿智不寒而栗。当丁梅斯代尔不堪精神的煎熬和折磨死去之后,“奇灵沃斯身上全部的活力与智力,似乎立刻丧失殆尽,生命之树很快便枯萎死亡。”[5]234齐灵沃斯与霍桑所指向的 “人类灵魂的破坏者”如出一辙。小说的结局说明了一个事实:任何人都不能超越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秩序与规范;一旦有人向这种秩序与规范挑战,必然不会有美好的结局。
小说《福谷传奇》讲述了1841年以乔治·李普雷为首的一群知识分子试图创建乌托邦实验基地——布鲁克农庄(Brook Farm)的故事。霍桑创作这部小说时,美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人们的观念和思想发生着急剧的转变。小说中,面对新生的社会制度以及传统的田园生活,人们面临着一系列的矛盾与抉择,小说呈现了霍桑对人性善恶和社会现实的理性反思。小说中,霍林华斯(Hollingsworth)以慈善家自居,认为福谷的制度不合理,需要一定程度上的改革。他一开始就抱着改造人心的崇高理想来到福谷,甚至把福谷所有人都看作需要改造的对象。他凌驾于他人之上,凭借福谷改革事业的领导人身份威胁科尔服从自己的权威。他说:“如果你不和我一起向伟大的目标奋进,又如何能够成为我的终生朋友呢?”[9]212霍林华斯以改革为借口对他人进行控制的欲望表现得非常强烈。诗人科弗代尔(Miles Coverdale)评价:“霍林华斯难以付出感情去真诚对待一个有自己独立观点的人,只是对那些专注于他的人感兴趣。”[9]318霍林华斯以福谷的名义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把别人当作满足自己虚荣心的工具。齐诺比娅(Zenobia)是一位具有独立思想的坚定的改革者和女权主义者。对于霍林华斯,她愤怒说到:“全是自私! 再无其他,什么也没有,只有自我!自我!自我!”[9]337在她眼中,改革家霍林华斯外表之下只有自私和冷酷。科弗代尔不愿顺从霍林华斯,霍林华斯便无情地抛弃了他。霍林华斯罪孽的最主要、最黑暗之处则是扼杀了他自己内在的良知,使得原本伟大的福谷事业被毁掉了。科弗代尔是一位羸弱敏感但又深沉的文人,寻求兄弟姐妹间的真正的平等互爱是他参加福谷事业的初衷。可是他的初衷并没有能够实现,原因是他人格上的阴暗面占据了主导地位。他多半是出于哲理方面的好奇心理去观察周围的人,他认为自己的心理状态会毁了自己和伤害到福谷中所有的人;因而,他这样说:“我探究过霍林斯沃斯,深感有负于他。介于本能和理智探究人们的七情六欲,不是一种健康人的智力活动,它渐渐地使我的心都丧失了人性。”[9]132科弗代尔原本决定“用道德、智慧和同情的方法去改造那些恶人”[9]98,但他的“慈善”召来的只是冰冷的魔鬼,他的内心也失去了全部温暖,“他像所有雄心勃勃的人那样不可避免地最终变成了契约奴”[9]332。在小说《地球的大燔祭》(The Earth’s Holocaust,1844)中,霍桑写道:“人的心眼儿只有中等大小,怀抱着自私的目的去度量他人的心,甚至不惜一切手段去与之争夺。既不能达到改造他人的目的,自己还可能被这种‘恶’纠缠得不能脱身。”[10]
“天堂大门的侧边有一条通往地狱的路。”[9]278福谷事业失败的终极原因是权力的诱惑和野心的驱使导致人心异化。人们对心灵堕落的忽略才是对社会进步最致命的打击。霍林华斯和科弗代尔本来身怀神圣的使命却最终沦为“自私、贪鄙、伪善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9]163,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之恶夹杂着使人向善的光环,从而让人忽略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小说呈现了人道主义理想与人心之恶之间的不可调和。美国著名思想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曾经说过:“当一个人不完善自己,人性中的虚假和伪善便会带来令人厌恶的结果。”[11]小说中,慈善家改革热情的背后暴露了人性缺陷和道德危机,霍桑所要表达的也就是这样的一种忧虑。缺乏善的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责任担当意识,这些原因直接导致了“未来社会美好蓝图”的福谷事业的最终解体。
小说《七个尖角阁的房子》讲述了平钦和莫尔两大家族几代人的恩怨纠结故事。在序言中,霍桑就表达了小说的道德主旨。他这样说:“上代人的罪行会延续到后代,这种罪行会成为难以驾驭的真正的危害。”[12]6平钦家族罪行的延续,给他人和社会带来的危害是极其巨大的。平钦家族的老一辈玩弄权术,以卑鄙手段抢夺了原始居民莫尔家族的土地,建造了一栋带有七个尖角阁的豪华宅邸,从此,平钦家族的后代在这掠夺而来的土地上绵延了下来。平钦上校(Colonel Pyncheon)身上的品性与清教社会那些贪婪与反叛人物的形象有着诸多的相似,他代表了平钦家族老一代。为了夺取马修·莫尔(Matthew Maule)的祖产,他恶毒策划了“行巫术”的罪名,把它强加在马修头上。结果,马修在“清巫事件”中被处以绞刑,这就使得莫尔家族与平钦家族从此结下仇恨。马修被处死之前给平钦家族下了咒语:“男性族长将死于非命(God hath given him blood to drink!)。”[12]27这个咒语很快就应验了。平钦上校突然死于那个带七角阁的房子落成的当天,使用阴谋手段夺来的财产也埋葬了他。然而,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平钦上校所犯下的罪恶又绵延到子孙。到了平钦法官(Judge Jaffrey)这一代,他利用诬告手段将堂弟克利福德(Clifford)送入监狱,使之在监狱度过了30年,这几乎毁掉了克利福德的一生。他还变本加厉,企图逼迫海孜巴(Hepzibah)交出房子和财产。平钦法官继承了平钦家族的贪婪品性与世袭的罪恶,其罪恶与平钦上校的罪恶几乎如出一辙。“灾祸与过失均是由于自己内在的欲望, 不断地索取、不断地追逐所导致,因此老子告诫我们要学会知足。因为‘祸莫大于不知足, 咎莫大于欲得’。”[13]对于平钦家族的人犯下的罪恶,霍桑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说:“一个人干尽了坏事,他将积累了一大堆邪恶,那像花岗岩一样坚硬的邪恶会重重地压在他的灵魂上,直到永远。”[12]209
对于当时科学快速发展的现象,霍桑并非持盲目乐观的态度。他发现,人们对科学知识的盲目追求往往导致忘记自己追求的最终目的,欲望会引领人性走向道德的沦丧。霍桑短篇小说聚焦了一些具备一定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所犯的利己主义罪恶,霍桑将之定义为 “理智之罪”。在其小说《伊桑·布兰德》(Ethan Brand,1850)中,霍桑这样解释“理智之罪”:“它凌驾于人类的最基本的情感之上,凌驾于对上帝的敬重之上,为满足其强烈的目的甚至不惜牺牲一切。”[10]67小说《拉帕西尼的女儿》(Rappaccini’s Daughter)中,拉帕西尼医生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工作者,他既是植物学家,又是生理学家,他对科学的态度是严谨的、一丝不苟的;然而,“他对科学比对人类更关心,他对病人的兴趣仅仅在于他们是某种新试验的对象”[10]143。拉帕西尼为了自以为的科学利益,为了实现获得一种新药的目标,为了确定有毒植物对人体的影响,他不惜将女儿贝阿特丽丝(Beatrice)作为实验品,并最终夺走了女儿的生命。他的对手巴格利欧尼教授(Prof. Baglioni)这样评价他,“他是一个纯正的科学家! 好像是把自己的心都在蒸馏器里提炼过了。”[10]207拉帕西尼因为对科学的极端狂热而完全忽视了道德良知,科学在他手中衍变为残害人性的工具。按照霍桑在小说《伊桑·布兰德》中的描述:“那个时代是智力超前而道德滞后。”[10]89在短篇小说《胎记》(The Birthmark)中,霍桑更为深入地探讨了知识分子的“理智之罪”。科学家艾尔默(Aylmer)无法容忍妻子乔治安娜 (Georgiana)脸上长了个胎记,他试图发明药物消除它。虽然“胎记是上帝印在人身上致命的瑕疵,是与生俱来的,也是难以消除的”[10]257,但不管如何,艾尔默“相信科学可以提供无穷无尽的可能,也自信科学家可以一步步掌握知识,产生强大的创造力去解开事物的秘密”[10]327。艾尔默经过不懈的研究,终于研究出一种药液。乔治安娜喝下药液之后,胎记倒是消褪了,但“那致命的胎记已牢牢揪住了生命的奥秘”[10]358,乔治安娜的生命也随着胎记的消失而消逝了。艾尔默以崇高的科学事业掩盖其狂妄的利己之心蕴含了个人伦理道德的沦丧。通过叙述“理智之罪”引发的悲剧,霍桑表现了因对科学知识的狂热追求而导致人性恶肆意蔓延现象的担忧。
普遍性是伦理的基本特征,普遍性的事物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作为活生生的个人,具有感知和直觉的能力,然而这种能力却是隐蔽的;因而,具有普遍性的伦理需要个人敞开自我。因此,“在伦理的世俗化和社会化过程中,个人就得消解自己的内在性,去适应外在的普遍性并表达自我,从一个具体的人转变为一个具有普遍性本质的人。每一个具体的个人都需要在普遍性这个范畴中找到自身的据点,遵守伦理的规范和准则,从而可以获得来自彼此的理解。”[8]57在人与人及社会的伦理关系上,霍桑一生都没有接受超验论者所倡导的个人主义思想以及个人利益高于他人和社会的理念。那些追求自我利益和主观道德的个人主义者脱离了他人及社会的理解,表现为一种“利己主义”之恶,其不会被他人及社会所接受。一切个人理想都应该建立在对人类基本关系有利的基础之上。霍桑认为,无论个人的理想有多么远大和崇高,但如果它损害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正常伦理状况,那么,它本质上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恶。
二 对伦理道德困境的审视与思考
霍桑小说阴郁的氛围中潜藏着一双洞察世事的慧眼。霍桑既是一位伟大的局外人,又是一个超越时代的深刻的观察者。詹姆斯(Henry Jame,1843—1916)这样评价:“霍桑作品观照了人类的灵魂与良知,力图探索人类内心深处全部深层奥秘。”[14]霍桑作品深刻揭示了人性中阴暗的一面。人性的阴暗面和人性的缺陷保持着某种联系,也与人的生命与活力保持着某种联系,对此,霍桑通过其作品进行了揭示。同时,霍桑仍不忘肯定与彰显人性中善的光辉和道德的力量。那就是,人应该真诚地袒露自己的罪恶,这样才有希望获得罪的赦免,回归伦理之道。他认为,应该以善行去洗刷罪恶,以净化人心,使它向善的方向发展,从而达到消除人心的恶、实现人性的善和改良社会风气的目的,可以说,“霍桑小说善于把人的道德反省改造与对伦理的严肃性思考统一起来”[15]。霍桑小说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着力揭示人性中不可避免的某些缺陷;同时,他又不懈地寻找弥补这一人性缺陷的途径。他四部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在心灵上都经历了一次精神的洗礼和完成了一次道德的嬗变,这种安排寄予了霍桑希望人们遵循伦理道德规范和准则的理想,也是他对当时人们所面临的道德困境的审视和深刻思考的结果。霍桑曾说:“人生在世应该生活得更美好,上帝不会玩笑人生。”[1]132霍桑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神圣的信念来进行创作的。
小说《红字》中,毁坏生命的恨和促进生命生长的爱形成了人性中相互对抗的两股力量。齐灵沃斯犯了破坏人类灵魂之罪,直接导致牧师丁梅斯代尔不堪精神重负而憔悴死亡;但是,齐灵沃斯在临近生命终点时,将他的全部财产留赠给了牧师丁梅斯代尔和海丝特的女儿珠儿,齐灵沃斯人性善的一面没有完全丧失。英国著名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 )认为:“一种真正的道德应该是为了他者的道德,他者不是认识和情感的客体,不是理性算计的对手,仅仅是一个需要承担道德责任的对象。”[16]在一定程度上,齐灵沃斯没有完全失去人性中爱他人的能力,他最终的行为具有浓郁的忏悔色彩,其接近于世俗观念的道德救赎与完善。聂珍钊认为:“从伦理意义上而言,人是一种斯芬克斯因子(Sphinx Factor)的存在,由人性因子(human factor)和兽性因子(animal factor)组成,人性因子是指人类在从野蛮向文明进化过程中出现的能够促使自身进化为人的因素。人性因子可以使人产生伦理意识,实现从兽到人的转变。兽性因子是人的动物性本能,是人在进化过程中动物本能的残留,导致人在经历生物选择之后依然存在非理性因素。斯芬克斯因子是文学作品伦理表达的核心内容。”[3]17因而,人性因子是人之为人的关键因素,人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是因为作为高级因子的人性因子控制了低级因子的兽性因子。齐灵沃斯身上斯芬克斯因子的不同组合导致了他性格行为的变化。他的自尊心曾经遭受到一定程度上的伤害,因此,他的眼睛蒙上了尘埃,心灵堆满了污垢,这使他成为阴险邪恶的化身。牧师丁梅斯代尔的死亡使他的人性因子控制了兽性因子,激发了他的理性意识,他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悲剧产生了深刻的反省,这种透彻的反省使他重新成为具有伦理意识的人,从而超越了自我,实现了与他人的和谐。齐灵沃斯最终把宽容、善意和爱通过实际行动投射到自己最亲近之人身上,驱散了人性中的阴霾。最终,他在善与恶的纠葛中获得了人性的升华,实现了自身伦理道德的嬗变。
小说《七个尖角阁的房子》中,霍桑讥讽道:“这些人是那样看重外在的东西,他们玩弄权术,不惜一切手段掠夺、积累、安排财富,显示出卓越的才能。”[12]269杰弗里(Jaffrey Pinchon)为了财产而杀害了舅舅,却嫁祸于堂弟克利福德(Cliford);年轻的克利福德替杰弗里背上了罪名,在监狱里呆了30年。霍桑对克利福德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这样说:“无法捉摸的天意总是让他的日子不好过,不让他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他是那些人生一片混乱人们的例子和代表。终其一生,他都在学着如何倒霉。”[12]217海波吉巴(Hepzibah)对于弟弟克利福德遭受的迫害无能为力,甚至动摇了对上帝的信仰。她说:“上帝对个人的冤枉不加干预,也不对一个孤单灵魂的痛苦给予安慰。”[12]163父权制文化深深影响了海波吉巴,她背负着拥有古老的高贵门第的头衔,长期以来,始终秉持“贵妇观念”,过着与周围的人相隔绝的生活。然而,这种生活让她一直生活在压抑之中而无以自拔,因为,她的世界是想象的、苍白的和不安的。莫尔家族的霍尔格雷夫热情劝导她:“在以往的历史上,有绅士、淑女这样的头衔的人意味着有特权,可以获得想要的东西,令人向往。在今天,尤其在未来的社会情况下,这种头衔就不是特权,而是束缚了。”[12]231霍尔格雷夫鼓励她放下历史包袱,不要留恋依靠先辈的功绩而生活,要创造自己真正的生活。霍桑对被欺辱的“卑贱者”倾注了深切的同情,他借叙述者之口说出:“此时温暖的阳光照进了所有的窗户,伴随而来的是上帝对每个人施以特别需要的关怀和怜悯的爱。”[12]262拥有特权地位的平钦上校和平钦法官猝死在象征权力的橡木椅子里,他们手中的权力也随即一起烟消云散。人禀七情而生,欲望既能导向人性的善,也能导向人性的恶。平钦家族的前辈过着专横跋扈、贪婪、冷酷与欺诈的一生,是欲望勾引出了他们人性中的恶魔性因素,遮蔽了人性的本真,他们也因而最终葬送在人们对七角楼的诅咒里。平钦法官的财产和乡间的田地依法由海波吉巴继承,但她却放下了贵族身份,过起了平民的生活。克里福德虽然出狱后身体虚弱不堪,状态不是很好,但是变得轻松幸福多了。姐弟俩最终从祖辈利己害人的罪恶阴影中走出来,重获平衡和安宁,过上了美好的生活。霍桑的这种情节安排隐含了特定的寓意,即个人的优越力量不可以过于强大,过于膨胀的利己主义欲望是自寻烦恼,甚至会引火自焚,危及他人与社会;因而,人们应该谨慎德行,莫要为非作歹。
小说《玉石雕像》是霍桑继《福谷传奇》之后最为成熟的作品,书中掺杂着情感、悬疑与伦理等多重因素,其可谓既有伦理的厚重又有时尚的轻逸。小说的主人公是贝尼山伯爵多纳泰罗(Donatello),他的祖先是半人半神半兽的农牧神。贝尼山老城堡远离人世的喧嚣,犹如世外桃源。多纳泰罗生活在这样的城堡里塑造了自己非常突出的性格,那就是 “自由、无所畏惧、不受约束的一种自然天性”[17]7。他就像个不懂规矩的孩子仅凭感觉、冲动、本能判断为人处世。多纳泰罗对跟踪他所爱女孩米莲(Miriam)的地宫幽灵般的神秘人充满了仇恨。多纳泰罗除掉了生活中邪恶的神秘人,与此同时,他自己也犯了罪,受负罪感煎熬的多纳泰罗最终进入狱中服刑。《玉石雕像》就是一部极好的关于道德上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改造的范本。多纳泰罗真正从心底里重新认识“罪与罚”,重塑道德人格,完成了自我精神上的洗礼和道德上的救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代表作《忏悔录》中,忏悔者为寻求良心的安定平和,站在审判台前接受灵魂的审判,最后实现灵魂的救赎。忏悔意味着对生命的敬重、对道德信仰的崇敬与追求。多纳泰罗虽然犯了令自己悔恨终身的罪恶,但他对道德伦理的认识在赎罪过程中不断获得提升。聂珍钊认为:“自由意志也称为自然意志,它是构成兽性因子的核心组成部分,主要源自于人类的动物天性,主要通过各种欲望,如性欲、食欲等表现出来。”[18]出于人性中兽性因子的自由意志,多纳泰罗谋杀了邪恶幽灵般的神秘人以保护他所爱的女孩免受神秘人的跟踪,他的杀人行为完全出于一种自发性的动机;但是,不管怎样,人们必须遵守伦理规范和秩序,否则就会受到应有的惩罚。谋杀罪给多纳泰罗带来了无法消除的恶名,更是极大程度上改变了他的自由和不受约束的天性,他因此陷入忧郁和迷乱之中。他感叹到:“痛苦与罪行也同样会降临到我的头上,它无疑与我与生俱来。”[17]159“第二天早上,他的精神世界就像是经历了一场大病而崩坍了,与前一天晚上差异是如此之大。”[17]162此后,多纳泰罗做出决定,把自己囚禁在阴暗又怪诞的修行处(owl nest),修行处内部布置了具有宗教道德教喻的装饰,他要在此氛围中进行真心实意的忏悔。这一过程充满了自我折磨的色彩,其目的是以此唤醒心里的理性意志,从赎罪过程中去重新获得一种人性善的信仰。小说的结尾,霍桑为多纳泰罗留下了光明的前途,赋以他重生的希望与尊严。“虽然失去了天真,但由于对恶有所认识从而获得了人性。”[19]多纳泰罗伦理意识的觉醒是在外部伦理环境影响下由罪行引发的自我觉醒,其以忏悔的方式完成了自我人格的升华。虽然过程充满考验与痛苦,但是这一过程是多纳泰罗由不谙伦常到信奉伦理道德的嬗变之路,其意义深远。霍桑始终认为:“内在世界一旦净化,外在世界游荡的众多罪恶都会自行消失。”[20]从这个意义上讲,《玉石雕像》这部具有道德寓言性质的小说揭示出人类心灵罪恶的可怕,其希望人们能够正视人性的阴暗面,确立道德自律的信仰,以消除罪恶。小说宣示了“人性的光辉,忏悔的力量”这一永恒的主题。
只有在善与恶的人性纠葛中充分自审,才能抵达忏悔与救赎的高度;只有不断反省被各种欲望遮蔽的人性中的丑恶,才能步入到人性向善的终极轨道。通过伦理的纠葛叩问人性的复杂性,叩问何为善,何为恶,就是霍桑小说的伦理内涵。霍桑对人性的观照是悲悯的,他也是怀着这种情感去书写生活中的磨难以及人性中那庸常的罪过。因为拥有这份悲悯之心,所以霍桑在直面人们面临的伦理困境、在冷静审视与探索人性的隐秘之时,能够报以善意的理解。即使面对《玉石雕像》中多纳泰罗那样的罪过,他在愤怒之余,对主人公也是同情的、怜悯的。他的小说带有人道主义的温情与宽厚,在自己笔下那些在伦理的黑色地带徘徊的人物触犯伦理之后,霍桑愿意赋予其救赎之道。
罪恶发生的不可避免是一种人类社会的现实,它是真实存在于人类心灵之中的人性成分。人心的罪恶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道德规范在心灵上的缺失和沦丧。人类社会为了克服自身固有的缺陷,建立并逐渐完善了伦理道德的秩序与准则。霍桑小说思想内容深刻之处在于其对恶的批判与对人性善的探索二位一体的展示。他的作品试图从不同的角度,通过对人心之恶的揭示与对道德嬗变过程的书写,呈现道德自律对人自身、他人命运以及社会影响的重要性,霍桑希望从人内在的力量出发去寻求一种有效的罪恶救赎方式,去寻求解决人们所面临的道德困境的途径。伦理道德层面的“善”不可见,但它又是一种绝对而真实的存在,它代表着真理和普世精神,更是一种捍卫社会和谐的秩序与准则,人类对这种永恒的“善”的追求就是最好的信仰之一。人类对心灵之恶的修正与道德嬗变的过程是渐进式的,无法在极短的时间里得以实现。霍桑作为一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始终如一地把对人性阴暗面的批判以及对伦理道德困境的审视与思考融入的自己创作之中,其作品也因此具有极为丰富的伦理道德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