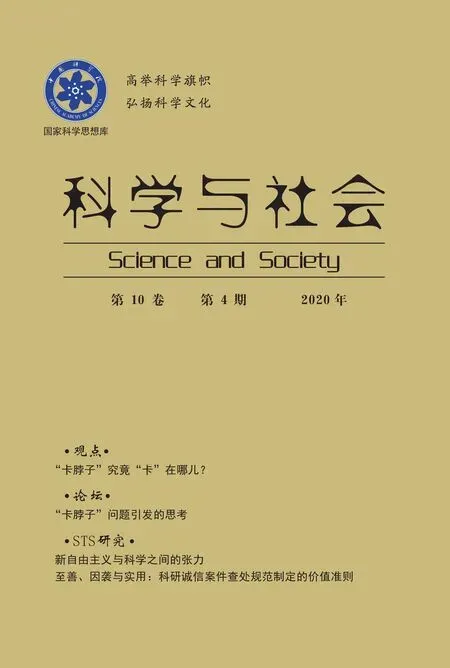论身体对于VR技术使用的特殊作用
苏 昕 汤书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唐•伊德(Don Ihde)认为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现象学忽视了技术维度,没有对技术与身体的关系展开论述。梅洛-庞蒂提到拐杖是支持引导盲人行走的工具,是盲人的知觉的延伸,所以技术是身体的延伸。伊德吸取了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的内涵,却在阐释人与技术四种关系的时候,偏向经验主义的知觉阐释,即外在物体对感官简单刺激的集合,把知觉直接当成一种已知的结论,而没有论述知觉的发生过程,以及知觉经验是如何构建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将技术的范围缩小了,侧重于可触的实在技术物。身体与技术在当下的具体技术发展情境下,到底呈现怎样一种关系?尤其在虚拟现实技术这样一种虚实结合的技术新形式下,身体对于技术具有怎样的重要地位?身体对于技术的设计过程和体验过程存在怎样的建构作用?本文从知觉现象出发,从身体维度阐述虚拟现实情境下身体与技术之间相互塑造的作用特征。
一、基于身体动觉捕捉的虚拟现实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VR)基于身体动觉(kinesthetic sense)的捕捉。技术系统契合身体运动控制机制,并且尝试建立相吻合的虚拟空间参考坐标。[1]虚拟交互是发生在虚拟空间的动态技术活动。头显里虚拟世界的呈现是以头部的运动来进行视域的拓展,所以说虚拟现实技术在动态的解构中建构。如果没有身体的运动,那么虚拟现实技术呈现的是一个静止的局域型的画面,身体与技术之间是完全割裂的,有着明显的界限,身体并不能够对技术的世界产生认知,或者对于技术中介的世界产生认知,身体与虚拟现实技术就像两个浑然不觉、擦肩而过的客体,没有交集。戴上虚拟现实头显后的一刹那,身体对于局域性的虚拟画面会产生对虚拟事物的部分认知,这也是一种短暂的交互。视觉的投射本身就是运动的一种表现,身体已经实现了运动,所以说对于身体动觉的捕捉是虚拟现实技术交互的基础条件。
1.技术微观的运动链和技术链
不同于传统的光学动作捕捉技术常有的遮挡问题,惯性动捕技术(Inertial motion capture)属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微观技术范畴,包含了惯性动捕技术,更加贴近真实身体的印射,实时完成姿态跟踪任务。人体的分层结构将身体分为不同层级,由各个关节和骨骼组成运动链。1876年,弗朗茨•勒洛(Franz Reuleaux)在《机械运动学》中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链接”概念,后来生物学等领域将其称为运动链,通常指身体运动功能导向的各个单位相互联结构成的系统。比如肩关节、肘关节、腕关节以及子骨骼组成了运动链,也即通过运动链上的关节的组合来共同完成一个动作,身体的运动通过多个分支的运动链的协调统一来完成。人体的动作是三维空间的综合运动,彼此互补,协调发力,身体的这种协调运动是通过运动链来实现的。[2]惯性动捕技术通过惯性动捕节点装置对身体关节和骨骼运动信息进行采集,将惯性传感器节点佩戴在身体运动链的相应部位。对身体运动链的信息跟踪与记录催生了技术链的构建。技术链包含身体运动的时间性以及时间域内的量变关系。一个动作节点伴随着另一个动作节点,技术对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位移的身体运动进行记录,才能构成完整的运动轨迹。这一技术链包含加速度计和角速度陀螺仪以及磁力计,对身体运动的位移、旋转角度以及运动方向进行数据采集,也就是说对身体动作的方向方位,运动的距离,是否转身以及旋转的角度进行监测。[3]惯性动捕技术链的构建使得虚拟现实技术可以为用户提供一种更自然的方式,与虚拟世界的元素进行交互。它使我们能够执行同步动作,例如在驾驶时换档,并完成更复杂的任务,或者更加精细化的动作;打开抽屉并抓住物体,手指交叉和握手,这些动作都可以在虚拟空间完成。[4]反向运动学(Inverse Kinematics)使用运动学方程式,基于末端执行器的空间位置来计算还原运动链的位置信息。[5]也就是说已知末端效应器(End Effector)的位置数据来推断主关节以及其他关节的旋转角度和位移信息。正向和反向的运动学对于身体的监测路径是不一样的。正向运动学则是相反推算路径,即从关节的旋转角度和位移信息来推断末端效应器的位置信息。无论是正向运动学还是反向运动学原理,都印射着技术链对于运动链的呼应,技术节点之间彼此链接的关系隐含着时间性。
传统的光学动作捕捉技术无法对蹲下或者拥抱等动作遮挡的身体部位进行监测,惯性动捕使用反向运动学的算法,也即IK算法可以弥补机器未监测到的数据空缺。运用智能算法可以捕捉身体运动过程中的运动链的数据,并将这些运动数据信息导入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建构身体运动习惯的模型。这项技术尝试建立一个身体图式,也即梅洛-庞蒂对于知觉-运动系统的阐释。技术尝试构建一个无比贴近真实身体的“虚拟身体”。根据末端效应器的运动路径推算出具体关节运动的角度和位置信息,尤其在无法检测到一些运动身体的信息时,则采用惯性动捕通过身体数据的算法分析,来推算出这次运动的具体数据和信息。对于身体信息的推算则是基于身体图式的基础。正是有了身体图式的前意向性,身体在运动中不自觉流露出身体习惯,惯性动捕系统对于虚拟身体的运动捕捉,才能还原一个整体的和全面的数据信息,再输出为虚拟身体本身的运动形态。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技术系统构建虚拟身体的“身体图式”的过程。
身体图式提供了虚拟现实技术交互过程得以完成的基础,并且虚拟现实技术尝试在虚拟空间里构建虚拟身体图式,用数据的算法形成虚拟身体的“思考”,进而填补交互过程中拥抱、握手和下蹲等动作的肉身部位隐藏导致的数据缺失。惯性动捕系统只是虚拟现实技术的组成技术形式之一,强调的是对动觉的捕捉。虚拟现实技术与感官知觉相结合,力图达到对于视觉、触觉以及嗅觉等感官知觉的模拟和仿真。惯性动捕技术强调身体图式的基础性地位,并尝试建构与身体的格式塔特征相吻合的技术形式,其他技术如眼球追踪、肌电模拟等与惯性动捕技术有着相似的技术设计目标,也即技术契合运动身体的知觉发生机制。
2.身体图式的动觉内涵
身体图式不是知觉经验的综合,也不是对于身体性的纯粹感知。身体图式是一种知觉-运动系统。身体图式包含了所有的肢体的统一,通过身体图式感知身体肢体的位置。[6]身体图式表现为一种先验的前意向性的特征。身体本身具有空间性,身体空间表现为一种基点的特质,即以身体空间出发来衍生虚拟现实技术的空间。身体不再是外在的纯粹的对象,而是连接现象空间的入口。[7]身体的各个感官不是一部分在另一部分旁边,孤立地排列于身体中,身体具有一定的空间性,不用测量也能感知鼻子在脸上的位置,即身体具有一种源始性的和先验的空间,并以此出发与世界产生交互。身体图式具有格式塔特征,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且各个部分没法割裂开来。身体空间不是外在物理空间,身体运动也不是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位移,身体空间是一种源始的、与生俱来的身体自身运作的结构框架,身体自有的、先验的空间性表现在不自觉地“举手投足”间,比如手持手柄来抓取相应的虚拟物体,头部会跟着手部的操作而变换方向,这一系列的身体运动并非是身体计算好的,而是一种不自觉的身体习惯。具有先验性特征的身体图式为虚拟现实技术中虚拟空间的展开,以及身体与虚拟事物的交互奠定了基础,虚拟现实技术的设计过程也默认了身体图式的特征,以一种“心照不宣”的经验模式,设计通用的技术交互过程和形式。相对而言,脑反应区域受损,即身体图式结构破坏的、无法统筹身体各个部位动作的病患,是无法完成虚拟现实技术的交互的,因其不具有身体图式的默会习惯,也无法协调地完成与技术交互的身体运动。
向技术物敞开的身体给知觉经验提供了附着点的基础性架构。梅洛-庞蒂强调身体向世界中去的趋向性。身体从来不是独立的和分割的个体。身体表现为敞开的趋向,使得身体图式本身给知觉经验的积累提供了基础性框架。梅洛-庞蒂认为身体是一个开放的与外界不断交流的结构,一个可以包含所有知觉图式的装置。他将身体视为一个开放的结构,认为各种感官的知觉附着在上面,形成了身体的格式塔体系,这些感官知觉绝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互相融合在身体图式之中。所以说,虚拟现实技术的设计、完成和运作得益于身体图式的奠基,呼应了虚拟技术对于动觉的需求,也即虚拟现实技术交互中身体运动的必要性。同时身体习惯的内在结构的形成,也为虚拟现实技术交互的动态过程提供了基础。
二、身体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的内在同构效应
1.身体技术的“虚拟现实”结构
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认为人们以传统的方式知道他们身体的使用过程,同时阐释了身体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通过重复、互动和模仿的形式,将步行、游泳、挖掘等活动带入并组织起来。[8]在身体与世界的交互过程中身体技术建立起来且不断拓展内容的外延。有些学者阐释的身体技术是指身体使用技术物的技能。[9]它更贴近于从技艺、技能的层面,去理解技术以及身体使用技术的经验。也有学者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出发将身体技术放在文化发展进程中,强调身体技术的文化、习俗和社会维度的内涵。本文将身体技术放在具体的虚拟现实技术情境中,阐释身体与技术的关系,将身体技术概括为两个方面的内涵。这两个方面内涵都体现着身体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的内在同构特征。身体技术既是指身体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和特质,是源始的身体特征,又指技术工具使用过程中形成的体验经验在身体内积累的身体技术。前反思的身体是一个格式塔的整体,身体源生技术是技术活动产生的前提和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又改变着知觉经验。身体技术提供了技术活动得以展开的基础,技术也构建了身体技术图式。身体技术在身体与技术的双向建构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具体来看身体技术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身体技术是先验的、与生俱来的,是身体自身的控制力、身体的行为行动、身体空间的内在表达。无论是静止的状态、运动的状态、自身独处的状态,还是与世界交互的状态,身体技术都是存在着的,内在于身体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是每个不同的个体具有的生命体征。梅洛-庞蒂认为,人类在世界上最初的关注点就是身体对其周围环境的适应。[10]人类拓展生存环境,发明技术工具,人与事物交互,在对物的持续占有中来表达自己的意图并实现自己的目标。身体意图的表达是通过身体对于世界的适应,也就是通过身体内在的调整来实现的,梅洛-庞蒂从这一过程来解释身体与世界的关系,同时这种身体的适应也是身体技术的一种表现形式。第二方面的身体技术就像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对莫斯的身体技术理论的赞同,通过日常的活动和经验进行共享和塑造习惯,技术情境下身体在知觉经验的积累过程中获得身体习惯,知觉则是在外在技术物的影响下形成的。基于本己身体的身体技术基础之上,吸取前人的技术经验,逐步形成独属于自己的身体技术。这里的身体技术有着被技术改造或者就像梅洛-庞蒂所说的技术适应的过程,但与此同时,技术物又是身体创造的,并可以在使用的过程中考量其与身体的契合程度和延伸的程度,以及根据现实使用中的新需求来进行技术调整。所以说,无论是身体对于技术物的适应,还是技术因身体而做出的适应性调整,都是同时发生的,是一个过程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
虚拟现实技术与身体技术的关系和传统的技术物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虚拟现实技术的主体是虚拟身体,技术交互的过程是虚拟体验,身体意向的投射不是投射在物质性的技术物上,而是投射在虚拟空间里。身体与虚拟现实技术设备是实在的接触,比如手柄的持有、头显的佩戴、数据衣的穿戴和激光扫描系统的跟踪,技术输入和输出设备提供了物质性的中介,但最终的沉浸式体验还是身体处在虚拟空间,与虚拟空间中技术物的交互,拓展了身体技术的外延。这一交互系统相比传统的技术物与人的系统具有更为复杂的结构,身体在这一过程中要将手柄的使用方法和具体的控制力度、方向、力回馈的判断等,与虚拟空间的物的运动和方向对应起来,获得复杂的多层次身体技术。这一身体技术综合地将物质性实体与虚拟物研判相结合,包括接触的虚拟现实设备的使用、虚拟物的操纵、以及设备和虚拟物互相联结关系的把握这三个方面的身体技术。
2.虚拟-现实眩晕的技术困境
无论是源始性的身体技术,还是使用技术工具过程中形成的身体技术,都是虚拟现实技术的基础,这一点与传统技术物具有同样的特征。同时虚拟现实技术又能够拓宽身体技术内涵的边界,身体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是具有内在同构效应的,这两种“技术”互相依存,相互建构,呈现着一体化的趋势。身体无法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或者身体无法到达某些场域时,技术表现为现实世界的再现或者创造出超越现实的世界,身体沉浸在虚拟现实情境中获得相应的知觉体验。虚拟现实技术是身体技术的延伸和扩展,身体技术又为虚拟现实技术提供了基础性的技术储备,使得虚拟活动得以产生。
虚拟现实技术现在依然存在虚拟-现实眩晕,不同于晕动症,这种在虚拟和现实之间转换导致的眩晕症状,使身体处于虚拟现实混沌的状态。从身体出发来思考虚拟-现实眩晕的原因,在于身体技术内在的结构中没有相应的技术内容。重复的身体技术过程才能成为习惯的方式。[11]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认为感觉和知识的体现与运用可以使人的能力与不断变化的新技术经验互动。也即是说身体通过意向的投射与技术世界产生交互,使得知觉经验不断积累。同时这些经验的积累和知识内涵的丰富,使得身体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新技术形式。身体技术是一个人生存的烙印,是身体对于世界的适应。我们采用和适应技术,体现身体在此过程与世界互动的能力。梅洛-庞蒂确定了习惯的三层含义:生物,运动和文化习惯,这些习惯影响了交互过程中人们对新技术适应的不同能力。[12]在人机交互研究的背景下,界面交互要求身体具有一定水平的能力,计算机对于身体运动的监测和捕捉,输入计算机触发相应的动作指令,所以在使用过程中学习和控制身体具有重要的意义。[13]身体技术为虚拟现实技术提供了产生、发展的基础和技术设计的源泉,为身体与虚拟现实技术的交互提供了物质性经验,虚拟现实技术不同于传统的物质性技术物通过接触体验获得知觉和认知,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结构性的、虚实结合的,尤其强调放在联结的物中来积累知觉经验的系统,进而拓展身体技术的外延。所以身体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具有内在的同构效应,正是因为有着身体技术,才有身体与虚拟现实技术交互的可能,同时身体技术的结构特征又显现着虚拟现实技术发展的程度和高度。
三、契合身体知觉的技术设计
1.技术与身体知觉之间的符号语言
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里对于知觉的阐释是放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的,既是知觉本身,又是知觉着的动态过程。身体知觉分为源生知觉和技术建构的知觉,技术建构的知觉又分为当前情境的具象技术建构的知觉和其他技术建构的知觉。本文将技术建构的知觉研究又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技术设计过程中对知觉的分析,另一个维度是技术使用过程中对知觉与技术关系的分析。
身体的源生知觉以及带有技术建构烙印的知觉,都是技术交互形成的条件和基础。这就要求技术设计要和源生知觉以及已有的技术建构知觉进行契合,这样技术才能在交互活动中与身体已有知觉进行结合。知觉场内新事物与旧事物交互融合,拓展了新技术情境中的知觉形式和内容的外延。具象的新技术为身体已有知觉定制“符号”,即身体与技术交流的科学语言。这种形式化语言,即人工语言,在特定的逻辑或数学规则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无直观意义的符号、代码来表述思想。[14]技术根据身体已有知觉的形式和内容特征进行思考、设计,创造出无限贴合身体知觉的科学语言。这种科学语言又在瞬间转化为与身体契合的符号,表现为可视可听可感的视频、音频和触感的结合。身体接收到这个符号后又给予相应的反应,从而建立起身体与技术之间的联系和交流的通道。所以,在虚拟现实技术的现象场中,技术设计出与身体已有知觉沟通的知觉符号,建立与身体知觉契合的科学语言。这样,身体才能在新技术建构的现象场中不断拓宽身体知觉的外延,从而更加真切地与技术产生交互。
2.技术设计的主客体的可逆性
在这个过程中,身体已有知觉以一种开放的姿态面向虚拟现实技术,当然这是在虚拟现实技术设计已经契合身体知觉的前提下。技术也以一种开放的姿态与身体进行知觉的交流。身体以知觉的形式来表达,技术设计以身体知觉为参照并试图通过知觉的表达来和身体进行沟通交流,二者都有一种向对方展示的可逆性。身体知觉与技术建构知觉相契合的过程中,技术的内部算法将身体知觉的反应,即身体意向行为投射的内容转化为电信号,通过计算机运算,输出为相应的身体感官知觉可以读懂的图像、声音和画面等等这些语言。身体在某种程度上又再一次看到了“自己”刚刚投射的意向性运动动作,身体再一次看到了“自己”。本文将这种技术情境中的环形结构称为可逆性。身体的可逆性是梅洛-庞蒂一开始用来形容本己身体的侵越的概念,后来用来形容与世界的可逆性的关系,表现为身体往世界中去,同时世界也将其自身展开来给身体看,身体才有了解世界的可能。这里同样适用于身体与虚拟现实技术交互的现象场,表现为身体知觉与技术的符号性沟通。身体看到了技术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身体与技术之间建立起一个环形的结构。当然,这是在虚拟现实技术使得身体沉浸在虚拟空间里的情况下,沉浸性是虚拟现实技术的特征之一,使身体相信自己是处在真实世界之中的,技术体验是具有沉浸性的知觉体验。这就要求虚拟现实技术设计要以身体知觉为技术原点,从身体知觉出发,建立起一个无限契合身体知觉图式的、能向身体发射共通性符号的结构性技术范式,这是虚拟现实技术设计的指导性方向和目标。而当下的眩晕症、头显过重等等技术问题,也是由于技术设计没有和身体知觉完全契合导致的技术难题和困境。所以,技术设计在某种程度上要模仿身体语言和身体运作的原理。
以上分析了技术设计的身体主体性思维,即以身体知觉出发,将技术放在一个身体-主体性的地位进行思考和互动。同时,也要将技术放在客体的位置上进行思考和分析,因为技术的考量方式便是在技术使用的过程中对技术进行评测。由此虚拟现实技术使用过程中的用户身体感知则尤为重要,这就要求技术设计具有身体-客体的维度,从与身体知觉进行契合的角度来设计,比如对于眼球运动信号的捕捉,对于双目视差的仿真,对于手指力度在操纵指令上的印射,包括上文提到的惯性动捕对于身体运动数据的捕捉和预测,这是作为身体知觉客体的对象角度与身体契合。这里的主体与客体分别针对身体与技术交互过程中的相对主体和相对客体,身体与技术其实都是主客体的统一,在此是以技术设计为出发点,来阐释技术设计过程中的身体的主客体位置,是一种具体技术动作指令环境之下的相对区分,在整个虚拟现实技术与身体的交互过程中,身体与技术是主客体的统一,具有可逆性。
四、技术经验来源于身体实践
实践-知觉模型在20世纪初的现象学运动中不断发展起来。受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存在主义的影响,梅洛-庞蒂认为生活世界基于日常经验。在自我-世界实践中,知觉为客观现实的体现和对于物的占有,是身体的知觉经验的具体化和明晰化。身体以一种图式向世界展开,世界也以一种结构性的特征向身体展开,身体表现为一种在世界中存在的特性。本文认为这种可逆性凸显了实践-知觉的结构特征。关于梅洛-庞蒂对于知觉的图形-背景的强调,即是把知觉放在一个现象场域中探讨。现象场域是指世界向我们呈现和展开的生动的体验层,是一个整体包含着技术物、他者以及身体主体等在内的系统,这不意味着纯粹内省心理学或直觉主义。现象场不是“意识状态”,而是行为活动中的我们-他人共同组成的意义整体。[15]梅洛-庞蒂超越了胡塞尔将“场”阐释为意识体验的功能性场所,以及表明意识体验的可证实性和可知性的场的概念。梅洛-庞蒂进一步将“场”阐释为现象场域,知觉发生在现象场域中,对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否定也可看出其对现象场域的阐释。经验主义将知觉理解为一个没有联系的感性材料的综合,忽略了身体的主动性,而将其简单地视为刺激的反应;而理性主义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将知觉阐释为意识活动。知觉不是单纯的颅内判断和思考,而是身体与世界交互的产物,没有充分认识到身体往世界中去的趋向性和身体地位的重要性。所以知觉活动既不是纯粹的客观材料的集合,也不是内部的意识状态,而是一种含混的朦胧的活动。知觉世界存在的现象场域也就是梅洛-庞蒂所谓的生活世界。现象场域不是单独存在的,也不是颅内的纯粹意识,而是身体参与的、与世界互动的系统性的场域。现象场域本质是要复归到实践的特性上来。身体也成为情境中具有表达任务的现象身体了。
1.实践背景下的技术经验
在技术哲学现象学中关于技术经验的阐释更多地集中于经验转向的宏观论述。实践层面的技术经验,在技术具身的情境中,用特殊的方式将技术包含在我的经验之中。[16]本文认为技术经验不只局限于具身情境中,技术经验强调的是技术居间调节的知觉经验的格式塔变化,强调技术与身体的重要地位和交互性关系。举一个拐杖的例子。在使用拐杖的过程中,不用测量拐杖到地面的高度,拐杖旋转的角度,身体也会自然地运用拐杖辅助走路。在一开始使用拐杖时,身体不熟悉它的长度,触感等。在身体运动的过程中,在身体与技术物的交互过程中,身体图式的内容得以丰富,拐杖这一技术物成为身体的延伸,身体逐渐形成拐杖使用习惯的技术经验。技术哲学研究中发生了经验“转向”。传统的理解把技术当成整体的抽象的事物,并在此基础上将技术与人类发展联系起来,而经验转向则是把技术拓展为具体的技术形式来作为研究对象,并开始研究具体技术对于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影响。[17]本文阐释的技术经验存在于技术设计者的设计活动中,即技术创造者在创新的过程中对于相关领域技术经验的积累和使用,还有一个层面是使用者在与技术发生交互活动过程中积累的身体经验。所以技术经验存在于技术活动以及技术设计过程中,具有两个方向的意涵,也可以说是以主体和客体来划分为技术设计的经验和身体技术经验两个方面。
身体经验在本质上和身体技术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身体技术强调对于虚拟现实技术的使用和把控,以及身体图式和结构的改变。身体经验是身体在使用技术过程中不断积累的内化于身体的知识和认识的经验内容,可以是对技术的操控和把握,也可以是技术交互过程中的心得、体会、技巧以及情绪,都属于身体经验的范畴。身体经验是理性和感性维度的结合,包含可复制的显性经验以及不可复制、只可意会的隐形经验。两种身体经验的结合可以和技术设计经验结合起来。技术设计的经验是站在技术创新者本位的,技术设计者在创新和完善技术的过程中不能只关注科学技术的呈现,还应回归身体经验,关注技术设计与身体经验相契合的模式建构。这也要求技术设计者具有一定的技术设计经验和技术体验经验。只有通过身体体验虚拟现实技术的沉浸,才能知觉出技术设计的漏洞,以及技术没有与人的知觉结合紧密的地方,才能将积累的技术经验传授给后来的设计者。技术设计经验以技术体验经验为基础,技术体验经验的获得也即身体参与的身体经验的获得,是重复性的多层次体验知觉。只有在这个过程中,设计者才能把实践建构的知觉经验融合到技术设计的过程中,进而达到与身体更加贴合的设计。
2.信息时代技术创新的身体复归
从身体技术经验到身体设计经验以及身体体验经验的获得,是本文根据虚拟现实技术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的不同视角进行的分类,统一于技术创新的进程,技术经验的创新离不开身体,要求身体必须在场。现阶段虚拟现实技术刷新率和分辨率不够高使得画面延迟,这种延迟与声音和触觉的感知具有时间误差,会让受众的听觉、视觉等感官知觉分离,进而在虚拟情境中无法完全沉浸。这些技术现存的弊端是技术设计经验对身体经验的捕捉和呈现不够全面和完善导致的。上文提到,虚拟现实技术对于身体运动习惯的捕捉,可以通过对于身体运动的数据监测进而构建身体运动的惯性模型,对身体某些动作的隐藏部分进行预测,进而达到对于身体经验的模拟。技术设计过程中没有对身体的运动原理和内部结构更为详尽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存在着一些无法解释的身体现象。科学家对于身体的探秘依然是内在性和超越性的统一。这方面技术经验设计受制于相应的身体体验的空白。
现阶段的虚拟现实技术与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及大数据(Big Data)的结合,在技术使用过程中可以增强交互性、沉浸感。同时,站在技术经验的角度上,大数据对于身体经验的关注也可以通过对于身体知觉模型的建构、解构以及建构和再建构的过程不断调试和完善,试图构建一个对于身体经验的记录。通过人工智能的加持,技术和身体交互的情况下,对于身体知觉的反馈进行一定的预测和判断。所以说,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进行融合,将技术设计追溯到身体知觉的源头和身体运动过程的知觉体验,并将这些数据建立模型,进行分析,通过算法达到对于身体意向投射的预测,使得技术经验与身体经验相契合。所以说技术设计的过程以及技术经验的获得必须要求身体的在场,这样才能使技术与身体的交互活动更加自然,沉浸感更强,身体才能获得基于真实或者超越真实的知觉体验。
五、结 语
以上从身体本位出发探讨虚拟现实技术情境下身体对于技术的重要地位和特殊作用,将具体的惯性动捕系统的技术分析与现象学理论相结合,认为技术链的构建基于身体动觉的捕捉,真实身体在虚拟空间的印射达到对于身体运动的模拟和仿真,技术尝试构建“虚拟身体”,填补交互过程中的身体隐藏导致的数据缺失;通过智能算法形成虚拟身体的“思考”,基于身体的动作捕捉来形成身体运动数据库,建立惯性模型,达到对于运动意图的预测。在这一过程中,身体技术复杂性和多层次性便体现出来。
本文比较了技术与身体交互的系统与传统技术物与人的交互系统。虚拟现实交互系统具有更为复杂的结构,要综合把控物质性实体与虚拟物相结合的操作系统,包括接触的虚拟现实设备的使用、非接触的虚拟物的操纵以及设备和虚拟物互相联结关系的把握等方面的身体技术。身体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具有内在的同构效应。正是因为身体技术,才有身体与虚拟现实技术交互的可能。身体知觉的基础性地位决定了技术创新要结合技术设计过程和技术使用过程两个维度,建立起一个无限契合身体知觉图式的、能向身体发射共通性符号的技术范式。技术设计以身体知觉为参照并试图通过知觉的表达来和身体进行沟通交流,二者都有一种向对方展开的可逆性,身体知觉与技术建构知觉相契合的过程中,技术的内部算法将身体知觉的反应,即身体意向行为投射的内容转化为电信号再输出,身体在某种程度上再一次看到了“自己”刚刚投射的意向性的运动。本文用这种身体的可逆性创新地诠释了侵越的概念内核。技术设计的主客体具有可逆性。从身体技术经验到身体设计经验以及身体体验经验的获得,是虚拟现实技术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的不同视角的经验的体现,统一于技术创新的进程。技术经验的创新离不开身体,要求身体必须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