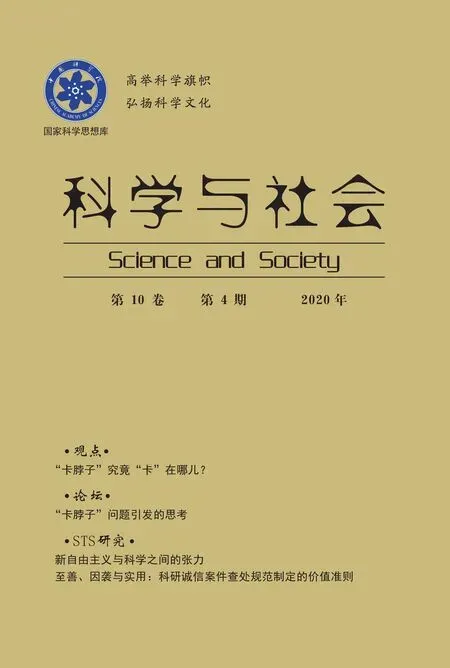重视基础教育拔尖人才培养,解决我国“卡脖子”问题
郑永和(北京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院)
焦点:中美之间竞合格局的急速转变使得高层次人才流动更加紧张,过去我国可以借助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人才交流吸引一些高水平科技人才,但当下我国必须着眼未来抓紧大量科技人才的自主培养,以此破解关键技术领域人才匮乏这一“卡脖子”问题。教育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根本途径,不断涌现的创新型人才是国家拥有持久竞争力的根本保障,建设科技强国、实现创新发展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教育。
近年来,我国经济与科技实力大幅提升,科技发展从早期以开放、跟踪为主要特征到如今实现了部分领域与发达国家并行、领跑的新阶段。中美经贸关系逐渐由“合作大于竞争”向“竞争大于合作”转变,双方竞争格局开始发生显著变化。为全面压制我国发展,特朗普政府推行单边主义和经济霸权主义,从贸易、科技、人才等多方面对我国进行全方位打压,试图围堵和孤立中国。2018年美国制裁中兴事件发生后,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引起高度关注,围绕抢占科技制高点的战略竞争成为两国博弈的核心议题。
实现科技创新,必须建立强大的创新科技人才队伍。人才作为科技创新发展的第一资源,恰是破解美方压制的关键“七寸”。那么, 相比美国我国科技人才的培养究竟如何?从人工智能(AI)领域来看,《2019全球AI人才报告》显示,全球AI论文发表的学者中44%是在美国获得的博士学位,我国本土培养的博士数量是其1/4;同时AI人才流动性很强,美国仍是对全球顶尖人才吸引力最大的国家。今年6月,《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名为《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秘密武器:中国人才》的文章指出,“截至2018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公民中,有90%的人在毕业后会继续留在美国至少5年,这些数字没有下降的迹象”。直观来看,我国科技人才流失现象严重,而且我国在科技尖端领域的拔尖人才培养仍有缺失,大多数人出国的初心是为了深造,不少人才在美国等其他科学技术强国成长为一流科学家。中美之间局势转变使得人才流动更加紧张,如果说此前我国还能借助美国进行科技人才培养,从而牵动我国部分行业的发展,那么当下我国必须抓紧自主培养大量科技人才,破解关键技术的人才匮乏这一“卡脖子”问题。
教育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根本途径,不断涌现的创新型人才是国家拥有持久竞争力的根本保障,建设科技强国、实现创新发展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教育。一方面,紧抓高等教育中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以超常规方式加快培养一批紧缺人才,为国家解决“卡脖子”问题实现最直接供给。另一方面,紧抓青少年科学教育,从基础教育阶段做好拔尖人才的充足储备。面向未来30年后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我国必须为青少年拔尖人才提供适当成长路径,赢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最前端。
一是要更新对拔尖人才培养的观念认识。教育公平不是指人人平均的教育,而是人尽其才的教育。公平的教育应当是为不同的学生提供适应其能力与需求的教育,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潜能。大众对于拔尖教育即高智力儿童的精英教育的片面认识,导致基础教育阶段的拔尖人才培养在全国层面难以开展。正视拔尖人才教育是教育公平的重要体现,应当使有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获得拔尖人才培养机会,因材施教,助力拔尖人才发挥自身潜能。
二是要实现拔尖人才培养的体制创新。拔尖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当前大多政策关注高中及高等教育的拔尖人才培养,但未能深入打通到基础教育阶段,形成对拔尖人才发现、保护、科学引导的合理体系。首先,在选才上加大拔尖人才的甄别力度,允许在基础教育阶段遴选科技特长中小学生,组织专家设计论证科学而灵活的选拔机制,也可借鉴国外做法,采用主动报名和学校推荐双轨制。其次,在育才上支持设立科技特色天才班、科技特色学校,集中力量投入科技资源保障拔尖人才的专门培养,要让那些有杰出能力又积极探索科学的青少年有学习和实验的地方。最后,要保障成才学生的合理通道。
三是要重视拔尖人才成长规律的系统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遵循青少年成长规律推进科学教育的战略目标和发展方向,那么人才成长的规律研究必须得跟上,为拔尖人才培养提供理论保障。研究内容可包括但不限于:(1)对拔尖人才认知规律的探索,如拔尖人才的阶段性成长特点、思维方式、环境影响因素等;(2)对拔尖人才教学培养的探索,如拔尖人才的评估方式、培养模式、教学支持等;(3)对拔尖人才社会支持的探索,如政策、体系、机制、社会文化等。
四是必须加强青少年整体对基础科学的正确认知。基础科学强调个体对外部世界的客观认识以及动态的知识发现过程,要培养学生形成基于科学价值观认同的科学行为与科学思维。如果青少年从小对“无用之用”的基础科学缺少好奇,只是知道科学知识,但不知道科学知识怎么来的、科学何用、如何用科学思维方式解决问题,那么创新又从何谈起?面向科技新时代,必须将重视基础科学教育作为重要时代特征。
在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高考指挥棒作用下,一些具有特殊天赋的人才有时无法脱颖而出。2020年起启动的“强基计划”取代自主招生为拔尖人才提供了新的出口,旨在最大程度公开化、公正化实现人才选拔,但这一方式凸显了“回归高考”的特点,高考成绩仍是人才选拔的主要标准,仅从分值占比上看,高校的自主权在一定程度是被缩减了。为解决培养储备人才的“卡脖子”问题,必须正确认识“木桶效应”已不再适应当前时代,如何让各类人才拥有足够的平台尽可能延伸自己的长板,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是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