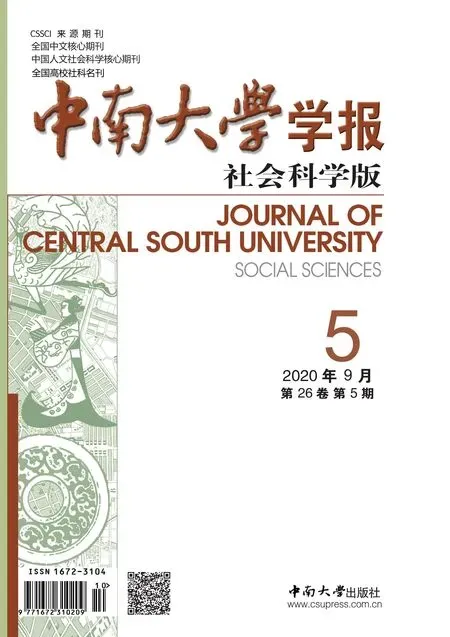康德如何看待恩典对克服“根本恶”的作用
——与韦政希博士商榷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长沙,410082)
众所周知,康德的道德神学提出了“上帝存在”这个“公设”,把上帝当作实现德福一致(至善)的条件。如果我们把上帝赐福于配享幸福者当作其恩典,则道德神学中自然包含了恩典思想。不过,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1793,以下简称《宗教》)一书中,康德关注的主要不是这个意义的恩典,而是人自甘堕落、心灵颠倒(“根本恶”)时外在神力对人改恶向善的作用。一般认为,作为强调理性和自由的启蒙思想家,康德在人重建原初向善禀赋(即克服根本恶)的问题上,强调的是人自己的力量和作为,而非外在神力的援助,仅当人自己作出全部努力、因而配得上神的协助之后,才可以希望恩典降临。康德虽未否定恩典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将之虚化并置于次要地位。但是,韦政希博士在《康德宗教哲学中道德自律与恩典的一致性》[1]一文中提出,仅仅从理性宗教视角将恩典理解为一个“实践理性的悬设”而将之概念化,会导致恩典不能给予人们克服根本恶的力量。他将恩典概念“实在化”,提出道德自律和恩典是康德分别从理性宗教和启示宗教视角来看待同一件事的结果,具有内在一致性:一方面,启示宗教中的恩典虽无法被人认识,但还是作为人改恶向善的本体论前提起作用,主要表现为能够帮助人实现心灵革命,而不像人自己那样只能进行心灵的逐渐改良;另一方面,理性宗教中的道德自律是人获得恩典的实践论前提。他还认为,康德对其宗教哲学中“二律背反”的解决已间接解决了道德自律与恩典的矛盾问题[1](26)。他不满足于仅仅从康德承认需要假定神力援助这一点来理解道德自律(人力)与恩典(神力)的一致性,而是在两者互为前提的意义上理解其一致性,并将之归结为康德宗教哲学同时包含了理性宗教和启示宗教,由此认为康德“既宣扬了人的自由意志,又强调恩典对于我们的改恶向善的必要性,将奥古斯丁主义和佩拉纠主义中的积极因素都统一起来了”[1](32)。
笔者将韦政希博士的观点概括为四个:其一,不能将康德的恩典概念仅当作一个实践理性的悬设使之概念化,而要看到恩典对克服根本恶的实在作用;其二,道德自律只能促成改良,人心革命只能指靠恩典;其三,恩典与道德自律互为前提,恩典是道德自律的本体论前提,道德自律是恩典的实践论前提;其四,康德对宗教二律背反的解决体现了恩典与道德自律、启示宗教与理性宗教的一致性。第一个观点提出了应如何理解康德的恩典概念,它究竟是实是虚的问题;第二个观点提出了恩典的作用,即恩典是否造成人心革命的问题;第三个观点提出了恩典与道德自律是否互为前提的问题,其关键是恩典能否作为道德自律的本体论前提起作用;第四个观点提出了康德是否消除了恩典与道德自律的矛盾,即启示宗教中的恩典与理性宗教中的道德自律是否和谐一致的问题。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并依康德原意,把韦政希博士所说的“道德自律”理解为人凭借“自力”来重建原初向善禀赋①。
一、康德的恩典概念究竟是实是虚?
韦政希博士说,通行理解“将恩典理解为一个实践理性的悬设而将之概念化,但一个概念化的恩典是无法给予人们去除根本恶的力量的”[1](26)。通行理解如何通过将恩典理解为实践理性的悬设而将之概念化,他并未解释清楚。由于康德并未把恩典说成是实践理性的悬设,就像其道德神学把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说成是实践理性的悬设一样,因而有哪些研究者把恩典理解为实践理性的悬设,这是需要指明的。同时,“概念化”是何含义,也需要给出解释,是指恩典原本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实在的存在物,通行理解将之概念化?由于康德确实也谈论恩典概念,所以通行理解如果谈论康德的恩典概念,并不存在把某个非概念的东西概念化的问题。不过,虽然“将恩典理解为一个实践理性的悬设而将之概念化”的说法含义有些模糊,但“一个概念化的恩典是无法给予人们去除根本恶的力量的”这句话,还是大致表明了他的意思,即通行理解仅仅把恩典理解为一个类似于实践理性悬设的假定,导致恩典不能在人克服根本恶时发挥实在作用。
笔者揣测韦政希博士不会反对康德曾谈论恩典概念,他反对的只是把康德的恩典概念理解为一个“虚概念”(指一个没有实在效力的假定),而主张把它理解为一个“实概念”(指一种有助于克服根本恶的实在神力)。恩典概念涉及的,是上帝对于人克服根本恶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康德把“论重建原初向善禀赋之力量”(6:44)当作《宗教》第一篇“总附释”的标题,并且说也可以叫作“论恩典作用”(von Gnadewirkungen,6:52)。所以,在理解康德恩典概念的含义时,关键不在于是否承认恩典在克服根本恶中的作用,而在于在多大程度上承认这一作用。因为康德首先强调人需要凭借自己的力量努力改恶向善,然后才有资格配享神的可能的助力,因而通行理解会按照康德的思路,把恩典理解为人自己付出努力之后的一个必要的补充假定,这可能就是韦政希博士所谓“将恩典理解为一个实践理性的悬设而将之概念化”的含义。
韦政希博士说,康德在《宗教》第一篇“总附释”中主张道德自律与恩典对于克服根本恶都是必不可少的,“康德指出,一方面,我们必须按照道德法则过着一种有道德自律的善的生活,成为一个善人;另一方面,对根本恶的解决,上帝的恩典这种超自然的协助是必要的”[1](28)。可以承认,在克服根本恶的问题上,康德并未一概否定恩典的作用,拒绝神的助力,但他并不直接断言“恩典这种超自然的协助是必要的”,而是说“必须假设这种援助”(6:44)。他写道:“假定一种超自然的协助对于成善或变得完善是必要的,那么,无论这种协助仅在于减少阻碍,抑或也在于积极的援助,人都必须事先做到使自己配得上接受这种援助,且必须假设这种援助(这是非同小可的),就是说,把力量的积极增长纳入其准则。”(6:44)这里谈到两点:其一,人要接受神的援助,必须事先做到使自己配得上接受它,即首先做到“自力更新”(凭借自己力量的运用成为一个新人),然后才有资格接受“外援”,即神的超自然协助;其二,康德在假定超自然协助为必要的情况下,认为人必须“假设”这种援助,这表明他并不一概拒绝恩典,而是视之为一种必要的假设。
对康德而言,人的“自力更新”毫无疑问是“实的”,就是说,人通过自身力量而实现心灵革命并重建原初向善禀赋,这不仅“应该”,而且“能够”,因为“应该”蕴含了“能够”,这是他一再强调的一项原则(6:45;6:47;6:50)。康德认为,人必须能够希望,“通过运用自己的力量,而达到那条通向那里的[指通向心灵革命]、由一种从根本上改善了的意念向他指明的道路”(6:51)。人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所为,才能被评判为在道德上是善的;倘如是外在神力使人心重新变得完善,那就不是人自己的功德,他也就不会是道德上的善人了。他由此把下述命题当作他所支持的“道德的宗教”,即“善良生活方式的宗教”的一条基本原理,“为了成为更完善的人,每个人都必须尽力做力所能及之事,而且,仅当他不埋没自己的天赋才能(《路加福音》,第19章,第12—16 节),为了成为一个更完善之人而利用自己原初的向善禀赋时,他才能希望通过更高的协助来弥补他力所不及的东西”(6:52)。同时,他依据这一原理来反对“祈求恩典的宗教”(die Religion der Gunstberwerbung,6:51),即“纯然祭拜的宗教”。在这种宗教中,人妄自尊大,自以为无需成为一个更完善之人,上帝就能够通过赦免其罪孽而使他享受永福,或者以为仅仅通过祈祷,上帝就会把他变得完善。康德还把如下命题当作不证自明的基本原则:除善良生活方式外,凡是人自以为为了让上帝喜悦还能够做的事情,都仅仅是宗教妄想和对上帝的伪侍奉(6:170)。这是一种宗教妄想,人在为善良生活方式付出自己的努力之前,就可以“白白地”(ganzunsonst,6:172)获得恩典,并以超自然的方式造成善良生活方式。
同时,对康德而言,哪怕他说“必须假设”神的援助,这种援助始终还是“虚的”。这不仅因为人只有付出自己的努力之后才能希望接受这种援助,而且因为这种援助对人而言是“无法探究的”(unforschlich,6:45),是一种“超自然的”神力。他因而提出:人完全无需知道这种援助存在于何处,而且难以避免的是,当它的发生方式在某个时刻得到启示时,其他人却在其他时刻对它形成了不同的概念,并且都自以为真诚。但无论如何,下述原理是有效的:“知道上帝为他永福在做或做过什么,这不是根本的,因而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相反,“为了配得上这种援助,每个人自己必须做些什么,这是根本的,因而每个人都是必要的”(6:52)。通过这一鲜明对比,康德把恩典置于次要地位,否定了它对于人的得救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自力更新”为主,神力援助为辅,是他在重建原初向善禀赋、克服根本恶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康德在第一篇“总附释”的末尾,在一个长脚注中对该“总附释”以及另外三卷的三个“总附释”做了一个说明,借此也更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恩典概念。他说,这四个总附释本来可以使用下面四个标题:(1)论恩典作用;(2)论奇迹;(3)论奥秘;(4)论邀恩手段。它们似乎属于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的“补遗”;它们不属于纯粹理性的界限之内,但与之接壤。理性意识到了在满足其道德需要方面的无能,因而把自己扩展到那些据说能弥补那种缺陷的超越的理念,但并不把它们当作扩展了的财产据为己有。理性并不否认这些理念之对象的可能性或现实性,只不过它不能把它们纳入自己思维和行动的准则。理性甚至带着人们可以称之为“反思的信仰”的信仰而指望:如果在无法探究的超自然物的领域中还有更多的某种东西,它虽然不能为理性所理解,但对于弥补理性在道德上的无能是必要的,则这种即便不可认识的东西也会对理性的善良意志大有裨益。康德还把这种“反思的信仰”与宣称自己是一种“知识”的“教条的信仰”相对立,认为在“反思的信仰”看来,“教条的信仰”是不真诚的和僭妄的。可见,康德很谦逊地对待神恩所涉及的各种超验理念,他仅仅在“反思的信仰”名义下给予承认,并反对将它们当作“教条的信仰”。他还指出,一旦我们把这些道德上的超验理念引入宗教,就会导致不幸的后果:(1)被认为的内部经验( 恩典作用) 的结果是狂热(Schwärmerei);(2)所谓外部经验(奇迹)的作用是迷信(Aberglaube);(3)在超自然事物(奥秘)方面的所谓知性顿悟,其结果是顿悟说(Illuminatism),即术士们的幻觉;(4)对超自然事物施加影响的大胆试验( 邀恩手段) 的结果则是魔术(Thaumaturgie)。所有这些做法都超越了纯粹理性的界限,而且属于“教条的”而非“反思的”信仰。
康德特别就恩典作用指出:如果理性坚守其界限,就不会将恩典作用纳入其准则,正如它不会将其他超自然事物纳入其准则一样,因为在超自然事物那里,理性的一切运用都终止了。他还指出,在理论上说明这些恩典作用的根据何在,是不可能的;而在实践上使用恩典理念,其前提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要使用恩典理念,就需要预设一个规则,告诉我们为了达到某种东西,就必须自己去作出某种善;而期待恩典作用却恰好意味着相反的东西,这就是说,善(道德上的善)不是我们的行为,而是另外一个存在者的行为,因而我们只能通过无为(Nichtstun)来获得它,这是自相矛盾的。”(6:53)所以,康德仅仅在“反思的信仰”的意义上承认恩典作用是不可理解的东西,但反对把恩典作用纳入理性的准则,不论是为了其理论的还是实践的运用。这些论述,与韦政希博士试图把恩典概念“实在化”的做法是冲突的。康德反对把恩典作用纳入理性的准则,仅仅在“反思的信仰”名义下给予承认,这表明他反对把恩典作用“实在化”。
在第三卷“总附释”中,康德在把神的恩典与人的本性相对照的情况下,把恩典概念视为“超验概念”。人自己按照自由法则能够作出的善行,都可以称为“本性”(Natur),它属于“人力”,不同于恩典这种外在“神力”。我们可以找到把握本性的线索,但不能认识恩典。恩典是否在我们身上起作用,在什么时候起作用,以及起什么作用和起多大作用,“对我们始终是完全隐蔽的”,而且在这方面,“理性对于其发生所遵循的法则一无所知”(6:191)。所以,他认为恩典作为一种超自然协助的概念,“是超验的,和一个纯然的理念,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向我们担保其实在性”(6:191)。甚至仅仅把这个理念假设为纯然实践意图中的理念,也是很冒险的,并且与理性难以统一,因为一切道德上的善行都必须归功于我们自己,而不能借助于外力。康德承认自由同恩典一样都属于超自然的对象,因为自由也是不能最终说明的。但他认为,我们至少可以知道用来规定自由的那些法则,而关于恩典这种超自然的援助,就彻底一无所知了。所以,他认为我们只能一般地假定:凡是本性在我们身上不能造成的,只要我们尽量运用我们的本性,恩典就将会造成它,此外,我们对此理念就不能做任何使用了。这一理念完全是“超越的”,把它当作神圣之物敬而远之是“有益的”(6:191)。
总之,康德本人的说法,与韦政希博士的解读并不吻合。尽管在“反思的信仰”中承认恩典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但康德明确反对把恩典概念“实在化”。在他看来,恩典作为一种“超自然的协助”是完全不可认识和把握的,因而恩典概念也仅仅是一个超验概念,一个纯然的理念,绝不能纳入理性的准则。
二、恩典与道德自律是否分别促成人心革命和改良?
在从“实”的方面理解康德的恩典概念时,韦政希博士把恩典的作用与人的心灵革命联系起来,认为在康德那里,道德自律仅仅促成人的逐渐改良,而心灵革命仅仅是恩典的作用。他写道:“基于理性宗教中作为有理性的人和启示宗教中作为属灵的人的划分,康德分别把道德自律和恩典与人的改良和革命联系起来。在面对根本恶时改恶向善,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皈依——一个旧人通过心灵的改变成为一个新人,亦即革命;这个改变的过程就是改良。革命是改良的本体论前提。”[1](30-31)
诚然,康德确实既从量又从质,既从外在行动的合法性又从内心动机的道德性来谈改恶向善,因而区分了仅有外在行动合法性的逐渐改良和内心思维方式的彻底革命,但是,说一个旧人通过心灵改变成为一个新人是“革命”没有问题,说这个改变的过程就是“改良”却是误解。如前所述,康德把原初向善禀赋之重建理解为建立道德法则的纯粹性,他因而要求仅仅把法则作为规定任意的充足动机,要求人们仅仅出自义务而行动。一个把法则之纯粹性纳入自己准则的人,虽然并不因此就是神圣的,但已经“踏上了在无限进步中接近神圣性的道路”(6:46)。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行动往往只能做到合乎法则,而不能出自义务即出自对法则的敬重。合法性只是表面的“德性”,人们只能逐渐获得这种“作为现象的德性”,一些人将之称作(在遵守法则方面的)长期“习惯”。人虽然可以通过逐渐获得这种表面德性而改变自己的行事方式,坚持做不违背法则之事,但并不需要心灵的转变,而只需要习俗的转变。此时,他可以成为“律法上的善人”,但还不是“道德上的善人”,即上帝所喜悦之人(6:47)。相反,要成为“道德上的善人”,就不能通过逐渐的改良,而是“必须通过人的意念中的一场革命”(6:47),即一种向意念的神圣性准则的转变来促成,通过心灵的这一革命性转变,一个旧人才能变成一个新人。
韦政希博士把通过心灵革命而造成的由旧人到新人的转变过程说成是改良,这就混淆了革命和改良的原则界限。他这样理解,很可能是把心灵革命之后对纯粹动机的践行过程当作改良了,他没有认识到,改良还根本未涉及思维方式的革命,因而绝非心灵革命之后的转变过程。从时间上说,革命并不是在改良之前发生的,而恰好是在改良过程中才出现的。在心灵革命之后,一个人当然还需要把转变了的内在思维方式贯彻于外在行动之中。因此康德谈到心灵革命之后,一个人虽然就原则和思维方式而言是一个接纳善的主体,但“仅仅就不断的践行和转变而言才是一个善人”(6:48)。这当然是在强调内心革命之后还需要落实到实践中,但这个实践过程是心灵革命之后才展开的,完全不同于仅仅造成“律法上的善人”的改良过程。
正是由于误将心灵革命之后的践行过程当成了改良,韦政希博士才提出“革命是改良的本体论前提”。这一命题是不适当的,因为康德并没有提出改良只能在革命之后进行,而是说没有革命仅有改良还不够,习俗的转变还有待发展到心灵的转变。如果认为康德把革命当作改良的本体论前提,而革命又取决于恩典,那么,这确乎把恩典当作道德自律所促成的改良的本体论前提了,于是,外在的神恩就成了人的心灵转变即重建原初向善禀赋的先决条件,人的道德自律就成了一个次要的附带后果。但是,这与康德的恩典概念完全相悖,违背了康德“自力更新”的基本原则,意味着要把神恩不合理地纳入理性的准则。事实上,康德明确指出:不论是就思维方式的革命而言,还是就感官方式的改良而言,都是“人所必要的,因而也是可能的”(6:47)。“应该蕴含能够”原则不仅仅适用于改良,而是同时适用于革命和改良。当康德说,如果人“通过惟一的一次不可改变的决定,扭转了他曾是一个恶人所凭借的准则的最高根据”(6:47)时,他不是断定这一“决定”和由此导致的“扭转”是神恩之事,而是将之视为人自己的内心革命。如果这不是人自己所为,人就没有资格去期待恩典,不能希望凭借他纳入其准则的道德法则的纯粹性和坚定性,走上从恶到更加完善的不断进步的美好道路。
韦政希博士之所以把外在恩典当作革命的原因,并且把革命当作道德自律所促成的人的改良的本体论前提,很可能是由于误解了康德的一个说法。康德说:“对于能够看透心灵的(任意的所有准则的)理知根据、进步的无限性对他来说也就是统一性的那一位,即对于上帝而言,这件事就等于说他现实地是一个善人(上帝所喜悦的人)。在这种意义上,这种转变就可以被看做是革命。但是,对于只能按照其准则在时间中获得的对感性的优势来评价自己及其准则的力量的人的判断来说,这种转变就只能被看做是一种向善的永不间断的努力,从而也就只能看做是对作为颠倒了的思维方式的趋恶倾向的逐渐改良。”(6:48)这是说,人的内心转变作为超感性之事是人自己不能看透的,而只能被“知人心的上帝”看透,所以人只能把自己从旧人到新人的转变视为逐渐的改良。但是,这并不是说人的心灵革命就是上帝在看透人心时的恩典作用。康德在此谈的是两种不同的观察或判断方式,而不是在肯定神恩是心灵革命的根源。总之,把心灵革命归结为外在恩典的作用,仅仅肯定道德自律对于促成人的改良具有作用,并且把恩典促成的革命当成道德自律所促成的改良的本体论前提,这与康德关于恩典作用的论述不相符合,因而是不能成立的。
三、恩典与道德自律能否互为前提?
韦政希博士在提出革命是改良的本体论前提时,实际上已经肯定了恩典是道德自律的本体论前提,他也确实认为,“启示宗教中的恩典虽然无法被人们所认识,但它还是作为人改恶向善的本体论前提起作用”[1](26)。与此同时,他又肯定“理性宗教中的道德自律则是人们获得恩典的实践论前提”[1](26)。于是就有了两者的互为前提,以及在互为前提中的内在一致性。他还说:“人只有以其精神被动地获得恩典,才具有自由意志的主动性。同时,人只有主动地进行道德自律,才可以接受恩典。”[1](26)这其实在说两者互为条件:人的主动性以受动性为条件,反过来,人的受动性又以主动性为条件。他认为,“如果没有包括恩典在内的上帝的活动,我们就无法理解人的来源,也无法理解人的人格性,根本恶的问题也无从解决。”他甚至断言:“没有恩典,康德的实践哲学就失去了本体论根基,无从建立。”[1](30)
韦政希博士把道德自律视为获得恩典的实践论前提,这一点没有大的问题,与康德强调人“自力更新”具有优先性的思想相一致。只是需要指出:在其“人只有主动地进行道德自律,才可以接受恩典”的命题中,“可以”很可能只意味着“能够”,即从“能力”或“可能性”意义得到理解,而不像康德那样从“允许”的意义来理解。康德一再强调:人只有首先“自力更新”,然后才有“资格”,即配得上希望恩典。韦政希博士并未阐明这一点。
主要问题在于,他夸大了恩典作用,把它说成人们获得道德自律的“本体论前提”。何谓“本体论前提”,他并未作出清晰界定,我们只能通过“人只有以其精神被动地获得恩典,才具有自由意志的主动性”这一说法来了解其含义。但是,“人以其精神被动地获得恩典”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人如何能够“以其精神”而“被动地”获得恩典?当人被动地接受恩典时,他是被动的,而“以其精神”的说法却赋予人以某种主动性。他想表达的也许是:人首先因为恩典成为一个受造的属灵(具有Geist)之人,然后才可以主动地发挥其自由意志的作用②。
该说法对应于他所说的“康德原理”的三条预设的第二条。他在文章中引用黄士平的观点[2],把“应该蕴含能够”叫做“康德原理”,认为该原理包含三条预设:(1)理性不会命令人们去做不可能的事;(2)人的人格性;(3)圆满实现道德法则,必须延续时间而且时间必须足够长。第一条预设是康德在《实用人类学》中提到的,其实不过是“应该蕴含能够”原则的“同义反复”,自然不能说明恩典是道德自律的本体论前提;第三条预设涉及灵魂不朽公设,与恩典充当道德自律的本体论前提也没有关系。只有第二条“人的人格性”才可以通过某种解释与启示宗教的恩典发生关联。照他所说,人格性可以同时从理性宗教和启示宗教的角度理解:“一方面,人格性从理性宗教角度说明人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服从自己的人格性就是服从理知世界的法则,即道德法则……另一方面,就启示宗教角度而言,人格性强调了人作为上帝意志的造物中的不被时空限制的禀赋(这其实已经蕴含了第三条预设)。”[1](29)他把人格性的超越感性、通向理知世界的特性与第三条预设相联系,认为人作为理智者以其精神而获得无限的生命,并且认为这个无限的生命“就其是上帝的灵(Geist)所赋予而言是被动的”[1](29)。可见,他是把上帝创造属灵之人当作上帝对于人的恩典,此时,上帝赋予人人格性禀赋和无限的生命。他认为人的自由意志的主动性,依赖于人被动接受的这份恩典,于是得出恩典是道德自律的本体论前提的结论。
这些观点包含不少问题。例如,把人格性与第三条预设相联系就显得牵强,因为人格性的超感性特征表明人可以进入超感性的理知(知性)世界,而第三条预设说的是人的德性完善需要无限延续的时间,两者不是一回事。又如,他并未阐明人格性与人格性禀赋的关系。在《宗教》中,康德更多地在谈论人格性禀赋,它正是需要重建的原初向善禀赋之核心,就是指道德法则理念连同对法则的敬重(理知意义上的人性理念,6:28),这种禀赋一旦被自由任意纳入其准则,就是实现出来的人格性,也正是重建禀赋的目标。韦政希博士可能是把人格性禀赋视为上帝给予人的恩典,或者认为上帝创造了具有此类禀赋的人,即所谓属灵的人,但他却直接从启示宗教的角度把人格性理解为恩典,即上帝赋予人的无限的生命,而未意识到在康德这里,人是否把人格性禀赋纳入自己的准则,是由人的自由意志来择定的,而绝不能托付给神恩。
韦政希博士依据《宗教》中出现der Geist Gottes 一词的一段话,认为康德是以启示宗教的视角谈论人的不受时间所限的生命,人的属灵的无限生命是“上帝的灵”所赋予的,它们本质相同,都是Geist。这种理解,也存在很大问题。康德是在论述“教会信仰以纯粹的宗教信仰为最高诠释者”时提到的der Geist Gottes(6:112)。他提出:我们要以纯粹的宗教信仰为标准来诠释教会信仰。因而即使《圣经》被认作是神的启示,这种启示的最高标准也是:《圣经》在教训、督责和使人完善方面都是有益的。而由于人的道德完善构成了所有理性宗教的真正目的,因此,道德完善也就构成了经文诠释的最高原则。康德接着指出:“这种宗教是上帝的精神(Geist),它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6:113)此句中,这种宗教(diese Religion)从前文看只能指“这种理性宗教”,而非“启示宗教”。康德还把“上帝的精神”解释为“通过教导我们,也同时凭借诸行动原理而使我们振奋的精神”。此句中“使我们振奋”的原文是uns beleben。将之译为“赋予我们生命”,易使人想到“上帝的精神”创造了属灵之人,而不是说它使我们这些属灵之人在精神上受到激励或鼓舞。康德接着还说:“上帝的精神”把《圣经》在历史性信仰方面还可能包含的一切,都完全与纯粹道德信仰的规则和动机相联系。这就更清楚地表明,这个“上帝的精神”恰好是理性宗教、而非历史性的启示宗教的概念。韦政希博士未认识到康德试图对《圣经》中的上帝启示做纯粹理性的诠释,因而不适当地把“上帝的精神”当作启示宗教的概念了。
韦政希博士在断言恩典是道德自律的本体论前提时,其恩典概念具有多义性和含糊性,但无论如何,他所理解的恩典都不能成为道德自律的本体论前提。
首先,人格性不可能是作为道德自律之本体论前提的恩典。这是因为,在《宗教》中,人格性意味着堕落之人将心中始终存在的法则理念连同对法则的敬重重新纳入其准则。这恰好等同于原始向善禀赋即人格性禀赋的重建本身,当然不等于这一重建的本体论前提。
其次,人格性禀赋不可能是作为道德自律的本体论前提的恩典。诚然,康德非常看重人格性禀赋在心灵完善中的作用,虽然人性败坏或颠倒,但他始终对心中的人格性禀赋(道德禀赋)抱有极大信心,不仅认为在它之上不能嫁接任何邪恶(6:27—28),而且认为我们必须假定它作为善的种子以其全部纯洁性保留下来(6:45)。原初向善禀赋的重建,并非获得一种业已丧失了的向善动机,而仅仅是建立道德法则(作为全部准则之最高根据)的纯粹性。因此,康德把它视为心灵中唯一值得惊赞的对象,认为这一惊赞是正当的,也是鼓舞心灵的。人格性禀赋具有神圣的、超感性的起源,虽然不能被人理解,但必然有振奋心灵的作用,鼓舞人心作出只有对自己义务的敬重才能要求它作出的牺牲。但人格性禀赋并不属于超自然的神力(即恩典),而恰好属于人的本性,即人自己的力量。所以,康德谈到重建时,说的是“这种凭借自己力量的运用的重建”(6:50)。显然,人格性禀赋是与恩典无关的人自己的力量。而且,即使我们承认人格性禀赋是上帝造人时赋予人的一种恩典,它也绝不是康德在此所说的协助人改恶向善的外在神力,因为它被说成是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的禀赋。既然人格性禀赋不是康德在此所谈的恩典,自然不可能构成道德自律的本体论前提。
最后,“上帝的精神”造就的属灵之人,也不是作为道德自律的本体论前提的恩典。如果脱离文本语境,在一般意义上泛论人的道德自律首先需要一个受造的属灵之人,这当然没有问题。但在人克服根本恶的问题上,却不能把这个受造的属灵之人当作协助人改恶向善的外在神力。受造的属灵之人,就像人格性禀赋一样,都属于“人”而非“神”的方面。韦政希博士会说,他并未把“上帝的精神”所造成的结果(受造的属灵之人),而是把“上帝的精神”的作用当作道德自律的本体论前提,“上帝的精神”是启示宗教中恩典之源泉,它把属灵的、无限的生命赋予我们。但前文已表明,康德并未把“上帝的精神”说成是造就了一个属灵之人,而是在说它对于人心起着鼓舞作用,促使人心完善。这种鼓舞人心的作用,与人格性禀赋鼓舞人心的作用,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在论述同一件事情。所以,即便康德把“上帝的精神”说成是自上而下地对人心起作用,也不同于历史性启示宗教所说的神的神秘启示,而是人格性禀赋自下而上的鼓舞作用的一种变换了角度的表达。
总之,在克服根本恶的问题上,需要严格把恩典限定为神从外部助人改恶向善的超自然协助,而不能把人所具有的人格性禀赋或者把具有此种禀赋的受造之人当作人“自力更新”的本体论前提,也不能泛论“道德自律”,而要严格地把它理解为人的“自力更新”。一旦我们遵守康德的恩典概念,就会发现他根本没有把无法规定的恩典当作人“自力更新”的本体论前提。至于人格性本身,由于恰好意味着重建禀赋的目标的达成,需要人自己所为,更不可能是什么本体论前提。而“上帝的精神”的作用,虽表面上不同于人格性禀赋的作用,但康德实际上认为两者殊途同归,都服从于道德宗教的真正目的,因而也不同于康德所批判的“邀恩的宗教”中的各种神秘恩典,而只能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理性的启示”,与理性宗教或纯粹道德宗教相一致。
四、启示宗教中的恩典与理性宗教中的道德自律是否和谐一致?
前文指出,康德在第一篇“总附释”末尾曾提出理性应坚守其界限,不将恩典作用(超自然协助)纳入其准则。如果在实践上使用恩典理念,其前提就自相矛盾:使用恩典理念需要预设一个告诉我们如何行善的规则,但期待恩典作用却恰好意味相反的东西。这就把道德上的善不是归于我们自己,而是归于另外一个存在者的作为,因而想不通过自己付出努力而“白白地”获得它。康德明确反对这种矛盾的做法,并将之视为“邀恩的宗教”加以批判。
第一篇“总附释”中的这些思想,贯穿在《宗教》全书之中,尤其是其余三篇的“总附释”之中。在第二篇“总附释”中,康德反对从“奇迹”意义上来理解耶稣。在他看来,只要我们揭开大众化的表象方式的神秘面纱,就会发现:“对于人们来说,除了最真挚地把道德基本法则纳入自己的意念之外,就不存在任何得救……而且,为使我们不致以迷信的方式通过不以任何思想转变为前提条件的赎罪,或者以狂热的方式通过自认为的(纯粹被动的)内心顿悟来补充这种信赖的不足,并且与建立在自身主动性之上的善的距离始终很远,除了一种良好奉行的生活方式之外,我们不应赋予这种善以任何其他的标志。”(6:83)第三篇“总附释”在论述“救赎的奥秘”时,康德认为那种神秘的上帝救赎堕落之人的观念,是与自发性相悖的,而自发性是一个人具有道德上的善恶之前提。“根据自发性,这种善如果能够被归功于它的话,就必须不是出自另一个人,而是出自他自己。”(6:143)任何“他者”,包括上帝,都不可能代替每个人自己作出善行。在第四篇“总附释”的末尾,康德明确指出:“……从蒙恩前进到德性并不是正确的道路,正确的道路毋宁是从德性前进到蒙恩。”(6:202)这是表明有两条非此即彼的道路,而康德自觉选择的是从德性到蒙恩之路,反对的是从蒙恩到德性之路。韦政希博士把恩典理念作实践运用时势必陷入的矛盾,说成是恩典与道德自律的矛盾,并认为康德在第三篇中关于宗教哲学的二律背反的解释,在理性宗教与启示宗教相统一的框架下解决了这一矛盾。在他看来,二律背反的正题代表启示宗教的恩典说,它把救赎或恩典当作上帝赐予人属灵生命的行为,反题代表理性宗教的道德自律,它把善良生活方式视为人的意志行为。但是,康德对二律背反的解释是否真的消解了恩典理念作实践运用时陷入的矛盾?这是令人怀疑的。
所谓康德宗教哲学中的二律背反,是康德在第三篇论述“教会信仰逐渐过渡到纯粹宗教信仰的独自统治,即接近上帝之国”(VII)中提出来的。康德在此提出,建立在作为经验的启示之上的历史性信仰只有局部有效性,而缺乏真正的教会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因此历史性信仰虽然能够成为一种教会信仰,但尚未是完全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纯粹宗教信仰,只有后者才能被视为普遍必然的。康德由此把真正的、唯一的教会所采纳的信仰,称为“造福于人的信仰”(6:115)。这是每个对于享受永福具有道德接受能力的个人的信仰,是纯粹的宗教信仰。而与纯粹宗教相反的,是一种“侍奉神灵的宗教”,它信奉的是一种“奴役性的”和“有报酬的”信仰(6:115)。造福于人的信仰是一种自由的、建立在纯粹心灵意念上的信仰,即道德的、高尚的信仰;奴役性的教会信仰则是不道德的,它误以为通过毫无道德价值的行动,即一个恶人由恐惧和希望所强制而能够采取的行动,就能使上帝喜悦,不像前者那样预设一种道德上的善念为必要前提。
康德接着说了造福于人的宗教包含人希望永福的两个条件:其一,是在属神的法官面前得到赎罪,这就是救赎(偿还罪孽、解脱、与上帝和解);其二,进入一种新的、符合其义务的人生,这是对自己能够在一种今后奉行的善良生活方式中使上帝喜悦的信仰。两者共同构成同一种信仰,而且必然相关。如果我们认为一个条件可以必然地从另一个条件派生而来,则要么是对我们负有的罪孽抱有信仰而产生出善良生活方式,要么是对任何时候都要奉行的生活方式的真实而积极的意念,按照道德上的作用因的方式产生出对赦免的信仰(6:116)。前者构成了正题,认为教会信仰优先于善良生活方式,首先相信上帝为我们做的事情(恩典),本质上是“因信称义”;后者构成了反题,认为善良生活方式优先于教会信仰,主张为了配享恩典而必须先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本质上是“因德称义”。
康德是在同一种造福于人的信仰内部、依据两个条件的不同结合方式(何者优先并引出另一方)来理解正题和反题,而并未把正题与反题分别当作奴役性信仰和造福于人的信仰的原则,因而并没有直接通过这一二律背反来体现历史性宗教中的奴役性信仰与纯粹道德宗教中的造福于人的信仰的根本对立。康德这样做富有深意。他固然站在理性宗教的立场上赞同反题,认为我们只能凭借自己在遵循义务方面的努力而配享恩典,但认为如果我们把正题中的信仰理解为“合理的信仰”(der rationale Glaube),则从它开始导出善良生活方式,就与从善良方式开始导致这种信仰殊途同归,没有实质区别。这要求我们把对“圣子”耶稣的信仰,与道德的理性理念相联系,并将之当作我们的行动准绳和动机。此时,在这个“神-人”的现象中,不是他落在感官中、或通过经验被认识的东西,而是我们加给他的那种蕴含在我们理性中的“原型”(道德完善性理想),才是造福于人的信仰的客体,“而这样一种信仰与一种上帝所喜悦的生活方式是一回事”(6:119)。这里并没有两个相反的原则,而仅有同一个实践理念,我们之所以由这种理念出发,要么是由于它把原型表现为存在于上帝之中并从上帝出发,要么是把原型表现为存在于我们心中,但在两种情况下它都把原型表现为我们生活方式的准绳。因此,康德认为二律背反仅仅是表面上的,它不过是把在不同关系中被看待的同一个实践理念,误解为两种不同的原则。
韦政希博士看到康德对二律背反的这一解释,由此认为康德消解了启示宗教的恩典与理性宗教的道德自律的矛盾,但他忽略了最关键的一点,这就是康德的解释是在同一种造福于人的宗教内部进行的,此时的宗教信仰,已经被康德做了理性化、道德化的诠释,不再是侍奉神灵的宗教中的奴役性信仰了。而这种侍奉神灵的宗教,在启示宗教的历史上客观存在,也是康德极力批判的对象。他的解读以偏概全,简单地把经过康德理性诠释的启示宗教等同于启示宗教,因而没有认识到同一种造福于人的信仰的两个观察角度的统一,并不意味着理性宗教中造福于人的信仰与历史上存在的侍奉圣灵的宗教中奴役性信仰的矛盾的解决。
事实上,康德在对二律背反作出上述解释之后还接着指出:如果有人把对一度出现于世的“神-人”现象的现实性的“历史信仰”,当作造福于人的信仰的条件,那就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原则,即经验性的原则和理性的原则。于是,无论从它们当中哪一项出发,都会出现“真正的准则之争”(6:120),而且任何理性都无法平息。也就是说,对耶稣的经验性-历史性的信仰,完全不同于对他的理性信仰或纯粹道德信仰。前者依然属于侍奉神灵的宗教,不属于真正的造福于人的信仰,它只是从信仰开始,但不会导出善良的生活方式。如果人们想仅仅凭借这种信仰就可以赎罪,从而把善良生活方式的决心推迟到罪孽洗清之后,就会导致心灵遭受奴役。如果这种信仰被描绘为这个样子,就好像它具有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能够从根本上造就一个“新人”,那么,它就必然被视为是直接由天国(并与历史性的信仰一起)授予和唤醒的。在此情况下,就会导致理性的“致命的跳跃”(salto mortale)。康德在此引用了保罗的话来表明上帝无条件的旨意:“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6:121)
可见,我们固然可以认为康德通过对基督信仰的特殊诠释消解宗教二律背反的矛盾,把对耶稣作为道德“原型”的信仰与善良生活方式统一起来,但却并不能认为康德由此就消解了神秘恩典与道德自律的真正矛盾。第一篇所说的矛盾,并没有在第三篇中通过康德对宗教二律背反的解释而得到解决,康德在此仅仅是认为可以对启示宗教作出理性的诠释,由此将之同纯粹道德宗教统一起来,而绝非认为任何启示宗教都是纯粹道德宗教,其恩典说都不需要加以抵制和批判。
谈到作为启示宗教的基督教,即便康德承认《圣经》包含了“最纯粹的道德上的宗教学说”(6:107),也依然认为这种学说难以同它所包含的教会规章达到和谐,因而他并未简单地接受基督教中的恩典说,而是对“圣经神学家”的恩典观念持批判态度的。韦政希博士认为康德“将奥古斯丁主义和佩拉纠主义中的积极因素都统一起来了”,似乎康德既宣扬了人的自由意志,又强调恩典对于我们的改恶向善的必要性。这不仅与康德在《宗教》一书中的论述相矛盾,而且与康德在《学科之争》中对“圣经神学家”的恩典观念的批判不一致。
在《学科之争》中,康德描述了包括奥古斯丁、路德等人在内的神学家的恩典观念:“最后,就神的诫命在我们的意志上的实施而言,“圣经神学家”确实不必指望人的本性,亦即人自己的道德能力(德性),而是必须指望恩典(一种超自然的,尽管如此同时也是道德的影响),但人也不能以别的方式,而是只能凭借一种内在地转变心灵的信仰来分享恩典,但毕竟又可以期望从恩典得到这种信仰本身。”(7:24)这就指出了圣经神学家的恩典观念的内在矛盾:他们一方面想凭借信仰来分享恩典,另一方面又把这种信仰的获得托付给恩典。在他提出的四条释经原理的第三条当中,康德指出:“行为必须被表现为从人自己对自己的道德力量的利用中产生的,不可以被表现为一个外部的、更高的、人被动地与之发生关系的作用因的影响的结果;因此,对在字面上显得包含着后者的经文的解释,就必须以有意地与前一条原理一致为基准。”(7:42—43)而在前一条即第二条中得到强调的是:在宗教中一切都取决于行为(Tun,7:42)。这些论述,都表明康德把人自己的作为视为配享恩典的前提,而并不认为恩典反过来构成人“自力更新”的所谓本体论前提。同《宗教》一样,康德在《学科之争》中也把人格性这种超感性的道德禀赋归于人的“本性”,并由此认为恩典不外乎就是“本性”,这是立足于其道德宗教而把基督教的恩典思想解释为属于人的本性的东西,于是,基督教中的神秘恩典说就在其理性的诠释中达到了与其纯粹道德宗教的一致。
五、结语
通过上述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韦政希博士夸大了恩典作用,过分强调了恩典与道德自律、启示宗教与理性宗教的一致性,忽略了康德对“邀宠的宗教”或“侍奉神灵的宗教”及其神秘恩典说的严厉批评,对启示宗教概念也存在误解。他把康德仅指一种必要假设的超验恩典概念解读为一个指称实在神力的恩典概念,从一开始就背离了康德的恩典思想,在夸大恩典作用时把外在恩典所促成的人心革命,错误地当成人逐渐改良的本体论前提,进而不适当地把恩典与道德自律说成是互为前提的,并在互为前提的意义上将两者刻画为没有矛盾的。韦政希博士认为康德对宗教二律背反的解释消解了恩典与道德自律的矛盾,是由于他没有看出其正题和反题都属于纯粹道德宗教的造福于人的信仰,因而有别于侍奉神灵的宗教的奴役性的信仰,因而也就未能认识到正题与反题的和解,并不代表康德本人所赞同的造福于人的信仰同一切奴役性信仰的尖锐对立的消解,由此忽视了康德在《宗教》全书中对以狂热、迷信、顿悟、魔术等为特征的神秘恩典说的全面批判和清算,看不到康德同奥古斯丁、路德等圣经神学家的根本对立。
注释:
① 本文引用的康德原文,主要出自《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部分引自《学科之争》,引文主要采用李秋零先生的译本,见其主编的《康德著作全集》第6 卷和第7 卷,部分引文中的术语有微调,如heilig 统一译为“神圣的”。正文括号中标记的数字,是皇家科学院《康德全集》的卷数和引文所在页码。
② 笔者曾就此与韦政希博士交流,他承认这就是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