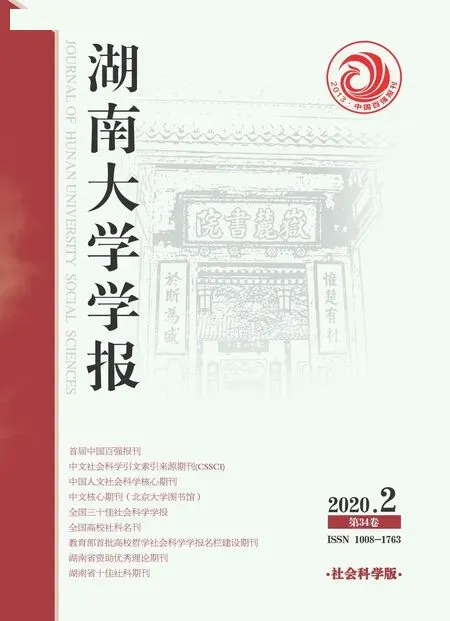中国奁产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当代价值*
谢 蔚
(湘潭大学 法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从古至今,陪赠嫁妆与给付彩礼一直是我国较为普遍的婚嫁习俗。并且随着社会分工逐渐明确、经济的不断发展、男女平权等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加之独生子女适婚年龄的到来,女方家庭提供的嫁妆数额有逐年提升的趋势,这种趋势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尤为明显[1],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以及关于婚约财产的实务纠纷。而严格来讲,婚约财产是男女双方及其亲属因婚姻而赠与男女双方或双方亲属的财产[2],应当包括通常我们所说的“ 嫁妆”和“ 彩礼”。但我国关于婚约财产之规范,只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中对“ 彩礼”的返还作出相对完备的解释,并未明确规定嫁妆的归属,学说也缺乏对嫁妆引发的法律问题的探讨。而在考察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关于嫁妆的纠纷时,嫁妆因婚姻关系解除后的返还、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女方原生家庭赠与财产的权利归属等问题普遍存在于司法判例的争议焦点当中。也从实践中反映出与“ 彩礼”具有同等历史传统的“ 嫁妆”婚俗亟需实证法之规范。因而需要转变角度,从中国传统的奁产制度(嫁妆)的历史发展、社会伦理基础的变化等角度来了解嫁妆这一婚俗现象存在的历史文化基奠、其在现代社会存在的规范价值以及它在民法典中的应然构建。
一 奁产制度之源起
(一)作为古代“ 婚意”成就要素之奁产
中国古代的嫁妆又称“ 奁产”“ 妆奁”。“ 奁”最早写作“ 籨 ”,按照《说文解字》中的解释 :“ 鏡籢也,俗做奁……盛香器也 ”,原指古代女子的梳妆盒,后引申为女子嫁妆之意。奁产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奴隶主贵族女子的媵婚,并随着聘娶婚的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婚嫁习俗。媵,陪送也,媵婚始于商代,盛于春秋,是奴隶贵族间的婚姻现象,诸侯女子的婚嫁须陪送一定的媵妾、媵臣及媵器。[3]媵婚在众多史书中都有记载,早期的媵婚甚至不仅涉及财产关系,例如《吕氏春秋》记载商之开国重臣伊尹是作为媵臣陪嫁于汤[4]。《诗经》中也有描绘西周分封韩之国君娶妻之盛况,韩侯到未来岳父的封地迎亲,多辆四马八銮的车辆熙熙攘攘,女方陪嫁之媵妾也多不胜数[5]。
随着西周、春秋时期的聘娶婚制度出现,原只出现于贵族婚嫁习俗中的奁产、聘礼渐渐普及于庶民。《周礼·地官·媒氏》记载 :“ 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 ”、“ 天子加以大璋,诸侯加以谷圭,庶人则用缁帛”[6],即娶妻所付的聘礼规格统一为彩丝五两,天子另外加上玉璋,诸侯加上车马和玉圭,平民则可用黑色布衣替代。《诗经·卫风·氓》中“ 以尔车来,以我贿迁”也是对嫁妆这一婚俗的描绘,诗里提及的“ 贿 ”,即有奁产的意思。在娶聘婚制度中,是否具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聘财妆奁决定了婚姻是否成就。其中,聘财即 “ 六礼”中的纳征,是古时婚约成立的标志。收受聘礼前,男女双方要谨守“ 男女大防”;收受聘礼后,对外男女双方已经可以以夫妻名义行事。妆奁与聘财虽均为婚约财产,但相较于聘财这一婚姻缔结必备礼仪,奁产则仍是作为一般化的民间习俗而存在,具体的出资额度则由娘家自由把握。
(二)宗族家长制下奁产与夫家财产之混同
秦汉时期,原专属于贵族间的奢靡婚嫁之风,由于上行下效,使得婚礼重财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风俗。婚姻重功利的现象则不再是贵族或是富者专有,平民阶层也有了重妆奁的风气。考察汉代婚嫁的史料,其中厚嫁女重聘财的记载屡见不鲜。如《盐铁论·国病》中写道汉代无论贫富在“ 厚嫁女”上都存在攀比心理,为女备嫁使得富人破产,穷人更是为此生计艰难[7];又如《史记·司马相如传》记载卓文君的嫁妆包括了百名侍者、“ 百万钱”以及一应衣被财物,她因出嫁所带走的家产规格甚至等同于家中男子的家产分成比例。
因婚约财礼的数额愈大,奁产的归属成为了婚姻家庭财产中的重要的问题。一方面,自春秋以来儒学家们建立的礼法强调宗法制,即“ 宗族一体”“ 家长制统治”“ 同居共财”。这些理念表现在儒学典籍《礼记》中有 :“ 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8]、“ 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妇或赐之饮食、衣服、布帛、佩帨、茞兰,则受而献诸舅姑 。”[9]作为“ 子妇”即儿媳,既不能拥有个人财产,也无权自由支配家中财物,取得的“ 赐之之物”也要“ 献诸舅姑 ”,即公婆。《张家山汉墓竹简》中也有记载“ 女子为户毋后而出嫁者,令夫以妻田宅盈其田宅。 ”,即女子作为户主出嫁后其田地纳入夫家田宅中。另一方面,实践也有将女子嫁妆区别于子孙别产的“ 私货 ”,视妇女嫁妆独立于家产的惯例,秦简有间接的判例得以佐证: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有“ ‘夫有罪,妻先告,不收。’妻媵臣妾、衣器当收不当?不当收 。”[10]强调了妻子的陪嫁媵臣妾衣器的所有权的独特性,在没罚家产时不同于夫家财产,不用被官府收走。汉代关于“ 弃妻,畀之其财 。”[11]也从侧面佐证了奁产属于妻子私产,相对独立于家产。此外,还有女子利用嫁妆补贴生活,孝顺舅姑,资助夫家的事例,也体现了女性具有一定的奁产支配权。由此可见,秦汉时期家长制下“ 共财”与“ 异财”的矛盾已初见端倪,但是这一时期主要还是以宗族式大家庭同居共财为主,女子因婚嫁带入夫家的奁产并入夫家家产,仅拥有有限的所有权,在“ 离婚分家”时允许其带走。
二 奁产制度之演进
(一)独立于夫家家族财产的奁产初现
魏晋至唐初期,在嫁娶上继承了前代重妆奁聘金的习俗,甚至盛行起了财婚。赵翼在《廿二史劄记·财婚》中指出 :“ 魏、齐之时,婚嫁多以财币相尚,盖其始高门与卑族为婚,利其所有,财贿纷遗,其后遂成风俗,凡婚嫁无不以财币为事,争多竞少,括不为怪也 。”[12]到了唐代中后期,因科举制发展,承自魏晋时期的门第观念受到冲击,“ 当门第失去了它在婚姻交易中的分量时,嫁妆就自然成了婚姻组合中的一个重要环节[13]。”再加上“ 才子佳人”婚恋观的兴起,出于与新兴贵族(因科举制获得官职的士子)联姻的需求,对嫁妆的重视从上至下影响了唐代社会的婚恋观念。自此家族中有未婚女子则往往会为其准备上丰厚的嫁妆,甚至有家族族规对族内适婚女子的嫁妆数额进行规定,如“ 凡男女婚嫁之礼,(男)言定后用钏子一对,绯绿彩两段,下饷钱五贯……女则银十两,钱三贯 。”[14]重嫁妆之风盛起之下,未婚女性从家族分得确定的财产作为奁产甚至渐渐作为律令被固定下来。《开元令·户令》规定 :“ 兄弟亡者,子承父分(继绝亦同)。兄弟俱亡,则诸子均分。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姑姊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 。”[15]这在保障女性奁产权的同时也进一步激化了前朝关于同居共财及别居异财的矛盾。一方面,唐代仍然禁止女性“ 蓄私财 ”,《唐律》中以“ 七出”中“ 盗窃”[16]限制女子财产权。社会上也极为推崇“ 夫妻一体”的婚姻观念,鼓励女性将财产贡献于夫家。《太平广记·费子玉》中有记载的“ 唐天年间,犍为参军费子玉死后见到妻子,妻子要他还钱,子玉云 :“ 夫用妇钱,义无还理”[17]。另一方面,唐代律法上也有将奁产独立于家产的规定。《唐律疏议·户婚》中“ 诸应分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妻虽亡没,所有资财及奴婢,妻家并不得追理 。”[18]直接规定妻子娘家所得独立于家族财产,分家时不分这部分财产。且唐仍延续了“ 弃妻,畀之其财”的规定,即婚姻关系结束后,女子可以带走自己的陪嫁,甚至唐代还有休妻时给与一定赡养费的案例。[19]
(二)大家族制瓦解背景下女性奁产支配权之强化
宋朝沿袭了唐关于奁产的一系列规定并进一步细化。宋朝时也有立法保障未嫁女的奁产期待权。《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记载:“ 未嫁均给有定法。诸分财产,未娶者与聘财,姑姊妹在室及归宗者给嫁资,未及嫁者则别给财产,不得过嫁资之数 ”、“ 在法,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20]。宋朝由于宗族式家族合居逐渐瓦解,小家族制逐渐成为社会家庭制度主流,奁产的归属也成为分家时的焦点。一方面《宋刑统》延续了“ 妻家之财不在分限 ”,且宋代对奁田的过户手续以及税收进行了详细规定以明确妇女的田产嫁妆即奁田的归属。宋徽宗有敕令 :“ 凡民有遗嘱并嫁女,承书令输钱给印文凭 。”[21]宋朝时还出现了一众妇女持有其奁产,并以自己名义典卖奁产的记载。[22]另一方面,《宋史·食货志》中也有记载 :“ 女适人,以奁钱置产,仍以夫为户 。”由此可见,自唐宋时起律法及社会文化上更强调“ 夫妻一体”而非家长制下的“ 同居共财 ”,奁产由“ 献诸舅姑”转变成“ 以夫为户 ”,从家长支配下的家产中分离出来,成为了夫妻间特有财产,约定俗成由妻子支配。
明清时期继承了前朝“ 厚于嫁女”的风俗,尤其明朝时商品经济发展,获得一定财富的商人往往企图通过联姻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23],这进一步影响了社会风气,至清时嫁女陪产之风愈发攀比,中产之家也耗费大半家产,家境更差的家庭甚至要典卖产业。[24]这一时期,一方面女性从家族所获奁产愈多,且婚后对奁产的处分权也有所提升。明清小说以及一些史稿中多有女性自持奁产不用于家用,女性在遗嘱中分配自己的奁产等事例。可见这一时期,家庭观念更盛,但女性在家族内部的地位也有所提升。
随着中国婚礼重财风俗的发展,女子出嫁拥有一定妆奁的权利被立法得以确定。唐以前,虽常见描述厚嫁之风的史料,但受限于较低的女性地位以及门当户对婚恋观的影响,通常不发生阶层流动,不同阶层间也不通婚,在婚礼彩礼方面的社会矛盾尚不十分尖锐。唐朝科举制的进一步完善,历经了世族门阀的衰落与寒门士子的崛起,推动了世家与寒门的联姻,重嫁妆的风气盛起,再加上唐代女性地位上升,为减少“ 失婚”现象,立法者规定了女子有分原家之产而作为嫁妆的权利。这也是宗法制下大家庭逐渐转变为小家庭的表现。奁产所有权也从封建家庭中家长所支配的财产之一转变为小家庭中夫妻间财产,并在风俗上一般由妻子支配。宗法制的大家庭虽渐渐瓦解,但中国长期处于封闭的小农经济,宗法社会相对稳定,这一变化过程相对缓慢,具有家长权的封建小家庭长期存在。
三 近代西方法律思想的引入对奁产制度的冲击
(一)清末民初立法进程中对传统奁产制度的摒弃
清末在编纂《大清民律草案》之初, 参与编纂的大臣们均主张以民事习惯调查作为该草案制定的基础, 并希望尽量将本国民事习惯归纳、吸收入成文法,以此来保障该草案颁行以后能够适应我国社会的需要。而后,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也确实进行了大量的民间习惯调查工作,但在当时的立法条件下,却难以将之成文化。[25]因此宣统三年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中几乎没有看到本国民事习惯对其产生了何种影响。不仅未对传统奁产制度进行规定,甚至连整个婚约制度都未涉及。之后北洋政府制定的《民国民律草案》则尊重了我国关于婚约聘财等习惯,规定定婚因交换婚书或已纳聘财而生效力。但南京国民政府于1930年施行的《中华民国民法》又再次摒弃了我国传统的奁产聘财制度,转而接受西方的婚姻契约理论,明确排除了婚约财产在法律上具有强制履行力,仅仅规定婚约解除时无过失方可以向过失方请求赔偿。[26]
(二)奁产制度被西方婚姻契约财产制所吸收
而后,由于西方法律思想引入中国,民国开始一系列妇女解放运动,妇女权利意识得以觉醒,传统家庭模式中的男尊女卑的观念受到冲击,夫妻间平等观念得到传播。虽农村内地传统宗族势力仍存在,但在较开放的城市,接受新思潮的知识分子等青年人开始批判传统婚姻制度,探索新的理想家庭模式。国民政府《民法亲属编》中规定了联合财产制、共同财产制、统一财产制、分别财产制四大类财产制,其中法定财产制为联合财产制。在联合财产制中,奁产不属于特有产[27],规定其作为妻原有财产由夫代为管理,但丈夫无处分权,且负有报告其状况的义务;共同财产制中则规定,妻子的财物,除奁产等特有产外,均转移于夫,妻只有固定价额之返还请求权;分别财产制则无特有产设置,但直接保留了女子对奁产的所有权、管理权及使用收益权。[28]没有了家长权约束下的婚姻制度,随着夫对于妻身份上的支配力减弱,夫对于妻之财产上的支配力亦随之减弱,四种财产制对女性财产权约束力不相同,但都最低限度承认女性拥有一定的财产权,即允许妻子保留嫁妆这一特有产。自此,提倡宗族家长制的封建伦理秩序逐渐崩溃,男女平权这一价值导向渐渐取代了自然法中的伦理秩序成为新的主导婚姻法的价值,主要表现为在婚姻中个人主义兴起,家长制及夫妻间不平等被废除。这点表现在家庭财产领域即立法上保障了女性对其陪嫁的奁产的权利,确定了女性相对独立的财产地位。
社会变革,旧有的家庭伦理制度崩溃后,家庭法主导价值转向了人权和基本权利。[29]这一背景下,家庭法开始承认女性的独立地位,倡导男女平等,反映在家庭财产领域即确定减弱甚至取消丈夫对妻子财产的支配权,在夫妻共同财产上也强调夫妻双方平等地享有所有权与处分权。奁产作为女性的婚前财产成为妻子个人财产,奁产制度融入现代婚约财产制度当中。
四 我国现行嫁妆法律规制之评述
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受前苏联法律之影响,废除了我国传统的婚约聘财、奁产制度,规定“ 禁止任何人藉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 ”,聘财、奁产都被斥为“ 封建陋习 ”,而到70年代又将批判的角度从“ 封建陋习”转向为“ 剥削阶级的旧习俗”。[26]1980年《婚姻法》及2001年的《〈婚姻法〉修正案》均保留了“ 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规定,但修正案细化了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规定,区分了夫妻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也正是夫妻间个人财产的承认使得女方对嫁妆的所有权主张有了可适用之余地。2004年的《〈婚姻法〉解释二》第22条规定 :“ 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 。”2011年,最高法院又发布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该解释第7条规定 :“ 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
按照以上之规范,赠与嫁妆如若为原生家庭在婚姻登记之前所为,则当属女方个人之财产,对于此,不管是理论还是实务当中皆无甚争议。如果赠与嫁妆为婚姻登记之后所为,相关司法解释则只回应了关于不动产赠与的争议。2004年的《〈婚姻法〉解释二》第22条这一司法解释的出台无疑是对婚约财产制度进行规范的一大进步,但划分标准过于绝对。按照我国婚姻成立时间的确定原则,婚前婚后的界限当以婚姻登记的时间为准,而民间习惯中却往往以婚礼庆典的时间为准,以此来推断赠与方(父母)是对一方还是双方赠与的意思表示却有不妥之处。再者,婚姻关系确定之后可能因工作调动、新添人丁等因素再进行购房置物之事也是常态,所以该司法解释显然没能解决好诸如婚后购房之类的现实问题。因此,2011年,最高法院又发布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该解释第7条进一步对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的不动产赠与以产权登记为判断标准进行推定,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视为仅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双方父母都进行了出资,而产权只登记在一人名下的,视为子女按各自父母出资比例按份共有。关于原生家庭对子女的不动产赠与似乎已经规定的较为完备,但对一些动产的赠与却没有加以规定,特别是像汽车、不属于不动产登记范围的“ 车库、车位”以及名贵珠宝首饰等其他贵重物品,都是原生家庭特别是女方亲属对女子进行赠与的常见类型。这些都未被法律或司法解释所规定,目前我们只能类推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22条,但此条司法解释前述之弊端在动产之适用时更为突出。
五 民法典时代“ 嫁妆”制度之立法反思
“ 法律规范的存在在于其效力;而法律规范的效力,虽然并不等于某些事实,但却是以这些事实为条件的 。”[30]我们在考虑重构“ 嫁妆”制度之时,必然是考虑到嫁妆问题仍是实践中大量存在并将长期存在的婚俗现象,即有其存在之必要性。现代女方原生家庭之赠与很多时候都不会以陪赠“ 嫁妆”之名或者以赠与“ 女方特有产”之名而为之。较为常见的是男方以“ 彩礼”之名对女方父母及(或)女方家庭的其他亲属进行婚前赠与之后,女方家庭再全额或者从中抽出部分甚至有的会再额外添加一部分作为“ 嫁妆”赠与女方或者新人夫妻双方。现今城市居民大多为独生子女家庭,一般鲜见女方家庭索要纯粹作为自己养育女儿的补偿的所谓“ 彩礼”;但在农村地区,特别是多子女家庭,给付作为对女方原家庭纯粹的经济补偿性质的“ 彩礼”尤为常见[31]。
纵观我国嫁妆(奁产)制度的历史演进,设立嫁妆原初之目的更多地是对不享有分家析产之权的女性以一定的财产补偿,或者换言之,为古代继承权之代偿;再者是通过保护女子对嫁妆的所有权,来保障女子在夫家的家庭地位以及避免女子因婚姻关系的解除而生计艰难。我国现有的嫁妆婚俗已经大致剥离了继承权代偿之目的(功能),因为我国《继承法》明确了男女之间享有平等之继承权,但很多时候会因为父母通过遗嘱排除了出嫁女子的继承权而使该功能又时而“ 复辟”。因此,不管是中国古代的奁产制度,还是当代的嫁妆婚俗,其主要之规范目的仍为保护女性在婚姻关系解除或因遗嘱被剥夺继承权时的财产权利,以保障女性的生存权益。除此之外,嫁妆在新时代又具备了其一些新的目的,即对婚姻关系持续期间的家庭的一种经济支持。但对于嫁妆及彩礼等婚约财产制度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一、二、三审稿当中都未体现。
按照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人大法工委的答复,《民法典》完整稿应当会在今年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进行审议。但《民法典》正式施行之后,原有的司法解释是否继续有效,还是规定仅与新的《民法典》相冲突的司法解释才无效,官方并未明确。仅通过《民法总则》第10条规定之习惯渊源来调整普遍存在的嫁妆婚俗必然收效甚微[32]。鉴于此,《民法典》有必要回应包括嫁妆和彩礼在内的婚约财产问题,除了应当保留《〈婚姻法〉解释二》第22条以及《〈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7条之规定,还应该把动产嫁妆纳入规范之中,并且按照原生家庭赠与子女财产的时间以及赠与财产的类别进行分类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