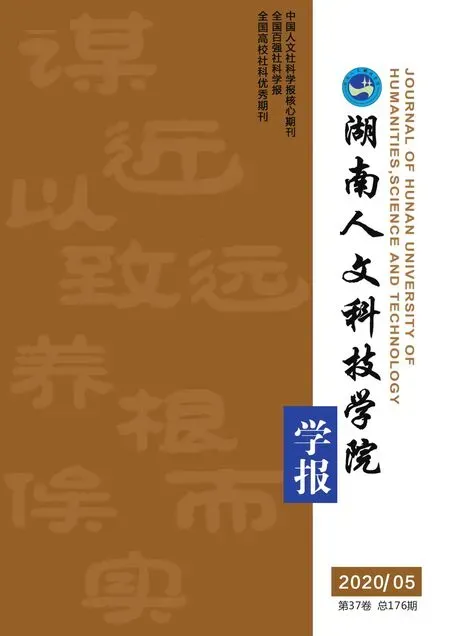论实事求是之“是”的求真、真理与创新之维
文 祥
(湖南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
人们常常将“真理”理解为对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认识,以为一旦发现了真理就获得了自由,也就可以一劳永逸地照章办事了。其实,这是对真理的极大误解,是我们过去常常走向机械、僵化、教条主义的根本原因。这样的“真理”顶多只是接近自然领域里的规律而已,如牛顿力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与牛顿三定律所揭示的物理世界,与有没有人类的存在是没有关联性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人类还没有产生之前,以及在人类对自然认识由浅到深的不同阶段上,自然界里的物体运动都是始终如一地遵循着牛顿力学所揭示的规律来运动的。而在社会、人事领域则根本不存在这种所谓的“铁律”,因为人已经成为社会、人事变化过程中的自变量因素,社会、人事本身将随着人对社会、人事认识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从根本上来讲是不同于自然界领域里的规律的。这一点,如果我们从非还原论的观点来看就不难理解了。
另外,“真理”永远都不具备静止在那里等待着谁去发现的实体性,而是此事物之为此事物、彼事物之为彼事物时各事物之间以及与关联着的周围世界的相应关系。用我们熟悉的方式来说,即“真理”就是“实事求是”之“是”,是各事物之间以及与周围世界之间的关联。而此关联状态下,此事物之为此事物、彼事物之为彼事物就表示事物之“是”,此时就是事物相应的“真”之状态,我们对于“真”之状态下事物间相应关系的寻求过程就是“求真”的过程,而所求得的“真”之状态下事物间的相应关系就是我们所谓的“真理”,只有把握了“真理”才有可能在现实中驾驭事物实现创新性发展,也才有可能在实践的检验中合规律地把事情办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实事求是”的全部含义。由此可知,“求是”实质上涵盖着“求真”“真理”与“创新”三个维度,是统摄着“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大全”世界的。
一、求“是”、求“真”与“此在”
“真”之状态就是事物之所“是”之时的处境,而把握什么是“是”,是我们澄清本文所论问题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而之后对“是”时事物的“此在”之理解,也就可以直指事物之“真理”了。
首先,我们知道,世间万事万物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而如何把握不断流变着的事物,从而能够恰当地应对好流变着的事物,使得人们因而处于主动的、自由的状态,这是人们永恒追求的境界。人们对于各种流变着的事物的正确把握之时,其实就是求到“实事求是”之“是”的时候。
然而,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就要对“实事求是”之“是”有一个正确且深刻的理解,而西方哲学中对于“是”的探索有助于告诉我们什么是“实事求是”之“是”。汉语中的“是”字,是一个会意字:表示太阳在上,手在中间,脚在下面。在《说文》中的本义为:直,正。若从抽象的角度来理解,就有我们人对事物的理解与事物本身正好相符之意,也即“形而上”刚好可以罩住“形而下”,这恰与西方哲学两千多年来探讨“是”(being)的宗旨具有一致性。遗憾的是,我国古人虽已提出“是”之要义,但后人却对其缺乏系统的探索,而西方哲学中对此问题持久的探索早已思想成果丰硕。我们若能将上述二者贯通,那么西方哲学家们两千多年来对于“是”的探索成果则直接就可以为我所用了。由于“是”是整个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而对什么是“是”多以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揭示得最为深刻,所以有必要了解他对“是”的揭示。不过,国内重要的相关译著都将其译为“存在”。
王路教授在《读不懂的西方哲学》中认为,“being”应该译为“是”,而国内将其译为“存在”存在问题,人们之所以读不懂西方哲学,很大程度上与将“being”译为“存在”有关[1]。但是,如果都译成“是”,也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因为“是”在某些语境中的确又要取“存在”的意思。由于长期以来“being”被译为“存在”已经广为人知,为避免增加新的误解,也就尊重译作,仅强调一下:所译海德格尔名著《存在与时间》中的“存在”就是“being”一词,也即是“是”。海氏该著作的晦涩难懂是出了名的,但该著作思想深邃、影响深远。据他指引,若要弄清楚这个“是”是什么意思,有必要回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相关思想上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追问“是”其实就是追问“实体是什么”中的“是”是什么。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逐步澄清三个问题:第一,实体(指研究对象)是什么;第二,为什么是它;第三,如何是它,也即它是如何生成的。这三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理解“是”。也就是说,要理解“是”是什么,其实就是要理解“实体是什么”中的“是”是什么。为了便于理解,下面以锤子为例来分析和理解何为“是”。
如果指着静止的锤子追问上述的第一个问题:锤子是什么?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显然要先回答亚里士多德的第二个问题,“它为什么是锤子”的问题。而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又要先回答第三个问题,“它如何是锤子”的问题。要回答第三个问题就容易了。只要挥动着“它”在“捶打”钉子的过程中,“它”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锤子”了。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它”才“是”锤子。换言之,“锤子”只有在“捶”钉子的过程当中,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锤子”。在第三个问题得到了解答之后,第二个问题便迎刃而解:“因为它正在捶打钉子,所以它是锤子”。再进一步,第一个问题同样得到回答:“锤子就是正在捶钉子的东西”。由此可见,实体“合目的性”的发挥功能之时才“是”它本身,此时的状态就是它的“真”之状态,此时的“锤子”才真正的是“锤子”。由此可见,“是”就是对此事物之为此事物、彼事物之为彼事物的内在规定性的本质把握。也就是“形而上”的精神对“形而下”事物的本质把握。
其次,在明白了“是”时的“形而下”事物即被认为是“真”的之后,理解海德格尔的“此在”就可以直逼我们对“真理”的理解了。仍然继续上面锤子的例子。当某人“挥动锤子捶打木板上的钉子”时,锤子所“是”之时的关系性存在就是锤子的“真理”。此时的“锤子”与“挥动者”一起指向“木板上的钉子”,“锤子”是嵌入在“挥动者”与“木板上的钉子”这条意向弧中间的。此时的“锤子”绝不是孤立的存在者,而是一种动态的关系性存在,此时此状下的锤子,海德格尔称之为“此在”。“此在”当然是存在者,但并不仅仅是无数存在者之中的一种存在者那么简单。从逻辑层次上来看,“此在”这种存在者与通常所谓的存在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个存在者在它的存在中与这个存在本身发生交涉。”[2]14
也就是说,这个存在者之所以是“它”,是由于我们对它之“是它”已经有所领会了,这个“它”与“是它”已经发生关联。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此在总已经出自某种‘为何之故’把自己指引到一种因缘的‘何所缘’那里,这就是说,只要此在存在,它就总已经让存在者作为上到手头的东西来照面。此在以自我指引的样式先行领会自身;而此在在其中领会自身的‘何所在’,就是先行让存在者向之照面的‘何所向’。作为让存在者以因缘存在方式来照面的‘何所向’,自我指引着的领会的‘何所在’,就是世界现象。而此在向之指引自身的‘何所向’的结构,也就是构成世界之为世界的东西。”[2]101
简言之,“此在”并不是简单孤立的“存在者”,而是与周围世界有着各种因缘关联的存在者,并具有时间上指向未来的和空间上指向他处的意蕴。为了便于理解,不妨以“木匠正挥动锤子在捶打钉子”的这一情景为例来进行分析。这个时候,木匠没有刻意想着“锤子”,而是他的手拿着锤子“正在捶打着”木板上的“钉子”,脑子里面只想着“把钉子捶进木板”。将此时的“意向弧”描述出来就是:“锤子”在木匠手中正与他“一道指向”“木板上的钉子”。现在来分析该“意向弧”的“意向性结构”:“在木匠正捶打着的手中”就是锤子的“何所在”;“指向木板上的钉子”就是锤子的“何所向”;“为了捶打木板上的钉子”就回答了“木匠挥动着的锤子”的“为何之故”;“被木匠挥动着的锤子”处在“挥动着锤子的木匠”和“指向木板上的钉子”这样一条意向弧当中,回答的正是“处在某种因缘存在方式当中的锤子”的“何所缘”;而“一道指向”这一“何所向”的结构将“被挥动着的锤子”“挥动锤子的木匠”与“木板上的钉子”这三者勾连了起来,构成了一个世界整体,此处“一道指向”的结构就是构成“锤子”之为“此在”的东西。这是我们以“木匠捶打木板上的钉子”的“意向弧”为例,对“此在”内在的意向性结构进行的分析。显然,“此在”是具有“意向弧”的一种关系性存在的主体,它与周围事物具有复杂的关联。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对“此在”的理解较之对“是”的理解更为复杂,因为对“此在”的理解是建立在对“是”的理解之上的。“此在”所指任何事物就是“是”其自身之时的“真”之状态下的关系性存在的主体,而“真理”正是“此在”之事物所关联着的各种相应关系。对“此在”的深刻理解无疑最有助于我们直逼对“真理”本质的把握。虽然实际生活中的事物比上面锤子的例子更为复杂,但人总是要先学会爬和走然后才学会跑的,对简单例子中“此在”的理解是我们进一步把握复杂事物之“此在”的基础和方法途径,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达至对复杂事物的“此在”的领会和“此在”状态下之“真理”的本质把握。
二、求真、真理与创新
接下来,我们开始探讨“求真”“真理”与“创新”的关系。“求真”是人类思维活动领域的事情,主要体现为一种精神活动,其目的在于把握到“真理”,而“创新”一定是将在思维活动中所把握到的“真理”推向未来的“可能现实的现实”[3]26,也即将其实现出来,或者是在生产实践当中制造出来,或者是将新的思想记录(包括各种传播记录方式,甚至口授)下来,或者直接以行为的方式处理随后可能发生的事情,等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外化”出来,或说“现实化”。人们在求真过程中对“真理”的把握之际往往就是“创新”可能实现之时。无疑,“求真”乃是求得“真理”的先在行为,更是实现自觉“创新”的先决条件。
由于世间万事万物总是在不断地流变着,时空不同,事物之所“是”也就不同,“真”之状态也随之变化。此时“此在”之事物所关联着的各种关系性存在即“真理”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因此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真理”静止地在那里等待着人们去发现,“真理”一定是变动不居的。当然这就是我们对熟悉而难以把握的所谓“辩证法”的理解了。而辩证法大师黑格尔之所以将哲学定位为“关于真理的科学”的深刻性也就在这里。诚如孙正聿指出的,黑格尔的哲学“为当代哲学重新理解‘哲学’及其所追求的‘真理’提供了具有哲学史意义的‘思想地平’”[4]。
正因如此,“求真”才那么难,求得“真理”才成为人类永恒的追求。而对“真理”的把握之不易,也就说明了人们“创新”之艰难。然而,在此求索之路上,若能深刻领会“存在先于本质”这句存在主义的口号,也许有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到事物的不断流变及其各种关联,从而有利于我们更加自觉地解除思维上的既有束缚,最终实现不断创新的目的。
为了实现创新目的,首先,需要认识清楚的是,“创新”是在原有基础上的重新组合或新的发现,且不管何种具体创新对象,总是一定满足两个特性:一是所开创出来的东西是原来没有的,不管是实物还是思想;二是所开创出来的东西一定要合乎未来事物自身的本性。一方面,若对于实物来讲,创新就是创造,就是发明,其特性比较容易理解。如手机的发明,在发明它之前所应具备的观念、技术、材料等条件都已成熟,就缺在实践当中将那些既有要素重新组合后付诸实践了。在现实地组合出第一部手机之前就没有手机,但是“潜在”的手机已经存在了,也即一种“可能现实”的“手机”只差变成现实的手机了,这是特性一。当然所发明的手机一定要符合物理学的各项原理,且手机要符合人们对它特定的目的要求,也就是一定要符合手机这一事物“可移动”“方便拿在手上”的本性,此乃特性二。只有这样,手机才能在后来的组合实践当中实现出来。
相反,如永动机,的确是过去所没有的,符合特性一,但由于不符合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违反了现实事物的本性,也不满足特性二,所以纵然是人们所欲求的,也无法被发明创造出来。再如屠龙刀,也许符合屠龙的原理上的要求,但由于人们并无对它的需求,因此也不会被发明创造出来。由于“屠龙刀”是思想虚构的一个概念,不是“可能现实”,因而将来也不存在实现的可能,因此它也不是“创新”,特性一与特性二也就都不满足。由此可以说,任何发明创造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特定的目的需求,且现实地制造出了过去所没有的东西。
另一方面,对于非实物形态的思想来讲,“创新”就是“发现”,其所需满足的两个特性相对较难理解。但我们举例说明可以有助于理解。例如毛泽东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原有理论基础上的创新。不管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话,但是毛泽东说了。说这是创新,是因为当时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及其所率领的部队有先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生存下来的需要,它满足特性一,而后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事实说明了它符合中国革命实践的本质要求,这满足了特性二。
其次,“创新”之为“创新”的确需要后来的实践来证实,但根本要求还是我们在求“是”的过程中,对既有事物“是”时“真”之状态的深刻理解和对相关“真理”的把握。如为什么毛泽东说了老祖宗没说的话就是“创新”,而其他一些人也说了些新话就不是“创新”了呢?我们知道,后来的历史事实证实了毛泽东的话是“创新”的,而其他人的很多话就不是“创新”的。“创新”之为“创新”需要后来实践的证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是马克思主义颠扑不破的真理。
然而,这里确实存在一个理论创新与实践检验之先后的问题,实践检验对于理论创新有点像“事后诸葛亮”,如果肤浅一点理解,似乎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逻辑。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如果是单个人的单打独斗,则与个人既有力量的强弱程度关系极大,也就是说胜负是由偶然性因素决定的,但群体性甚至全民性的革命则完全不是由单个人的既有力量这类偶然性因素所决定的。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远远不是一朝一夕取得的。它需要在把握事物运动变化之“是”的基础上,先在地把握事物未来发展变化之趋势,进而在宏大的革命实践当中调动各项因素进行重新组合,从而才创立了“新”的理论。
如果毛泽东没有对我国当时社会各阶级状况的深入分析和农民运动的广泛了解与调查,就无法把握到我国当时革命运动之“是”,当然也就无法重新组合出在“农村扎根”的创新性思想。也就是说,如果毛泽东没有对我国当时社会各阶级状况、农民运动等实践的了解,就不会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理论上的“创新”。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可见,在“创新性”的思维活动中,历史事实在两个维度上出场,一个是事后实践的检验,那个实践与理论是一种外在性关系,另一个是事前实践要素的重新组合,这个实践与理论是一种内在性关系。而在整个“创新性”的实践活动中,内在性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跳出肤浅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地看问题的逻辑,从而走向更加深入地对事物进行内在性分析的路径。
第三,对既有事物的内在性分析才是最为根本的让“创新”这种“可能现实”变成现实的实现之路。内在性分析就是逻辑分析,也就是哲学分析中的本体论研究。不难理解,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其自身的逻辑,此事物之为此事物、彼事物之为彼事物就是由于形而上的某事物能够准确指称形而下的该事物实体(即本体),当某事物之为该事物就表示它是其所是,而这需要深入追问到某事物是否已是该事物的“是”之本体论层面。我们对不断变化的某事物的这种理性把握建立在对该事物发展逻辑的领会之上,是对其进行哲学思维的结果。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事物本体在现实时空中的不断生成,或者说都是事物发展的自身逻辑在现实时空中的展开。
用金岳霖的话来说就是,逻辑是可能的现实,现实却是可能现实的实现,也即现实就是逻辑的实现或本体现实化后的现实[3]26。这种哲学分析无疑是非常深刻和重要的,但却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缺乏的,诚如冯友兰强调的,改造中国学术必须大量吸收西方哲学中这种“正的方法”的养分。当我们达到了对事物本体之“是”的领会后,若以文本的形式来表述“是”,其实就表示“求”到了事物的“真”之状态下事物间所关联到的各种要素之整体的“真理”,而将此理性把握到的事物动态变化之脉搏用理论的语言表达出来,就是“创新性的”思想,之后在社会实践当中随着此事物自身逻辑的展开而不断生成,也即事物在可能现实的现实化中不断地变成了现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真理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很明显,没有深入的内在性分析就不可能把握到事物之“是”,当然就无法窥视到其中的“真理”,“创新”也就无从谈起。
三、为什么要论“是”
承上所论,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若能自觉把握到“真理”,就能不断地实现“创新”,这是我们之所以非常看重“求真”的真正原因。实事求是讲的是求“是”,但据以上分析,求“是”实际上已经是涵盖了求“真”、求得“真理”与实现“创新”的全部内涵了。由于“真”或“真理”都是一种“主客二分”的知识论表述,从哲学上来讲,这样的表述总是容易造成误解的[5],相对容易走向静止地、僵化地、机械地理解事物的方面,所以总是难以把握事物流变着的发展逻辑。这是我们思想上经常容易堕入教条化、僵化局面的深层原因,也是我们常说“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的根本原因。
其实,人们常说的“辩证法”之所以难以驾驭也就是因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常常停留于“主客二分”的知识论层次上造成的。事实上,在实践的过程中,主体认识客体并不是机械的反映关系,而是主体与客体高度相互作用才生成的,如有学者指出的,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人们“根据实践的目的,因势利导地改变规律赖以起作用的条件,从而引导规律起作用的具体方式”,最终才能“实现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统一”[6]。
显然,没有对流变着的事物的精准把握,便不足以懂得何为规律赖以起作用的条件,更不可能懂得如何进一步引导规律起作用的具体方式,因此,其中真意便是要求“主客一体”,也即达到对事物之“是”的深刻把握。不过,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运用的是对象性的科学语言,不同于哲学的话语系统。这无疑是我们广大研究者需要特别注意的,因为理解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将西方传统哲学思想融汇到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当中来。诚然,西方哲学中“主客一体”的本体论分析方法,也即文章中多次讲到的对“是”的哲学分析,由于其极力避免对象性思维的语言传统,所以有利于贯穿“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世界,因而有利于“主体参与”去把握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逻辑,从而可以较好地避免“主客二分”的知识论分析方法的弊端。该弊端指知识论分析方法是一种表象思维,对前提缺乏一种进一步生成性的动态理解。
不妨举一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面的例子,我们常说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获得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这个结论可能会有人虽然表面不说但心里却不以为然,认为这只是政治上的说教而已。为什么会有人这样认为呢?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停留在“主客二分”的知识论理解层次上的知性思维方式造成的。如果仅仅停留于知识论层次上去理解问题,那就是停留于上面讲到的依靠后来的实践来证实前者的“事后诸葛亮”或“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逻辑,诚如列宁所说的“真理和谬误只有一步之差”,这样的理解就是由于差了那么一步,结果就变成了谬误。而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到“主客一体”的本体论、生成论的层面来理解的话,那么就会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怎么来的进行追问,那么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本身,以及无数老百姓愿意牺牲生命来选择跟着共产党走的历史画卷就会涌现在脑海中,因而,我们就会得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取得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的结论。这就是中国革命实践按照自身的逻辑不断展开、不断生成的必然过程。
而一旦有了此生成论意义上的“主客一体”的深刻理解之后,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就是历史赋予的、就是人民赋予的,具有历史逻辑上的必然性,因此我们党的领导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思考中国现当代政治问题时的逻辑起点,而根本就不会在这个问题上相信那些肤浅的所谓“成王败寇论”了。
由此可见,“主客一体”的本体论层次的理解之重要,而哲学中对“是”的分析就是本体论的分析,是把握到了贯穿“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世界的有效通道,是我们深刻理解事物本身发展逻辑的重要途径。西方哲学之贯穿始终的就是对“是”的分析,正好可以滋养和深化我们的思想。这也正是本文从西方哲学视角来立论的初衷。人们常说的,哲学之所以不是知识而是“爱智”,学习哲学之所以可以获取“智慧”的真正原因其实也就在这里。值得一提但有些遗憾的是,其实我们古人提出来的“道”“天人合一”等思想本来是可以直接对接“主客一体”的本体论层次的思考的,但长期以来由于“主客二分”的知性思维习惯,竟然致使这些深刻的思想被玄化了,结果没有充分发挥其启迪智慧的应有作用。
然而,我们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研究时,若能在汲取西方哲学中关于“是”的思想的同时,关注到中国古代哲学的“道”与“天人合一”等思想,便有可能恰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介,会同中西哲学,从而将古今中外的哲学思想汇聚成强大的思想洪流。这必将有利于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征程,有助于我们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