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的多元开发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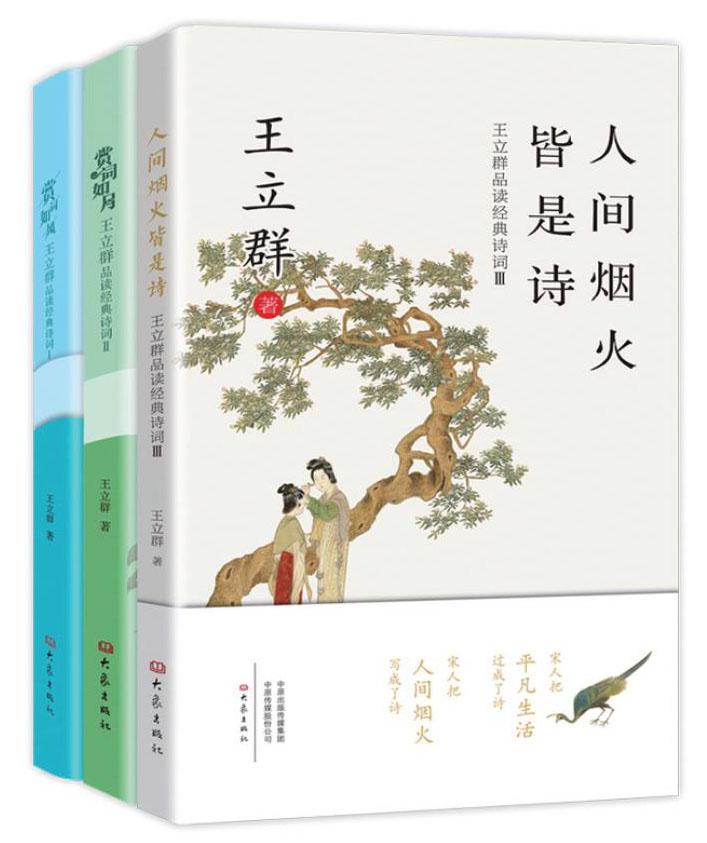
【摘要】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建立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的基础,也是中华文明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核心要素。近年来,随着图书行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与细分市场格局的变化,传统文化经典类图书的开发面临许多新的情况。文章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代表《史记》为着眼点,通过对其近年来的多样开发形式进行分析,从而获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类图书多元开发路径的启示。
【关 键 词】传统文化;文化经典;《史记》;多元开发
【作者单位】李小希,大象出版社。
【基金项目】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自主选题“新时代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出版研究”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237.9【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0.22.016
优秀传统文化是建立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的基础,也是中华文明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核心要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总结、书写与阐释,从古至今,无论民間还是官方,经典的出版与传播从未停止。《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以说,从六朝时期最早的《史记》抄本,到北宋第一次将三家注与正文合而为一[1],再到今人对《史记》进行注释与白话文翻译,对《史记》的开发从未停止。因此,将《史记》作为个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的开发路径进行总结、归纳和探索,无疑具有典型意义。
一、 2015—2020年《史记》类图书出版概况
笔者以开卷、当当等书业平台公布的数据为基础,以“史记”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个别书名不包含“史记”的图书,可在相关图书中关联,将年销量在1000册以上的图书计入考察范围。由此可以看到,2015—2020年,《史记》类图书共有将近35000个品种,其中包括同一本书的套书和单本书的重复统计,以及再版和初版与修订版重复统计的情况,因此总量应该低于这个数字。总的来说,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别。
1.《史记》原典类
即对《史记》旧籍进行影印、整理点校、注释翻译,或精选《史记》中部分篇章进行导读等。如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点校本(《史记》2014年修订版);韩兆琦评注《史记》普及本(岳麓书社,2012年)和学术性较强的《史记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初版为2004年,2016年修订);张大可的白话本《史记》(商务印书馆,2016年)和百家汇评本《史记》(商务印书馆,2020年);张大可、丁德科编著的《史记观止》(商务印书馆,2016年)等,均精选《史记》中的部分文段,并配上导读、注释等。
2.《史记》少儿类
即针对青少年或者儿童读者的需求对《史记》原典进行改编,配有大量图片或漫画,趣味性及普及性较强。如张嘉骅的“少年读史记”(青岛出版社,2015年)和“给孩子的史记”系列(青岛出版社,2019年)等,选择《史记》中适宜孩子阅读的情节改编成历史小故事或漫画等。
3.《史记》解读类
即不以呈现《史记》原典为目的,而是以《史记》为研究和解读的对象,阐释作者对《史记》或者《史记》所记录的历史的看法与评价,其中饱含个人的价值观、历史观和人生观。如杨照的《史记的读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聚焦司马迁所处的历史背景及其叙事视角与态度,在讲解《史记》的同时希望为今人阅读历史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王立群的“读《史记》”系列作品则堪称解读类图书的开创者与翘楚,自2008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王立群读《史记》”推出后,十余年内热度不减,是比较系统、全面解读《史记》的长销书。
二、 《史记》类图书开发出版特点分析
1.传统的开发出版类型始终热度不减
传统的开发出版类型如上文所提到的原典类,其立足点是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史记》原典,而不对其做进一步的开发[2]。因此,图书定位始终没有跳脱古籍的范畴,功用也始终停留在历史史料层面,目的是为读者学习研究《史记》提供方便,也为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提供可靠的史料依据。
《史记》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的代表,其所记录的历史、反映的文化内涵及司马迁饱含深意的春秋笔法,都是通过原典传达出来的,抛开原典去谈《史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无法行得通的。而且,在书籍流传过程中,每个时代都会涌现出贴合当时市场特点的经典,这对《史记》的注解、翻译和阐释方式都提出了不同要求,因此对《史记》的传统开发始终热度不减。
2.专业性与普及性同步推进
《史记》的历史与文学价值决定了其作为史料的学术价值,但绝不仅限于学术界。对经典文献的开发,除了抢救性地整理和注解,还有如何更好地将其中的精华以恰当的方式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以更加方便快捷的方式体会其魅力。对于带有学术研究性质的作品,则需要考虑如何更好地通俗化、大众化,让更多的人能够读懂、爱读,这也是近年来《史记》类图书开发的一个大趋势。前者如《史记》普及本、《史记》青少年本、“史记故事”等,后者如“王立群读《史记》”系列图书等。专业性与普及性的同步推进,迎合了不同需求的读者群体,也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3.少儿类《史记》读物异军突起
《史记》少儿版的开发,较早可追溯至1956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史记故事选》。该书选取《史记》中的22篇人物故事,用通俗的语言进行介绍,虽然书前的内容提要称此书“便于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阅读”,但终究不是针对少年儿童开发,而此前市场上针对少年儿童的《史记》类图书不仅数量少,而且不成体系。
近年来,少儿类图书呈井喷式发展,针对少儿的《史记》类图书也应运而生。尤其是青岛出版社2015年推出的“少年读史记”系列图书火爆市场后,“少儿读史记”“青少年读史记”“少年趣味读史记”等相似的书名、定位和体例的作品大量涌现。《史记》青少年版选本除选取《史记》中的历史故事进行讲解外,还设计有成语、字词、文学常识、小游戏等栏目,更加贴近少年儿童需求。
三、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多元开发的启示
1.以传统开发的成果为基础
王岳川在《儒家经典重释的当代意义——〈大学〉〈中庸〉讲演录》中指出,经典的重释必须以经典文本为基础,注重对经典文本的回归。我们对待经典的态度是:当代对经典的解读要最大限度接近经典原典的内涵和意义,同时考虑当下的文化语境,让经典在新时代焕发生命力,尽可能阐释经典的当代意义[3]。这对我们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类图书开发的思路具有重要意义。
一般而言,经典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会被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形成新的理念。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无论哪一代人对经典的解释都不可能做到完美,这也是《史记》不断被解读、阐释和出版的原因。《史记》的传统开发正是基于这种经典重释理念的最基础的做法,因此改编、解读、漫画化、儿童化等开发方式都必须在此基础上进行。也就是说,在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的多元开发路径时,至少要坚持以下两点。
(1)不能脱离经典原典去臆想。经典原典始终是该类图书开发的基础,无论图书的内容与体例如何创新,对经典原典的内涵展示都是不可或缺的。如《史记故事》等图书设计了原典展示的环节,“王立群读《史记》”系列虽然是对《史记》的解读而非助读、导读,但也在书中展示了所讲历史事件的原文以方便读者理解。
(2)在解读、改編的过程中,无论方式、风格与原典是否相差甚远,都要最大限度地接近经典的原本意义。与当代的现实情境结合,挖掘经典中具有现实意义的内涵和价值追求是必须且有意义的做法,但挖掘的核心不能脱离原典的内涵与价值取向。 如“少年读史记”系列和“王立群读《史记》”系列都放弃了本纪、世家、列传的分类,前者把相同身份的人放在一本书中讲述,分为《帝王之路》《霸主的崛起》《辩士纵横天下》《绝世英才的风范》等;后者则把原典不同篇目里同一个人的故事汇聚起来,勾勒出秦始皇、项羽、汉武帝等重要历史人物的形象[4]。作者在解读这些人物时,常常融入个人的感情。如《少年读史记·帝王之路》讲到舜年少时受到父亲和弟弟的欺侮,除了凸显原典中传达的舜孝顺、贤良的品质,还提到舜在逆境中运用智慧解决难题,乐观面对挫折的精神 [5]。这虽然不是原典直接传达出来的,但是与其内涵并不冲突,这样的生发是有意义的。
2.讲好中国故事始终是主线
梳理《史记》类图书不难发现,除了学术性的开发,对《史记》的解读与呈现始终都离不开历史故事的讲述,这是因为《史记》本身就是历史事件的记录,司马迁的记述方式也带有很强的故事性与演绎性。不单是《史记》,历史类的文化典籍皆如此,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如诸子百家、诗词曲赋中,故事元素始终存在。因此,将讲好中国故事作为一条主线十分有必要。
(1)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中符合当代中国故事价值观和有利于增强国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以及有助于增加读者知识储备的不同功用的故事,分门别类地讲解、翻译、点评。如王立群的《历史从未走远——王立群读史札记》以《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宋史》为对象,结合当代热点问题,讲解和点评其中饶有趣味和意义的历史人物故事,颇有以史为鉴的味道,很好地提炼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的精髓,实现了当代讲述的通俗化飞跃。
(2)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中的故事元素改写或重组,形成真正的故事。如《论语》为语录体,生动性有余而完整性不足,哲理性有余而叙述性不足,我们可以将碎片化的叙述补齐,或梳理孔子与弟子交谈的事例,或勾勒孔子的生平,从而增强《论语》的可读性。前者如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论语》(果麦编,2020年),将原典内容打破,精选出50个片段编写成小故事,孔子与学生的交往仿佛一个现代课堂,一部《论语》仿佛一部校园小说;后者如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写给孩子的论语课》(张玮,2020年),以聊天的形式将《论语》的文段穿插其中,展现了孔子的一生及《论语》的由来,纵向的系连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
3.利用“明星效应”促进不同类别的图书融会贯通
“明星效应”中的“明星”包括两个方面:一指“明星书”,一指“明星作者”。“明星书”和“明星作者”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利用他们的明星效应可促进不同类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类图书融会贯通。
“明星书”指在市场上引起极大反响、销量可观的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类图书。“明星书”虽然在推向市场之初仅契合部分读者或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但是在大获成功后,很快就会形成以其为中心的一系列延伸作品。如青岛出版社2015年的“少年读史记”系列出版成功后,又于2019年推出“给孩子的史记”系列,读者定位为10岁以下的儿童。该系列选择了40则趣味性更强的历史故事,所配图画也由之前类似汉画像砖的绘画风格转为漫画风格,并增加了拼音,体例设计更适合学龄儿童或亲子阅读,这种延伸开发实现了读者群体的细化与跨越。
如果说读者群体的扩张是一种纵向开发的话,那么“少年读西游记”“少年读国学”“少年读徐霞客游记”系列则是一种横向的开发,围绕有关《史记》的“明星书”延伸出更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进行开发的图书,不同类别的经典在同一个框架内完成重构与再生,从而使传统文化的普及与传播得到了有效实现。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类图书而言,目前的“明星作者”以参加电视台的热门节目如《百家讲坛》《中国诗词大会》而获得大众喜爱的学者居多。与“明星书”效应相似,“明星作者”的代表作火了之后,延伸产品很快诞生。一是内容上的扩展,如以讲清代帝王著称的阎崇年将着眼点稍稍调整,推出了“故宫”系列;以讲唐史著称的蒙曼将讲述角度从唐史转向唐诗,推出了“品最美唐诗”系列;以讲《史记》著称的王立群立足诗史结合的观念,推出了“品读经典诗词”系列,等等。二是读者对象的扩展,如蒙曼主编的“了不起的中华文明”系列(化学工业出版社,2019年)为一套针对儿童的传统文化读物,包括美食、节气、文字、书画等多个方面;“王立群智解成语”系列(大象出版社,2014—2018年)读者对象为中小学生,该系列从成语的使用出发,结合社会热点和历史典故来展开分析。这些以“明星作者”为核心的扩展性开发,实现了从历史类传统文化经典图书向古典建筑、诗词、语言文字等多种传统文化经典图书的转变,拓宽了多元开发的眼界。
通过对市场上《史记》类图书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一是要以传统开发模式为核心进行其他路径的开发;二是将讲好中国故事与解读传统文化经典融会贯通;三是利用“明星书”及“明星作者”的号召力以一带多,形成系列高质量、高热度的传统文化经典读物。当然,这些开发路径基本上只停留在图书范畴内,新媒体时代,如何利用新媒体更好地展示原典和对原典进行解构、再生,又是一个新的议题,有待继续挖掘。
|参考文献|
[1] 贺次君. 史记书录[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2] 金鑫荣. 出版与外译:优秀传统经典的出版路径研究——以百年来《史记》的出版与传播为例[J]. 中国出版,2018(13):25-29.
[3] 王岳川. 儒家经典重释的当代意义——《大学》《中庸》讲演录(之一)[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10):60-76.
[4] 王立群. 千古一帝秦始皇[M]. 郑州:大象出版社,2016.
[5] 刘洁. 少儿国学图书《少年读史记》出版策划的成功之处分析[D]. 青岛:青岛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