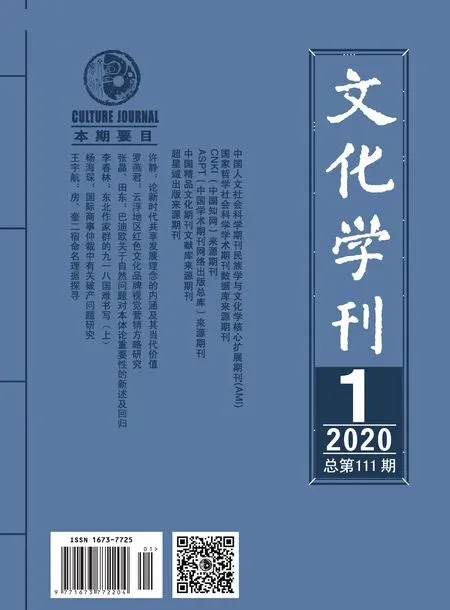方寸之间见波澜
——课桌文化审美研究
李 邦
信息化时代,学校早已不是不闻窗外之事的象牙之塔。社会上的任何重大变化都会很快传播到校园里来。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一方乐土的教室里的中心地带,课桌形成了一种较为丰富多彩的、带有强烈校园青春色彩的文化存在——课桌文化。在课桌文化这个圈子中,既可以不求回应地独抒性情,也可以成语接龙式的你言我语,这种具有相当程度私密性的公共空间应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然而,近年来,课桌文化走向式微,这反映了学生群体的感知方式的变迁。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更具广阔性与私密性的网络已经成为学生最大的学习之余的公共空间。另外,学校层面的参与,课桌文化不仅被当作毁坏公物的不道德之举,还被当作一种分神离心的愚昧之举,清除课桌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上演于各大校园,并且学生那看似无处安放的过剩精力又逐渐被其他得到学校主流认可的校园文化分走了“阵地”。从实用功利的角度来说,消除课桌文化无可厚非,然而,饶有趣味的是,课桌文化却野火烧不尽,其中缘由耐人寻味。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课桌文化明显不是学生单纯学习之余的消遣现象。它可以被看作是学生式的休闲审美文化,是其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具有相当丰富的审美特性。另外,课桌文化是一种多层次的学生公共空间,是学生日常生活和消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生紧张繁忙的学习之余发挥着其他公共空间难以替代的作用,它为管窥当代学生日常生活审美化提供了一个可供解读的存在。
一、丰富多彩的作品
从表现形态来看,课桌文化既有学生在百无聊赖之下在课桌上做出的涂抹、素描等无意识之举,也有费神专注的诸如雕刻、贴纸、写作、装饰等的有意为之。毫无疑问,学生对这些司空见惯的日常学习用品熟稔于心,它们毫无形式主义者所言的陌生感,很难令学生产生审美冲动,何以在学生的摆弄中变作审美文化的符号?其实,由于其区别于整体环境的特质以及学生由此被唤起的某些特殊想象,因此一些日常学习用具、摆件便被注入了审美性质。整齐划一的环境包括排列有序的课桌、讲台、黑板、门窗等布局安排,还包括那些张贴于墙壁的大同小异的警语、格言等标语与名人画像、贴纸画等装饰布置。所有外在环境当然不是为了给学生营造一种审美愉悦的氛围,而是出于功利考量,即最大化激励学生全神专注。对于整日待在教室的莘莘学子来说,学校这种整体环境几乎总是千篇一律,他们目之所及没有例外。这类高高在上、拒绝学生染指的经验媒介定会阻碍学生那随时骚动不安的审美诉求的实现,进而促使学生生活在别处,寻求其他客观对应物。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学生触手可及的便是日常学习用具,如学生自由涂抹的、带有印记斑斑的课桌上摆着由废弃笔芯粘合的自制笔筒和撑满教辅的带有卡通贴纸的书架。种种学生就地取材搭建的审美意象由于灌注了学生自己的创造及想象显得别开生面,与冰冷的、毫无人情味的其他装饰形成巨大差别,并且,这些用具并不是由于其便于使用而如此摆设、装饰。这些用具的使用功能不会因为其放置位置、外在装饰等变化而有所增加,学生也无意通过这些手段来让学习用具更方便地被使用,种种物品此刻已然脱离了其使用功能所蕴含的日常工具性,宛若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把破烂的锤子,不再具有那种在手边随时可用的熟悉感,由此,课桌变成了纯粹的审美对象,让久浸功利意识之流的学生找到了可以安居的家园。换句话说,尽管其题材来自于学生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但课桌文化通过有意淡化审美对象中的实用主义色彩,成功地将审美意识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其典型操作便是以学生学习生活中的学习用品和诸如水杯、小镜子等日常器物作为装点。另外,它们交织着校园之外流行的各种构件,如桌面上刻上某些新新人类所共享的网络符号、贴上某明星的小海报、某堆书籍中耷拉着一本封面绚丽的娱乐杂志。这种奇怪的混搭和杂糅以一种高傲的姿态,无声地表示拒绝为教室统一化的装饰所驯服的意愿,张扬着学校整体教学所无法顾及的学生的种种个性,从而具有奇异纷呈的美学效果。如果说学生所处的环境以及其在学校的生活方式是一种“重复”“复制”的特征,课桌文化恰好就是对这种主流的反驳,其体现出来的美学特征始终都带着极为纯粹的青春气息,它直率单纯、热烈纯粹。就算有粗俗成分,也无伤大雅。对学生来说,课桌文化本身笼罩了一种特殊的“灵韵”,这种独一无二性在于,学生以自己的一方课桌为中心,以独具个性的方式去表达专属于学生的思想情感,和学校主流的严肃正经形成较大反差,这种特有的反差吸引着那些偶有松懈的学生加入创作洪流去施展自己的“神通”。
二、漫不经心的创作者
从创作行为的特征来说,在井井有条的教室环境中,这些课桌文化的创作者便充当了本雅明所津津乐道的“浪荡子”[1]这样一种角色。本雅明视野中的漫步者,对巴黎街头所囊括的一切诸如攒动的人群、鳞次栉比的屋舍、目不暇接的商品,都抱着鉴赏家的态度进行观摩与玩味,且漫无目的,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与当时主流对一切事物的功利主义态度形成了强烈反差。课桌文化的创作者身处教师苦口婆心的知识训诫中,埋首于贴满墙壁的格言、口号的谆谆教诲中,却神思八荒,在自我松懈的心不在焉的世界里,拒斥外界对自己的规训。对于这种“浪荡子”态度,本雅明将其解读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反抗[2]。对象牙塔的学生而言,这种对外在世界的偶尔为之的倔强拒斥多少也保留了一种反抗底色。当然,这种反抗没有上升到社会反抗这样一种政治层面,也不是要推翻教师、学校对自己主导的暴力式造反,剥去了相当的严肃性后,这种反抗针对的便是以学校为代表的外界对自己一以贯之的、鲜有松懈的操办、安排。以学校为代表的主体就如资本主义市场上的迷人的、永远泰然自若的商品[3],总是对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发挥移情的魔力,每个人都成为其潜在的顾客,难逃魅力统摄。每个学生都是被其无所不在的目光所统摄,都是它所必须安排的“顾客”,每个学生都在其中能找到心有所属的“商品”。在这种长久的互动游戏中,购买者的主体性逐渐丧失,不是顾客选择商品,而是商品根据顾客的购买实力将其划为三六九等,最终变为“顾客”被商品所挑选这一令人汗颜的局面。具有相当主体意识的学生就如“浪荡子”一样,尽管可能有充裕的经济实力去和商品发生共鸣,但就是不愿意被商品的魔力收编,大有任其波澜壮阔、我自岿然不动的态势。毫无疑问,学校的班级制授课中偶尔难免会陷入自说自话、罔顾他人意志的教学情境中,此时,有些无法跟上教学节奏的学生将课桌文化的创作以及欣赏当作逃逸学校整体安排的出路也不足为奇了。相较于学校组织引导的如板报、画报、海报等同样具有一定自由的创作活动,课桌文化的创作有即时性,学生兴之所往,随意发挥,完全没有外界安排下的重压,同时,它契合了学生时间,特别是休息时间零碎的特点,不用长时间的投入。这种自由发挥不啻为个人主体精神的肆意张扬,它完全决定于创作主体的心灵意志,它有可能变为对讲台上唾沫横飞的教师涂鸦,对其言行举止的夸张模仿。在创作后,完成了自己作为主体对外界“施暴”的想象性反杀,夺回了那种被教师肆意蹂虐的自我主导权。毫无疑问,这种反抗某种意义上在学校主导的连续性统摄中撕开了一条豁口,学生在这裂隙之中成为了自己的主人,实现了自我的完满。当然,这种“浪荡子”的态度远不是时下一些对课桌文化所定性的所谓狂欢,课桌文化不是一种对既有秩序的实际颠覆(过分抬高课桌文化反抗特征的颠覆性毫无必要),也不是创作者阴谋十足的攻击,只不过是一种煞有介事地自娱自乐罢了,毕竟“浪荡子”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悠闲从容的一员。某种程度上来说,课桌文化无关紧要,但正是这种无关紧要造就了其独特的魅力。可以说,这种反抗实际上是对既定秩序的认同,一种祈求其更加完满的另类形式,类似于孩子对父母的抱怨,有些时候责之切不过是由于爱之深。
三、结语
毫无疑问,课桌文化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在学生群体之中生产和传播着特定的意义与轻松娱乐。轻松娱乐是课桌文化不可或缺的基本特质。学生在课桌文化里分享各种具有文化意味的符号,创作和传播着形态各异的审美存在,这些存在以特定的方式成了娱乐的载体。它们与学生姿态的正襟危坐和教室环境的严肃正经等形成巨大反差,时常可以让学生产生超越眼前“苟且”的愉悦感,获得精神上的快乐、自得。由课桌文化所创造出来的各种审美文化的符号拥有魅力的主要根源也在于此,课桌文化存在的美学理由也在于此。至于其愤世嫉俗的吐槽、低俗粗陋的讽刺、别有用心的鼓动等所谓负面情绪和内容,看似有所指涉,甚至戾气十足,实际上是一种不必认真对待的异类小众,这也实在不足以被当作妖魔化课桌文化的口实,这些偏激过分的成分甚至会被课桌文化的其他成分消解于内部之中。忽视课桌文化上述美学特征以及对学生而言的重要意义,对其兴师动众的消亡之举可能事倍功半,而对其大唱挽歌也可能为时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