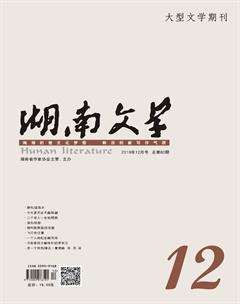晚洲
佘意明
南方的城市多依江而建,江中不乏人文地理积淀深厚的沙洲。不过,说到城与洲的关系之亲密,莫过于株洲,株洲是全国唯一的一座以“洲”命名的城市。
株洲,古代多槠树,江中多沙洲,合二为一,是为“株洲”。但今天能看得见的洲只剩晚洲、空洲、桑洲等几个,更多的洲因江流冲刷、河道治理等原因消失了,仅留下萝卜洲、八斗洲、刘家洲、马洲等三十多个带洲的地名。
在历代文人的眼里,洲是挺有诗情画意的,古今以洲为题材的诗文不计其数。最早写洲的诗,是《诗经》开篇的《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曲《关雎》,婉转轻扬,流传千年。
株洲之洲,美在晚洲。晚洲是株洲面积最大也最具文化底蕴的沙洲,是株洲之“洲”的符号与象征。其风情魅力,不亚于《关雎》中的沙洲。
一
晚洲,现在又名挽洲,但我以为叫晚洲更有诗意。很早就想去晚洲,却一直没有成行。一个春风沉醉的日子,经朋友之约,到了心仪已久的晚洲。
离开株洲城区三十多分钟,汽车便进入渌口区王十万境内,透过车窗远远望去,江心有一座小岛,像是从水上漂来的,静卧于湘江之上,那便是晚洲。停车,摆渡,瞬间便到了岛上。
晚洲,最早因与杜甫的结缘而闻名,这也是洲上妇孺熟知的一段骄傲的历史记忆。
公元七六九年农历三月,经历数年的颠沛流离,诗圣杜甫已穷困潦倒,为了谋生计,想去投靠自己的好友衡州刺史韦之晋,便从长沙湘江坐船南渡,经过晚洲。
映入诗人眼帘的这座沙洲,看起来很原始,或也曾凝聚过历史的风云。清代《湘潭县志》记载六朝时期,晚洲曾一度是古湘西县治所在地,志中的《故城图》在晚洲处标注了“湘西故城”。晚洲是六十年前从湘潭县划入株洲的,上面是否真曾有一座城市,我没有考证过。
杜甫这次欣然上岸,登岛游历,感慨作诗《次晚州》:“参错云石稠,坡陀风涛壮。晚洲适知名,秀色固异状。棹经垂猿把,身在度鸟上。摆浪散帙妨,危沙折花当。羁离暂愉悦,羸老反惆怅。中原未解兵,吾得终疏放。”
杜甫说“晚洲适知名”,那么,晚洲因什么而知名,他没有明说。但从他的诗中看,那个春天,他没有见到半点六朝风雨留下的痕迹,眼下充满了奇花野草、参差云石的原始景物。古城消失后的晚洲,变成猿猴的樂园了。杜甫一个外乡人,想必是听了附近居民说有一个神奇的猴岛,而慕名登上晚洲的。
遗憾的是,眼前的岛上并没有看得见的与杜甫有关联的人文遗迹,只在晚洲东面的湘江边,一个供人上岸的缓坡处长着一棵两人才能合抱的大樟树,枝干虬曲苍劲。我无法知道这棵樟树的年龄,它虽被雷劈掉了小半边,但仍然顽强地活着。
站在樟树下,当地居民充满敬意地说它曾为杜甫拴过船。我想,那与其说是对樟树的敬意,不如说是对杜甫的敬意,对文化的敬意。我见过南方很多上了年岁的古树,都会被当地的居民附会一些名人故事或灵异传说。无意之中,它们便会因赋予了某种神圣或神秘感而得到保护,这大概算是草民的一种智慧。
这棵古樟老而不死,或许是要使自己成为杜甫游历晚洲的永远见证者吧。
二
我长期研究湘东人文地理,站在古樟下,便想起了另一个人,张舜民,北宋诗人、画家、进士,谪官途中到过晚洲,当年是否也在这棵古樟上拴过船?洲上的人说这里是过去坐船的人唯一上岸很方便的地方,想必他也在树上拴船。
北宋元丰年间,宋神宗劳师攻打西夏,在军中掌管机密文字的张舜民目睹宋军惨状,悲愤写下“白骨似沙沙似雪,将军休上望乡台”的诗句,一个叫李察的官员称他讥讽朝廷而予以弹劾,张舜民被贬为监郴州酒税。文人被罚去收酒税,在宋朝屡见不鲜,司马光也“享受”过。这温柔的一刀,多少带点羞辱的意思。
公元一〇八三年腊月,张舜民由水路从北而来,或许是羡慕杜甫留下的江山胜迹,也登临晚洲,作《行次晚洲》诗:“腊月遭霖雨,孤舟舣暮滩。数声归雁断,半岭野梅残。无复论偕老,何时展急难。江湖卧周岁,此夕最难安。”
寒冬腊月,江湖漂泊,满目凄荒,孤独难耐,诗人的心情是很糟糕的。
张舜民的诗见于他的笔记游记《郴行录》。书中还记录了他这次所见所闻:“癸巳,次晩洲。洲上平广,土壤如北方,居人止一两家。自朱洲之西,水中处处有三石,形如坏冢,土人谓之黄牛石,出没水中,颇为舟船行人之患,过者避之。”他眼中的晚洲已不是杜甫所看到的原始野岛,洲上有人家居住了。
株洲,古代亦写作朱洲、槠洲。张舜民对株洲最大的贡献是,不仅记下了晚洲当时的地理人文,还是已知的历史上第一个提到株洲之名的文人。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在湘水边凭吊远去的古人,不免感怀。张舜民这位孤独的谪官,恰似那啼血的杜鹃,用自己的苦难吟作化成晚洲美丽的文化遗产。
晚洲,因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灵气,有了杜甫、张舜民这些名人的活动便多了文化的内涵。
三
告别古樟,穿过几片田垄、几户农家,我们听到几声孩子稚嫩的读书声。一处围墙院内,便是晚洲(挽洲)小学。
晚洲是有历史底蕴的,晚洲学校也不例外。一九二七年,一位名叫文旺炎的外村人,见岛上没有学校,孩子读书不便,就抱着满腔的热情在这里的文家祠堂办起了一所只有一个老师、二十多个学生的小学。
共和国建立后,来晚洲学校读书的越来越多,开始有了初中,最多的时候有七个班,一百五十多个学生,老师达到十四个。一九七八年,晚洲学校撤销了初中,改为小学。九十年代后,洲上很多青壮年出去打工、做生意,晚洲小学的生源急剧减少,如今只有五个学生,两个半老师。五个孩子年龄不一,读书的年级不一,老师们便采取背对背的复式教学办法。
晚洲小学的老师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段难忘的经历。校长兰红建是晚洲本地人,戴着一千多度近视眼镜,兼教数学。他一九八一年考入晚洲小学做“代课老师”,曾一度离开。他说“那时候经济困难,民办老师工资低,总想出去做事,但一想到孩子一张张天真无邪的小脸蛋儿,走了才真感到不舍”,于是又回来教书了。教语文的曾老师快退休了,家在洲外,每周五回家,周日返洲,白日教学,夜里陪伴她的是天上的星星月亮和窗外的宿鸟鸣虫。为了让孩子们记住乡愁,曾老师要求学生背诵杜甫写的《次晚洲》诗。教英语的何老师还要负责外校的教书,每周坐渡船到晚洲给孩子们上两节课,只能算“半个”老师。兰校长表示,这里即使只有一个学生,他们也要坚持下去。
晚洲小學虽然条件艰苦,但老师们以九十多年前文旺炎一个人支撑一所小学的故事激励自己,守望相助,静待花开。这是一个地方重教文化的精神传承。株洲是湖湘的一块耕读文化之地,历史上共有二百六十多名进士,还出现了凌登龙、罗典等岳麓书院著名的山长。
晚洲小学老师的艰苦奉献精神终于引起了各种新闻媒体的关注和赞扬,学校得到政府的支持和社会的关爱,市县领导还跑来和几个孩子一起过“六一”。他们的坚守终于开出了美丽的鲜花。
很多人用一生去做一件事情,最初并非崇高,或是一种生活所需,甚至是无奈孤独的,慢慢地变成一种自然而然而又单调重复的坚守,突然地在某个时刻,被一束亮光打在身上,在那些外人眼里,陡然地变得明亮、高大起来。因此,一个人能够在平平淡淡的生活之中做一点有实际意义的事情,着实比那些虽然有很好的初心却走着走着忘记了的人要美好,活得也更踏实。
四
离开晚洲小学,穿过一段水泥路,转入了田间的小道,只见农人摔着鞭子赶着牛在田里犁地,三三两两的鸟儿在刚翻过的地里找虫子吃,间或溅起朵朵小水花,一派田园风光,那情境很能唤起人的怀旧记忆。时光荏苒,如今还这么驱牛耕地的很少见了,铁犁多躺在农具博物馆了。
再走一段,小路就通向了一户农家,我们想歇一歇脚,看看村民的生活。面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主人十分热情,还燃放起鞭炮。
株洲当地普遍的习俗是过年的时候客人来家才放鞭炮的,但晚洲却不管什么季节,保持着来客就放鞭炮的本土淳朴民俗。
这家的主人是一位五十开外的农家女子,热情地给我们泡茶,拿花生、瓜子待客。她说家里只有两口子了,男人干农活去了,孩子在株洲城里上班。
她的话里有点点的苍凉。晚洲和中国很多乡村一样,人口在减少,这个一点六平方公里的洲上,有一个行政村,唯一的经济来源是种植农作物,没有什么来钱快的行当。青壮年为了寻找更好的出路,慢慢出去打工或者搬走了。洲上户籍人口本来有一千一百多,如今常住的只有三百多人,而且大多是老人。
谈起洲上的风物特产,她兴致突然高起来了。晚洲农产品丰富,比较有名的有黄辣椒、萝卜、赤豆、花生等等。她家里准备了一些剁黄辣椒、赤豆等,就是准备孩子休息的时候回家来拿的。
黄辣椒号称为晚洲一宝,皮黄透明,比普通辣椒更辣,是湘菜中的上乘佐料。晚洲附近的黄辣椒也是有故事的。西晋末年,醴陵县令杜弢率领在湘州流离失所的巴蜀人起义,史称“杜弢之乱”。朝廷派陶侃等前往镇压,三一五年农历八月,陶侃队伍开拔到王十万一带,遭遇连日阴雨天气,士兵伤风感冒,进军遇挫。陶侃见当地老百姓家有黄辣椒,便弄来煮汤,每人一碗,士兵大汗淋漓,精神振发,一鼓作气,歼灭了杜弢乱军。
晚洲萝卜远近闻名,个头匀称,肉松脆甜,味道可口,消食化痰,还可生吃。晚洲的萝卜还进了方志。清代《湘潭县志》记载了一条当时民间流行的谚语,“上洲芦菔下洲瓜”,古人说的芦菔,就是今人俗称的萝卜,“上洲”指的是空洲上游的晚洲。
辞别这户农家,行走在晚洲的乡间小道上,我们会时不时地碰上一些人,从衣着和言谈举止就能判断出那是城里游客。现在城市显得拥挤了,城里人喜欢去乡间寻找自然和诗意。
晚洲孤悬江中,风光绮丽,洲上农人的生活是简单的,民风是淳朴的,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原乡的诗意吧。但这世间很多美好又似乎都是别人家的,你看到的乖孩子是“别人家的孩子”,你欣赏的好风景是“别人家的风景”,晚洲上人口减少便是很好的诠释。
五
从古至今,人总在努力追求理想的住所。
晚洲是美丽的,宁静的。到了晚洲,你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岁月静好。她远离都市的喧嚣与浮躁,或许属于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心目中的“人诗意地栖居”的那种愿想之地,奢念之境。虽然晚洲农人的生活还有些许的简陋与缺失,但世上就没有完满的东西,就如那断臂的维纳斯。正其如此,中国那些偏远的乡村景物总能较完整地保存着。
晚洲是原乡的,幸运的。自然界孤悬的洲岛或者人迹难至的荒山野岭,最初是给予苦难人托命安身的地方,但人却利欲熏心,忘自然之本,使那些世外桃源之美惨变为绿水青山之殇。媒体纷纷曝光陕西秦岭、东北牡丹江等地削山毁林违建别墅或私人庄园,就是明证。
因无序挖沙,株洲古老的潦洲岛已在江面消失,如今晚洲又面临挖沙船的侵蚀,所幸晚洲村民打响了“护岛保卫战”,晚洲的保护也引起了地方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对株洲来说,保护晚洲尤其重要,如果晚洲这几个仅存的沙洲消失了,株洲之名便会不符其实。
一片孤洲,就是一个世界,但这个世界又与外面的那片世界是同血脉紧相连的。晚洲人那种对文化的尊重,那种耕读精神的传承,那种可贵的自然保护意识,不正是千百年来株洲文化精神的积淀吗?
不是渲染,不是造作,晚洲确实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但愿下次我到来的时候,晚洲依然会那么恬静、温婉。
责任编辑:吴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