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在野
高上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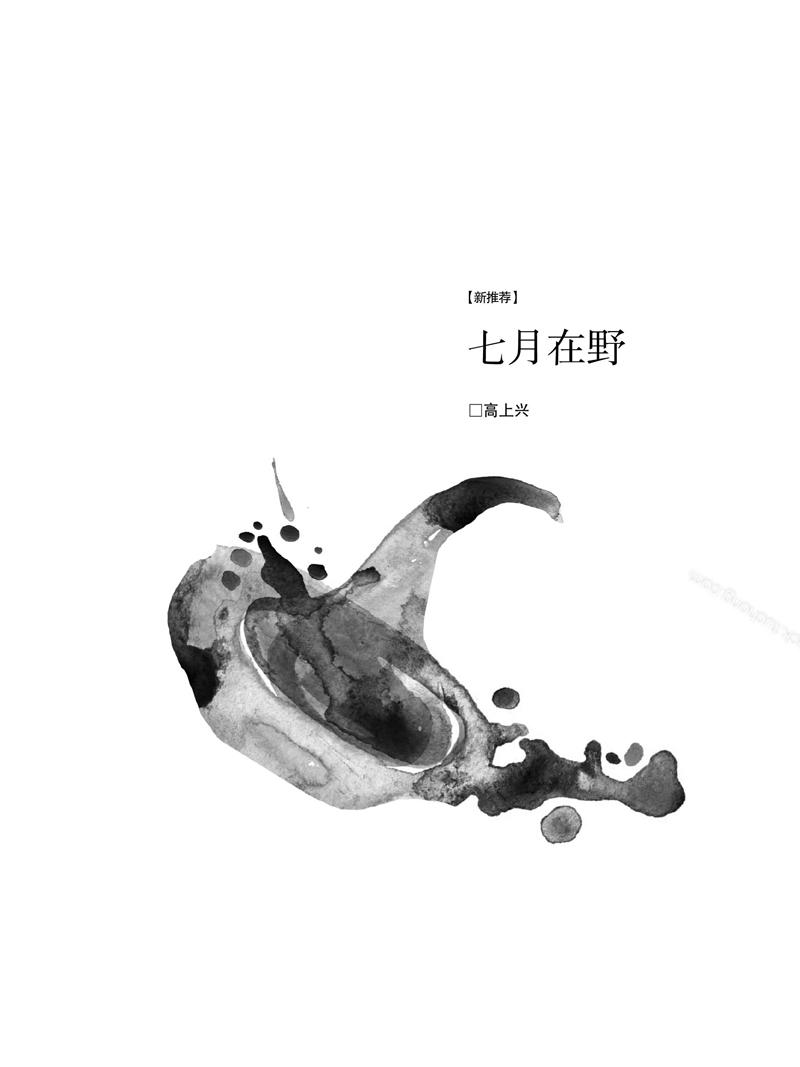
七月里桃桃总给我打电話。
她说:“他又笨又固执,像一坨狗屎。他不肯挪个窝,屋子里又臭又暗。他整日整日待在床上,我真受不了他。他真的恶心死了。”
她说:“真的,我真受不了他。总有一天我会被他气死。我真是作孽,上辈子杀人放火,这辈子摊这么个弟弟。他也没叫过一声姐姐。”
那时候我在空调房间里听她抱怨。七月的小城到处都是热浪。空调房外,消防车笛声由远而近。我走到窗子边上,没有看到消防车,只有一层层山横亘在远处。桃桃就在那里,在这小城边缘的山腰上,我想象她扶着一棵桃树给我打电话。
那个山腰上的村子到处都是树。梨树、桃树、板栗、杨梅、橘树、甜槠、苦槠、枫树、松树、杉树、柳树,漫山遍野,全放开了疯长。松鼠在甜槠树头跳来跳去,林子里充满唰啦啦的声响。
“楼下四个标间,楼上六个单间,门头种花,屋后有菜。冬天就吃萝卜和青菜。这地方离城说远不远,说近不近,一准儿有客人,上海的、杭州的、温州的,就喜欢这调调。”桃桃说。
我没想到桃桃真这么干了。那是五月,有一个下午她忽然跟我说,她要回村子里,整修房屋,开一家客栈。她问我客栈取个什么名好,我告诉她这事儿太难了,等她建成了我再帮她取也不迟。
我们又说了一些别的什么话。我以为她就说说,不想七月里她真这么干了。她指挥着装修工把家里拆得乱糟糟的,在地底下埋了管道,又在每一间客房里新辟了卫生间,安装了空调和电视。在她做这些事的时候,她那十七岁的傻子弟弟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死死关着门,不让任何一个人靠近他的领地。
“真是受够他了。”她说,“他帮不上一点忙。他不肯挪出他的房间,有时候他把屎拉在每一间房间里。我要疯了。”
“我要疯了。”她一遍又一遍地说。通过电话,我听到她屋后林子里,知了没完没了地疯叫。
她的客栈梦想,她的傻子弟弟,她的老屋改造,七月里我们聊的基本是这些。我想聊一点别的,哪怕是起一丁点话头也行,但桃桃从不提别的。
八月。八月里桃桃和她的傻子弟弟打了一架。
那天桃桃把弟弟骗出了房间,搬出了他的那些幼稚的玩具、破篮球、沾满灰尘的凉鞋。这一间在僻静处,虽然阴暗,但打个窗子,换上新木板墙壁,装好家具,就能成为一个好单间。
傻子在外面玩了一会儿知了就回家。他进了门,上了楼梯,在楼梯口站定,手里拿着长竹竿,头上全是汗水。他的宝贝被一样样丢出房间,木地板发出巨大的嘭嘭声。
他们就打了起来。
一个二十七岁的大姑娘,和一个十七岁的大孩子,在他们家的二楼,乒乒乓乓打了一架。过后,两个人各自在那里哭。
阳光从屋顶的缝隙倾泻而下,灰尘在一道道光柱里上下翻滚。
九月初傻子把钥匙吞到了肚子里。
“他真吞下去了,那么大的钥匙。”桃桃说,“我们都吓坏了。”
“他想住那,你就让他住吧。”我说。
“一开始,我们都默认他住那了。反正,空着也是空着。”桃桃说,“他乐意住,那就住吧。”
傻子把他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一件一件搬进了新装修好的屋子。他用一块脏兮兮的旧纸板,把窗子蒙上,整日整日待在屋子里,把臭烘烘的短袖扔满房间,在半夜像牛一样嚎叫。
“我知道不行了。他不能住那儿。你想想,哪个客人会住在一个傻子边上呢?”桃桃说。
桃桃准备把傻子搬到屋后的小房子里去。过去那里是猪圈,但现在已经整修好了,除却光线不足外,足以住人。
傻子把门看得死死的。在屋里时堵门,出去就锁门。
“有时他笨得要死,有时他又是个贼。”桃桃说,“我们有三把钥匙,全被他偷去了。他把钥匙像宝一样藏着。”
那天早上,桃爸一早在大堂守着。看他出来,就跟他拿钥匙。
“我爸跟他要。他不给。”桃桃说,“我爸就去拉他,想夺过来。他早防着我爸,一下子就冲了出去。十七岁,他都十七岁了。力气大得很,我爸都拦他不住。我爸就说,你去,你去我就把锁敲掉。”
“他就不说话了,站在那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又可气又可怜。我爸看看我,又看看他,不知道怎么好。我就跟我爸讲,去把锁敲掉,换一把好了。”桃桃说,“谁想到,他把钥匙放进了嘴里。”
“我就讲,有本事你吞下去啊。吞不下去我就给你塞下去。”桃桃说,“我也是被他气死了,才这么说。谁想他真吞了下去。”
我想象有一把冰凉的钥匙,划伤了我的喉咙,坠入到了我的胃里。这时我感到我的胃有一点隐隐约约的不舒服。
“他吞得真快。我和我爸都吓坏了。我站在那里,双腿都软了,在那里一直抖。我爸拉着他,掰开他的嘴,想让他吐出来。他吐了一地水,钥匙却没有出来。”桃桃说。桃桃又说了一些当时的情形,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我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少年。他眼眶里有眼泪在打转,却毅然地把钥匙吞进了肚子。
“说起来,我真该感谢那把钥匙。”桃桃说。
“别这样。他是你弟弟。”我说。从医院取出钥匙以后,桃桃弟弟大概感觉到大势已去,自己把东西搬到了后面,整天蜷缩在那里。
九月中旬来了第一批客人。她自己取了一个客栈名字,做了牌子挂在外面,叫桃木屋。那段时间,朋友圈里到处都是桃木屋的照片。
我终归是靠不住的,我知道。我总是说,等以后怎么怎么,再怎么怎么。给桃木屋取名是这样,以前在北方,和桃桃相处也是这样。
“满城灯火。半轮明月。你若来,就住最僻静那间。”十月开始的时候,桃桃说。
我们先后从北方溃逃回来后,桃桃好像大人大量,把以前我在北方开给她的所有空头支票,都一笔勾销了。
十月我在桃木屋。我住傻子那房间。203。
203。是的,没错。我进门前仔细看过。我对面是206,隔壁是205。有了编号,房间就有了秩序。
推开窗子,远处是云,云朵下是小城。如果我有一架望远镜,我可以一直看到小城里我屋子的阳台。
“满城灯火,半轮明月。”桃桃没有骗我。在桃木屋,的确可以见到这样的景象。
桃桃来过。她说:“这屋子,你是第一个客人。”
在沈阳,她租住的那间单身公寓,她也说过这样的话。不过她多半不记得了,她只是随意说了说,在房间里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我打量四周,屋子里很干净。我试图找到傻子住过的痕迹,但所有的一切,都被抹除了。
“你弟弟不傻。”我说,“他的镜头感很强。”有一阵子,傻子在门口劈松木段子。几个外地客人围着他拍照。
“帅哥,笑一个。”他们说。
“帅哥,把斧头举起来。”他们说。
傻子高兴的时候就根据他们说的,摆出一个个姿势;不高兴的时候就朝他们挥舞着斧头,口里啊啊叫着。他们拍了他。我看过他的照片,很不错。
“是。”她说,“他有时会正常。但只是有时。就像电路,有时通了就正常,不通就是个傻子。”
“我不指望他能帮我什么忙。”她说,“只要别添乱。等我赚了钱,就给他买个老婆。”
“他从没叫过我一声姐姐,但总归是我弟弟。”她说,“想想,有时觉得挺对不住他。他那么爱他那脏兮兮臭烘烘的屋子。如果,如果哪天我不在村子里,就随便他,随便他待在他那屋子里吧。可是我要赚钱啊,傻子也要娶老婆。”
她一直说着傻子。我们一起在小城上的高中,一起去沈阳上的大学,毕业谈了一场恋爱,决定要留在沈阳好好发展,没多久先后从沈阳溃败回小城。我们有那么多值得说的,但我们什么也没有说。
桃桃只说她的桃木屋和她的傻子弟弟。往事清零,爱恨随意?大概吧。对我这样的,终归靠不住的人,还有什么好说呢?
桃桃出门后,我看了一会儿电视。这时候我听到床底下有什么东西在活动,类似于一只蟑螂或飞蛾。
我拍了一下床,那声响就停止住了。隔了一会儿,那东西又响了。我得把它弄出来。弄死它。这样,我才能安心地在这个地方一觉睡到天亮。
我下了床。在床底下照了照,床底干干净净,床板是新的木床板。除却一些粗糙的毛刺外,别无所有。
那东西一定躲在某处。我在外头找了一根木棒。关了灯,在夜色里等待那东西。好一会儿没有动静。
隔壁有走动声,大概是房客在倒一杯水,或者干点别的什么事。随后有人敲门,闹哄哄一团糟,他们把电视声音开得很大。在房间里大声谈笑。大概还抽了烟——我想。满房间都是烟味,他们的床,他们的衣服,他们的窗帘,他们的地板,他们的电视屏幕,烟味无孔不入,粘滞在每一个角落。而那里,本该堆满金黄色的稻谷,寒冬里谷仓充满了暖烘烘的香味。
好一阵子,隔壁才安静下去。我将木棒靠在墙壁上,和衣而卧。也许,本无别的东西。或者,那东西已经悄然远遁,就此与我两不相见了。
没有声音。对了,没有声音就是万事大吉。可是——也许,那东西正在慢慢靠近我呢。它有着长长的触须,红色的复眼,毛茸茸的脚……借着黑暗做掩护,它正一点点靠近我。心怀叵测。
开灯。下床。一条粗壮的青尾巴壁虎趴在我的床头上。哦。这可怕的东西,它身上有那么多的细小的疙瘩,有冰凉的、白色的肚皮。冷汗很没出息地从我的发根冒了出来,后背也湿漉漉的。一条壁虎,就击穿了我的所有。我的肚皮庞大、身躯沉重,四肢冒着鸡皮疙瘩,体内有无尽冷汗。
桃桃一早就带着几个客人出去了。傻子看起来心情不错,坐在竹篱笆下玩泥沙。一些散落的,还没来得及被清理掉的沙子,被傻子堆成一個个微缩版的小沙丘。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傻子在我身后。我感觉到他在看我。
但我回头的时候,他已经站起来走远了。我在屋檐底下逗金鱼。桃桃在屋檐底下放了一只玻璃金鱼缸。五条金鱼在鱼缸里没玩没了地游来游去。什么人往里面丢了饭粒和面包屑。它们没有吃。它们总在游来游去,它们的一生,它们的吃喝拉撒,都在这透明的鱼缸里,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
桃爸领了几个人进来,给他们安排了房间。
“村头那家明天嫁女儿。”桃爸说,“我这里刚好有客房。怎么样?后来睡得好吗?”
他说的是昨晚的丑事。我用木棒驱离那条侵入我房间的壁虎,它爬得极快,在墙壁上游走,毫不费劲,一度脱离我的掌控,钻入了床底下,消失不见了。有大半个小时,我都在房间里乒乒乓乓,对抗着那入侵的壁虎和内心的恐惧。后来桃爸用手轻松弄走了它。
“房间都很干净的,你放心住。”桃爸说。他叫了傻子,他们一起去收拾房间。我在村子里走,这村子依山而建,规模并不很大,但多古树古房,很有些意思。
几个拍照片的在路上走走停停。
“这里到处都系(是)虫子。”一个说。他的口音有些古怪,有点偏上海,又有点偏广东那一带,让我一时半会儿看不准他是哪里人。
“你住203,我住205,我们是隔壁。”他说。我想起来,昨天我在房间里对抗壁虎的时候,他探进头来看了一下。隔了一夜,我忘了他的脸。没想到他倒记得。
他说:“你空手来?”
他看了我,好像我手里应该提着点什么似的。那么,我手里该拿着点什么?哦,我明白了。我也该拿着个相机,像一个摄影家。
“这里真不错。”他说。他调了焦距,拍了一张。
他说:“真不错,这里。空气好,天空也好。前几年我在巴黎举办一个摄影展,有个摄影家Mark Rodin,我们在一起喝咖啡聊摄影艺术,他说起过最美的天空。就系(是)这样的天空。”
“我的名片。回聊。”他说。他给了我他的名片。小跑着跟上他那已经走远了的同伴。这时候我想起来,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过。我把名片放进口袋里。
桃桃和夜幕一道回来。
傻子从楼梯下来,他站了一会儿,呜呜叫着,把自己当成一架飞机开走了。
我们聊了几句,没有提到壁虎。我本来想说的,但却无从开口。
我能说些什么呢?告诉桃桃有一条可怕的壁虎进了我的房间?告诉她我拿着木棍满屋子追赶才将它驱逐出去?告诉她我竟然被一条壁虎吓出了一身冷汗?
我没有说。她没有问我住得好不好。——原本我以为她会问,这样我就会一股脑儿将一条壁虎进了我的屋子的事,告诉她。
或者,不说壁虎。说点别的也行啊。从沈阳溃逃回来后,我在小城没有找到工作。我一天天窝在家里,把空调打到最低,再穿上厚衣服,看古装穿越剧聊以度日。
“等我们回到小城,从家里到公司,就五六分钟的路。到那时,我们下班后,可以看电影、跑步、逛街,远比在大城市舒服多了。”在从沈阳溃逃回来前,我给桃桃开了一张美丽的空头支票。
我跟桃桃说,我先杀回小城,到那时,再不济也能混个小城优秀青年当当。我说着话,就自己先从沈阳逃回小城了。隔了半个月,桃桃也溃逃回来了。她没有投奔我,直接上了山,开起了民宿。
凭良心说,桃桃没有投奔我,实在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桃爸小有积蓄,又宠她,民宿说开就开,绝不是空头支票。不像我,被失业这头巨熊按在地上,啪啪打脸。
什么人叫了她。她就去了。我在屋子大堂一角喝茶,翻一本劣质的、薄薄的小册子。雕花窗、对联、门匾、碑刻、古树、长桅杆、石虎……小册子一页页翻过。这个弹丸小村,几百年来出了两个贡生、三个秀才。
门外夜色一点点渗透蔓延开来。几百年前,山脚下小城一片昏暗,这小村子却灯火通明。年轻人结束劳作,在灯火下夜读。晴耕雨读。或者,红袖添香夜读书。
——现在,所有的都已经远去。曲终人散。游戏终结。
桃爸从外面进来。脸很红,酒气比人先到。他坐在我对面。
我给他倒了一点茶水。
“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他说,“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他反复说。
“喝点水。”我说。他喝了茶,给自己添了。
“如果我桃桃是儿子,我就一辈子值了。”他说。
“女儿也好。”我说。但这话了无意义。
“如果小虎能有桃桃一半,不,百分之一,我就值了。”他说。他大着舌头,满嘴酒味。我想早点起身回房。
“我跟桃桃讲,桃桃,小虎再傻也是你弟弟,是我的儿子。”他说,“桃桃对弟弟没一句好话。她把他搬到后面去。小虎讲,前面空着,不让我住!桃桃讲,你猪样臭,我那里不是猪圈。我跟桃桃讲,桃桃桃桃,他从小就住那间,你赶他到后面,他睡不着觉。”
“桃桃吼我,桃桃讲,都是你惯着他。本来就笨,给你惯出懒。……”他没完没了地说着,忽然趴在桌子上大哭起来,声音很大。
杯子倾倒,茶水满桌子流淌。我说:“你醉了,你回房间休息。”我拉他,他弓着身子趴着,像一只巨大的硬邦邦的虾。他上辈子一定是一只冻虾,下辈子、下下辈子也是。
“桃桃,桃桃。”我叫桃桃。桃桃不知道在干什么,没有一点声音。两三个房门打开,有人探出头来。
我和桃桃把他送回房间。
“你爸喝多了。”我说。
“没有。”桃桃说,“他就这样,我已经习惯了。有什么爸就有什么儿,在某一些方面,他和傻子是一样的。”
她还想再说一些话。但我毫无兴趣。我一点也不关心他们家的事。她的爸爸,她的傻子弟弟,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说:“我回房间了,有事叫我。”她只好住口。
回房间。关上房门后,我看到了地板上的沙子和那条死壁虎。一条断了尾巴的、肥壮的壁虎,翻着肚白躺在地板上。这是一种警告和威胁吗?这傻子弟弟。
窗外有繁星点点,山脚下小城灯火通明。山风吹进屋子,我一点也不困。喝了太多茶水,我胃很不舒服。
楼下房间有人打呼噜。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一声。我不知道发出声音的人是谁,不知道他或她长什么样,也不知道她或他经历过什么。但我知道,此刻,他或她就躺在我的地板下面,我们隔着大约三米距离。
我迫切地想见一见他或她。在这样的夜晚,我们既非朋友,也非亲戚,却在这樣一个原本跟我们毫无关系的地方,无端端地住了一夜。
天亮了。他或她就起身,走了。走他或她的路,可能有很多好运等着。也可能,天降横祸,生死无常。当然,最有可能是他或她,把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下去,毫无改变毫无新意。
——他或她,永远也不会知道,在一个夜里,在他或她头顶上三米的地方,有一个陌生人,这么漫无目的的想过他或她的前途。
隔壁没有一丁点声音。那帮人没有回来。他们已经走了,在这个地方住了一夜,拍了一些照片,就此远去。后来他们想起来,觉得像梦一样遥远。
我把手放进口袋里。摸到了那张名片。我将它取出来,翻看了一会儿,名片上有一个中文名字、一个英文名、一个手机号、一个座机号、五个头衔——这些,对我而言,毫无意义。
我将它丢进了垃圾桶。他已经走了,自此与我两不相干。我确信。这样是安全而体面的。
这时候我听到有脚步声。有人站在了我房门外。他开始捶门,一下,一下,又一下。什么人骂了一声,又没声了。
傻子。我知道。我开了门。他闯了进来——
“我要睡这里。”他说。他坐在我的床上。他身上到处都是泥巴,好像在什么地方跌了一跤。
“是你把壁虎放进我的房间。”我说。
“我没有。”他说。
“是你。”我说,“你带来了沙子。”我示意他看垃圾桶。他的那条死壁虎,此刻就躺在那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