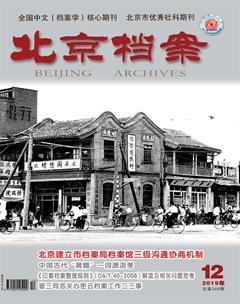新时期档案价值鉴定研究:背景、标准、主体
摘要:档案工作领域的发展变革深刻影响着档案价值鉴定工作实践,为了在新形势下做好档案价值鉴定工作,我们应当拓展档案价值鉴定的范围,从以“官方记录”为主逐渐覆盖至其他社会组织乃至个人所形成的文件,运用多元化的鉴定标准,依靠社会多方力量共同实现构建完整的“社会记忆”,以及满足日益广泛的社会利用需求的鉴定目标。
关键词:档案价值鉴定鉴定标准鉴定主体
档案价值鉴定是档案管理活动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业务环节。近年来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使得档案工作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也面临很多新的挑战和新的问题,如何在新形势下做好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亟须我们深入探讨、研究。
一、为何鉴定:变化的鉴定工作背景
进入新世纪以来,档案工作领域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发展变革,深刻影响着档案价值鉴定工作实践。
(一)档案管理价值取向的转变
档案管理的价值取向表明了档案管理活动的目标指向,即“为谁而管”。[1]当前,我国的档案管理工作正经历着从“为国家”向“为社会”的转变,档案管理的利益主体从国家扩展到以国家为主的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广大公民。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为国家”是档案管理得以安身立命的职责所在。在古代,档案属于统治者的工具,只有享有特权的人才可能利用档案,即使是到了近现代,档案利用的特权逐渐被动摇并最终成为公民的一项法定权利,但是档案管理“为国家”的价值取向却始终没有改变,档案保管机构关注的重点仍然是“官方记录”,服务对象主要还是政府机构。随着我国社会步入整体的、全面的转型时期,政府职能和角色转变对档案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社会记忆观”“大档案观”等理论的出现也使得人们对于档案和档案管理有了全新的认识,正如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所言:“20世纪末期公众对档案的认识,或至少对用纳税资金建立起来的档案馆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即档案现在是‘属于人民,为人民服务,甚至通常由人民管理……在普通公民看来,档案不仅要涉及政府的职责和保护公民的个人利益,而且更多的还应为他们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地方感和集体记忆。”[2]这就要求我们在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中不仅要重视国家权力因素,也要关注公民权利因素,从而更好地实现对“社会记忆”的重构和对社会文明的传承。
(二)档案资源范畴的拓展
在档案管理价值取向从“为国家”向“为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档案管理工作领域逐步延伸,档案资源的范畴不断拓展,一些原本游离于体制外的档案资源得到了重视并开始被纳入规范管理,民生檔案、信用档案、健康档案、家庭档案、社区档案、口述档案等更贴近社会生活的档案资源纷纷涌现。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也给档案管理工作带来了巨大冲击,新技术的应用不但催生了电子文件、社交媒体文件等新型档案资源,而且使得档案文件数量以几何级数暴增。可以说,如今档案管理工作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不再是档案资源的不足,而是如何在信息海洋中鉴别出高质量、高价值的档案信息,对其进行合理、高效的管理和开发利用,有效发挥其证据价值、信息价值乃至文化价值。
由此可见,在档案管理从“国家模式”逐渐向“社会模式”转变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选择并保存“社会记忆”,从而更好地满足日益广泛的社会利用需求成为我们重新审视档案价值鉴定的重要着眼点。
二、如何鉴定:多元化的鉴定标准
简单来说,档案价值鉴定的目标就是通过“鉴”与“毁”来实现更好的“存”,依据什么标准完成这一目标至关重要。在这里,笔者从价值作用角度把档案文件划分为两大类进行论述:一类是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在职务活动中形成的文件材料,是服务于社会运行的活动证据,我们可以称之为证据型档案文件;另一类是普通公民或者公民群体在生活、娱乐等一般社会活动中产生的文件材料,属于公民的“个人记忆”或者“集体记忆”,我们可以称之为记忆型档案文件。[3]
(一)证据型档案文件的鉴定标准
证据型档案文件的价值源自其信息内容的有用性,因此证据型档案文件的价值鉴定主要是根据其信息内容的重要性,结合考虑其形成背景及过程进行分析、判断,同时对电子文件、社交媒体文件等数字型文件还要进行技术评估。
1.内容标准,这是档案价值鉴定最常用也是最主要的评判标准。一般来说,内容反映形成者的主要职能、重要业务活动以及机构人员利益的文件材料的价值较高。多年的实践证明,运用内容标准进行鉴定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尤其对于基层文书业务人员和档案业务人员来说这些法规和业务标准是非常实用的操作指南。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难以从正面对文件材料的价值进行鉴定,可以反向从处置风险的角度进行评估,也就是考虑如果文件材料不被保存会出现哪些后果。例如,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就认为在新的数据环境下预测文件的价值具有较大难度,转而对不保存该文件所带来的风险进行鉴定。[4]
2.职能标准,这是对宏观鉴定理论的实际运用,即通过分析文件形成者的职能、业务活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和与社会的互动,决定“形成者的哪些职能和活动应该被记录(而不是哪些文件应该被保存)”“哪些文件形成者或‘职能(而不是文件本身)最为重要”,从而切实锁定那些可能最具有潜在档案价值的文件或文件系列。[5]把文件形成者的权威性、职能及业务活动的重要性等作为评判文件价值的重要因素,可以弥补内容标准的不足,尤其适合应用于电子文件的鉴定。由于宏观鉴定面对的不是单份文件,而是某种职能的文件集合,表现为一种“批处理”方式,因此,在文件管理系统设计中嵌入机构的职能分析方案,按照一定的准则将文件的鉴定工作模型化,从而可以实现对电子文件的自动鉴定。[6]
3.技术标准,这是针对电子文件、社交媒体文件等数字型文件的新的鉴定标准,包括对文件真实性、完整性及其存储环境、系统安全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因为在数字环境中原件的概念被弱化,数字设备保存的是再现数字型文件的能力,数字型文件的每一次呈现都是基于应用程序和硬件重新组合保存的数据,[7]因此需要通过对文件元数据的捕获与维护来保证其真实性。同时由于电子文件管理系统、社交媒体平台等具有高度的动态性,数字型文件所面临的安全风险会随着存储载体、管理系统的不断更新而增加,因此在数字型文件正式归档前必须进行相应的技术鉴定。
(二)记忆型档案文件的鉴定标准
常见的记忆型档案文件包括私人档案、家庭档案、不同社群形成的社區档案等。此外,在目前非常热门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各种机构、社会组织及个人用户形成的非职务性社交媒体信息也属于此范畴。笔者认为,由于记忆型档案文件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因此记忆型档案文件的价值鉴定应当是在尊重个性的基础上依据社会总体的价值导向建立普适性的标准。[8]其中,尤其要关注文件当中隐含的社会关系因素和情感因素。
1.关系标准。记忆型档案文件相对来说系统性不强,内容比较琐碎和私密,同时又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参与性,因此,其价值鉴定不能只着眼于文件信息内容本身,更要着重考虑当中所反映的社会关系,这在社交媒体文件的鉴定中尤其突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用户之间以信息内容和人际关系为基础展开各种互动,形成各种关系网络,因此社交媒体文件的价值判断要通过文件信息内容本身、与其他文件的关系以及文件生成者之间的关系来进行具体分析。例如,社交媒体平台上热门话题的互动热度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着社会关注度,互动热度越高,社会关注度就越高,其重要程度也越高,作为“社会记忆”予以保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也就越高。[9]
2.情感标准。与证据型档案文件的形成具有很强的目的性不同,记忆型档案文件主要并不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产生的,当中寄托着更多的人的情感,这在私人档案、家庭档案中尤其突出,因此其价值鉴定应该充分尊重其背后隐含的情感价值。例如,2004年6月在广东诞生的第一家“私人档案馆”——屈干臣档案馆收藏有各类档案资料2万多件,除了少数珍品,更多的是日常生活当中再平常不过的个人物件,例如证件、证书、奖章、手稿、书画、照片、收藏品等,这些档案资料既是屈干臣本人人生经历的见证,满载着过往生活的记忆,也是一个时期社会变迁的缩影,能够从微观角度反映出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
三、由谁鉴定:多层级的鉴定主体体系
目前,在实际工作中档案价值鉴定主体主要包括文件形成机构的文书业务人员、档案室业务人员和档案馆业务人员,然而,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社会发展趋势,仅仅依靠上述人员难以达成既要构建完整的“社会记忆”又要满足广泛的社会利用需求的鉴定目标。笔者认为,今后档案价值鉴定工作需要社会多方共同参与,协作完成,考虑到当前我国档案管理层级结构,档案价值鉴定主体体系可以由三个层级组成:第一层级是文件形成机构的文书业务人员、档案室业务人员及技术人员;第二层级是档案馆业务人员;第三层级是以档案专家为主的各领域专家顾问,此外,还可以引入社会力量作为补充,比如商业机构、学术机构、社会团体、网络平台管理者、不同的社会群体以及普通的社会公众等。
1.文件形成机构的文书业务人员、档案室业务人员及技术人员是档案价值鉴定的主要力量。其中,文书业务人员、档案室业务人员一方面负责宏观层面上的机构职能与业务流程分析,区分重要职能活动、一般业务活动所产生文件材料的不同价值,另一方面完成微观层面上的文件价值判定,主要考虑文件材料对于本机构的现行价值、机构“记忆”留存等因素完成鉴定工作;技术人员主要负责数字型文件的技术鉴定,还负责文件管理系统的维护以及模块功能的提升和开发,以更好地实现数字型文件的自动鉴定。
2.档案馆业务人员除了按照规定定期审查馆藏档案,根据社会发展状况适当调整档案的保管期限,还应当介入档案文件的前期鉴定,指导文件形成机构制定文件鉴定方案,根据机构的不同特点划定不同的归档范围,而不是被动地接收文件形成机构移交的档案文件。
3.以档案专家为主的各领域专家顾问基于社会、历史、文明的考量,对档案文件的社会价值和未来潜在价值进行分析、判定,在宏观意义上将档案文件的价值鉴定扩展到社会价值的考虑、“社会记忆”的留存以及潜在的历史、文化价值的预见性上,[10]避免仅从文件形成者本身及其业务活动本体出发鉴定的片面性。
4.社会力量可以作为档案价值鉴定主体的补充,通过吸纳不同社会群体的意见可以更好地了解社会的利用需求,挖掘潜在利用群体。例如,在荷兰的PIVOT(Proj? ect to Implement the New Transfer Period)项目的实施流程中,由相关政府机构的专家、相关机构的文件实践管理者和国家档案专家共同完成“三方咨询”方案之后会进行民众的网上评价,民众的意见和建议会作为对“三方咨询”方案的有效补充。[11]值得注意的是,在记忆型档案文件的价值鉴定中,社会力量应当成为鉴定的主要力量。由于记忆型档案文件的多样性、海量化,档案保管机构无法承担起以传统模式完成数以千万计的新形式、新内容的文件材料的鉴定任务,因此我们应当把记忆型档案文件的鉴定交给形成者,由他们决定哪些文件材料需要长久保存,档案保管机构只需在大方向上加以引导,同时对于社会价值较高的档案文件可以以适当的方式征集进馆,成为国家档案资源体系的有益补充。
综上所述,随着档案管理工作逐步向社会公共事务演变,尤其是社会人权、民主、公平、正义等理念在档案管理工作中的渗透,档案价值鉴定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和挑战,为此,我们应当适应社会的发展引入新的鉴定标准和鉴定主体,构建多元化的鉴定标准体系和多层级的鉴定主体体系,以更好地实现构建完整的“社会记忆”以及满足日益广泛的社会利用需求的鉴定目标。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张莉.档案管理:价值转向与范式转换[J].档案学研究,2008(4):11-14.
[2][加]特里·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C]//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7:152.
[3][8][9]谭彩敏.社交媒体文件归档管理研究:鉴定标准与管理模式[J].浙江档案,2018(3):10-12.
[4]宋魏巍.大数据环境下电子文件鉴定研究[J].北京档案,2015(12):16-19.
[5][加]特里·库克,李音(译).宏观鉴定与职能分析[J].中国档案,2012(1):51-53.
[6]俞玛丽.用宏观鉴定战略指导电子档案鉴定实践[J].档案时空,2015(8):31-33.
[7]周文泓,加小双.数字时代的国外电子文件鉴定观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档案学研究,2015(12):19-21.
[10][11]马帅章.宏观鉴定下档案鉴定主体的组织与职能探析析——以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例[J].档案管理,2012(6):18-20.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档案馆